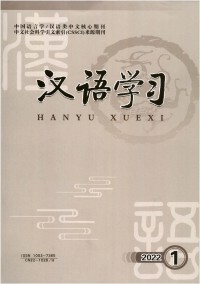語義學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語義學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yōu)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博弈論語義學邏輯哲學思想論文
摘要:賈可·辛提卡是當代著名的邏輯學家,他創(chuàng)建了博弈理論語義學,用博弈論的方法來刻畫命題理解,從而判定命題的真值。博弈理論語義學對命題的真值判斷標準是符合論的,這與維特根斯坦前期的“圖象論”如出一轍,而這種符合關系的建立則直接源自于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言游戲說”,通過語義博弈建構圖象與世界圖示之間的關系。可以說,維特根斯坦哲學是辛提卡博弈論語義學的直接思想來源。
關鍵詞:博弈論;語義學;邏輯哲學
賈可·辛提卡是當代著名的邏輯學家,他將博弈論與語義學直接結合起來,創(chuàng)建了博弈論語義學。辛提卡用博弈論的方法來處理命題,就是要確定命題的值,即命題的真或假。同經典邏輯一致,辛提卡預設了命題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給出一個定義域D,任何名稱都可以在這個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論語義學的核心是將量詞短語看成專名,將句子看成語句函項,然后在給定的定義域D中選擇相應的個體將句子中的量詞短語替換,從而達到消除量詞,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選擇了博弈論,他將人們對句子的理解過程比喻為一個兩人博弈,兩個參與人分別為“我”和“自然”,每個回合必定要分出勝負,不容平局,那么對于一個句子S,根據規(guī)則,博弈雙方輪流將S約化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約化的句子不再包含變量和連接詞,即原子句,此時雙方就可一決輸贏。如果這個原子句為真,則我取勝,自然失敗;如果這個原子句為假,則自然取勝,我失敗。運用博弈論語義學,我們能夠從大量的語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簡化的語句,從而能夠輕松地判定這些語言信息的真假。理解這一理論的關鍵是理解定義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可以說是維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學的綜合:“語言博弈”概念源于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語言游戲說,而它的理論核心則是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圖象論。
一“圖象論”與命題真值
維特根斯坦是學界倍受關注的大師,其前后期思想的迥異恰當地詮釋了他的哲學主題:“哲學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活動。”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論語義學所強調的也是動態(tài)的理解命題,這與維特根斯坦哲學在本質上殊途同歸。
維特根斯坦哲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圖象論”。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和后期哲學的目的都在于通過研究語言的結構和界限來理解思想的結構和界限。維特根斯坦工作的基點,就是回到邏輯的出發(fā)點,即考慮命題的性質。這樣,真的界限就構成了語言的界限,維特根斯坦所考慮的就是關于事實的話語。“人給自己造出事實的圖象”②。維特根斯坦指出:命題是實在的圖象,“圖象是實在的一幅模型”③。“圖象是一種事實”④。“圖象所表現者即是其意義”⑤。“圖象的真假在于其意義與實在的符合與否”⑥。維特根斯坦認為,圖象與它所圖示的事實之間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這種關系“由圖象元素與物項的配合而成”⑦,這種關系本身也是一種圖象;二是“凡圖象,不論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實在———對或錯———所必須與實在共有的東西,即是邏輯型式,亦即實在的型式。”⑧所以,“每個圖象亦是一邏輯圖象”⑨。“對象是簡單的”⑩。“對象構成世界的本體。因此不能是復合的。”
產品語義學視野下的現代藝術論文
一、產品語義學研究與現代藝術設計教育
產品語義學(ProductSemantics),是語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對象是人類設計產品和使用產品過程中出現的形式結構,以及形式符號所包涵的意義。現代產品語義學研究在工業(yè)設計領域里常表現為設計作品功能與形式表達的方法。“在不加以絕對化的情況下,語義學態(tài)度及其語言分析的具體方法對于理解作品具有重要意義。”產品語義學是藝術設計領域中人與人之間視覺傳達和意義表述的研究的重要途徑,也是現代藝術設計專業(yè)教育中常常使用的手法。產品語義學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產品設計形式在傳達過程中的規(guī)律性、內在解釋、不同形式表號在語義方面的構成關系。20世紀以來,在結構主義理論影響下,產品語義學研究成為現代設計理念傾向于結構與功能體系的理論基礎。與此同時,現代藝術設計也發(fā)生了相應的改變。以德國藝術設計教育的核心基地——包豪斯學院為中心,現代主義設計理念在國際設計領域中嶄露頭角。隨著國際主義的泛濫,以標榜“形式追隨功能”的現代產品設計和建筑設計真正成為了藝術設計領域內的主導。通過產品語義學研究發(fā)現,設計是一個完整的“表達—傳遞—接受”的體系,設計師的語言或詞義往往借助于符號或藝術符號傳達給受眾,而受眾總是間接地領會符號的內涵,二者之間唯一的媒介就是“功能”。因此,結構主義產品語義學在包豪斯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包豪斯的創(chuàng)建者格羅佩斯曾說:“包豪斯深信,在家居用品以及家具之間,一定有著理性的聯(lián)系,因此,我們試圖通過在形式、技術以及經濟領域里進行系統(tǒng)化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從物品的自然功能與限制因素出發(fā),創(chuàng)造出它們的形式。”包豪斯藝術設計教育體系建立在傳達產品語義學基礎之上,形式符號的研究基于培養(yǎng)學生理解功能意義的方面。由此可見,盡管當時的語義學研究僅僅涉及美學領域,但是以包豪斯為代表的現代藝術設計教育機構已經把設計視作一種語義,甚至是生活語言,其表達的主旨內容就是對功能的滿足。因此,產品產品語義學是專門研究產品設計語言意義的學問。產品設計理論及其產品語義學研究架構始于戰(zhàn)后對于包豪斯藝術設計教育體系的延續(xù),在1953年德國烏爾姆造型學院出現的“符號運用研究”成為產品語義學的發(fā)端。烏爾姆造型學院的教育體系完全圍繞產品設計在工業(yè)社會中的語義傳達來進行,形成風靡世界的現性設計和功能設計教育觀。在強調功能與應用為理念的教育體系中,科學與工程學成為設計學科的重心。譬如,戰(zhàn)后德國布勞恩公司的產品設計便是學院師生共同設計實踐的成果。
二、產品語義學對我國現代藝術設計教育的意義
就當前的藝術設計教育來說,我國高等藝術院校所開設的藝術設計專業(yè)均采用基礎原理與技能、設計理論知識和設計實踐三個部分構建出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并以繪畫基礎課程群、設計專業(yè)基礎課程群,以及設計實踐環(huán)節(jié)課程群組成教學體系。但是,這種教學體系在教學過程中往往缺少文化內涵和現象分析的內容,使得學生一知半解,對很多內容的模糊和認識的不深刻。產品語義學研究的方法在這個方面可以有效地增強某些基礎課或專業(yè)課程內容的人文性和知識性,為推動設計文化顯露本土民族性的教育策略中起到推波助瀾的效果;與此同時,產品語義學在傳達產品的形式語義和設計符號的內容等方面對藝術設計教育教學體系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總而言之,產品語義學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式對我國藝術設計教育體系構建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說,它為藝術設計教育本身將帶來新的面貌,藝術教育就是產品語義學的內容,教育詞匯、篇章構成、制度銘文等都是產品語義學分析的對象。而藝術設計專業(yè)中所設計的造型語言和形態(tài)符號也是產品語義學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在當今高科技迅猛發(fā)展的信息社會里,譬如新媒體藝術、電子藝術、虛擬空間、數碼設計等詞義和設計元素的出現,容易為藝術設計教育者帶來新的思考。因此,如何正確理解這些新的詞義和內容以及辨析,產品語義學可以為現代藝術設計教育帶來全新的意義。
作者:李華陳小宇單位:重慶三峽學院美術學院
哥白尼轉折
1994年,布蘭頓發(fā)表了正文厚達741頁的代表作《清晰闡釋》(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貝馬斯發(fā)表長篇評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羅伯特·布蘭頓的語用學語言哲學”[1],高度評價了布蘭頓的貢獻,稱這部著作為“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如今,布蘭頓關于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2]在人才濟濟的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這位美髯公與麥克道爾(JohnMcDowell)一道堪稱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樣于1994年出版的《心靈與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譽為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羅伯特·布蘭頓(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對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蘭頓一直任教于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xié)會東部分會執(zhí)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杰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范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里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后發(fā)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于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于兩個主要思想:(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guī)范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歷史發(fā)展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fā)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在廣泛接受的自然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后,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內容過于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fā)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fā),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yè),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性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應用,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于,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方法、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影響。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回,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歷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復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于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表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yōu)先性,那么,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lián)系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tài)。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tǒng)稱為“IHFPR傳統(tǒng)”(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自然語言邏輯學論文
1邏輯學中的“意義”概念
1.1“意義”與內涵以模型理論(model-theory)為基礎的邏輯語義學試圖用集合、函項這類純集合論的概念去解釋意義。由此,邏輯上所假定的語言表達式的內涵是否可以和意義等同起來,這一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邏輯語義學的理論基礎是否牢靠。具體講,語言表達式的意義把它們同世界或世界中的實體相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有時具有復雜的形式。例如,一個謂詞和世界中能夠被它稱謂的實體的集合相聯(lián)系。如果要在邏輯語義學中避免假定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實體,方法之一就是假設“如果一個人是講表達式的外延,那么就可以避免講表達式的意義”(Frege1980:134)。然而這樣做就意味著必須把具有相同外延的非同義表達式(non-synonymousexpression)如“現任美國總統(tǒng)”和“奧巴馬”看作是相同的,這就相當于把表達式的內涵和意義等同起來。事實上,了解一個表達式的外延并不必然地包含著了解它的內涵,因為非同義表達式可能具有相同的外延。
反之,如果一個人知道一個表達式的內涵,也并不意謂著他一定知道這個表達式的外延,例如,我們完全了解表達式“是聰明的”的意義,可是并不確切知道誰是聰明的,誰是不聰明的。換言之,了解一個表達式的外延必須知道兩點:表達式的內涵和現實世界中的事實。這可以說是用內涵規(guī)定外延的嘗試。用外延來解釋內涵的概念可以把內涵看作一個“外延決定原則”(extension-determiningprinciple)(Allwood1977:183)。這個原則是一個考察可能世界并找出一個表達式外延的規(guī)則。然而,把內涵等同于從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項會產生很多困難。例如,模型論語義學(model-theoreticalsemantics)一般不會碰到這樣的困難:假定有某些邏輯上可能的世界,在那里司各特(W.Scott)沒有寫《威弗利》,那么作為兩個名詞短語‘司各特’和‘《威弗利》的作者’的內涵的函項由于并不是對所有主目都有相同的值,因而彼此不同。然而,假如我們換一個弗雷格(1980:67)的例子:數學表達式“3+1”和“2+2”雖有相同的外延(“Bedeutung”)即“4”這個數,但有不同的內涵(Sinn)。隱藏在這背后意思是,“3+1”和“2+2”表現了獲得相同結果的不同方式或程序。可是,如果像算術中對一個真值為真的語句所通常認為的,“2+2=3+1”是一個邏輯真理,那么“2+2”和“3+1”的值在所有邏輯上可能的世界里都是相同的“4”這個數。換句話說,表達式“3+1”和“2+2”相當于從可能世界到數的相同的函項,因此必然具有相同的內涵。概言之,如果我們把內涵理解為從可能世界到實體的函項,那么邏輯上相等的表達式就表現為具有相同的內涵。這一結論顯然就不再支持弗雷格內涵是獲得外延的途徑的觀點。學術界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提出很多方法,比如,Car-nap(1947)認為,語言上的同義(linguisticsynonymy)不應該定義為模型論意義上的內涵同一,而是應該包括他稱之為內涵同構(intentionalisomorphism)的某種較強的東西。如果某種“組合表達式”(constituentexpressions)具有相同內涵,并且它們也同樣是由具有相同內涵的成分構成的,那么由這種組合表達式構成的語言表達式就具有相同的內涵。可以看出,這一觀點接近于弗雷格用Sinn所表示的意思。
1.2“意義”與真值條件在語言學中,把意義轉化為“真值條件”遭到很多學者的反對。很多從事語言哲學和邏輯學研究的人對“語句S是真的,當且僅當……”這一觀點非常熟悉,然而,很多語言學家一聽到“‘Snowiswhite.’當且僅當‘雪是白的’……”,就立即表示反對并指出,“真同語言學研究毫無關系”,并且,“說明哪個語句是真的,哪個語句是假的,不是語言學家的任務”。這種反對事實上混淆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一個語句的真值和一個語句的真值條件。說明一種語言中哪些語句實際上是真的確實不是語言學研究的任務;然而說明語句為真的條件,即這個語句在何種條件下是真的就須要考察語言的意義問題。如上文所述,假設我們把一個語句的內涵看作一種原則,依據這種原則,我們可以在每個可能世界中賦予這個語句以真值,并且希望我們的理論具有某種“心理實在性”,即語言表達式所描寫的成分在某些方面與出現在語言使用者的心靈中的東西相對應。
如果事實如此,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在賦值于一個語句以作為它的解釋,以及在了解一個陳述(statement)的實際表述時我們所做的,這二者之間是否具有任何相互關系。以語言表達式具有真值條件為基礎,我們可以期望當聽到一個陳述句時,就可以觀察這個世界并對在這個世界中這個語句是真的還是假的進行考察。我們甚至還須要想象一下,當這個語句是真的時候這個世界應該是什么樣子;并且,如果我們認為說話人是值得信賴的,我們可以相應地改變我們所想象的世界的觀念。這樣,似乎在真值條件語義學(truthconditionalsemantics)中關于語句的解釋和語句的了解過程之間并不是十分符合的。雖然如此,邏輯學家對這一點還是做出了相應的研究。其中,這兩個觀點是值得借鑒的:“把可能的語言或語法作為抽象的語義系統(tǒng)來描寫,因而符號是與世界的各個方面相聯(lián)系的”,以及“關于心理的和社會的事實的描寫,因而這類抽象系統(tǒng)中的一個特殊系統(tǒng)是由個人或人群使用的系統(tǒng)”邏輯語義學只討論第一個問題,而關于語言表達式的運用問題則與它無關。按照Lewis的觀點,“混淆”這兩個問題“只能引起混亂”。當然也有人反對這一觀點并認為,相關研究只有從語言符號使用的研究中進行抽象才有可能實現,因此應該把語言作為聯(lián)系符號和世界各個方面的一種系統(tǒng)來研究。事實上,邏輯語義學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明確說明應該怎樣對一個簡單表達式的意義進行解釋;相關研究仍然沿襲了傳統(tǒng)邏輯學中的觀點,這就使得意義看似很抽象。然而邏輯語義學對傳統(tǒng)邏輯的發(fā)展就在于,它對語義問題研究的推進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從簡單表達式的解釋獲得復雜表達式的解釋的方法。這可以說是形式對語言意義研究的最重要貢獻。正因如此,“我們不應該希望邏輯語義學確切地告訴我們在什么情況下‘下雨了’這樣的語句是真的;但是它能告訴我們在這個語句和它的否定‘沒下雨’為真的各自情況下,它們之間的關系”(Allwood1977:188)。
2邏輯與自然語言分析
功能翻譯理論
摘要:中國傳統(tǒng)翻譯理論只有宏觀的論述,缺乏方法論,操作性不強。本文簡述了功能翻譯理論,詳細地探討了該理論的理論基礎,并用關聯(lián)理論予以論證,豐富了它的內容。
關鍵詞:功能翻譯理論;基礎理論;闡釋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theoryconsistsonlyoftranslationprincipleswithoutconcretemethodologyanditcannotbeappliedtopracticaltranslating.Thispapergivesabriefaccounttofunctionaltranslationtheory,probesintoitstheoreticalbasisandmakesconvincingexpositionofitbyusingrelevancetheorysothatitenrichesitscontent.
Keywords:functionaltranslationtheory;basictheory;exposition
功能翻譯理論強調,翻譯是一種特殊的交際形式,涉及三種文本:原語文本、譯者的圖式文本和譯語文本。對于原語文本,最重要的是抓住作者的修辭功能正確理解原語的修辭功能,是產生理想的圖式文本的關鍵。而正確把握原文的認知圖式又是正確理解原文修辭功能的基礎。理想的圖式文本來自原文的認知圖式,來自對原文作者的修辭意圖的準確把握。在這個圖式文本的基礎上,產生怎樣的譯語文本,除了修辭功能等值之外,還應該考慮翻譯的目的和讀者對象。
一、功能翻譯理論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