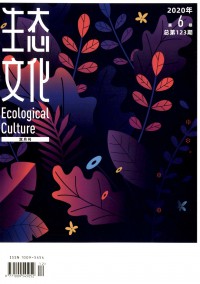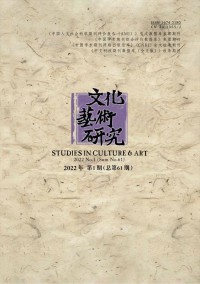文化文學(xué)期刊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文化文學(xué)期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xué)習(xí)和借鑒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yōu)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英美文學(xué)在中國的發(fā)展概況
主要外國文學(xué)期刊及其發(fā)展歷史
從新時期的歷史背景我們可以看到,一種環(huán)境下文化的發(fā)展也必然會經(jīng)歷階段性的變化,而英美文學(xué)在我國的介紹和傳播離不開主流刊物的推動。建國以來,我國先后成立過許多專業(yè)出版社來出版發(fā)行英美文學(xué)作品,發(fā)展到今天,最具代表性的是《譯林》、《外國文藝》、《世界文學(xué)》等。當(dāng)我們研究英美文學(xué)在我國的發(fā)展時,可以通過上述幾個核心期刊對于英美文學(xué)的譯介,在刊登內(nèi)容、方式、語言等的不同,來體會我國在不同時期對英美文化的態(tài)度。《譯林》創(chuàng)刊于1979年11月,從江蘇人民出版社的《譯林》編輯部發(fā)展到譯林出版社,從一個地方性刊物發(fā)展到全國著名的期刊,其發(fā)展歷史可以見證中國對于英美文學(xué)譯介的發(fā)展。《譯林》在創(chuàng)刊伊始,便將自身定位為“以譯介外國當(dāng)今有影響的新作為重點”,因此其內(nèi)容的選材聚焦在當(dāng)代西方通俗文學(xué)作品。通過對這些文學(xué)作品的譯介,使得《譯林》成為人們了解西方當(dāng)代社會和生活的一個窗口,為人們提供了一定的資料和信息。然而,其刊登的內(nèi)容也給它帶來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如創(chuàng)刊初期的《尼羅河慘案》在讀者中引起波動的同時也使其編輯部卷入一場不大不小的風(fēng)波,當(dāng)時正值“”剛剛結(jié)束、人們思想開始解錮的時期,這樣一部小說的刊登引起了社會的爭論,而爭論的結(jié)果是使人們思想豐富的同時,該本期刊也得到認同。后隨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物質(zhì)、思想的發(fā)展,《譯林》刊登的內(nèi)容也有相應(yīng)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無不彰顯著特定時期的主流思想和文化的影響。《世界文學(xué)》最初創(chuàng)辦于1953年,刊名為《譯文》以紀(jì)念魯迅先生;1959年改名為《世界文學(xué)》,主要刊登中國學(xué)者的評論;十年動亂期間該期刊一度停辦;1977年重新恢復(fù)出版,次年正式復(fù)刊。該期刊以發(fā)展我國文化事業(yè)和精神文明建設(shè)為其辦刊宗旨;就閱讀對象而言,其為文化創(chuàng)作者、理論界和高校師生提供了豐富的外國文學(xué)名著,體現(xiàn)著其精英路線和名家名篇的發(fā)展之路。《外國文藝》創(chuàng)辦于1979年,以“介紹當(dāng)代外國文學(xué)作品”作為其創(chuàng)刊宗旨,系統(tǒng)且重點地介紹了外國著名作家、藝術(shù)家及評論家的作品和理論,為了解國外的文化思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資料。就內(nèi)容而言,其選篇相對較短,更多的關(guān)注作者的文學(xué)成就等,并且該刊每年的第一期用于介紹上年度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從而使讀者能夠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學(xué)的發(fā)展動態(tài)。上述三大外國文學(xué)期刊在創(chuàng)刊宗旨和刊登內(nèi)容方面有著區(qū)別,但是三者在中國介紹西方文化和英美文學(xué)的譯介方面都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三者的發(fā)展歷史也向我們講述著中國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和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與融合歷史。
從外國文學(xué)期刊的發(fā)展探視其對英美文學(xué)的譯介
《世界文學(xué)》、《外國文藝》、《譯林》在創(chuàng)刊之初的定位和宗旨的區(qū)別使其在刊登內(nèi)容的選擇上各有側(cè)重,當(dāng)我們研究英美文學(xué)的譯介時,便可以從不同時期各刊物對于英美文學(xué)譯介的側(cè)重點和內(nèi)容的選擇為切入點深入研究。《世界文學(xué)》其刊名中“世界”兩字便將關(guān)注的范圍大為擴展,說明了它所關(guān)注的是世界著名作家及作品。在創(chuàng)刊初期,由文化界名人擔(dān)任歷屆主編,保證了文章選取和翻譯的質(zhì)量。同時,隨著國內(nèi)思想的變化,雜志所選取的文章也會有內(nèi)容和國別的變化和差異。這種變化和差異讓我們看到當(dāng)時中國的主流思想方向,也讓我們看到當(dāng)時的人們對于英美文學(xué)的態(tài)度及對其文化的接受和理解程度。《譯林》作為人們了解世界的窗口,其所刊登的是最近國外發(fā)表的作品,更直接地反映國外的現(xiàn)實生活,其所關(guān)注的重點是經(jīng)濟發(fā)展前沿的國家和地區(qū)。自創(chuàng)刊以來,其發(fā)表的長篇小說中,英國和美國的作品占有極大的比例。而對于這些作品的刊載,隨時間的變化有所不同,或以一種評論形式出現(xiàn),或以完整的翻譯,或者夾譯夾評,刊登的形式和內(nèi)容是對于英美文化譯介的體現(xiàn)。《外國文藝》以文學(xué)為主,但是也兼具了美術(shù)和文學(xué)理論的內(nèi)容。其刊登內(nèi)容除國外的詩歌、小說、評論等文學(xué)作品外,還包括美術(shù)作品和美術(shù)家的介紹。通過這樣一種多元的形式,使人們更好地了解國外的文化。在這些內(nèi)容中,如將英美文化的內(nèi)容按照時間順序羅列歸類,會看到不同時期對于不同的文化內(nèi)容、思想流派和藝術(shù)流派的介紹和評論。透過這些文字的東西,我們收獲的是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學(xué)者們對于外國文化的引介和思想訴求,同時也體現(xiàn)著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想。歷史是一個縱向的脈絡(luò),我們對英美文學(xué)譯介的研究需要通過縱向的時間梳理來獲得其發(fā)展的路徑,也需要橫向的比較總結(jié)其不同特點。新時期主要的外國文學(xué)期刊的發(fā)展歷史,為我們呈現(xiàn)出英美文學(xué)在我國的譯介發(fā)展,同時,不同期刊內(nèi)容的對比也會讓我們看到在同一時期不同視角下的英美文化在我國的發(fā)展。沿著這樣一個方向去探尋和研究,我們能夠更好地去樹立中心,探尋英美文學(xué)在我國的譯介發(fā)展。
外國文學(xué)期刊在英美文學(xué)譯介方面的發(fā)展方向
發(fā)展是一個前后相繼的過程。我們探尋外國文學(xué)期刊對英美文學(xué)的譯介研究的意義莫過于為英美文學(xué)在我國的發(fā)展尋得一定的方向。通過歷史的脈絡(luò)分析和世界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來推動英美文學(xué)的譯介發(fā)展:首先,外國文學(xué)期刊應(yīng)適應(yīng)新時期的要求不斷做出調(diào)整和變化。新時期,信息和科技的發(fā)展給傳統(tǒng)出版行業(yè)帶來了極大的挑戰(zhàn),信息的不斷豐富和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發(fā)展使得紙質(zhì)媒體受到?jīng)_擊,在這種情況下,外國文學(xué)期刊的發(fā)展方向和前景是不得不考慮的。競爭中求生存,形式變化的同時也需要內(nèi)容的極大豐富和調(diào)整,但是,內(nèi)容的變化還應(yīng)該掌握當(dāng)下的思想文化發(fā)展方向,為社會思想的發(fā)展做出正確的引導(dǎo)。其次,在出版內(nèi)容的選擇上,應(yīng)該秉承其創(chuàng)刊宗旨,選擇優(yōu)秀的作品。主流刊物對于社會思想和文化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想開放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各種思想不斷涌入,國外的文學(xué)作品不斷豐富,文化內(nèi)容不斷多樣化,而這不斷擴容的文化背后隱藏著一些問題或者危機。為保證刊物的質(zhì)量和刊登內(nèi)容的影響力,在選擇之初便應(yīng)做好文學(xué)作品的嚴(yán)格把關(guān)審查。再次,注重中西思想的融合。英美文學(xué)的譯介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的移植,這移植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沖突和矛盾,但是移植的最終目的是實現(xiàn)一種融合,即中西文化的完美融合。這一目的的實現(xiàn)對于推動我國文化的繁榮和精神文明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在譯介英美文化時,應(yīng)充分考慮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市場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背景下人們思想和文化的發(fā)展變化,以一種更為有效的方式來推動英美文化與國內(nèi)文化的融合。最后,擴大刊物所傳達的信息量。新時期信息化是其重要標(biāo)志之一,這必然帶來信息的極大豐富,而這對信息傳遞的媒介而言則會帶來一定的壓力。我們對于英美文學(xué)的譯介在正確傳達其所體現(xiàn)的文學(xué)氣息和文學(xué)背后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的同時,也應(yīng)注重相關(guān)信息的傳達。這種信息或體現(xiàn)于文學(xué)作品中,或體現(xiàn)于某種時評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學(xué)作品,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的譯介工作者和文學(xué)期刊的關(guān)注和重視。
當(dāng)代文學(xué)發(fā)展視覺化趨勢淺議
內(nèi)容摘要:科學(xué)技術(shù)迅速發(fā)展的過程中,視覺文化因為自身具有的迅捷、便利等特點不僅成為了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主流,而且推動了各個領(lǐng)域的改變和發(fā)展。創(chuàng)作語境的變化以及文學(xué)視覺審美形體的變化,擴大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傳播影響的范圍。所以,當(dāng)代文學(xué)在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應(yīng)該通過建立全新視覺文化評價范式和話語體系的方式,提高文學(xué)視覺素養(yǎng),才能在滿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視覺化發(fā)展趨勢的基礎(chǔ)上,為我國文學(xué)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堅實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視覺文化時代;文學(xué);分析
科學(xué)技術(shù)迅速發(fā)展的過程中,視覺文化因為自身具有的迅捷、便利等特點不僅成為了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主流,而且推動了各個領(lǐng)域的改變和發(fā)展。創(chuàng)作語境的變化以及文學(xué)視覺審美形體的變化,擴大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傳播影響的范圍。所以,當(dāng)代文學(xué)在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應(yīng)該通過建立全新視覺文化評價范式和話語體系的方式,提高文學(xué)視覺素養(yǎng),才能在滿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視覺化發(fā)展趨勢的基礎(chǔ)上,為我國文學(xué)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堅實基礎(chǔ)。
一.當(dāng)代文學(xué)發(fā)展視覺化的特征分析
1.文學(xué)視覺化傳播形式
(1)文學(xué)期刊具有的圖像化傾向特點。經(jīng)過深入的分析發(fā)現(xiàn),文學(xué)期刊的圖像化特點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外在包裝越來越注重視覺元素,裝幀也向著豪華精美的方向發(fā)展。比如,《收獲》《當(dāng)代》《上海文學(xué)》《長城》《人民文學(xué)》《山花》等純文學(xué)期刊已經(jīng)認識到了封面裝飾營銷的重要性,徹底改變了傳統(tǒng)的以黑、灰等暗色調(diào)為主的裝幀形式,采用了明亮度較高且新穎搶眼的亮色,吸引讀者的眼球,從這些封面照片不僅詳細的記錄了當(dāng)下真實、生動的社會生活,而且隨著文學(xué)期刊中圖片數(shù)量的不斷增加,使得文學(xué)期刊與以往相比更具內(nèi)涵。其次,內(nèi)在欄目設(shè)置過程中視聽藝術(shù)類欄目比重的大幅度增加。經(jīng)過深入的調(diào)查分析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的文學(xué)期刊主要是以文字性或以文字為主的欄目,而經(jīng)過改版后的文學(xué)期刊則采取了將文字與影視、攝影、繪畫、雕塑、廣告等視覺媒介藝術(shù)緊密的融合在一起的方式,增強了文學(xué)期刊的視覺藝術(shù)效果,反映出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向圖像時代靠攏的發(fā)展趨勢。
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研究論文
一、甘肅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呈現(xiàn)載體簡介
(一)網(wǎng)站甘肅境內(nèi)有較大影響的文學(xué)網(wǎng)站,主要是西北文學(xué)網(wǎng)(甘肅文學(xué)網(wǎng)),此外還有有些綜合網(wǎng)站的文學(xué)版塊,如中國甘肅網(wǎng)•原創(chuàng)文學(xué)。西北文學(xué)網(wǎng):由甘肅省文學(xué)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主辦、《甘肅文藝》刊物對其鼎立支持。網(wǎng)站分新聞中心、甘肅文藝、作家博客、文學(xué)社團、原創(chuàng)連載、作家檔案、作家動態(tài)、期刊雜志、原創(chuàng)短文、圖書連載等版塊。中國甘肅網(wǎng)•原創(chuàng)文學(xué):中國甘肅網(wǎng)是甘肅省委、省政府最大的綜合性新聞門戶網(wǎng)站,其下轄的“文化旅游頻道”就包括“甘肅原創(chuàng)文學(xué)”版塊,有一些平實溫婉、如家常語而不失含蓄蘊藉的散文、小說作品。
(二)博客、微博博客承載了甘肅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很大一部分作品,辛勤耕耘在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天地中的幾乎所有作家和們都有著不止一個博客。幾乎所有通過紙質(zhì)媒體成名的傳統(tǒng)文學(xué)作家也紛紛開博。這些博客不只是普通的網(wǎng)絡(luò)日志,更是網(wǎng)絡(luò)出版與發(fā)表文章的專有名詞,代表了急速成長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活動。甘肅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一個相當(dāng)重要的載體,就是作家、博客組成的一個龐大的、彼此交流融合、互相滲透的大圈子。除了作家、們個人的博客,飛天博客作為甘肅人的博客家園,吸引、匯聚了一大批熱心文學(xué)、文化的甘肅網(wǎng)絡(luò)們,其中也有一些不錯的作品。微博是繼博客之后的又一個信息交流平臺,信息量更大,傳播速度更快,發(fā)感慨、曬心情,更短小精悍、內(nèi)容更簡潔,不失為網(wǎng)絡(luò)寫作、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一大便利交流平臺。作家、們的微博,也是展示、推介自己作品的很好的平臺。
二、甘肅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部分作家作品分析
棲息于紙媒與網(wǎng)絡(luò)的兩棲作家主要指,在從事網(wǎng)絡(luò)寫作之前,已經(jīng)在紙媒上發(fā)表過很多東西,有的還擁有一定的知名度。他們走向網(wǎng)絡(luò)的途徑有兩條,一是把已經(jīng)在紙媒上發(fā)表過的東西貼到網(wǎng)上去,擴大影響力;二是把新寫的東西在網(wǎng)上先發(fā)表出來,同時或稍后再在紙媒上出現(xiàn)。馬步升、人鄰、楊永康、習(xí)習(xí)、楊獻平、韓松落、沙戈、王若冰、雪瀟、爾雅等人即此類作者,“甘肅小說八駿”“甘肅詩歌八駿”“甘肅兒童文學(xué)八駿”也大多位列其中,他們的創(chuàng)作成就有目共睹,已經(jīng)取得了相當(dāng)?shù)奈膶W(xué)聲名與地位,他們是近年來“全面展示我省文學(xué)原創(chuàng)陣容和實力的一個重要品牌,在全國文學(xué)版圖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們的主要創(chuàng)作成就在傳統(tǒng)文學(xué)方面,此不詳述。甘肅是中國的詩歌大省。“在連續(xù)三屆魯迅文學(xué)獎優(yōu)秀詩歌獎評選中,全國共有15名詩人獲獎,其中有4位是甘肅詩人;在權(quán)威的詩歌年度全國選本中,將近20%的名字屬于甘肅詩人。”與傳統(tǒng)文學(xué)一樣,活躍在網(wǎng)絡(luò)世界且成績較為突出的甘肅詩人也有不少。內(nèi)蒙古詩人柳蘇為“網(wǎng)絡(luò)詩人”下了這樣的基本定義:“一貫在網(wǎng)絡(luò)上寫詩發(fā)詩,并有自己的平臺(博客),積極參與網(wǎng)絡(luò)詩歌的組織和交流,并通過網(wǎng)絡(luò)造成一定影響,具有網(wǎng)絡(luò)詩歌成就。有詩歌而不符合上述條件的,嚴(yán)格地講,不能稱之為網(wǎng)絡(luò)詩人。”靜川、柳蘇排列出一個“網(wǎng)絡(luò)詩人大集會”榜單,其中甘肅網(wǎng)絡(luò)詩人包括:馬蕭蕭、李繼宗、王懷岐、蝴蝶飛飛、竹溪、劉青之、江一葦、楊慧娟(女)、李王強、安文海、阿陽、綠木、雪的精靈、岳非、旱子、西北步子、郭文沫?汪彤、李彥周、包文平、趙應(yīng)軍、亨一、……等71位。例如:甘肅天祝人旺秀才丹,藏族,網(wǎng)名“阿里狼客”,現(xiàn)在西北民族大學(xué)工作。早年曾在紙媒上發(fā)表了大量作品。
2004年,他創(chuàng)辦“藏人文化網(wǎng)”,自己擔(dān)任總監(jiān)。他是“天涯社區(qū)”“詩選刊論壇”“詩江湖”“星星詩歌論壇”等全國許多家文學(xué)網(wǎng)站或論壇的活躍分子,發(fā)表了大量的網(wǎng)絡(luò)詩歌作品,先后擔(dān)任“天涯社區(qū)天涯詩會”等多家文學(xué)論壇版主,建立多個個人文學(xué)博客。剛杰•索木東,甘肅卓尼人,現(xiàn)在西北師范大學(xué)工作。他早年亦在紙媒上發(fā)表過大量文學(xué)作品。21世紀(jì)初,索木東開始接觸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最早加盟了旺秀才丹創(chuàng)辦的“藏人文化網(wǎng)”并擔(dān)任文學(xué)極地版主(藏巴哇),后來成為文學(xué)頻道的主編。索木東亦是“天涯社區(qū)”“故鄉(xiāng)社區(qū)”“詩選刊論壇”“星星詩歌論壇”等全國多家文學(xué)網(wǎng)站或論壇的活躍分子,發(fā)表有大量的網(wǎng)絡(luò)詩歌作品,他先后擔(dān)任了“莽昆侖論壇”“大敦煌論壇”等文學(xué)論壇的詩歌版主。他以自己的故鄉(xiāng)———甘南草原作為創(chuàng)作母題,他的詩歌也大體被劃歸到鄉(xiāng)愁詩的譜系,在詩歌中,他認同、歸依民族,思念、眷戀故鄉(xiāng),摯愛、追尋文化,詩歌深邃而斑斕。裕固族人蘇柯靜想發(fā)表在文學(xué)紙媒上的作品早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有《紅系腰》《堯熬爾》《姑娘蘇姬斯》《夢中故鄉(xiāng)》《薩里瑪珂》等詩歌作品;也有《雪蓮》《白駱駝》等小說作品,其中影響力較大的部分小說被收入《狂奔的彩虹馬》、《裕固族文學(xué)作品選讀》。蘇柯靜想于2005年開始涉足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其小說《薩爾走過的草原》曾獲得“電信杯”金張掖首屆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大賽小說類優(yōu)秀獎。以網(wǎng)絡(luò)為主陣地的作者,在甘肅已有很多,其中作品量較大、影響較大、且寫作水平比較高的,有蕭蕭眉兒、毒化、香山紫煙、漢字999、老圈、閆海東、海杰等。例如,蕭蕭眉兒(鄭曉紅)于2004年開始寫作,2005年被甘肅省作家協(xié)會吸收為會員。蕭蕭眉兒的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其中所深蘊的真情以及折射出的深厚的底蘊,甚至有人這樣盛贊她———“荒涼的西北升起一顆耀眼的文曲星”。她的《我思我愚》《誰來拯救你,我的父老》《媽媽,您給上帝捎個話》,讓人心生震撼。盧克強是一位曾經(jīng)在甘肅隴東山區(qū)插隊的老三屆知青,從2002年開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長篇小說《窄門》《上海人在非洲》和一些中短篇小說,不過他真正為人們所了解、熟悉,主要歸功于在網(wǎng)絡(luò)載體上的發(fā)表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2005年,甘肅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家盧克強位居“搜狐十大作家”排行榜第三,《盧克強中短篇小說集》還獲得由甘肅省委宣傳部批準(zhǔn)設(shè)立,由甘肅省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共同主辦的全省最高專業(yè)文學(xué)獎———2008年揭曉的“第二屆甘肅省黃河文學(xué)獎”中短篇小說類優(yōu)秀獎。
東北文學(xué)論文:談?wù)摉|北文學(xué)創(chuàng)作媒介與文學(xué)社團考
本文作者:葉立群單位:遼寧社會科學(xué)院
在進步愛國的文學(xué)副刊中,影響力最大的是《大同報》《夜哨》文藝周刊。這個周刊有兩大特點。第一,立場鮮明。編者陳華在1933年8月6日的刊詞《生命的力》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不要“彷徨,躊躇”,要起來“以自己為武器去抗?fàn)帯薄N膶W(xué)史對此做出了中肯的評價,“從《夜哨》發(fā)表的大量作品來看,體現(xiàn)了編輯的宗旨。最鮮明的特點是:一些進步文學(xué)青年所描寫的對象,已由過去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表現(xiàn),開始轉(zhuǎn)向工農(nóng)勞苦大眾。所反映的思想內(nèi)容,除暴露社會的黑暗外,同時指出斗爭的方向,預(yù)示著前途的光明”[1]137。第二,以此為陣地的進步作家多,作品的社會反響大。在共出刊的21期《夜哨》上,發(fā)表了蕭紅的短篇小說《兩個青蛙》《啞老人》《夜風(fēng)》等,蕭軍的短篇小說《下等人》,羅烽的短篇小說《口供》,金劍嘯的短篇小說《星期天》,李文光的短劇《黎明》和中篇小說《路》。這些作品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激發(fā)了飽受凌辱的民眾不畏強暴、勇于反抗壓迫的信心。“九一八”事變后,盡管東北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中國共產(chǎn)黨始終堅持對淪陷區(qū)文學(xué)活動的領(lǐng)導(dǎo),甚至直接領(lǐng)導(dǎo)創(chuàng)辦文學(xué)副刊。其中《哈爾濱新報》的《新潮》副刊即為黨直接領(lǐng)導(dǎo)的重要副刊之一。“這個副刊是由一些進步文學(xué)青年創(chuàng)辦的,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公開的報紙文藝副刊。報館地址在哈爾濱道外十三道街。經(jīng)常為副刊寫稿的有:羅烽、舒群等。”[2]14《新潮》發(fā)表的作品,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深刻揭露了日偽統(tǒng)治下的反動和黑暗社會本質(zhì)。《新潮》共出刊半年,1932年9月,松花江大水沖垮了報館,副刊也隨之停刊。淪陷區(qū)存在時間最長的進步文藝副刊是白朗在《文藝協(xié)報》主編的《文藝》周刊。從1934年1月18日到12月17日,共出48期。作品主要有連載小說、詩歌、散文、連載文論,作者包括金劍嘯、羅烽、白朗、蕭軍、蕭紅、舒群、代生、梁山丁、唐景陽等地下文藝工作者與進步文學(xué)青年。代表作品有蕭軍、蕭紅合著的短篇小說《一個雨天》《鍍金的學(xué)說》《破落之街》《期待》《患難中》,蕭紅的小說《麥場》《麥場二》,金劍嘯的《云姑的母親》,梁山丁的《黃昏的莊上》《無從考據(jù)的消息》,白朗的《逃亡的日記》《四年間》等。這些作品真實地描繪了當(dāng)時農(nóng)村的破敗,人民的悲戚生活,也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情緒和抗?fàn)幘瘛?/p>
壓制與抗?fàn)帯獪S陷期文學(xué)期刊的“歌與哭”東北淪陷時期文學(xué)期刊的產(chǎn)生,其背景是復(fù)雜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是曲折而艱辛的。最初允許創(chuàng)辦文藝期刊,在政策層面仍然是日偽統(tǒng)治者出于統(tǒng)治的需要,想借此擴大宣傳,美化日偽政權(quán)。但推動文學(xué)期刊走向繁盛的最重要的動力,卻是文學(xué)自身發(fā)展的需求。淪陷區(qū)最早的期刊是1932年創(chuàng)辦于沈陽的《大同文化》,后辦刊地點又經(jīng)兩次遷移:1935年4月遷長春,1936年3月遷大連。“該期刊內(nèi)容多系宣傳所謂‘滿洲建國’的意義與闡述‘王道主義’的文章,以及美化日偽政權(quán)的文藝作品。這是敵偽統(tǒng)治者的御用刊物。”[1]1401932年,《淑女之友》在沈陽創(chuàng)刊,該刊發(fā)表的文藝作品雖在文藝界產(chǎn)生較大影響,但多屬唯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作品。隨著文學(xué)創(chuàng)作隊伍的成熟,報紙的副刊因其容量有限,已經(jīng)難以適應(yīng)豐富的文學(xué)內(nèi)容。于是,那些革命的和帶有進步傾向的創(chuàng)作者開始開辟新的陣地,創(chuàng)辦大型期刊。1934年底,當(dāng)時最具影響力的《鳳凰》在沈陽創(chuàng)刊;1935至1936年,《新青年》《興滿文化月報》《滿洲新文化月刊》《斯民》《滿洲文藝》等先后創(chuàng)刊。“期刊的出現(xiàn),改變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完全依附于報紙副刊的局限,篇幅的增大,作品表現(xiàn)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也就有了比較充分的展現(xiàn),東北文學(xué)的發(fā)展有了適宜的陣地。”[3]116《鳳凰》是帶有明顯進步傾向的期刊,刊登了大量介紹國內(nèi)文藝動態(tài)和進步作家情況、作品及評價的文章,發(fā)表了如蕭然的《漢子》、吳瑛的《夜里的變動》、扉子的《老聶的話》、尹鳴的《小三子的命運》等在當(dāng)時產(chǎn)生較強反響的進步作品。其他幾種期刊刊登進步作品,則要策略得多。如《新青年》是協(xié)和會奉天省事務(wù)局創(chuàng)辦的,在發(fā)刊詞中強調(diào)其辦刊宗旨是“統(tǒng)一青年思想”“克制外來之思想”“復(fù)興滿洲之文藝兵挽救出版局之沒落”。盡管如此,進步作家仍然沒有放棄這樣的陣地,他們?nèi)匀辉趬褐浦邪l(fā)出吶喊。刊于《新青年》的馬尋作品《宵行》,秋螢作品《雪地的嫩芽》,都是通過較隱諱的方式,抒發(fā)了思鄉(xiāng)之情,揭露了敵人的殘暴。1937年后出現(xiàn)的較有影響力的期刊有《明明》《藝文志》《文選》《作風(fēng)》《新滿洲》《麒麟》《青年文化》等。與上一階段相同,這一時期期刊的公開辦刊宗旨更多為日偽政權(quán)服務(wù),如《藝文志》標(biāo)榜兼收并蓄,鼓勵寫與印主義,實際上是鼓吹為偽滿洲國振興文藝。《新滿洲》提出“以忠愛孝義協(xié)和為宗旨”。這些期刊發(fā)表了許多為日偽統(tǒng)治涂脂抹粉的文章。《文選》是當(dāng)時斗爭性最強、刊登進步作品最集中的期刊。時任《文選》編輯的進步作家秋螢在創(chuàng)刊號的《刊行緣起》中指出:“現(xiàn)階段的文學(xué)已經(jīng)不是超時代的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或個人主義的牢騷泄憤了。現(xiàn)在的文學(xué)是教養(yǎng)群眾的利器,認識現(xiàn)實的工具。”《文選》共發(fā)行兩期,首期刊載的進步作品有山丁的《狹街》、白樺的《飲血者》、石軍的《擺脫》、姜靈非的《三人行》等。第二期刊載了李妹人的中篇小說《鍍金的像》、秋螢的中篇小說《礦坑》。這些作品,通過各種形式,反映出了被奴役、被壓迫的農(nóng)民、市民和礦工的悲慘境遇和反抗的心聲。淪陷期文學(xué)期刊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它們成為文藝論爭的重要載體。1938年后,淪陷區(qū)文藝界爆發(fā)了激烈的文學(xué)論爭,出現(xiàn)了兩種對立的文學(xué)觀,一種是提倡“描寫真實”“暴露真實”的文選派觀點,一種是倡導(dǎo)“寫與印”主義的藝文志派觀點。1937年,日本人城島舟禮創(chuàng)辦的《明明》提出了“寫印主義”的倡導(dǎo),在創(chuàng)刊紀(jì)念特大號發(fā)表了“百枚小說”(即400字原稿紙100頁),隨后又推出了“城島文庫”叢書,出版了古丁、小松、爵青、石軍等人的作品。《明明》停刊后,古丁、小松、爵青等人在《藝文志》的發(fā)刊辭上提出“藝文之事,端在寫與印,其所寫,無嫌天地之大,芝麻之小,倘有真意,自可求傳;其所寫印,無論滄海之巨,粟粒之細,倘存善根,當(dāng)能久遠。”大力倡導(dǎo)“純藝術(shù)”。文選派觀點的明確提出始于山丁發(fā)表于《明明》的《鄉(xiāng)土文學(xué)與〈山丁花〉》,他指出:“不論在時間和空間上,文藝作品表現(xiàn)的意識和寫作的技巧,好像都應(yīng)當(dāng)側(cè)重現(xiàn)實”。
并且強調(diào):“滿洲需要的是鄉(xiāng)土文學(xué),鄉(xiāng)土文學(xué)是現(xiàn)實的。”山丁提出“鄉(xiāng)土文學(xué)”的主張后,馬上遭致藝文志派的批評,嘲諷“鄉(xiāng)土文學(xué)”作者亂提主義,指責(zé)“鄉(xiāng)土文學(xué)”是地域主義,有偏狹性。隨后,山丁、秋螢、梅娘、袁犀、金音、冷歌、李喬等,陸續(xù)在《文選》等期刊發(fā)表文章,批評寫印主義,極力倡導(dǎo)不能逃避客觀現(xiàn)實。沉默中的吶喊與屈膝———淪陷期文學(xué)社團的“功與罪”在東北淪陷的14年中,文學(xué)社團異常活躍,高峰時有據(jù)可查的社團就達二百多個。由于當(dāng)時復(fù)雜的社會生態(tài),社團的成因、訴求、形態(tài)也有著很大的差異。最早的文學(xué)社團出現(xiàn)在1933年初,它們萌芽于文學(xué)愛好者的聚集交流,后依托日漸興盛的文學(xué)副刊而成熟,到了1934年即在數(shù)量和影響力上達到了一個鼎盛期。1934年11月3日《滿洲報》載文提到的文學(xué)社團就有19個,即:冷霧社、新社、飄零社、白光社、白眼社、白云社、新潮社、紅葉社、旭日社、曦虹社、濃霧社、凋葉社、落潮社、野狗社、ABC社、寒光社、寒寂社、凄風(fēng)社、春冰文學(xué)研究社等。其中最有成就的社團是冷霧社、新社、飄零社和白光社。這些社團的重要特點是屬于依托副刊自發(fā)形成的同人社團,各有鮮明的創(chuàng)作追求,團結(jié)和培養(yǎng)了大批作家。其中冷霧社依托沈陽《民報》的《冷霧》周刊,主要成員有成弦、馬尋等;飄零社依托《撫順民報》的《飄零》周刊,主要成員有孟素、秋螢、曼秋、石卒等;新社依托《沈陽民報》的《蘿絲》周刊,主要成員有楊蕭梅、碧波等;白光社依托自印社刊《白光》和《奉天周報》的《白光》周刊,主要成員有小松、雪萍、夢園、文文等。四大社創(chuàng)作特點鮮明,被研究者評價為:“標(biāo)榜追求完美的冷霧社;因襲歐洲古典創(chuàng)作的新社;貼近現(xiàn)實的飄零社;講求純藝術(shù)的白光社。”[4]6東北淪陷后期,隨著報紙副刊的凋零和期刊的興起,出現(xiàn)了依托期刊的文學(xué)社團。這些社團的特點是規(guī)模較大、審美趣味和藝術(shù)主張更為明確的、創(chuàng)作園地更為堅實廣闊。其中明明派(藝文志派)依托《明明》和《藝文志》期刊;文選派依托《文選》期刊;文叢派依托《文叢》期刊。這些社團在創(chuàng)作的同時,堅持自己的文藝主張,并進行了長期的藝術(shù)觀念論爭。在日偽的白色恐怖統(tǒng)治下,淪陷區(qū)抗日愛國的文化人士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斗爭。在這一時期,產(chǎn)生了“L•S(魯迅)文學(xué)研究社”和“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小組”等進步文學(xué)社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詩人田賁組織的“L•S(魯迅)文學(xué)研究社”。這個文學(xué)社1936年創(chuàng)辦于遼寧省蓋縣,主要參加者為田賁曾經(jīng)的同學(xué)、學(xué)生和文友。他們秘密傳遞借閱進步報刊,研讀左翼書籍,利用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并喚醒受壓迫的同胞。后又創(chuàng)辦了《行行》《星火》等刊物,宣傳抗日愛國思想。哈爾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小組”的領(lǐng)導(dǎo)人為共產(chǎn)黨員陳紫(關(guān)毓華),成員包括關(guān)沫南、宿學(xué)良、劉煥章、王忠生、佟世鐸等。他們積極組織進步青年,以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進行抗日活動。在日偽統(tǒng)治者的嚴(yán)密控制下,文藝界的反抗斗爭雖如野火般旺盛,但終究還是要在地下奔涌。那些御用文藝組織和反動的日本作家同人文藝團體卻大張旗鼓的活動,蒙蔽民眾,毒害人民。主要的日人作家同人文藝團體包括“滿洲浪漫”“作文發(fā)行社”“鵲”“撫順文學(xué)研究會”“滿洲短歌會”“北滿歌人社”“大連川柳會”“滿洲新短歌協(xié)會”“關(guān)東洲詩人會”“滿洲誹句會”等。1941年3月23日,日偽政權(quán)出臺《藝文指導(dǎo)綱要》,規(guī)定文藝團體組織、研究機構(gòu),一律由敵偽政權(quán)直接領(lǐng)導(dǎo)。
隨之,日偽扶植的御用文藝組織“滿洲文話會”“滿洲藝文家協(xié)會”“滿日文化協(xié)會”“藝文志事務(wù)會”等紛紛成立。日偽政權(quán)為這些文藝組織提供資金,支持他們的活動和出版。他們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漢奸文學(xué)和殖民文學(xué),粉飾美化王道樂土,歌頌侵略戰(zhàn)爭,攻擊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
通俗文學(xué)論文:民俗文學(xué)興起的剖析
本文作者:初清華作者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xué)
通俗文學(xué)興起的主要原因
首先,“”后因為傷痕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產(chǎn)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而獲得極大自信的文學(xué)界,于1980年6月25日、7月14日,《文藝報》分別在北京、石家莊召開座談會,著重漫談文學(xué)表現(xiàn)手法探索問題,并以筆談和會議紀(jì)要的形式發(fā)表,希望引起討論。王蒙針對“不懂”得批評而提出“也要照顧少數(shù)人的喜聞樂見”,以及“每一篇作品的讀者,都不會是全民,而只能是人民的一部分”,李陀認為文藝界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藝術(shù)形式”上,張潔、宗璞等人也作了有關(guān)的發(fā)言,當(dāng)時創(chuàng)作中也吸收了“現(xiàn)代派”表現(xiàn)手法。這都表明此時的創(chuàng)作者“專業(yè)知識分子”的覺醒,開始注意文學(xué)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的探索。
本來,文學(xué)家的精英意識,使得他們的創(chuàng)作放棄社會中絕大部分的讀者對象,即使是在天津文聯(lián)召開“通俗文學(xué)研討會”以后,盡管中國作協(xié)第四次代表大會也邀請了香港新派武俠小說作家梁羽生參加,但中國文聯(lián)和中國作協(xié)仍是本著治理整頓的態(tài)度。中國文聯(lián)委托中國作協(xié)主辦的《文藝報》、《文藝情況》,于1985年前后刊登的文章中總是把“通俗文學(xué)”等同于地攤小報,進行批評,提請有關(guān)領(lǐng)導(dǎo)部門注意。如《文藝情況》1985年第1期刊載了三篇:筱凱《讀部分小報札記》,若華、曉言《個體書攤見聞》,小微《關(guān)于“通俗文學(xué)熱”———記天津一次研討會》。而《文藝報》1985年第1期“怎樣看待文藝、出版界的一個新現(xiàn)象”欄目中,刊發(fā)三篇文章,鮑昌《一個引人注目的新的文學(xué)現(xiàn)象》提出要求“作家、評論家、文藝界領(lǐng)導(dǎo)干部,應(yīng)當(dāng)從思想上重視起來,對通俗文學(xué)做做調(diào)查研究”,夏康達《一個需要引導(dǎo)的文學(xué)潮流》,提出“指導(dǎo)當(dāng)前的通俗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幫助讀者提高審美水平”。黃洪秀《我們的文藝要開倒車嗎?》則態(tài)度激憤地指責(zé)通俗文學(xué)。
試以《廣西“通俗文學(xué)熱”調(diào)查記》為例作一說明。1984年底,《文藝報》記者王屏、綠雪到南寧、河池、柳州和桂林等地作了采訪和調(diào)查。首先,作者把通俗文學(xué)定位于一種文化現(xiàn)象,認為“為數(shù)不少的篇章并不具有文學(xué)的特征”。認為出版物編輯“追尋最大量的讀者群,順應(yīng)他們的欣賞要求,是這類報刊的共同特點。一些編輯的審稿標(biāo)準(zhǔn),以‘不出問題’(主要指政治問題)為界,重視娛樂、消遣功能”,導(dǎo)致“很難看出這些作品在思想藝術(shù)質(zhì)量上有較明顯的提高和發(fā)展,而只是明顯地表現(xiàn)出:以‘拾遺補缺’取勝,占有廣大的讀者群;作為一種文學(xué)現(xiàn)象,帶有突發(fā)而又缺乏種種思想藝術(shù)準(zhǔn)備和有意識地引導(dǎo)扶植的特點”。由此可見調(diào)查者的矛盾心理,既不愿意承認這是一種“文學(xué)”熱,但又不得不承認讀者確實將其視為文學(xué)作品,不愿意從文學(xué)界創(chuàng)作和批評中存在的問題找原因,而是把“通俗文學(xué)”對所謂“純文學(xué)”、“正統(tǒng)文學(xué)”、“官辦文學(xué)”、“雅文學(xué)”造成的沖擊,歸咎為出版界的問題。這就決定了該文把“通俗文學(xué)熱”興起的主要原因簡單歸為“無非是文藝界和其他部門(基本是事業(yè)單位)所走的生財?shù)慕輳健4蠹倚恼詹恍?小報就是賺錢的。至于文學(xué)價值等等已不為這些刊物優(yōu)先考慮”,“主辦者經(jīng)過了不自覺到自覺,從被動到主動這樣一個過程”,認為綜合治理“通俗文學(xué)熱”中出現(xiàn)的問題,“涉及報刊管理和體制、辦報辦刊的指導(dǎo)思想等有待改進的環(huán)節(jié)”,最后也順帶提出提高讀者審美趣味的問題[4]。不管如何,通俗文學(xué)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關(guān)注。
而新時期之初中央對群眾文化的重視,以及對民間文學(xué)、古籍整理的提倡,促進了通俗文學(xué)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