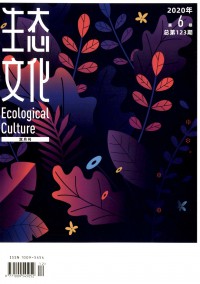文化觀念民間藝術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文化觀念民間藝術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民間藝術的象征體系
民間藝術的深層次文化內涵較為穩定,幾乎不因社會文化變遷而發生改變,這不僅因為這些文化內涵與人類的本能性需求密切相關,更為重要的是,深層次文化內涵通過代代相傳的象征體系,已經深度內化為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了。格爾茨認為,共享性的、普遍的“意義只能‘儲存’在象征”中。反而言之,只有“儲存”在象征中的意義才具有普遍性與共享性,因為象征比較直觀,無需借助語言文字的解釋,人們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意義,而且,在象征沒有受到歷史意識與哲學觀念批判的地方,象征體系就是生活常識,人人稔熟,了然于心。我們發現,民間藝術通過復雜的象征體系,使其文化內涵具有了普遍性與共享性。就民間造型藝術而言,除了小部分直接再現社會生活,把日常生活作為審美觀照對象,絕大部分是依據象征體系創造的,這個象征體系由形象、圖案、符號、色彩等構成。形象系列主要來自古老的圖騰崇拜,如老虎、豬、牛、羊、麋鹿、龜、龍、蛇、魚、蛙、鳳凰、朱雀、向日葵等形象,這些形象在民間的剪紙、刺繡、印染等作品中隨處可見。另一類形象雖然來自日常生活,卻并非單純地將日常生活作為審美觀照對象,而往往在古老的象征思維的影響下,通過民間故事賦予其某種神話內涵,將其納入象征體系之中,如無錫惠山泥人中的“大阿福”,也許是先有了這個形象,為了神化這個形象,就有了民間傳說“沙孩兒”勇斗猛獸的故事。再有一類形象則是通過諧音被賦予某種象征意涵。如桌案上擺著花瓶象征著平安;畫一位官員騎著一頭梅花鹿,寓意是“進祿”;畫一個胖娃娃騎著大鯉魚,寓意是年年有余。我們發現,即使是當代的一些單純再現日常生活場景的民間剪紙、繪畫中,民間藝術家仍然會在場景中加個龍、鳳、兔子等吉祥物形象,可見象征意識以及古老的象征體系對民間藝術影響之深。在民間藝術的象征體系中,除了極為豐富的具體形象系列之外,還有大量相對抽象的圖案或符號,比較著名的如雙喜、如意、中國結、九宮圖、八卦圖、陰陽魚、“盤長”、卐字等,這些抽象符號大都來自中國陰陽、五行、八卦哲學觀念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觀念。如卐字符,據唐代慧苑《華嚴音義》載,卐本非漢字,原為古印度的印度教、佛教的吉祥符號,武則天時期才權制此文,“音之為萬,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盤長”符號也可能來自佛教,張華就認為,“盤長”并非是對“盤腸”形象的模仿,而是來自佛教的法器“盤長”。在中國民間造型藝術中,色彩也是有象征意義的,如紅色象征著熱血、生命,是中國人心目中鎮邪的色彩;白色象征冬天的白雪,意味著萬物凋零與死亡,是中國人的喪服色彩;綠色象征著春天、大地、生育,所以傳統婚禮中新娘子往往穿紅戴綠。在中國民間觀念中,色彩甚至與空間、時間,乃至人倫道德之間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系。具體而言,東方主青色,西方主白色,南方主赤色,北方主黑色,中央主黃色;春主青色,夏主紅色,長夏主黃色,秋主白色,冬主黑色;紅色象征熱血、忠勇,黑色象征正義,白色象征奸邪。誠如靳之林所言,中國民間美術并不全按照事物的固有色彩來處理,更不同于西方的條件色彩體系,而“是以陰陽觀、五行觀與八卦觀為基礎的觀念色彩體系”。深入考察一下民間表演藝術,我們驚訝地發現,民間表演藝術也受到了象征思維的深刻影響,從舞臺、服裝道具到人物造型、表演流程,以及表演內容,都有某種象征性內涵。舞臺以及服裝道具的設計作為民間造型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上是受制于象征體系與象征思維的。比如古戲臺的藻井形式的頂棚,井頂一般為圓形的明鏡形式,象征著天圓地方,人在天地之間,頂棚的內壁上大都繪有民間常用的雙魚、龍頭、八卦等象征性形象或符號。就民間藝術的表演流程來看,大都有固定的程式,比較典型的是儺戲中的請神、祭神、送神與秧歌中的“謁廟”、“排門子”、跑場圖等。尤其是秧歌中的場圖,看似隨心所欲,變化不定,其實基本圖式是相似的,而且大都暗含著某種象征意義。張華在研究秧歌場圖時發現,人們花很大力氣排練的秧歌場圖,對于參與者來說,遠不如“扭”和“逗”來得利落、痛快,對于觀眾來說,也大多看不出其中的門道,鬧秧歌之所以重視場圖顯然不是出于娛樂或審美的目的,而是因為“那些圖式也許是作為某種神秘內容的巫術象征,因而被認為具有了相應的神秘功能。而踩過它們,按它們的模式去跑舞圖,就會得到某種超現實目的的實現”。
這樣具有象征意義的民間表演程式,不僅是在秧歌中,也是中國民族民間舞的共同特征。在民族民間舞中,手心向上為陽,手心向下為陰,陰手陽手有著不同的象征,舞步上,先出哪只腳,如何變化,步距、方位、秩序,往往各有定數。就民間表演藝術的內容而言,儺戲的象征性內涵最為顯著,甚至可以看作是象征體系的儀式化演練。在儺戲演出中,神壇、神像、神物的布置,巫師穿戴的面具、法衣等服裝道具,巫師的念咒、作法以及神靈附身的模擬性表演與念唱神話等,無不具有象征性內涵。正是借助于象征體系,儺戲表演者將人們從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帶進了神圣世界之中,實現了人與神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和解。不僅儺戲的內容具有象征性意義,許多地方歌舞小戲也有著豐富的象征性意義,如浙江湖州地區流行的歌舞小戲《掃蠶花地》,就是通過模擬性地表演掃地、糊窗、撣蠶蟻、采桑葉、喂蠶、捉蠶換匾、上山、采繭等一系列與養蠶生產有關的動作,敘述養蠶生產勞動過程,說唱祝愿蠶繭豐收等吉祥話語,借助于象征體系表現其在審美娛樂之外的民俗文化意涵的。通過象征體系,民間藝術的深度文化內涵轉化成了日常生活常識,人們耳濡目染,代代相傳。且不論專職從事儺戲表演的巫師,就是傳統社會中鄉間那些無知無識的村婦村姑,也熟知各種各樣藝術形象的象征性內涵。靳之林在陜北考察時曾有意問一群剪紙的姑娘,“魚戲蓮”圖案是什么意思,對方說,就是談戀愛的意思,靳之林又問,那“魚唆蓮”圖案是什么意思,對方一下子羞得漲紅了臉,一位抱著孩子的婦女就替她們回答說,“睡在一塊兒了唄!”有一位姑娘剪了一個“蓮里生子”圖案,說必須放在“魚唆蓮”中,而不能放在“魚戲蓮”中,那位抱著孩子的婦女就解釋說,如果放在“魚戲蓮”中,那就是說還沒結婚就生了孩子。由此可見,不管是民間藝術家,還是鄉間普通婦女,對民間藝術形象的象征性內涵都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對其界限區分得很嚴格。我們看到,通過民間藝術及其象征體系,在沒有文字的底層社會,民眾活態傳承著最古老的民族文化觀念。
二、民間藝術的當代意義
由于民間藝術的文化內涵的核心是原始的、世俗的文化觀念,因此,在古代社會,官方與文化精英往往漠視、貶抑民間藝術,雖有所謂“采風”制度,卻并非因為真正尊重民間藝術,而是為了補察時政之得失,以通上下之情。除卻晚明的李贄、馮夢龍、凌蒙初等少數人,在古代絕大多數文化精英的眼中,無知無識的鄉民是沒有能力創造自己的文化的,他們只是教化的對象,他們的信仰是不合禮制的、愚昧的“淫祀”,他們的繪畫、雕塑是缺乏意境的匠人之作,他們的音樂連一貫比較重視底層民眾的白居易也認為“嘔啞嘲哳難為聽”。尤其在宋元之后,民間戲劇藝術蓬勃發展起來,由于其內容比較粗俗,不合禮教,有的甚至暗含著某種抵抗意識,因而,官方時常下令禁止。早在南宋時,就曾“京都新禁舞齋郎”,明清時期更是禁令不斷。“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在西方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研究的影響下,一批文化精英開始重新審視民間藝術,有人認真搜集、整理民間歌謠,有人甚至提出向民間藝術學習,但是,在這些文化精英的意識深處,他們仍然認為民間藝術在文化內涵方面是低俗的、不合時宜的,需要改造、提升,如哈華在1950年代初討論秧歌時說,“北方的舊秧歌、皮影戲、自樂班、大小戲班、瞎子說書、吆號子等,南方的昆曲、南詞、念佛句、山歌、彈詞、評話、花鼓燈、秧歌等,數量之大,深入群眾的程度,遠超過新文藝和新秧歌,新的還趕不上舊的,有計劃有組織的發展新秧歌,改造舊秧歌,是向封建文藝奪取陣地工作之一,是一個艱巨長期的戰斗。”誠然,民間藝術中有一些不文明、不健康的思想內容,需要清理、改造、提升,但是,民間藝術是一種尚未從生產、生活中分化出來的渾然的藝術形態,其精華與糟粕往往是共生的,很難剝離,因此,我們也許應該謹慎地批判、改造,積極地保護、研究。尤其在文化全球化的當代語境下,由于文化劇烈地變遷,人們普遍面臨著文化傳統斷裂所造成的文化認同困境,我們更應該正確認識民間藝術的文化內涵,重估其當代意義。首先,民間藝術通過象征體系成為一種民族共享性的文化符號,它是社群成員之間社會交往與情感交流的媒介,有著重要的文化認同與社會團結功能,而且這種功能在現代社會尚未喪失。比如,孩子生日、老人壽辰時親戚贈送禮幔,喪禮上親友贈送各種紙扎等,這些生活中的藝術品不僅促進了親友之間情感層面的交往,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一定的禮儀,他們共享了這些文化符號中的文化意涵,強化了他們之間的文化認同,有利于社會形成有機社群。尤其是民間集體表演藝術,如節慶、廟會時的演出,就其本質而言,其實是文化認同儀式的演練,通過審美化的儀式,人們直觀地體驗到他們在情感、文化上是一個共同體。在鑼鼓喧天、載歌載舞的熱鬧之中,人們陶醉了,即使平日鄰里之間、家庭內部有一些矛盾、爭吵,此刻也和解了。
晚近二十年來,在鄉土社會逐漸解體的當代,不僅華北的鄉村,甚至一些大都市,傳統節慶、廟會反而大有復興之勢,也許“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中,廟會依然會保留在現代城市民眾的生活之中,并且成為人們文化認同與審美需求的一種表現形式”。其次,民間藝術中積淀著豐厚的傳統文化內涵,它一直是傳統文化的象征,是族群文化記憶的載體,是我們活態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面對民間藝術的象征體系,尤其是通過一次次操演傳統的民間集體表演藝術,我們可以直接感受到當代的社會文化生活與傳統的社會文化生活之間的連續性,感受到我們并沒有遠離祖先以及他們的情感與信仰。毫不夸張地說,民間藝術可以讓我們與祖先共享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文明,讓我們直觀地理解民族的文化傳統。在大傳統已經斷裂的當代中國,以民間藝術為主要載體的文化小傳統也許是我們通往過去,重建傳統文化延續性的重要途徑。也許正是意識到了這點,新世紀以來,國內興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運動,而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目錄中,民間藝術占據其中一半以上。再次,民間藝術建構了一個關于過去的象征的空間,有利于形成一種“無場所的記憶”,這對于“離土”進程中的當下中國有著特別的意義。眾所周知,人不可能僅僅活在當下,生命的意義離不開記憶,尤其離不開來自社會生活的“集體記憶”。德國學者揚•阿斯曼認為,集體記憶中具有“凝聚性結構”的是文化記憶,所謂文化記憶是指對共同的過去的記憶中所包含的共同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以及對重要事件的回憶所提供的解讀當下生活意義的重要維度。對于文化記憶而言,穩定的社會空間以及諸如文字、圖片、儀式等一整套符號體系是非常重要的。人們被迫遷居陌生的環境會有種種不適應,其重要的心理根源就在于記憶喪失了社會空間的依托以及熟悉的符號體系。在當代城市化進程中,大批農民失去了祖祖輩輩生活的社會空間,進入陌生的城市空間之后,出現了文化記憶與文化認同危機問題。湯姆•米勒在中國調研時發現,城市里的“外來務工人員過著封閉式的生活,無論社交還是居住,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我們課題組2013年在江蘇地區調研時也發現,80后、90后外來務工人員與城市居民之間仍然存在嚴重的交往困難,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觀念不同,比重為27.5%。在原有生活空間喪失的情境下,凝結在民間藝術中的符號體系與文化理念卻是可遷延的,通過傳承民間藝術,可以建構起一種“無場所的記憶”。事實上,“離土”的鄉民也非常渴望通過民間藝術重溫他們的鄉土記憶與文化認同。高小康發現,在遠離鄉土文化的都市,蘭州濱河馬路的休閑帶有成群的人在唱《花兒》,廣州越秀公園景區中心的客家山歌墟,不僅有大量客家人來此自發地唱山歌,而且臺下往往聚集很多聽眾。
三、總結
總而言之,民間藝術并非僅僅是審美的對象,還是一種有著悠久傳統與深厚內涵的文化形態。這種文化一旦活態傳承下來,“就會建構起當下文化生態的多樣性,并成為當下文化形態的參照”。因此,對于民間藝術的文化內涵,我們不僅不應該鄙視其粗俗、不合時宜,相反,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其悠久的傳統,經久不息的生命力,以及其當代意義,努力將其轉化為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
作者:季中揚胡燕
文檔上傳者
- 地域文化旅游文化品牌
- 文化資源建設文化思考
- 市文化局文化總結
- 文化翻譯和文化傳真
- 文化沖突和文化震蕩
- 文化局文化藝術安排
- 后殖民文化音樂文化
- 文化局強化文化服務講話
- 傳統文化中的廉文化研討
- 產業文化創業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