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抗震救災(zāi)精神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完善抗震救災(zāi)精神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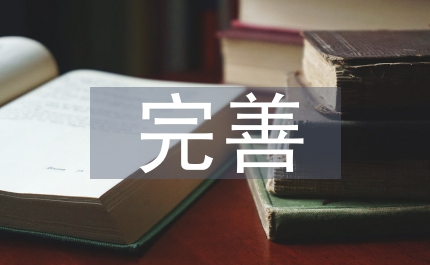
在我們的許多先賢眼里,冷漠、麻木、自私是舊時(shí)代中國國民性。魯迅深受日俄戰(zhàn)爭中中國人“欣賞”自己同胞被殺戮的情景刺激,憤而棄醫(yī)從文,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義的“看客”形象。梁啟超痛陳,“‘旁觀’二字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zhì)也”,“‘無血性’三字為吾全國人所專有物也”。林語堂發(fā)出沉重嘆息,我們“有太少的公民,太多的私人”。柏楊甚而激憤地說:“從沒有一個(gè)社會和一個(gè)民族,像中國人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正是由于冷漠、麻木、自私,中國社會成了令孫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盤散沙”。
然而,面對突如其來的汶川大地震,當(dāng)代中國人展現(xiàn)出的是別樣的風(fēng)采、別樣的情懷、別樣的精神:不再是“一盤散沙”,而是具有高度的動員力、凝聚力和整合力;不再是冷漠、麻木,而是大勇大愛;不再是自私,而是大仁大義。在政府和軍隊(duì)快速高效實(shí)施救援、災(zāi)區(qū)人民頑強(qiáng)自救的同時(shí),社會自發(fā)的救援力量也如潮水般涌入災(zāi)區(qū)。全國NGO迅速啟動救援計(jì)劃。一支支志愿者隊(duì)伍緊急馳援災(zāi)區(qū)。獻(xiàn)血的人們在大街上排起了一條條長龍。更多的人則慷慨解囊。據(jù)民政部統(tǒng)計(jì),截至2008年7月8日12時(shí),全國共接收國內(nèi)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總計(jì)567.80億元,實(shí)際到賬款物563.17億元。多少故事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中國人向來是只有到了最危險(xiǎn)的時(shí)候,才會發(fā)出最后的吼聲。這是導(dǎo)致中國積弱積貧的一個(gè)因素,但也是中國屢經(jīng)患難而不滅的重要原因。“最危險(xiǎn)的時(shí)候”不是生活的常態(tài),八級大地震亦屬“黑天鵝”事件。但是,中國人抗擊汶川大地震所體現(xiàn)的精神風(fēng)貌,具有較為堅(jiān)實(shí)的內(nèi)在制度基礎(chǔ),并非轉(zhuǎn)瞬即逝的電光石火。
在一些先賢看來,中國人冷漠、麻木、自私并非天生而然,其禍因乃在于中國人長期備受“專制之毒”。孫中山指出,在清代,“集會有厲禁,言論無自由,遂至習(xí)非成是,幾將吾人樂群之性,團(tuán)結(jié)之力,消滅凈盡,此散沙之象所由呈也”。又說:“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凈盡,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云幸矣,豈復(fù)能期其人心固結(jié)、群力發(fā)揚(yáng)耶!”梁啟超分析中國人不愛國的原因是“后世暴君民賊,私天下為一己之產(chǎn)業(yè),因奴隸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屈于奴隸,積之日久,而遂忘其本來也。后世之治國者,其君及其君之一二私人,密勿而議之,專斷而行之,民不得與聞也。有議論朝政者,則指為莠民;有憂國者,則目為越職。否則笑其迂也,此無怪其然也。譬如奴隸而干預(yù)主人之家事,則主人必怒之,而旁觀人必笑之也。然則雖欲愛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既不敢愛不能愛,則唯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主人之榮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dāng)∫?主人之中落也,則褰裳以去也,此奴隸之恒性也。”林語堂則認(rèn)為,中國人自私的“原因在于缺乏足夠的法律保障。這與道德無關(guān),罪惡在制度。如果一個(gè)人有公共精神,他就會有危險(xiǎn)。那么很自然,他就會對國家大事采取漠然置之的態(tài)度;如果對貪婪腐敗的官吏沒有懲罰,那么,要求人們不貪婪,不腐敗是對人性提出了過高的要求。”老子說:“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在專制制度下,國家權(quán)力取代了共同體的自治權(quán)力,官僚機(jī)器直接操控社會。共同體內(nèi)的一切事務(wù)都由掌握陰謀秘計(jì)的官僚治理。這必然導(dǎo)致共同體自組織能力的斫喪,共同體成員參與公共事務(wù)的精神、相互間的聯(lián)結(jié)和信任也隨之而萎頓。正因?yàn)槿绱?傳統(tǒng)中國人在非常時(shí)期展現(xiàn)的積極精神缺乏相應(yīng)的制度支撐,不能延續(xù),時(shí)過境遷,冰消瓦釋,一切又恢復(fù)如昔。
而今,中國進(jìn)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已是三十年,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已基本確立。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的建立,解構(gòu)了中國以政治為統(tǒng)帥的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三位一體結(jié)構(gòu),社會獲得了自治能力,市民社會應(yīng)運(yùn)而生。黑格爾認(rèn)為,市民社會雖是一個(gè)個(gè)人追逐自己特殊利益的私人領(lǐng)域,但是“在這一領(lǐng)域中,道德具有獨(dú)特的地位”,因?yàn)橹挥性谶@一領(lǐng)域中,個(gè)人才會反思自己的特殊性,持有作為特殊而獨(dú)立的個(gè)人應(yīng)具的責(zé)任心,從而使“偶然的和個(gè)別的援助成為一種義務(wù)。”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促進(jìn)了中國社會分工的深化。在涂爾干看來,分工既是社會有機(jī)團(tuán)結(jié)的主要源泉,也是道德秩序的基礎(chǔ)。有機(jī)團(tuán)結(jié)是社會功能和個(gè)人自由相容相生、相輔相成的團(tuán)結(jié)。有機(jī)團(tuán)結(jié)源于社會成員在活動層面的互補(bǔ)性和意識層面的共生性,因?yàn)榉止な菇粨Q成為必然,交換使行動者在功能上互補(bǔ),在意象上互生:“交換就是這種依賴關(guān)系的外在闡釋,對其內(nèi)在和深層狀態(tài)的外在表現(xiàn)。正因?yàn)檫@種狀態(tài)是持續(xù)的,所以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意象系統(tǒng),其主要的功能就是連續(xù)性,這正是交換所缺少的屬性。我自己的意象與另一個(gè)使我完善的人的意象是不可分離的,這不只是因?yàn)樗囊庀蟛粩嗯c我的意象相互融合,更是因?yàn)檫@種意象就是對我的意象自然而然的完成。這樣,它就成了我們意識連續(xù)的、恒定的組成部分,我們再也缺少不了它,甚至千方百計(jì)地強(qiáng)化它。”在人與人的關(guān)系上是這樣,在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上,集體意識不再是強(qiáng)制性的,不再阻礙個(gè)人的自由發(fā)展,于是,關(guān)于個(gè)體尊嚴(yán)、專業(yè)分化、公平正義和職業(yè)道德的新的一致性成為社會團(tuán)結(jié)與個(gè)人自由正面結(jié)合的基礎(chǔ)。市場經(jīng)濟(jì)是“合作的擴(kuò)展秩序”,超越了血緣、地緣的束縛,其發(fā)展推動了公德在中國的滋長。當(dāng)代社會資本理論認(rèn)為,市場分化模式對促生社會資本尤為重要,當(dāng)行為人致力于以貨幣形式使其自身和行為商品化時(shí),當(dāng)政權(quán)和法律發(fā)現(xiàn)其合法性信賴于維持貨幣購買力時(shí),當(dāng)各種市場以擴(kuò)大和延伸信任的方式水平和垂直分化時(shí),社會資本的各種重要來源就會產(chǎn)生。這種分散的信任感使人們更愿意在親族、社區(qū)和地方網(wǎng)絡(luò)之外的行為中投入他們的金錢、時(shí)間和情感承諾。研究表明,許多人參與志愿者組織的一個(gè)重要目的就是積累社會資本。如果說計(jì)劃經(jīng)濟(jì)制度使人成為工具,那么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則使人成為主體。隨著人的主體性的確立,人固有的惻隱之心、悲憫情懷及“推己及人”的人道精神勢必復(fù)蘇。可以說,市場經(jīng)濟(jì)、市民社會是孕育中國抗震救災(zāi)精神的母腹。由于有制度基礎(chǔ)的保障,中國抗震救災(zāi)精神絕不會在震后消散,只不過表現(xiàn)將有所差異。
在中國,有人視人為經(jīng)濟(jì)人,祭起經(jīng)濟(jì)人法寶,反對計(jì)劃經(jīng)濟(jì),為市場經(jīng)濟(jì)開路。同時(shí),也有人出于維護(hù)計(jì)劃經(jīng)濟(jì)、反對市場經(jīng)濟(jì)的目的,認(rèn)為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將打開潘多拉盒子,釋放出經(jīng)濟(jì)人這一魔鬼,導(dǎo)致物欲橫流、道德淪喪、人文精神消解。也許因?yàn)樗姑苁枪诺浣?jīng)濟(jì)學(xué)的創(chuàng)始人和集大成者,《國富論》的影響力大于《道德情操論》,許多人便將經(jīng)濟(jì)人這一概念的發(fā)明權(quán)歸于斯密,并以為斯密是自私自利的倡導(dǎo)者。其實(shí),這是一個(gè)莫大的誤會。據(jù)考證,經(jīng)濟(jì)人這一概念的創(chuàng)造者是帕累托,而非斯密。在斯密看來,一個(gè)利己的人,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道德存在,人同時(shí)兼具利己心和同情心,“無論人們會認(rèn)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gè)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guān)心別人的命運(yùn),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外,一無所得。”斯密的偉大貢獻(xiàn)在于對利己與利他相統(tǒng)一的中間機(jī)制的研究,那就是基于“旁觀者”的“同情”的道德約束機(jī)制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jīng)濟(jì)機(jī)制。斯密承認(rèn),“每個(gè)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guān)心自己”,但正是這一點(diǎn)要求人們尊重天然的正義法則:“對自己幸福的關(guān)心,要求我們具有審慎的美德;對別人幸福的關(guān)心,要求我們具有正義和仁慈的美德。”斯密認(rèn)為,促使人保持其行為之“合宜性”的根本原因是人類普遍具有的同情心,它使人通過想象、參與、分享和模仿等方式,形成諸如仁慈和正義等基本道德情操,從而對人的利己心構(gòu)成約束。盡管斯密說過被廣泛引用的名言“我們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但從其整個(gè)思想體系來看,他無疑是將道德基礎(chǔ)作為市場有效運(yùn)行的一個(gè)前提條件。前文對中國抗震救災(zāi)精神的產(chǎn)生的分析表明,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與道德具有高度一致性,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能提升道德水準(zhǔn)。
災(zāi)后重建更為繁重、艱巨、長期,極其需要發(fā)揚(yáng)抗震救災(zāi)精神。要使抗震救災(zāi)精神在災(zāi)后重建中得到充分發(fā)揮,必須進(jìn)行重建制度創(chuàng)新。本著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形成最大合力的原則,合理的制度模式應(yīng)是:政社分工、分別主導(dǎo)、相互配合。公共產(chǎn)品供給和災(zāi)民基本生活救濟(jì)由政府主導(dǎo),吸納社會參與。其它領(lǐng)域則由社會主導(dǎo),政府給予政策支持。
目前,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運(yùn)動正方興未艾。只要推進(jìn)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shè)、健全法制、完善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加強(qiáng)市民社會建設(shè),抗震救災(zāi)精神就必定能進(jìn)一步固化,從而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的偉大動力。
論文關(guān)鍵詞抗震救災(zāi)精神;固化;制度基礎(chǔ)
論文摘要汶川抗震救災(zāi)中,當(dāng)代中國人所表現(xiàn)出的高度動員力、凝聚力和整合力,所表現(xiàn)出的大勇大愛、大仁大義,與舊時(shí)代國民性中的冷漠、麻木、自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抗震救災(zāi)精神,具有較為堅(jiān)實(shí)的內(nèi)在制度基礎(chǔ)。要使這種精神進(jìn)一步固化,應(yīng)該繼續(xù)推進(jìn)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shè),完善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加強(qiáng)市民社會建設(sh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