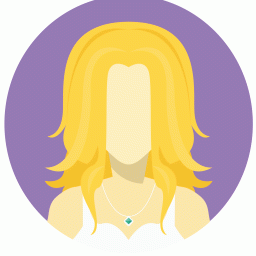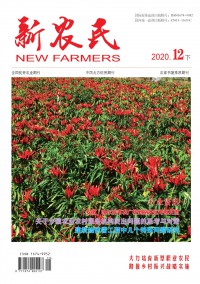農民集體上訪中選擇性激勵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民集體上訪中選擇性激勵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集體上訪處于既無法被強令禁止但又受到警惕、壓制乃至打擊的尷尬境地。“有組織抗爭”反映了農民集體上訪的規模和組織化水平已經提高。能有效地代表大量個人的組織的出現需要應用‘獨立的和選擇性的激勵’來抑制搭便車行為。農民集體上訪的經費主要來自參與者個人自費、自發集資、捐款、村組集體的“小金庫”等等。農民集體上訪都是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非利他。上訪有非常明確、具體的利益要求。上訪代表之間、上訪代表與普通村民之間始終存在利益分歧。如果不采用機制化的“選擇性激勵”對上訪代表進行實質保護,而僅僅停留在“道義”支持水平上,上訪代表的積極性必將嚴重受挫。
[關鍵詞]上訪;選擇性激勵;維權
一、概念的界定
1.集體上訪
廣義上,“上訪”等同于“信訪”;狹義上,“上訪”是“信訪”的一種。本文采用廣義上的“上訪”概念。“信訪,是中國公民組織化的意見表達方式。信訪,就是公民通過書信、電話或訪問等形式,向黨政機關及其負責人,以及人民團體、新聞媒介反映情況,提出批評、建議、意見、要求和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提出控告、檢舉”。[1](p104)
信訪是以行政方式治理國家的一種非常救濟手段:首先,信訪部門不是專門機構,更不是司法機關,而是在各級國家機關1內部設立的一個部門。只有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才有權依照法定程序監督司法,法院不可能憑信訪部門的意見立案、再審。信訪可以說是一種非法治的申訴和救濟方式。其次,信訪部門處理問題的主要手段是受理并接待群眾的來信來訪,但并不保證信訪中反映的問題能夠解決,有的甚至連解決程序都進入不了。再次,根據“歸口管理、分級負責”的規定,群眾反映一級國家機關的問題,最終還必須回到這一級國家機關去處理。[2]這容易使上訪者遭到壓制、打擊報復,使他們只能循環往復地不斷上訪,期盼上級領導親自過問或直接批示予以解決。
個人上訪是上訪者直接找他可以信任的上級政府伸冤訴苦的行為。而在集體上訪中,盡管上訪行為本身是對政府信任的表現,但這種信任卻是首先通過對上訪代表或上訪組織的信任來表達的。政府對上訪代表和上訪組織與自己“爭奪群眾基礎”、“挑戰政府權威”無疑是高度敏感的。在官員們看來,集體上訪很可能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操縱和利用,成為“反社會主義”的工具。因此,集體上訪處于既無法被強令禁止但又受到警惕、壓制乃至打擊的尷尬境地。[3](pp.315~316)
農民是務實的,在他們看來,“你以個人身份出面,再狠,狠得過政府?你以組織出面,雖然只是個村民小組,但上面也得當回事。再說,他鄉政府巴不得你來亂的,好抓住你的把柄。”[4](p122)集體上訪中,如何把握“踩線不越線”的尺度,既獲得“政治正當性”,不被抓住把柄,又通過集會、靜坐示威等“邊緣政治行為”擴大影響、施加壓力、得到實際利益,這個分寸很難把握。
借鑒李連江、于建嶸等人的觀點,1998年以前的農民維權可稱為“依法抗爭”,是農民運用國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維護其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損害的政治活動。采用的主要方式是上訪,以訴求上級政府的權威來對抗基層干部的“枉法”行為。1998年以后,農民的維權進入“以法抗爭”或稱“有組織抗爭”階段。[5](pp.32~33)“農民有組織抗爭,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為領導核心,通過各種方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非正式社會動員和信息交流網絡,以中央或上級政策為依據,以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土政策為抗爭對象,以直接動員農民抵制為手段,以宣示和確立農民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為目標的一種政治性抗爭”。[6](p1)“有組織抗爭”反映了農民集體上訪的規模和組織化水平已經提高。
2.選擇性激勵
“選擇性激勵”一詞,源自奧爾森(MancurOlson)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他指出:“能有效地代表大量個人的組織的出現需要應用‘獨立的和選擇性的激勵’來抑制搭便車行為。”[7](p374)個人是否自愿加入利益集團,不僅取決于這些組織提供給所有成員的集體利益,也取決于它們是否以多種利益形式對參加者予以個人化激勵,以及以繳納費用、罰款和其他個人化制裁形式所實施的懲罰。[7](p19)因為盡管成員們對獲得集團利益有共同興趣,卻都希望別人承擔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擔了成本,一般總能得到集團提供的利益。[8](p18)所以,“對一個完全依賴于其成員的自愿參與和捐款的利益集團來說,這個組織剛開始會有大量的個人參加;并且在最初的幾次集會上會有大量的捐款。隨后,參加者和捐款數量會不斷減少,直至該組織萎縮為只有獻身于‘事業’的活動家組成的‘硬核’,或者完全失敗。”[7](p376)除物質上的獎勵和制裁外,“社會制裁和社會獎勵也是‘選擇性激勵’。不服從的人受到排斥,合作的個人被邀請參加特權小集團。”[8](p71)社會地位和社會承認可視為對個人的社會獎勵。社會制裁則可以表現為社會壓力(特別是輿論壓力)、人際關系緊張、聲望下降等。
二、“選擇性激勵”在農民集體上訪中的體現
下面擬結合4個案例分析農民的集體上訪中“選擇性激勵”的作用,包括:
(1)案例一:應星在《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一書中提供的關于四川省平縣大河電站沖刷區農民上訪的材料。大河電站建成于1978年,歸地區行署管轄。電站建成后,沖刷和淹沒的土地涉及四個鄉鎮,引起農民持續的聯合上訪,要求給予補償。1982年以后,上訪逐漸升級,組織化水平越來越高。[3]
(2)案例二:于建嶸在《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一文中提供的關于湖南省衡陽縣(即H縣)農民上訪的材料。自1992年起,衡陽縣20多個鄉鎮的一些農民因負擔過重和干部作風等問題多次上訪縣、市、省和中央,并逐漸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減負上訪骨干隊伍,其中被稱為“減負上訪代表”的核心人員有80多人。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依據中央和省政府的有關政策組織并帶領農民對縣、鄉兩級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國家法律的土政策進行各種形式的抵制。[6]
(3)案例三:郭正林在《當代中國農民的集體維權行動》一文中提供的關于湖南省李家灣農民上訪的材料。1987年李家灣一部分土地被征用。鄉政府同村里簽訂了土地款入股合同,將5.6萬元土地征購款轉移到了鄉政府。鄉政府用從各村籌集的資金建了一棟商業大樓。1991年,鄉政府變賣大樓,得款300萬。按合同規定,李家灣村應分得本利10萬元,但鄉政府拒絕履行合同。村民開始集體上訪。[4]
(4)案例四:阿古智子在《從“上訪”的“曖昧性”看中國農村社會的權力、利益和秩序》一文中提供的關于內蒙古赤石村農民上訪的材料。上訪的焦點是非法采伐公有林、村干部挪用公款、稅費征收不合理、農業承包中的欺詐行為、救濟糧發放不公等。[9]
1.分攤上訪費用,均分上訪收益
農民集體上訪的經費主要來自參與者個人自費、自發集資、捐款、村組集體的“小金庫”等等。[4](p126)
在案例一中,上訪經費“一個來源是上5組的群眾集資,另一個是電石廠(為上訪移民接管)的剩余資金或物資折價款”。[3](p207)通過長期有組織的集體上訪,移民從國家一次次的“開口子”中獲得了幾十萬元的補償。
在案例三中,李家灣村民“大家一致同意每個村民分攤25塊錢,并在上訪信上一連按下100多個手印”,約定討回被鄉政府占用的10萬多元征地款后,每家分得1400塊。[4](pp.116~118)
2.對上訪代表的獎勵
(1)物質獎勵
物質獎勵,主要指經濟上的補償。如在案例一中,“上訪代表的旅差費實報實銷;上訪代表一切誤工補貼,暫按每天2元補助;召開代表會議,代表每天按1.2元補助;因上訪造成的經濟損失一概予以賠償”。[3](p206)
物質獎勵也可以表現為其他形式。如在案例二中,“在減負上訪代表洪阿斌服刑期間,他的妻女得到了四鄉八鄰的關照……一次下著大雨,一位與他們家沒有任何親戚關系的農民從十幾公里外的地方趕來幫助他家修理房頂”。[6](p3)
(2)社會獎勵
社會獎勵主要表現為對上訪代表的尊重和保護。如在案例一中,移民上訪中流傳著一句話:“帶頭打官司2的要整死,廣大的災民要餓死”。也就是說,像許老師這樣帶頭“打官司”的挨了整,群眾的口糧就不會得到保證。保護許老師不受政府的傷害,也就是移民在為自己的實際利益而戰。[3](p409)
又如在案例二中,“減負上訪代表受到了農民普遍尊重。對這一點,‘減負上訪代表’有切身感受。他們都非常肯定地認為,由于參加了減負活動,自己到農民家里受到了歡迎,政治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特別是當這些‘減負上訪代表’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打擊時,就有許多農民自發地出來保護和幫助他們……事實上,有多起農村群體性事件正是為了保護和營救這些農民利益代言人而發生的”。[6](p2)
3.對不合作者的懲罰
懲罰措施主要有罰款、群體排斥、輿論壓力等。在案例一中,1990年3月,移民決定到大河電站“鬧飯吃”。“是大河電站占用了我們的土地,我們就找電站要飯去,督促上面來解決……按照每大姓出兩人的標準選出10名代表……向電站要的錢到手之后,每個代表分160元……全鎮村民,凡不去電站吃飯的,每人每天扣5元,不給糧食”。[3](p277)“去了不準中途退出……在事情沒有解決之前,工作組發放的糧食補貼款不能領,誰領了誰就是叛徒”。[10](p234)如果誰敢出面說許老師的不是或膽敢為工作組說句話,就要遭到與工作組同樣的下場。[3](p410)
三、農民集體上訪中的利益博弈
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得出了兩條關鍵結論,其二便是“選擇性激勵”在集體行動中的必要性。結論的得出源自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假設: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7](p4)對這一假設的批判早已連篇累牘,主要是說它是一種抽象的人性論,人并非永遠處于自私的動機狀態,也并非每個人都是自私的。但有一點應該明確:任何理論都有設定,或者說適用范圍。在一般情況下,農民仍然符合上述假設,集體上訪不是出于無私的利他主義,而是維護或爭取個人利益的動機。在農民組織起來進行集體上訪時,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尤為重要。
比如在案例一中,移民雖然支持許老師上訪,卻在他因第一次計生事件3受到傷害時袖手旁觀。他們認為上訪是關乎大家,也關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而許老師在計生問題上與政府的過節只是他個人的事。[3](p409)
同樣是在案例一中,“僅8月22日和23日兩天,電石廠又有幾圈銅絲和一套銅板被盜。負責看守電石廠的移民精英加強了看守力量,卻還是擋不住你拿我拿的偷盜潮。移民當年在討伐區鄉辦電石廠的劣跡時說他們把電石廠辦成了一個‘大家拿’的廠。現在上5組還沒有把電石廠的產權接收下來就已經阻止不了電石廠成為新的‘大家拿’的廠了。”[3](p260)而電石廠實際上是大河移民后期上訪資金的主要來源。
而從動機上看,農民集體上訪都是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非利他動機。上訪有非常明確、具體的利益要求。即使為了“面子”,也是出于維護自身地位和尊嚴,仍然不是利他,盡管效果可能不只對自己有利。即便是上訪代表中有所謂不怕犧牲、不計得失的“英雄主義情結”,也仍然反映出獲得社會承認的自利動機。而且,上訪本身就是獲取“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源”的途徑之一。社會聲望的提高、視野的開闊、能力的鍛煉使上訪代表的人生有了質的飛越。
在上訪過程中,利益博弈始終存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算盤”,都想把自己的利益要求納入集體目標。上訪代表之間、上訪代表與普通村民之間始終存在利益分歧,在大方向上大家可能一致,但在具體目標、斗爭策略、利益分配等問題上并非鐵板一塊。分裂、背叛時有發生。這些在案例一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大河移民精英在上訪中逐漸分化成三批力量:第一批是以村民組長為代表的法定精英。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為群眾爭取最大經濟補償。上5組與下3組在10萬元補償的分配上又存在著矛盾。第二批是以許老師、王學平、梁永德等為代表的上訪班子。他們是在外面拋頭露面與區鄉對著干的人,是區鄉處心積慮打擊報復的對象。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將貪官拉下馬以保證自身安全。他們既反對移民匆忙分錢,更反對電石廠立即開始生產,因為這就意味著對舊帳的默認,可能導致告區鄉貪污的官司被撤銷。第三批是以梁永生和林學倫等為代表的電石廠班子。他們是經區鄉正式任命的村民組聯辦企業的負責人,是上訪斗爭果實的合法接收者。區鄉打擊報復的矛頭一般不會指向他們,而電石廠一旦運轉起來,利潤則由他們掌握。告倒區鄉,與電石廠班子沒有直接利害關系。倒是電石廠不生產,他們就只能守著一堆破銅爛鐵。因此,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如何尋求經濟發展和安置勞力,以鞏固自己的地位。[3](pp.145~146,p401)
每一批精英都代表著群眾的一部分利益,同時又加上了自己的利益。不僅普通群眾的這部分利益與那部分利益可能發生沖突,普通群眾的利益與其利益代言人的利益之間可能發生沖突,群眾利益代言人之間的自身利益更可能發生沖突。
在利益攸關的時刻,農民為了保全自己,出賣上訪代表。湖北省咸寧市通山縣大路鄉塘下村農民余蘭芳,為“村小學教學樓建成豆腐渣”、“村財務十幾年不公開”和“稅費改革違背上級政策”等問題,上訪八個多月,自費近3萬元,跑了2萬多公里,找了十幾個部門,受盡白眼和屈辱,沒想到不僅問題解決不了,反倒被判勞教一年半。通山縣公安局使用了逼供手段,要村民們證明余蘭芳有罪:“總共把我關了38個小時,幾班人輪流審問,不讓睡覺,飯也不讓吃飽……我從內心感到害怕了,就按照他們的意思違心地寫了材料……他們說不簽就把你關到牢里去……大路鄉派出所方揚禮所長握住我的手在每張紙上按了手印……半夜里,我冷得打顫,用報紙裹在身上取暖,后來寫了保證書才被放出來。”[11](pp.51~55)在政府的威逼下,余蘭芳就這樣被村民們出賣了。而事實上,上訪所反映的問題本來就與她無關,是這些村民們請她出頭的。面對壟斷權力的政府,農民的力量是單薄的,單個農民的力量更是渺小,他們自保的行為選擇也是符合其自利本性的。
四、“選擇性激勵”不可或缺
由于農民一般情況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選擇性激勵”對當代中國農民集體上訪是適合的。正如奧爾森所言,一個完全依賴于其成員自愿參與和捐款的組織是沒有前途的。農民集體上訪如果長期處于臨時性的低組織化水平,特別是沒有有效的“選擇性激勵”,是沒有前途的。
長期以來,農民形成了依賴心理,總是期待有人站出來替自己伸冤,或者期待上級領導出面解決自己的問題。但是,在集體上訪中,如果長期依賴上訪代表做“無私奉獻”,是難以維持的。且不問上訪代表的“英雄主義”熱情能持續多久;長期上訪的話,飽受打擊、負債累累,甚至連生存都會成問題。
如在案例二中,湖南省衡陽縣曾經以整頓社會治安等名義對“減負上訪代表”進行過“集體辦學習班”、“掛排亮相”、“罰款”、“抄家”、“關押”等形式的打擊。[6](pp.7~8)上訪代表鄧夫賓的妻子說:“他領導農民減負上訪全是靠家里的收入,有時還將我養的豬賣掉給他作路費,在經濟上沒有給家里帶來一點好處。”[6](p3)又如在案例四中,“雖然村民們盡自己所能資助上訪,但上訪代表們大多負債沉重,甚至沒錢送孩子上學。”[9](p263)
更有甚者,如果不采用機制化的“選擇性激勵”對上訪代表進行實質保護,而僅僅停留在“道義”支持水平上,上訪代表的積極性必將嚴重受挫。他們如果放棄上訪,或被“招安”,集體上訪就更難組織起來。
在案例四中,上訪代表被公安局以“煽動群眾、擾亂社會秩序”等罪逮捕。干部還勸誘上訪代表:“如果你們停止上訪,我們可以給你們補償金”。在政府的利誘下,原作為上訪代表很活躍,后來在村委會選舉中當選為新主任的張建對農民上訪中要求解決的問題不熱心了,“儼然成了政府那邊的人了”。[9](pp.252~263)
而在案例一中,馴鹿鄉上訪代表謝明全本來是被群眾自發推舉出來的上訪精英,卻最早被收買。上訪前,他在馴鹿鄉市場管理辦公室當臨時工,是個很有些油水的位置。在他開始組織上訪后,鄉里將他辭退了。1986年4月聯合進京上訪后,鄉里許諾,只要他停止上訪,就讓他復職。謝明全答應了。他這個主要代表一被“招安”,馴鹿的上訪勢頭頓時就被遏制住了,其他的上訪精英受到了各種刁難。但是,等上訪的風頭稍微平息以后,謝明全在區鄉的“秋后算帳”中還是未能幸免。他很快又被停職。等他想重新組織上訪時,已是樹倒猢猻散的局面了。[3](pp.199~200)因為“大家都明白了一個道理:你領頭去鬧,又不能比別人多領一份,大家分的都是一樣的;而鬧不好,就可能是你自己去背包坐牢。窮歸窮,但在家里的日子總是要比在遣送站、在看守所的日子要輕快一點,還是息訴吧”。[3](p302)
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4和國家賠償等司法救濟制度不能有效保護農民利益的情況下,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農民選擇了集體上訪。但是由于力量對比的懸殊,集體上訪中,農民如果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造成聲勢,獲得“合法性”,或者說“政治正當性”,就很難與政府長久對抗。因此,注意利用“選擇性激勵”,尤其要對上訪代表進行物質獎勵和實質保護5,是集體上訪得以持續,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選擇性激勵”的使用關系到以集體上訪為核心的農民集體維權行動的前途,應給予充分的重視。【參考文獻】
[1]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2]郭國松.審視信訪[N].南方周末,2003-11-13(A6).
[3]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從"討個說法"到"擺平理順"[M].北京:三聯書店,2001.
[4]郭正林.當代中國農民的集體維權行動[J].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001,No.19.
[5]陳初越.維權,以法律的力量:本刊專訪中國社科院農研所于建嶸博士[J].南風窗,2003,10(下).
[6]于建嶸.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湖南省H縣調查[J].戰略與管理,2003,No.3.
[7][美]丹尼斯C.繆勒(Mueller,D.C.).公共選擇理論[M].楊春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8][美]曼瑟爾·奧爾森(MancurOlson).集體行動的邏輯[M].陳郁,郭宇峰,李崇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5.
[9]阿古智子.從“上訪”的“曖昧性”看中國農村社會的權力、利益和秩序:以內蒙古赤石村“上訪”研究為例[A].徐勇.中國農村研究:2002年卷[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0]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1]何紅衛.上訪村官為何被判勞教[J].南風窗.2003,7(下).
[12]姜彩熠.小民告官,難乎哉?:我親歷和47起行政訴訟案件的思考[J].南風窗,2003,7(上).
[13]李鈞德.上訪該不該被判刑:河南省唐河縣五名上訪村民被判刑的調查[J].了望新聞周刊,2003,No.14.
[14]李昌平.從“刁民”到“公民”:普通農民張丕慶的問政之路[J].南風窗,2003,3(上).
[15]朱雨晨.一個新農協的誕生[J].南風窗,2003,10(下).
[16]許志永.“上訪”顯現的社會病[N].南方周末,2003-12-04(A11).
[17]唐昊,陳壁生.走農民合法維權之路[J].南風窗,2003,10(下).
[18][美]莫里斯(Morris,A.D.).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M].劉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9]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以轉型期中國農民為對象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0]刁杰成.人民信訪史略[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
[21]程同順.當代中國農村政治發展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22]郭正林.當代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程度、動機及社會效應[J].社會學研究,2003,No.3.
[23]楊龍.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政治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注釋】
1既包括政府機關,也包括人大。
2農民習慣性地把與政府抗爭說成是“打官司”,并非實指,主要形式仍然是上訪。
3第二次計生事件時,許老師得到了農民的自發保護。這時他已是集體上訪的總操控者了。
4行政訴訟有四難:立案難、審理難、勝訴難、執行難。[12](pp.38~39)
5而且這比物質懲罰和社會制裁更容易實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