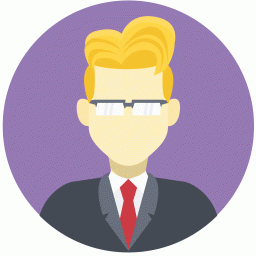近世廣西農民家庭農場規模效益考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近世廣西農民家庭農場規模效益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近世以來,廣西的農民經濟普遍形成了一種“戶耕十二畝”的經營規模。本文就是在筆者過去研究的基礎上,對這種經營規模的效益在近世中的變遷展開考察。并且,將這種考察置于一個廣闊的宏觀視野之中,即進行跨地域的橫向比較。最后,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上探討了近世廣西農民農場勞動生產率徘徊不前的制約性因素。
小農經濟,或者說個體農民經濟,是傳統農業生產的基本形態。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從事個體生產的農民,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農,就其小塊土地經營和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而言,都是“小農”。本文考察的對象即為這種小農的家庭農場。
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水平上看,廣西歷來就屬“南蠻之地”,被視之為落后地區。在中國傳統經濟的區域發展序列中,廣西直到明代以前還處于“未發展”狀態,明清以來廣西才跨入“發展中”行列。[i]廣西盡管從明清開始就作為南方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腹地,但直到20世紀中葉其傳統農業和小農經濟仍完整地保存著,從這個意義上說,廣西又是研究發展中地區傳統農業和農民經濟變遷的典型。同時,本文研究的時間跨度為1800—1950年的150年時間,其中既包括清代前期的歷史,又包括近代的歷史。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能對廣西農民經濟變化的研究作一個長期而連續的考察。筆者將這150年統稱為“近世”。
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作為透視農家經營活動所依據的主要指標,過去學術界單從土地所有權的角度對其進行了片面性研究。近年來,一些學者嘗試從土地使用的視角展開對小農經營的研究,并取得了卓有影響的成果。[ii]筆者過去曾對廣西近世農民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做過考辯,[iii]在此基礎上,希冀進一步探討他們經營規模的經濟效益。
一、勞動生產率:近世廣西農民家庭農場規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
據筆者過去的考訂,1800—1950年間廣西農民家庭農場出現了一種“戶耕十二畝”的經營規模的標準模式,并在廣西全境逐步地得以普及。[iv]本文將探討農民的耕作規模與產出效益之間的關系,而衡量它們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標志即為農戶的勞動生產率。有關農民勞動生產率的界定,學術界歷來就有頗多爭議,但學者們似乎都認為傳統小農的勞動生產率在若干方面與近代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存在著差異。在此,筆者采用李伯重的界定方法。他認為傳統小農的勞動生產率具有三個特征。首先,在勞動時間方面,近代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以日或者小時為單位,而傳統農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則應以年為單位。其次,在勞動者方面,近代工業中勞動生產率以勞動者(工人)為單位,而傳統農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則往往以勞動者(農民)的家庭為單位。最后,在勞動成果方面,近代工業中的勞動成果,通常以貨幣產值來計算;而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由于商品經濟不夠發達,農業中的勞動成果,在許多情況下是以實物來計算的。[v]
大體來說,李伯重以上所開列的傳統農業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三個特征,也適用于近世的廣西。根據本文的考察對象,此處的勞動生產率應是一個農戶一年內在其家庭農場上生產出來的產品總量。
(一)1800—1950年廣西農作物畝產量的變化
估算農戶勞動生產率的第一步,即為估算農戶家庭農場的畝產量。畝產量的變化,可以通過三種不同的方式來實現:(1)每播畝作物畝產量的變化;(2)每畝耕地復種指數的變化;(3)畝產值較高的作物與畝產值較低的作物之間的互相替代。
我們首先來看看作物復種制在廣西的變化。據研究,清代前期廣西有兩種復種制逐漸地發展起來。一種是雙季稻,因廣東移民遷入,其在廣西東南部的梧州、潯州、郁州等府州有所發展。另一種是稻麥二熟制,在桂北地區也發展起來了,但范圍很小,僅局限于慶遠府、桂林府的極個別州。[vi]而在雙季稻區也并非全是種植兩季水稻,潯州府屬的貴縣直到光緒年間農民仍只種植一季水稻。[vii]因此,盡管清前期實行一年兩熟制的地區占廣西總面積的40%,但復種指數最多也不會超過120%。[viii]另據學者統計,清后期廣西各地的陂塘建設非但沒有停滯,反而有所加強,尤其表現在南寧地區。[ix]因此,清后期與水利密切相關的雙季稻種植在廣西應當有所發展。據周宏偉研究,廣西在清后期雙季稻的種植由桂東南四府推廣到桂南的南寧府。[x]據此,可以估算出至清后期,廣西作物的復種指數當在130%左右。至于廣西20世紀的作物復種指數,據筆者估算,即1933年為140%,1943年為150%,1946年為120%。[xi]由此可知,1800—1950年間,廣西作物的復種指數是逐步提高的。
150年間廣西主要作物的每播畝產量的變化卻相對復雜,因為各地方志的有關記載都十分零散,尚有學者依據各種方志對清代(包括前期和后期)廣西的水稻畝產量進行了考證,但都是將復種指數計算在內。因此,筆者根據以上估算的復種指數對以下兩組畝產量進行還原。清代前期的畝產量是依據郭松義的研究,他估算當時廣西水稻的畝產當在410市斤,合343斤。[xii]按當時120%的復種指數還原,清代前期廣西水稻每播畝產量大體在286斤左右。周宏偉的研究提供了清代后期廣西水稻畝產的數據。他考證了廣西各地水稻的畝產量,筆者將他所考證的這組數據分別乘以各自的權數,即可得到當時廣西平均的水稻畝產量338斤。[xiii]然后再按130%的復種指數折算,則可以估算出當時廣西水稻每播畝產量大約在260斤上下。進入民國以后,時人對作物畝產量的調查和估算日趨科學。當時廣西各種官方統計報告中引用最多的水稻畝產量數據是1935年由張培剛等人在廣西各地做的糧食調查數據。張培剛等人通過對廣西99個縣水稻畝產量的調查,估算出當時廣西水稻平均每播畝產量為251斤。[xiv]盡管民國時期的水稻每播畝產量低于清代,但若是乘以復種指數,前者的每畝產量仍要高于后者。現將廣西各時期水稻每播畝產量和每畝產量列表如下:
以畝產值較高的作物取代較低的作物,是提高畝產的一個有效方法。150年間,廣西出現了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種植擴大而水稻種植減少的顯著趨勢。有清一代,廣西經濟作物種植面積雖然無從查考,但據研究,當時廣西經濟作物的種植規模盡管不如廣東,但其推廣速度仍是較快的,甚至在某些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已超過了水稻的種植面積。[xv]民國以后,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即開始出現在官方的統計報告中。1914年,廣西的糧食種植面積占全省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絕大多數,經濟作物僅占3%;1933年,廣西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增加到5.3%。[xvi]從這種數據,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時期廣西經濟作物的種植仍在繼續擴大。當時廣西主要的經濟作物有苧麻、煙草、花生、甘蔗、豆類、瓜子、芝麻、藍錠、油菜等。這些經濟作物的產值一般都比糧食為高。譬如,依1933年廣西省政府的統計,其每畝的平均產值分別為:“煙草(土種)為7.61元,苧麻為16.38元,甘蔗為22.53元,而在糧食作物方面,同年的玉蜀黍只為1.95元,水稻只為5.27元,前者的價值大于后者的4~5倍。”[xvii]這就是說,同一單位面積的收益,經濟作物較糧食作物高出若干倍。故此,經濟作物的擴大,也就使得農田畝產量隨之而明顯增加。
以上三方面足以說明1800—1950年間廣西農民家庭農場的畝產量有了緩慢的提高。由于這三方面畝產量變化的途徑都與“戶耕十二畝”的經營模式密切相關,[xviii]所以當這種經營模式在廣西各地逐漸普及之時,廣西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也必定隨之發生變化。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一變化。
注釋:
[i]高王凌:《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第12~24頁。
[ii]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中有關江南農民經營規模的研究,三聯書店,2003年。
[ii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iv]徐毅:《廣西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與經濟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學歷史系2001級碩士學位論文,藏于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v]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第321頁。
[vi]郭松義:《清前期南方稻作區的糧食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1期。
[vii]民國《貴縣志》卷10,“物產”引光緒縣志。
[viii]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1頁。
[ix]李閏華:《民族交往與近代廣西農業的發展變化》(未刊稿),廣西師范大學歷史系99級碩士生學位論文,藏于廣西師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x]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2頁。
[xi]徐毅:《廣西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與經濟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學歷史系2001級碩士學位論文,藏于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xii]郭松義:《清前期南方稻作區的糧食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1期。
[xiii]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頁。
[xiv]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17頁。
[xv]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241頁。
[xvi]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頁。
[xvii]胡學林等著:《廣西經濟建設諸問題》,廣西省訓練團教材,1948年,第27頁。
[xvii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一、勞動生產率:近世廣西農民家庭農場規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2
(二)1800—1950年間廣西農民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發展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談的農民,僅指農村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如前所述,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取決于其一年內實際勞動的日數和所獲得的總產量。因此,如果農民的實際勞動日數隨產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話,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仍然可能停滯甚至下降。因而,了解農民一年內實際勞動日數的變化,同了解產量的變化同樣重要。關于當時廣西農民勞動日數的問題,可從兩個方面分析:一是農民一年內的總勞動日數;二是耕地畝均勞動投入。在此,首先引入一段明清時期的史料:
吳、浙農家甚勞,橫之農甚逸(注:橫,指明代橫州,在今廣西橫縣)。其地皆山鄉,有田一丘,則有塘潴水。塘高于田,旱則決塘竇以灌。又有近溪澗者,則決溪澗,故橫人不知有桔槔。每歲二月布種畢,以牛耕田,令熟秧二、三寸即插于田,更不復顧。遇無水方往決灌,略不施耕蕩鋤之工,惟薅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薅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獲,每一畝得谷二石者為上。此亦習于逸情而不力耳。又有畬禾,乃旱地可種者。彼人無田之家,并瑤、壯人皆從山嶺上種此禾。亦不能多工,亦惟薅草而已,獲也不減水田。彼又不知種麥之法,故膏沃之地,皆一望蕪莽不顧。[i]
根據這段史料,并結合李伯重對明清江南農民經濟所作的研究,可以推論出:
1、農民一年內的總勞動日數:農業生產的一個特點是具有鮮明的季節性。因此,農民在一年中有相當多的空閑日子。從以上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廣西農民在明末清初之際要比同時代的江南農民安逸,而當時嘉興有句流行的農諺,即“農夫半年閑”。[ii]因此廣西當時農戶的年耕作日肯定不會超過180天。而史料中“六月皆已獲”之語也進一步證明了這個數據。近代廣西,據統計,農家每年的農閑時間在5~6個月左右。[iii]也就是說,近代廣西農戶一年花在大田勞作中的時間在6~7個月之間。
2、耕地畝均勞動投入:據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水稻種植中所使用的人工,自耕田至收獲,每畝十余個,加上灌溉(車水),運送肥料等,共15個工作日。[iv]而從以上的史料可知,當時廣西農戶既不用桔槔灌溉,又鮮少施肥,故可推知清代前期,廣西平原地區的農戶種植一畝水稻大約只需10個工左右。在近代廣西,筆者根據張培剛等人對廣西7個縣農民水稻種植的生產成本及損益的調查,推算出7縣農民一畝稻田的投工量,現匯制成表2:
資料來源:據張氏的《生產成本表損益表所用之折算率及計算方法》、《正苗秈稻生產成本及損益》、《早秈生產成本及損益》、《晚造秈稻生產成本及損益》等表推算而得,各表詳見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22~25頁。
在表2中,天保農民每畝稻田的投工量之所以要比其他地區高出近一倍,并不是因為當地農民耕作技術細致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區,而是當地的水田大多處于山領之中,所以耕作時耗工較多。除了天保之外,桂平農民單位稻田的投工量也要稍高一些,主要是因為當地水稻種植技術歷來為全廣西最高之處,其細致程度可與鄰近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相媲美。若推算桂平縣兩造水稻的平均投工量,則為15個左右。
從總體上看,自明末清初以來,廣西農民一年勞動日數和每播畝作物的勞動投入日數變化都不大,因此經營方式的變化對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所起的作用當然就成為了關鍵。各種不同的經營方式,都是建立在特定耕作方式的基礎之上的。具體地說,在“戶耕十二畝”的經營模式的持續和普及中,一年兩熟制以及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種植的增加起了關鍵性的作用。[v]相反,在這種模式出現之前,廣西的農戶生產仍以一年一作制居主要地位,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種植很少。這些差異,可以導致同一耕地的畝產量發生很大的變化。因此,盡管1800—1950年間廣西農民耕地面積有所減少而農民一年總勞動日數及每茬作物勞動投入數沒有變化,但是勞動生產率卻仍有可能提高。
在此,我們把以上的所得出的結論引入這里的分析,那么可以看到:
1、由于復種指數的增加,清代至近代廣西的農民實際經營規模變化并不如表3第一行所顯示的情況。[vi]我們把上文估算的復種指數乘以戶均耕地數,可得該表的第二行數據:
從上表可知,農戶實際的耕地規模總體上是在逐步增加。
2、由于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的畝產值高于水稻,所以多種甘蔗和煙草,即使耕作面積縮減,但產量卻可增加。如前所述,一畝蔴田或一畝蔗田的凈產值大約為水稻的4~5倍。因此將一畝稻田改為蔴田或蔗田,實際上就意味著該農戶的經營規模面積擴大了4~5倍。
3、根據表1和表3,我們可以估算出廣西幾個重要歷史時期的農戶糧食生產率。1800—1850年一個農戶的產糧數為4633斤。1850—1900年一個農戶一年的產糧數為4428斤。1900—1950年農戶的產糧數有兩個:1933年為4638斤;1943年為4367斤,所以這一時期的糧食生產率為4638~4367斤。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廣西專業化程度較高的小農是從清代后期才出現的,[vii]他們的生產率顯然要比清前期稻農的生產率高。比如一戶蔴農種植熟蔴地,每年收獲以三、四次。[viii]據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每畝蔴田產蔴84斤,[ix]而一戶蔴農平均可經營蔴地8畝,[x]那么它一年的生產率為2016斤,合米8064斤,比清代前期一個稻農生產率增加了一倍左右。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地是,在農民勞動生產率的研究中,必須注意到勞動人手的數量問題。在近代農村工商業發達的桂東南地區,由于男女勞動分工的發展,清代前期農民家庭農場上的勞動人手是兩個(農夫和農婦二個),而在清后期大田勞作主要落在了農婦肩上。[xi]一個勞動者的實際播種面積,在1850年以前是8畝,而1850年后都在17畝以上,后者比前者多出一倍以上;而一個勞動者(主要是農婦)的年總產量在清前期是2316斤,而清后期以來則至少在4367斤以上,這也說明了農婦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從總體上看,廣西在150年間除了專業化小農和個別地區的農婦生產率有明顯的提高之外,一般農戶的糧食生產率還是有些微的提高,但波動很大,具有不穩定性。
[i]《君子堂日詢手鏡》,引自《廣西歷代農業史料》,廣西農牧漁業編輯室編印,1986年,第94頁。
[ii]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第334頁。
[iii]鄭家度主編:《廣西金融史稿》上冊,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94頁。
[iv]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第334頁。
[v]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vi]對廣西近世各時期農戶農場經營規模的估算參見徐毅:《廣西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與經濟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學歷史系2001級碩士學位論文,藏于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vi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viii]張先辰:《廣西經濟地理》,桂林文化供應社,1941年,第69頁。
[ix]廣西統計局編印:《廣西統計年鑒》第二回,1944,第196頁。
[x]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二、比較視野中的廣西農戶勞動生產率
從全國范圍來看,廣西歷來就是一個地瘠民貧的省份,農業經濟較為落后。到底廣西與同時代全國的平均水平,甚至是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國的農戶勞動生產率相差多大的距離,這仍需要進行對比性的計量分析。據張培剛將其在廣西的糧食調查與全國的情況所做的比較,“廣西糧食作物之每畝產量,遠較全國為低,計除秈粳稻與玉蜀黍相差三分之一,小麥相差達四分之一外,其余各項相差均達一倍,且如高梁、甘薯兩項相差達一倍有余。”[i]
另據新近的研究成果,英國在18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前,甚至在16世紀的農業革命之前,其農業就有了長足的發展。13—14世紀英國小麥畝產為每英畝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相當于中國1畝產76市斤,合64斤。當時英國中等農戶的耕地面積大約為10英畝,相當于62畝。所以,13—14世紀英國農戶的勞動生產率是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ii]關于16世紀的畝產量,每英畝16蒲式耳或368公斤是一個廣為接受的估計,[iii]相當于中國一畝產118市斤,合99斤。據侯建新估算,由于農業勞動力不斷向外轉移,16世紀英國個體農戶的勞動生產率為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iv]工業革命前夕的18世紀,農業進步尤其明顯。據特納研究,小麥畝產量在1750—1851年間從18蒲式耳增長到28蒲式爾。[v]以單位畝產20蒲式耳計,即使假定農業勞動者沒有擴大耕作面積(仍以16世紀的戶均15英畝計),18世紀英國農業生產率即已達到300蒲式耳或6900公斤。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1)從整個增長的動態過程來看,英國農業無論在畝產量還是在勞產量方面都呈現顯著的、穩定的發展勢頭,并且勞產量的增長速度要快于畝產量的增長速度。與此相比較,廣西農業盡管在畝產和勞產方面也有增長,但除了極個別地區和農戶之外,其增長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多么地不穩定!而且廣西農業的畝產量增長率要高于勞動生產率。(2)從增長的量上看,英國三個階段的小麥畝產量始終低于廣西稻田的畝產量。然而,英國農戶的糧食生產率在三個階段中卻一直高于廣西農戶:13—14世紀的英國農戶的勞產率高于1800—1850年廣西農戶的2%;16世紀英國農戶的勞產率高于1850~1900年間廣西農戶的60%;18世紀英國農戶的勞產率則至少高于1900~1950年廣西農戶的66%。事實上,工業革命前夜的英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仍要高于中國的發達地區在近代早期、甚至近代的農業生產率。依李伯重估算,明代后期江南一個普通農民的糧食生產率為3125斤,清代中期則為3700斤。[vi]據此,我們可知,17世紀中期江南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比英國16世紀的低43%,19世紀初期江南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則比英國18世紀的低46%。
17—20世紀當江南、廣西乃至整個中國的農業生產力仍然踟躕于傳統經濟的桎梏時,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首先在英國,早在18世紀工業革命的前兩百年——大約在16世紀,其農業勞動生產率即取得了突破性增長。在英國歷史上,同時也是在人類歷史上,這個國家第一次能夠持續向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不斷攀升的生活水準。在此期間,英國雖然人口持續增長,實際生活水平仍然提高了35%。諾斯等將這種人均產量的增長稱之為“真正的增長”。[vii]
[i]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27頁。
[ii]詳細估算過程見侯建新:《現代化第一基石——農民個人力量與中世紀晚期社會變遷》第二章,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iii]波梁斯基:《外國經濟史》(資本主義部分),三聯書店,1958年,第46頁。
[iv]侯建新:《農民個體力量的增長與英國自然經濟解體》,《歷史研究》1987年第3期。
[v]M.E.Turner,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Englandin18thCentury,EconomicHistoryReview,Aug.,Vol35,1982.
[vi]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第336頁。
[vii]道格拉斯·諾斯等:《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61~162頁。三、路向何方:廣西近世農戶土地經營及農業發展中的困境
(一)廣西農民農場規模效益有效提高的微觀障礙
如上文所述,廣西近世農戶的勞動生產率僅有些微提高。至于阻礙廣西農戶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原因,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是源于廣西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使農民產生的“貧惰”思想所致。[i]近來又有學者從交往的角度,認為清代至近代廣西區域、民族間的經濟交往的有限性直接導致了廣西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緩慢。[ii]然而,筆者認為,廣西自1800年以來小農經營成本過高,甚或經營虧損是一個重要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廣西小農農場經營成本過高呢?筆者認為,這與明清以來廣西在被整合到嶺南區域市場的過程中,其經濟地位和角色的日趨邊緣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明清以來,隨著兩廣谷米貿易的發展,廣西逐漸地被整合入以廣東為中心的嶺南區域市場之中。當時廣西的經濟發展水平大大低于廣東。谷米東運是廣西的主要財源之一,此外廣西向廣東輸出的主要商品還有花生、藍靛和木炭,成為廣東的糧食和手工業原料供應地。與此同時,廣東轉往廣西的商品包括布匹、鐵器、絲綢、食鹽、瓷器等手工業品和咸魚等海產品。[iii]進入近代以后,兩廣貿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時期,在輸往廣東的貨物中,最多的仍舊是谷米,其次是木材和柴。而且,在廣西的對外貿易中,按成數估算,每年有1600多萬貨物輸往廣東,占廣西出口總值一半以上。由此可見,兩廣貿易在廣西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iv]這種農產品、初級產品與較高級的手工業制成品的交換,實際上使廣西處于依賴廣東的邊緣地區的地位。不管是西谷東運還是東貨西來,都直接地影響著廣西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19世紀的廣東士紳彭泰來就以道光時廣西的一次“遏糴”為例,較為深刻地分析了廣西農村經濟在這一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自潯、梧達于南寧,皆東方泛舟之役所必至。……然販之稍殷,則遏商塞涂,顆粒不使東下。……農粟內死,估運外廢。食操舟者千余家,失業為狗鼠盜……傳聞橫州米積不得出,蒸郁糾結如李梅。……廣西服用百貨,無一不資于廣東。東鹽十日不至,則千里淡食,天災流行……”。[v]20世紀以后,特別在新桂系主政時期,仍有人不斷提出反對西谷東運,而主張在廣西發展經濟作物的意見。[vi]以上的史例大多是些描述性的分析。以下,筆者就根據民國時期的文獻和數據,從小農的生產成本和經營核算的角度,對谷米貿易對廣西農民日常經營的影響試作一計量分析。
據張培剛等人1935年在廣西所做的糧食調查和事后估算,從廣西運米至廣東,由于中間層層運銷環節過多,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昂,所以生產東運谷米的農民的收入所得與谷米的消費者所付價格之比僅為70∶100或80∶100。這是在假定“農人在售出糧食時,不受商人或其他中間人的非法剝削”的情況下估算的結果。但對這一假定,張培剛自己認為都是不可能的,僅是為了便于估算。[vii]張培剛等人同期在計入農民所得比例的基礎上,對廣西7縣各類水稻的生產成本及損益又作了調查和估算,見表4。
資料來源:據張氏的《生產成本表損益表所用之折算率及計算方法》、《正苗秈稻生產成本及損益》、《早秈生產成本及損益》、《晚造秈稻生產成本及損益》等表推算而得,各表詳見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22~25頁。
從上表可知,百色、天保、龍津、桂林四縣農民生產水稻的收入和支出相抵,仍略有盈余,宜山、賀縣、桂平三縣農民生產水稻的收入與支出相抵之后,則出現了虧損。但是,在表4中,農戶的支出指的是水稻的生產成本,并不包括農民的生活支出。據1935年農民收支情況調查,當時廣西12個縣780戶農民的周年家庭消費支出為227.58元。[viii]由此可以推論,若農民僅僅經營東運的水稻,上述7縣農戶的核算中則沒有一家是收支相抵的,全都會出現虧損。盡管廣西的每個農戶都不可能只經營水稻,但是從這一水稻的經營核算中,我們可以大體地了解到當時廣西西谷東運使農戶生產水稻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實上,進入20世紀以后,廣西農戶的周年所有收入與支出(即收入包括作物收入、畜產收入、租出農具牲畜的收入、農場副產收入、家庭工業收入、副業收入等;支出包括農場支出、家庭消費等)相抵也出現了虧損。[ix]
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以后,兩廣之間的不等價交換,還進一步表現為廣西的農產品和初級產品與機制工業品的不等價交換。因為從19世紀中葉開始,廣西隨著嶺南區域市場一起逐漸地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兩廣貿易中,農產品與機制工業品的比價在近代是越拉越大。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系統的農產品和工業品的比價指數,在此只能盡量用相關史料展開描述性分析。如來賓縣“農產品既賤,收入自然有限,購入品又種種物價高超所入,定必不敷所出,農村之經濟日困。”[x]
時至20世紀30、40年代,廣西農產品與機制工業品之間價格的剪刀差進一步拉大。1942年廣西柳城等12縣的農村經濟調查對農產品價格、農業勞工的價格和農民日用品的價格在20世紀30、40年代之際的變遷作了詳細的統計和分析。首先是1937年到1941年這12個縣農民出售的農產品價格變遷為:稻谷上漲了16倍,玉米上漲14倍,花生上漲8倍,蔗糖上漲17倍,桐油僅漲了一倍半。其次是被當作商品出售的農業勞動力價格的變遷:1937年至1941年上漲7倍弱,月工的工資上漲僅3倍,日工的工資上漲8倍半。其上漲的速度較農產品更慢。至于農民購入的日用品的價格,以農家應用最普遍需要的食鹽,棉布等為例,融縣棉布上漲34倍;食鹽上漲49倍;火柴上漲了50倍,其他洋布五金、西藥的上漲率,當然更甚。該調查稱,在這種農村物價剪刀差的情況下,大量中農、貧農破產。[xi]
小農農場經營成本的高昂,甚或經營虧損,直接構成為廣西小農長期積貧積弱的微觀障礙。所以,那些將廣西農業的不充分發展歸咎于當地農戶的貧弱,只是觸及到問題的表層原因,并沒有探及其深層原因。
(二)廣西農民農場生產率提高的宏觀瓶頸
廣西農業經秦漢大開發以后,沿至宋代,已形成為稻作——畜牧——林藝三位一體的農業體系。[xii]進入明清以后,宋代廣西這種三位一體的農業體系逐步變異,其主要表現在:一是明清之際,隨著玉米、番薯、麥類的傳入與“西谷東運”的大規模展開,桂人的主糧繼稻米之后,又有玉米、番薯何麥類先后補入,形成主糧新組合。[xiii]再加上這一時期旱地經濟作物的勃興,廣西種植業內部的稻作——旱作種植格局最終定型。二是廣西畜牧業日益萎縮。時至民國,“畜牧乃成為廣西農家之副業,……利用農閑及婦孺之勞力及荒閑之曠地,以雜糧、菜葉、谷類、苗梗,飼養家畜。”[xiv]三是林藝獲得更大發展。木材的開采廣度、強度加增,部分天然野生林產資源開發殆盡,人工培植桐、茶、杉木、棕等經濟價值較高的林木漸成規模。[xv]可以說,在1800年之前,廣西新的稻作——旱作——林藝三位一體農業體系已經代替了原有的農業體系。
1800年以后,“戶耕十二畝”的經營規模逐步形成。廣西一般的農戶都兼營稻作、旱作和林藝。因為“戶耕十二畝”的經營規模既包括水田規模,也包括旱地規模。農戶不僅可以水旱輪作,而且在旱地也多進行旱地作物與林木間作。[xvi]由此,新三位一體的農業體系構成為廣西農民農場運作的宏觀經濟環境。
如前文所述,在兩廣貿易的影響下,廣西農民家庭經營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得不重新配置即有的經濟資源。而廣大農戶的這一資源配置轉向都是與廣西即已存在的新三位一體農業體系相結合。在農戶的家庭經營中,它體現為水旱輪作、稻林結合或是水旱林兼作等形式。作者在過去的研究中就曾指出,當時小農的這些經營形式屬一種投工少,投資少,過多倚重當地資源的經營方式。[xvii]在這里,我們想進一步指出,小農稻林結合、水旱輪作或水旱林兼作等經營形式,在其內部也存在著相互協調,相得益彰的關系。下面就以大瑤山瑤農的有關情況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近代以前,大瑤山的瑤農“因為開墾荒地耕種,例需丟荒。”但到近代,瑤農往往“就可把它種樹。等到耕地肥力消失不能再種作物時,樹也長成了。象這樣的地把種植作物和造林結合起來,則種樹和幼樹的管理就不要另費較多勞力。等到樹木長大,只需要砍伐運輸的人工;如種油茶、油桐、茶葉等經濟林,則只需要一些鏟山和收籽的勞動而已。故林業的經營是費工少而收入多的生產。”[xviii]從中可以看出,瑤農經營林藝主要是依賴于適于生長林木的山地。因為這些經濟林木“對土壤要求不甚嚴格。”[xix]
據研究,英國17—18世紀的農戶開始普及一種叫諾福克輪栽制。在這種輪作制中,糧食作物(小麥、大麥)與牲畜飼料作物(蔓青、苜蓿)交替種植。這種制度下的耕地還可以和牧場輪流交替,形成“轉換型畜牧飼養”(convertiblehusbandry),從而不僅提高了牲畜產量,而且還恢復或提高地力。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加了農場中畜力畜肥的使用。[xx]黃宗智將英國農戶農場的這種變化稱為是單位農場勞動的“資本化”,與江南單位農場上勞動投入的“過密化”形成鮮明對照。[xxi]廣西的新農業體系和英國的諾福克制度相比較,都是投工少,在各自內部的組件都能相得益彰的農業體系。但兩者仍存在重大的差異:英國諾福克制度是一種高資本的農業體系,而廣西的新三位一體農業體系卻是低資本的農業體系。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并不象英國與江南是由于在勞工投入上的差距所致,而是廣西與英國的農業體系內部相得益彰的關系的差異。諾福克體系內部是農牧業之間的相互結合與協調,牧業可以為農業提供充足的畜肥和畜力,從而提高整個英國農業的資本化程度;而稻作——旱作——林藝體系從本質上說,仍屬種植業的范疇。旱作、林藝與稻作相結合主要是彌補了廣西農戶勞力少、資本少的缺陷,而且進一步使廣西農戶倚重于當地的自然資源。結果抵制了廣西農業向節約勞動的資本化方向的發展,而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也就成為泡影。其實,這正是廣西農業體系和小農經營中的最大一個弱點。
以上,圍繞150年廣西小農家庭農場規模效益的提高與不提高,做了詳細的個案分析與考察,并與江南、英國等地同期的個體農戶的相應狀況做了比較。對于廣西農民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生產遲遲未能實現快速、持續的增長這一問題,從上文的實證分析和跨地域比較中,似乎也能找到某些思考的線索。
[i]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0頁。
[ii]李閏華:《民族交往與近代廣西農業的發展變化》(未刊稿),為廣西師范大學歷史系2001屆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藏于廣西師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iii]陳春生:《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6頁。
[iv]楊乃良:《民國時期兩廣貿易交往及其對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廣西社會科學》2001年第一期。
[v]《說賑》下,《廣東文征》第30卷。
[vi]胡學林等著:《廣西經濟建設諸問題》,廣西省訓練團教材,1948年10月,第26頁。
[vii]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127~130頁。
[viii]千家駒:《廣西省經濟概況》,商務印書館,1936年,農業之部。
[ix]千家駒:《廣西省經濟概況》,商務印書館,1936年,農業之部。
[x]廣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編:《廣西各縣農村經濟狀況》,1925年,來賓部分。
[xi]摘自《廣西柳城等12縣農村經濟調查》,《廣西農業通訊》第2卷第7、8兩期合刊,廣西省政府農業管理處編印,1942年8月。
[xii]弋德華、李炳東:《廣西農業經濟史稿》,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1~311頁。
[xiii]弋德華、李炳東:《廣西農業經濟史稿》,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6頁。
[xiv]張先辰:《廣西經濟地理》,桂林文化供應社,1941年,第71頁。
[xv]徐毅:《近代民商與民族經濟開發——桂北湘南平地瑤的經濟特征》,《甘肅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xv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vi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viii]廣西壯族自治區編輯組:《廣西瑤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冊,廣西民族出版社,1987,第429頁。
[xix]弋德華、李炳東:《廣西農業經濟史稿》,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21~222頁。
[xx]M.Overton.AgriculturalRevolutioninEngl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AgrarianEconomy,1500~18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p.116~118.
[xxi]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叉: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AReviewofReturnstoScaleofFarmManagementinModernGuangxi
Abstract:Anormoffarmsizeof“afamilyworkstwelvemu”hadappearedandspreadinvillagesofGuangxisincemoderntime.Firstly,onthebasisoftheauthor’spastresearch,thepaperverifiesthechangeofreturnstoscaleoffarmer’scultivatedlandmanagement.Secondly,thepapercomparesfarmlaborproductivityinGuangxiwiththatinotherareasofChinaduringthesameperiodandthatinEnglandduringtheearlymodernperiodonthebroadmacro-perspective.Lastbutnotleast,theauthorinterpretsavarietyofconstrainedfactorshavingledtounderdevelopmentoffarmlaborproductivityinmodernGuangxifrombothmicroandthemacrolevels.
KeyWords:FamilyFarm,ReturnstoScale,LaborProdu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