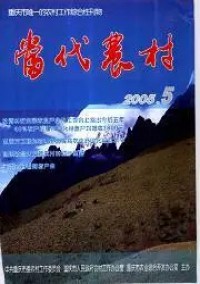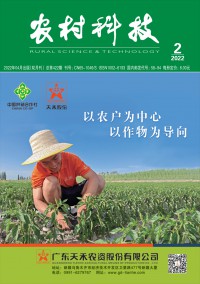農村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地區差異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村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地區差異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問題的所在
在過去十多年里,中國農村工業的高速增長改變了農村的社會和經濟面貌,而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對收入分布具有重要影響已成為共識。大部分研究結果認為,相對于農業收入而言,非農業收入的分布較為不均勻。而且,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在從總體上改善農民收入的同時,加劇了農民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在貧困地區。
既有的研究成果論證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例如唐平,1995;趙人偉等,1997;Rozelle,1996:ChenandFleisher,1996;李實等,1998;陳宗勝等,1999;萬廣華,1998)。有學者認為,收入分配不僅僅表現為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它同時又是影響甚至于決定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變量(李實等,1998)。可是,收入分配及其變化更多地表現為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就是說,制度變化因素和經濟發展因素構成了收入分配格局及其變化的直接和間接決定因素(李實、趙人偉,1999)。因此,筆者認為,如果中國農村收入分配出現不平等度擴大的結果,那無疑是制度變遷和經濟政策在執行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問題,或現有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著缺陷。
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和地區差異,以及農村非農收入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和作用進行認真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涉及的問題有: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布的現狀和特征如何,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國各省(區、市)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現狀、特征和變動趨勢是什么,等等。
二、文獻回顧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如果國家間收入差別是由各國資源的初始稟賦不同所造成的,那么,隨著各國經濟向平衡增長路徑收斂,這些差別會逐漸消失。換言之,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與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負相關關系,隨著經濟增長的趨同,落后地區最終將趕上發達地區(Barro,1998)。但是,也有學者對超過100個包括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并不存在一種普遍的絕對趨同現象(Ben-David,1998)。林毅夫等(1998)認為,改革以來中國的地區發展差異,比較突出地表現在三類地區之間。蔡昉等(2000)的研究結果也表明,中國在改革以來的地區經濟發展中,不存在普遍的趨同現象,卻形成了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趨同“俱樂部”。同時,中國地區經濟發展中存在著有條件趨同。
以庫茲涅茨假說為核心的理論則認為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兩會之間的關系表現為倒U型曲線: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收入差距會擴大,而后經過短暫的穩定,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收入差距逐步縮小。盡管有大量的學者利用截面資料或歷史資料對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做了進一步的論證,但是,這些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受到了另一些研究人員的質疑和批評(盧嘉瑞、陳永國,2001;彭玉生,1998)。王檢貴(2000)的研究表明,近年來,無論從經驗事實還是從計量方法上看,“倒U假說”都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許多捍衛“倒U假說”的文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懷疑。
在中國,關于居民收入區域差距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倒U假說”在中國成立與否和經濟轉型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展開的。陳宗勝的收入分配課題組和趙人偉的收入分配課題組分別利用不同的收入差距測度指標,不同的基尼系數計算方法和不同的數據來源,對全國總體上及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分別得出了改革開放以后,全國總體上及城鎮內部、農村內部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和發展中逐步擴大的結論(趙人偉等,1994;陳宗勝,1999;趙人偉等1999:陳宗勝等,2002)。
如果以收入分配差距的測算指標和計算方法來區分,泰爾指數方法,高鴻楨(1995)、魏后凱(1996)、李實等(1998)、張平(1998)、蔡昉等(2001)分析了全國不同區域或者不同人群組間的收入差距的變動狀況。根據基尼系數分解法,向書堅(1998)、陳宗勝(1999)、陳宗勝等(2002)分析了中國全體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基于不同的計算方法和利用不同來源的數據得出了兩種不同的基尼系數,可是,對研究方法和使用數據來源的認識上的差異,引發了兩方對收入分配研究的學術爭論(陳宗勝,2000;李實,2000;陳宗勝2002;李實,2002)。
盡管海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場出發,對中國居民收入區域間差異做過許多研究,但是,對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區域間差距進行深入研究的文獻少之又少。只有張平(1998)、萬廣華(1998)、彭玉生(1998)、蔡昉等(2001)、唐平等(2001)和張曉輝(2001,2003)等通過對抽樣數據的實證分析,對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現狀、區域間收入分配差異和形成差異的原因等進行了詳細分析。張平(1998)指出:既有的研究描述了農村區域間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分析了拉開中國農村區域收入差距的原因,認為農村非農化,特別是鄉鎮企業,是拉開中國農村區域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還有研究指出:非農收入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的分布存在著明顯的區域間不均衡。除了一類地區的鄉鎮企業收入占全年純收入的比重達到14.5%外,其他地區的這個比重分別只有4.6%,2.8%,1.3%(唐平、來維寧,2001;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2001)。由此看來,依靠發展農村非農產業來提高農民收入和解決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鄉鎮企業并沒有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在全國均衡地發展。特別是1998年以后,受國有企業改革、外資企業進入和城市民營企業發展的挑戰,鄉鎮企業在各個地區的發展極不平衡,這無疑是農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和數據來源
為了彌補既有文獻的研究缺陷和不足,同時,為了避免上述關于收入分配的學術爭論中所出現的由于對研究方法和數據資料的認識不同而發生不必要的誤解,本文采用統計分析的方法,利用Excel軟件處理數據得出基尼系數,研究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地區差異。與既有文獻通常局限于分析農村三大區域之間或者農村三大區域內部收入分配的差異有所不同,本文以省(區、市)為分析單位,詳細分析全國農村各省(區、市)間及各省(區、市)內部收入分配的狀況。
(一)指標說明
測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標有很多,比如舒爾茨系數、基尼系數、阿特金森尺度、泰爾指標等,本文將使用基尼系數來測定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1.基尼系數的計算模型。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很多,本文采用一種比較簡潔的方法,即將研究對象按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分成若干組,計算每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W;和人口比重Pi。
2.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的定義。雖然基尼系數可作為測定社會收入在社會各集團之間分配平均程度的主要指標,但是,由于基尼系數只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居民收入分配的狀況,相同數值的基尼系數可能表示極不相同的收入分配善,而且基尼系數數值易受收入人分組的影響而導致數值大小的變化,因此,用基尼系數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非盡善盡美。
在庫茲涅茨提出的“倒U假說”的基礎上,S·羅賓遜(1976)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論證庫茲涅茨“倒U假說”的一個僅含極少假設條件并且非常簡單的模型(王檢貴,2000;王韌,2003)。本文重新定義了該模型中變量的經濟含義,借鑒該模型分析省(區、市)內部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變動趨勢。即假定一省(區、市)內部非農產業居民和農業居民在農村居民總體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W1和W2,非農產業居民和農業居民的收入的對數均值分別為Y1和Y2,非農產業居民和農業居民的收入的對數方差分別為A2和A22,Y表示一省(區、市)的農村居民收入的整體對數均值,A2表示一省(區、市)的農村居民收入的整體對數方差。
眾所周知,一個群體內部成員收入的方差本身就表示了收入的離散程度,因而,方差經常用來測量群體內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方差愈大,表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愈高,反之則不然。將方差取對數后,這一性質不僅不會改變,而且有利于統計上求和。因此,本文將農村居民收入的整體對數方差(A2)定義為農村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用于測算一省(區、市)內部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的計算模型。中國農村經濟由農業部門和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部門組成,農村居民收入來源于農業部門和非農產業部門,因此,按收入來源不同可以將農村居民分為農業居民和非農產業居民兩大群體。因此,一省(區、市)的非農產業居民人口比重W1,和農業居民人口比重W2的關系為:
W1+W2=1(2)
如果一省(區、市)農村居民的總數為T,非農產業居民和農業居民的數量分別為T1和T2,每個居民的實際收入為M;則有:
因此,農村居民收入的整體對數方差為:A2=W1A12+W2A32+W1(Y1-Y)2+W2(Y2-Y)2(4)將(2)和(3)代入(4)中,可以消去W2得:
A2=aW12+bW1+c(5)其中,a=-(Y1-Y2)2,b=(A12-A22)+(Y1-Y2)2,c=A22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村中非農產業人口的比重將不斷增大,從(5)式可以得知,A2是變量W1的一個二次函數,由于a≤0,因此,該函數是一條開口向下的拋物線。
(二)數據來源
本文搜集了1996~2002年全國各省(區、市)農民收入分配的原始數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筆者計算基尼系數使用的是農業出版社公開發表的、由農業部統計的各省(區、市)農民收入分配的原始數據,這與《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按收入五分法計算的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據不同。同時,本文計算農村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使用的是國家統計局公開發表的、由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統計的全國分縣(市)社會經濟調查的原始數據。筆者在進行實證分析前,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村消費者價格指數(1985=100),對全部數據進行了處理,保證了所用數據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可比性。盡管存在誤差,但本文所采用的數據盡可能完整地代表了全國農村各省(區、市)各年農民收入分配的真實狀況。
四、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狀況和地區差異
(一)農村居民收入分布特征和變化趨勢
圖1(略)是1998年和2003年全國農戶收入總體分布圖。從圖1(略)可以判斷,全國農戶收入的對數分布表現為偏正態分布曲線,而非對稱的正態分布,這符合國際慣例。但是,全國農戶收入的對數分布曲線從1998年的負偏正態分布向2003年的正偏正態分布轉化,其特征表現為收入分布曲線從1998年的“瘦高”狀態向2003年的“矮胖”狀態轉換,表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農戶的數量在增加,半數以上農戶的家庭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戶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嚴重。
(二)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的變化趨勢
表1(略)是以農民人均收入的不同統計分組計算的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分別以縣、鄉、村為分組單位)。從表1(略)可以看到,以不同的統計分組所得到的同一年的基尼系數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按縣分組和按村分組的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的差距主要是由農民人均收入分組間距的大小不同而造成的。由于相同分組的各年之間的分組間距是相同的,因此,并不影響同一分組的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數的比較。從總體上看,1996~2002年,按縣、鄉、村分組的農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都表現出不斷增大的趨勢。換言之,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持續惡化之中,無明顯改善的跡象。其中,按村分組的基尼系數最大,從1997年的0.2742上升到2002年的0.3017。結論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李實等,2004)”農村的基尼系數反而有所下降,從1995年的0.381下降為2002年的0.366”的研究結果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與張曉輝(2001)和龔紅娥(2002)的研究盡管在數據來源和計算方法上存在著差異,卻是一致的。
(三)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和地區差異的比較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改革深入,農村居民收入應該出現不斷增長的局面。可是,1985年后,由于城市改革推進,城市就業機會增多,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城鄉居民的收入差別除個別年份有所縮小外,總體上呈擴大趨勢(宋洪遠等,2003;張曉輝2003;盛來運等,2003)。農民增收難,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更難(盛來運等,2003)。1997~1999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再次放慢。這期間,受國內外綜合因素的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回落,1997~199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分別增長4.6%、4.3%、3.8%,3年平均實際收入增長速度不足1996年的1/2(唐平等,2001)。而中央政策研究室和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2001)的研究則指出:對于家庭經營中非農產業不發達、種植業結構單一的糧食生產農戶來說,糧食價格不斷下降,成為增加農戶收入的主要制約因素。中部、西部地區農戶家庭經營收入下降是造成東部與中部、西部農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因素。但是,筆者認為,區域之間農業生產結構的差異和非農產業分布不均勻無疑對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影響,自然條件等要素的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也不應忽視。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急劇上漲造成生產成本上漲更是造成糧食主產區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不可輕視的重要因素。
表2(略)是全國(西藏除外)各省(區、市)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以村分組的基尼系數變化率。筆者提出用基尼系數變化率來判斷不同省(區、市)的基尼系數變化趨勢,希望對不同收入區域的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有一個全面了解和正確判斷。從表2(略)看,以聚類分析結果劃分的不同收入組的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存在著明顯的區域特征,而同一收入組內部各省(區、市)基尼系數的大小也不盡相同。在高收入區,北京、上海和浙江的基尼系數變化率明顯偏高,江蘇、廣東與其他高收入省(區、市)相比較,收入分配的變化跡象較小,而福建和天津的收入分配則出現明顯的惡化傾向。在中等收入區,只有吉林和海南的基尼系數明顯縮小,其中,吉林的變化率為28.21%,引人注目。湖北、安徽的基尼系數變化率在2%上下波動,尚無明顯改善的跡象。而該收入區的其他省(區、市),除廣西外(廣西也是中國的大米主要生產省之一),全屬于農業部設定的糧食主產區,其中,既有鄉鎮企業發展先進的山東、遼寧,也有傳統糧食主要生產省黑龍江、江西、河南和湖南,還有小麥主產區內蒙古。
相對于中等收入區的糧食主產區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惡化的傾向,低收入區的西部傳統貧困省(區)的收入分配則出現明顯改善的傾向。除了山西、新疆和青海的基尼系數變化率分別為-12.35、-7.71%、-13.38%外,寧夏、陜西、云南、貴州、甘肅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都引人注目。對此,至今尚無有文獻專門報告過。因此,分析這些省(區)收入分配明顯改善的原因,對于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的開發和西部地區扶貧政策的實施有著重要意義。貧困地區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的改善究竟是至今為止所實施的扶貧政策和退耕還林政策的效果,還是非農產業落后地區農民外出打工收入增加引起收入結構變化的效應,尚有待今后的調查研究。
綜上所述,在農業部核定的13個糧食主產區中,除了吉林和四川的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有顯著的改善外,江蘇、湖北和安徽表現出不明顯改善的跡象,其余省(區)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則有明顯惡化的傾向。從總體上來看,高收入區和低收入區的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明顯改善的傾向,而中等收入區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則表現出日益惡化的傾向。
圖2(略)表示了1997年和2002年中國(不含西藏、臺灣、香港、澳門)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與基尼系數的關系。由圖2(略)可以知道,目前在中國農村,基尼系數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間還不存在明顯的倒U型關系。換言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農村居民沒有出現收入差距縮小的跡象,相反,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不斷擴大。
(四)中國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和地區差異的比較
農村居民收入可以分為農業收入和非農產業收入,由于農村分區域的農業收入和非農產業收入無法得到,本文以分區域的農村的農業增加值和非農產業增加值作為農業收入和非農產業收入的代替值。在不考慮人口流動的情況下,一個地區扣除農業增加值以外的農村GDP是由該地區農村中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村居民創造的。根據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計算模型,可以計算出2002年全國農村總體及各省(區、市)的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本文在計算進使用了國家統計局公開發表的由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統計的全國分縣(市)社會經濟調查的原始數據。根據計算結果分析,2002年,中國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和中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相關系數R2為0.3865,說明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與經濟發展間不存在比較顯著的關系。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在各省(區、市)間存在顯著差異(見圖3(略))。從全國范圍來看,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最高的是上海和浙江,分別達到了1.059和1.22,最低的是安徽和江西,分別是0.232和0.286。與表2(略)中基尼系數的地區差異相比較,可以發現,各省(區、市)農村居民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的地區差異顯著大于各省(區、市)基尼系數的地區差異。
將全國30個省(市、區)(因數據收集原因,臺灣、甘肅不包括在內)劃分為與表2(略)相同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類地區,從圖3(略)的結果可以發現,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在三類地區間存在明顯差異,而且,在同類地區內的各省(市、區)之間也表現出了分化的特征。在高收入組,北京、江蘇、福建的農村居民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明顯低于同組的天津、上海和浙江,農業收入和非農產業收入的差距可能是造成這些省(市、區)農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在中等收入組,黑龍江、吉林、河北的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明顯大于同組的山東、遼寧、海南、湖北和內蒙古。在低收入組,四川、山西、青海、陜西的農村居民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明顯大于同組的其他地區。可見,影響中國農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盡管非農業收入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存在著明顯的區域間差異,但是,同屬于糧食主產區的各省(市、區)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又表現出明顯分化的特征,其中的原因尚待今后的調查研究。
五、研究結論
根據以上關于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和區域之間差距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研究結論:
第一,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對數分布曲線從1998年的負偏正態向2003年的正偏正態轉化,表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農戶的數量在增加,半數以上農戶的家庭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戶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嚴重。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二,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狀況在持續惡化之中。目前在中國農村,基尼系數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間還不存在明顯的倒U型關系。
第三,在糧食主產區中,除了吉林和四川的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有顯著的改善外,江蘇、湖北和安徽表現出輕微改善的跡象,而其余省(區)則有明顯惡化的傾向。從總體上來看,高收入區的北京、上海和浙江以及低收入區的寧夏、陜西、云南、貴州和甘肅的農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明顯改善的傾向,而中等收入區的糧食主產省(區)的農村則表現出收入分配日益惡化的局面。
第四,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在各省(市、區)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從全國范圍來看,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最高的是上海和浙江,最低的是安徽和江西。
第五,同屬于糧食主產區的各省(市、區)的農村居民的總體收入不平等指數表現出明顯分化的特征,其形成原因尚待在今后的調查研究中通過實證分析加以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