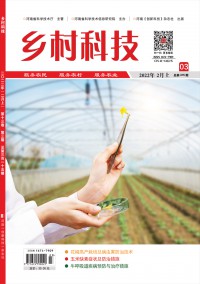鄉村管理文化轉換思路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鄉村管理文化轉換思路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由于海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明清時期的潮州地區已發展成為全國的富庶之地,為保證財源的穩定供給與政治上國家大一統的需要,清代中央政府加強了對這一海疆難治地區的管理,尤其是廣大而分散的鄉村社會。
(一)縣衙設置與分而治之
“民非政不治,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常相為用矣”[2](船7),縣衙處在政治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交匯點上,其自身完善與否對鄉村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與前代一樣,潮陽縣衙的基本構成亦是三班六房,此外另設有號房、刑杖房、庫房、承發房,實為“十房”之設。縣衙內部官員主要包括知縣、縣丞、典史、教諭、訓導等[3](P35)。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清代如此大縣竟沒有“主簿”之設,卻保留著“縣尉”一職[4](5);其二,一縣設有三個巡檢司署:召寧、吉安、門嗣[31(P36),巡檢司署如此之多。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對這一難治之地的高度重視。普寧縣為小縣,縣衙中自然不設縣丞一職。值得注意的是:其一,普寧縣雖為小縣(轄三都時),卻設有云落巡檢司署[53(P229),由此可知,當地也不易治理;其二,典史的職責。明代典史的職責是掌管文移出納,清代則演化為稽察獄囚、負責監察。普寧縣因為不設主簿、縣丞等知縣屬官,典史的職務就更為繁重,不僅帶領眾差下鄉辦事[4](P397),而且也從事圍捕海盜的行動[4](P384);其三,幕友之設,史載:“幕友不能平,勸申文與之辯。”[4](P395)為加強潮陽地區的管轄,清初中央政府在前代分而治之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調整。史載:“世宗嘉靖四年,析潮陽置惠來。邑故所統地,民依險阻,多逋,負宏治末,流賊劫掠。正德七年,巡按御史熊茼,因耆民方宗珙等呈請,奏增縣治以彈壓之,至是分置惠來縣。四十五年,復析潮陽置普寧。而析潮之洋烏、誠水、黃坑三都置縣,日普寧。神宗萬歷九年,洋誠二都,復歸潮陽。”C3](P29)僅剩一都的普寧縣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知縣藍鼎元指出:“但潮陽、普寧接壤,要害之處在貴山、誠水,不在洋烏。惟是綏靖地方,必從吏治民生起見,則潮普割都分治之舉,確不可易。而貴山半都之宜割,洋烏大半之宜仍舊,尤確乎不可易也。”[4](P63)由于后一舉措十分不利于地方治理,清朝初年經中央批準,普寧縣疆域再次調整:“至雍正十年,巡撫楊題準將潮陽之減水一都八圖,貴山之下半都五圖,洋烏都之尾一設一圖,俱割歸普邑,共計一都一十四圖,合黃坑一都一十四圖,實有都四,為圖二十有八。”[5](P1o7)
(二)中央政府對地方知縣的任用
鄉村社會的治亂與本地區縣官群體的施政狀況密切相關,史載:“牧令為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系百姓之休戚,故自古以來慎重其選。”[6](P1)以潮陽縣為例,拙文從出身、任期、籍貫三個方面考察中央政府對知縣的任用。潮陽縣知縣的出身有兩個特點:其一,出身繁雜。有清一代,這一地區的知縣總共有12種出身,它們分別是供事、歲貢、拔貢、副貢、監生、增生、廩生、附生、生員、吏員、舉人、進士[3](P198—200),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知縣來源的多元化。其二,知縣出身以舉人、監生、進士為主。光緒《潮陽縣志》所載120名知縣,舉人出身的有31人,監生有20人,進士有l4人,其它出身均為數不多,其中無記載的有8人,出身從九品的一人[3](P198—200),舉人、監生、進士三者之和約占總數的65%。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下,潮普地區知縣出身較低。據“康雍乾時期61縣知縣出身統計表”所知,三朝時期的61個縣中,舉人與進士出身的知縣所占比例分別為40.3%、44.2%、52.5%,而潮普地區舉人與進士出身的知縣所占比例為37.5%。據民國《內鄉縣志》載,清代河南省內鄉縣歷任知縣113人,除30人出身記載不詳外,其余的83人中有進士l6人,占20%,舉人37人,占44%,其它監生、貢生、拔貢等30人,占36%[7]。固然,出身高并不一定代表能力強,如清代普寧縣十一名著名知縣中,無一名進士,僅有兩名出身于舉人,其它分別出身于貢生、拔貢、供事、例監、吏員、歲貢[5](P250—252)。然而,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央對邊疆的重視程度不如腹地,這無疑成為地方社會難治的原因之一。潮陽縣志所載120名知縣,從順治八年(1651)至光緒十年(1884)時間跨度總計223年,如此之下,這一地區知縣的平均任期不到二年。與清代知縣平均任期2.5年相比[8](P31),這一地區知縣的任期普遍較短。由此看來,雖然這一地區頗為難治,然而知縣任期卻明顯短于全國平均水平,這種狀況極不利于本地區的社會治理。眾所周知,“欲盡吏職非久任不可”[9](P9),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地方社會的難治也有來自中央政府人為的因素。有清一代,潮陽縣有沿海背景的知縣總共10人,分別來自浙江、江蘇、廣東與福建,其它絕大多數來自內陸地區,其中包括一些旗人[3](P198—200),這固然是回避制度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潮陽縣最為有名的三位知縣:藍鼎元、吳均、臧憲祖均來自東南沿海地區,藍鼎元是福建漳浦人,吳均是浙江錢塘人,臧憲祖是廣東廣寧人,而且藍、吳二人位列《清史稿》“循吏傳”[10](P]3010),成為有清一代的名宦。這似乎告訴我們,出身海疆地區的官員在沿海地區做官更容易政績突出。由此看來,雖然清代中央對這一難治之地也設縣治理,然就知縣的任用而言措施反而不力,此種情形之下,潮普地區鄉村社會的難治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地方基層官府對鄉村社會的管理
在清代潮普地區,作為政治國家的象征與最基層的官府,縣衙及其派出機構巡檢司署行使著管理鄉村社會的各項職能。
(一)縣府對鄉村社會的管理縣府在潮普地區推行都、圖的行政區劃,以利鄉村社會的管理。潮陽縣共“十三都圖。縣郭都九圖,坊長六,民里三。附郭都七圖,俱民里。峽山都十九圖,糧里六,民里十三。黃龍都十一圖,糧里三,民里八”[3](P40),普寧縣“都四、圖二十八、社三。黃坑都,十四圖,上中下三社,就十四圖分計四百鄉寨。減水都八圖,計一百三十余鄉寨。貴山都五圖,計九十余鄉寨。洋烏都一圖,計三十余鄉寨”[5](P107)。由此看來,潮陽縣糧里、民里劃分明確,而普寧縣又有“社”的設置。為確保錢糧征收,兩縣都加強版籍管理,縣志詳細記載了戶口、土田、賦役、科則等項事宜。當然,這一地區難治也與此有關,例如潮陽縣“時務,惟在版籍混淆,地畝不清。有田無糧之弊,累靡終極”[4](P249)。潮普地區的約保體系主要由約長、鄉保與鄉長組成,縣府設籍對約保嚴格管理。史載:“按十三都約保名籍,吏唱馬鳴山不到。余(知縣藍鼎元)佯怒日:‘無禮哉,此不到者皆賊也,當捕至。⋯Eel(17425)當地約長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約長不僅設籍管理,而且由縣府直接任免,趨于職役化。史載:“此梅花鄉訟棍,無所不為者。曾充鹽埠,販私鹽起家,復充約長,充保正,皆遭斥革。”[4](P442)學界對此也有關注:“在鄉約的發展過程中,民間性是一貫的,但與官府的關系呈現出日益密切的傾向”[11],乃至“清政府則將其民間性轉變為官方化、制度化”[12](P75)。其二,“總約長”之設。史載:“魏令君(知縣)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號曰總約長,仕鎮益驕橫,無所畏。”[41(P42''''3)由此可見,總約長在當地鄉村社會擁有很高的地位。鄉保的設置因地區而異。例如有學者指出:“(兩湖地區)鄉約一般按保而設,管轄區域基本相同,因此往往將兩者合稱為鄉保。”[12](P75)然而潮普地區的鄉保、約長是按“都”而設[4](P425),且鄉保是指一個人。史載:“遍詢鄰居陳孫典、房族劉紹萬、劉國來、劉文忠,鄉保楊鼎顯,則公喜肅守分。”[4](P421)由于約長、鄉保合稱為約保,這里的“鄉保”一詞可能是“保正”的另一稱呼。此外,潮普地區鄉村社會也有“水保”,史載:“過林八渡,為水保方東升所獲,連舟擒捉以去。”[43(P424)有關當地“鄉長”,史載:“次日回報,龍頭鄉并無其人。命曳下鄉長夾訊之。鄉長乃言。”[4](P395)據乾隆《普寧縣志》載,龍頭為普寧縣貴山都三圖下的一個村[51(Pll1)。由此看來,“鄉長”即是“村長”。這一結論得到多處史料的佐證,如史載:“其人日:‘須問鄉長’。即遣役喚棉花村鄉長。”[4](P415)這里的鄉長管理一個村,相當于“甲長”,這說明這一地區有可能以村為單位進行保甲編制的。為加強鄉村管理,清朝十分重視社會教化。在落實這一政策方面,潮普地區可謂表率。雖然宗教管理機構僧會司、道會司都已久廢[3](P37),然而當地仍保存著完整的教化系統,這主要包括縣學、書院、義學、社學等組成的教育體系,名宦祠、鄉賢祠、忠義孝悌祠、節孝祠、坊表、廟、壇等組成的祭祀空間,以鄉飲酒禮為象征的“重民、親民”儀式等[3](Pl5)。不僅如此,而且縣府一再加強鄉約所的建設。如普寧縣“雍正八年,奉文設立約所。乾隆二年,復奉文又添設。今一在城隍廟,一在上社鯉湖隱陀庵,一在中社湖東花菜寺,一在中社大塌墟,一在下社新橋庵,一在下社廣平墟,一在塘邊公館,一在溪東仔墟,一在貴嶼寨雙忠廟”Es](P135)。一個小縣只鄉約所就達九處之多,由此可見縣府對民眾教化的重視。此外,縣令捐建、創建、與紳民共建的育嬰堂、養濟院、癩民所、養阡所等[3](Pl13)也兼有社會教化的功能。
(二)巡檢司署對鄉村專區的管理有學者指出,“(清代)縣級衙門并非皇朝統治的終點,巡檢司署等基層官署是相當一部分州縣中位于縣級行政衙門與村落之間的重要行政官署”,[13]潮普地區即是如此。以潮陽縣三個巡檢司署為例(桑田巡檢司順治十七年被裁減,故不在計算之內),筆者從三個方面予以考察。首先,駐地與品級。史載:“招寧巡檢司署在縣東招收都達濠城,門嗣巡檢司署在縣北直浦都關埠,吉安巡檢司署在黃龍都峽山埠。”[3](P36)三巡檢司均設在潮陽縣“重地”,掌控著以都為轄區的鄉村社會。品級方面,盡管縣志中許多巡檢沒有官品記載,然而學界對此基本達成共識,認為其品級為從九品[14](Pl13)。其次,出身與任期。由于官品最小,三個地區巡檢的出身低微且多樣化,這其中包括吏員、司獄、貢生、監生、廩貢、附生、武生、供事等,然總體來看,當地巡檢多出身于吏員與監生,藉貫遍布于大半個中國[3](P209—212)。當地巡檢的任期自半年至十幾年不等。然總體來看,當地巡檢任期三年左右者居多,而且愈往清代后期,其任期愈短[3](P208—212)。第三,司署與職權。巡檢司署在人員配備上都是一樣,除長官巡檢外,另有一名書吏、兩名皂隸,弓兵若干[3](P130—131)。巡檢主要是維護轄區治安,“掌緝捕盜賊,盤詰奸偽,凡州縣關津要害并設之”[15](P2211),同時也調解民間糾紛、進行社會救濟、教化轄區民眾等,從而協助知縣工作。例如梅元,“康熙二十一年為云落司巡檢,至則編戶口冊,一街一巷,必于隘口設柵,以街中人司之,計戶值宿,周而復始。又令各舉老成者,命街長,使董一街之事。月之朔望,集紳耆講誦六箴,畢即按冊躬履清查”[16](P393)。巡檢司署不僅設在鄉村管理的重點地區,有固定的治所與轄區;而且巡檢為知縣屬官的同時,也是朝廷命官,有朝廷封印與品級,有自己所屬吏員、皂隸與兵丁,巡檢與知縣的關系近似知縣與知府。我們覺得,巡檢司署是潮普地區鄉村管理中相對獨立的最底層行政官署。潮陽一縣設有三個巡檢司署,僅有三都的普寧縣也設有一處巡檢司署,這使得官府的統治延伸到“都”一級的鄉村,由此可見官府高度重視這一地區的治理。當然就實際效果而言亦不盡然,例如史載:“群賊橫行莫當,一日數犯不諱,善良受害,何可勝言。半由潮屬三年荒欠,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風”[4](17393)。
三、民間社會的自我管理
盡管設有縣衙與巡檢司署這些官方管理機構,然而,這種治理僅是官方為完成考成之責而對鄉村社會進行的宏觀管理,在廣大而分散的潮普地區鄉村社會里,民間權威以各種方式發揮著自治的功能。學界對此多有探討,這里僅以“族議”、“規約”為例。鄉寨是潮普地區村民的主要居住形態,普寧縣“鄉村人家皆鱗次環聚而處,日某寨。寨雖小,必有書館,延師以課童子”Es](P395),潮陽縣馬氏“故巨族,其丁男兩千有奇,分三寨鼎足而居”[4](P422)。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人們,來自不同的籍貫、信仰、語系與時代,面臨著來自陸海的各種威脅,這種情形之下,筑寨自保、聚族而居就成為歷史的必然,相應之下,宗教內部自治性突出,這集中體現在“族議”的社會調理功能方面。史載:“(知縣)藍鼎元方理堂事,見儀門之外,有少婦扶老嫗長跪其間,手展一楮戴頭上。遣隸役呼而進之。則老嫗鄭氏,年八十六矣。(經過藍鼎元的嚴審),阿梅服曰:‘是也,阿梓乃我從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索找田價,我不依,彼一時短見,服毒圖賴’。族中李晨、李尚諸人,勸我代為殯殮’。鄭氏日:‘原約兩間房屋,永為棲身,今拆去瓦桷,置我婦姑于何地?且公議贍養一年,今尚少四月,李阿梅遂昧良心乎?”’[4](P3S6)在李阿梅愿意遵守族中“公議”的情況下,藍鼎元作出最終處理,“從寬令其(李阿梅)修屋給米,免行笞杖,俱各和好如初”[4](P386)。知縣藍鼎元對“族議”的維護無疑是對宗族裁決的一種尊重,這不僅使民間權威得到官方的認可,而且官府也可以省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在潮普地區鄉村社會里,各種地方勢力不僅顯示出強烈的內聚性,而且還張揚著濃烈的排外意識,這種歷史上形成的民間心理認同,在官府看來,則是“負氣喜爭,好勇尚斗,睚眥小嫌,即率所親而哄,至以兵刀相格,如臨大敵。強者凌弱,眾者暴寡。歃血拜盟之風,村村仿效。世家大族,輕蔑孤姓,呵斥之若童仆之不如”[4](P295—296)。此種情形之下,協調各種力量的鄉規民約就顯得十分重要。史載:“延長、埔上、塘子等鄉,輪流以灌溉其田。八九月之間旱,江、羅兩家侍強眾,紊規約,不顧朔日為楊家水期,恣意桔槔。楊仙友不服,操刀向阻,弟兄楊文煥、楊世香隨之。羅明珠奔回告其鄉老江立清,號召鄉眾荷戈制梃,環而攻之。眾寡不敵,仙友奸焉。”[4](P381)在刑罰用盡仍以不知抵塞的情況下,藍鼎元巧用楊仙友的“幽魂”對質,最終找出了殺人兇手,藍鼎元“即將江子千、江立清諸人,按律定擬,解赴大吏”[4](P382),一場嚴重的械斗命案最終告破,民間規約在官威之下繼續得以遵守,鄉村社會的用水秩序得以恢復。
四、中央與地方、官府與民眾的對立和相得
在潮普地區鄉村管理實踐中,由于諸多歷史與現實因素的相互影響與制約,官府與民眾、中央與地方不時地上演著一幕幕既對立又統一、既相得又相補的歷史話劇。
(一)中央與地方的對立與統一
潮普地區(普寧、潮陽兩縣)在廣東省潮州府境內,屬于山海一體下的邊疆移民社會,人口眾多,這種社會生態環境、海洋發展的歷史傳統、明清以來世界橫向發展所導致的外部吸引等諸多因素,使得這一地區保持著“外傾式”海洋發展的趨向。而政治國家的遷海、禁海、武裝鎮壓等導致的逆反心理,卻又強化了地方社會反抗中央而走向海洋發展的傾向,乃至泛化為一種穩定的區域心理。在這一海疆鄉村社會里,地方勢力、海洋貿易與民間信仰三位一體形成與中央政府的對抗,釀成“難治”的歷史格局。在這方面,中央政府與地方勢力對潮陽縣西南地區控制權的爭奪即是明證。史載:“馬氏故巨族,仕鎮豪雄獷悍,尤為馬氏之冠。捐貲作太學生,自是儼然士林,群盜不復日大哥,而共稱為馬老爹矣。馬老爹之名震潮郡,撫按承差,道府胥役,皆潛與往來。拘之三十有四年不能獲。或設法籠絡之。彭令君以五都錢糧,委之征收,仍攘竊如故,且侵欺科派,無所底止。支令君赫然振怒,移檄守將,親詣仙村擒捕之,仕鎮命三寨皆閉門據守,支令君憤恨不能已。上官左右皆馬氏腹心,且反于支令君督過,不得不渙然冰釋。仕鎮威震惠潮,莫敢有萌擒捕之想者。魏令君以西南地方,委之看守,號日總約長。”[4](P423)由此看來,馬仕鎮依托強大的家族勢力、士人的身份,通過廣泛的社會交往,尤其是買通上司,其勢力盤根交錯,儼然發展成為一方割據力量,地方官府對其只能采取羈縻政策,從而暫時使得中央與地方利益獲得統一,僅是在形式上維持著國家大一統的政治格局。雖然知縣藍鼎元利用計謀將其緝獲,然而“經一年又逾兩月,仍未咨革監生,而余(藍鼎元)以奉參離任”[4](P425),出獄后的馬仕鎮重新掌握了潮陽西南地區的控制權,“吾友很余(藍鼎元)不將馬仕鎮撲殺,若使巨奸逸罰,則貴山都百里內外,遭其殃害無有已晴,不知誰之過也”[43(17426)。
(二)官府與民眾的對立與相得
據史料記載,清代潮陽縣120位知縣中,被革職的有七位,分別由于貪婪、未完錢糧、荒淫貪酷、受累、貪污、魚肉士民而激起變亂[3](P199)。他們統治時期,官府與民眾可謂是勢不兩立。與此相反,清代潮陽縣出現的循吏共有八位[3](P262)。毋庸諱言,“失職”知縣與循吏治理下的鄉村社會都不是歷史的常態,長期治理潮普地區廣大鄉村的是那些占絕大多數的“中性”之吏。此種歷史情形之下,官民之間的相得與相補即成為一種必然。簡言之:其一,以官治民。例如,臧憲祖“康熙二十一年由監生任潮陽知縣,廉明慈惠,興革悉當。時屆戶口紊亂,無籍可考,民苦虛糧之累,憲祖編額維均,一清夙弊。濱海多斥鹵地,民以肩挑為生涯,暖丁屢奪之,憲祖為劑其平。又倡義塾,請豁免行追雜稅”[33(P261)。此外,臧憲祖在“康熙二十四年始建義學,康熙二十五年捐俸續建文廟,康熙三十年鼎建文昌廟”[3](P175)。由此看來,知縣臧憲祖施政期間,其鄉村治績主要有均錢糧、免雜稅、治矚丁、修建義學與文昌廟等,這些政績涉及到了知縣傳統的三大職責:錢谷之責、教化之責與治安之責,可謂以官治民的典范。其二,民助官治。例如在鄉村社會教化實踐中,知縣藍鼎元意識到,“余不佞,不能家喻戶曉,惟有隨事誘掖,樹之風聲,使知孝悌仁讓,則所望于諸生助我者非細也”[4](P197)。鄉村建設方面,知縣藍鼎元深感受官府力量的單薄,“有棉陽書院,于普豈可無文明書院。但土木之興,工程浩大。清河筑塔,建高閣而開書院,自笑清俸無幾,未免有蚊力負山之虞,余敢不與斯邑縉紳先生、好義樂施諸人士共之”[4](en4)。上述事例鮮明地體現出民助官治的必要與必然。其三,官民共治。在潮普地區鄉村管理的實踐中,官民之間合作共事也是十分常見。史載:“汪公臨此,普邑既輕徭役,除積弊,厥績有成。乃慨念學宮廢壞,明倫堂未建,士子末由肆業于是。會商掌鐸,彭公司訓、潘公大加,創葺工財,慵值一切各出俸資,絕不以擾民,而民咸樂為之。使不日而告成,期間拮據經度,則彭公實任其勞。”[5](P403)教育是大事,也是地方官府治理鄉村社會的重要手段。汪公上任以來推行一系列惠政,這使得百姓受益的同時,自己在地方社會也樹立起權威,接著本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這位知縣倡導官民共建學宮、明倫堂,這種官民合作的方式不僅解決了大興土木的難題,而且使“民咸樂為之”。有關官民合作治理領域,有學者提出了“共域”理淪,“在官方自域與民間自域之外還存在著廣大的共域,像納稅、孝悌、財產、婚姻、繼承、偷盜等內容,因直接關系到國家的治理、社會的秩序、地方的治安,也是國法始終予以規范的。這些方面便屬于官民‘共域’的部分,其中亦多體現出官民的共同參與”[17]。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顯示出今人對古代基層社會管理的反思與重視。
雖然清代廣東潮普地區鄉村社會管理僅僅是一個個案,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不僅引領我們走向歷史、檢視傳統,而且又使我們回歸現實,反思現代,探求鄉村管理傳統文化現代轉換中的變與不變。明清時代,我國東南海疆地區之所以難治,其根本原因在于過于“自衛”的國家海疆政策違背了時展的大勢,阻礙了海疆近代化早期向海洋用力的外傾式發展,“難治”的深層意義是一種針對地方的國家話語,而潮普地區無疑成為這一歷史時期整個東南海疆的一個縮影。在清代潮普地區鄉村社會里,盡管存在著中央與地方在海洋發展方面的抑制與反抑制,盡管存在著管理政策與管理實踐方面的種種失誤,盡管存在著為數不少的貪官酷吏,但是中央政府與地方基層政權仍然進行著一定程度上的有效管理,尤其是四個巡檢司署的設置,將國家政權對社會的管理深入到“都”一級的鄉村,可謂特殊地區特殊管理的典范;另一方面,在基層官府默認或有意引導的情況下,民間力量的積極參與使得官民之間實現了相得與相補的治理格局。為此,盡管清代潮普地區鄉村社會頗難治理,但是始終未發生劇烈動蕩,基本上保持了穩定發展。
“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今天,我們理應汲取清代廣東潮普地區中央、地方與民間共同參與的立體治理機制的歷史經驗,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國家與鄉村、官與民三種基本關系,在復雜多變的現實管理實踐中,努力實現多種二元關系之間的相得與相補,努力實現鄉村社會管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進而言之,我們一般認為,傳統鄉村善治的基本內核乃在于中央與地方、國家與鄉村、官府與民眾三種基本關系的良性運作,亦即中央、地方、民間三者的共同管理且相得與相補。當今,盡管鄉村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遷,鄉村管理體制、結構、機制與模式與以往大相徑庭,但這一基本內核仍然沒變,此即鄉村管理傳統文化現代轉換中的變與不變。當然,鄉村管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研究是一項復雜而系統的工程,其內涵絕不是上述那么一點,這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