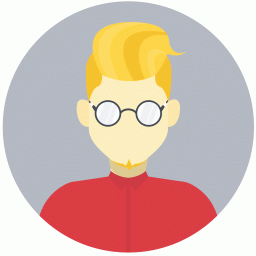商業(yè)新業(yè)態(tài)隱性功能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商業(yè)新業(yè)態(tài)隱性功能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進(jìn)入21世紀(jì)后,中國(guó)城市迎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商業(yè)消費(fèi)變革,而這種變革的重要標(biāo)志就是源自西方的以大賣場(chǎng)、超市、便利店等為代表形式的商業(yè)連鎖新業(yè)態(tài)的迅速崛起,這些“新業(yè)態(tài)”所體現(xiàn)出來(lái)的以人為本的經(jīng)營(yíng)模式、服務(wù)理念產(chǎn)生的資源整合以及消費(fèi)文化出新、生活方式引導(dǎo)等“隱性功能”,不僅悄然“型塑”了人們的消費(fèi)行為,還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cè)谙M(fèi)場(chǎng)所及其它社會(huì)公共場(chǎng)所的行為方式和價(jià)值取向,提升了當(dāng)代城市人的文明水準(zhǔn)。
對(duì)城市社區(qū)服務(wù)的無(wú)形延伸
對(duì)于變動(dòng)中的社會(huì)的認(rèn)識(shí),社會(huì)行動(dòng)者有意安排的、人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預(yù)期后果”,可以看作是某些事物的“顯性功能”的體現(xiàn),而其不為一般人所察覺的、內(nèi)在的、潛在的作用,需要通過(guò)比較、深化才能發(fā)現(xiàn),即是其“隱性功能”的體現(xiàn)。(注:宋林飛:《西方社會(huì)學(xué)理論》,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頁(yè)。)在現(xiàn)代消費(fèi)社會(huì),商業(yè)新業(yè)態(tài)的“顯性功能”主要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交換”上,而其隱性功能則主要體現(xiàn)在“社會(huì)交換”新時(shí)空的打造上。
當(dāng)前在中國(guó)城市迅速崛起的商業(yè)零售“新業(yè)態(tài)”,其產(chǎn)生、發(fā)達(dá)的土壤是現(xiàn)代西方消費(fèi)社會(huì),“新業(yè)態(tài)”構(gòu)建的消費(fèi)者、消費(fèi)媒介以及整體社會(huì)系統(tǒng),都具有“現(xiàn)代性”的特征。我們無(wú)法想像,假如沒有社會(huì)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性”,靠大規(guī)模連鎖和信息技術(shù)支撐、踐諾經(jīng)營(yíng)模式和服務(wù)理念的沃爾瑪?shù)攘闶劬揞^,怎么會(huì)有今天的規(guī)模和影響力。基于這樣的認(rèn)知,來(lái)分析“新業(yè)態(tài)”及其映射的消費(fèi)行為,就有助于我們清晰發(fā)現(xiàn)其“隱性功能”。由于“隱性功能”不像“顯性功能”在系統(tǒng)的表面直接顯現(xiàn),而是隱藏在系統(tǒng)的深層結(jié)構(gòu)中或者與相鄰子系統(tǒng)的交匯區(qū)域,前者比后者距離社會(huì)生活的常識(shí)性知識(shí)更為遙遠(yuǎn),觀察者就不僅要“睜大眼睛”往深度觀察,同時(shí)還要運(yùn)用分析、比較、聯(lián)想等抽象思維方法和概括能力,進(jìn)行綜合探討。如果說(shuō)“新業(yè)態(tài)”的“顯性功能”較多地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性”——直接的消費(fèi)功能方面,那么其“隱性功能”則較多表現(xiàn)在“社會(huì)性”和“文化性”——間接的福利功能與符號(hào)功能方面。這實(shí)際上也表明,在整體社會(huì)系統(tǒng)中,消費(fèi)的子系統(tǒng)一方面是發(fā)揮著商品供應(yīng)的直接功能,另一方面又在不停地作用于相鄰的子系統(tǒng)和整體系統(tǒng),在“顯性功能”與“隱性功能”的同步發(fā)揮中促進(jìn)整體系統(tǒng)的均衡、可持續(xù)運(yùn)轉(zhuǎn)。
“新業(yè)態(tài)”的高度“控制性”,是充分體現(xiàn)在“顯性功能”方面的——消費(fèi)者進(jìn)入其中從存包到乘電梯進(jìn)入商品區(qū),從推著手推車自選商品到最后在出口處結(jié)賬——這種單純的買賣過(guò)程是事先設(shè)定好的程序,而且同一個(gè)連鎖組織下所有的門店都是一個(gè)模式。對(duì)這種被“控制性”,筆者曾以美國(guó)當(dāng)代社會(huì)學(xué)家喬治·里茨爾的“麥當(dāng)勞化”為基礎(chǔ),提出了現(xiàn)代人消費(fèi)的“沃爾瑪化”命題。(注:消費(fèi)行為的“沃爾瑪化”是筆者在2004年9月出版的著作《城市商業(yè)新業(yè)態(tài)與消費(fèi)行為大變革》(東南大學(xué)出版社)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主要指城市居民在大賣場(chǎng)等新業(yè)態(tài)空間實(shí)施購(gòu)物過(guò)程中的受控制性行為,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shuō)是當(dāng)代社會(huì)“麥當(dāng)勞化”的進(jìn)一步延伸。對(duì)于“沃爾瑪化”的概念,經(jīng)濟(jì)學(xué)界和管理學(xué)界通常還有另外兩種共識(shí):一是對(duì)員工應(yīng)當(dāng)享有的社會(huì)福利的剝奪,二是指對(duì)供貨商的剝奪以及對(duì)城市社區(qū)商業(yè)平衡的破壞。截至2005年5月,沃爾瑪已在中國(guó)開設(shè)了46家賣場(chǎng)。另?yè)?jù)美國(guó)《財(cái)富》雜志2005年7月15日公布的全球“財(cái)富500強(qiáng)”最新排名,按年度運(yùn)營(yíng)收入計(jì)算,商業(yè)連鎖巨頭美國(guó)沃爾瑪公司以2879.89億美元的年?duì)I業(yè)額連續(xù)第四年蟬聯(lián)榜首。)
“沃爾瑪化”在控制家庭消費(fèi)的同時(shí),其所具備的“控制性”又對(duì)眾多家庭起到了福利功能,只不過(guò)這種“福利功能”并不是商家本來(lái)要達(dá)到的目的,而是在行動(dòng)過(guò)程中產(chǎn)生的一種連帶性的結(jié)果。同樣,在當(dāng)今中國(guó)城市,“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本”的“新業(yè)態(tài)”的經(jīng)營(yíng)與服務(wù)定位,就決定了其在鄰里、社區(qū)乃至城市大區(qū)域的公共服務(wù)功能,而不是單純的賣日常消費(fèi)品。便利店具備的“家庭小飯桌”功能,社區(qū)大賣場(chǎng)、社區(qū)超市具備的“家庭大廚房”功能,實(shí)際上都是發(fā)揮了超越買賣行為的延伸的社區(qū)服務(wù)功能。為了營(yíng)造人氣,強(qiáng)化親和力,樹立社區(qū)好鄰居、好伙伴的形象,上海聯(lián)華、南京蘇果等大型連鎖企業(yè),不僅把“修家電”、“調(diào)房子”、“請(qǐng)名醫(yī)”、“送盆菜”納入到服務(wù)體系中,而且還和金融、電力、通信、郵政等行業(yè)聯(lián)手,提供交電話費(fèi)、手機(jī)充值、買電、寄信、賣報(bào)、租車等家庭生活的一切需求。(注:張曉琳:《中國(guó)大賣場(chǎng)》,企業(yè)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即使是超級(jí)零售巨頭沃爾瑪、麥德龍、家樂福等,也是生鮮、食品的經(jīng)營(yíng)面積超過(guò)一半,把自身定位為“社區(qū)生活基地”,而不是高檔商場(chǎng)。“新業(yè)態(tài)”提供的應(yīng)有盡有的社區(qū)服務(wù)項(xiàng)目,給城市家庭的便利是“顯性”的,但由此讓鄰里、社區(qū)居家產(chǎn)生的歸屬感,建立起來(lái)的一個(gè)無(wú)形的服務(wù)網(wǎng)絡(luò)以及對(duì)促進(jìn)城市社區(qū)空間的“有機(jī)化”,并形成一個(gè)具有親和力的交往空間,卻是“隱性功能”產(chǎn)生的結(jié)果。
與傳統(tǒng)的商業(yè)業(yè)態(tài)如農(nóng)貿(mào)市場(chǎng)、百貨商店等相比,“新業(yè)態(tài)”具有社區(qū)服務(wù)、商業(yè)服務(wù)、娛樂交往及教育學(xué)習(xí)四大功能,這也是目前城市社區(qū)應(yīng)該提供的功能。本來(lái),按照傳統(tǒng)的社區(qū)規(guī)劃,商業(yè)設(shè)施和其它服務(wù)設(shè)施、文化中心等是分開的,超市的主導(dǎo)功能是“商業(yè)服務(wù)”,不能“越位服務(wù)”,但由于“新業(yè)態(tài)”的功能的先導(dǎo)性,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承擔(dān)了相鄰子系統(tǒng)應(yīng)當(dāng)發(fā)揮的功能,而且逐步形成了社區(qū)的“中心地”,在家庭消費(fèi)看來(lái),只要能達(dá)到“一站式”完成生活的各項(xiàng)服務(wù)的目的,就是最有成效的功能。(注:李程驊:《新業(yè)態(tài)與南京都市圈消費(fèi)的“中心地化”》,《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05年7期。)“新業(yè)態(tài)”所體現(xiàn)的這種“隱性功能”,本是無(wú)心插柳,但由于市場(chǎng)的功能太有威力了,使其在發(fā)揮商業(yè)服務(wù)“顯性功能”的同時(shí),又以自身的福利功能,促進(jìn)了社區(qū)服務(wù)資源“集聚化”以及自身社區(qū)服務(wù)“隱性功能”的釋放。
在對(duì)“新業(yè)態(tài)”與消費(fèi)行為互動(dòng)中產(chǎn)生的社區(qū)公共服務(wù)“隱性功能”的理論分析中,會(huì)發(fā)現(xiàn)支持系統(tǒng)運(yùn)轉(zhuǎn)的功能,是一個(gè)功能結(jié)構(gòu),而結(jié)構(gòu)本身的多層次性,使功能在發(fā)揮的過(guò)程中,“隱性”的一面和“顯性”的一面經(jīng)常同步體現(xiàn)出來(lái),當(dāng)某些功能“隱性”的一面廣為知曉后,就有可能上升為“顯性”的層次,促進(jìn)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內(nèi)部的進(jìn)一步分化與“通則化”。作為社區(qū)的公共服務(wù)功能,本身超越了消費(fèi)子系統(tǒng)的“區(qū)域”,與相鄰的居住、交際、娛樂、交通等子系統(tǒng)相互作用、相互侵蝕,對(duì)實(shí)施者“新業(yè)態(tài)”的商家來(lái)說(shuō),發(fā)揮的是“隱性功能”,但對(duì)于相鄰的子系統(tǒng)及整體社會(huì)系統(tǒng)來(lái)說(shuō),是商家展現(xiàn)的與普通商品銷售一樣的“顯性功能”。實(shí)際上,在消費(fèi)一經(jīng)濟(jì)一社會(huì)的不同層次結(jié)構(gòu)的系統(tǒng)的運(yùn)行中,消費(fèi)的這種“隱性功能”具有的傳導(dǎo)性更強(qiáng),結(jié)構(gòu)的多層次性,系統(tǒng)的多復(fù)雜性以及結(jié)構(gòu)與系統(tǒng)之間的多重關(guān)系,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jìn)了彼此的互相支持,推動(dòng)整體系統(tǒng)的優(yōu)化和升級(jí)。結(jié)構(gòu)分化的四個(gè)基本過(guò)程,在對(duì)系統(tǒng)的功能作用上,“顯性”層面和“隱性”層面往往也處在互為表里的結(jié)構(gòu)層次上,以最大限度推進(jìn)系統(tǒng)的整合。
悄然打造“社會(huì)交換”的新時(shí)空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無(wú)論是個(gè)人消費(fèi)者還是家庭消費(fèi)者,在日常消費(fèi)行動(dòng)上,其“現(xiàn)代性”不僅僅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人”的“計(jì)算性格”上,還體現(xiàn)在“社會(huì)人”的“歸屬感”上。消費(fèi)行動(dòng)是滿足生活需求的社會(huì)行動(dòng),也是最常見的突破階層界限的公眾接觸方式。在城市中,可以供現(xiàn)代人交流溝通的公共場(chǎng)所很多,比如市民廣場(chǎng)、公園等,在那樣的空間里,市民重視的是各自的休閑,是“熟悉的陌生人”,往往是互不干涉的。但在開放、自選的“新業(yè)態(tài)”的消費(fèi)空間里就可能不同了:消費(fèi)行為上的“趨同性”,消費(fèi)心理上基本一致的認(rèn)同感,使市民圍繞購(gòu)物技巧、圍繞對(duì)同一類商品的功能、文化意義的討論以及在生活品位上的相近性,可以面對(duì)面交流,在無(wú)形中造就一個(gè)個(gè)消費(fèi)共同體。因此,“新業(yè)態(tài)”的消費(fèi)空間,不僅僅具有消費(fèi)者和商家的“經(jīng)濟(jì)交換”的“顯性功能”,還具有促進(jìn)以社會(huì)需要、精神需要滿足為目的的“社會(huì)交換”的功能,這種功能作為“隱性功能”,具體又體現(xiàn)在三個(gè)層面上:消費(fèi)者之間的“社會(huì)交換”、消費(fèi)者與商家之間的“社會(huì)交換”以及對(duì)一個(gè)全新的“市民社會(huì)空間”的營(yíng)造。
在消費(fèi)空間里,消費(fèi)的首要目的性,決定了社會(huì)交換與經(jīng)濟(jì)交換是伴隨在一起的,交換是在“規(guī)范”的體系里和共同的心理期望中進(jìn)行的。為此,霍曼斯指出:小范圍社會(huì)現(xiàn)象與大范圍社會(huì)現(xiàn)象的差異只是在于它們的復(fù)雜性水平,而不在于構(gòu)成它們的基本過(guò)程。這種復(fù)雜性有兩種形式。首先,維續(xù)行為的往往不是直接得自他人的原初報(bào)酬,而是諸如貨幣和地位之類的概化的強(qiáng)化刺激;其次,報(bào)酬可能是一種以迂回或間接的方式才得到的。這類交換的穩(wěn)定性的確立是基于權(quán)威的規(guī)范和模式,而這些規(guī)范和模式又仿佛是以此前的基本交換為基礎(chǔ)的。(注:[澳]馬爾科姆.沃特斯:《現(xiàn)代社會(huì)學(xué)理論》,楊善華等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yè)。)當(dāng)代美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彼得·布勞進(jìn)一步認(rèn)為,“人們大多數(shù)的快樂都植根于社會(huì)生活中”,人們彼此為對(duì)方做事,管這些事情叫恩惠、幫助或者援助,并不索要任何直接的或明顯的回報(bào)。盡管如此,但通常說(shuō)來(lái),他們會(huì)收到社會(huì)認(rèn)可作為回報(bào),或者至少預(yù)期他人在將來(lái)某個(gè)時(shí)刻會(huì)幫他一個(gè)忙。因此,在任何情況下,人的往來(lái)都意味著交換。(注:[澳]馬爾科姆.沃特斯:《現(xiàn)代社會(huì)學(xué)理論》,楊善華等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8~79頁(yè)。)鑒于這樣的認(rèn)識(shí),作為人類行為一部分的社會(huì)交換,在很大程度上是“當(dāng)別人作出報(bào)答性反應(yīng)就發(fā)生、當(dāng)別人不再作出報(bào)答性反應(yīng)就停止的行動(dòng)”,“在彼此的交往中,人類傾向于受到一種欲望的控制,這就是想獲得各種各樣的報(bào)酬”(注:P·M·布勞:《社會(huì)生活中的交換與權(quán)力》,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20、17頁(yè)。)。但不是所有報(bào)酬都是能有具體量化的價(jià)格來(lái)體現(xiàn)的,能否直接用價(jià)格來(lái)體現(xiàn)出來(lái),就是經(jīng)濟(jì)交換和社會(huì)交換的區(qū)別所在。首先,與經(jīng)濟(jì)交換遵守契約合同相比,社會(huì)交換不作任何具體的規(guī)定和承諾,“回報(bào)的性質(zhì)不能討價(jià)還價(jià),而須留給作回報(bào)的人自己決定”(注:P·M·布勞:《社會(huì)生活中的交換與權(quán)力》,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20、17頁(yè)。)。其次,經(jīng)濟(jì)交換在交換過(guò)程中,其利益是可以準(zhǔn)確計(jì)算和預(yù)測(cè)的,不會(huì)引起雙方的責(zé)任、感激、信任感等。社會(huì)交換則帶有濃重的情感色彩,“沒有明確的價(jià)格,沒有統(tǒng)一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報(bào)酬的價(jià)值具有模糊性。例如愛、感激、贊同等”。針對(duì)社會(huì)交換的特殊性,后來(lái)有社會(huì)學(xué)者將其歸納為五種屬性:突生屬性、自愿屬性、模糊屬性、信任屬性、潛在屬性,并把社會(huì)交換獲得的報(bào)酬分為內(nèi)在性報(bào)酬(把交往過(guò)程本身看作報(bào)酬)、外在性報(bào)酬(把交往過(guò)程看作是實(shí)現(xiàn)更遠(yuǎn)目標(biāo)的手段)、內(nèi)在性和外在性報(bào)酬兼有三種。(注:宋林飛:《西方社會(huì)學(xué)理論》,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8頁(yè)。)
當(dāng)代中國(guó)城市的健康家庭,生活空間往往包括單位空間、居住空間以及交往消費(fèi)空間。(注:李程驊:《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城市住宅空間的社會(huì)學(xué)思考》,《江海學(xué)刊》2003年第1期。)而在現(xiàn)代消費(fèi)社會(huì)的背景下,社會(huì)交換和經(jīng)濟(jì)交換還有一個(gè)很明顯的不同點(diǎn),那就是在交換行為的實(shí)現(xiàn)空間上,前者不一定講究,后者則必須講究,否則就大大影響“交換”的效果。經(jīng)濟(jì)交換可以是兩個(gè)交換者的互動(dòng)行為,不一定有第三人在場(chǎng),但社會(huì)交換往往發(fā)生在群體交往的空間里,在“交換”的過(guò)程中有多人在場(chǎng),而在場(chǎng)群體成員的情緒、行為,則對(duì)獲取的“報(bào)酬”產(chǎn)生直接的左右作用,并提升或降低“報(bào)酬”的價(jià)值。“新業(yè)態(tài)”所構(gòu)建的結(jié)構(gòu)空間,不僅是個(gè)購(gòu)物的空間,還是社會(huì)交往的公共空間。首先,在這個(gè)空間里,消費(fèi)者一方面要達(dá)到購(gòu)物、滿足自身多種消費(fèi)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還希望在這里得到“友好的招呼”、消費(fèi)知識(shí)的學(xué)習(xí)以及對(duì)某個(gè)熱點(diǎn)問(wèn)題的共同看法或爭(zhēng)論,并結(jié)成興趣一致的休閑、娛樂的小組織或團(tuán)體,強(qiáng)化自身價(jià)值觀念的認(rèn)同感——“消費(fèi)社會(huì)也是進(jìn)行消費(fèi)培訓(xùn)、進(jìn)行面向消費(fèi)的社會(huì)馴化的社會(huì)”。(注:[法]讓·波德里亞:《消費(fèi)社會(hu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頁(yè)。)由于“新業(yè)態(tài)”空間中人的接觸的多層次性、高頻率性,使消費(fèi)者在滿足經(jīng)濟(jì)交換(與商家買賣)的基礎(chǔ)上體現(xiàn)的非經(jīng)濟(jì)交換行為,如休閑、交往等獲取“社會(huì)交換”的欲望,能在消費(fèi)者互動(dòng)的過(guò)程中得到最大限度地滿足。當(dāng)然,“社會(huì)交換”的不確定性,常常會(huì)改變?nèi)藗兊摹盎貓?bào)”預(yù)期。這是必須有思想準(zhǔn)備的。其次,人的需求與欲求,總是在消費(fèi)的過(guò)程中不斷發(fā)現(xiàn)的。在現(xiàn)代消費(fèi)社會(huì),人的消費(fèi)需求越強(qiáng),所需要的相關(guān)功利非功利的幫助、認(rèn)同就越多。在新業(yè)態(tài)的空間里,消費(fèi)者和雇員高頻率會(huì)面,鄰里消費(fèi)者之間也經(jīng)常會(huì)面,在無(wú)形中就形成了一個(gè)模擬的人際關(guān)系的世界。消費(fèi)者和超市的雇員之間建立起一種象征性的交換關(guān)系,這種象征性關(guān)系包含著一種持續(xù)的循環(huán),即給予和接受的循環(huán)。“在超市中,除了那些高度特殊的非常有限的交換類型之外,還將有一大批范圍廣闊的東西需要交換。即不僅僅只是服務(wù)和金錢之間的有限交換,而且像情感、感覺、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洞見等等之類的東西也都需要被交換。”(注:[美]喬治·里茨爾:《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理論》,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頁(yè)。)“新業(yè)態(tài)”對(duì)社區(qū)的“福利功能”,很容易使店員與顧客之間建立誠(chéng)信、信用關(guān)系,強(qiáng)化“關(guān)系營(yíng)銷”,讓消費(fèi)者獲得比較強(qiáng)的社區(qū)歸屬感,因?yàn)樵趪?guó)人的心目中,人際關(guān)系也是一種交換行為。再者,“新業(yè)態(tài)”的“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本”的高度“集聚性”帶來(lái)了人氣、高頻度的互動(dòng)交往,在這樣的空間里,受“規(guī)范”、氣氛的影響,消費(fèi)者更樂意進(jìn)入、長(zhǎng)時(shí)間逗留,并在交往的過(guò)程中樂于謙讓,更具有“社會(huì)交換”的激情和意向,“社會(huì)交換”的效率會(huì)進(jìn)一步提高。可以說(shuō),“新業(yè)態(tài)”的“以人為本”的商業(yè)精神,“以生活為本”的經(jīng)營(yíng)模式和服務(wù)理念所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高度集聚的公共消費(fèi)空間,實(shí)際上起到了新型的“市民廣場(chǎng)”的作用。這個(gè)消費(fèi)空間,延伸了城市的公共領(lǐng)域,兼具了“市民廣場(chǎng)”的功能,等于造就了新的“市民社會(huì)”的空間,本身也成了新的城市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生長(zhǎng)點(diǎn)。在當(dāng)前中國(guó)城市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中,最需要營(yíng)造的是共享的城市空間,但現(xiàn)在最具有“市民性”的社會(huì)空間,不是在大而無(wú)當(dāng)、只供觀賞的市民廣場(chǎng),而是在集消費(fèi)、休閑、體驗(yàn)、娛樂等為一體的“新業(yè)態(tài)”空間里“新業(yè)態(tài)”通過(guò)公共消費(fèi)空間中消費(fèi)行為的多向互動(dòng),所產(chǎn)生的強(qiáng)化“社會(huì)交換”的“隱性功能”,對(duì)于渴求擴(kuò)大社會(huì)交往的現(xiàn)代人來(lái)說(shuō),無(wú)疑是一種新的滿足。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當(dāng)基本的物質(zhì)需要得到滿足后,人們更看重社會(huì)需要和精神需要,而社會(huì)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滿足,則必須通過(guò)社會(huì)交往和社會(huì)交換行動(dòng)來(lái)實(shí)現(xiàn)。作為社會(huì)人,離開了社會(huì)交往和社會(huì)交換,個(gè)人就會(huì)處于社會(huì)資源的匱乏狀態(tài),即社會(huì)匱乏。社會(huì)匱乏反映在心理上就是孤獨(dú)感、感情饑渴、危機(jī)感、挫折感、絕望、嫉妒、失常等心理失衡狀態(tài)。社會(huì)匱乏產(chǎn)生社會(huì)性需要,即對(duì)愛、友情、受尊敬、被接受、榮譽(yù)、名望和自我實(shí)現(xiàn)等需要,它是人們結(jié)成一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從事社會(huì)互動(dòng)的原因之一。(注:張鴻雁主編:《后現(xiàn)代城市.休閑城市》,東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頁(yè)。)因此,對(duì)于現(xiàn)代消費(fèi)者來(lái)說(shuō),在公共空間里進(jìn)行情感交往是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而消費(fèi)空間提供了接觸和交往的可能。在當(dāng)今中國(guó)城市,以大賣場(chǎng)、超市、便利店等代表的“新業(yè)態(tài)”空間,已經(jīng)演化成了不同等級(jí)的“交往空間”,大賣場(chǎng)成了家庭購(gòu)物、休閑的新場(chǎng)所,超市和便利店也成了鄰里、社區(qū)的交往中心之一。特別是城市家庭中退休的老人,對(duì)超市這種“隱性功能”具有更強(qiáng)的認(rèn)同感。
對(duì)現(xiàn)代“消費(fèi)倫理”的潛在培育
一個(gè)社會(huì)系統(tǒng)的穩(wěn)定運(yùn)轉(zhuǎn)總要建立在對(duì)一個(gè)價(jià)值文化系統(tǒng)的“內(nèi)化”上(注:[澳]馬爾科姆.沃特斯:《現(xiàn)代社會(huì)學(xué)理論》,楊善華等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頁(yè)。),“新業(yè)態(tài)”的功能,表面看是商業(yè)服務(wù),進(jìn)一步審視是滿足消費(fèi)者的社會(huì)需求,但最終的核心功能是體現(xiàn)在其文化的“規(guī)范”上。因此,“新業(yè)態(tài)”的又一個(gè)重要的“隱性功能”,是通過(guò)制定的“文化”規(guī)則來(lái)提升“經(jīng)濟(jì)倫理”與“消費(fèi)倫理”水準(zhǔn),達(dá)到不斷“型塑”系統(tǒng)中的其它成員以及消費(fèi)行為的目的,以適應(yīng)現(xiàn)性社會(huì)的需求,保持系統(tǒng)的平衡。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經(jīng)濟(jì)人”的“計(jì)算性格”、“社會(huì)人”的從眾心理,常常影響經(jīng)濟(jì)倫理與消費(fèi)倫理的功能發(fā)揮。但是,“在交往日常實(shí)踐中,必須貫徹認(rèn)識(shí)解釋,道德要求,帶表情的敘述和利用,并且通過(guò)能夠按照形式的觀點(diǎn)的運(yùn)用兌換形成一種合理的聯(lián)系”(注:[德]哈貝馬斯:《交往行動(dòng)理論》(第二卷),洪佩郁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頁(yè)。)。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社會(huì)的急劇變化,造成的是社會(huì)危機(jī),是在人的心靈上喪失了三種東西,那就是共識(shí)、秩序和意義。因?yàn)槿狈沧R(shí),產(chǎn)生許多誤會(huì)和沖突,引發(fā)彼此的疏離甚至仇恨;由于缺乏秩序,顯得無(wú)規(guī)范、無(wú)紀(jì)律,似乎倫理和組織都失去了應(yīng)有的功能;缺乏意義,使得生活沒有目標(biāo),人生迷失了方向。人們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人際關(guān)系就變得緊張,由緊張引起人的心靈封閉。在消費(fèi)系統(tǒng)中,作為主體對(duì)象的人,其行為在系統(tǒng)中起到平衡整體的作用,在“理性”的條件下,應(yīng)該扮演“合格消費(fèi)者”的角色。在整體社會(huì)系統(tǒng)中,消費(fèi)子系統(tǒng)要與生產(chǎn)系統(tǒng)等相關(guān)聯(lián)的子系統(tǒng)保持和諧的關(guān)系,就必須扮演產(chǎn)業(yè)鏈中的“合格的伙伴”的角色。傳統(tǒng)的商業(yè)零售業(yè)態(tài),由于是生產(chǎn)什么賣什么,缺乏綜合的控制能力和技術(shù)制約,這種“隱性”的控制作用比較小,只考慮商品本身的質(zhì)量及能否按時(shí)拿到貨,靠的是道德底線維系合作,至于廠家在制造產(chǎn)品的過(guò)程中是否“道德”,商家是不需要關(guān)心的。但“新業(yè)態(tài)”在體系和技術(shù)上的強(qiáng)大控制力,使這種“隱性”的功能在新的消費(fèi)社會(huì)中作用明顯。近幾年,沃爾瑪?shù)瓤鐕?guó)零售巨頭在國(guó)內(nèi)的采購(gòu)量逐漸加大,尋找的生產(chǎn)供貨商也越來(lái)越多,但這些巨頭們?cè)趯?duì)生產(chǎn)商的“考核”中,不僅僅關(guān)注產(chǎn)品的質(zhì)量、價(jià)格,還要看廠家是否采用綠色生產(chǎn)方式、是否用童工、是否按時(shí)發(fā)放薪水等,表面看來(lái),廠家的這些行為與商家是不相干的,但在跨國(guó)零售巨頭們看來(lái),既然我們結(jié)成了商業(yè)領(lǐng)域中的伙伴關(guān)系,就是結(jié)成了一個(gè)命運(yùn)共同體,就是整體系統(tǒng)與子系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對(duì)方的風(fēng)險(xiǎn)傳導(dǎo),就會(huì)形成自身的風(fēng)險(xiǎn)。同時(shí),還認(rèn)為在雙方互動(dòng)的過(guò)程中,必須恪守君子之風(fēng),對(duì)采購(gòu)人員送支筆、請(qǐng)杯茶都是“行賄”,因?yàn)檫@樣有可能導(dǎo)致供應(yīng)商之間的“不公平競(jìng)爭(zhēng)”。(注:《沃爾瑪?shù)慕?jīng)濟(jì)道德》,《中國(guó)青年報(bào)》2003年8月7日。)另一方面,商家一切都是為顧客服務(wù)的,像沃爾瑪文化的一個(gè)重要理念就是高度關(guān)注競(jìng)爭(zhēng)、顧客和成本,員工接受生意伙伴哪怕是一瓶汽水的饋贈(zèng),最終都得由顧客埋單,因此禁止任何饋贈(zèng)。正是靠這種制度,它能對(duì)商品從工廠到貨架上的整個(gè)物流過(guò)程精準(zhǔn)控制,把運(yùn)輸和存貨成本降低到了零售專家稱之為前所未有的水平,“擠掉”了任何多余的東西。(注:《建立在討價(jià)還價(jià)基礎(chǔ)上的沃爾瑪》,《洛杉礬時(shí)報(bào)》2003年12月23日。)在沃爾瑪看來(lái),這一切的直接目的都是為了降低成本,強(qiáng)化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力,但卻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qū)λ械暮献骰锇槠鸬搅耸剂衔醇暗慕?jīng)濟(jì)倫理的約束作用。而且,這種理念也同時(shí)控制消費(fèi)系統(tǒng),促進(jìn)消費(fèi)者對(duì)其建立的商業(yè)倫理和消費(fèi)倫理的認(rèn)同,提升自身在消費(fèi)行動(dòng)中的“道德性”。(注:李程驊:《挑戰(zhàn)“沃爾瑪化”——中國(guó)城市商業(yè)業(yè)態(tài)的戰(zhàn)略選擇》,《社會(huì)科學(xué)》2005年第12期。)
在一個(gè)健康運(yùn)行的社會(huì)里,經(jīng)濟(jì)應(yīng)該是道德的,消費(fèi)更應(yīng)該是道德的。在社會(huì)大系統(tǒng)中,人的消費(fèi)行為的倫理性的重要體現(xiàn),是在自身獲得利益的同時(shí),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不能破壞系統(tǒng)的規(guī)則。在傳統(tǒng)零售業(yè)態(tài)的空間里,由于系統(tǒng)的“控制性”不強(qiáng),付款不排隊(duì)、顧客與營(yíng)業(yè)員之間的沖突等現(xiàn)象司空見慣。但“新業(yè)態(tài)”具備的“預(yù)測(cè)”、“控制”的功能,則能消除這些現(xiàn)象。比如引導(dǎo)顧客按順序排隊(duì),實(shí)際上也是在灌輸公共空間遵守秩序的公德意識(shí)。當(dāng)然,“新業(yè)態(tài)”的這種“隱性功能”的發(fā)揮,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主觀設(shè)計(jì)的,而是客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像到麥德龍購(gòu)物的顧客必須開“透明發(fā)票”,其本意是便于退換貨時(shí)雙方無(wú)糾紛,但由此強(qiáng)化了消費(fèi)者的誠(chéng)信意識(shí)、契約意識(shí)。不過(guò),有社會(huì)責(zé)任感的商家,有時(shí)也會(huì)通過(guò)自身的主動(dòng)行為來(lái)倡導(dǎo)一種公益的理念,比如麥德龍?jiān)谌澜绯珜?dǎo)“綠色消費(fèi)”的觀念,實(shí)行塑料包裝袋有償使用,既把自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廣為傳播出去,又使消費(fèi)者在從不理解到理解的過(guò)程中,樹立綠色環(huán)保的消費(fèi)意識(shí),以在整個(gè)社會(huì)形成健康的、綠色的、可持續(xù)的消費(fèi)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新業(yè)態(tài)”體現(xiàn)的培育新的“經(jīng)濟(jì)倫理”和“消費(fèi)倫理”的“隱性功能”,實(shí)際上是用自身的文化價(jià)值體系來(lái)“內(nèi)化”消費(fèi)系統(tǒng)和整體社會(huì)系統(tǒng),優(yōu)化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和運(yùn)轉(zhuǎn)質(zhì)量。這落到實(shí)處,實(shí)際上就是在無(wú)形之中“型塑”了消費(fèi)者,讓消費(fèi)者具有“理性”、“現(xiàn)代性”,創(chuàng)造新型的“消費(fèi)文化”。在西方的消費(fèi)者行為學(xué)中,不同的社會(huì)階層在消費(fèi)心理上有三種表現(xiàn)方式:一是出于希望被同一階層成員接受的“認(rèn)同心理”,人們常會(huì)依循該階層的消費(fèi)行為模式行事;二是出于避免向下降的“自保心理”,人們大多抗拒較低階層的消費(fèi)模式,如自認(rèn)為是有名望的富翁,可能會(huì)認(rèn)為跟普通百姓坐在一起吃路邊攤上的食物,是一件非常有失身份的事情;三是出于向上攀升的“高攀心理”,人們往往會(huì)喜歡采取一些超越層次的消費(fèi)行為,以滿足其虛榮心。(注:江林主編:《消費(fèi)者心理與行為》,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180頁(yè)。)這種由不同消費(fèi)心理造成的消費(fèi)行為上的差別,說(shuō)到底是缺乏各階層都能接受的文化,而傳統(tǒng)的消費(fèi)空間無(wú)不具備較強(qiáng)的等級(jí)色彩。但是,進(jìn)入現(xiàn)代消費(fèi)社會(huì),日常消費(fèi)結(jié)構(gòu)的趨同,百萬(wàn)富翁與普通中產(chǎn)階層對(duì)消費(fèi)符號(hào)意義理解的接近,具有超強(qiáng)“控制力”的“新業(yè)態(tài)”商家就有條件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各個(gè)階層都認(rèn)可的消費(fèi)大空間。具有現(xiàn)代性的空間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消除不同階層原來(lái)的隔閡,造就一個(gè)和諧的空間氛圍。對(duì)此,喬治·里茨爾曾比較早地運(yùn)用后現(xiàn)代的理論對(duì)沃爾瑪?shù)南M(fèi)空間的包容性進(jìn)行應(yīng)用研究:沃瑪特中心以“壟斷性”創(chuàng)造了一種情境,一種使所有購(gòu)物者別無(wú)選擇、無(wú)法抗拒的情境。(注:[美]喬治·里茨爾:《后現(xiàn)代社會(huì)理論》,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頁(yè)。)
在中國(guó)商業(yè)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中,商業(yè)新業(yè)態(tài)承載了重要的整合功能。大賣場(chǎng)、連鎖超市在中國(guó)城市的蓬勃發(fā)展,所創(chuàng)造的“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本”的消費(fèi)空間、社區(qū)空間,實(shí)際上也是一個(gè)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情境空間”,并衍生出與“現(xiàn)代性”對(duì)應(yīng)的新型消費(fèi)文化:既講效率,也講人情;既承認(rèn)分層,又不加劇分層,打造出一個(gè)以社區(qū)群體而不是收入、職業(yè)分層的具有共享功能的公共消費(fèi)空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國(guó)式的“社區(qū)大賣場(chǎng)文化”。這種現(xiàn)象,也驗(yàn)證了商業(yè)新業(yè)態(tài)未來(lái)的發(fā)展,必須更為注重應(yīng)對(duì)“本土化”的挑戰(zhàn)問(wèn)題。(注:張鴻雁、李程驊:《商業(yè)業(yè)態(tài)變遷與消費(fèi)行為互動(dòng)關(guān)系論——新型商業(yè)業(yè)態(tài)本土化的社會(huì)學(xué)視角》,《江海學(xué)刊》2004年第3期。)對(duì)于這一點(diǎn),就像城市的住宅區(qū)規(guī)劃建設(shè)一樣,不同階層的人居住相對(duì)分隔但又共享一個(gè)社區(qū)空間,使社區(qū)充滿有機(jī)性。商業(yè)新業(yè)態(tài)“在改變了人們的消費(fèi)行為、帶來(lái)了新型消費(fèi)生活方式的同時(shí),還促進(jìn)了城市社區(qū)的有機(jī)化”。無(wú)疑,其打造出共同的“消費(fèi)天堂”、“精神圣殿”,盡管是“隱性”的,但同樣起到了“內(nèi)化”整體消費(fèi)系統(tǒng)中不同價(jià)值觀念的作用。在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的大背景下,現(xiàn)代城市確實(shí)需要這種各階層都認(rèn)可的新型消費(fèi)文化——在“新業(yè)態(tài)”這樣的場(chǎng)所里,消費(fèi)行為上差別的淡化,使消費(fèi)者具有共同的滿足感、歸屬感。而這種共同的滿足感和歸屬感,則是新型的社會(huì)系統(tǒng)穩(wěn)定均衡運(yùn)轉(zhuǎn)的基礎(chǔ)——消費(fèi)的滿足能帶來(lái)精神的滿足,精神的滿足會(huì)促進(jìn)人們以積極的態(tài)度對(duì)待生活、對(duì)待社會(huì),并走出自我,走出家庭,強(qiáng)化公民的責(zé)任感。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商業(yè)報(bào)告 商業(yè)倫理論文 商業(yè)銀行 商業(yè)文化論文 商業(yè)模式論文 商業(yè)保險(xiǎn) 商業(yè)分析論文 商業(yè)銀行監(jiān)管法 商業(yè)管理論文 商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 紀(jì)律教育問(wèn)題 新時(shí)代教育價(jià)值觀
- 商業(yè)賄賂
- 現(xiàn)代商業(yè)設(shè)計(jì)
- 商業(yè)賄賂
- 商業(yè)保險(xiǎn)
- 商業(yè)改革
- 英語(yǔ)商業(yè)信函剖析
- 商業(yè)地產(chǎn)投資
- 商業(yè)競(jìng)爭(zhēng)管理
- 商業(yè)藝術(shù)設(shè)計(jì)
- 商業(yè)秘密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