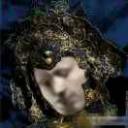外交政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外交政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外交政策分析認知視角的出發點
冷戰期間占國際關系理論主導地位的現實主義認為外交決策過程是一個理性的選擇過程,政府或者其主要的領導者在追求國家利益時是一個理性的行為者,在決策的過程中能夠獲得所有決策(選擇)所需要的信息,對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通過一個開放的過程選擇能給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政策選擇。這些學者認為,國際體系制約和影響政策的選擇,個人很難對外交政策的結果有任何影響,不同個性的人在同樣條件下會做出同樣的決定,“名字和面孔可能改變,但(國家)利益和政策則不會改變。”用官僚政治模式研究外交政策決策過程的學者則認為,外交政策是在復雜的官僚機構中制定的,政策制定過程對效率的追求要求徹底擺脫個人的私心雜念,感情好惡,因此決策機制和過程限制和制約了個性發揮作用,過于強調個人的作用往往陷入唯心主義的陷阱。
辯證唯物主義在強調人的一切心理現象都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認為人的心理對客觀現實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機械的反映,并不像鏡子映照物體那樣。人對現實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長期形成的個人特點、知識經驗、世界觀等密切相聯系的。人對客觀現實世界進行認知的過程不僅受到認知對象(客觀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到主觀因素,如信仰、需要、興趣、知識經驗以及知覺對象對生活和實踐的意義等的影響。外交政策分析的認知視角是與這樣的辯證思維相一致的。這種視角因個人在冷戰結束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冷戰結束的方式而變得更為引人注目。這種認知(個人,個性層次)的視角(理論、方法或模式)通過對決策者及其信仰和認知過程的研究來理解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方面來理解和研究外交決策者與外交決策結果的關系。有的側重于對決策者信仰系統的研究,有的側重于對決策者認識過程的研究,有的則側重于對決策者的信息處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學者則將精力放在對外交決策者個性的研究上。概括起來,這些學者認為決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響,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不一樣的;或受到決策者信息處理方法的影響,一般是比較封閉和保守的(close-minded),對外界的變化適應是緩慢的,或者對外界的變化有一種抵制態度,拒絕接受這些變化;或者認為決策者對形勢的判斷有時候是不準確的,決策者在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往往受到錯誤認識的影響,或者是根據對現實世界的錯誤認識制定外交政策。這種方法強調對外交決策者及其認知過程的研究,認為不同的決策者參與外交決策可能會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結果。
從認知角度對國際政治的研究開始于1930年代。當時一些學者將一些心理學的基本概念和方法運用于對外交決策的研究。他們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國家的特點,對戰爭的態度,公眾感情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等。如所謂的“戰爭開始于頭腦之中”,就是說從發動戰爭者頭腦中一產生發動戰爭的這種想法以后,戰爭的機器就開動了,而不是在戰場上。但是由于這些學者缺乏國際政治或國際關系的背景,而現代含義上對國際關系的研究則剛剛開始,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缺乏對心理學的了解,因此這些研究并沒有得到國際政治學者的接受。
盡管如此,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一產生,就有不少學者將個人層次和認知的因素作為影響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變量進行研究,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日益引人關注。如沃爾茲在其經典的《人、國家和戰爭》一書中在分析戰爭的根源時提出的第一個意象(image)就是人。這種意象認為,“人的邪惡,他們錯誤行為導致了戰爭,如果個人的美德能夠被普及,就會有和平。”(注:KennethWaltz,MantheS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p.39.)他在闡述這一意象時提出,“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學的理論,”“世界歷史的發展離不開創造歷史的人。”(注:Ibid.,p.28.)同一時期的另一位國際關系理論大家賴特也以同樣的筆調指出,“國際關系不能僅僅局限于政府間的關系,結論不能建立在認為它們(心理學)不能提供足夠的預測和控制的假設的基礎上。”(注:QuencyWr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Appleton,1955),p.433.)博丁也指出,“我們必須認識到決定、影響國家政策和行為的人并不是對‘客觀’實際環境的反應。決定我們行為的是我們認知的世界,而不是現實的世界。”(注:QuotedinJerelRasati,“ThePowerofHumanCognitionandPolicymakerBeliefsinForeignPolicyandWorld
Politics,”manuscript.)羅森諾在呼吁建立比較外交政策的理論時提出了影響外交政策的五個層次的自變量,其中一個就是個人,也就是決策者。(注:JamesRosenau,“Pre-TheoryandTheoryofForeignPolicy,”inApproachesto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Politics,R.BarryFarrelled.,(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6),pp.97—100.)但系統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并將這種方法運用到對國際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學界關注的是斯布羅特夫婦(HaroldandMargaretSprout)。
二、主要理論:從認知一致理論到社會認知理論
斯布羅特夫婦在1956年發表的“國際政治背景下人——環境關系的假設”一文引起很大的反響,九年后又被擴充成一本書。他們指出,一切客觀的環境和現實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或者更確切地說,通過決策者的心理過程才能發揮作用。決策者一般都有一種“從內向外”看問題的方法,來自外界的信息通常是經過由他們的態度、信仰、動機構成的“透鏡(lens)”,有選擇地過濾和吸收后才有意義的。“一個人的價值觀和其他心理傾向指導著他有選擇地關注周圍的環境,他根據有意識的記憶和潛意識的經驗去解釋經過他選擇的周圍環境。”(注: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p.118.)這種被觀察到的環境被稱為“心理環境(psychologicalmilieu)”,它和“操作環境(operationalmilieu)”,或者是現實的客觀環境或地理環境是有區別的。“從決定和決策的過程來看,重要的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如何認識環境的,而不是環境到底是什么。”(注:Ibid.,p.224.)但是決策者制定了外交政策以后,就必須在操作環境或現實環境中執行。他們指出,對于研究決策過程來說,掌握研究決策者對“操作環境”的認知,也就是“心理環境”,對理解和認識外交政策的制定,打開制定外交政策“黑匣子”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外交政策是否能夠實現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所確定的目標,則取決于政策是否符合實際環境。決策者的心理環境和現實環境的不一致可能導致不符合實際的外交政策結果。這一時期從認知視角對國際政治進行的研究受心理學中態度(attitude)或態度變化(attitudinalchange)的影響,根據認知的一致性(cognitiveconsistency)的觀點,人在認識和把握現實世界時依賴于主要的信仰,而且盡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也就是說,人們在理解和認識客觀世界時會保持基本的信仰系統,會回避、抵制與自己的基本信仰不一致的信息,特別是與自己的信仰的核心不一致的信息和材料,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信仰和對外界信息的處理方式影響決策者對形勢的認知過程,認知過程影響外交政策的結果。
運用這種認知的視角進行研究的突出代表是霍爾斯蒂對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的研究。霍爾斯蒂根據有關認知的理論將信仰系統分為兩部分:對現實的影像(imageofthefact)和對前景的影像(imageofwhatoughttobe)。前者影響對現實的認識,后者實際上是一個人的價值觀,直接指導著對外政策的制定。信仰系統是包括對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系列的“印象”構成的,是一套物質世界和社會環境進入人腦所必經的過濾器。決策者根據自己對現實的印象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據現實制定政策。在決策過程中每一個決策者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現實環境(外部)經過由基本信仰構成的鏡片的過濾,形成對現實的反映,然后影響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信仰的差別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人們對現實看法的不同,最終解釋了國家間外交政策的不同。霍爾斯蒂搜集了434份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的資料,包括他在國會的證詞,答記者問,演講等,然后利用“內容分析(contentanalysis)”的方法對杜勒斯的所有講話進行分析,特別是他3584次提到蘇聯時的用詞。他發現杜勒斯對蘇聯懷有非常難以改變的“敵人的印象(imageofenemy)”,不管蘇聯的政策如何變化。這一結果和心理學中的“認知的一致性”理論是完全吻合的。如杜勒斯不愿意接受、不信任來自蘇聯的與他對蘇聯的印象不一致的信息,一旦遇到這樣的信息,他或者去尋求與他的印象一致的信息來否定原有的信息,或者對這些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釋。這種對外界變化的生硬態度源于一種他認為蘇聯“天生是不可信任”的固有認識。他認為,“只要蘇聯是一個共產黨統治的一個封閉的社會,它就代表杜勒斯價值觀念核心的對立面。此外,可能挑戰這種認為蘇聯在本質上是不可信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來自蘇聯,因此很不可信,而且通常是含糊不清的,足以使人產生各種各樣的解釋。”對蘇聯所采取的緩和政策,杜勒斯則認為這是因為蘇聯外交政策失敗和力量不足的外在表現,而不是因為蘇聯愛好和平。比如1955年蘇聯與西方簽署了《奧地利國家條約》,允許奧地利在西方陣營內保持中立,導致了東西方國家關系的緩和,對此杜勒斯認為這決非因為蘇聯有善意,而是因為蘇聯農業政策失敗而導致的國家虛弱和蘇聯整個對西方政策失敗的結果。此后對于蘇聯為緩和國際形勢裁減軍隊120萬,杜勒斯也認為,蘇聯的出發點是惡意的。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經過記者一輪輪問對之后,一個記者說,“從您今天早上所說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您更喜歡讓這些人當兵?”杜勒斯回答說,“當然,我寧愿讓他們站在那里站崗,也不希望他們去制造核武器。”(注:OleR.Holsti,“TheBeliefSystemandNationalImages:ACaseStud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ForeignPolicy,ed.JamesRosenau,(NewYork:FreePress,1967),p.548.)霍爾斯蒂對美國原國務卿杜勒斯的案例研究從決策者認知的角度揭示了美國對蘇聯的政策以及美蘇之間矛盾的升級。
另一個有影響的研究信仰與外交政策結果關系的學者是喬治。他在“行為準則(operationalcode):研究政治領導人和決策的一個被忽視的方法”一文中對列特斯(NathanLeites)1953年出版的《布爾什維克研究》一書中提出的“行為準則”進行了提煉,提出“行為準則”指“政治領導人對政治和政治沖突的信仰,歷史發展可以決定程度的看法,以及其正確戰略和策略的觀念等。”他將蘇聯共產黨的信仰分為哲學信仰(philosophicalbelief)和策略信仰(instrumentalbelief)兩個方面來研究蘇聯共產黨領導核心的信仰對蘇聯外交政策決策的影響。(注:AlexanderGeorge“theOperationalCode:ANeglected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13,2,(1969).)這些準則可以通過對10個問題的回答來得出。反映哲學信仰的5個問題是:(1)政治生活的“本質”是什么?政治從本質上是普遍和諧的呢?還是沖突的?政治對手的基本特點是什么?(2)最終實現一個人的基本政治價值觀念和追求的前景是什么?一個人能樂觀嗎?還是必須是悲觀的?在哪些方面應是悲觀的?在哪些方面應是樂觀的?(3)政治前景可以預測嗎?在什么意義上,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是這樣的?(4)人們從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和“掌握”歷史發展的進程?個人在“推動”或“影響”歷史朝自己所期待的方向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5)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機遇”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反映策略信仰的5個問題是:(1)選擇政治行動的目標的最佳手段是什么?(2)實現政治目標的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3)如何計算、控制和接受政治行為的風險?(4)什么是實現利益采取行動的政治目標的“最好時機”?(5)實現目標時采取的不同手段的效用和作用是什么?“行為準則”和另外一些學者對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的思維步驟進行研究所提出的“認知過程圖(cognitivemap)”是一致的。“認知過程圖”是指對外政策的制定者在特定環境下理解環境的一套信仰,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它認為,決策者在觀察形勢并根據需要做出一定決策的過程中一般要經過四個步驟:信仰的擴充(initialamplificationofrelevantbeliefs),尋找先例(解釋事件),評估后果,尋求可供選擇的政策,做出外交政策的決定。他們為領導人的行為及其過程確定了界限。(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in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ContinuityandChangeinItsSecondGenerationeds.,Laura
Neacket.al.,(NJ: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95),p.57.)喬治在他文章中指出“行為準則”又可以稱作“認知過程圖”,但是“行為準則”因為喬治的提煉和推廣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影響了很多人運用“行為準則”的方法來研究領導人的外交政策,不僅被用來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不少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注:DavisB.Bobrow,“TheChineseCommunistConflictSystem,”Orbis,9(Winter1966);H.BoormanandS.Boorman,“StrategyandNationalPsychologyinChina,”TheAnnals,370(March1967);TangTsouandMortonH.Halperin,“MaoTse-tung''''sRevolutionaryStrategyandPeking''''sInternationalBehavior,”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59,(March1965).)而且也被用來研究其他國家或人的外交政策。(注:StephenG.Walker,“TheInterfacebetweenBeliefsandBehavior:HenryKissinger''''sOperationalCode
andtheVietnamWar,”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no.21,1977.)
從1970年代開始,政治心理學的研究經歷了一個認知的革命,認知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視。一些學者又開始用社會認知理論(socialcognitivetheory)或圖式理論(schematheory)研究對外政策制定過程個人的作用和影響。這種理論認為,個人是認識上的吝嗇鬼(cognitivemiser),他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依賴于現存的信仰和圖式(思維結構)去解釋客觀世界。他們在發展認知一致性的基礎上提出了態度或信仰是相當復雜的,內部是由多種不同的內容組成的,因此認知的過程也是相當復雜的。處于核心部分的信仰是很難變化的,但是處于邊緣部分的因素則非常容易變化,并最終可能影響到中心信仰的變化。在理論方面比較能代表這一時期成就的是杰維斯的《國際政治中的認識與錯誤認識》。他在提出從四個層面上對國際政治進行研究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決策者的認識過程對外交決策,乃至國際政治的影響。如認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響外交決策的,外交決策者又是如何從歷史中學習的,態度是如何變化的,外交決策者對現實錯誤認識的規律及其影響等等,進而提出了認知對研究外交決策和國際政治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撇開決策者對世界的信仰和他們對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釋關鍵性的決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6),p.28.)
與此同時,一些對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會認知或圖式理論的方法。如拉爾森對遏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關檔案材料,對從二戰結束前的1944年到1947年冷戰爆發這一段時間內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魯門、哈里曼、貝爾納斯、艾奇遜等對蘇聯的認識發展過程進行的研究。他發現艾奇遜對蘇聯的認識基本上是穩定的,而其他幾個決策者對蘇聯的認識則經歷了從盟友到對手乃至敵人的變化過程,進而提出沒有一種關于認知的理論能夠解釋所有美國對蘇聯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變化過程。(注:DeborahW.Larson,OriginofContainment:APsychologicalExplan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5).)羅賽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對卡特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員的信仰及其對外政策的影響進行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指出在上臺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員卡特、萬斯和布熱津斯基的世界觀是基本一致的,都非常樂觀。他們都不贊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權力政治和均勢外交,認為那些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國的價值觀和美國外交政策的優勢,希望與蘇聯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但是隨著蘇聯在全球擴張的升級,從第一次埃塞俄比亞與索馬里的戰爭開始,布熱津斯基對蘇聯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到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后徹底改變了對蘇聯的認識,而萬斯基本上保持了對蘇聯原來的認識。卡特先是搖擺于萬斯與布熱津斯基之間,但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后徹底倒向布熱津斯基。羅賽蒂指出,決策層的信仰和對世界的認識越一致,那么這個國家外交政策越可能與這個統一的信仰一致;相反,如果決策層的信仰和對世界的認識不一致,外交政策就有可能與這個國家決策層的信仰不一致。(注:JerelA.Rosati,TheCarterAdministration''''sQuestforGlobalCommunity:Beliefsand
TheirImpactonBehavior(ColumbiaS.C.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Press,1987).)這兩個研究都反映出對外政策決策者的信仰和對世界的認識是可以變化的,盡管這種變化因決策者的教育程度(是否專家)、他們所擔任的職務、以及決策時的形勢特點而異。
三、主要方法:內容分析、案例分析與過程追蹤
外交決策的過程常常被認為是一個“黑匣子”,研究者很難了解這個黑匣子內部所發生的事情,除非自己參與了這個決策過程,或研究者本人就是外交決策者。但是相對于決策過程來說,對認知過程的研究就更難了。可以說決策者在做出對外政策決策時的心理過程屬于外交政策決策過程的“黑匣子”內的“黑匣子”,它處于其它一切影響外交政策結果的因素與外交政策結果的中間。人們常常說國際環境的變化引起國家外交政策的變化,或者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國內政策的變化導致了外交政策變化,但是實際上,所有這些國際的或者是國內的變化或變量本身是不會自動發揮作用、影響對外政策的決策過程和結果的。外部環境或因素都必須通過決策者的信仰、認識、態度、個性等構成的凸鏡的“過濾”才會變得有意義。換句話說,這些外在的因素只有被決策者觀察到,并被決策者在決策時考慮在內,它們才會有意義,才會成為影響外交政策決策的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揮作用,影響對外政策的結果。正如羅賽蒂所說,“把信仰作為因果關系的核心的主要優勢是在理解外交政策時把環境和心理的因素結合到一起。同時,因為認知的方法是研究決策者的‘心理環境’的,因此學者在研究時還應該對‘操作環境’的直接影響保持敏感以使對外交政策有一個全面的認識。”(注:JerelRosati,“ACognitiveApproachtotheStudyofForeignPolicy,”inForeignPolicyAnalysis,p.67.)
在從認知的視角對外交政策進行研究時,常常會發現不同的學者運用不同的心理學概念,如認識、認知、信仰、動機、印象、信息處理過程等等。這種不一致說明不同的學者在從認知的視角對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進行研究時往往會側重不同的方面。他們在將這些因素作為變量研究其對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和結果的影響時往往先對這些概念進行自己的界定,進而展開研究。羅賽蒂1999年在外交學院進行講學的時候告訴筆者,這些不同的內容(概念)相互關系如何,在頭腦中是如何組織起來,并構成人的信仰系統并發揮作用的,至今還沒有理順,這應該是這一領域將來的一項任務。在多元主義的美國,這可以說是難以實現的目標。但是無論如何界定,這些概念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在運用到對實際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研究時難以操作。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中一般借助兩種方法,一是“內容分析”法,也就是通過搜集研究對象所發表過的言論,可能的話對研究對象本人或對與其一同工作者的采訪,報紙對研究對象的報道,以及傳記等二手材料等,對有關內容進行分析,如數某一個詞用法的次數,對研究對象在談到某一個國家或事物時常常使用的詞進行分類歸納等手段,得出研究對象對一個國家或者事物的認識(或者是錯誤認識)、態度、乃至信仰,以及制定或執行某一項外交政策的動機。進而找出研究對象在制定外交政策的過程中的認知過程,找出認知、信仰等其它心理因素對外交政策是如何產生影響的。本文所提到的絕大部分研究都是借助這一方法進行研究的。霍爾斯蒂關于杜勒斯的研究作為“內容分析”的一個典范被多個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的論文集收入。
另一個手段是案例分析。信仰或認知對外交政策結果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參與對外政策制定者發揮作用的,因此在從認知視角對外交政策進行分析和研究的過程中,一般采取案例的方法,這些案例有對重要決策者一個人的研究,如研究較多的有對杜勒斯、基辛格、美國前總統威爾遜、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等對其國家外交決策有重大影響的一些外交決策者的研究;有對一個重要的決策群體進行的研究,如對前蘇聯共產黨核心信仰的研究(如行為準則),以及利用這樣的方法對中國共產黨信仰系統的研究,對美國做出入侵古巴豬灣的決定和處理古巴導彈危機時的肯尼迪政府決策小組的決策過程的研究,以及對杜魯門和卡特政府決策小組的研究等;也有對精英群體,或知識分子的研究,如沈大偉在《美麗的帝國主義》一書中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美國觀的研究等。(注:David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m:ChinaPerceivesAmerica1972—1990(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在探索信仰、認知與外交政策結果的關系時,有兩種方法是經常使用的。一個是“過程跟蹤程序(processtracingprocedure)”,這種方法追蹤和研究決策者認知變化的詳細過程,比如說決策者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如何影響決策者接受和分析來自外界的信息的,這種信息處理方式和結果導致決策者是如何判斷形勢的,決策者根據這種對形勢的判斷在決策過程中考慮了幾種可能的選擇,最后為何選擇了最終的政策等等。這種對決策過程的詳細的研究能夠揭示出信仰、認知過程與外交政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causalrelation)。但是這種方法比研究決策過程的官僚政治更難,因為它需要更多更詳細,而且又都是更難以獲得的材料,需要完全借助心理學的手段。因為信仰無形,認識過程又看不見摸不著,對其發展變化更難把握。為解決這一問題,一些學者在研究時采取的方法之一,是運用跨領域的比喻和同一領域的類比,把看不見的或不容易理解的現象和事物與一種一般人都比較熟悉的東西或事物相比,從而使人們更加容易理解決策者的觀點和看法。(注:KeithL.Shimko,“ForeignPolicyMetaphor:Falling`Dominoes''''andDrug`Wars'''',”inForeignPolicyAnalysis,pp.71—84.)這種方法在國際關系中常常被使用,比如,美國在冷戰期間的“遏制”政策原意則是用容器(container)把蘇聯“裝(contain)”起來,翻譯為“遏制”。這里共產主義的蘇聯被看作是一種哪兒低就往那里流的一種“禍水”,美國領導人對蘇聯的認識經過這樣一個比喻就非常清楚可見。人們比較熟悉的類似比喻還很多,如國際關系史中的“冷戰”、“多米諾”理論、軍備“競賽”、的“紙老虎”的觀點等。伊拉克占領科威特之后,美國政府則把伊拉克的入侵說成是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強奸”,這里顯然是將之比做現實生活中一種人們不能容忍的一種暴行,說明美國認為伊拉克的行為必須得到懲罰,美國對伊拉克的打擊是一種正義的行為。從克林頓政府開始,美國稱一些他認為不負責任的國家為“流氓國家”,則是把國家行為比作是一個生活中人們熟悉的“流氓”。這些比喻都使抽象的東西變得形象具體,使研究者能夠把握研究對象對事物的認識及其發展。
與比喻稍有不同但可以達到同樣效果的是利用同一領域的類比。也就是把一些不清楚的決策環境與歷史上人們熟悉的事件或情節進行類比,從而使人們對新的模糊不清的形勢有一個相對清楚的認識。杰維斯在研究錯誤認識產生時說,“國際上以前發生的事為政治家提供了廣泛的可以想象的環境,使他能探測到(事物間的)基本模式和因果關系,幫助他理解他的世界。”(注: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p.217.)如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形勢與歷史上希特勒占領捷克蘇臺德區后的形勢進行類比,從而看到美國決策者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和看法。(注:YuenFoongKhong,AnalogiesatWar:Korean,Munich,DienBienPhu,andtheVietnam
Decisionof1965(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2).)如布什政府最近用“邪惡軸心”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比作二戰期間的德、意、日等,這樣就可以看到美國外交決策者對這三個國家的認識。借用這樣的方法可以理解一些外交決策過程中決策者的認知心理過程。如美國決策者在做出對朝鮮戰爭進行干涉時的認知過程通過幾個比喻和類比則非常清楚了。首先,美國認為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是“禍水”,必須“裝(contain)”起來(比喻);其次,朝鮮戰爭的爆發被認為是莫斯科指導下的共產主義在全球進攻的一部分,這一點與事實是完全不符合的,因此可以說是一個錯誤的認識(misperception);第三,在產生了這樣的錯誤之后,美國決策群體運用了一個非常錯誤的類比,也就是把朝戰的爆發以及北朝鮮在戰場上的優勢比作希特勒占領蘇臺德區,日本占領中國東北,意大利占領索馬里等,如果不采取果斷措施,那就是綏靖。(注:杜魯門在回憶錄中敘述了他就是根據這樣類比來看待朝鮮戰爭爆發后的形勢的。見HarryTruman,Memoirs,vol.2,YearsofTrialandHope(Gardencity,N.Y.:Doubleday,1956),pp.332—333.)因此美國政府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導致了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對手打了一場戰爭。
另一種方法則是“一致程序(congruenceprocedure)”,也就是不研究決策過程,更不研究決策者的心理過程,因此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個人心理過程的詳細材料,只需一方面找出決策者的基本信仰,另一方面找出決策者國家的具體的外交行為,如果它們一致了,就說明決策者的信仰對這個國家的對外政策產生了影響。如沃克利用“行為準則”模式對基辛格的研究。這種方法相對來說要容易一些,但是,它只能回答對外政策決策者的信仰與決策結果之間的相互聯系(co-relation),而不能確定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更不能解釋外交政策決策者的信仰與外交決策結果之間不一致的現象。M·赫爾曼提出,一個處于支配地位的決策者是否對外交感興趣,對周圍環境是否敏感,以及是否有外交的經歷,或者是否受過相關專業的教育等三個變量可以解釋領導者的信仰與外交政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她通過對對外政策決策者的個性的研究試圖建立起決策者信仰與外交政策結果的關系,解釋為什么有時候決策者的信仰影響外交決策的結果,而有時候則沒有什么影響;為什么有的領導人的信仰影響其國家的對外政策,而有的領導人的信仰則不發揮作用。由于篇幅有限,這里不擬展開。(注:MargaretG.Hermann,“EffectsofPersonalCharacteristicsofPoliticalLeadersonForeignPolicy,”inWhyNationsAct,p.57;MargaretG.Herman,CharlesF.HermannandJoeD.Hagan,“HowDecisionUnitsShapeForeignPolicy:DevelopmentofaModel,”Paperpreparedforthe1991Annual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SocietyofPolitical
Psychology,Helsinki,Finland,pp.4-5.)
認知的視角只是外交政策分析(從廣義上說是對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研究)的視角之一。影響對外政策決策結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對外政策分析理論要求從多個角度和多個層次來研究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及其對外交政策結果的影響。但是由于認知的視角處于影響外交政策的所有變量與外交政策結果的之間,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各個層次,特別是隨著對外政策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認知的視角對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進行研究,包括對中國外交的研究。(注:研究中國外交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AllenS.Whiting早期對中國外交的研究《中國跨過鴨綠》(ChinaAcrosst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1960)和《中國深思熟慮的威懾》(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1975)都是采用傳統的理性行為的方法,但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關于中國外交的書則是從認知這個角度來研究的。見ChinaEyesJapa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類似的專著還有GilbertRozman,TheChineseDebateAboutSovietSocialism,1978—1985(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Shambough,BeautifulImperialist.YongDeng
andFeilingWang,eds.,IntheEyesoftheDragon,ChinaViewstheWorld(Lanham:Rowman&LittfieldPublishersInc.1999).GeraldChan,Chineseperceptionson
InternationalRelations:AFrameworkforAnalysis(London:MacmillanPress,Ltd.,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