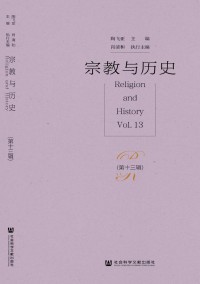宗教倫理儒學(xué)思考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宗教倫理儒學(xué)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我只是一個(gè)學(xué)歷史的人,又曾幸運(yùn)地參與了儒學(xué)文化的最后階段”.余英時(shí)作為當(dāng)代海外卓有建樹的歷史學(xué)家,以豐富的史料,對(duì)中國(guó)文化演進(jìn)歷史、內(nèi)在規(guī)律作實(shí)證描述與客觀考察,創(chuàng)建獨(dú)到的文化建設(shè)觀。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一個(gè)“韋伯式的問題”,開發(fā)中國(guó)文化礦藏,尋覓支持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倫理原因,在學(xué)術(shù)界發(fā)大音響。他在這方面所做的貢獻(xiàn)主要體現(xiàn)于他的名著《中國(guó)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一、對(duì)“新教倫理”的詮釋
在余英時(shí)看來,韋伯的理論貢獻(xiàn)在于:指陳西方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除了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的原因外還有文化與精神的原因,這樣的一種原因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背景,這也就是所謂的“新教倫理”,也稱為入世苦行(inner�worldlyascatechism)。
韋伯認(rèn)為,加爾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別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側(cè)重此種思想所波及的地區(qū)如荷蘭、英國(guó)等地。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達(dá):勤勉節(jié)儉天職罪。如余英時(shí)所表達(dá),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儉、誠(chéng)實(shí)、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勵(lì)人們“以錢生錢,而且人生就是以賺錢為目的,不過賺錢既不是為了個(gè)人的享受,也不是為了滿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換句話說,賺錢已成為人的‘天職’,或中國(guó)人所謂‘義之所在’”。這樣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則是在這種精神支配下,人必須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來實(shí)現(xiàn)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將韋伯思想與馬克思?xì)v史唯物主義相比較,指出韋伯所論,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zhǔn)”的歷史理論,因此不可原封不動(dòng)的套用于中國(guó)史研究。但韋伯的理論又和馬克思的理論一樣,“其中含有新觀點(diǎn)與新方法”,足以啟發(fā)非西方社會(huì)的歷史研究。相對(duì)于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濟(jì)決定論,韋伯認(rèn)為文化與精神也可以在歷史運(yùn)行中發(fā)生重要作用。
不過韋伯也不是“歷史唯心論者”,他在肯定宗教對(d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shí),又認(rèn)為資本主義不純粹是宗教改革的結(jié)果。如余英時(shí)所分析,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的興起可以歸結(jié)于三個(gè)互相獨(dú)立的歷史因素: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社會(huì)政治組織以及當(dāng)時(shí)占主導(dǎo)地位的宗教思想。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是在此三者交互影響下發(fā)生的。這樣,韋伯便從多元視野,對(duì)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起因與結(jié)果,作出廣泛意義上的判斷。他對(duì)新教倫理與西方發(fā)展的關(guān)系所做的不同凡響的解讀,某種意義上啟發(fā)歷史學(xué)家對(duì)世界社會(huì)發(fā)展史做重新審訂。
二、一個(gè)“韋伯式的問題”
余英時(shí)試用韋伯觀點(diǎn)對(duì)中國(guó)歷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問的是:在西方資本主義進(jìn)入中國(guó)之前,中國(guó)的傳統(tǒng)宗教理論對(duì)中國(guó)商業(yè)活動(dòng)究竟有沒有影響?如果有影響,具體內(nèi)容又是什么。他承認(rèn)自己提出的是一個(gè)“韋伯式的問題”。
他也生怕所從事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的理論,但又說盡管已經(jīng)歷史所用的方法相同,但只要結(jié)論不同,就可以避免這個(gè)傾向。余英時(shí)研究的結(jié)果,中國(guó)傳統(tǒng)宗教對(duì)本國(guó)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曾經(jīng)起過積極的作用,而韋伯則在他有關(guān)中國(guó)文化的論述中竭力說明:中國(guó)傳統(tǒng)宗教與文化無(wú)法導(dǎo)引出類似西方的資本主義。
這里我們要介紹的余英時(shí)的文章(實(shí)際已成一部著作的規(guī)模)的題目是《中國(guó)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全文共分三編:上編,中國(guó)宗教的入世轉(zhuǎn)向。這一部分主要研究中唐以來新禪宗與新道教。中編,儒學(xué)理論的新發(fā)展。重點(diǎn)分析新儒家與新禪宗的關(guān)系,并論及中國(guó)宋明理學(xué)的發(fā)展,具體分析由程、朱到陸、王各種思想的發(fā)展情況。下編,中國(guó)商人的精神。以十六至十八世紀(jì)為時(shí)代斷限。他說自己在這編中所照應(yīng)到的不是商業(yè)發(fā)展的本身,而是商人和傳統(tǒng)宗教倫理特別是新儒家的關(guān)系。這三編有獨(dú)立性,但又相互關(guān)照,連成一個(gè)完整的體系。
余英時(shí)在文中提出一個(gè)重要議題,即入世與出世的問題。他覺得這個(gè)問題關(guān)系到世界各地區(qū)表現(xiàn)出的“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gè)共同特征。
一個(gè)宗教要使其與現(xiàn)代化結(jié)合,并對(duì)其發(fā)揮有益作用,一個(gè)緊要的問題就是一方面是“出世”的,一方面又是“入世”的,承認(rèn)“此岸”,重視人生,以出世的超越精神,盡力做入世的最現(xiàn)實(shí)的事。余英時(shí)論及唐代佛教變化,指論從社會(huì)史角度來看,重要一點(diǎn)就是從出世轉(zhuǎn)向入世。而惠能所創(chuàng)造的新禪宗,在這一發(fā)展上尤具突破性和革命性的成就。余英時(shí)說,有人稱他們是中國(guó)的馬丁·路德是有理由的。惠能立教的基本意義是“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后世通行的《壇經(jīng)·機(jī)緣品》記錄他的話,有“字即不識(shí),義即請(qǐng)問”等語(yǔ)。他還說,惠能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說,在當(dāng)時(shí)佛教界是一個(gè)獅子吼。佛教精神從出世轉(zhuǎn)向入世,便是從這一句話中體現(xiàn)出來。不過余英時(shí)也承認(rèn),惠能的宗教革命最初僅限于佛教范圍之內(nèi),而且唐代的宗教派別甚多,禪宗不過是其中的一支,這一革命實(shí)際上是靜悄悄地發(fā)生在宗教世界的一個(gè)角落里,并沒有掀動(dòng)整個(gè)世俗的社會(huì)。
正如余英時(shí)所分析的,路德也好,加爾文也好,還都是將此世看成是負(fù)面的,是人的原罪的結(jié)果。但是他們的進(jìn)步在于他們已經(jīng)反對(duì)單純的寺院修煉,已經(jīng)覺悟只有入世盡人本分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途徑。他們的“天職”觀,更力證入世符合上帝愿望。入世苦行的思想,之所以在加爾文的教派中發(fā)展到最高,是因?yàn)樗奶炻氂^更加積極,對(duì)入世理論的辯護(hù)更有力。余英時(shí)引《壇經(jīng)》第三十六節(jié)中《無(wú)相頌》,曰:“法元在世間,于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這一《頌》在通行本中又改成:“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其所含的“入世”意義就更加清楚了。《五燈會(huì)元》卷三有《百丈懷海章》記載:“師凡作務(wù),執(zhí)勞必先于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qǐng)息之。師曰:吾無(wú)德,爭(zhēng)合勞于人?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yǔ)流播寰宇。”余英時(shí)說,從百丈的語(yǔ)言中可見,他們?cè)趫?jiān)持一種教義,已經(jīng)對(duì)傳統(tǒng)的教義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轉(zhuǎn)化,在教徒的心中發(fā)生高度的緊張。因?yàn)橐郧胺鸾掏皆谑聦?shí)上不能完全免于耕做是一回事,而現(xiàn)在已經(jīng)完全確定耕作的必要?jiǎng)t是另一回事。推斷百丈的話語(yǔ),只要作事而不滯于事,則無(wú)罪可言。這是用超越與嚴(yán)肅的精神來盡人在世間的本分。
余英時(shí)在說到新道教時(shí),稱道全真教云:全真教有兩個(gè)理論,一是“默談玄機(jī)”,即是“識(shí)性見性為宗”;一是“打勞塵”,即是“損己利物為行”。所要說的是若無(wú)前者,終生在勞動(dòng)中打滾,永無(wú)超越的可能;若無(wú)后者,則空守一心,也不能成道。余英時(shí)說,這實(shí)際上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yè),稍知加爾文教義者不難看出這正符合‘以實(shí)際意識(shí)和冷靜的功利觀念與出世目的相結(jié)合。’”余英時(shí)論全真教與禪宗也有不同的地方,它的入世傾向在一開始便比較明顯,比禪宗來得更直接與深切。新道教對(duì)中國(guó)民間有深而廣的影響,其中有一個(gè)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歷劫,在人間完成“事業(yè)”以后才能“成正果”、“歸仙位”。同時(shí)凡人要是想成仙也必須“做善事”、“立功行”。
前面說的是禪宗與道教。如果說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人們自然會(huì)想到“儒、釋、道”。余英時(shí)在論說中國(guó)傳統(tǒng)中的近代性轉(zhuǎn)化時(shí)也將目光注意到儒家。他承認(rèn)中國(guó)儒學(xué)發(fā)展到宋明時(shí)代是一大轉(zhuǎn)折,從這時(shí)候起中國(guó)儒家出現(xiàn)了近代性演化。
他論說克勤克儉、光陰可惜的思想都是儒家的古訓(xùn),但是到后來,尤其是門第時(shí)代,這樣的思想便被無(wú)形中淡化。到了新禪宗入世運(yùn)動(dòng)發(fā)起,特別是新儒家發(fā)生之后,中國(guó)儒家中的這種思想種子再次闡發(fā)。朱子在教育門人時(shí)常說:“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wú)一歲,只見老大,或然死者”。余英時(shí)說,新儒家將浪費(fèi)時(shí)間看作是最大的罪惡,與新教倫理毫無(wú)二致。不過他說,“在這一問題上新儒家其實(shí)也受到了佛教的刺激”。朱熹有言,“在世間吃了飯后,全不做些子事,無(wú)道理。”余英時(shí)解釋云:這里所說的做事雖然不全部說是生產(chǎn)勞動(dòng),但其所宣揚(yáng)的是只要在做對(duì)社會(huì)有益的事,則可以心中無(wú)愧。這和新教的工作觀依然十分相似。新教認(rèn)為人必須有“常業(yè)”(fixedcal-ling)。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去從事同一類職業(yè),即使不是體力勞動(dòng),只要為上帝努力“做事”即可。余英時(shí)說,只要將上帝換為“天理”,即可發(fā)現(xiàn)新儒家的社會(huì)倫理有許多與新儒家的思想合節(jié)。新儒家與以往的儒教最大不同之處是前者找到了生命超越的根據(jù)。新教徒以為入世苦行是上帝的絕對(duì)命令,上帝的選民必須以此世的成就來保證彼岸的永生,新儒家則相信“天理”,人生在世,必須在自己的崗位上勤勉“做事”以“盡本分”。做事不是消極的,必須“主敬”。主敬的方向一方面是對(duì)“事”,另一方面對(duì)于消除內(nèi)心緊張來說,又其所敬方向又是對(duì)“天”,對(duì)“理”,這樣中國(guó)新儒家就有了宗教承當(dāng)?shù)囊饬x提升。
三、心、性說新解與“信仰得救”中國(guó)禪宗強(qiáng)調(diào)“心、性”。《壇經(jīng)》第二十八節(jié)說“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慧觀照,不假文字。”余英時(shí)解說惠能的觀點(diǎn)與馬丁·路德的思想已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即重在“本性”,自由解經(jīng),“不死在句下”。敦煌寫本《壇經(jīng)》三十一節(jié)說:“三世諸佛,十二部經(jīng),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得善知識(shí)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shí)。若求善知識(shí),望得解脫,無(wú)有是處。識(shí)自心內(nèi)善知識(shí),即得解脫。”
宋明新儒學(xué)與以往儒學(xué)最大的不同之處是關(guān)于心性論的闡述。如余英時(shí)所說,韓愈雖然首創(chuàng)儒學(xué)的復(fù)興,但在心性論方面無(wú)所貢獻(xiàn)。他有《原性》一文,但與宋明的思想境界距離甚遠(yuǎn)。在韓愈的時(shí)代,只有禪宗有心性的功夫,儒家在這方面完全是一個(gè)空白。新禪宗“求心見性”,對(duì)俗世的吸引力就在這里,給世人(顯然也包括中國(guó)儒家)提供了一個(gè)精神上的最后歸宿,俾使人得以“安身立命”。與韓愈同時(shí)的還有李翱,著《復(fù)性書》三編,注意以《中庸》、《易傳》為根據(jù),討論心性。他的觀點(diǎn)沒有擺脫佛教糾葛,但心性學(xué)萌蘗初現(xiàn)。余英時(shí)說明,真正的心性學(xué)直至宋朝新儒家出現(xiàn),方逐漸達(dá)至成熟境界。事實(shí)上將朱子理學(xué)與陽(yáng)明心學(xué)作比較,將儒家心性之學(xué)加以發(fā)展具有最大貢獻(xiàn)的應(yīng)說是后者。王陽(yáng)明承續(xù)思孟學(xué)統(tǒng),收納佛學(xué)精粹,反對(duì)死守經(jīng)典,主張內(nèi)觀本心。他以“良知”釋心性,將中國(guó)儒家的心性思想推至高峰。
西方新教思想中有“因信稱義”的說法,反對(duì)宗教煩瑣的禮儀,認(rèn)為信徒只要內(nèi)心具備真誠(chéng)的信仰,就可能獲得上帝的信任與愛顧,成為神的“選民”。余英時(shí)認(rèn)為,禪宗的“求心立命”與新儒家的心性論,已具備西方新教“因信稱義”的精神內(nèi)容。
余英時(shí)說,我們已經(jīng)看到一個(gè)事實(shí),即新禪宗對(duì)新儒家的最大影響不在“此岸”而在“彼岸”。儒家自始即在“此岸”,是所謂“世教”,在這一方面自無(wú)待于佛教的啟示。但是到了南北朝之后,佛教與儒學(xué)士大夫都已經(jīng)看到儒家只有“此岸”而無(wú)“彼岸”,以儒家的習(xí)用語(yǔ)言即是有“用”而無(wú)“體”、有“事”而無(wú)“理”,這是一個(gè)嚴(yán)重的問題。
新儒家因新禪宗的挑戰(zhàn)而開展自己的心性論,最后找到了“彼岸”。但是也要看到新儒家的“彼岸”論一開始就不同于佛教的彼岸論,儒家的彼岸是“實(shí)有”而不是“空寂”。誠(chéng)如朱子所說:“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shí);釋言無(wú),儒言有。”所以儒家所建立的“彼岸”只能是“理”的世界與形而上的世界。同時(shí)中國(guó)心性論的建立又表明,一個(gè)信仰者只有通過對(duì)“心”的關(guān)照,才能獲得對(duì)“理”的覺悟。
我們通常都在說“終極關(guān)懷”,但關(guān)懷的到底是什么?似乎誰(shuí)也說不清楚,其實(shí)這樣的“關(guān)懷”也就是對(duì)生命的“最終理由”,即“生命基礎(chǔ)”的關(guān)懷。在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地區(qū),都將這種理由與“神”連接在一切。而儒家的世界里沒有神,而讓人生與“天命”、“天理”以及“心、性”聯(lián)系在一起。強(qiáng)調(diào)前者的是朱子的理學(xué),強(qiáng)調(diào)后者的是王陽(yáng)明的心學(xué)。
王陽(yáng)明思想在中國(guó)為什么不能成為主流學(xué)說?這實(shí)在是一個(gè)有趣味的問題。這也許因?yàn)椋膶W(xué)太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知覺,天理與天命意識(shí)被沖淡。這就產(chǎn)生兩個(gè)弊病。其一是從人的深層意識(shí)來說,都有一個(gè)依賴感的問題。人的依賴感覺是在童年時(shí)代因?qū)δ赣H的依賴而發(fā)生發(fā)育出來,進(jìn)而成了終身的心理記憶。王陽(yáng)明思想使人只是相信自己,使這樣的依賴得不到最安全的安放位置。“依賴”表現(xiàn)為權(quán)威與外界兩個(gè)因素,如果不是“外界”的,就沒有安全;同樣如果不是“權(quán)威”的也不會(huì)有安全。王陽(yáng)明將個(gè)體的良知確定為主要的,就使這兩個(gè)條件部分地失去了。顯然理學(xué)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外界的最大權(quán)威“天理”的“依賴”,可依賴感自然要?jiǎng)龠^“良知”。我們承認(rèn)宗教的設(shè)神說教對(duì)人有更大的可供依賴的成分,也就是這樣的原因,世界大多數(shù)民族都有宗教。中國(guó)沒有宗教,而創(chuàng)造出“天命”與“天理”,到后來將天命改為了天理,取消其最后的宗教氣息。這也許是因?yàn)橹袊?guó)不容有天上的“神”與地面的“皇”爭(zhēng)奪權(quán)威的緣故。強(qiáng)調(diào)“天理”也被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特點(diǎn)所決定。心學(xué)說“心”,人皆有“心”,其“心”何多,則國(guó)家與民族思想容易走上渙散的一途。說天理只有“一個(gè)”,對(duì)于一個(gè)統(tǒng)合社會(huì)來說,更具有思想的契合性。
以上所說,只是一種“也許”的假說,筆者曾經(jīng)有過這樣的見解。然而做細(xì)致的思考又發(fā)覺,心學(xué)對(duì)于世道人心的匡正,又比理學(xué)來得有效。這是因?yàn)椋蹶?yáng)明所說的“心”(也包括王陽(yáng)明之前心學(xué)開創(chuàng)者如陳白沙等人的思想)不是一個(gè)懸空不定的“心”,王陽(yáng)明也說天理。只是,他要搞清楚的是天理與心之間的關(guān)系。
請(qǐng)看他與自己學(xué)生的對(duì)話。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王陽(yáng)明回答:“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愛又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陽(yáng)明則曰,“心即埋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說:“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fā)之事父便是孝。發(fā)之事君便是忠。發(fā)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誠(chéng)然,朱熹說天理是在建立彼岸世界,然而怎樣使天理到達(dá)人心呢?他的意見先求于外,由外至內(nèi),因此有“格竹子求天理”的故事。所設(shè)計(jì)的精神通道是:格物求理。這樣,求“理”的方法就顯得煩瑣,向“理”的道路總覺得壅塞。而陽(yáng)明的精神路徑則通捷得多:“致良知”“天理”,或者說是“直觀本心”即可得到達(dá)“天理”。強(qiáng)調(diào)只要“心”里“有”著,“天理”的光線就可以直射心扉,使內(nèi)心精神通徹透明。理在我心,不必外求。與朱熹比較,王陽(yáng)明同在建立中國(guó)人的彼岸世界,但是這個(gè)彼岸不是遙不可及,而是捫心可悟,垂首可見。如果說朱熹所社的彼岸遠(yuǎn)在天邊,陽(yáng)明的彼岸即在心頭。一個(gè)有信仰的人不假它物,直與天理溝通。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朱熹之功在于建立了中國(guó)人的信仰世界。他的“理”實(shí)是一個(gè)信仰光源,是中國(guó)式的“彼岸”世界。朱熹之弊在于,他沒有找到一個(gè)通向“信仰”與彼岸的方法與道路,他所設(shè)計(jì)的“格物致知”方法,難以實(shí)行。如此,屋無(wú)窗無(wú)法照見“理”的光源;海無(wú)舟無(wú)法抵達(dá)“理”的彼岸。明知有“理”,無(wú)法至“理”,無(wú)奈而嘆!陽(yáng)明之功在于直說“心”的意義,實(shí)際是說何必開窗,心即為窗,何必借舟,心即為舟,何必格物以求“理”,心即是理。理為信仰的目標(biāo),心為信仰的根據(jù)。堅(jiān)其信仰的根據(jù),理必獲得。有心方有理,無(wú)心理難得。顯然,與朱熹比較,陽(yáng)明的心學(xué)更與基督教新教所主張的“因信稱義”相近,在建立現(xiàn)代性信仰世界方面所做的貢獻(xiàn)更大一些。
四、憂心
余英時(shí)也為儒學(xué)的21世紀(jì)前景憂心,恐其將為“游魂”。他說,從全面來看,中國(guó)近世的宗教轉(zhuǎn)向其最初發(fā)動(dòng)之地是新禪宗。
新儒家的運(yùn)動(dòng)是第二波;新道教更遲,是第三波。這是唐宋以來中國(guó)倫理發(fā)展的整個(gè)趨勢(shì)。“這一長(zhǎng)期發(fā)展最后匯歸于明代的‘三教合一’”.然而儒家于中國(guó)將來的命運(yùn)究竟是怎樣的呢?中國(guó)有沒有儒家復(fù)興的希望?中國(guó)以至東亞是不是如同杜維明所說的有一個(gè)“儒學(xué)第三期發(fā)展”的前景?對(duì)于以上的問題,余英時(shí)的論文透出些須的疑惑,為儒家于今后的困境為難。
關(guān)于儒學(xué)再興,余英時(shí)覺得有一個(gè)問題需要解決,即是致力發(fā)揮其固有的“踐履”精神與“人倫日用”性格,還是象現(xiàn)在這樣僅將其局限于一種“論說”。如屬前者,儒學(xué)便以“游魂”為其現(xiàn)代命運(yùn)。后者,“則怎樣在儒家價(jià)值和現(xiàn)代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之間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聯(lián)系”,又是一個(gè)不易解決的難題。
問題在于儒學(xué)的存在與其所依附的制度有著重要的聯(lián)系。儒學(xué)與制度的關(guān)系既然已經(jīng)被割斷,儒學(xué)存在的前提也就沒有了。不同的是,基督教曾經(jīng)與世俗制度結(jié)合在一起。宗教改革與啟蒙運(yùn)動(dòng)之后,宗教與世俗制度是分離了,但它是有教會(huì)組織的宗教,最后還可以寄托在教會(huì)制度之中。
他又認(rèn)為,中國(guó)在傳統(tǒng)時(shí)代到處有講學(xué)的地方,書院、私塾與明倫堂,通過鄉(xiāng)約、小學(xué)、勸農(nóng)、義莊、族規(guī)作多方面的努力,盡量將儒家倫理推廣到社會(huì)去。譬如明末清初朱伯廬根據(jù)儒家倫理所寫的《治家格言》,就是因?yàn)橛辛松鲜鰲l件才在社會(huì)中獲得廣泛流傳。現(xiàn)在儒學(xué)已經(jīng)沒有這樣的條件。儒學(xué)只在大學(xué)里才具一席之地,只能依附在大學(xué)制度之中,此外只有一些零星的儒學(xué)社群,但也往往依附在大學(xué)體制之中。余英時(shí)發(fā)問:“那么是不是儒學(xué)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學(xué)講堂和少數(shù)學(xué)人的講論之間?這樣的儒學(xué)其可能的最高成就是什么?”是的,我們同意余英時(shí)的說法。一個(gè)有價(jià)值的學(xué)說,必須在“人倫日用”中發(fā)揮作用,而不能僅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對(duì)象。
假如中國(guó)無(wú)論從家庭到社會(huì)“儒家教育都沒有寄身之處”,而只是駐留在大學(xué)的講堂之上,那么任其一部分知識(shí)分子論說現(xiàn)代儒家思想如何高妙,“又怎樣能夠傳播到一般人的身上呢?”,80年代新加坡“‘儒家倫理計(jì)劃’的失敗便是一個(gè)前車之鑒。”從余英時(shí)研究的成果中我們依稀間看到了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儒、釋、道)中現(xiàn)代精神的微弱閃光,雖其“微弱”,畢竟“閃光”,由此增添從事中國(guó)文化建設(shè)的信心。余英時(shí)的研究又告訴我們,儒家文化在今天的更新所遇到的困難將會(huì)很大。中國(guó)人的“精神貧困”,不亞于物質(zhì)的貧困,中國(guó)人在精神建設(shè)上所化的力氣,將不會(huì)少于物質(zhì)建設(shè)。
文檔上傳者
- 宗教
- 宗教藝術(shù)
- 宗教
- 宗教藝術(shù)
- 宗教藝術(shù)
- 科學(xué)宗教
- 反宗教傳統(tǒng)
- 宗教對(duì)英語(yǔ)影響
- 宗教永恒哲學(xué)
- 宗教和科學(xué)
熱門文章排行
相關(guān)期刊
- 宗教事務(wù)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