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有限政府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法和有限政府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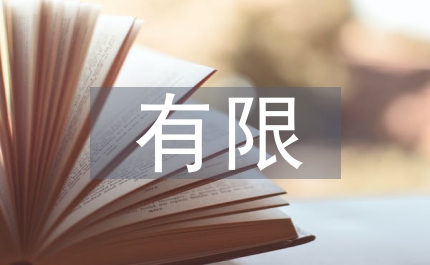
洛克被稱為“自由理論之父”1,對自由主義諸原則作了最早的理論闡述。他對宗教寬容、政治自由及經濟自由所作的論述涵括了現代自由主義的大部分問題,構筑了一個以“開明國家”為核心的、包括自然權利、寬容、法治和反抗等理論的早期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如果說自由是洛克政治思想的出發點,那么,法治便是其歸宿。本文擬對洛克法治思想進行梳理,旨在分析其運思理路,進而說明,自由是洛克法治思想的根本規定,法治的基礎在于個體權利確立,法治針對的是無限制的專制王權,而它的最終落實,則賴于有限政府(憲政)的建構。
一.權利:法治的基礎
洛克自由主義思想以自然權利為根基。與先前和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一樣,洛克把自然狀態設定為他的政治思想的邏輯起點。“洛克設想自然狀態的目的不是為說明人們像什么樣子,而是為了說明人們作為上帝的創造物有哪些權利和義務”2,從而闡明政治權力出現的邏輯基礎。這個基礎將決定著政治權力的面貌:“為了正確地了解政治權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們必須考究人類原來自然地處于什么狀態。”3。洛克雖繼承了自然法理論傳統,但是卻使這一傳統發生轉變,“古代自然法的學說在近代思想發生了本質變化,自然法從規范人們行為的法則轉變為個人的自然權利。對這一轉變作出最早貢獻的是霍布斯,而使這一轉變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則是洛克。”4由此,洛克開創了以自然權利來達至自由的路徑的先河,這和日后的功利主義構成了論證自由主義合理性的兩大理路。洛克以權利構造自由時,是分兩步作出理論闡述的。
第一步,洛克嘗試說明人類處于自然狀態時的權利處境。
上帝造人,人類社會始于自然狀態,人從自然法(上帝)那里所獲得的自然權利。洛克把自然狀態定義為:“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他們在自然法的范圍內,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和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而毋須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5同時洛克又加以這樣的限定:“這也是一種平等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一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沒有一個享有多于別人的權力。”6因為自然法對自然狀態起支配作用,自然法,即理性,指導著生活于其下的人們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至這一切的終極原因,洛克訴諸上帝,“上帝既創人類,便在他身上,如同在其他一切動物身上一樣,扎下了一種強烈的自我保存的愿望”7。人皆為上帝的創造物,人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的生命都無奪予之權,基于以上這點,以及上帝給予人同等的能力和共享同為上帝所創的世界權利,因而人是平等的。除了生命、財產和自由的權利外,在自然狀態中,人還有兩種權利(或權力):“第一種就是在自然法的許可范圍內,為了保護自己和別人,可以做他認為合適的任何事情"8,第二種則是“處罰違反自然法的罪行的權力”9。
上述的定義和界定突顯了自然狀態中人的權利——自由行動和處理財產、人身之權利——與保存自身及自保不成問題時保存他人的義務,而理性則為這些權利義務的基礎。同時,由于理性,自然狀態“是自由的狀態,卻不是放任的狀態。”10在自然狀態中,自然法即理性,是為上帝所賦予的、自然狀態中先驗存在于人的內心與行為的唯一尺度,其中的人以個人身份獲得權利義務,從而構成了自然法的法權主體,因而個人就是具有自主性的個人,換言之,在洛克的自然狀態中,人與人的關系是遵從個人主義的,秩序與人際關系的基點是具有生命、財產與自由權利的個體。
第二步,洛克闡明人類由自然狀態過渡到政治社會后的權利境況。
處于自然狀態的人是自由與平等的,卻不是完美的,因為自然狀態不存在共同的裁判,“充滿恐懼與經常危險”11。具體而言,自然狀態的缺陷體現在三方面:第一,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種確定的、眾所周知的法律,以作為大家共同接受和承認的是非標準和裁判他們之間一切糾紛的共同尺度。第二,在自然狀態中,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來裁判一切爭執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在自然狀態中,往往缺少權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并使它得到應有的執行。由于自然狀態存在這些缺陷,生命、財產和自由這些自然法賦予人的權利便得不到保障。于是洛克認為,只有從自然狀態過渡到政治社會、建立公民政府,人的自然權利才能得到保障,而過渡的途徑就是人們訂立契約,過渡的代價是放棄個人的自保及自保不成問題時保護他人的權力與懲處違反自然法者的權力:“真正的和唯一的政治社會是,在這個社會中,每一成員都放棄了這一自然權力,把所有不排斥他可以向社會所建立的法律請求保護的事項都交由社會處理。”12具體來說,“第一種權力,即為了保護自己和其余人類而做他認為合適的任何事情的權力,他放棄給了社會,由它制定的法律就保護他自己和該社會其余的人所需要的程度加以限制。……第二,他把處罰的權力完全放棄了,并且按社會的法律所需要的程度,應用他的自然力量(以前,他可以基于他獨享的權威,于認為適當時應用它來執行自然法)來協助社會行使執行權。”13需強調的是,作為自然權利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的權利卻留歸個人。同時,這些權利構成了政治社會中政治權力的界限。
在洛克的理路中,通過契約從自然狀態過渡到政治社會的人們,他們的自然權利——財產、生命權——并沒有讓渡出去,而是留歸個人;個人以這些保留下來的權利構筑自治的市民社會。對于由個人交出某些權利所形成的政治權力及其實體國家,洛克又把他們圈定在保護生命、財產和自由的范圍內。“在洛克的學說中,個人是第一位的,社會、國家是第二位的;個人是本源,社會、國家是派生的;個人是目的,社會、國家是手段。”14社會先于國家產生,國家對社會、個人作出承諾。因此,洛克在自然狀態中所發現的個人主義基因經契約換算后并沒有因讓渡出自然權力進入政治社會而丟失或變異,而是成為政治社會個體自由的重要資源。而政治社會中的秩序,以及指導秩序的規則,是以擁有生命、財產和自由權利的個體的人為基礎的,換言之,政治權力是以個體出讓部分權利的結果,權力由權利生成,權力在權利之下。
二.專制王權:法治的敵人
“洛克譴責所有形式的專制主義。”15個人從自然狀態中獲得不可讓渡的生命、財產和自由的權利,并且這些權利并不能因為自然狀態向政治社會狀態的過渡而失去,但這些權利并不會自動獲得保護,即使在政治社會中,它們依然面臨著許多威脅。對洛克而言,對這些權利的最大威脅就是專制主義了。
洛克對專制主義批判的立足點仍然落于自然法所賦予的平等、不可讓渡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權利。“專制權力是一個人對于另一人的一種絕對的專斷的權力,可以隨意奪取另一個人的生命。這不是一種自然所授予的權力,因為自然在人們彼此之間并未作出這種差別。它也不是以契約所能讓予的權力,”16既然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賦予,那么,人就沒有剝奪自己的生命的權力,那么,任何人也就不會擁有支配他人生命的權力。當以專斷的權力來支配他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時,行使專斷權力的人便“拋棄了上帝給予人類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準則的理性,脫離了使人類聯結成為一個團體和社會的共同約束,放棄了理性所啟示的和平之路,蠻橫地妄圖用戰爭的強力來達到他對另一個人的不義的目的,背離人類而淪為野獸,用野獸的強力作為自己的權利準則”。17
專制主義不僅是生命、財產和自由權利的最大威脅,而且在專斷的權力下,人的權利境況還不如在自然狀態下可欲,“如果不是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權利和財產品見,如果沒有關于權利和財產的經常有效的規定來保障他們的和平與安寧,人們就不會舍棄自然狀態的自由而加入社會和甘受它的約束。不能設想,如果他們有權力這樣做的話,他們竟會有意把支配他們人身和財產的絕對的專斷權力交給一個人或較多的人,并給予官長以力量,由他任意地對他們貫徹他的毫無限制的意志。這是要把自己置于比自然狀態更壞的境地,在自然狀態中,他們還享有保衛自己的權利不受別人侵害的自由,并以平等的力量進行維護權利,不論侵犯是來自個人或集合起來的許多人。”18既然專制王權之下人的權利境況不如自然狀態,那么,專制王權絕不應是自然狀態過渡的方向與目標,它與洛克的理想——公民社會——是絕然相反的:“絕對統轄權,無論由誰掌握,都決不是一種公民社會,它和公民社會的格格不入,正如奴役地位與財產制格格不入一樣。”19
洛克之所以拒斥專制王權,原因還在于他對人性的較為樂觀的估計:人們在他們自己交出兩種自然權力及這兩種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情況下,人們能理性地運用其所保留的其余自然權利(自由、生命和財產權)而自由和平地生活,并不需要一個充訴全社會的霍布斯式的“利維坦”來保證社會秩序的實現。
三.法與有限政府:法治的精神
以自然權利為基礎,洛克看到了自然狀態的缺陷,進而指出人類要從自然狀態向政治社會過渡的必要性,但是,政治社會有可能走向專制。而專制主義與人的自然法所賦予的不可讓渡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權利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政治社會應如何建構?為此,洛克以法與有限政府的理論來塑造政治社會。
在洛克的理路中,法與有限政府的理論是與自然狀態相勾連、與專制王權邏輯相反的。或者說,法與有限政府理論是以自然狀態和專制王權作為參照系的。它們兩者的共通之處在于缺少共同的裁判者:自然狀態在橫向維度上、公民與公民之間缺共同裁判者;專制王權在縱向維度上、公民與政府之間缺少共同裁判者。兩者都易淪為戰爭狀態。
如前所述,洛克認為自然狀態存在三種缺陷:缺少確定、眾所周知的法律;缺少裁判者;以及缺少執行自然所需的必要權力。洛克認為,“那些不具有這種共同申訴--我是指在人世間而言--的人們,還是處在自然狀態中,因為既然沒有其他的裁判者,各人自己就是裁判者和執行人,這種情況……是純粹的自然狀態。”20在自然狀態中,“由于人人有懲罰別人的侵權行為的權力,而這種權力的行使既不正常又不可靠,會使他們遭受不利”21因為,“人們充當自己案件的裁判者,這方面的不利之處確實很大,因為我們很容易設想,一個加害自己兄弟的不義之徒就不會那樣有正義感來宣告自己有罪。”22在專制王權下,“只要有人被認為獨攬一切,握有全部立法和執行的權力,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君主或他的命令所造成的損失或不幸,就無法向公正無私和有權裁判的人提出申訴,通過他的裁決可以期望得到救濟和解決。因此,這樣一個人,不論使用什么稱號--沙皇、大君或叫什么都可以--與其統治下的一切人,如同和其余的人類一樣,都是處在自然狀態中。”23
在自然狀態中,“人們受理性支配而生活在一起,不存在擁有對他們進行裁判的權力的人世間的共同尊長,他們正是處在自然狀態中。但是,對另一個人的人身用強力或表示企圖使用強力,而又不存在人世間可以向其訴請救助的共同尊長,這是戰爭狀態。”24另一方面,“誰企圖將另一個人置于自己的絕對權力之下,誰就同那人外于戰爭狀態”。25由此,自然狀態與專制王權將由于共同裁判的缺位,而淪為戰爭狀態:“戰爭狀態是一種敵對的和毀滅的狀態。因此凡用語言或行動表示對另一個人的生命有沉著的、確定的企圖,而不是出自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就使自己與他對其宣稱這種意圖的人處于戰爭狀態。”26敵對與毀滅的狀態下,個體的生命、財產與自由權利又何從保障?既然每個個體都平等地擁有自然法所賦予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權利,在自然狀態中,每個個體以自然法為參照是平等的,但自然法的執行權在在每個人手中,亦即是說,此時自然法便是與涉案者同一了,這對于涉案的另一方來說,就沒有平等可言了;在專制王權下,則專制統治者的意志成了統治者與公民關系的準則,平等更是無從談起。于是,在自然狀態——橫向維度上——沒有實在的共同準則來規范的個體間關系;在專制王權下——縱向維度上——沒有共同“尊長”調整統治者與公民的關系。因此,必須構建共同的尊長、共同的裁判者來避免自然狀態、專制王權的弊端,走出戰爭狀態。
由此,共同尊長、共同裁判者的建構就成了確立公民社會的關鍵了。在洛克的理論邏輯中,共同尊長、共同裁判者就是維系社會秩序的一種規則(法),這種規則(法)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說,對于具體的發生沖突的各方(包括政府、統治者)而言,規則是第三方,與沖突各方利益無涉,不能與任何一方同一,否則就不具超越性。易言之,人不能充當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規則也不能為涉案者所規定與操縱。通過這種超越性的規則,社會橫向層面上可以理順公民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在縱向層面上則可調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這種承認超越性規則(法)、以超越性規則(法)主治的政治社會,就是處于法治狀態了。而由這種具有超越性規則所主導的政治秩序,也就是憲政了——即通過確立作為根本規則的憲法,然后以憲法規范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安排程式,對整個政府的組成及運作程序作出規定,換言之,憲政就是對政治權力、公民權利的具體內容的規定和對兩者邊界的劃定,旨在為政治生活提供一個政治架構和秩序指南。法治是憲政的狀態描述與價值所在,而憲政則是法治的實體化與程序化。由法治與憲政所塑造的政府,就是有限政府了——政府權力受到法的約束。具體而言,洛克的法治與憲政構建有如下幾點:
首先,確定不可侵犯與剝奪的公民權利,以這些公民的權利限定政府權力運行的范圍,從而使這些公民權利構成政府權力的邊界。洛克說,“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27,洛克這里所指的財產是包括生命、財產與自由的28,換言之,保護生命、財產與自由的權利就成了政府的目的。“政府除了保護財產之外,沒有其他目的”29,在此,洛克則指出了政府權力的范圍。
其次,是具有至高性的法的確立。在洛克的理論中,法的至高性體現為兩個方面:首先,告別自然狀態,以“同意”為前提訂立契約過程,實質也就是創憲的過程。契約的訂立,也就意味著憲法(Constitution)的產生。而政治(公民)社會、政治權力是契約——(憲)法的產物,這本身即意味著契約——(憲)法高于政治權力,政治權力、政治社會為(憲)法所統治,作為契約產物的政府,本身即意味著政府之權力不能超越契約,是契約之下的政府。其次,契約——(憲)法高于成文法。在洛克看來,法是同意與契約的產物,同時更是源自自然法,支配立法權最初和最基本的亦是自然法,“人們制定的成文法律不能夠決定其本身就是一切法律和政府的基礎,而且它的法則只是從上帝和自然的法律那里接受而來的東西。”30所以法并不是純粹的人為之物,而只是先驗的自然法的一種表達和發現而已,人類所制定的法律必須服從自然法。在此意義上,法是一種超驗價值。
同時,法律雖是作為擁有“最高權力”立法機關所制定,但其效用卻具有兩面性,即從國家出發,限制和支配政治權力;以及從個人著眼,保障個人自由。在此基礎上,洛克指出,“哪里沒有法律,那里就沒有自由。這是因為自由意味著不受他人的束縛和強暴,而哪里沒有法律,那里就不能有這種自由。”31這說明洛克已深刻把握到了“法治下的自由”這一現代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洛克認為:“法律按其真正的含義而言與其說是限制還不如說是指導一個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當利益,它并不在受這法律約束的人們的一般福利范圍之外作出規定。”32洛克在這里展現的是自由主義法治觀的一個基本立場:法律應是被動型防守性的,其功能是為社會成員生活提供一個必須的行動框架——“維護人的自由與人的尊嚴的架框”33,這個框架確定了一個范圍,范圍內個人“隨其所欲地處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動、財富和他的全部財產······在這個范圍內他不受另一個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34這點正是哈耶克所說的法治之法應具有的“抽象特性”,法律的意義只在于確定和守衛這個范圍,而不在于對這個范圍內的個人進行積極性、申張性的指導,在這范圍內,個人的動機、決定和目標均由個人自主決定,因而從這角度來看法律又是一種工具——“當我們說它們具有工具性時,個人在遵守些法律的時候,實際上乃是在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非立法者的目的。”35
第三,權力分立。洛克認為,如果同一批人同時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力,借以使他們自己免于服從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執行法律時,使法律適合于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從而使他們與社會的其余成員有不相同的利益,這就違反了社會和政府的目的。這點是“權力分立學說的精髓”36。
具體而言,洛克把源于人自然權力的政治權力劃分為三種: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立法權是指享有權利來指導如何運用國家的力量以保障這個社會及其成員的權力。”37對外權則“包括戰爭與和平、聯合與聯盟以及同國外的一切人士和社會進行一切事務的權力。”38而執行權則為執行法律之權力。三種權力中,最高權力是為議會所掌握的立法權,而且立法權決定政府的形式:“政府的形式以最高權力、即立法權的隸屬關系而定,既不可能設想由下級權力來命令上級,也不能設想除了最高權力以外誰能制定法律,所以,制定法律的權歸誰這一點就決定國家是什么形式。”39至于執行權,則和對外權一樣同是輔助和隸屬于立法權。而因為執行權與對外權的行使都需社會的力量,兩者很難分開由不同的人行使,所以總是聯合在一起的。另外,立法機關的召集之權在行政機關手中。
立法權雖是最高權力,但洛克同樣予以高度的警惕。洛克認為立法權應以社會的公眾福利和保障人民財產為限,因而立法權必須受到以下限制:第一,它們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而且法律面前應人人平等,不論貧富,一視同仁,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第二,這些法律除了為人民謀福利這一最終目的之外,不應再有其他目的;第三,未經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決不應該對人民的財產課稅;第四,立法機關不應該也不能夠把立法權轉讓給任何其他人,或把它放在不是人民所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進一步而言,這個最高權力并不是無條件存在的:“立法權既然只是為了某種目的而行使的一種受委托的權力,當人民發現立法行為與他們的委托相抵觸時,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權力來罷免或更換立法機關。”40
如羅素所言,“出人意料的是,盡管司法組織在洛克時代是個議論得火熾的問題,關于司法組織他卻一言未發。”41洛克雖提出了某些分權的原則,但其理論“不是純粹的分權學說。”42洛克提出的立法、執行與對外三權的界說離現代政治制度中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尚有一定距離。“洛克的著重點都在于政府職能的劃分”43,與其說洛克對三種權力作出劃分,不如說他是辨別了國家的三種職能。因而從某個角度來看,洛克只是提出分權的雛形,但與這個雛形相比,洛克對專制權力的警視更為引人矚目——這個雛形的某些含糊性在其強勢反專制權力立場下并沒有構成對自由的邏輯吞噬。
第四,公民權利同意下的政府課稅。洛克說,“政府沒有巨大的經費就不能維持,凡享受保護的人都應該從他的產業中支出他的一份來維持政府。但是這仍須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們自己或他們所選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數的同意。因為如果任何人憑著自己的權勢,主張有權向人民征課賦稅而無需取得人民的那種同意,他就侵犯了有關財產權的基本規定,破壞了政府的目的。因為,如果另一個人可以有權隨意取走我的東西,那么我還享有什么財產權呢?”44洛克所論述的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的邏輯關系落于實踐操作層面時,突出地表現在課稅問題上:就政府權力而言,無稅收即無公民權利保障,因此公民必須納稅;對公民來說,沒有公民的同意,就沒無稅收,因此政府必須體現民主,“未經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決不應該對人民的財產課稅”45。公民的同意是賦稅的基礎,是政府課稅的合法性所在,而公民同意的制度體現就是代議制。因此,法治與憲政原則的實際操作就體現于公民、代議機關對政府賦稅權力控制上。
綜上所述,洛克在自然狀態中探尋到人的不可讓渡的生命、財產與自由權利,同時,洛克發現,自然狀態中因為自然法的不確定性、缺少自然法的裁判者及執行自然的必要權力,所以自然狀態并不是一種可欲的狀態,因而人類必須走出自然狀態,過渡到政治社會。另一方面,人類過渡到政治社會后,規定人類社會秩序的規則又可能被專制統治者意志所主宰,法律的裁判權和執行法律的權力也可能同時為專制統治者所僭取。為走出自然狀態與專制王權的二難困境,使人類社會橫向的公民間關系與縱向的公民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系都能有公正的規則與裁判者加以調整,洛克提出法與有限政府的理論,構建一個憲法框架下的旨在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分權、制衡的有限政府體系,以憲法來規范公民間、公民與政府間的關系,從而化解了自然狀態與專制主義的二難困境。1[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6頁。
2鄧恩:《洛克》,臺北聯經1990版,第53頁。
3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頁。
4李強:《自由主義》,社會科學出版社會1997年版,第74頁。
5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頁。
6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頁。
6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頁。
7洛克:《政府論》上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74頁。
8洛克:《政府論》上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79頁。
9洛克:《政府論》上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79頁。
10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頁。
11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7頁。
12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3頁。
13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9頁。
14李強:《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頁。
15[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7頁。
16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6頁。
17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6頁。
18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5頁。
19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7頁。
20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3頁。
21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8頁。
22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2頁。
23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5頁。
24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4頁。
25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3頁。
26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2頁。
27洛克:《政府論》上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77頁。
28“我所謂財產,在這里和在其他地方,都是指人們在他們的身心和物質方面的財產而言。”洛克:《政府論》上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06頁。
29洛克:《政府論》上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8頁。
30洛克:《政府論》上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05頁。
31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6頁。
32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5~36頁。
33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版,第318頁。
34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6頁。
35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89頁。
36M?J?C維爾:《憲政與分權》,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8頁。
37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9頁。
38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90頁。
39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1頁。
40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91頁。
41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172頁。
42M?J?C維爾:《憲政與分權》,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69頁。
43M?J?C維爾:《憲政與分權》,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56頁。
44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8頁。
45洛克:《政府論》下篇,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