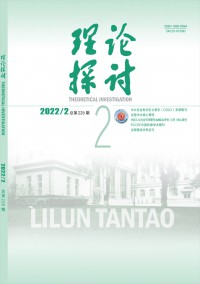探討傳統文學中的行上之游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探討傳統文學中的行上之游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山水描摹在漢賦中有容量的擴充。漢賦鋪張揚厲的格局,直欲包攬宇宙萬物,體物瀏亮,極力追求形象的逼真再現,是其藝術特色。這樣的創作涵量下,山水自然被擴大特寫,例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張衡《南都賦》,皆有以工筆藻繪狀景的篇幅,充分發揮漢賦“鋪采擒文,體物寫志”的特質。漢賦雖有許多宮廷苑囿和游獵宴樂的敘寫,這些鋪陳中也置入了“游”的活動,然而,直至倡言高蹈風塵的亂世,文人在游仙的心態中意外發現山水的媚姿,始著意加以描摹。“莊老告退,山水方茲”,山水意識胚蘊成形,方能衍生美學意義的觀覽,然這卻是在魏晉之后才更加清晰的。作為一種書寫文類,山水的面目于焉始漸明朗。魏晉時期多有名士與僧道交游的情形,或訪宗教名山,在游覽山水中契道。由于天下分裂,南北交通受阻,士人就近郊游覽,甚至搭蓋精舍和私人林園,開發“再造自然”。《世說新語》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于軒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棲止于林園,也可以領受濠濮之趣,顯示魏晉人已能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認同“游”予人身心的滌蕩。文士常因生活調性、思想廣度和文化素養相似,彼此交游往來,詩文酬答。漢末鄴下詩人集團的宴集是然,他們表述了及時行樂和企慕仙界的心聲。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上巳節,王羲之集名士于會稽山修禊宴集,一觴一詠間,將優游至樂化為文字:“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蘭亭集序》王羲之除仕之后,“與東土人士盡情于山水之游”,從山水中認知天地,歌詠優游之樂:“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蘭亭詩》,在崇山峻嶺、清流激湍中暢敘幽懷,證悟了藝術的精神,隱然有宋人記游兼議論的先聲。
形上之游
“實境之游”行跡的迤邐動線,淬煉了游者的內在心靈,而心靈的軌跡,卻可以不受有限行蹤的制約,任憑心神飛馳,萬里遨游。“形上之游”便屬于這種虛擬的經驗,超脫現實的想象是其翱翔的雙翼,在山水記游文學蔚為一大門目之前,這類的旅游就已經存在。這種型態的“游”往往跨越現實條件的藩籬,并對應主體的特定心境,甚至有其文化內因。文學史上的形上之游可以約略歸為數端,首先是莊子的《逍遙游》。《逍遙游》之“游”應是一種精神存有的型態,主體的精神獲得高度解放,因而得以逍遙游乎天地六合,人生也可視為一場大“游”。再者,則是被窘迫的現世擠壓而啟動前往他境的旅游。這類的形上之游反襯現實的成分較為濃厚,將所向往的圖像置入虛擬的他境,個體以心靈遨游的方式補償現實的挫敗,游覽時的逍遙是暫時性的。此類文學以屈原的《遠游》為代表,并成為后世“游仙”文學的祖源。而穿梭于虛、實、眠、覺的“夢游”,揭露了主體的精神狀態,也和現實經驗有一定程度的對照,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即是一場富有象征意義的夢中的游歷。心靈狀態既可決定“游”的質量,透過想象的作用,亦能產生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虛擬經驗。陸機《文賦》和劉勰《神思》關于文學創作的美學論述,剖析了創作過程的心理活動,賦予“游”另一層面貌。神思馳動,驅策筆毫,得以籠天地萬物于方寸之間,這類的“游”已是藝術美學的范疇。在分析蘇軾的記游文學之前,有必要回顧形上之游在文學史上的重要類型。以下就這數種類型和主要的作品稍作分析:
(一)莊子《逍遙游》的雙重意義
“游”多含有嬉游的成分,在實際游覽的過程中,個體的心靈狀態是決定旅游效驗的關鍵。外在觀游所見,會牽動內在觀省,決定此趟“游”的差異。因此,以精神自主的形上之游為體,才能使主體的實境之游獲得“游”應有的能量,無往不樂,這個本脈可上溯莊子的《逍遙游》。《逍遙游》描擘了無憂的境界:“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①《莊子》探討在廣袤的宇宙中,渺小有限的個體如何自我措置的問題。莊子的哲學可以“游“一以貫之,而“游”有兩種意義:“人生百年”和“自由”,莊子皆以“游”作為比擬。對于不滿百歲的生命,旅游,是短暫的出走;但向現實告一段假之后,終是要回歸常軌。然而,對比無窮蔓衍的時、空間軸,人所寄寓的形體是如此微渺,彷佛在電光石火的瞬間,就走到此生的終章,而此有限身又往往有無窮苦。這是一場等同于生命長度的旅程,卻往往伴隨偌大的苦悶,人又應該如何找到自己的歸屬坐標?徐復觀如此解釋莊子的“游”:心的作用、狀態,莊子即稱之為精神;即是在自己的精神中求得自由解放;而此種得到自由解放的精神,在莊子本人說來,是“聞道”,是“體道”,是“與天為徒”,是“入于寥天一”;而用現代的語言表達出來,正是最高的藝術精神的體現;也只能是最高的藝術精神的體現。莊子把上述精神的自由解放,以一個“游”字加以象征。一個凝滯的心靈,只能在感官所及的領域泅泳,現實環境一旦隨際遇而被折磨,世界也就萎縮了。唯有宣告精神獨立,上達至天,下放于地,與宇宙的時空間軸力求迭合,才能對現實的束縛免疫。這是一種無累于現實的自由能量,得以擁有“游”的能力;精神自由解放,才能使“人生百年之游”有所超脫。莊子認為“無所可用”是精神解放的條件,“用”是社會所決定的價值,一旦被世俗奴役,斧斤伐之的命運就尾隨而來了。莊子觀察現實,認識到個體的有限,產生悲劇意識;相對于此而發展出“逍遙游”的觀念以反制束縛,用“游世”的至樂消化在世不可抗力的悲劇②。魏晉是老莊思想勝出的另一個高峰時期,社會秩序崩解,士人欲思遁逃,或避居山林,或清談玄游;究其根柢,還是在被極度壓縮的現世生命中,追求精神的解放,找尋安頓自己的方法。這一場百年的人生之“游”,必須建立在形上的“逍遙”,否則只能在外物的拘執下走到旅程終點,精神終究是無法安頓。回溯文學史,身心受到震蕩的文士往往從道家思想找尋支持。莊子的《逍遙游》是建立在松散人際關系的綁縛之上,因而成為士人的精神浮木。《莊子》是蘇軾思想的重要構成,以莊子《逍遙游》為代表,追求精神自由和安頓的生命態度,也成為蘇軾超越的根源。在晚年的歲月,蘇軾對人世百年之游的本質有更清楚的認識,也更得見其對《逍遙游》精神的內化及實踐。
(二)屈原《遠游》的仙境周流
游仙詩作為中國文學一抹特殊的色彩,貫穿各個朝代,在動蕩晦暗的時局下,更成為文人共同的聲音。就這個層面而言,屈原的《遠游》篇當可定位為游仙文學的始祖。在時間、空間的雙重壓迫下,人的心靈特別渴望超脫現實,求得短暫的解脫,并將想象投射到潛意識的理想世界。關于屈原遠游的動因,王逸《楚辭章•遠游序》云: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托配仙人,與俱游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①“妙思”也就是超現實的幻想,通過幻想,而有“托配仙人,與俱游戲”的仙境周流,可知這是未臨實境的虛擬之游。屈原不堪“讒佞譖毀”、“俗人困極”的現實擠壓,于是透過遠游,到想象染色的世界遨游追索,傾訴理想,肆意逞懷,并從這個想象世界得到支持。《遠游》鋪設了與仙境周流的歷程: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于微閭。……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②屈原去鄉就遠,固然有如《哀郢》“遵江夏以流亡”、“過夏首而西浮”的實際行旅經驗,更有如《遠游》“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以想象力虛擬的游歷。這段想象的旅程,有“太儀”到“于微宮”的空間位移,也有時間上“朝”至“夕”的推移,更虛設了與”“顓頊”、“黔嬴”等仙人的互動情節。在極度痛苦的現實煎迫下,屈原展開了精神之旅,上下求索,追尋正道,營造了離體的旅游經驗。“悲時俗之迫厄兮,愿輕舉而遠游”。依息相存的現世一旦被俗化,個體在迫厄的空間壓制下脫遁無門,因而精神出軌;冀望超越有限,至具有補償作用的“他界”潛詠心靈,甚或滯留不歸。一則亦是時間的代序遞嬗,產生人事無常、去日苦多的喟嘆,死亡的陰影在心靈底層的伏流中騰涌,加深了對不死樂園的企慕。回歸遠游的本質,可知屈原顯然是用濃烈的色彩看待家國,“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無法通過浪漫情感加諸于內心的重重包圍。因此,雖“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消遙”,高喊“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③,然一心眷戀故國,不能自已,終至無法再繼續此生的旅程。
(三)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的夢游
在文學史上,以夢境為隱喻的作品數量龐多,若鎖定有“夢中游歷”經驗并對應現實的作品,則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相當具有代表性。李白在《夢游天姥吟留別》的夢境和述夢筆調,不但是向屈原夢境“傳達潛在的理想與渴望,寄語于神靈的虛幻世界”的繼承,也對政治受挫的蘇軾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吳帆、李海帆在《幻的浪漫夢的真實———論蘇、辛的夢幻詞》一文中提到:“《離騷》可以說就是記載一場大夢。而唐代李白諸游仙夢幻詩的創作,在屈賦以后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④東坡與稼軒雖生活在不同的歷史年代,但他們在政治上卻有著相似的遭遇,都受政敵排陷,都壯志難酬,都幻想超脫現實,去尋求一個理想境界。于是借鑒李白的浪漫主義手法,創造飛天游仙式。④上述的論點,印證了以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的“夢游”作為對照蘇軾“夢游”的合理性。尤其,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詩名即以“夢游”為題,可見李白將之視為一場夢中的游走經驗,有別于文學史上諸多單純藉夢喻理而缺少夢中游歷情節的文學作品。李白以浪漫筆法寫天姥之夢,固然因“夢游”本身即有超現實色彩,其夢境的情節單元更如符號化的語言,儼然指向李白內心幽微之處。蘇軾夢中游歷的經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潛意識活動,晚年的“仇池”之夢可視為私我神話的建構。蘇軾以“夢”為主題的文學中,即有一部分是這種特殊游走經驗,其創作的才能可與李白作時代的對應。
結語
“形上之游”是形體不需移動的“游”,回溯文學史,可以找到幾種不同的表現方式,本文從莊子、屈原、李白及其相關的作品中汲取典型。莊子的《逍遙游》有兩重意義,其一是代表精神的高度自由,其二是代表人生在世的百年之游。短暫的人生之游,常有許多不可抗命的悲苦。莊子《逍遙游》的“游世”觀欲消融悲劇,游于“無何有之鄉”,達到精神的大逍遙;以“忘”、“喪我”破除拘執,從精神層面解放自我,并找尋身心的安頓。老莊思想常是亂世的精神救贖,飽受政治煎迫的蘇軾秉持莊子《逍遙游》的游世觀作為生命態度,“逍遙游世”的精神更是其垂老投荒之時,轉化放逐悲苦、找尋精神安頓的重要模式。屈原《遠游》為后世“游仙”文學的鼻祖。屈原不堪現實擠壓,乃幻生仙境之游,有周歷天地的游覽動線和侶仙游戲的情節,實則為想象虛擬之“游”。《遠游》中的仙境周流是因不容于此世,轉往他境寄托理想;另外,時間意識的深化也會使詩人投向往仙鄉,尋求永恒回歸,皆與浪漫情致有關。“游仙”有其時代的變因,若鎖定其中“仙境周流”的情節,可以觀察到因“敘妙思”而特為“文采鋪發”(《楚辭章句•遠游序》)的創作特質。尚理的宋代相對較少此類非現實的筆調,蘇軾充滿“妙思”、“鋪發”的仙境周疾流書寫,在宋人中頗為特殊。不同的政治時空和心理趨向,蘇軾的放逐模式與游仙情調自然與屈原有異,亦不同于魏晉談玄論道的仙篇,但在超現實的書寫上則與屈原有相承的脈絡,更是“游”在文學創作上表現的美感趣味。“夢游”揭露了主體的精神狀態,古代有許多對夢的解釋,莊子和屈原也有夢喻的篇章。若鎖定“夢中游歷”經驗的文學作品,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即是一富有象征意義的夢游書寫,有出發、游往以至回歸的完整結構。雖然天姥之夢亦有游仙情節,但特別之處,在于“夢游”的主體是在睡眠狀態完成這場游歷。天姥夢境的情節彷佛是潛意識活動的象征,又可與現實呼應,從李白在夢醒后的結語即可加以窺探。
作者:譚科宏單位:嘉應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