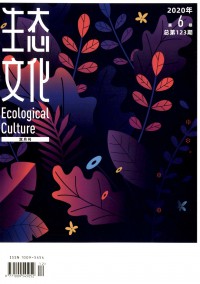文化特征設計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文化特征設計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提要】20世紀中國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現為西化派、國粹派與折衷派的矛盾與沖突。執守著不同追求的文化學者們在中國畫的認識上同樣也存在著不同的選擇。因為文化學者的影響力,這些選擇對20世紀中國畫創作與教育均產生了巨大影響。探討20世紀中國文化特征與中國畫觀念的不同選擇,對于我們從深層次思考中國畫創作及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
【摘要題】美術史
【關鍵詞】20世紀/中國文化/中國觀念
【正文】
20世紀中國文化的總體特征表現為矛盾的交織與對抗沖突。執守著不同追求的文化學者們依據自身的觀念模式決定著他的文化選擇。這些文化選擇又直接導致了他們各自對中國畫的不同認識。因為文化學者的影響力,文化選擇下所表征出的中國畫觀念對20世紀中國畫創作與教育產生了巨大影響。探討20世紀中國文化特征與中國畫觀念的不同選擇,對于我們從深層次思考中國畫創作及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20世紀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中國,已經處于動蕩狀態。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封閉幾千年的中國大門,中國在空間上進入了世界史,在時間上跨入了近代。中國一次次被打,一次次抗爭,在面臨著民族危亡的關頭,有志之士們都在思索著保國、救國的良策。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運動,他們都有著文化的性質,但對中國社會的真正觸動并不大,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運動并沒有觸動當時的社會文化心理,只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才真正觸動到了社會文化心理,從而引起人們本質意義上的思考。
社會文化是一有機的系統,這一系統呈現出層次的結構特征。在社會文化結構層次中,最外層的是物質形態層,也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器物”層面,它涵蓋了人類以物質形式所體現的文化,包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一切數以千萬計的與人的衣食住行發生關系的“物態文化”實體。其次是典章制度層,它涵蓋了人類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維護有序社會而創制的規則、體制和機構,是一種非物態文化。第三層是行為習俗層,它包括人的日常行為所蘊含的意義以及歷時性社會的約定行為即習俗,它們顯示的傳統觀念最為直接。第四層,也就是文化結構最深層、即心理活動層,它包括社會文化心理結構廣泛的觀念系統及認知智能活動。[1]
我們再來對照地看這些運動。先是洋務運動,引進的是西方物質文化,意欲用器物來增強國力,以對抗歐洲列強。這次運動只觸及文化的最外層,顯然并不能真正帶動中國思想文化的轉變。后來又有維新運動,追求“君主立憲”,進行政治改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實現政體革命,但它所解決的只是文化典章制度層面的問題,所以仍然不能解決中國本質問題。雖然這幾次運動的主導目標都是明確的,且一次比一次深化,但最后都失敗了。只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它觸及到文化的最深層——社會文化心理,所以在中國產生了久遠的影響。[2](p37)因此,人們才最終認識到,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不僅是國力的落后,制度的落后,更是社會文化心理的落差。所以,20世紀我們的思想家們把改革的重點指向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社會文化心理。
但是社會文化心理的轉變,絕不是一蹴而就的,畢竟它既處在文化的最深層,也鏈接著文化結構中的各層面。在找到了參照對象,并有了對比之后不實現轉化自然是封閉的表現。中國兩千多年的變化是如此微乎其微,甚至長時段地循環往復或根本原地踏步,正說明了它缺少反思與轉化的“資源”。[3](p366)但有了參照,又不能囫圇吞棗地全盤接受,對傳統文化進行否定式改造。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找到了“西方”這一積極有效的參比對象,但我們仍然沒有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歷史學家龐樸分析說:“事后看起來,這個任務(五四新文化運動)完成得并不好,原因之一是當時的人差不多都犯了一個毛病。這個毛病是:或者站在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上,或者站在華夏中心主義的立場上,提出了全盤西化論和中國文化本位論,而未能客觀地對待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2](p40)這正說明由于我們急不可待的心態,從而犯了偏執一端的錯誤。正是這一心態使20世紀前期中國文化總體特征未能超越三種指向上的偏頗,即西化派、國粹派與折衷派。
文化“西化派”堅持科學主義立場,同時又有泛化科學的作用,從而把科學推向了神圣的祭壇,使之成為一種“宗教”,以至于游離了科學的本質。“西化派”認為,中國的落后與衰敗是傳統文化內在生命力的散失,舊文化和舊的社會機制一樣腐敗無可救藥,中國傳統文化只能成為歷史。現代是西方的現代,是科學的現代,中國的現代化只能是西方現代文化的異地移植,中國只有全盤西化,全體變革,全面推進,才能實現社會的包括文化的現代化。這全然是“歐洲中心論”和“文化進化論”的立場,是“世界主義”與“全球一體化”的思潮。這種極端的思維方式不僅在20世紀前30年十分猖獗,后來的“”與80年代的文化熱,某種意義上講也是“西化派”思想的余緒,只不過“”的偏執,既對傳統,又對西方。
文化“國粹派”,緊緊抱住中國幾千年傳統不放松,并標榜為“人文主義”,刻意懷舊,從而變得因循守舊。他們站在華夏本位主義立場,堅持中國傳統文化本體的新舊交替與延續。他們認為中國文化內性有著一貫的恒定性,其價值觀和社會文化心理有著內在發展的邏輯,因而中國文化的變革與發展既不需要外在的參照,更無須吸納異族文化的因子。文化“國粹派”為平衡因西方列強的侵略而造成心理失衡,千方百計尋找“天朝大國”的神圣,于是以“中源西流”來貶低西方,從而抬高中國,其本質還是其狹隘的文化眼光在作祟。[4]文化“國粹化”顯然名義是在愛國,實際是社會文化發展及演變的絆腳石。這一思想余毒雖然并未能以“運動”的形式在20世紀后半期重演,但它有著根深蒂固的力量,在社會發展中產生負面影響。
文化“折衷派”表面上是“兼容并蓄”,似乎有著將中國人文傳統與西方科學主義融合的傾向,但實際是基于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的折衷,或各取一半,或各打五十大板。文化“折衷派”最終仍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立場走折衷路線,所謂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既未能真正吸收西方文化有益成分,也未能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20世紀30年代之后這三種文化傾向被文化的“左”、“右”傾所取代或置換。30年代之后,中國文化再度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先有抗日戰爭,后有解放戰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文化的特征表現為一元化傾向。文化的“左”、“右”傾現象一直延續到70年代后期,中國有了改革開放之后,文化才真正獲得多元狀態,但同時中西文化之爭又被再度升級,民族化與世界化,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沖突,又成為中國文化最突出的特征。
20世紀中國文化的特征,我們在分析過程中更多地把它看成了“問題”,這期間不排除許多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與演進有過更為合理的看法與見解,但中國文化之現象清楚表明,它是以“問題”在各個時期產生著文化的輻射力。我們關注這些“問題”,正是為了更好地認清,它是如何對中國畫與中國畫教育產生輻射作用的。
二、思想文化界的“領袖”們對中國畫的主張
中國畫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動蕩的年代,它倍受我們的文化改革家的關注,因為如果文化改革不觸動這帶有標志性意義的中國畫傳統,似乎任何改革都未能觸及到問題的本質。同樣,對中國畫的認識與探索也直接牽涉到文化立場的選擇與文化價值的判斷。可以說五四前后的思想家們幾乎沒有不論及中國畫的。另一方面,這些觀點在中國畫領域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他們不是中國畫的創作家,甚至都不太全面理解中國畫,雖然他們的出發點更多在于對中國文化的關注,但由于思想家們特殊的身份與地位,直接影響了藝術家們對中國畫觀念的新選擇。這里我們僅選擇三位特殊的人物,一位是陳獨秀,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在20世紀早期的中國,其文化地位極為突出,而且他又多次談及中國畫;另兩位是與當時在藝術界頗高聲望的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有著交往并顯示出師生關系的康有為和蔡元培。
在三人之中,康有為出道最早,影響在先。康有為屬于受地道“中學”教育成長起來的思想家與政治家,憑借其開闊的文化視野,他早年并不守舊,相反對西學還有著極大的興趣。[5]康有為的維新變法在政治上是有其現實意義的,它突破了狹隘的民族本位論的束縛,走出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的羈絆,并有“中國今日之政,非西洋莫與師”[6](p283)的開放胸境。如果我們排除康有為在政治上從“改良”走上“守舊”的影響,在文化上他始終堅持積極引進西方的態度,這于20世紀前葉閉關自守的中國文化是有劃時代意義的。
康有為的書法家的身份,使得他在關注中國文化轉型過程中,把視角自然也鎖定在了中國畫轉型上。但他并非眼見西方“高遠”而言辭見解過激,這與其政治上的改良似乎有著一定的血緣關系。康有為本堅守中國畫傳統而屬于“國粹派”人物,但歐洲之行實在讓康氏震動不小,當他親眼目睹拉斐爾繪畫的寫實魅力之后,他的感觸引起了他對中國畫改革的思想傾向。這里有首七言古詩及題跋,頗能反映康有為當時的思想:“畫師吾愛拉斐爾,創寫陰陽妙逼真。色外生香饒隱秀,意外飛動更如神。拉君神采秀天倫,生依羅馬傍湖濱。江山秀色圖霸遠,妙畫才能產此人。”題跋為:“吾游羅馬,見拉斐爾畫數百,誠為冠世。意人尊之,以其棺與意之創業帝伊曼奴核棺并供奉堆翁石室中,敬之至矣。一畫師為世重如此,宜意人之美術畫學冠大地也。宋有畫院,并以畫試士,故宋畫冠古今。今觀各國畫,十四世紀前畫法板滯,拉斐爾未出以前,歐人皆神畫無韻味。全地球畫莫若宋畫,所惜元明后高談寫神棄形,攻宋院畫為匠筆,中國畫遂衰。今宜取歐西寫形之精,以補吾國之短……”[7](p86-87)
通過拉斐爾繪畫之寫實精神,自然聯想到中國畫的宋代風格,故有“宋畫冠古今”之結論。由此,康有為更看出明清寫意畫的失之“形準”現象。1917年他在《萬木草堂藏畫目》序言中較為明確地提出了自己對中國畫的主張,可概括為:推崇五代兩宋繪畫,貶斥元、明、清寫意風格,推重形似之作。認為宋畫“為十五世紀前大地萬國之最”,而清朝以來則“衰敝極矣”。衰敗之由,是文人畫家對寫意畫的倡導,以及把元四家“超逸淡遠”畫風視為正宗的畫論。他主張中國畫應“以形神為主而不取寫意,以著色界畫為正而以墨筆粗簡者為別派。士氣固可貴,而以院體為畫正法。”并預言中國畫改革趨勢必為“合中西畫而為畫家新紀元”。[8]
由此,康有為對中國畫的態度已十分明朗:中國畫寫實之路乃為坦途。20世紀初,徐悲鴻等堅持寫實主義改造中國畫的選擇不能排除受康有為這一見解的影響。分析康有為這一藝術主張的源起,首先不能排除與其政治改良主張的一脈相承性,但有一點并不為人們所關注:康有為對于中國畫乃至繪畫的認識與見解并沒有超出“票友”的水平!他雖精于中國傳統書法,由此間及對中國畫的理解,但理解的深度與具體創作家的體悟終究是兩回事。在驚嘆歐洲古典藝術之寫實精微之后,那種普通人對自然形之“真”的認同,必然超出創作家通過對自然之體悟而搜妙所創之“真”,康有為并未超越“普通”的身份。“畫得像”幾乎成為所有的普通人品讀藝術作品的一種恒常的標準!好在康氏畢竟不是一般的普通人,他受深厚的傳統文化之熏染,并由書法對中國畫有所理解,故才會有這“合中西畫而為畫家新紀元”的論斷。及至陳獨秀,又完全兩樣了,其“革命”的偏執,非讓“中國畫”置之死地而后快!
陳獨秀屬于政治家兼思想家,它表現出的言行總是革命性大于思想性。陳獨秀對藝術的見解完全服務于他的思想文化運動的需要,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性。
陳獨秀對中國畫的主張見于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美術革命——答呂澂》一文。他認為:“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因為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采用西洋畫寫實的精神。”這是陳氏在呼喚繪畫中的“賽先生”。由此,他在畫史上尋找這種寫實的傾向:“中國畫在南北宋及元初的時代,那描摹刻畫人物禽獸樓臺花木的功夫還有點和寫實主義相近。”惟“寫實”是舉!因此他對元之后的寫意畫痛恨之極:“自從學士派鄙薄院畫,專重寫意,不尚肖物。這種風氣,一倡于元末的倪、黃,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代的三王更是變本加厲。人家說王石谷的畫是中國畫的集大成,我說王石谷畫是倪黃文沈一派中國惡畫的總結果。”這文辭充滿了“革命”的火藥味!接著陳獨秀不無號召地說:“像這樣的畫學‘正宗’(四王),像這樣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9]
陳獨秀對于中國畫本質東西也是知之甚少,顯然他對中國畫改良的主張中有許多康有為的影子,但他更為激進,這與陳、康思想上的差異有關。陳獨秀的中國畫主張名義上是改良,事實上已是全盤否定了,因為他的出發點是希望中國文化的發展應建立在對傳統的徹底反叛上,以擁護他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這是地道的科學主義泛化論。當然,客觀上中國畫的“四王”余緒在當時的京城影響也實在太大。可是,“四王”風格能全面代表“中國畫”嗎?同樣,“寫實”風格也不是西方繪畫的全部,他的反“四王”擴大為反“中國畫”,與學西方只引進“寫實”風格的主張,這些都是極端片面的激進思想的呈現。
陳獨秀這一文化主張,因其突出的地位和名望,格外受到人們重視。我們不排除陳氏文化主張在當時的啟蒙意義,可是這一激進傾向性的余緒又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后來的“”和80年代文化熱中的反傳統思潮。雖然它們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但正如我在開篇所論及的,處于文化深層的社會文化心理在文化變革中舉足輕重。陳獨秀的文化選擇為許多人所接受,并觸及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這樣在往后的日子中,一旦有外部因素的激發,便又重演出一幕幕“鬧劇”來。
相對于康、陳,蔡元培的文化選擇以及對中國畫的主張便顯得較具學術傾向。這與其身份中的教育家、思想家因素有著直接的聯系,當然更是其傳統教育與歐洲留學的知識履歷的一種折射。
作為教育家,蔡元培自然十分重視教育方針的擬定和教育目標的實現。其開放的眼光與廣博的學識使其深悟:對于現實的中國,科學教育與“人”的教育均有著極重要的意義與迫切性。他說“行人道主義教育,必有負于科學與美術”,認為“科學美術應為新教育之要綱”,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將“美育”視為自由進步的象征和人性的自我解放。[10](P9)將“美術”提到與“科學”齊平的地位,并視“美育”為“宗教”。當然這里的“美術”是今天“藝術”的概念。這種對“美術”的推崇,著實讓當時的美術家們甚為激動。20世紀前期的三位美術教育家——徐悲鴻、劉海粟與林風眠,無一不受其直接影響,也無一不受其關照與提攜。某種意義上講,蔡元培既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奠基人,同時也是20世紀中國美術教育的精神“領袖”與文化導師,他的思想直接影響了中國現代美術教育體系的形成。
蔡元培重視美育與美術自然還有與他思想深處相關的更多東西,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挖掘的。但這里我們主要在于揭示他對中國畫的看法,以及這些看法對當時美術教育家們的影響。蔡元培直接談及中國畫的言論不多,更沒有形成關于中國畫觀念轉變的系統見解。原因很簡單,他雖然在當時許多美術教育家心目中是領袖、是導師,但學業有專攻,作為一名在學術領域已有相當建樹的學者,他是不會像政治家那樣隨便“鼓吹”,從而產生本不該有的“號召”力,所以,蔡元培的中國畫態度總是隱約地包含在他的演說與文章之中。
因對美術的偏愛,蔡元培對中西繪畫之異同,他還是能見出其本質差異的。早期他較傾向于對西方古典藝術的鐘愛。1916年他在《華工學校講義》中說:“中國畫家,自臨摹舊作入手。西洋畫家,自描寫實物入手。故中國之畫,自肖像而外,多以意構,雖名山水之圖,亦多以記憶所得者為之。西人之畫,則人物必有規范,山水入有實景,雖理想派制作,亦先有所來,乃增損而潤色之。”“中國之畫,以書法為緣,而多含文學之趣味。西人之畫,與建筑雕刻為緣,而佐以科學之觀察,哲學之思想。故中國之畫,以氣韻勝,善畫者多工書而能詩。西人之畫,以技能及意蘊勝,善畫者或兼建筑、圖畫二術。而圖畫之發達,常與科學及哲學相隨焉。中國之圖畫術,托始于虞夏,備于唐,而極盛于宋,其后為之者較少,而名家亦復輩出。西洋之圖畫術,托始于希臘,發展于14、15世紀,極盛于16世紀。近三世紀,則學校大備,畫人伙頤,而標新穎異之才,亦時出于其間焉。”[10](p53)1918年《在中國第一國立美術學校開學式之演說》中也說:“惟中國圖畫與書法為緣,故善畫者,常善書,而畫家尤注意于筆力風韻之屬。西洋圖畫與雕刻為緣,故善畫者,亦或善刻。而畫家尤注意于體積光影之別,甚望茲校于經費擴張時,增設書法專科,以助中國圖畫之發展,并增設雕刻專科,以助西洋畫之發展也。”[10](p77)1919年《在北大畫法研究會之演說詞》中開始提出中國畫改革的宏觀建議:“中國畫與西洋畫,其人手法不同。中國畫始自臨摹,外國畫始自寫實。芥子園畫譜,逐步分析,乃示人以臨摹之階。……西人之重視自然科學,故美術亦從描寫實物入手,今世為東西文化融和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自當采用。抑有人謂西洋昔時已采用中國畫法者……彼西方美術家能采我之長,我人獨不能采用西人之長乎?故望中國畫家,亦須采用西洋畫布景實寫之佳,摹寫石膏物象及田野風景,今后諸君均宜注意。此予之希望者一也。又昔人學畫,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寫,即工匠技師,刻畫模仿。今吾輩學畫,當用研究科學之亦法貫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經心之習,革除工匠派構守成見之譏。用科學方法以入美術。”[10](p81)顯然字里行間,有傾向于西方寫實藝術的態度。
但是,不久之后蔡元培的看法發生了一些變化,他更看清了中西藝術各有所長,于是才有了更高見解的“融合”觀點。這一見解不僅表現在對劉海粟藝術評價上提及了法國后期印象主義,并對之認可。[10](p150-153)1924年在《史太師埠中國美術展覽會目錄》序言中,蔡元培更明確地說:“中西美術,自有互換所長之必要。”這便正式提出中西美術應互換所長,認識到西畫之長的同時也發掘出中國畫長處之所在了。接著又說:“采歐人之所長以加入中國風,豈非吾國美術家之責任耶?”[10](p165)這里的“中國風”便是中國畫應保留的長處,雖然蔡氏沒有清楚點明這“風”的特征,但顯然它是中國畫傳統的精華之處,是中國畫優于西畫古典風格的“傳情達意”特征。蔡氏這一見解也許是由原來局限于西方學院的資源轉向了對歐洲社會美術探索新動向的關注而形成,尤其是法國后印象派對當時西方畫壇的全力沖擊;抑或是他從劉海粟、林風眠等中國藝術家油畫作品中所表現的傾向和強烈的中國式個性獲得啟迪。總之,蔡元培對中西美術的看法發生了較大的轉變,這一轉變直接影響了林風眠及后來的國立藝專對中西畫教育模式的探討,同時也對劉海粟上海美專教育方針的擬定起著宏觀指導作用。
如果說這三位文化界的領袖對美術創作與美術教育所產生的影響主要發生在20世紀前半期,那么魯迅與文藝見解所產生的指導作用則在20世紀后半期有著巨大的影響。不過,他們的主張較多“革命”色彩,藝術被從屬于政治運動,藝術的個性品格被功利目的性所取代,藝術為戰爭宣傳、藝術為工農兵服務、藝術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等一元藝術觀使得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維系在一個統一的模式之下。因此,分析魯迅與對中國畫的主張,頗有牽強之感。因為中國畫獨立的品格也被功利目的性所取代,畫種淡化于它的宣傳與服務意義。
三、重要美術教育家不同中國畫觀念的呈現
20世紀中國畫觀念的呈現不僅與文化界的領袖們有著直接關系,而且他更充分地表現在美術教育家的言行之中。可以說,20世紀中國畫教育模式的形成,與這一時期一些代表性的美術教育家對中國畫觀念的選擇直接有關。本節將選取20世紀主要的美術教育家,看看他們有過怎樣的中國畫觀念。為了分析的便利,我們有意將觀念相對接近的放在一起,并比較相近中的相異性。
1.金城與潘天壽
金城1878年出生,潘天壽則為1897年,相差近20歲。在年齡上他們可算作是兩代人,但在“中國畫”這一方陣地上,這一前一后兩位“大師級”人物,共同守護著傳統,前者偏于晉唐宋元,后者立定文人畫傳統而努力實現現代性演進。
金城成長的年代,處于鴉片戰爭后的洋務運動時期,顯然金城的早期教育“中學”、“西學”已趨于對稱,但“中體西用”仍是主流,故偏于“傳統”的觀念十分盛行。1902年,金城24歲便赴歐留學,入英國鏗司大學專攻法學,學成回國后一直從事與法律相關的政府工作。金城一生主要工作似與中國畫沒有任何聯系,他之所以熱衷于中國畫,與其少時對丹青的雅好十分有關。金城竭力推崇傳統,也致力于傳統中國畫的發展與演進。也許是他政府要員身份之故,并又得大總統徐世昌的鼎力支持,他創辦了他樂于從事的“中國畫學研究會”,網羅京城中國畫名家,共同探討中國畫創作,挾掖后學,影響極大,故有民初北京畫壇“領袖”之稱。[11]
金城對中國畫的觀念屬于守成派,這與當時北洋政府“守成主義”文化態度、中日畫界的頻繁交流以及金城個人趣味等都有一定關聯。當時對西方的學習還主要是物質、技術方面的引進,“西潮”的文化性特征并不強,但在物質方面的觸動下,人們愈加對傳統文化有著固守的心理,而且,北洋政府的文化態度極為明朗。金城作為政府要員,自然也有這一背景因素的存在。中日文化有著傳統的淵源,日本更早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他們已覺察到民族文化在當代文化建設中的重要意義,中日繪畫的頻繁交流從側面啟發金城等必須對傳統進行再發掘。另外,金城在個人興趣上一直傾心于傳統中國畫,后來他有了英國的五年留學生活以及1910年歐美國歷時10個月的考察,通過放眼世界,對比中他找到了他所推崇的宋元傳統,尤其是宋人工筆,其中也不無“科學”的因子,于是定為畫學之“正宗”。
潘天壽早年雖也有“私塾”的經歷,但更多接受的是民國新式教育,在啟蒙思想影響下的潘天壽,雖然也有著“西方”的參照,但他沒有選擇“西化”之路,也沒有折衷地“以西改中”,而是愈加對傳統熱愛與執著,這與他獨特的人生經歷不無關系。[12]只要是執守傳統,必然更多地關注中國畫中的“文人畫”,因為這一“寫意”特征最能體現傳統的文化精神,也最具民族之特色。所以潘天壽在中國畫觀念選擇上義無反顧地鎖定了傳統“文人畫”一路,以顯現其對“中國風格”的深愛。后來潘天壽也對“文人畫”當代演進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尤其在圖式的視覺張力拓展上,使其作品不再是純粹意義上的文人把玩,而有了展廳效應,符合于現代人的欣賞要求,從而有了新時代的品格傾向,但其作品的本質趣味仍然是傳統的,是中國的。
對比金城與潘天壽中國畫觀念,同是對傳統的守護,同是對傳統的再發現與現代演進,金城的現代性意識在傳統本身中尋覓與提取,而潘天壽則在實現傳統轉化,因此表現出不同的趣味追求。因為金城更重發掘與提取,因此較少思考傳統中國畫的轉化與出新,潘天壽十分重視傳統的當下意義,并有意要演進與轉化中國畫傳統。但潘天壽把中國畫傳統局限在“文人畫”一面,一旦“文人畫”文化基礎出現缺失,便就失去了演進與轉化的前提,其當下意義便徒具“圖式”的形態,而沒有了“共鳴”的內涵,尤其是他對明清“文人畫”傳統的偏愛,而這一時期的“文人畫”本身已是“圖式”大于“意趣”。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2.高劍父與徐悲鴻
之所以將高劍父與徐悲鴻放在一起敘述,是因他們都用“寫實”的方式來改造中國畫,只不過在“寫實”來源的渠道上有所不同,以及改造產生的效果上存在差異而已,而這兩種途徑在20世紀中國畫界的影響,卻大相徑庭。
高劍父,1879年出生,年少時就受過廣東畫家居廉影響,也從法人學習木炭畫,后來去日本留學,深受日本畫影響。當時的日本畫即是日本傳統畫與西畫融合的產物。他從日本畫中吸取了西洋寫實因素與色彩表現,并與中國畫筆線相結合,創造“嶺南畫風”。[13]
高劍父的中國畫觀念是典型的“折衷派”,所謂“集中外之大成,合古今而共冶”的新國畫,便是以保留中國畫的工具材料為前提,用西方(更多是日本畫)寫實之造型,并與時代、革命聯系起來。高劍父在日本參加中國同盟會,曾以革命家身份在廣州創辦《軍民畫報》《時事畫報》,宣傳革命,參加起義斗爭,因此其“折衷中西”中有了些“革命”色彩也就可以理解了。他的《復興中國畫的十年計劃》儼然是高氏“藝術革命”理想的藍圖,其龐大的計劃、實施的決心、措辭的激越之情,透視出些許宗教情結。然而高氏對中西繪畫的理解終究是淺層的,他的這種“一廂情愿”在當時的中國是注定要破產的,最后只能作為“地方畫派”在畫壇延續著。
相比較而言,徐悲鴻中國畫觀念更多地順應了時代潮流,或者說徐氏的成功更多地來源于他獨特的個人際遇。[14]徐悲鴻1895年出生,一位農家子弟,只是靠著對藝術的執愛,一點點累積,一步步攀升,以至于20世紀中國畫創作風格的取向,大半時間都由他的主張所左右。他對中國畫“獨特偏見,一意孤行”的態度,因時代的需要而被社會認可、接納并傳播,當然也與他的人格魅力不無關系。
徐悲鴻早在1917年其24歲時就提出“惟妙惟肖”標準的中國畫改良論,并堅持了一生。[15]那時的徐悲鴻還沒有去歐洲留學,去接觸學院派藝術。那么是何種因素促成了徐氏這一選擇呢?由徐悲鴻生平得知,他的父親徐達章為“擅寫生”的中國畫家,“擅寫生”本身就透露出對自然對象本身形態的關注。后來徐悲鴻由臨摹吳友如石印人物畫始,進而也作些人物與景物寫生,因此重視“造型”似乎偶然地自徐悲鴻繪畫起步便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還有便是20歲去上海半工半讀時,得見康有為,拜為師,康氏對“寫實”的鐘情自然也會感染到這位長于傳統中國畫的“弟子”身上。徐悲鴻后來一直信奉中國畫必須堅持寫實主義,當然也與他在法國留學,專注于古典風格有關。
相比于高劍父,徐悲鴻的中國畫改良主張,較少一些感情的沖動,他對中西繪畫的理解遠遠深于高氏。重視造型確實有利于改良中國畫,這是國門打開后藝術界的共識,但改良的途徑是千變萬化的,如何借鑒這一寫實“造型方式”顯得極為重要,畢竟中西繪畫以各自的語言方式已經延續了這么久。中國畫造型準確了,但它自有的獨特品格是否會因之而失去?再者,“寫實”作為一種造型觀念存在,或許更有利于中國畫的改良,如果僅僅照搬西式寫實模式,將注重筆墨的中國畫變成水墨素描式的繪畫,那將不再是“改良”了。在這一點上無論是高劍父還是徐悲鴻都有“矯枉過正”之嫌。
今天,我們看到這兩個宗派均有傳人,而且徐氏中國畫觀念在經過幾代人不斷拓展探索后,也確實有些建樹,因此許多人便對“寫實”入主中國畫有認同之感。我卻不這么認為。因為對“寫實”的過分強調,客觀上攪亂了人們對中國畫新時代演進的多角度全方位嘗試性探索,中國畫因為對寫實性“西畫”的參照,似乎只存在一種視角的拓進,這一“觀念”的獨尊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畫形態的多姿演變。當代中國畫多元狀態的形成,本于20世紀前半期就應該出現,現在應是漸成氣候的階段,其責任由誰來負?
3.劉海粟與林風眠
從人生經歷上和對待藝術的態度上,劉海粟與徐悲鴻更有可比性。劉海粟,1896年出生,比徐悲鴻小一歲,兩人的出生地相距也不過百里,但他們的家境卻有著天壤之別。如果說藝術都是他們自幼的興趣,那么,在以后人生之路的選擇與前行中,劉海粟更多得力于家庭的支持。當然,劉海粟的才情與氣魄是鑄就他日后光輝更直接的因素。
劉海粟幼年可能也接觸過中國畫,但絕不會像書法作為“日課”那樣,畢竟新式學堂所學內容仍以“四書五經”為主。14歲他到上海進周湘“布景畫傳習所”之后,不僅眼界大開,而且傳統與現代的感染同時在劉海粟身上發生著作用。[16]這時的劉海粟對繪畫的認識還十分膚淺。這一點也不像徐悲鴻通過自己的刻苦,年輕時就已在中國畫領域奮斗了多年,并有了較好的造型與筆墨基礎。但也正因為如此,劉海粟到法國之后,更能接納現代藝術,而不像徐悲鴻執守著古典而不能容忍“現代派”。由此,劉海粟順著西方現代藝術找到了中國畫張揚個性的石濤與八大山人,恰好這一傾向性也十分貼合于劉海粟這位出身于富門弟子的外向型性格。劉海粟中國畫觀念便鎖定在了傳統個性藝術的反叛與恣縱一路,西方現代藝術中利于張揚個性的手法也被他“借用”過來,因而落得個“粗枝大葉,深紅慘綠”的美名。[17]重視豪情與個性是劉海粟積極的一面,就是這豪性與氣度讓20世紀多少人為之折服!“海粟大師”的影響力至今仍讓人感懷。但這豪情更需要畫內功夫的支撐,這不僅是造型上要求,更是對語言的提煉。毫無疑問劉海粟在這方面關注得不夠,但也符合中國的國情,畢竟傳統中也有特重豪情的大寫意,他們都是一時之英才,劉海粟的中國畫觀念自然也會有難以計數的受眾。
林風眠對中國畫的探索相比較于劉海粟要艱辛得多。林風眠,1900年出生,與20世紀一道成長起來,也如同20世紀一樣,一生坎坷不平。[18]在留學法國之前,他只是初知繪畫,到了法國他便有了不受任何條件限制的選擇,這與劉海粟有著較大的類似。不過他不像劉海粟是主動地選取,林風眠較為內向的性格與重思索的品格,必須有外在強有力的因素給予觸發。這么說林風眠也是幸運的,因為他在法國開始也是隨大流去學“學院派”,并極為崇拜他的老師——寫實主義大師戈猛。但后來他知遇楊西斯這位教育功績大于雕塑成就的法國學者,正是這位良師,讓他重新認識到了東方的魅力。
林風眠的觀念中是否存在“中國畫”的概念是個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他既沒有中國畫系統的基本功,在法國又是主學油畫,而他所發現的東方是東方的大藝術,并非局限于中國畫,但他確實用了半生在“中國畫”(他也稱彩墨畫)這塊領地上耕耘。所以有學者說他是中國畫工具材料的改造者,而非傳統中國畫的改造者。[19]作為美術教育家,他又不能拒絕對“中國畫”的認識表達自己的態度,于是在許多場合他只提中國繪畫,而認為傳統的中國畫“十分之八九,可以說是對于傳統的保守,對于古人的摹仿,對于前人的抄襲”[20],基本上是全盤否定。這種一竿子打死的態度正說明林風眠對傳統中國畫的精神與語言缺少深入的理解與把握,至少他只提取了傳統中國畫有限的一點寫意趣味,僅此而已!不過林風眠的中國畫觀念以及他自身的探索還是為我們探討中國畫現代演進提供了較多啟發,所以20世紀末,對林風眠的探索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
比較劉海粟與林風眠的中國畫觀念,雖然同是對西方現代藝術的吸納,劉海粟在回歸傳統并進行形式的借用,他的影響更多得力于他的氣度與豪情,但缺少藝術本體的魅力;而林風眠卻總是在自行創造,無論是傳統還是西方現代,都在服務于他的需要,一旦社會為藝術創作提供了更廣闊的自由空間時,林風眠的重“創造”探索必然為人們所重視。
四、結語
20世紀的中國文化是探索的百年,傳統文化在人們心里積淀得太深太廣了,所以突然間和也有著悠久傳統的西方文化相遇時,便有了強烈的沖突之感。而且,引進是一個過程,它同時受到引進人認識的深化的影響,異域文化的“可容”也需要時間和過程,它是在兩種文化不斷的交流、傳播過程中才得以逐步實現。在文化相容的這一過程中,它需要借助于一個共同的因素維系著,才可能展開交流與融合,這共同因素可看作文化的內核,它是深埋于文化內層的社會文化心理。開始內核較少共同因素,隨交流與傳播的頻繁而逐漸增多、加強。內核牽動文化外層結構實現轉換而達到可容狀態,但同時也受制于文化外層結構,異域文化的可容是一個動態的漸次的演變過程。20世紀出現的文化特征,最突出的表征就是未能順應這一異域文化可容的規律,而急于求成,各種文化心態便凸顯出來:或西化,或守舊,或折衷。臺灣學者林毓生提出人文重建應采取“比慢”的態度,是頗有哲學見地的。[21]
我們的文化領袖們在這樣一個文化氛圍中,其文化選擇必然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相對而言,蔡元培先生更顯出學者的理性,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大學理念,對于中國文化建設其意義還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當時中國社會之現實,蔡元培的思想與境界又太過于理想主義了[22],他不太明確的中國畫主張,借助于他的名望還是有著不小的影響的,中國畫的探索不再以西方繪畫作為一個獨立的參照對象,而是多少看作了“樣板”的存在,這便延誤了從中國畫“本體”出發,并借助于西畫的刺激,來實現自身的創造性轉化。
在對中國畫認識上,美術教育家們顯然存在著諸多分歧,但有一點卻是普遍的共識:文人畫傳統式微了,必須對中國畫進行改革。雖改革的路向各不相同,但又都能堅持“中體西用”,中國畫的工具材料并沒有太大置換。金城、劉海粟、林風眠似乎都在發掘傳統:金城找到了宋元接近“寫實”的傾向;劉海粟在石濤、八大山人中找到了藝術家個性,同樣有貼合西方現代派注重藝術家個性張揚的特征;而林風眠從傳統中國繪畫中提取的是一種趣味,也有著與西方現代藝術互通因素。所以,他們發掘傳統是為了需要。高劍父、徐悲鴻、潘天壽是真正意義上的改良或改造傳統。高劍父用日本畫寫實與用色的方式;徐悲鴻用西方古典藝術寫實的方式;潘天壽用西方現代藝術強調視覺張力的方式。但他們分別傾向于革命性、現實性與文人性,又帶有明顯的偏于一端的取向,也是為了需要。這六位大師級的人物作為藝術創作家對藝術的探索是可取的,但用之于中國畫教育,顯然都有著“以偏概全”的不良后果。
【參考文獻】
[1]西方學者對此有各種各樣的分類和分析。參閱RolandBarthes著Elementsofsemiology,transl.A.laversandColinSmith,HillangWang,NewYork,1977,pp.25~34.
[2]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M].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
[3]吳冠軍.多元的現代性[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4]“中源西流”的基本意思是,西方的事物、技術和思想、知識等原本為中國所有,乃從中國流傳出去。中國現在再去學習這些東西,不過是中國文明自身的一種復興,而非向西方求索,是取回本該屬于我們自己的東西而已。近代名流如王韜、鄭光應、陳熾、王之春、薛福成、康有為、章太炎等人均有此觀念。
[5]康有為1884年曾買到一只僅300倍的顯微鏡,用它來看菊花瓣,長度有一丈多長,再看螞蟻,長有五尺多,于是“適適然驚”,他便有了一篇《顯微》的雜文:“由三百倍之顯微鏡視蟻,而蟻可為五尺。而推之它日制作日精,則必有三千倍之顯微鏡,視蟻,則蟻之大當為五丈,……若有三億倍顯微鏡觀蟻,則蟻應百萬萬兆于吾地球。”可見康氏對科學設備先進性的驚訝!見康有為《康有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5頁。
[6]論文網
[7]劉海粟.齊魯談藝錄[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5.
[8)康有為.萬木草堂藏畫目[N].中華美術報.1918年.
[9]陳獨秀.美術革命——答呂澂[J],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1918年1月15日.
[10]蔡元培.蔡元培美學文選[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11]關于金城的生平及中國畫學研究會,參閱云雪梅《中國畫學研究會的美術教育》,載潘耀昌編《20世紀中國美術教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第40~57頁.
[12]關于潘天壽的生平,參閱徐虹《舊題新解:歷史·環境與個性·風格》,載《潘天壽研究》,第二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第171~188頁.
[13]關于高劍父的生平事跡,參閱李偉銘《高劍父與“復興中國畫的十年計劃”》,載潘耀昌《20世紀中國美術教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第116~132頁.
[14]關于徐悲鴻的生平事跡,參閱陳傳席《徐悲鴻》,石家莊:河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5]徐悲鴻《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上的演說》,載《繪學》,第1期.
[16]關于劉海粟的生平事跡,參閱《劉海粟研究》,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3年.
[17]陳小蝶《從美展作品感覺到現代國畫畫派》,載《美展匯刊》,1924年4月,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編輯組發行,南京.
[18]關于林風眠的生平事跡,參閱拙著《林風眠》,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9年.
[19]參見郎紹君《林風眠的藝術歷程》,載《守護與拓進:二十世紀中國畫談叢》,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1,第21頁.
[20]林風眠《我們所希望的國畫前途》,原發表于1933年1月《前途》創刊號.
[21]參閱林毓生“人文重建所應采取的基本態度”,載《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第19~22頁.
[22]參見郎紹君《論中國現代美術》,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8,第12~14頁.
文檔上傳者
- 地域文化旅游文化品牌
- 文化資源建設文化思考
- 市文化局文化總結
- 文化翻譯和文化傳真
- 文化沖突和文化震蕩
- 文化局文化藝術安排
- 后殖民文化音樂文化
- 文化局強化文化服務講話
- 傳統文化中的廉文化研討
- 產業文化創業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