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當(dāng)下形態(tài)反思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知識分子當(dāng)下形態(tài)反思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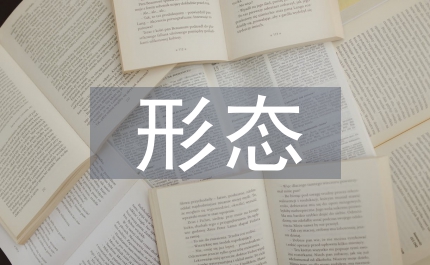
在90年代的文化思潮中有一種極力消解知識分子作用的傾向。對于這種自虐自殺傾向,筆者未敢茍同。一方面因為作為社會結(jié)構(gòu)中的一個特定角色,知識分子不會消亡,還會履行歷史派定給他的職責(zé);另一方面是因為這種傾向人為地表達(dá)了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立場,它不是出于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認(rèn)識論,就是為了奪取一種話語權(quán)力而故意制作的聳人聽聞之談。
筆者的上述表述絕不是出于文化自戀。要認(rèn)識社會機(jī)制對知識分子的阻隔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局限及由此命定知識分子不可能成為“社會英雄”,這并非難事。然而我仍然相信知識分子在推動社會發(fā)展和完善人生上的作用,尤其對于促進(jìn)中國社會和文化轉(zhuǎn)型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正是為了表達(dá)如此一份期待,本文對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展開對象性研究。在揭示他們問題的過程中提醒他們?nèi)绾巫⒁庑迯?fù)和完善自己的人格[1]。法國著名社會學(xué)家布爾迪厄說過,知識分子如果在批判社會的同時不把自己當(dāng)作批判和反思的對象,就不會獲得關(guān)于社會世界的真理性認(rèn)識,當(dāng)然也就不會對社會世界有什么作為[2]。
一、思想者與社會良心的消隱
從七十年代末到整個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把握住了歷史給予他們的表現(xiàn)自身價值的契機(jī),勇敢地充當(dāng)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啟蒙的先鋒。盡管挫折和磨難不時降臨到他們的頭頂,但他們還是義無返顧地向“左”的革命文化模式發(fā)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其悲壯性、其崇高的殉道主義精神使整個社會為之動容。在憤懣不平中,人們猛烈地結(jié)構(gòu)那些符號暴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但是在時間之針撥向九十年代初,知識分子的社會意識卻出現(xiàn)了高度的萎縮。一個普遍的問題是他們對存在的境域問題失語或缺席。許多人從關(guān)系到民族命運(yùn)的場域紛紛撤退。發(fā)展到極端,人文學(xué)者不談社會,作家藝術(shù)家不涉指實現(xiàn)。他們把自己幽閉在精神的象牙塔里,或者小心翼翼地繞過雷區(qū)、制作玄學(xué);或者把寓言當(dāng)外殼,涂抹一些常人猜不透的文字。相當(dāng)一些人在九十年代初把自己的撤退和逃脫說成是超越,洋洋自得地炫耀他們關(guān)注的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為了給自己的卑怯尋找理由,他們還給知識分子作了新的定位,即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學(xué)術(shù)人,利用畸形的市場機(jī)制為自己的文化生產(chǎn)打開了一點銷路的人,或者借助些許自由的文化空間而獲得一點虛假聲名的人,還竭力為這種機(jī)制唱贊美詩,似乎現(xiàn)在是知識分子做學(xué)問的最佳時代,任何牢騷滿腹,、怨天尤人都是無病呻吟的表現(xiàn)。一言以蔽之,在敘述領(lǐng)域、在文化生產(chǎn)場中彌漫著庸人氣乃至腐朽的僵尸氣。
這里我不想和同行們討論歷史的進(jìn)步與否,因為社會的必然進(jìn)化會為每一個時代的的存在提供合法化的理由。我也不想說明學(xué)術(shù)的真正發(fā)達(dá)需要怎樣自由的社會空間作保障,因為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會有明確的感受。我只想針對那些“搞純學(xué)術(shù)”的觀點重溫一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zé)任及學(xué)術(shù)價值的社會尺度。這也許是被人訕笑的烏托邦理想主義的表述。然而那些歷史上偉大的先驅(qū)者已經(jīng)為我們出示了足夠的經(jīng)驗范例,即知識分子必須保持對人類事物的高度關(guān)懷。可以這樣認(rèn)為,自從人類社會締結(jié)以來,在人文科學(xué)中就沒有脫離社會的純學(xué)問、純知識;所以所有進(jìn)入這個場域里的人,都要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并從那里獲得實現(xiàn)資源。學(xué)術(shù)上的高低不像有些文章裝腔作勢、故作高深地說些讓人不明不白的話,而在于你的言說是否能夠啟發(fā)人去尋找更好的存在方式。古往今來那些偉大的智者總是面對人類社會,特別是現(xiàn)實世界說話。他們切入問題的具體性往往都達(dá)到令人驚訝的程度。這些問題(如性史、麻風(fēng)病院、學(xué)術(shù)人)散見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只是為麻木的人們所不覺。而一經(jīng)他們的介入,一經(jīng)他們的考古挖掘,馬上便形成對當(dāng)下統(tǒng)治秩序和傳統(tǒng)積習(xí)的驚世駭俗的挑戰(zhàn)。對現(xiàn)實具體問題的干預(yù)并沒有使他們膚淺,相反給他們的深刻造成了有力的憑借,使他們成為由此升華的獨(dú)一無二的思想家。薩特的存在主義或許存在著巨大的紕漏,可是他對忽視人的革命哲學(xué)的抨擊,他為尋求人之自由所做的探索,使他永遠(yuǎn)刻在人們的記憶中。魯迅也許像某些詆毀他的人所說的那樣沒有專門的學(xué)問,由對國民弱點的揭發(fā)所造成的深刻,使他成為在20世紀(jì)里沒有一個國人能夠超越的思想家。錢鐘書的聲名與其說是因他的學(xué)術(shù)成果而成就,不如說他因無情解剖現(xiàn)代腐儒的小說《圍城》而成就。一當(dāng)他與世隔絕,將自己封閉起來,他的影響也就無從談起。以他為楷模而又缺少他那清高與骨氣的人更何足掛齒。為一些人津津樂道的形而上實際是在腐敗和黑暗面前喪失良知、為自己走向行而下所找的借口和托詞。那些倡導(dǎo)個人化寫作的言論也并不都表現(xiàn)出對意識形態(tài)的拒斥,人們常見的多是渺小個體的孤芳自賞。以90年代的文學(xué)批評為例,真正有點價值的寥寥無幾。反倒是發(fā)揚(yáng)魯迅精神的年輕后生摩羅、余杰、林賢治特別令人刮目相看。由此我們確信,社會價值是衡量學(xué)術(shù)價值的重要尺度。
由于知識、學(xué)術(shù)是科學(xué)和理性的表征,因而就規(guī)定了知識分子在社會生產(chǎn)場域中的特殊作用,即啟示人們鏟除野蠻和暴力而走向文明和民主。真正富于歷史責(zé)任感的知識分子必須自覺地肩負(fù)兩項使命,一是不斷發(fā)現(xiàn)更為文明更為民主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一是不斷揭露現(xiàn)存社會秩序的問題。薩特和馬爾庫塞把揭發(fā)批判現(xiàn)存社會的缺欠當(dāng)成知識分子的天職。他們的觀點盡管遭到了科學(xué)理性精神較強(qiáng)的思想家布爾迪厄的反對,可是在民主和自由并不發(fā)達(dá)的、專制和暴力十分盛行的社會場域中,他們的思想無疑更富于生氣。面對斯大林時代或斯大林的恐怖統(tǒng)治,誰能否認(rèn)《焦?fàn)柦鹩蔚馗贰ⅰ督苣崴骶S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島》出現(xiàn)的偉大意義?承受著“”時代的高壓,誰不為天安門詩歌的自由噴涌而感到痛快?由于知識分子不在社會生產(chǎn)場的中心,只能處于邊緣,因而其思想上的懷疑與批判不可能解決生產(chǎn)場的根本問題。在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人就以此戲稱知識分子為“文化英雄”,并公開懷疑他們的作用。但是思想的力量不可低估。從歷史發(fā)展的軌跡上看,它不但能夠消解舊有統(tǒng)治方式的合理性,而且能夠激發(fā)人們對良性社會結(jié)構(gòu)的思考。不止如此,那些在批判舊世界的過程中為人類發(fā)現(xiàn)了文明之普遍原則的思想家還會贏得人們永恒的愛戴。張角、黃巢、普加喬夫是歷史上不可或缺的革命家。但是偉大的啟蒙主義者狄德羅、盧梭在人們精神上產(chǎn)生的影響恐怕更為久遠(yuǎn)。直到現(xiàn)在,他們?yōu)槿祟悩?gòu)筑的現(xiàn)代性也不能說過時。因之不能小覷知識分子的思想預(yù)設(shè)作用和精神批判作用,知識分子也理當(dāng)以獨(dú)特的方式來顯示自己存在的價值。以為知識分子不在社會結(jié)構(gòu)的中心因而放棄應(yīng)有的責(zé)任是短視;面對邪惡而不置一詞是懦夫;為謀取一點蠅頭小利而蠅營狗茍是蠕蟲。90年代知識分子話語在精神向度上出現(xiàn)了高度萎縮,簡直可以用平庸化來形容。新世紀(jì)的知識分子顯然需要同此舊我告別、重塑自己的人格,像魯迅所說敢于做扶哭叛徒的吊客,像本雅明所言驕傲于做一個波西米亞流浪漢。當(dāng)然,強(qiáng)調(diào)知識分子以獨(dú)特的方式介入到社會生產(chǎn)場域并不等于否定其他種種文明行為的可能性。雖然那種大轟大嗡的廣場情結(jié)已被許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證明為破滅了的現(xiàn)代神話,但當(dāng)社會需要張揚(yáng)一種普遍的公理和正義時,像雨果、左拉、托爾斯泰、薩特那樣挺身而出、仗義執(zhí)言還是人們熱烈期盼的。據(jù)布爾迪厄的描述,左拉為猶太軍官德雷弗斯公開辨冤一事構(gòu)成了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模式[3]。正是按這種文化模式面對現(xiàn)實世界他們被當(dāng)作社會正義和良心的代表、創(chuàng)造文明和民主秩序的信使。中國知識分子是否需要告別平庸而走進(jìn)世界知識分子的行列呢?
二、權(quán)力的仆從
人類文化史上那些偉大的先驅(qū)為知識分子完成了一種獨(dú)立的人格。這種人格把自由和自我價值的意義提到了極限,照亮了人之為人的最佳存在方式。
作為人類精神的化身。這些先驅(qū)的偉大不僅在于他們對自由及自我價值追求的自覺,更在于他們對權(quán)力意志者的拒絕。布爾迪厄在他的反觀社會學(xué)中指出,整個人類社會的結(jié)構(gòu)可以概括為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4]。一般說來統(tǒng)治者總是要把其他人當(dāng)作實現(xiàn)自己意志的奴仆與工具,而畏懼于他們的權(quán)力,被統(tǒng)治者多半都安于歷史給定的命運(yùn)。獨(dú)立知識分子出現(xiàn)的意義就在于他們不相信這個歷史宿命,并以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來起訴這個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模式的荒謬。他們極力維護(hù)自我的尊嚴(yán)、抗拒一切強(qiáng)暴的掠奪和奴役。貝多芬一腳踏破魏瑪宮廷的等級制,不給迎面而來的王公貴族讓路,反而逼得他們閃在路旁向自己問安。一個堅定的信念支撐著貝多芬的腳步:公爵在世上成千上萬,而貝多芬只有一個!塞維特斯為爭取個人對《圣經(jīng)》的自由解釋權(quán)同新教領(lǐng)袖加爾文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即使面對火刑的威脅,他也絕不對自己的注釋改動一字一句。他的肉體雖然被燒成了膠狀物,可他獨(dú)立的思想、獨(dú)立的精神卻戰(zhàn)勝了新的獨(dú)裁者而成為歷史的永恒。
進(jìn)入文化生產(chǎn)場域的每個分子都應(yīng)當(dāng)懂得這一游戲規(guī)則:牢牢地把守住自我。他不屬于任何階級、集團(tuán)和個人,只屬于自己。如果說他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中還有身份,那么他應(yīng)是不偏不倚的人類事物的仲裁者。少數(shù)人可能借他的思想財富圖謀私立,然而他的本意卻是為全人類共有。知識分子應(yīng)有的獨(dú)立人格決定他不去逢迎、巴結(jié)、討好任何權(quán)勢者。林賢治有言:“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疏遠(yuǎn)權(quán)力的。”假如我們敢于面對權(quán)力常常是統(tǒng)治者壓迫別人的工具這一事實,你就不會感到林賢治的表達(dá)有什么問題,更會同意德國作家亨利希·曼的說法:“一個向統(tǒng)治階層靠攏的知識分子是在背叛精神。”[5]
中國當(dāng)代知識分子不是沒有做過高貴的選擇。在80年代的啟蒙思潮中他們曾努力掙脫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做精神獨(dú)立的文化生產(chǎn)者。特別的在批判官本位的過程中他們高揚(yáng)了精神文化的巨大價值,明確地為自己的文化人角色作了歷史定位。
可是好景不長,到了90年代他們的價值觀念發(fā)生了逆轉(zhuǎn)。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就有依附官僚的傳統(tǒng),新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不但沒有改變傳承千年的格局,反而強(qiáng)化了對知識分子的領(lǐng)導(dǎo)體制,這就決定了他們難有精神上的獨(dú)立,其文化生產(chǎn)基本上是為政治權(quán)力服務(wù)。只是因為殷勤效命及十年仍沒達(dá)到當(dāng)政者的滿意,反而受盡了摧殘和凌辱,他們才在社會及文化轉(zhuǎn)型之初對“官本位”進(jìn)行了聲討。然而骨子里他們并未脫盡奴隸意識,與以往所不同者是他們把自己的奴性驅(qū)逐到了無意識區(qū)域。90年代,由于眾所周知的政治經(jīng)濟(jì)原因,知識分子及其生產(chǎn)開始貶值,權(quán)力開始大大升值,這是沉積到意識低層的奴性意識浮到了意識的表面,知識分子中間滋生了權(quán)力拜物教的可鄙現(xiàn)象。因為切身感到文化生產(chǎn)本身不能給生產(chǎn)者帶來榮譽(yù)、地位、金錢,而領(lǐng)導(dǎo)卻能給予,因此相當(dāng)一些知識分子向庸碌無為的官僚調(diào)情。為了評職晉級,他們或者不惜縮短身子低眉順眼地按長官的意志辦事;或者努力擦抹原有的思想鋒芒,讓自己的大腦追隨權(quán)力話語而轉(zhuǎn)動。一位70年代末通過力主社會主義悲劇而揚(yáng)名、后來又企圖以無意識文藝心理學(xué)改造主流文藝思想的所謂理論家就突然轉(zhuǎn)換了面孔,成為主流話語的生產(chǎn)機(jī)器,甚至請回“左”傾時代的棍棒批評,隨意打殺精神的異端。他如愿以嘗地得到了最高教席,可也把自己的丑陋暴露于天下。
布爾迪厄在他的反思社會學(xué)中準(zhǔn)確地揭示了學(xué)術(shù)機(jī)制與政治機(jī)制的同源性[6]。這種同源性決定了許多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和雙重人格。一方面對于權(quán)力上的統(tǒng)治者,他們是被統(tǒng)治者,另一方面在學(xué)術(shù)體制內(nèi)他們又可能是文化統(tǒng)治者。在我們這里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景。而且由于政治體制對學(xué)術(shù)體制的嚴(yán)格規(guī)定性,我國知識分子的雙重人格更為嚴(yán)重。在發(fā)達(dá)國家知識分子在學(xué)術(shù)體制內(nèi)作一個文化統(tǒng)治者是受集體無意識支配的結(jié)果,而在我們這里則明顯地表現(xiàn)為一種自覺。那些體制內(nèi)文化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不要說,其發(fā)言人總要以“官”的口吻說話,好象他們是被特殊授權(quán)來宣布文化世界的真理的,誰也不容置疑、必須加以實行。就是有些民間團(tuán)體諸如各種學(xué)會之類也如法炮制。那里學(xué)術(shù)的高低、有無權(quán)威不由學(xué)術(shù)本身來確定,而由職務(wù)、級別、種種非學(xué)術(shù)因素來確定。你有職務(wù)、有級別才有生產(chǎn)學(xué)術(shù)的資本;無職務(wù)、無級別,就無生產(chǎn)學(xué)術(shù)的資本,只能接受壓抑者的壓抑。包括相當(dāng)一些學(xué)術(shù)會議的發(fā)言與不發(fā)言也都照此規(guī)則辦理。由于權(quán)力如此重要,所以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對學(xué)術(shù)不感興趣,千方百計掙當(dāng)學(xué)會的理事、常務(wù)理事、副會長、會長等等。而一旦如愿以嘗,便仿照政治體制,實行“世襲”;即使早該頤養(yǎng)天年、毫無學(xué)術(shù)能力的老朽也不肯讓賢。占據(jù)這些職務(wù)有很多便利,他們有機(jī)會成為評獎委員會的委員、新聞出版界關(guān)注的頭面人物,借此他們可以給自己出書、給自己評獎。以上種種文化統(tǒng)治者控制著大大小小的文化山頭,形成密不透風(fēng)的統(tǒng)治,把學(xué)術(shù)生產(chǎn)場變成了為權(quán)勢者提供象征性服務(wù)的區(qū)域。
還有一種趨勢不能忽視,就是相當(dāng)一些知識分子,尤其青年知識分子不滿足于學(xué)術(shù)圈內(nèi)的榮譽(yù),當(dāng)官場的大門向他們打開后,絕大多數(shù)人爭先恐后地踏上它的臺階。在學(xué)術(shù)上他們給人造成一種開放、前衛(wèi)的良好印象,似乎是知識分子話語的代表。然而他們對政治生產(chǎn)場的游戲規(guī)則比文化生產(chǎn)場的游戲規(guī)則還要精熟,一旦撈到一官半職,便玩得出神入化。在提攜者面前,他們是謙虛有為的青年;面對同行,他們是被“理解”精神所照拂的對象。照理說,我們對他們的選擇不該有過多的腹誹。社會總得有人管理,有文化的人管理總比沒有文化的人管理要好。問題是他們的文化生產(chǎn)與政治生產(chǎn)反差太大。人們希望他們進(jìn)入仕途后能夠把新文化精神帶入政治生產(chǎn)場域,使之走向理性和民主。然而從事實上看,這些受過新時期最好教育的一代人最為油滑。你別指望他們會把新文化精神帶入政治生產(chǎn)場域,他們會一絲不茍地恪守舊的規(guī)則,并且以溫和、不讓你惱怒的方法將這些規(guī)則貫徹到底,達(dá)到那些僵硬的官僚達(dá)不到的目的。長篇小說《國畫》通過朱懷鏡的描寫為我們提供了如此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朱懷鏡80年代早期的大學(xué)生,受過啟蒙主義文化精神的乳哺。但是一旦進(jìn)入官場之后,他就開始自我異化和被權(quán)力異化。表面上他信仰理性、民主、自由,而實際上他始終把丑惡的權(quán)力當(dāng)作思想和行為的軸心。為了向上爬,他把朋友的無價之寶——國畫無償?shù)厮徒o了市長。為了實現(xiàn)一筆骯臟的政治交易,他又消災(zāi)滅火把另一個朋友的尖銳新聞稿件扼殺在搖籃之中,使罪大惡極的縣委書記逍遙法外、平步青云。在無論權(quán)力生產(chǎn)場域還是文化生產(chǎn)場域,他都顯得文質(zhì)彬彬、極有修養(yǎng),然而行賄受賄、吃黑打黑、聲色犬馬,他無所不為。在他心目中不要說人類、民族的意識沒有,便是人子之義務(wù),他也不作任何承擔(dān)。他唯一追求的目標(biāo)就是滿足自我對這個物質(zhì)世界包括女人的充分占有欲。從朱懷鏡反觀現(xiàn)實中一些紅光滿面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官員,你會相信:他們是徹底令人絕望的一代。
掃視了知識分子的官場化傾向,我們就會明白90年代的思想文化狀況。一個時期里不斷有“大師”的呼喚及沒有“大師”的困惑。試想在一個極少數(shù)人做學(xué)問、多數(shù)人仰視權(quán)力、為權(quán)力服務(wù)的文化場域里能指望什么思想大師出現(xiàn)呢?中國知識分子要能有大師誕生,除了要爭取獨(dú)立自主的學(xué)術(shù)機(jī)制而外,必須把自己由一個權(quán)力的仆從變成一個具有自由意識的批判權(quán)力的思想家。尼采、薩特、馬爾庫塞等等已經(jīng)成功的地走過了這條道路。
三、文化知識的商販
文化知識是知識分子的資本,也是知識分子問身于社會的憑籍。由于文化知識能夠給人類創(chuàng)造巨大的福利,作為回報,人們給知識分子一定的酬勞。知識分子不是上帝,他要有相應(yīng)的物質(zhì)給養(yǎng)才能生存,因而對于他們靠著文化知識而謀生,有點知識眼光,不應(yīng)有任何異議。但是靠知識謀生只是知識分子存在的第一義,他不帶終極性。知識分子對文化知識還有更高的追求。文化知識就其本質(zhì)性存在來說是為了把人引向高度的文明。這個質(zhì)的規(guī)定性要求從事精神生產(chǎn)的人必須首先走向文明。也就是說他不能僅僅把知識當(dāng)作食利的手段,還要把它當(dāng)作目的本身來對待。所謂“目的本身”即承認(rèn)文化知識作為真理認(rèn)識的神圣性、純潔性、不可動搖性。當(dāng)對世俗利益的謀求不以損害知識為代價時,我們可以保持兩者共存;當(dāng)利益的謀取有辱知識的尊嚴(yán)時,我們首先要捍衛(wèi)知識的圣潔律令。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可悲的動物。其可悲性在于作為一個有精神生活的動物有時會因無度地追求官能享受而迷失自己的精神家園,淪為一般動物的水平。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就是以自身脫俗的追求幫助人們恢復(fù)記憶,找回精神家園——這是人的最高存在之境。就此而言知識分子是人類精神的守望者,他們對知識的態(tài)度帶點宗教感情和形而上的意味。正是憑著自我對世俗性的超越,他們才能產(chǎn)生出更多的真理。本世紀(jì)法國思想界的最后幾位大師(無論薩特、德里達(dá),還有布爾迪厄)走的道路是頗能給人啟發(fā)的。如果僅僅考慮體制內(nèi)的優(yōu)厚待遇,維護(hù)既定秩序,那么他們完全可以走上體制內(nèi)的統(tǒng)治地位。然而他們不滿足于作為一個食利者而存在,為了尋找智慧的“寶瓶”,他們走上了反叛體制的道路。他們關(guān)于這個世界的新知識、新思想盡管不可能被我們完全接受,但在許多方面達(dá)到了世紀(jì)末的高峰。
以此反觀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xiàn),卻令人大失所望。文化知識在他們那里失去了任何真理性、目的性、神圣性,只剩下了前面所述的第一義:謀利的手段。相當(dāng)一些人利用市場機(jī)制來生產(chǎn)知識和銷售知識。他們不管是否真知、是否為我們的文化語境所需要,只要是新的、時髦的、能夠給自己謀得響亮聲名的東西,就炒作、搬運(yùn)、販賣。例如作為一個殘留著許多中世紀(jì)的野蠻、黑暗和暴力的民族,我們最需要傳播人道主義、自我意識等等現(xiàn)代性話語。可是據(jù)有些人說,西方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后現(xiàn)代精神,為了與他們?nèi)〉猛剑覀円驳孟馊说乐髁x、流放自我。他們給人道主義、主體性哲學(xué)編排的罪名是:可以產(chǎn)生希特勒、產(chǎn)生法西斯主義。可是他們恰恰忘記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書種指出的,希特勒的產(chǎn)生不是民主自由思想發(fā)展的結(jié)果,而是民眾蒙昧的必然、權(quán)威主義(奴隸主義)性格的必然。又如當(dāng)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和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被作為正反兩方面的話語誤讀過來后,馬上就有人拾起自造的“東方主義”破旗反對同樣是自己捏造出來的亨廷頓的西方文化中心論及其對東方文化的歧視。令人不可思意的是這些東方主義者正是不久前還在國內(nèi)大面積播撒西方后現(xiàn)代話語的批評家。那個猛烈攻擊張藝謀向西方陳情的人,自己就曾拋棄母語而用外來語(如體驗美學(xué)、卡里斯馬情結(jié)等等)寫書,“向西方陳情”。他們由后現(xiàn)代到新保守主義的轉(zhuǎn)換之快使國內(nèi)外學(xué)者無不感到駭然。趙毅恒就曾著文表達(dá)過自己的困惑。其實人們的困惑是不必要的。因為你的困惑都是出于對學(xué)術(shù)的真誠而產(chǎn)生的,而令你困惑者是不講究學(xué)術(shù)上的自我和真誠的。他們什么信念都沒有,所有的只是商場中的實用主義、機(jī)會主義。即不管什么貨色,那管是截然對立的東西,只要使我第一個獲利、出名,我就叫賣。還有一層內(nèi)容沒被好心的人們點破,就是當(dāng)亨廷頓的國情咨文被誤讀到中國后幾乎成了敵視東方文化的典型文本,因而也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民族文化的自衛(wèi)情緒和敵視西方文化的情緒。期間染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中國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大概害怕自己的名字同亨廷頓連在一起,害怕被指責(zé)為主張全盤西化的異類、西方文化侵略者在中國的內(nèi)應(yīng),所以才迅速改換門庭,張揚(yáng)東方主義,給自己戴上新保守主義、愛國主義的帽子。然而這種迎合更令人惡心。
福柯說過,話語即權(quán)力。布爾迪厄則醒目地揭示了文化生產(chǎn)中的顯赫權(quán)力——命名權(quán)。他指出:“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無法命名之物的權(quán)力……是一種不可小看的權(quán)力。”它的學(xué)術(shù)首創(chuàng)權(quán),權(quán)威、派別領(lǐng)袖、盟主的進(jìn)身權(quán),而且所命之名一旦“被用在公眾場合”,廣泛流通起來,還會具有“官方性質(zhì)”[7]。布爾迪厄非常惋惜法國知識分子在學(xué)術(shù)上謹(jǐn)慎小心的態(tài)度,這使他們沒能抓緊命名權(quán)。然而對中國知識分子不必?fù)?dān)心,別看我們沒有生產(chǎn)自己思想的能力,卻十分富有制造大聲名的本領(lǐng)。一些青年知識分子似乎特別內(nèi)行。當(dāng)許多學(xué)人還以傳統(tǒng)政治學(xué)的觀點來打量“話語即權(quán)力”,表示出種種驚異和困惑莫解的神情時,他們便迅速領(lǐng)悟了福柯表述的重大意義:話語不但能夠產(chǎn)生出權(quán)力,也能產(chǎn)生出名利、地位。不斷推出新話語,就能壟斷文化生產(chǎn)場的全部權(quán)力,使天下所以舞文弄墨的人都跟著我走。相當(dāng)一些刊物出于同樣商業(yè)化的目的,為他們提供陣地,幫助他們制造“圈子化”的批評,實行話語霸權(quán)。僅以文學(xué)批評為例,在90年代就有“新狀態(tài)”、“新體驗”、“新生代”、“晚生代”等種種命名。對于一定現(xiàn)象的命名不可一概否定,然而它必須是嚴(yán)肅的、謹(jǐn)慎的,既能符合實際,又能包孕一定的美學(xué)、文化內(nèi)容,使所命之名具有相當(dāng)?shù)姆€(wěn)定性,經(jīng)得住時間的考驗。可是看看90年代的文學(xué)命名究竟有何根據(jù)?又有什么學(xué)術(shù)價值?什么叫“新狀態(tài)”?從橫向上看,“新狀態(tài)”能夠說明哪個時間段的文學(xué)?哪一段現(xiàn)在進(jìn)行時的文學(xué)不可以叫“新狀態(tài)”?再從命名者對其內(nèi)涵的描述上看,什么寫自我、寫感覺,什么無文體界限、注重散文化,哪有特殊之處,說句不客氣的話,這些描述只是新時期文學(xué)批評成果的大雜燴而已。創(chuàng)作的實踐也證明,“新狀態(tài)”純系一種虛浮的預(yù)設(shè),至今就沒有一個“新狀態(tài)”作家表現(xiàn)出大氣候。同理,所謂“新生代“、”晚生代“都是些淺薄的命名,他們除了給命名者帶來了話語權(quán)力、幫助他們推銷了自己的產(chǎn)品而外,沒有任何意義。對于這種商業(yè)化的、世俗的行為,我們只能保持高度的冷淡。
問題不止于此。一個廣為流行的商業(yè)化行為是炒作。為了名、為了利、為了評職晉級,圈子之中、朋友之間、夫妻族內(nèi)互相吹捧,有的請人吹,有的化名自己吹自己。更有一些人成立文化制作公司,根據(jù)顧客的不同需要,明碼實價的寫作、出售各種文體的文章,從中牟取紅利。至于作家們?yōu)榇罂顐兏韫灥拢▽憟蟾嫖膶W(xué)之類),期刊出版單位出賣版面和書號,教育部門出賣文憑更是屢見不鮮。如此運(yùn)作的結(jié)果,文化生產(chǎn)的正常規(guī)則全被打亂,以假充真、魚目混珠的現(xiàn)象日甚一日。到現(xiàn)在學(xué)者不像學(xué)者,教授沒有教授的水平,知識分子隊伍里擠滿了混子騙子、文化奸商。可以預(yù)言,如果再不進(jìn)行反思和清理,知識分子將在畸形的市場機(jī)制中把自己推向絕路。這不是危言聳聽,筆者周圍的許多職工就對知識分子滿腹鄙夷。
①本文因主要研究問題,所以不能提及少數(shù)精英知識分子90年代的表現(xiàn),敬請他們原諒。
②參見《文化資本與生活煉金術(shù)》第92—10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見《實踐與反思》第295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④見《文化資本與生活煉金術(shù)》第85—86頁。
⑤以上兩段引文均見林賢治《娜拉:出走或歸來》248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
⑥見《文化資本與生活煉金術(shù)》第85—86頁。
⑦以上引文見《文化資本與生活煉金術(shù)》第9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