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手機一個社會學試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凝視手機一個社會學試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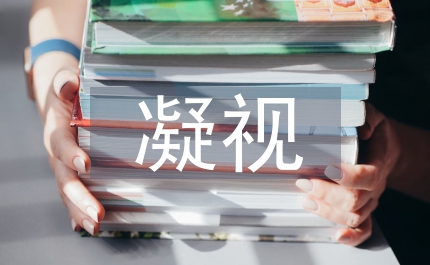
內容摘要:手機強勢存在,社會學卻對其相對默然。本文嘗試以手機作為發問社會的方式,通過對手機的“凝視”,以吉登斯現代性三大動力為基點,對手機、手機參與“實踐著”的社會事實所“體現”的現代、甚或現代之“后”作一初步分析。本文不擬提出一個“應然”結論,只欲在反思前提下,做出更具“后”特征的社會學試分析,讓眾家自由選擇、定奪。期盼以一孔之見拋磚引玉。
關鍵詞:手機溝通現代性“后”
正如涂爾干所言,“中介性的事例本身就必須作為一種獨立存在的結構來考察,并且,社會結構需要維持的機制。”手機作為現代社會的溝通中介,拋去其技術外衣,應該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而不是無語。
利奧塔(Jean-FrancoisLyotard)說:“了解社會,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首先選擇向社會發問的方式”,本文選擇了手機作為發問的方式。不過本文只是試圖遵循涂爾干倡導的“用社會事實解釋社會事實”,對手機這一復雜多面的社會現象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進行初步的解析,更期待由一孔之見拋磚引玉。
一.“凝視”手機
1.數據
公用電話剝奪了隱秘的私人談話空間,于是,靦腆的芬蘭人使手機應運而生。1990年全球手機用戶數目僅有1100萬人,2000年即已增至7億4100萬人,而到2002年初更是達到10億部。在這10年中,手機占所有電話用戶的比重從1990年的2%增加到1998年的38%,每百人擁有的手機數量從0.2增加到12.2支。據預測,到2008年全球用戶數目將達到目前的1.7倍,手機用戶將突破20億。
手機在中國的普及速度更加令人吃驚。據有關部門統計數據,截至2003年10月,我國手機用戶已達到2.5億,首次超過固定電話用戶數。雖然我國整體的普及率尚低,但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手機普及率已超過60%,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據中國信息產業部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運行司估計,到2004年中國內地手機用戶將達到3.2億。諾基亞的廣告似乎簡潔的概括出了這一切,“你每眨一次眼,世界就售出4部諾基亞手機。”
2.影響
手機已經深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政治操作、經濟產業、社會互動,個人生活安排,犯罪行為等等。不論是宏觀的社會結構,還是微觀的行為層面,手機都是無法忽視的科技裝置,也引發了許多社會議題。
菲律賓總統艾斯特拉達(JosephEstrada)2001年被人民趕下臺,手機扮演了重要角色。反對他的民眾用短信傳遞口號,組織、協調示威活動,導引群眾行動,避免與鎮暴警察正面沖突,減少可能造成的傷亡(KatzandAkahus,2002);街頭盯著手機看消息的“拇指族”,似乎正建構出一種全新的社會關系網;由對手機過分依賴形成的現代心理疾癥——“手機依賴癥”已悄然現身,如果身邊沒有手機,就會出現精神不振甚至煩躁焦慮的心理與生理反應。據調查,目前這種現象在青少年中比較嚴重;手機短信已被有些人斷稱為傳播的“第五媒體”,緊跟其后又將手機多媒體功能稱為“第六媒體”,這不單是文字上五和六的區分,重要的是凸現了媒介的“第四種權力”;當父母用手機完成親職責任——親子關系媒介化,當青少年用手機參與同輩群體的交往、吸收同儕文化時,手機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在消解著人類“最原初也是最常見的互動”(吉登斯,1979)?消解著家庭——人類原發地的結構?通過手機,現代男女情感的紅燈分外刺眼。手機只是工具,婚外戀才是內容,電影《手機》04年高票房的沖擊,似乎不僅僅是馮氏、戈氏的平民幽默所能涵蓋。手機真的變手雷——藏掖在現代人的腰間,隨時爆炸?
二、文獻回顧與質疑
1.文獻回顧
與手機相關的學術研究不像因特網研究那樣豐富多變,許多論者更慨嘆相關研究的缺乏(RobbinsandTurner,2002;KatzandAakhus,2002)。的確,即使國外對手機的學術研究,尤其是社會學研究,數量也不多。專書(論文合輯)只有Brown,GreenandHarper等人所編的《無線世界》(WirelessWorld:SocialandInternationalAspectsoftheMobileAge,2002)、KatzandAakhus所編的《長時連系》(PerpetualContact:MobileCommunication,PrivateTalk,PublicPerformance,2002)、Myerson的《海德格、哈貝馬斯與手機》(Heidegger,HabermasandtheMobilePhone),以及Rheingold的《聰明暴民:下一次社會革命》(SmartMobs:TheNextSocialRevolution)。已出版的論文則只有Katriel(1999)、Towsend(2000)、LeungandWei(1999)、KatzandAspden(1998)寥寥幾篇。(王佳煌,2003)而中文譯本在國內也只有臺灣出版的《聰明行動族》。
相形之下,國內學者更是采取默然的姿態,在筆者所涉及的資料范圍內,能見的只是傳播學對手機作的若干傳播技術的媒介分析的文章,且重點不約而同放在了僅是手機功能之一——短信的所謂“第五媒體”的相關研究。而專業的社會學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專業社會學家也只有張歡華《世界進入手機時代?》(社會,98:10),以及最近王寧教授在《南方日報》上的那篇更像社會學小品的“南方觀點”《“隨身帶”的現代性》探討了手機對現代性主體的建構作用。
2.質疑
社會學研究的相對漠視與其顯然的強勢現象并存。長久以來,社會學界有一種價值傾向,認為社會學只應研究“嚴肅的”、“有用的”、“重大的”問題,諸如階級階層、貧困、犯罪或社會發展等等。像手機一類現象,則被認為太瑣碎了、太膚淺了、太輕松了,不值得花費經歷。可是,隨著手機的暴漲、短信的鋪天蓋地,這種以瑣碎、膚淺為理由的“無動于衷”是站不住腳的。澳大利亞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根據收發信息時參與感官的多少從概念格上區分了“冷媒體”、“熱媒體”(麥克盧漢,2000),而在此,社會學者也似乎因感官上的參與選擇而對研究對象有了冷和熱的區分——網絡的熱和手機的冷。而現在的“技術跳出了工廠,不再僅僅充當生產力的角色,而是直接進入了千家萬戶,扮演著消費力的角色,因為它變成一種日常消費產品”(王寧,2004)而隨著技術的發展,尤其是GPRS技術,手機已不僅僅跳出工廠武裝了現代人的現代生活,它還武裝了網絡,把網絡引到了個人數據傳輸終端的角色上,網可以“隨身”了,眾家所熱衷的“虛擬社會”才可以真實的構成,通過把身體“捆綁”在手機上,由手機實現了身體的“無時不在”,參與到“身體不在場的互動中”(風笑天,2002),從而形構著“真實的虛擬”。如此,手機的社會學研究是這“第三域”研究的前提。是暗證了麥克盧漢所說的“顯而易見,通常就意味著熟視無睹”?還是暗證常人方法學批判傳統社會學自認為的“優越于日常生活”(楊善華、李猛,1999:65),從而在缺乏反思下對日常世界的“自命不凡”?不過清楚的是,這明顯與20世紀以降社會學界對日常生活的結構分析和實踐理性的“凝視”背道而馳。三、手機:一個過程的視角
“社會何以可能?”不僅僅是霍布斯式的關于秩序的思考,更是有著社會學旨趣的學者共同對社會生成與存在的發問。而在當代的普遍反思和實踐的趨向中,更能容易見到溝通賣力建構社會的影子,甚至在哈貝馬斯那里,達致“溝通理性”就是在尼采做出“上帝之死”的吶喊后,被福柯宣稱“人的消解”進而波德里亞所謂的“社會消解”之后的人和社會的重生之路。
對于互動結構的變遷,科爾曼曾有過對主體變遷的論述,互動主體已不再是自然人,而是法人、傳媒工具或是國家。互動結構的其他維度也在發生著變化,包括情景、道具、溝通本身的感官參與等等。以不斷滲透進生活,成為人類溝通互動必不可少的工具——手機為例,以上的變化清晰的衍發著。
1.傳統溝通
對溝通的關注來自經典社會學的傳統,盡管在二分的傳統視野下,這一更為取得微觀認同的社會行為依然在兩大傳統下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論是社會行為的討論還是對社會結構的訴求。溝通是人類社會交往的基本過程,也是一切社會賴以形成的基礎,這一是基本共識。借用社會心理學對社會行為的定義——個體或群體對他人或社會所給予的社會刺激的反應,而這個反應反過來又能夠成為他人的社會行為的刺激。在這里“刺激”是指來自人或環境的信息作用,而人的社會行為的發生發展本義就是一種廣義的信息溝通過程。(周曉紅,2000)因此,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薩丕爾輝十分肯定地說:“⋯⋯每一種文化形式和每一社會行為的表現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溝通。”
“行為協調的必然性要求在社會范圍內進行一定意義上的交往,而如果想把行為有效地協調起來,以便能夠滿足需求,則又必須進行交往”(S.Kanngiesser,1976)。英文的“溝通”一詞(communication)從詞源學角度,除可譯為溝通之外,還有傳播、交流、交際、交往之意,盡管有些差異,但在本原上都涉及信息和行為的交流或曰交換。(周曉紅,2000)溝通與互動交往,在許多社會學家那是兩個可以互換的概念,如果要作區分,可以說互動是溝通的廣義。已達成共識的是——最本源就是指“人際溝通”或“人際交往”,吉登斯就曾經明確指出,“最原初也是最常見的互動狀態是面對面的互動”(李康,1999:232)而隨著騰尼斯所說的傳統社區向現代社會的過渡,溝通的現代性如何體現?再進而是西方學者提到的“消費社會”中的溝通又會何去何從?下文試從手機這一將現代性引向自我從而重構自我體驗和身份的裝置對現代性甚至現代之“后”的溝通進行初步剖析。正如王寧所描述的,“盡管血液還是那血液、身體還是那身體,但是被現代性所‘武裝’的我們,卻再也不是從前的我們了”。既然“現代性通過‘迷你’技術的方式‘武裝’著我們”(王寧,2004),那武裝后的我們又是如何溝通的呢?
2.嵌入現代性的手機溝通
縱觀西方社會學文獻,一個核心的論題就是對興起于西歐并逐漸向全球擴散的現代工業社會的認識和把握。孔德的“三階段論”、斯賓塞的“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滕尼斯“社區”和“社會”、涂而干的“機械團結”“有機團結”、帕雷托的精英循環論、韋伯的“合理化過程”、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社會”等等,莫不是這些社會學締造者對“現代性”的凝視。把手機現象放在現代性的背景來分析正是社會學獨有視角之一。它為加深和拓寬對溝通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思路。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手機與現代性的聯系,不只是技術作為現代性內容之一這么簡單。手機的使用與普及絕不只是科學發展的內在理路所致,也不只是少數好奇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在興趣驅使下造成,而是有其結構的動力。而當今的結構大師吉登斯認為,“在20與21世紀之交,作為社會學基本問題的現代性(其過去的發展和現時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現了”,他的現代性界定言簡意賅:“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17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吉登斯分析了與現代性發展的動力機制密切相關的時空問題、脫域(disembedding)問題和信任問題。吉登斯斷言,現代性的這三個方面將促使社會關系在世界范圍內的重整和延伸,并維持相距遙遠的人之間復雜的互動。(轉引自文軍,2004)手機溝通與現代性的內在邏輯不妨借用這“三大動力”來尋找解讀路徑。
(1)手機溝通與時空重構
“時空的分離及其不斷的重新組合,在這種方式下所產生的社會生活有著精確的時空‘分離’(zoning)”(李康,1999:242-241)。時空的分離在吉登斯那是第一大動力,而手機的溝通不受時空的限制,可以說是手機的原始特點。手機脫胎于固定電話,其發明的初衷就是滿足移動通話的需要,這從手機的另一名稱中可以窺見一斑:手機。這一特點使“我們的觸覺更敏感了,感知距離更遠了、眼光更具有滲透力了”。手機“消除了時空距離對我們的束縛,改變了我們和世界的關系,使我們變得更有力量了。”(王寧,2004)
手機的基本特性與功能就是隨時隨地(any-time-and-any-where)的可接觸(contactability)與可獲得(availability)。這種特性與功能固然便利了人的生活,卻也造成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或生產與再生產時間的相互穿透與重迭,或者說是不同時間的界限模糊。用馬克思的理論來解釋,手機是現代性背景下,雇主延長相對勞動時間的新手段,它有助于雇主以間接的、微調的方式,延長雇用者的工作時間,榨取絕對剩余價值。(王佳煌,2003)不論被雇者是被迫在下班時間被雇主找到,還是自愿開機保持隨時可以聯絡的狀態,被雇者都已經卷入進生產,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為雇傭者創造剩余價值的結構性的鏈條中,無從逃脫。除非關機,可是沒有人想聽到再開機時電話的另一端告訴,“你已被解雇了”。
手機溝通不但貫串了公私生活的界限,促成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的交迭,延長了工作時間,而且也影響了我們對時間與空間的認知。空間不再是單一的空間,而是分離的、片段的、多重交迭的。時間也不再只是時、分、秒的時間,而是更多支離破碎的時間片段與區塊。使用者必須自己設法組合運用,因其職業性質與家庭狀況而發展出個人生活策略,在一定的限制內操控零碎化的時間,設法克服空間的限制,從而用手機協調工作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步調,并在時空的重組與重構同時,構筑其社會關系。正如Puro所言,工作時固然不易休息(偷懶),休息時更要不定時的接觸、處理工作事務(轉引自王佳煌,2003)。這種在工作與非工作時間的切換、調整,處理工作與私人事務的模式,不正像某些學者的比喻,或可以靈巧演奏爵士樂或可以操弄雜耍的行動(SherryandSalvador,2002)。除對時間的感受不再只是固定的小時與分秒外,更有了在社會時間系統內的重新認識——在社會時間系統上建立的流動的時間單位。最明顯的事例就是用手機隨時進行的訂餐訂票,隨時使自己的未來時納入社會時間系統的流動管理中,可能正是如此才可以在無時不在的等待和擁擠的人群、車群中從容,這也正是現代人的時間策略。可問題似乎是這樣,我們是否真的必要去等待和擁擠?
3G技術的應用會實現手機與因特網的隨時鏈接,將最成功的時間技術與空間技術緊密結合,再經由波德里亞所謂的“科技把消費從稀缺資源擴張成一種社會剩余物,消費便平民化、大眾化”(波德里亞,2001)的過程,手機的“隨身在線”就不再是夢想,更加強化了手機溝通的即時性和跨時空性。而且時空概念本身也浸透著吉登斯所言的現代性的顯著特征,是“外延性和意向性的交互關聯著”(洪曉楠、吳迪,2004)。時空不只是日常實踐全球化了的時空,還從外延和內涵上拓展到了新的域——“虛擬社會”中的時空。隨時召集你的伙伴,無論他(她)是在天涯還是在海角,在現實還是在虛擬,召開各種緊急會議,討論必須討論的重大問題,這便可以在手機的ICQ上應用,而不用搬上還是顯得沉重和昂貴的筆記本。
(2)“脫域”的手機溝通
動力之二:與時空的分離直接相關的是社會系統(從局部性中)逐漸脫離的過程(disembedding)(李康,1999:242-241)。在接受英國諾丁漢大學政治學教授回里斯多夫·皮爾森的訪談時(后收錄在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的附錄中)吉登斯清楚地講到“現代性的一個特點是遠距離發生的事件和行為不斷影響我們的生活,這種影響正日益加劇。這就是我所說的脫域(dis-embedding),即從生活形式內‘抽出’,通過時空重組,并重構其原來的情境。”
案例:電影《手機》的情節:
嚴守一在與情人私會之際,接到妻子的電話,說自己正在與同事費墨在一起,當妻子因為有急事給費墨通話時,嚴守一的謊言隨即敗露。電影后半段好友費墨的謊言,也是如出一轍地。
在火車上,嚴守一的舊情人武月突然打電話來,對方火氣挺大,由于“新歡”沈雪在身邊,嚴守一怕武月說下去不知輕重便裝傻,便扯著喉嚨喊:“啊⋯⋯說話呀,聽不見!⋯⋯你大聲點!⋯⋯我說話你能聽見嗎?⋯⋯信號不好⋯⋯我在火車上,回老家!⋯⋯喂⋯⋯”對方果然掛了電話。
從上述案例中可清晰看到“身體不在場”溝通情景抽離與斷裂。與傳統意義的人際溝通——整體性的交流行為,具有強烈的情景性——不同,手機溝通是發生在特定情景斷裂下的整體性溝通的肢解。暫且不論其中關于兩性情感的信任倫理的問題,其中的情景斷裂性以及整體性溝通的肢解確實是主人公行為成為慣習的結構特征,是其一再如此的條件和中介,縱容了嚴守一“慣習性”(布迪厄,habitus)的說謊。電影中的陰差陽錯其實就是特定情景斷裂下的破碎溝通的戲劇化表現。借用默頓的一個分析方法,通過對“反攻能”現象和“正功能”現象的對比研究,可以揭示不易為人發覺的“正常”的社會事實的存在。手機謊言分析顯然有助于發現情景抽離的實情。在面對面的人際交流中,說謊是需要很大的心理承受力和很高的技巧的,不僅要言辭從容,而且要聲色鎮定,稍有不慎,或許只是一個不自然的眼神,都有可能被對方識破。“單純”的手機溝通(與手機多媒體技術實現的功能相區別)大大地簡化了說謊的成本,說謊者不必掩飾自己的表情和動作,只需要聲音的演技。因為對方只能聽見聲音,情景、身體是抽離、缺失的。
吉登斯指出,最原初也是最常見的互動狀態是面對面的互動,而隨著溝通手段的變化,互動中的共同在場的范圍和具體表現形式也發生了質的變化。(李康,1997:233)而這質的變化正是由“脫域”實現的。傳統的人際溝通,話語溝通只是整體性的人際交流的一個方面,話語的溝通效果必須與表情、姿態、動作以及具體的情境協調起來,才能構成一個有效的、整體性的人際交流。手機的廣泛使用,強化了人際之間的話語溝通方式,但同時肢解了人際交流的整體有效性,而且溝通雙方是在不同的情景中,或者說,溝通雙方的情景彼此是不透明的。吉登斯提出要考察“在場可得性”(presence-availability)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互動能夠成功地進行,并不僅僅在于行動者在時空上的鄰近,而是因為他們在一定的時空區域內定位在能夠相互監控和安排各自行為的場景之中。(李康,1997:233)不妨借用戈夫曼的擬劇論,在“脫域”的情境中,作一番手機溝通的劇場分析,戈夫曼(ErvinGoffman)曾用戲劇理論(dramaturgy)來分析人們的日常行為,就像表演一樣,人們的日常行為在舞臺(前臺)、演員、觀眾、道具和后臺等等情境中發生。每個人在公共空間里的一舉一動都是一種表演,是一種印象整飾(impressionmanagement)。手機是我們表演用的、將現代性裝進口袋的新道具。這個道具讓我們聯系越密切,疏離感卻越強。我們停止了面對面的交談,到處都是沖著手機說話的人,他們對與他們擦肩而過的人視而不見。這場戲的一切都在不規則的發生著,消解著劇幕的本身。沒有了在場的其他劇組人員,只有一個人的獨角戲和不在場的旁白;沒有了前后臺的區隔,只有一個要求演員必須隨時隨地轉換腳本和角色的戲場,他要不停的表演;沒有了絕對的觀眾和純粹的“局外人”,只有不斷觀看并隨時加入的互動者;沒有了角色沖突,只有始終不斷矛盾著的主體和角色。
鳳凰衛視的主持人竇文濤就不止一次地在節目中掏出自己的手機,給嘉賓和觀眾展示其中一些有意思的短信內容。如此一來,誰是觀眾?誰是演員?誰又是局外人呢?在戈夫曼那里,前后臺是有嚴格區分的,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規則和慣習,若前臺的觀眾貿然闖入后臺,則會引起所謂的“崩塌”。可是,當演員主動邀請觀眾隨時進后臺,那會發生什么?還能繼續表演嗎?
再比如在公共場合,一般人說話一定有個聽話的對象,這個對象可以是成人、嬰兒,甚至貓狗等。但若一個人對著空氣說話,那一般人都會認為這個人心理不正常。然而一個常見的鏡頭上演了,如果這個人的手機裝上了耳機,再被頭發或衣領遮住,或者手機太小,藏在手掌里面,旁人聽見的、看到的就是類似獨白的對話,類似“心理不正常”者的行為。可是在脫域的規則下,這是多么“正常”的演出。但“問題是如果所謂的瘋子也戴上耳機,喃喃自語,那么我們要如何斷定誰是正常人,誰是瘋子”?(王佳煌,2003)手機鈴聲在脫域的現代場景中隨意穿行,使著這個便攜的隨身道具以神奇的現代性作著理性表演的消解,于是有了《手機》影片中的精彩對白,“對⋯⋯啊⋯⋯行⋯⋯噢⋯⋯嗯⋯⋯咳⋯⋯(停頓)⋯⋯聽見了。”“肯定是一女的打的。我能翻譯。(嚴守一學著男女兩種口氣),開會呢?對。說話不方便吧?啊。那我說你聽。行。我想你了。噢。你想我了嗎?嗯。昨天你真壞。咳。你親我一下。(停頓)那我親你一下。聽見了嗎?”這時眾人一同起哄:“聽見了!”道具借著現代性的特征穿破了舞臺規則,在情景斷裂的劇場和整體性溝通肢解的表演中,有些喧賓奪主。
這樣一種“抽離”的獨特的社會后果,按照德勒茲和瓜塔里的說法,“我們正從扎根于時空的‘樹居型’生物變為‘根居型’的游牧民,每日隨意(隨何人之意尚存疑問)漫游地球。”(轉引自馬克·波斯特,2001:25)雖然吉登斯認為這不過是“脫域”過程的一個方面,但他也承認“它確實部分地被新社會中覺察到的要求所驅動。人們期望組織起跨越時空的、更快捷、更有效的交往方式。”(吉登斯,2001)(3)手機與信任
需要提到的,吉登斯的動力機制三是“反思的運用”,似乎與信任相差頗遠,但不能忽視的是吉登斯接下來的論述,他把“反思”首先“運用”在了信任系統上。吉登斯那里的信任,更偏向于本體安全性的形而上的概念,與專業技能、專家知識和學者知識力直接相關。表面看,與這里所要討論的較低層次的人際信任不相關,但都是在一種吉登斯所謂的“脫域式”及“重嵌式”社會安排及社會關系下形成的信任問題。已達成共識的是,信任成為一切合作的基礎。面對陌生、沒有權威、抽離的情境,怎樣創建新的“名譽系統”顯得特別的重要。否則因為不知道自己在新關系中的位置、在買與賣交易中的優劣勢,自然不可能“合作”。知道誰可以信任、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是越來越重要的事情。人的社會生活的關鍵成功因素就在‘名譽’——我們每個人過去跟人交往的歷史,決定了別人對我們行為、人格的評價。
溝通的真誠在情景斷裂、溝通整體性肢解的結構下,邊際成本減少,現代的“經濟理性人”在“有限理性”現實前傾向選擇了謊言,實現其的“次優選擇”,當謊言成為慣習,建構著人的生活實踐,于是人們就在萊賓斯坦提出的“X(低)效率”上習慣的不斷選擇。如此,已經不只是道德倫理,更是本體意義關乎于“我在”的問題。在言語代替行動與思維的時代,無所指的能指肆意浮游,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亦是假,假亦是真,人們在這樣的迷局中,逐漸失去辨別真實的信心和能力。更主要的,我是我的語言編織出來的那個我,我是假的,被自己的謊言湮滅的假人,是一個只會說謊話的人。這不是角色沖突的問題。
博弈論經常會談到著名的“囚徒困境”。甲乙同案犯,隔離審訊。如果兩個都不招,因為證據不充分,兩人都只能判1年。如果一方招了,屬立功表現,功罪相抵,無罪釋放;而另一方則屬抗拒從嚴,判10年。但如果兩人都招了,則各判5年。結果兩個人爭先恐后地招了,結結實實地各判了5年。信任的價值在博弈間清晰的彰顯,當信任在人與人之間缺失時,社會就會原子化為彼此漠然的孤危的個體。更耐人尋味的是,正是在我們已經無法孤單,也不習慣孤單,在與他人那么“近”中,我們成為孤危個體的。《手機》里,嚴守一說:“要想說真話,恐怕就得返回到肢體語言時代了。”
這樣的境況在當前中國背景下,格外凸現。日常化了的信任焦慮,似乎是當下中國人一個普遍的隱痛。觀眾在《手機》中看到的是脫口而出的謊言和習以為常的欺騙,雖然戲劇化的表現自有其特殊的表現形式,但一個缺失了真誠的現代生活浮世繪仍可在人們心中引起共鳴。孫立平有一段借用“三個浪潮”的概念對中國當前這一“斷裂社會”的形象描述,“北京的中關村以及全國許多大城市中的“新技術開發區”、“科技園區”,即使是嚴格按照托夫勒的標準,這里也可以稱之為名副其實的“第三次浪潮”,“從中關村出去往西南走,十幾公里就到了石景山,在那里有全國著名的“首鋼”,還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業文明”,“而出了城市,到了廣袤的農村,那里則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孫立平,2003)在這樣一個斷裂的社會中,多個時代的社會成分共存在一個社會之中,在人際信任上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制度性紊亂。在傳統社會中,由于有比較穩定的文化倫理紐帶,人與人之間一般沒有復雜的經濟關系,所以社會的基本誠信是可以維持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強制性的指令使社會關系變得單一而機械,誠信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制度價值。傳統倫理在這個時生了嚴重斷裂,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誠信機制尚未建立起來。欺上瞞下,弄虛作假,稀薄冷漠,面對這種社會現狀,在法治尚不健全的時候,社會倫理道德也顯得蒼白無力。于是無處不在的欺詐與瞞騙,成為我們今天每個中國人最痛心也是最無奈的日常話題。基于移動信息技術所引發的溝通信任危機正是基于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上的。在各種“迷你”技術產品中,手機最為普及和流行。中國將成為手機的第一大國,顯示在這個高科技時代,中國并未落伍。但我們要問的是,手機正在改變中國,要改變到哪個方面?以及如何去面對改變?中國需要適應這種改變帶來的沖擊。這絕不是危言聳聽,這已經是一個很迫切的現實問題了。
最后,不妨借用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的架構,來看這一現代性“吊詭”現象的信任痕跡,若用默頓的術語也就是“好惡交織”。哈貝馬斯認為,真理由共識所構成,而共識是人們在沒有內外壓力和制約下的理想情境中進行交往溝通達成的。(阮新邦,尹德成,1999:174)暫時拋開溝通行動理論批判的視角,從正面看,溝通理性透過對人類語言行為的分析,肯定人際間真誠的溝通并非純然是一種手段,其本身是人類存在的目的之一,或者說這是人性的其中一部分。哈貝馬斯是強調以人際間的真誠溝通,代替目的理性所鼓勵的以滿足一己欲望為主導的行為,希望由此重新界定個人在宇宙間的位置。他沒有從宗教或超經驗的道德領域里尋找現代人的價值信仰,而是嘗試透過真誠的人際關系,在現世的日常生活里建立終極關懷的道德信念。對他來說,基于信任的真誠溝通不單只是達至人類相互了解的方法,其本身已構成了一種“共享的美善生活”(thesharedgoodlife)(阮新邦,1999)。也就是說,在真誠的人際溝通里,人類分享了相互依賴和信任的存在意義和喜悅,這是一種在人類共同分享的過程里才可以獲至的存在意義。
阮新邦曾就這一理論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應用做過一番探討,“傳統價值信仰的失落和以滿足純感官消費的生活方式,使得人類本來具有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思維日漸干涸,人際間的關系隨著這種生活方式的發展,以及政府的公共策略而出現嚴重的疏離狀態。哈貝馬斯所倡導的溝通理性正是要深入分析這些現代社會的問題,并進而展開批判。”(阮新邦,1999:167)基于手機溝通的“疏離”顯然在其所述的“現代社會的問題”之列。當我們停止了面對面的交談,到處是沖著手機說話的人,是以拇指說話的人“拇指一族”,我們隨時與他人聯系著,卻對與我們擦肩而過的人視而不見。這樣的人際溝通模式,跟哈貝馬斯提出的真誠溝通顯然是有很大分別的,但也正好看到了理想和理論層次的討論與現實世界發展的差距。
一方面,技術的發展確實擴展了溝通的范圍,增大了溝通的可能性,并且,使得身體不再有效的限制主體的位置。或者說“通訊設備使整個地球上的神經系統延伸到這樣的程度,使它能夠將我們的這一星球籠罩在,借用德日進(TeilharddeChardin)的術語便是,語言的意識域(noonsphere)內。”(馬克·波斯特,2001)同時,人與人的社會互動亦有可能藉由手機,發展出抵抗的策略與詮釋的論述,在物化的環境中,建構自身與周遭互動者的微觀生活世界。(王佳煌,2003)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另一方面,在高度科技發展和復雜的社會結構里,在溝通理性和科技理性的碰撞中,實現哈氏的“真誠溝通”是否要現代社會付出必然的代價?哈貝馬斯提出了有三個"有效宣稱"制約著人們可以正確地運用語言跟別人交往。第一個是"真理宣稱"。在認知層面上的交往過程里,我們是期望所使用的句子能夠反映外在世界的事實,并且是通過這些認知句子把相關事實告訴別人。因此,這些句子的"有效性"是取決于其能否達到事實的真相。說話者在這里遵守的是真理宣稱。第二個是"正當宣稱"。正當宣稱是語言使用者和別人交往時,要遵守支配著人與人交往的社會規范。人際的關系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規范構成。第三個是"真誠宣稱"。我們使用的句子是希望別人相信這是真誠表達我們內心的想法和感覺。(阮新邦,尹德成,1999:173)只是在現代的電信溝通方式中,這幾個宣稱會實現幾個,引發的信任危機是不是更清晰的根據。筆者認為這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并不是僅僅的一篇文章能解釋清楚。也需要不但的溝通和對話,嘗試實現研究上的“理想溝通”。四、結語
1.手機的溝通之“后”
變遷依然進行著,就像結構在不斷的生成一樣。在理論家的現代還是后現代爭論的“游戲”中,我們不妨在有些“狂歡、斷裂、碎片”的現代之“后”的景觀中駐足腳步,品味一下哈貝馬斯的一段話,“現代性是一項宏偉的工程,尚未完成,它具有開放性,遠未終結。”本文無意要在“現”和“后”的概念上作出清晰選擇(這在整個學界也遠未完成),只是清楚這是一個正在生成的過程,一個無限逼近的過程。因為我們已經可以在現實“生活世界”中看到波德里亞用以建構消費社會理論的諸如“仿像”(simulacrum)、“內爆”(implosion)、“超真實”(hyperreality)、“消費”(consume)、“致命”(deadliness)等概念的現實景象片斷,借用哈貝馬斯的術語這是一種“殖民化”,是科技、商品、符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且我們產生了疑問:這些是否也在用它巨大無比的商品、物質、符號的力量消解著人類溝通,讓溝通也“赤裸裸”的消費著——就像波德立亞所斷言的“三階段”的最后,“第一個階段,包括古代和封建社會,被交換的僅僅是物質生產中的剩余;在第二個階段即對馬克思來說具有核心重要意義的資本主義階段上,被交換的是全部工業產品的價值;而在第三個階段上,甚至以往曾經被認為是不可出讓的東西如‘德行、愛、知識、意識’也都可以交換”(轉引自喬治瑞澤爾,2003:118)英國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ScottLash,也在懇切地告訴我們發生著什么,“人不再尋求溝通過程提供‘意義說理’,卻極度要求‘瞬間快感的體驗’——只有別出心裁、前所未有、好笑突槌的事件或劇情,才能擄獲我們每天浮沉于信息中的茫然眼神。”這似乎也無獨有偶的描述了我們如此熟悉并每日體驗的手機短信溝通。
除了消費,還有我們被手機已然監視的身體,它該何去何從?手機的無與倫比的隨身性完成了在福柯看來頗具技術難度的“全景式的監獄”的輕松建造。如果你不想關機,就永遠在場,而且不只是聲音。在多媒體技術的“進化”作用下,手機的全球定位功能、拍照功能等等已經可以讓你的身體無時無刻“在場”。可是正如保羅·利文森所說,“我們每個人都夢想進展和成功——向往它的完成就存在于鈴聲那一段的聲音中”(保羅·利文森,2002:64~65),在被“電話線彼端的那位潛在的好萊塢制片人”的魅惑下,在眩人耳目地“內爆”著的——成功——“能指”的“符號系統”中,我們快樂的期待著,焦急地等待在手機旁邊,共謀著對我們自己的身體監視。
除了在“后”的場域中結構的變化,變遷的還有溝通的后果。“聰明暴民(SmartMobs)”、“暴民(Mobs)”、“快閃暴走族”(flashmobs)、“快閃族”、“聰明行動幫”雖然稱呼五花八門,但是在朦朧和混亂之中,他們來了,而且來勢洶洶!這個人群在萊茵戈德那里被描述為一個全球數字化趨勢下新興浮現的一個全新群族——“一群會用網絡、手機等,互相溝通、串聯并參與特定族群活動并做出實際行動的人”。這些人出沒在紐約、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奧斯陸、堪薩斯城、西雅圖到亞洲的新加坡、香港、臺北等全球各大都市,他們原本是躲藏在屏幕后面彼此互不相識的年輕男女,瞬間聚集在一起興致勃勃地到麥當勞跳芭蕾舞、到家具店里坐沙發、在購物中心忽然鼓掌起哄、闖進同一家書店尋找同一本書、在酒店的大堂內裝睡、在百貨公司前大喊“新年快樂”⋯⋯然后又迅速散去。萊茵戈德認為,“利用好這種社會關系并且駕馭這種社會運動,很可能是下一代科技的殺手級應用,是一個全新的商機所在,即將引發全球新一波消費文化革命。”不過,使我們更興奮的是,這對于社會學似乎更具顛覆性意義。
2.反思
《圣經》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么樣呢?”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于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是的,反省自己,也反思我們的社會學。這是現代性的一個品性。也是不論在哪個語境下——現代性的“困境”、“異化”,或是現代“后”的“致命”——中的出路。比如,然于手機這一司空見慣的景象,我們反思:社會學應該花費筆墨仔細研磨,正是熟視無睹中包含著意味深長。參考文獻:
[1]通信世界網,2004.2.23,15:32
[2]ChinaByte,2003-05-06,13:35
[3]周曉虹:《現代社會心理學——多維視野中的社會行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年,274—275頁。
[4]楊善華主編:《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版
[5]安東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爾森:《現代性-吉登斯訪談錄》,胤宏毅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
[6](美)保羅·利文森著:《軟邊緣:信息革命的歷史與未來》,熊澄宇翻譯,清華出版社,2002.4版
[7]阮新邦著:《批判詮釋與知識重建--哈貝馬斯視野下的社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4年版
[8](美)馬克·波斯特著:《信息方式——后結構主義與社會語境》,范靜嘩譯,周憲校,商務印書館,2001版,北京
[9](法)讓·波德里亞著:《消費社會》,劉成宮、金志剛譯,張一兵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5版
[10](美)喬治·瑞澤爾著:《后現代社會理論》,謝立中譯,華夏出版社,2003.1版
[11](加)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麥克盧漢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2]王佳煌:《試論手機社會學》(講譯稿)2003.4.14www2.nccu.edu.tw/~d261/advert/sogi.htm
[13]王寧:《“隨身帶”的現代性》,南方日報,2004.01.14
[14]布賴恩·特納編:《社會理論指南》(第二版),李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版
[15]謝立中主編:《西方社會學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8版
[16]文軍:《邏輯起點與核心主題:現代性議題與社會學理論的研究》,,2004.03.16
[17]張歡華:《世界進入手機時代?》,《社會》,1998.6,第10—11頁
[18]洪曉楠、吳迪:《吉登斯現代性思想再反思》,文化研究網/,2004.2.7
[19]/new/display/17108.html
[20]/new/display/14887.html
[21]電影《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