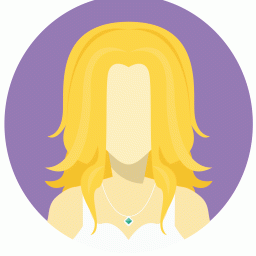華北青苗會組織結構和功能演變以解口村黃土北店村等為個案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華北青苗會組織結構和功能演變以解口村黃土北店村等為個案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青苗會”在清末民初曾經是華北地區農村基層社會的重要組織,它的誕生、發展和演變也與華北地區村落形態構成的特殊性密切相關。它的起源是華北農村在收獲季節為確保農作物不被偷盜者攫取,農民們不得不派遣家庭成員在夜間輪流到田間巡視,較富裕的家庭則雇用專門的看護人,這叫“看青”,一些鄰近居住的家庭也往往聯合起來雇用一個看護人保護田中谷物直到準備收割。
在收獲過程進行當中,許多地區有個習慣,那就是允許周圍村莊的窮苦農民進入田地拾取收割遺留下來的麥穗和谷物,這個習慣無疑是照顧那些窮人的慈善行為,卻也往往是地主與拾穗者之間發生沖突的主要根源,為了處理好這一習慣所造成的麻煩,華北農村往往自發組織起較為正式的機構解決類似的糾紛,這就是“青苗會”興起的緣由。從“看青”到“青苗會”,原來都屬于自發組織的性質,然而在二十世紀初,“看青”已開始從一個家庭自發的行動向村莊所擁有的集體性責任轉移。
“青苗會”功能從簡單向復雜結構的演變趨勢已經引起了社會史研究者的重視,目前出現了兩種有影響的對立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從清末到民初,隨著國家現代化策略向基層社會的不斷滲透和延伸,“青苗會”組織已從一種單純的“看青”功能演化為頗為復雜的地方自治機構。另一派學者的解釋則有所不同,他們根據滿鐵調查的資料發現,“青苗會”功能的變動恰恰證明的并不是村莊自身的成長和發展,而是標志著村莊的衰落。無論怎樣評價這兩派觀點,“青苗會”日益變成了一種復雜的地方功能組織當沒有疑問。本文通過河北三個村子即解口村、太子務村和黃土北店村“青苗會”組織的研究,試圖修正以往研究對“青苗會”功能的若干看法。
一、“青苗會”組織功能的雙面性
本文所探討的村莊之一解口村屬河北永清縣288個村莊之一,該村共有耕田1147畝,如按所有權劃分,耕田又可分為本業地、租地和當契地三種。該村擁有62戶人家,每家平均人口4.3人,擁有耕田18.5畝。戶姓以梁姓為最多,占全戶數58.1%。“青苗會”是解口村的七種重要組織之一(其余六個組織是村公所、禁賭會、祭塋會、路燈會、添油會、吵子會)。“青苗會”成立的確切時間已不可考,大約在清末就已出現。“青苗會”會員一般都設有會首或稱會頭一人,司理全會一切事宜,另有管事的或稱理事人八九人至十三四人不等,具體執行會內事務。還設有管賬先生一人,司理一切賬目,另外就是看青的或稱青夫一至二人,司理看守莊稼之職,防止偷竊及損壞事情的發生。“青苗會”的正規工作可以概括成寫青、看青和斂青三項。所謂“寫青”就是將青苗會應保護的青苗,劃分清楚,載之于冊,以便按冊保護青苗及收斂“青錢”的一種手續,在保護范圍內的耕田稱為“青圈”。青苗會成立的時間大約在玉米成粒之時,即陰歷七月初,或十三四日時,即陰歷八月中之時。寫青時應劃定青圈界限,清末以前青圈的界限劃分似乎從未發生過問題,但青圈內地畝的確實數字,卻不準確。每年寫青時,各地主報告青圈內的畝數常不確實,隨著村務中國家攤派費用的增多和青苗會功能的復雜化,迫使對地畝數的登記越加嚴密細致,除登記本村青圈以內的地畝外,還登記其青圈以外的地畝數,以便作為將來村中攤款的根據①。所以寫青實際上就是登記全村地畝數量,這說明其范圍已擴充到了青苗會本身事務之外而與村政相混合了,同時也證明青苗會的職責已經逐漸在溢出原有的單一職能。有的學者認為,為了明確村與村之間財政權與管轄權的界限,青圈亦成為村界,使村莊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擁有一定領土的實體②。有關“看青”職能的演變,我們在下面將進行討論,但“青圈”即為村界的結論恐怕有一定問題,因為解口村青圈內耕田的地主,不必屬于本村,也包括不少外村人。該村青圈面積為1530.5畝,村子恰居青圈的中心,直徑約為一里半,但圈內土地卻分屬六個村莊,“青圈”界限與村界顯然不一致。為了協調“青圈”內本村與外村人交納看青費有可能造成的矛盾,在“斂青”時形成了相應的協商和轉費制度,看青人將屬于自己看護的青圈但不居住于本村之人交納的看青費轉給相應的看青人,并接納對方轉交的“代征”看青費,有些地方村民稱這種“代征”為“聯圈制”③。據當時的調查,華北許多村莊都采取這種“聯圈制”,本村種外村圈地到外村交青錢,外村種本村圈內地到本村交青錢。
然而,“聯圈制”的實行一般只能在“青苗會”處于早期狀態下時才能發揮日常的作用,而國家權力的滲透導致“青苗會”功能復雜化之后,“聯圈制”因為只征收狹義上的看青費用,故而不能滿足現代征稅的要求。以解口村的“斂青”內容為例,“斂青”作為“青苗會”的最后工作,其內涵前后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斂青”在“青苗會”的原始形態時,只在禾稼谷物收割完畢后,收斂看青的費用,普通情況下在陰歷九月底或十月初舉行,但在光緒末年以后至民國初年,“斂青”的內容已經從單純的收取“看青費”擴展成了三項工作,即1.征收“青錢”:在光緒二十六年以前,每畝青錢為十六個制錢,后改為銅子四小枚。在民國元年時,增至二十枚;民國十九年時,每畝改為一毛。2.戶口費:這項費用大約在民國十八年開始征收,村民不論是否有耕田,只要被稱為一戶,就要納洋兩角五,村民叫做“灶火門”費,意思是按“灶火門”收費,每一個“灶火門”意為一個經濟獨立的家庭。3.村款費:這項費用包括村中一切花費,多則每戶多攤,少則每戶少攤④。從各種款項的劃分來看,“青苗會”的職責已遠遠越出了“看青”的范圍,而演化成了村級的征稅組織。“青苗會”在民國十七年以后有一個重要變化,土地登記和村差派遣以及斂錢攤款替代“看青”成為主要內容,同時“青苗會”的征稅功能也使得自然村顯示出了向“行政村”轉型的信息。
據萬樹庸對宛平縣黃土北店村的調查,此村“青苗會”的歷史就可清晰地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期,一是庚子(1900年)以前的地保時期;一是庚子以后的會首時期。黃土北店的地保姓施,已在村中住了十代,他擔當此職位是由縣政府指派的,以便在村內應酬官差,所以“地保”一職是現代警察制度建立以前的鄉村地方政治領袖,鄉與縣、縣與鄉種種關系都以地保作為溝通的媒介。凡由縣里派下的官差,每到一村,就向村民索要差費,所以地保即向青苗會的會員斂取,這樣一來,地保就會一面接應官差,一面向會員斂錢,便自然成為青苗會這種自然組織的領袖。“青苗會”的第二期改組是義和團事變以后外國軍隊攻陷了北京城,一部分官員為了追趕王室駐扎在清河鎮,要在一天的時間內向附近各村的民眾征收兩萬枚雞卵,如果沒有本地人員負責此事,就要親自下鄉奪取。以后隨著人事日繁,青苗會的組織系統為應付各種國家和地方的行政指令而變得日益復雜化了,最終擺脫了地保時期的初始狀態⑤。由于“青苗會”的事務與村中其它行政事務常常混淆不分,所以民國以后的人們談到“青苗會”時也往往不自覺地把它看作是村一級的日常行政單位。比如清河鎮的人們談到“青苗會”時就說:“談到我們鄉村中,都有自治機關,其中以青苗會(即村公所)為中心,村長、村副及會員為首腦,所管理的事,不過青苗會,應酬兵差官差,監督小學校,修蓋廟宇……”⑥可見“青苗會”已無法和村公所的職能相區分。
不過以上所述“看青”外延的擴大和組織行為的變遷,并不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滲入就一定賦予了“青苗會”這種組織以現代的新意。這表現在“青苗會”仍缺乏現代意義上的規范化管理,所有大小事情仍為會首和“管事的”所包辦,而且他們的位置都是世襲的,這種宗法性還表現在一切組織規則仍按習慣的程序處理,除出入賬之外,都是口頭的,毫無明文規定,有關一切事件的決議,也是在閑談中達成,只要無人反對,就默默地通過了。徐雍舜在《農村自治的危機》一文中曾經明確點明了“青苗會”功能擴大后的弊端,認為“組織變多了,村長、村副、閭長、鄰長、監察委員、調解委員、放足委員、財政委員、書記、校長、自衛團團總等等官銜,不一而足。村里的事情沒辦多少,而對外的事情卻極繁,今天征區公所辦公費,明天催保衛團餉金,后天征槍彈款,接著又是軍事捐、抗日捐、八厘公債、縣借款、教育費、房田草契費、中傭費、旗產留置費、警察費,征大車、征騾馬、征民夫”⑦。這里面的批評既包含了對“青苗會”功能多歧性的質疑,同時也暗示了其舊有組織形式基本沒有多大的變化。華北“青苗會”一方面開始應付日益繁重的國家攤派任務,另一方面卻仍保留了一些傳統社區內的職責,如需帶頭舉行求祈龍王賜雨等等宗教儀式。“青苗會”在其他村莊內也體現出了強烈的“兩面性”,包括管理一村公產(如廟宇、香火地、坑地、義地、官井、樹木等)以及重修或新造公共建筑。“青苗會”一方面要主持村級的“新政”事務,比如新式學校管理便操諸于青苗會或鄉公所之手,學校組織的最高當局如董事會和校長,往往也是青苗會的會首,由他們控制經費及用途,至于聘請教員和校役,添置教具,分配課程,規定假期等事,也都在他們監督之下。另一方面,“青苗會”仍操縱著村級的宗教和宗族事務,比如清河鎮以廟宇為中心的宗教活動,一般分公私兩祭。公祭每逢正月十五日,由村中領袖代表并統率村民至各廟致祭,并散放燈花,驅逐鬼怪,這叫“燈節”。至于六月二十四日關公生日,及“謝秋”、“祈雨”等活動,也都由青苗會或鄉公所領袖在廟內主祭⑧。
通過以上的材料分析,“青苗會”從清末至民國確實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其特征是職能分工更加復雜化了,已經完全越出了原初單純“看青”和“保衛”的作用范圍,而成為國家在基層實施新政的工具和手段。但這并不意味著華北“自然村”共同體體系已遭到了根本的破壞,因為“青苗會”除了其行政職能外,仍保留著鄉村秩序協調和保護人的角色,比如對宗教祭祀活動的控制與中樞作用。特別值得明辨的是,“青苗會”部分行政職能的國家化,并不意味著其基層權力系統發生了根本變更,這特別體現在對“會首”資格的遴選方面。
二、“青苗會”與鄉村權力網絡
解口村的“青苗會”作為早期自發組織形態時,在選擇會首的過程中,大致應符合以下標準:首先要家庭富裕,能給會中提供零用物品(如柴火、油等);其次要有空房能作為開會或存放會中公共糧食之用;最后是辦事能力強,自幼即幫辦會務,有一定經驗。“會首”的任期無一定限制,一般都是以家庭為單位,而不是以個人為單位,也就是說,只要家中富裕,雖人不能干,會首也必定由此家選出。所以“會首”之職往往是世襲的,或者可以說是財產標準創造和決定了會首世襲的條件。
自光緒元年至民國二十年,解口村共有六人出任會首,平均每人任期為九年半。從會首姓氏分布觀察,多集中于張、梁兩家,其中梁家在村中的戶數和人口數最多,張家則居第三位。在全村62戶中,梁家占36戶,為總戶數的58.1%,張家有4戶,占6.5%,可見“會首”的選擇也多少與其姓氏人口在村中所占的比例有相當的對應關系。光緒初年解口村的會首是張榮,張姓戶據說自明末始遷至該村,當張榮辦村事之初,曾開茶館于韓村鎮,喜歡與富人聯絡,后來又開了一家雜貨鋪,此鋪也是當時該村趕集時聚會的地方。除擁有一所雜貨鋪外,張榮還有本業地77畝,土房二十余間,大車一駕,是村里當時的第三富戶。除青苗會首一職外,張榮還兼村長、禁賭會長、路燈會長,活動能力很強,人皆稱“老張先生”、“張大爺”、“榮爺”。經訪談,張榮取得會首的原因曾經源于一段故事:同治十一年時,解口村全體村民同韓村鎮趙某爭訟,結果青苗會所有款項都已花完,張榮于是將自己耕田三十畝作為抵押品,借得款項后充當全村的訴訟費用。這件事結束后一年,村民商議每年從公款中撥出若干以賠償他所遭受的損失,同時選其為青苗會首管理村事,可見在緊急之時有財力墊付村款應是出任會首的最必要條件⑨。
張榮在光緒元年出任會首后,直到光緒十九年因年老精力不濟退位,在位共19年,由其子張彥山繼任。可是因為張彥山太不能干,被人稱為“狗熊”,搞得家產漸少,房屋傾塌,任職僅六年就下臺了,由梁家的梁江接任。梁江自二十歲時,即幫同辦理會務,取得會首位置時,已年屆五十。他家擁有本業地同租地共約百余畝,土房十二間,可是因為好飲酒,家中又無空房供開會之用,所以僅當了兩年就讓位給了梁春之子梁玉林。梁玉林有本業地二百余畝,磚房十二間,但因人口少有空房,又有現錢為會中墊用,所以是最合適的繼任人選,任期也較長,自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共十年。從此之后,解口村“青苗會”的會首位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為梁家所世襲和壟斷⑩。
“青苗會”的會首在有的地區也采取某種集體輪換制度,如宛平縣黃土北店村的“會首”多達二十名,在國家力圖以行政村的組織形式改變地方組織之前,二十名會首中以當上村長、村副者為最有權,在無村長、村副的名目以前,其中六位會首輪流管賬管錢,有了村長、村副的名目以后,每年另有一人管賬,如1932—1933年度為鄧浚海;1931—1932年度為劉廣生;1930—1931年度為劉廣生;1929—1930年度為秦世榮。此外另有司庫管錢。由于黃土北店村較富裕,會中每年都有存款,但又恐外村知道,抱怨在區內攤款不均,或被官府知道隨意加征提取稅款,所以賬目只有二十名會首知道,其余民眾一律不得而知。黃土北店村的“青苗會”盡管在外表上采取的是不同于解口村那樣的家族壟斷制,而是比較注重集體公正性的輪流策略,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其中的權力構成結構,就會發現其中宗族、知識和財富仍是謀求此項位置不可或缺的三項要素。在宗族關系方面,六位輪流掌權者中,除趙德章基本與他人沒有親屬關系外,其他五人之間都有連環套式的親戚關系,如趙本是趙玉林的叔叔,趙棟的堂兄,許寬的親家,同時又是葉方珍的妹夫。就知識經歷的構成比例而論,二十位會首平均年齡43.85歲,入學平均年齡是六年半,而全會讀書的比例是33%,沒有讀書的比例是63%,說明這些會首相對都受到了較良好的初級教育。就財富占有量來說,這二十位會首只占全村276家戶數的7%,卻擁有2930畝面積的土地,在全村7033畝耕地中占41.66%,平均每家擁有土地約為150畝,這與當會首負有的首要職能是墊款有關,親族關系和知識擁有量只是從屬因素。
黃土北店村“青苗會”對權力網絡的設計,采取了三級制的運作框架,即由二十名會首、六名會頭和兩名村長副村長的金字塔型制度構成,以應付民國以后自然村日益行政化的趨向,這種會首輪值制度從表面上突破了單一家族的世襲程序,也有可能會增加村莊征稅和其他行政部門的實際效率,但由于權力仍集中于少數擁有財富的家族之手,“青苗會”不過是在同一地點、同一人物的網絡中,同時擁有政治名稱和自治名稱的機構罷了。比如黃土北店村村北關帝廟的門口掛著“宛平縣第五區黃土北店村公所”的牌號,其實也同時是青苗會的辦公場所,村長、村副由青苗會六名掌權的會首輪流充當的時間是三年一個周期。比如1929—1930年度為趙德章與趙本;1931—1932年度為趙棟與許寬;1930—1931年為葉方珍與趙書林;1932—1933年度又是趙德章和趙本。華北的其它村莊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如太子務村青苗會首領稱為首事人,往往有一二十位之多,從這些首事人中推出一個“香頭”,“香頭”的位置相當于村長,“青苗會”的另一個職務叫“總管”,相當于村副,首事人同時又被稱為管事的。“香頭”的職位也采取輪流制,每人輪一年,村中有事由“香頭”負責召集,會場就設在他的家里。宣統元年間縣政府下命令選舉村正、村副時,由首事人公推,但實際上仍是由香頭接任,因此“香頭”制取消,首事人仍照舊。第一任村正、村副在任約有十年之久,民國元年起開始有自己的辦事場所。經過村正、村副選舉之后,“青苗會”改稱公議會,其實是同一回事,可見太子務村的青苗會仍保持了原有的管理系統。
通過比較解口村、太子務村的會首權力網絡及其功能,我們注意到,“青苗會”自身的權力機構和作用有相當的延續性,盡管國家在二十世紀初一直想通過行政控制的手段,力圖把華北一帶的自然村落置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總體規劃之中,以此來改變村莊內部的權力結構。從表面上看也確實部分達到了這個目的,因為“青苗會”的職能外延確實有所擴大,而且幾乎包容了國家基層行政的各個方面。但值得深思的是,“青苗會”表面功能作用的演變,其實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組織內部的權力構成和運轉方式,這些新型事務的實施大多仍是由原有的傳統社會網絡加以推動和完成的。比如真正操縱鄉村社區事務的仍是有經濟勢力的族人和與他們相關的社會關系,他們也負有篩選國家信息以保護地方族人利益的責任。
三、結論
正如本文開頭所討論的,華北的“青苗會”有一個從簡單的看青組織向復雜的行政組織轉變的軌跡,如何評價這種轉變基本上形成了兩種極端的對立觀點,一是認為“青苗會”依靠處理日益增多的行政問題而趨于復雜化,這恰恰增加了村莊的凝聚力;另一派觀點則認為,基層組織行政色彩的增強恰恰是自然村解體的標志,它喻示著村莊凝聚力的瓦解。目前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國家現代化策略逐步深入農村,鄉村領袖已無法依靠自己的財富和關系來樹立威信以得到村民的擁戴。通過以上研究我們發現,應把“青苗會”處理實際事務的類別日益增多所造成的村級表面的行政化,與鄉村傳統權力網絡是否真正瓦解區別加以對待。換言之,村莊事務中處理行政性能的增加,或村級領袖的更迭,并不意味著傳統的鄉村事務同時面臨解體。一個“青苗會”的會首有可能同時扮演催款征糧和主持鄉村宗教祭祀的雙重角色。“青苗會”自身也可能同時體現出這種雙面的作用,更應深思的是,鄉村百姓往往會操縱國家話語以為己用,他們表面上對國家行政意志的屈從,恰恰可能轉化為地方社會的權力資源。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不應只注意地方政府的軍事化、現代化與田賦負擔劇增的雙重壓力下傳統村莊的解體趨勢,而更應注意村規等隱性話語和權力之間的互動關系,即村民如何操縱村規以利于自己的行為,同時在此網絡中維持著村社共同體,而不使之瀕于瓦解。對華北“青苗會”的研究也應作如是觀。
①④⑨⑩梁楨《解口村大秋青苗會之概況》(民國二十年七月調查),《社會研究》第四十期,民國22年2月6日。
②③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第187—18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⑦徐雍舜《農村自治的危機———農村社會研究感想之二》,《社會研究》第十三期,民國22年11月29日。
⑥《青苗會送龍王》,《清河旬刊》第七十號,民國24年9月10日。
⑧黃迪《清河村鎮社區———一個初步研究報告》,《社會學界》第十卷,民國27年6月版。
⑤萬樹庸《黃土北店村社會調查》,《社會學界》第六卷,民國21年版。李懷印《二十一世紀早期華北鄉村的話語與權力》,《二十一世紀》1999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