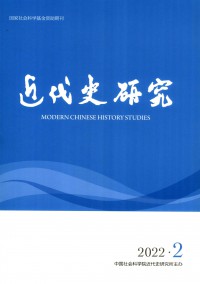近代民眾和醫生對鼠疫觀察和命名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近代民眾和醫生對鼠疫觀察和命名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從近代普通民眾和醫生的視野,探究他們如何描述鼠類活動和患者癥狀,以及如何命名鼠疫的,對于鼠疫辨別是有幫助的。雖然民眾和醫生對鼠類活動和患者癥狀有相當的認識,但并沒有將鼠疫和其他傳染病區分;對于鼠疫的命名,和以往相比,依然復雜多樣。
關鍵詞鼠類活動;癥狀;命名
TheobservationandnamingtoplagueofpeopleandmedicalpractitionersinmodernChinaLIYushang,ResearchCenterforHistoricalGeogra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
AbstractItishelpfultodifferentiateplaguefromotherinfectiousdiseasesfromthepointofviewofordinarypeopleandmedicalpractitioners,byobservingandstudyinghowtheyobservedtheactivitiesofrats,describedsymptomsofpatients,andnamedplague.Althoughtheyhadwellknownaboutsuchknowledge,theydidnotdistinguishthisdiseasefromothersandalsohadvariousnaming.
KeywordsActivitiesofrats;Symptom;Naming
一、問題的提出
研究中國歷史時期的鼠疫的學者碰到的難題之一,就是如何斷定史籍所載的某種疫病是鼠疫。醫史學界公認中國最早的鼠疫專著《鼠疫治法》出版于1891年,不過,此書并未廣泛傳布。廣東石城羅芝園據吳宣崇著作,并把王清任醫治北京霍亂時的解毒活血湯變化加減而成治鼠疫主方,編為《鼠疫匯編》,在羅芝園本人、各地中醫生和地方人士的幫助下,此書得以廣泛傳布,鼠疫及其治療方法才廣為民眾和民間醫生所知[1]。在治療鼠疫專書出現之前,醫者對此病茫然無知,如在云南,“受其害者百有余年,時醫無從下手,一概指為天災”[①],廣州的醫生也“鮮知其病所由來,但名曰核癥,而無從考其核之所由來”[2]。由于光緒十七年以前的民眾和醫生對此病認識不足,后世學者在利用歷史文獻來判定某種疫病是否是鼠疫時,就會產生分歧。
范行準和曹樹基都認為中國金元時期就有鼠疫流行[3]。曹樹基的研究表明,明代后期在華北、江南和四川等地,又爆發了兩次規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4]。這些研究主要是根據癥狀來判斷鼠疫的。對于辨別原則,范行準認為:乾隆以前,人們并不知道鼠疫的真正病源,直到乾隆年間才知道與死鼠有關;表現在病名上,醫家“多以片面的病狀命名,故往往同一種病因所發病的部位不同,而有幾種不同的病名”,因而鼠疫在歷史上的名稱十分復雜,諸如“時疫疙瘩”、“大頭天行”、“陰毒”、“陽毒”、“蝦蟆瘟”和“瓜瓤瘟”等都曾是各種類型鼠疫的俗名。以后,隨著人們認識上的進步,這些病名漸成為歷史名詞。[5]從民眾和醫生對鼠疫的認識程度出發,最大限度來辨別疫病的類型,這種研究方法是可取的。
范行準認為乾隆以前的民眾和醫生并不能認識鼠疫。考明末吳又可在《瘟疫論》中曾論及“疙瘩瘟”和“瓜瓢瘟”,至光緒年間,廣州名醫區德森在鼠疫流行面前,認為疙瘩瘟“即鼠核瘟也”,瓜瓢瘟“即標蛇癥也”,標蛇癥即為肺鼠疫,此癥“與疙瘩瘟病相同,治亦相同”[6]。光緒年間的醫生已經認識到“疙瘩瘟”和“瓜瓢瘟”只不過是人間鼠疫的兩種常見形態罷了,這證明了范行準研究的正確性。乾隆以后,隨著鼠疫的經常發生,民眾對于此疫有了相當的認識,知道此病的發生與鼠有關,也創造出各種避疫的辦法[7],對于患者的癥狀也有了相當的認識,這也證實了范行準的研究。
不過,直到最近,國外一些學者對這種辨別方法仍抱懷疑態度[8]。鄧海倫(HelenDunstan)的觀點在西方最具影響力,她認為辨別歷史時期某種厲害的傳染病是否鼠疫的標準,就是看這種疫病發生時是否伴隨著死鼠現象[9]。據中國鼠疫專家的研究,在人間鼠疫發生之前或同時,一般都會伴有鼠間鼠疫的發生[②],因而,歷史時期發生人間鼠疫時,也必然會出現死鼠現象。雖然自斃鼠現象對于確定某種疫病是否是鼠疫是有幫助的,但是這種研究方法并沒有考慮民眾和民間醫生對鼠疫的認識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也沒有考慮歷史文獻對疫情記載模糊不清的現實。如果僅僅相信有自斃鼠現象出現的疫情是鼠疫,我們就不能夠“復原”中國歷史時期的鼠疫。
乾隆后期鼠疫在云南爆發,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流行不斷。同治年間,雷州半島也爆發鼠疫,并于光緒年間傳至粵東和福建,此后,此疫頻繁發生,直到1949年以后人間鼠疫的流行才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中國其它地區,也時有發生。筆者無意介入清代以前對于鼠疫辨別原則的爭論,而試圖從近代民眾和普通醫生的視野中,考察他們對鼠類活動和患者癥狀的描述以及對鼠疫的命名。從這一角度觀察近代的鼠疫,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們對利用癥狀判斷鼠疫的疑惑,增加學者辨別鼠疫的方法,在人們追溯更早時期的鼠疫時,有所借鑒。
二、對鼠類活動的觀察
在人間鼠疫發生之前,一般會先有鼠間鼠疫發生,人間鼠疫的發生只是偶然現象。據1950年代廣東的調查,鼠間鼠疫的流行情形如表1所示。
表11950年代調查廣東各縣鼠類活動[③]
縣市
鼠類活動
儀縣
在發生鼠疫前后均有大批老鼠死亡,尤其是大流行時。當時鼠尸滿地鋪,幾乎每家一天都拾到一糞箕尸體。老鼠死亡的情況多是走到水缸邊或天井里大量喝水后死去,或在地上打滾一陣而死。且有死豬、死狗、死蒼蠅的現象。
香山
鼠疫前老鼠很多,多在地面行走,因天熱不能在地面住宿而遷徙到別一地方,經過一夜,就可掃出幾雙死老鼠來。老鼠從梁上跌下地面,或走出地面時就會死去,有時在街上就可看到死老鼠。這個時期,老鼠不在地面住而遷到樹上,或屋面上去住宿。鼠疫前先發現自屋梁、屋角跌出死老鼠,或發現老鼠爬出,在水缸邊或走出有水的地方喝水,未喝到水或喝了水之后,人們就發現有自斃鼠死在水缸邊或死在屋前后或屋角周圍。
欽縣
發病之前先有死老鼠,在天井、水缸邊,或跌落水死。雞鴨也有死亡。
海口
在鼠疫發生流行前及流行期中,自斃鼠多走路緩慢,毛豎起,無精神,見人不避,白天出來喝水,有的就死在水旁邊,或在路上死亡。
佛山
每次鼠疫發生必先有自斃鼠,多發現于床下、廚廁、冷巷、溝渠等地。
增城
均有死鼠,往往在該病發生前,在井渠、天井等地發現。死鼠中有大量的跳蚤。
興寧
在發生鼠疫前后均有死鼠發現,尤其在發生人間鼠疫前一二天多的時間,病鼠都是由鼠穴跑出,發呆,在空地上旋轉幾次即行自斃,亦見有在水井或其它地方吃水即行自斃。
紫金
老鼠本身有鳴叫聲,易以發現,速度極慢,行動蹣跚,常到有水的地方喝水,喝水后即死,但也有不喝水而死的。死的到處都可以看見,如道路上,溝渠里,屋內等。在鼠疫流行期間,也有先有老鼠成群搬家到荒效叢草中去的現象,但也有到半道死,也有死在山中的。
澄海
在鼠疫發生前普遍發現病鼠從樓上或屋頂梁上跌下,亦有從鼠洞爬出,步行蹣跚,行動不定,毛發聳然,精神疲乏,有到水溝吸水死亡。
海豐
在當時白天常見病鼠跑出洞外,行動顛蹶,不甚快捷,隨處找水喝,多死于水邊。
普寧
疫情前發見死鼠,蹣跚行走不畏人,毛發豎起,往水壩喝水,有死于地上或地下及水溝,在貧困污穢農家往往發現蛆蟲,金色蒼蠅到處亂飛,有些樓上死鼠成堆,鼠死后一月或十天即發現病人,更有些人發現成群隊搬家。
大埔
先有自斃鼠,臨死前多在街旁水井飲水,不怕人,飲水后即死亡。死亡皮膚松馳,失去光澤,肚飽漲。
因系1950年代的調查,故表1所列廣東12縣民眾和醫生對鼠疫流行中鼠類活動的描述甚詳。各地民眾的觀察主要包括以下五點:1、大批老鼠死亡;2、病鼠出洞不畏人,蹣跚行走;3、老鼠死亡的地點大都是在塘邊或農戶的水缸邊;4、有成群鼠類活動;5、死亡動物中雖然以鼠類為主,但也有家畜死亡的現象。云南民眾和醫生的觀察在某些方面與廣東相同。1957年昆明大漁村70歲的張松年老人回憶說:“癢子病是在同治壬申屬猴年說死的人多,病起之前先是老鼠來吃水,死在水桶面前,先死老鼠后死人。”西莊村92歲的張大爹回憶道:“發病前有大批老鼠死亡,我們叫鼠瘟,然后人就得病。”[④]
鼠類成群移動的記載特別值得注意。在1950年代云南的調查當中,也發現有同樣的現象,如在江川縣,“本縣在1868年回漢相爭到1860年止,死亡人數較多,繼后續發現老鼠大批死亡,家里出來的都是病,死者多在室內及村落周圍,雞也死,據說有一次有很多的,咬一個的尾巴由南門進來跑到縣政府里去,到大堂處就散了,以后就發生鼠死”[⑤],再如徵江縣,據調查:“在清同治十年(即辛未年)二月……在城內曾見老鼠搬家,一個咬著一個的尾巴從街上逃跑,至三四月間,西街子即有人患癢子病,迅速向城中傳來。”[⑥]北方也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如在甘肅阜城,“據說在發病前一年,村內黃鼠成災,幾乎村內的莊稼全部吃完”[⑦],在陜北定邊縣,據調查,民眾反映“1919年冬,黃河自宋家川(吳堡縣)以上全部封凍,當時曾見大批老鼠自山西排隊過河,至葭縣(佳縣)木頭峪一帶,30年初即見大批死鼠”[⑧],在鼠類成群移動之后,就發生了人間鼠疫。鼠類異常活動的記載對于我們辨別歷史時期的鼠疫是有幫助的,在此僅舉一例。
明崇禎年間有關鼠類異常活動的記載驟然增加,如《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389《開封府部》記載:“崇禎十四年,夏大疫,人相食,有鼠千百成群渡河而去。”順治《郾城縣志》卷8也有類似的記載:“崇禎十六年有鼠無數,群行田間,幾至成公徑,甚至與貓共處。”光緒《順天府志》卷69的記載稱:“崇禎十六年,先是內殿奏章房多鼠盜食,與人相觸而不畏。旦后鼠忽屏跡。”曹樹基從瘟疫的癥狀和時空分布上認為這兩年的疫情為鼠疫。其實,范行準早就注意到了明末鼠類異常活動的現象,他認為這些記載“暗示”著鼠疫的發生。從近代鼠間鼠疫流行過程中鼠類異常活動來看,范行準的這一判斷是有根據的。嘉慶《廬州府志》卷49《祥異》有更明確的記載:“崇禎十四年大疫,郡屬旱蝗,群鼠銜尾渡江而北,至無為,數日斃。”鼠類成群遷移和死亡的原因有多種解釋,雖然我們并不能將出現自斃鼠現象的“大疫”貿然斷為鼠疫;但如果考慮到瘟疫流行所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和極強的傳染性,加之有“毒瘤殺人”、“大頭瘟”、“疙瘩瘟”等記載,應當斷為鼠疫。
三、對患者癥狀的描述
在1950年代的調查中,不少被調查者曾感染過鼠疫,如在云南蒙自,在被訪問的216位老人中,有33人曾患過鼠疫[⑨],故而他們對于癥狀的描述十分可信。廣東各縣的描述如表2所示。
表21950年代調查廣東民眾和醫生對鼠疫患者的描述[⑩]
縣市
民眾和醫生對鼠疫患者癥狀的描述
新定
發熱,頭痛,惡寒,神志昏迷,兩眼充血,腹股溝或腋下有雞蛋般大小的腫核,病后數小時至二天內死亡。
湛江
起病時發高熱,頭昏頭痛,說胡話,也有全身發紅,昏迷,頸小腹股淋巴腫大,起病過程甚急,大部分死亡,快廿四小時,最長2-3天。
儀縣
先發熱,發冷,頭痛,全身不適,急躁不安,亂起譫語,頸部、腹股溝及腋窩淋巴腺腫大、劇痛。死亡急者幾小時死亡,一般3天內死。亦發現個別咳嗽吐血而亡。
儋縣
除腹股溝、腋窩和手腳都起核外,還有個別患者有咳血、胸痛等肺鼠疫的癥狀。
澄邁
腋腺長凸核,核部有發爛現象。死亡時間都在5-7天,過七天大都未死。
臨高
先有局部腫,逐漸全身淋巴腫。
梅縣
發寒,發燒,起癧結核,眼腔發紅,口唇發紫,譫語,舌甚至呈黑色,大渴。嚴重者可在幾小時內死亡。
順德
高熱,惡寒,昏迷,譫語,腹股淋巴腺腫大,起病后3-7天死亡。中醫師溫沉河、吳星槎謂患者約有30%皮膚并有發現菸斑,
佛山
惡寒,發熱,頭痛,眼紅,腫大,口渴,舌黃或黑、譫語。
惠陽
初起病很急,發高熱,畏寒,全身發軟,特別是腫大,多在腋窩及腹股溝鼠蹊部,紫色硬塊,或有鼻出血,咳嗽,急在24小時內或二天至三天就死亡
增城
初期腹股淋巴腺腫大,而后發熱頭暈頭痛,昏睡,腋下淋巴腫大,死后全身呈紫黑色。
興寧
多數是發熱,狂躁不省人事,鼠蹊部淋巴腺腫大,也有一些病例有咳嗽咳血的,多在3-4天內死亡。
龍川
突然寒戰發熱,呼吸急促困難,腋下及鼠蹺部淋巴腺腫大和潰腐。
海豐
死后皮膚顯黑色等狀況。
大埔
高熱,劇烈頭痛,口喝,譫語,昏迷不省人事,淋巴腺腫大化膿,數小時數天即死。
從表2可以看出,廣東15縣民眾和醫生對患者癥狀的描述相當細致,主要包括以下幾點:1、高熱畏寒,頭痛,昏迷,譫語等;2、死亡速度快,就大多數的患者來說,急者幾小時死亡,一般3天內死亡;3、描述最多的是淋巴腺腫大以及相伴隨的腫痛、化膿、潰腐現象;4、對肺鼠疫也有認識。民間醫生的觀察還要細致一些,如觀察到患者眼腔發紅,口唇發紫,舌粗,舌呈現黑色或黃色,死后皮膚顯黑色或者紫黑色等等。其它地區的民眾和醫生對癥狀的描述與廣東相同。如在陜北,據觀察,“癥狀以發燒、頭痛、昏迷為普遍,大部病例有局部或全身淋巴腺腫,綏德、米脂、橫山縣部分地區尚有咳嗽、吐血等疑似肺鼠疫的癥狀,但多見于流行后期”[11]。近代民眾和醫生對患者癥狀的觀察與現代流行病學并沒有太大差別。
雖然近代民眾和醫生對患者的癥狀已經有了相當地認識,但并沒有將鼠疫和其他烈性傳染病區別開來。如在云南,乾隆以后由于鼠疫頻繁發生,民眾和醫生已經知道了該病的病源,也十分清楚患者的癥狀,但當古典型霍亂于1817年傳入該省后[10],當地人并沒有將鼠疫和霍亂區別開來。道光三年,程含章上表云:“溯自乾隆己酉,地震山搖,邇來三十有五年矣,疫瘟流行,纏綿不已,或生癢子,或起毛疔,或手足麻木而不仁,或頭面昏沉而作熱。朝人暮鬼,命輒喪于斯。”道光十年,程含章又上表說:“云南陽愆陰伏,氣閉不舒,自乾隆己酉地震之后,疫疾大作,始于賓川,漸及于各府州縣。或生癢子,或足轉筋,或吐紅血,或兼瀉痢。四十余年以來,死亡者數十萬人。”[11]文中所描述的“起毛疔”、“生癢子”、“吐紅血”、“頭面昏沉而作熱”為鼠疫患者的癥狀,“手足麻木而不仁”、“足轉筋”和“瀉痢”則為霍亂患者的癥狀。時人并不能區分這兩種不同的疫病。即使到了1950年代,廣東海康縣的民眾仍然如此:“我們往往在訪問群眾時,他們所說的年冬病,有的地區連天花、霍亂亦稱為年冬病,故三種病在群眾是混淆不清,只有我們在調查訪問時,我們從中引導群眾將三種病主要癥狀分別開來。”[12]由于這幾種疫病都有極強的傳染性和極高的病死率,民眾根本沒有必要去細分。可見,民眾和醫生對于鼠疫的認識,直至近代,仍然存在著不足,這在命名上也有體現。
四、對鼠疫的命名
1950年代調查廣東各縣民眾對于鼠疫的俗稱如表3所示。
表31950年代調查廣東各縣民眾對鼠疫的俗稱[13]
縣市
俗稱
縣市
俗稱
羅定
發人瘟,或叫瘟疫、疫癥
廣寧
發人瘟、起核病
新興
大案、人瘟疫
鶴山
發人瘟、生核癥
江門
溫疫、核癥
恩平
流北癥
湛江
年冬病或年冬鬼
信宜
發人瘟、老鼠瘟、死老鼠病
儀縣
時癥、人頭癥、老鼠瘟、大水癥
新定
時癥毒核、標蛇毒核、時疫、核瘟、毒核、惡核
茂名
時癥、發人頭瘟
海康
年冬病
北海
碼小癥或零小癥
儋縣
起核癥
海口
核癥、鼠核癥、鼠痧、彈子病
香山
起核癥、疫癥、時行瘟疫、年冬病、鬼領
安定
瘟疫、瘟癥
梅縣
人瘟、時癥
順德
核癥
佛山
核癥
惠陽
瘟疫
龍門
癧子病、鼠疫
增城
人瘟、鼠氕、鼠疫
清遠
出核
樂昌
發人瘟
興寧
發人瘟、發癧子、時癥
仁化
人瘟
連平
老鼠瘟、發人瘟、時癥
紫金
人瘟癥、鼠瘟癥、老鼠病、鼠疫病
澄海
控槌案、浮核、瘟疫、著瘟
惠來
著人瘟、著大擺
海豐
鼠核癥、毒鼠瘟
普寧
當青青、打瘟癥、硬腳癥、驚沾瘟、大水案、著人瘟、瘟疫、著大板、棒槌案、大擺案、大頭天利、大頭瘟
揭陽
大擺案、瘟疫、控槌案、大水案、著人瘟、趕大批、浮核癥
汕頭
瘟疫、腳邊浮核病、惡核、鼠疫
潮州
人瘟、粒總、粒腫
據表3,根據民眾對鼠疫的命名原則,分為以下四類:
1、以癥狀命名腺鼠疫患者最明顯的癥狀是淋巴腺腫大,因此出現了大量帶“核”字的鼠疫病名,包括“浮核”、“毒核”、“起核病”、“標蛇毒核”、“惡核”和“出核”等稱呼。不同的出核部位有不同的命名:“浮核”是指鼠蹺部的淋巴腺腫大[14],“惡核”是指腋下的淋巴腺腫大[15]。“彈子病”和“癧子病”的含義與“核病”相似。鼠疫在潮州又被稱為“粒總”或“粒腫”,當地人對此的解釋是:患鼠疫病的人身上會浮現紅粒子,故稱之為“粒”,從前民眾把政府出差老爺稱為“老總”,老總到處殺人、捕人和搶奪財物[16],而患了鼠疫的人很快送命,二者聯系起來,就出現了“粒總”這一病名。澄海縣民眾稱鼠疫為“控槌案”,意指人被槌棒打中頭部,立即暈倒致死[17]。此類病名的出現顯然與民眾原始思維習慣有關。普寧縣的土著居民稱鼠疫為“大頭瘟”或“大頭天利”,調查者認為是腦膜鼠疫。溫病學上大頭瘟為腮腺炎;范行準和曹樹基認為,在金、元和明代中后期,也有稱鼠疫為“大頭瘟”的,范氏認為是腦膜鼠疫,而曹氏則認為是腺鼠疫。
2、以傳染性命名在上表101個鼠疫病名中,有34個是以傳染性命名的,包括“瘟疫”、“時疫”、“人瘟”或“時行瘟疫”等稱呼。在這一類病名中,有近一半被稱為“人瘟”或“發人瘟”。“人瘟”意指傳染性很強的疾病。可見,民眾在很多情況下把傳染性強、病死率高和對社會危害極大的疾病歸為一類,并沒有將其區分。
3、以發生時間命名1950年代鼠疫專業人員在廣東海康縣進行調查時,發現鼠疫、天花和霍亂被當地人稱為“年冬病”。民眾將發生時間相同的疾病歸為一類,于是創造出“年冬病”或“年冬鬼”這樣包含著多種疾病的病名。在缺乏有效避疫手段的社會里,為在疫病多發季節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民眾對疫病發生的時間十分關注。如茂名縣每當三月份時,當地人就到村外、野外去躲避鼠疫。在這種情況下,民眾自然會對那些經常危害當地社會的傳染病的發生季節相當熟悉,從而出現了以發生時間命名的鼠疫病名。
4、和鼠有關的命名在101個鼠疫病名中,只有15個病名與“鼠”有關。從與鼠有關的病名的數量來看,值得注意的倒是“鼠瘟”。范行準在《中國醫學史略》中也提到一本《鼠瘟寶卷》的書。“鼠瘟”即大量自斃鼠出現:“(鼠類)白天出來找尋食水,不怕人,毛豎直,走路蹣跚,不久自斃,群眾叫‘老鼠瘟’。”[18]有的地方稱鼠疫為“著大擺”或“鼠痧”,鼠疫如何與“打擺子”或發“痧”發生聯系,不得而知。民眾對鼠疫還有其它稱呼,調查報告并沒有說明其含義,姑且置之。
鼠疫在云南民間也有多種稱呼,如在宜良縣,“群眾的叫法也很多:如羊子疙瘩、火炸羊子、九頭羊子、格格癥、楊大哥、楊大爹的,他們也有少數講有吐紅痰的”[19]。在這些病名中,“癢(羊)子病”最為云南民眾所知。“癢子”,即羊睪丸,腺鼠疫患者身上會“生赤癢子”[12],人們由人身上所生“赤癢子”聯想到羊睪丸,“癢子病”這一病名由此產生。這一病名通俗易懂,故易為民眾所接受。“疙瘩瘟”是迤西地區民眾對腺鼠疫的稱呼,這一病名和“癢子病”一樣,都是人們對腺鼠疫患者腫大的淋巴腺形象描述,只不過它沒有與其它類似的事物聯系起來。肺鼠疫患者會“吐血痰”,民眾就以“紅痰”命名[13]。
最后來看醫生對鼠疫的命名。腺鼠疫被清代廣州的醫生稱為“核疫”[14];肺鼠疫被稱為“標蛇時疫”[15]。如上所述,民眾中也有稱鼠疫為“核疫”或“標蛇”的。1950年代的調查也證明民間醫生和民眾在鼠疫命名上并無差別,如連平縣當時鼠疫中醫病名為“冬瘟癥”。民眾與醫生對鼠疫命名具有一致性。
五、結論
近代民眾和醫生對鼠類活動和患者癥狀已經有了相當的認識;然而,出于避疫需要,民眾和醫生并沒有將鼠疫和其他傳染病區分。反映命名上,對鼠疫仍有多樣稱呼,這些病名并沒有隨著“鼠疫”一詞的傳播,而成為歷史名詞。從近代民眾和醫生的視野中去理解鼠疫,不僅為我們增加了利用鼠類活動辨別鼠疫的新標準,也使我們認識到,在復雜的民間社會中,從這一角度出發,綜合利用各種辨別方法,對于辨別疫病類型是有幫助的。
參考文獻
1李禾、賴文.羅芝園<鼠疫匯編>在嶺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價值.中華醫史雜志,1999,29(2):100-103.
2余伯陶.鼠疫抉微.見:曹炳章.中國醫學大成.第4冊.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732.
3、5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曹樹基.地理環境與宋元時期的傳染病.歷史地理(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83-192.
4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年).歷史研究,1997(1):17-32;曹樹基.《中國人口史》.卷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47-48.
6區德森.《時疫辨》.卷3.光緒二十七年.廣州宏經閣刻本.
7李玉尚.近代中國的鼠疫應對機制――以云南、廣東和福建為例.歷史研究,2002(1):114-127.
8CarolBenedict.BubonicPlagueinNineteen-CenturyofChina.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96.
9HelenDunstan.TheLateMingEpidemics:APreliminarySurvey.Ch’ing-shihwen’t-i,1975(3):1-59.
10李玉尚.霍亂在中國的流行(1817-1821).歷史地理(1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16-335.
11侯應中.《景東縣志稿》.卷15.民國十二年石印本,2.
12阮元等.《云南通志稿》.卷200.道光十五年刻本,18.
13楊瓊.《滇中瑣記》.騰越李氏鉛印本.
14廣東省醫藥衛生研究所中醫研究室.廣州近代老中醫醫案醫話選編.廣東科技出版社,1979,121-127.
15宋學亮.《鼠疫良方》.民國石印本,4.
文檔上傳者
- 溫州近代醫學探析
- 中日近代化分析
- 近代農村金融論文
- 政黨近代產生文學探討
- 近代美術藝術期刊插圖藝術研究
- 古代與近代武術變遷動因
- 加強農業近代化水平
- 鄂爾多斯地區近代移民
- 近代鎮集發展和變遷
- 近代農民離村和城市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