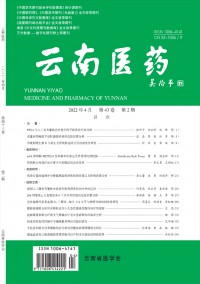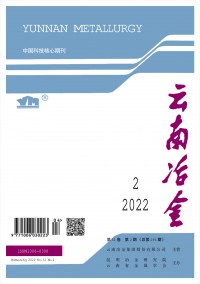云南花燈藝術探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云南花燈藝術探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云南花燈形成的年代大約在300多年前,但其演變成為花燈劇的年代,已無確鑿資料可查。花燈在辛亥革命前被稱為老燈,其藝術形式是一種歌舞,也是一種戲劇情節簡單的歌舞小戲,后來玉溪花燈吸收了滇劇表演形式,引進了若干新曲調,改編并創作了一些新劇本,當時被人們稱為新燈,后來花燈藝人大量移植滇劇、京劇的劇目,吸收它們的表演技巧及服裝,用花燈曲調演唱,形成燈夾戲。燈夾戲是花燈滇劇化的表現,燈夾戲很多曲調來自明清小曲,這些小曲傳人云南后,與云南的方言、風土人情結合,后來成為云南花燈曲調的突出特點。花燈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民間藝術,它與古代的社祭和燈節等風俗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迄今為止,云南花燈在其發展中,產生了幾次大的分化。第一次是花燈從宗教的社火活動儀式中分化出來,社火是宗教的根源,同時又是與巫術禮儀交織的歌舞活動。在過去,祈年去災是云南花燈最主要的宗教職能,沒有真正形成花燈戲劇藝術。可見花燈在以往的表演是人們消災去難、娛神的手段,但具體的花燈藝術表演,卻以其生動感人的故事情節和藝術感染力,使人們在終年勞作之余,從中得到娛樂、享受和教益。當花燈的宗教職能慢慢淡化,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火中的花燈由單純的娛神中分化出來,逐漸轉化為以娛人為主的獨立的藝術品種”⋯,這也就體現了花燈在藝術上的自覺。“審美意識走向自覺與審美意識的獨立分化互為表里,是審美意識發展史的必然趨勢。因審美意識走向自覺,即因自覺提出超越功利的獨立的審美需要進行審美活動,從而創造出自由的藝術”。如《開財門》里干哥干妹談情說愛,邊舞邊唱的“板凳抬一抬,干哥請進來,板凳梭一梭,干哥你請坐”,這時候,花燈已從“百戲”混合藝術活動中分離。因此只有花燈從這些混在一起的藝術活動中逐漸分離出來,它才逐漸具有了戲劇的藝術特性。后來,同為云南的花燈,又分為昆明一呈貢、玉溪、元謀、三姚一楚雄、彌渡、騰沖一保山、文山、師宗~羅平、紅河彝族花燈等支系。這些分化,一是分化后的花燈融入了該民族的、地區的藝術因素,因而使得花燈多姿多彩,內容豐富,本土味、地域性濃厚;二是這些分化,大都在花燈發展的早中期,在辛亥革命特別是建國后,花燈各個支系的藝術特征有逐漸趨于消失、融合之勢,體現出云南花燈戲劇藝術的成熟與定型。在歷史發展中,花燈綜合的主要對象是戲劇,在綜合中使自己從歌舞形態轉化為戲劇形態,這種轉化,往往從一個花燈歌舞節目的外圍開始,等到作為這一節目的核心部分,即唱本節目的主要調子部分,轉化為戲劇情節核心時,這一轉化才算是最后完成。傳統的云南花燈藝術包括有小唱、歌舞、戲劇及各類舞蹈、雜技、武術等多種表演形式,但在許多花燈小戲中,唱調子與戲劇情節往往混在一起。“花燈的唱腔音樂曲式具有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曲體共性,其豐富的唱腔曲調,正是因為歷史的、地域的條件使這些曲調既含有云南本土音樂文化營養的聚合再生成分,又含有明清小曲等廣闊地域的音樂文化交融的因素”[2]。其音樂結構與戲劇情節、戲曲沖突交織在一起,這便是云南花燈小戲的一個重要美學特征。20世紀20年代,辛亥革命引起了云南文化、藝術發生深刻變化,玉溪地區的花燈藝人從滇劇劇目中改編了一批劇目,并吸收了京劇、滇劇等的表演、唱腔和裝扮,最后發展成為行當齊全,形式完備的花燈戲劇,演出了描寫云南大地風光的《出門走廠》、《白扇記》等大戲,風靡一時。從此花燈跨入了另一個階段,即“新燈”,也叫“玉溪花燈”時期。實際上,這次轉化,開始于玉溪,卻完成于昆明,最后又成為市民藝術。新燈的轉化,讓花燈又新添了若干市民藝術的美學特征。
二、云南花燈的藝術特征
花燈的藝術特征有其發展形成的過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同時又有相對的變異性。花燈采取近距離的角度來觀察生活,它的思維方式和積淀于其中的戲劇概念,表現出了較為濃厚的生活氣息,正如有人所說,“花燈的根脈是燈味和戲味的結合。”“云南花燈歌舞廣泛流傳于云南漢族,及漢族與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是一種深受各族人民群眾歡迎的民問歌舞樂種,由于花燈歌舞表演內容常常帶有一定的故事情節,云南花燈歌舞又被歸入地方戲曲劇種的行列”[3,3。花燈藝術開始所關注的是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村生活和城市小市民的生活,正是這些基層的生活素材,構成了其藝術特征的堅實基礎。所以它的藝術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從花燈語言唱腔上看
由于歷史原因,云南形成了多民族雜居的局面,各地民族風情、方言、土語等產生較大差異,形成了云南花燈的許多支系,而云南花燈一般以農村生活、愛情婚姻、倫理道德為主體,鄉土氣息濃郁,形式短小,活潑,唱腔優美,很多融人“花燈”味的劇目,在唱詞、道白上都具有明顯云南方言特色。
(二)從花燈展示人物內容上看
云南花燈表現較多的是關于農村體裁和市民生活,具有樸實、粗狂的原始氣息,《霸王下山》里的霸王,《大王操兵》里的大王等,是他們少數民族英雄,是神的化身,是巫與丑的結合,他們能呼風喚雨,上天入海,除暴安良,救民于水火之中,這就使得一部分花燈戲劇表現出的人物蒙上了濃厚神秘的色彩。現代藝術家豐子愷總結農村戲曲審美問題時認為:廣大民眾對戲曲的喜愛,其趣味的中心不在于戲文的形式,而在于戲曲的內容。“戲劇沖動是人類的一種天性,戲劇活動是人類生命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戲劇是人類的一種生命行為。”天地大舞臺,戲臺小天地,在花燈和生活的關系之間,透露出一種原始的氣息,體現出云南戲劇與史詩、神話之間的傳承與創新。
(三)從花燈曲調來看
云南花燈集成了一千多首曲調,這也是云南花燈區別于其他劇種的主要標志之一。“花燈曲調雖然眾多,但常用的、實用的其實并不多,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現在的許多創作劇本,原有的許多基礎調,已不能滿足唱腔設計的需要”[。這些曲調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明清小曲,這些小曲在嘉慶、道光(1796—1850)年問已在云南開始流傳。二是來自民間的民歌小調,這類曲調,有源自云南本地,有來自省外,與云南當地語言相結合,成為云南花燈的一部分。三是從其他曲種、劇種吸收而來的曲調。如騰沖花燈《安安送米》唱的就是高腔,《小放牛》以吹腔演唱。
三、云南花燈保護與發展的再思考
具有原生態藝術和區域本土文化特色的云南花燈,從農村的田間地頭,演到城市的大雅之堂,內容豐富多彩,表演形式獨具魅力。“云南花燈及其花燈舞蹈的發生演進、相互影響、交融發展的規律與云南各族人民與中原漢族的歷史文化交往史表明:各地區、各民族的藝術審美意識形態的相生性和包容性,是構筑在類同的民族心理素質和共同信念智商的”,5]。隨著現代多種藝術的沖擊,娛樂審美的多元化,戲劇觀眾對傳統文化的冷漠等都是導致花燈消減繁盛的重要因素。以服務經濟為中心,人才老化斷層,表演技巧流失,各類專業人才匱乏,使得云南花燈劇目創作及演出舉步維艱,這些對于花燈藝術的保護與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健全保護制度,完善保護政策
總體來說,云南花燈藝術的保護可分為保護人、保護作品和保護文藝形式三個方面。而對于傳統的民族文化藝術進行保護,不僅有具體的理論指導,更須頒布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各級保護政策。
(二)建立花燈藝術學會。普及花燈藝術社團
通過這些“社團”組織研究花燈的歷史與現狀、傳統與創新,編寫云南花燈史、花燈劇團史等專著。一位從事花燈多年的老藝人說:“地方劇種的振興,需要有扛鼎之作,有領軍的名角,有固定的觀眾群。”對云南花燈收集整理,建立資源庫;對云南花燈藝術的資源進行調查,通過搜集、記錄、分類、編目、出版等方式,組織專家學者對云南花燈進行深入研究。
(三)建立人才培養資金,申請專向科研經費
加大教學資源的利用,探討民族教材、地方教材的創新與編寫,開設高等院校花燈專業。重視農村人才,培養農村觀眾,發揮文化館、文化站的基礎作用。“花燈應該還于民間,讓它在民間的土壤里面找到自己。”有人指出:花燈本是一個很俗的東西,但俗中見雅,雅俗共享,讓城市與農村連成紐帶,形成博大的文化消費市場。
(四)借助媒體,廣泛聯系
廣泛聯系各花燈專業表演團隊,共謀發展。花燈借助媒介、網絡,走上熒屏,提高知名度和美譽度,這無疑是保護與發展的一項創舉。云南省花燈劇院院長孫晉昆說:“如何突破體制機制的障礙,從年輕人抓起,在作品創新和人才培養等方面著力,讓花燈藝術抖落塵埃,重放璀璨之光,是需要認真思考的。”為適應觀眾審美情趣的變化,適應多元文化市場的競爭,適應文化體制的深入改革,花燈藝術更需有全面創新的意識:整理經典,推陳出新,加大市場營銷力度,提供“送戲下鄉”服務,形成吸引觀眾注意力的新“賣點”,形成具有上下游的文化產業鏈,云南花燈必將以其獨特的魅力,迎來美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