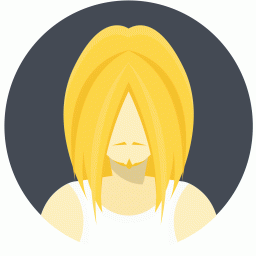國(guó)內(nèi)非制度生存探析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國(guó)內(nèi)非制度生存探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孟憲平曹小春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xué)
(1)與制度缺陷密切關(guān)聯(lián)。在好的制度和體制下,非制度化生存的活動(dòng)空間和作用機(jī)會(huì)是極少的。反之,因?yàn)橹贫鹊募s束力減弱,使一些人在行為時(shí)的規(guī)則意識(shí)減弱;因?yàn)橹贫壤砟畎l(fā)生變異,使一些人的心理減少了懼怕感;因?yàn)橹贫纫?guī)則不完善,使一些人期待著較大的非制度化空間;因?yàn)橐恍┈F(xiàn)象造成了制度損毀,又使一些人放棄制度另行一套。種種現(xiàn)象,都表明由于制度上的空檔、“空殼化”,使一些制度內(nèi)容成了擺設(shè)或墻上的風(fēng)景。制度空檔造成的制度之間的不銜接,給非制度化生存以施展能力的空間,使行為主體能夠按照自己設(shè)計(jì)的一套方案或程序達(dá)到既定目標(biāo)。制度缺陷造成的另一個(gè)負(fù)面影響是對(duì)人權(quán)的無(wú)視。人的權(quán)利,不論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政治權(quán)利還是文化權(quán)利,在經(jīng)受非制度化行為浸淫后,都會(huì)變得暗淡無(wú)光。在具體操作中,行為主體有時(shí)借助制度實(shí)施非制度化行為,有時(shí)違反制度實(shí)施非制度化行為,有時(shí)和制度若即若離貌合神離,靠心理權(quán)衡、利益取舍或貶抑他人演繹非制度化生存。經(jīng)過(guò)一系列活動(dòng),使原本不完善的制度體系再次遭受重創(chuàng),有益的內(nèi)容也被一層層剝落,留下一些干癟的條文和硬性的規(guī)定,此時(shí)的制度已經(jīng)是名存實(shí)亡了。因此,制度缺陷為非制度化行為提供了作用機(jī)會(huì),非制度化行為的盛行又使制度內(nèi)容一損再損,二者在交替中形成惡性循環(huán)。
(2)依靠利益博弈或潛規(guī)則來(lái)實(shí)施。利益博弈是非制度化生存的主要方式。對(duì)于非制度化生存主體而言,盡管它竭力想得到額外的收益,通常情況下卻不能明目張膽地公開(kāi)搶奪,其利益獲取自有一套方式。一曰依靠利益博弈,這是最常見(jiàn)的形式。博弈形式可能平靜也可能激烈,可能公開(kāi)也可能隱蔽,可能借助規(guī)則也可能逃避規(guī)則。其結(jié)果也有不同的形式,有雙贏的,有零和的,有單贏的或單輸?shù)摹6灰揽繚撘?guī)則。潛規(guī)則是制度外的規(guī)則,或者稱為不是規(guī)則的規(guī)則。潛規(guī)則是非制度化行為者的游戲方式,是行為主體為了順利實(shí)現(xiàn)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的一種心照不宣的形式。就活動(dòng)場(chǎng)所而言,潛規(guī)則可以存在于官場(chǎng)、商場(chǎng)、群體之間、階層之間;就活動(dòng)主體而言,潛規(guī)則可以由個(gè)人操縱,也可以由“單位”操縱;就活動(dòng)結(jié)果而言,潛規(guī)則可以盤(pán)活人脈,可以“絕處逢生”,可以“一本萬(wàn)利”,可以“平抑差別”,可以使欺心者得利、忠實(shí)者破財(cái),使德者受損、奸者獲益,使守法者減損資財(cái)聲名,使違法者增益不良財(cái)產(chǎn),其為禍也,不一而足。于國(guó),它有損形象;于社會(huì),它有礙和諧;于人,它侵犯權(quán)利;于己,它求得私利。非制度化生存的這種特征,存續(xù)數(shù)千年,自古及今,形式輾轉(zhuǎn),邐邐日新,危害卻未曾減弱,它總是在歷史的記憶和現(xiàn)實(shí)的表達(dá)中綿延。
(3)隨機(jī)裁量,手段各異。非制度化生存并沒(méi)有固定的范式,那些成為經(jīng)典的內(nèi)容,也只是為其它非制度化行為提供一種思路。行為主體也只是將它作為一種可以借鑒的參考材料來(lái)對(duì)待,這些經(jīng)典不像法律條文那樣具有明顯的約束力。而且,行為主體在實(shí)施非制度化行為時(shí),往往權(quán)衡周?chē)沫h(huán)境因素,比照一些參考事例做出自己的分析。因?yàn)榄h(huán)境在變,形勢(shì)在變,參與人也可能在變,相應(yīng)的行為決策和行為方式也在變。這使非制度化生存帶有明顯的隨機(jī)性,有利則行、無(wú)利則止是其基本原則。非制度化生存的手段也是隨機(jī)的,它不拘一格,形式靈活多變,不管如何,都試圖用不同的手段攻擊制度弱項(xiàng),形成各色各樣的發(fā)展?fàn)顟B(tài)。
(4)以損害國(guó)家、集體或他人權(quán)益為主要形式。非制度化生存大多是自利行為,其結(jié)果往往是損害他者利益。生活中,各種權(quán)益會(huì)牽動(dòng)行為主體的每一根神經(jīng),促使他們對(duì)處境做出不同的反應(yīng),輕者違反規(guī)則,重者藐視法律,心理上的極端性造就了行為上的極端性。結(jié)盟型的非制度化生存,往往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chǔ)之上,在共同的利益盟約下,行為主體把眼光集中在獲取利益上。由于結(jié)盟情況下,不可能在盟友那里獲得太多的利益,因此,第三方利益成了進(jìn)攻對(duì)象。對(duì)抗型的非制度化生存所涉及的利益比較復(fù)雜,一方可以從另一方獲取好處,也可以從其他方面獲得益處。還有一種多元主體參與的混合型非制度化生存,其利益獲取方式更是多樣,這種形式可以看成是上述兩種非制度化生存的復(fù)合結(jié)果。
非制度化生存的構(gòu)成要素
非制度化行為有自身的基本結(jié)構(gòu)和表現(xiàn)形式,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有所差別,但主要構(gòu)成大體上是相同的。
1.人是非制度化生存的最基本要素
馬克思認(rèn)為,人是社會(huì)活動(dòng)中首要的基本的因素。社會(huì)活動(dòng)都是人的有意識(shí)有目的的活動(dòng),離開(kāi)了人的活動(dòng),一切行為都會(huì)變得毫無(wú)意義。不過(guò),在非制度化生存中,行為人一般不是按照美的規(guī)律來(lái)建造社會(huì),而是以自己的“尺度”追名逐利。這里所說(shuō)的人,可以是單個(gè)的人,也可以是一個(gè)群體。這些個(gè)體或群體的行為都受到當(dāng)時(shí)環(huán)境的影響,又對(duì)環(huán)境發(fā)揮作用。不過(guò),在非制度化生存中,人更多地是按照功利主義行事,往往以犧牲社會(huì)利益或其它人的利益為代價(jià),表現(xiàn)出行為異化、心理異化和交往方式異化。一些人的心理中,可能只是為了顯示其“物理特性”,可能只是為了體現(xiàn)“經(jīng)濟(jì)人”的功能,可能只是為滿足低級(jí)的欲望,也可能是上述心理的匯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在非制度化生存中,缺少了人的活動(dòng),那就既沒(méi)有編導(dǎo)者,又沒(méi)有了劇中人。人將自己的意圖和欲望納入非制度化活動(dòng)之中,既為自己的利益追求去尋找場(chǎng)所和路徑,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和狀態(tài)。在這里,行為人可以顯示出非凡的“創(chuàng)造力”,卻不是為了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可以發(fā)揮“聰明才智”,卻不是為了社會(huì)的進(jìn)步;可以“創(chuàng)造財(cái)富”,卻不是與社會(huì)共享;可以“樂(lè)于助人”,卻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所有這些,都與人的利益及人的活動(dòng)掛鉤,在這一理念的引領(lǐng)下,行為人的關(guān)系就像黑格爾描述的市民社會(huì)一樣。“市民社會(huì)是個(gè)人私利的戰(zhàn)場(chǎng),是一切人反對(duì)一切人的戰(zhàn)場(chǎng),同樣,市民社會(huì)也是私人利益跟公共事務(wù)沖突的舞臺(tái),并且是它們二者共同跟國(guó)家的最高觀點(diǎn)和制度沖突的舞臺(tái)。”〔1〕309在非制度化行為主體之間,有些行為與黑格爾所描述的狀態(tài)是一致的,其利益關(guān)系就如狼與狼的關(guān)系一樣。這種關(guān)系是很少顧及人情的,“岸花飛送客,檣燕語(yǔ)留人”,大致可以描述其狀態(tài)。還有一部分人是帶著溫情脈脈的面紗的,它將親情、人情、關(guān)系、面子等融入其中,一方面顯示出對(duì)當(dāng)事人的“同情”與“眷顧”,另一方面希望表達(dá)自己的憐憫之情和惻隱之心,這使非制度化生存表現(xiàn)出溫和的一面。在人的推動(dòng)下,社會(huì)發(fā)展明顯地呈現(xiàn)兩條軌跡,一條是按照社會(huì)秩序和規(guī)范演進(jìn)的路線,體現(xiàn)了社會(huì)主體對(duì)個(gè)人利益的合理性追求,這是歷史的主流,而且隨著社會(huì)文明程度的提高會(huì)占據(jù)優(yōu)勢(shì)地位。恩格斯認(rèn)為,歷史是普遍理性的觀念發(fā)展史,是“民族的發(fā)展史”,也是群眾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進(jìn)行活動(dòng)”的歷史。另一條軌跡是按照非制度化的路徑發(fā)展形成的。這一路線已經(jīng)延伸了數(shù)千年,將人類(lèi)的利己主義傾向在社會(huì)的不同角落發(fā)揮出來(lái),形成一種“灰色文明”,其影響當(dāng)然是負(fù)面的。“在利益仍然保持著徹頭徹尾的主觀性和純粹的利己性的時(shí)候,把利益提升為人類(lèi)的紐帶,就必然會(huì)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tài),必然會(huì)使人們只管自己,彼此隔絕,使人類(lèi)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2〕663。處于這樣的狀態(tài),頹廢的不僅僅是社會(huì),還有人的心靈。“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對(duì)立的自然的、無(wú)精神內(nèi)容的要素被捧上寶座”〔3〕25。由于異化,正常行為被扭曲了,私利占據(jù)了社會(huì)活動(dòng)的大部分內(nèi)容和場(chǎng)所,那種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受到巨大沖擊。
2.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是非制度化生存的活動(dòng)場(chǎng)景
其一是社會(huì)規(guī)范。非制度化生存不是在混亂無(wú)序的社會(huì)背景中毫無(wú)阻礙地推進(jìn)的,它要受到制度的影響和約束。當(dāng)制度功能相對(duì)強(qiáng)大時(shí),非制度化生存的空間就會(huì)被壓縮;而制度影響較弱,則會(huì)給非制度化行為提供更多的作用空間。換句話說(shuō),非制度化生存總是在制度場(chǎng)景、制度平臺(tái)和制度氛圍中活動(dòng),它的效果是在制度背景下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其二是社會(huì)習(xí)俗。社會(huì)傳統(tǒng)文化是非制度化生存的又一活動(dòng)場(chǎng)景,它提供了非制度化生存的文化背景。非制度化生存必須在既有的社會(huì)心理習(xí)慣和約定俗成的慣例的影響,在長(zhǎng)期積累下來(lái)的社會(huì)道德氛圍中活動(dòng)。盡管社會(huì)道德、社會(huì)的行為習(xí)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著非制度化生存,行為主體卻不能將這些因素一概忽視,而必須在其影響下活動(dòng)。其三是人際關(guān)系。人際關(guān)系是非制度化生存的主要媒介,人際的優(yōu)劣、強(qiáng)弱、密疏,對(duì)非制度化行為的結(jié)果影響極大。一定程度上說(shuō),人際關(guān)系是非制度化生存中最微妙最不易把握的東西,是非制度化生存的最關(guān)鍵因素之一。
3.社會(huì)資源是非制度化生存的必要材料
實(shí)施非制度化生存,要么用金錢(qián)財(cái)物作為敲門(mén)磚,要么行為主體本身就擁有相應(yīng)的資源。通常情況下,空手套白狼的游戲是很少的,“免費(fèi)的午餐”只能是傳說(shuō)中的故事。正因?yàn)槿绱耍侵贫然袨橹黧w總是想方設(shè)法獲取資源上的優(yōu)勢(shì)地位,并借助這一優(yōu)勢(shì)來(lái)實(shí)現(xiàn)預(yù)期愿望。也正因?yàn)槿绱耍匈Y源的人總是想充分利用資源并把這種資源優(yōu)勢(shì)保持下去,沒(méi)有資源的則希望通過(guò)不同的方式挖掘資源來(lái)達(dá)到目的。在實(shí)際操作中,資源的類(lèi)型不同,所產(chǎn)生的影響力也不同;資源的多寡不同,其效果也不一樣。弗朗西斯•福山曾用“社會(huì)資本”解釋人的行為關(guān)系:在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和行為中,社會(huì)資本差異構(gòu)成“信任半徑”,影響著人際輻射的效果。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格倫•洛里、社會(huì)學(xué)家伊凡•萊特也都使用過(guò)“社會(huì)資本”一詞,后來(lái)社會(huì)學(xué)家詹姆斯•科爾曼和政治學(xué)家羅伯特•帕特南擴(kuò)展了這一名詞的含義。在中國(guó)社會(huì)中,“面子”和“關(guān)系”都可能成為社會(huì)資源,它們作為一種強(qiáng)勢(shì)文化符號(hào),被突出為重要的價(jià)值規(guī)范,深刻地影響著正常的社會(huì)生活。但是,在一些場(chǎng)合,操作者不會(huì)把非制度化過(guò)程想象得那么復(fù)雜,而是憑感覺(jué)、憑經(jīng)驗(yàn)來(lái)運(yùn)作。一旦有事,不是尋求制度保護(hù),不是發(fā)揮制度的維權(quán)功能,也不是訴諸相關(guān)的法律,而是先檢索有沒(méi)有熟人、有沒(méi)有關(guān)系、有沒(méi)有門(mén)路,然后“打通關(guān)節(jié)”、打點(diǎn)“各路神仙”來(lái)達(dá)到目的。
非制度化生存的現(xiàn)實(shí)悖論
1“.人情”與“法理”的悖論
非制度化生存主體的行為選擇,首先是在人情與法理之間做出權(quán)衡。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是熟人社會(huì),很多行為選擇離不開(kāi)關(guān)系背景和人情因素。按照儒家的觀點(diǎn),人的行為必須遵循儒家規(guī)范,禮儀廉恥是優(yōu)先考慮的內(nèi)容,長(zhǎng)幼尊卑是不能忘記的原則,忠孝節(jié)義是做人的基本規(guī)范,這些內(nèi)容在今天仍有積極意義。但是,當(dāng)一些人把它看成行為方式的唯一準(zhǔn)則,并作為現(xiàn)代社會(huì)行為的指導(dǎo)思想時(shí),必然與當(dāng)今社會(huì)的法理觀念形成悖論,因?yàn)楝F(xiàn)代社會(huì)中的法制理念是以法律制度來(lái)規(guī)范人的行為的。在法律語(yǔ)境中,一切人的行為方式又要放在法制天平上來(lái)衡量,一切人的利益獲取都要遵循法制原則。當(dāng)傳統(tǒng)的人情觀遭遇現(xiàn)代的法制觀時(shí),必然會(huì)產(chǎn)生觀念上的沖突和行為上的疏離。另一方面,在社會(huì)發(fā)展中,僅僅依靠嚴(yán)刑峻法實(shí)施治理也是不合適的。古代社會(huì)提倡的“衣裳之治”,現(xiàn)代社會(huì)提倡的以德治國(guó),都是與當(dāng)時(shí)制度并行的行為理念,我們現(xiàn)在講德治與法制結(jié)合也正是基于這種考慮。
2.“己”與“群”的悖論
非制度化生存中的“己”與“群”悖論,是個(gè)體利益和集體利益乃至國(guó)家利益的矛盾。單個(gè)行為主體對(duì)個(gè)人利益的追求,經(jīng)常會(huì)形成對(duì)集體的威脅,尤其是可分配的資料不足時(shí),對(duì)群體內(nèi)其它主體的生存權(quán)和發(fā)展權(quán)都是一種侵犯。而社會(huì)群體也在極力以制度化行為維護(hù)多數(shù)人的權(quán)益,在公權(quán)力的保護(hù)下形成群體與某些私利個(gè)體的矛盾。站在國(guó)家層面上看,國(guó)家要維護(hù)公民的利益,要實(shí)現(xiàn)公平、公正與和諧,必須從更高遠(yuǎn)的視角審視每一個(gè)個(gè)體和群體的行為,并以一定的方式抑制那些不法行為的泛濫和蔓延,以保護(hù)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這樣的情況下,國(guó)家公器與私人手段必然沖突,國(guó)家行為與非制度化行為必然矛盾,國(guó)家利益與某些私利必然存在悖論。
3.“私”與“公”的悖論
“私”與“公”的悖論是上一個(gè)問(wèn)題的延伸。自有集體出現(xiàn)以來(lái),財(cái)物就有了公私之分,而國(guó)家的出現(xiàn),進(jìn)一步明確了公私觀念和權(quán)利原則。朱熹曾講:“人只有一個(gè)公私,天下只有一個(gè)正邪”,“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4〕228可見(jiàn),所謂“公”,意在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秩序的合理性,當(dāng)人們用這一標(biāo)準(zhǔn)來(lái)評(píng)騭社會(huì)的具體行為、思想和言論時(shí),對(duì)伴隨著私人情感和私人話語(yǔ)的否定的是對(duì)于“私”的壓制,而私人對(duì)于公共秩序和制度的懸置,常常推動(dòng)他們?cè)O(shè)法規(guī)避社會(huì)秩序的約束,形成了“公”與“私”的悖論。非制度化生存意在改變既定的公私界限,將公有資產(chǎn)據(jù)為個(gè)人財(cái)產(chǎn),將他人財(cái)物轉(zhuǎn)歸己有,將社會(huì)利益異化為個(gè)人私利。另一方面,公共物品、公共權(quán)利和公共利益都被打上公有利益的印記,并被以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固定下來(lái),公共物品配置要按照制度原則進(jìn)行,公共權(quán)利的實(shí)踐要按照制度原則進(jìn)行,公共利益的實(shí)踐也要按照制度原則進(jìn)行。所有這些,都與私人行為之間形成一道鴻溝或籬笆,跨越鴻溝或翻越籬笆都會(huì)影響公私界限,都會(huì)在公與私之間形成糾紛,而填平鴻溝或拆除籬笆則會(huì)模糊公私界限,造成公私不分。公私關(guān)系中,一方堅(jiān)持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一方謀求部分人的利益,兩者利益的平衡點(diǎn)在哪里,是一個(gè)難題,因此二者的悖論是經(jīng)常存在的。當(dāng)屬“公”的領(lǐng)域占據(jù)主要空間,屬“私”領(lǐng)域中個(gè)人的思想難以成為共同的話語(yǔ)時(shí),公私領(lǐng)域之間的緩沖力量就消失了,柔性的活動(dòng)方式可能會(huì)轉(zhuǎn)化為剛性的制度原則,剛性的制度原則也可能轉(zhuǎn)化為柔性的活動(dòng)規(guī)則。
4.“身”與“心”的悖論
對(duì)于非制度化行為主體來(lái)說(shuō),“心”與“身”的悖論也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從心理上講,行為主體要承受各種可能的壓力。有來(lái)自精神方面的,成功的非制度化行為給人一種愉悅感,失敗的非制度化行為給人一種沮喪感;有來(lái)自經(jīng)濟(jì)方面的,財(cái)大氣粗者可以不在乎花錢(qián)多少,只要達(dá)到目的就行了,經(jīng)濟(jì)拮據(jù)者會(huì)權(quán)衡再三,不敢貿(mào)然出手;有來(lái)自道德方面的,有的人顧及良心和道德,有的人卻寡廉鮮恥。從行為來(lái)講,非制度化生存主體經(jīng)常游走于制度和非制度化的邊緣上,也承受著被制裁的風(fēng)險(xiǎn)。心理有重負(fù),身體有壓力,負(fù)罪感與疲憊感交織在一起,形成“心”與“身”的悖論。非制度化生存還造就一類(lèi)“失意者”,其思想游移,態(tài)度冷峻,言語(yǔ)憤青,在追求中抒發(fā)心中的不滿,欲得而不能,欲罷又不忍,心中壘塊難以排遣,生出許多郁結(jié)。在他們心里,“治財(cái)賦者,則目為聚斂。開(kāi)閫捍邊者,則目為粗才;讀書(shū)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視為俗吏”〔5〕43。
5“.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的悖論
非制度化生存又是權(quán)利和權(quán)力的較量。在非制度化行為主體看來(lái),“權(quán)力”力求獲利,并盡可能實(shí)現(xiàn)利益增殖;從制度視角看,權(quán)力應(yīng)該維護(hù)利益,并盡可能要求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公平公正。在社會(huì)發(fā)展中,“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的關(guān)系大致有以下?tīng)顟B(tài):(1)“權(quán)力”維護(hù)“權(quán)利”;(2)“權(quán)力”損害“權(quán)利”。兩種狀態(tài),將維權(quán)者和當(dāng)權(quán)者的心態(tài)在非制度化行為中顯示出來(lái),具有不同地位、權(quán)力、資本和資源的組織或個(gè)人,在社會(huì)舞臺(tái)上演繹出一幕幕活劇,使“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的悖論深入到社會(huì)肌體中。對(duì)于非制度化生存的悖論應(yīng)客觀看待,任何社會(huì)發(fā)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jià),不存在沒(méi)有任何代價(jià)的發(fā)展。“歷史向來(lái)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行進(jìn),文明進(jìn)步要付出道德的代價(jià)。”〔6〕5盧梭認(rèn)為,人的自然本性是向善的,但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私有制的出現(xiàn),人背離了自己的本性,在道德上會(huì)日趨墮落。這也符合一定的事實(shí),卻存在著極端傾向。康德把代價(jià)看成社會(huì)進(jìn)步的實(shí)現(xiàn)形式和動(dòng)力,他認(rèn)為,“惡是歷史進(jìn)步的動(dòng)力,是善借以實(shí)現(xiàn)的工具。但歷史的最終目的是善,發(fā)展道路是通過(guò)惡達(dá)到善”〔7〕92。馬克思恩格斯更是辯證地看待社會(huì)發(fā)展中的不良現(xiàn)象,他們?cè)诳疾熨Y本主義社會(huì)中的發(fā)展與代價(jià)的關(guān)系時(shí)指出:“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每一件事物好像都包含著自己的反面……技術(shù)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jià)換來(lái)的。隨著人類(lèi)愈益控制自然,個(gè)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xué)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wú)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8〕4。然而,面對(duì)非制度化生存的負(fù)面影響,我們不能消極回避,要積極探索應(yīng)對(duì)非制度化行為的方式方法。
非制度化生存與制度化生存的界限及可能的轉(zhuǎn)化形式
在社會(huì)發(fā)展中,制度行為和非制度化行為總是共生和互棲的。二者的邊界有時(shí)分明,有時(shí)模糊,它們?cè)诶妗⑶楦小⒌赖碌纫蛩刈饔孟滦纬闪藦?fù)雜的關(guān)系。而且,由于社會(huì)的變遷和人的認(rèn)識(shí)變化,原來(lái)的制度可能被廢除,轉(zhuǎn)化為非制度內(nèi)容;原來(lái)非制度化形式,可能會(huì)因形勢(shì)的變遷轉(zhuǎn)化為制度內(nèi)容。制度化行為與非制度化行為的邊界是經(jīng)常變動(dòng)的,沖突和調(diào)適不斷地經(jīng)常演繹著“異端思想”的蔓延與“主流領(lǐng)地”的捍衛(wèi),在邊界的清晰和模糊的變幻中顯示著制度的疏離或向心,它的存在與傳播使傳統(tǒng)的知識(shí)、思想與信仰世界的防堤越來(lái)越脆弱了。在此,我們分析以下幾點(diǎn):
第一,利益糾葛引起的邊界變化。學(xué)術(shù)界大多都贊成這樣一個(gè)觀點(diǎn),即利益沖突是人類(lèi)社會(huì)沖突的最終根源。當(dāng)社會(huì)制度在調(diào)解利益關(guān)系方面的功能減弱時(shí),便會(huì)滋生出一種替代形式,它在調(diào)解利益關(guān)系、調(diào)整利益格局中會(huì)起到另一種影響和作用,它在經(jīng)濟(jì)利益調(diào)整中以占有物質(zhì)為基礎(chǔ),在政治利益調(diào)整以保有地位為目標(biāo),在文化利益調(diào)整中以思想支配為目標(biāo)。通常情況下,在發(fā)生利益糾葛而又沒(méi)有良好的制度規(guī)范時(shí),資源配置會(huì)有利于強(qiáng)者一方,各類(lèi)利益主體的互動(dòng),使利益邊界移動(dòng),出現(xiàn)臨界現(xiàn)象或越界現(xiàn)象,使弱者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shí),不同權(quán)利主體也在力爭(zhēng)達(dá)到利益最大化,希望充分表達(dá)自己的權(quán)益。就主觀愿望講,一些權(quán)力主體也希望主動(dòng)跨越制度邊界,形成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態(tài)勢(shì),這會(huì)造成權(quán)力主體之間、公權(quán)與私權(quán)之間、實(shí)然權(quán)力與應(yīng)然權(quán)利之間的沖突。
第二,制度缺失引起的邊界變化。制度在調(diào)解社會(huì)沖突中起到降低社會(huì)交往成本、提供基本信息和實(shí)施必要監(jiān)督的作用,實(shí)際上為人的活動(dòng)設(shè)定了一個(gè)權(quán)利邊界。但是,非制度化行為往往跨越這一界限,形成一些人的特權(quán)現(xiàn)象,人為地?cái)U(kuò)大了不平等。由于制度缺失,不擇手段地爭(zhēng)奪各種權(quán)力的行為必然產(chǎn)生沖突,形成權(quán)力異化,導(dǎo)致權(quán)力腐敗的滋生和蔓延。由于制度缺失,一些行為主體會(huì)不擇手段地牟取私利,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爭(zhēng)取主動(dòng)機(jī)會(huì)。我國(guó)體制改革初期的“雙軌制”就是明顯事例,雙重模式和雙重規(guī)則的相互制約造成制度的一些功能紊亂。伴隨制度邊界的移動(dòng),社會(huì)邊界、信仰邊界、道德邊界、符號(hào)邊界、文化邊界和利益邊界亦發(fā)生變化,有的形同虛設(shè),使一些人可以“出入自由”、隨心所欲。到了這個(gè)時(shí)候,改劃內(nèi)容、調(diào)整格調(diào)已成為重振制度雄風(fēng)的必要手段了。社會(huì)主體的意識(shí)邊界是一個(gè)具有豐富層次和內(nèi)涵的“色譜”,這個(gè)邊界的擴(kuò)張或壓縮,邊界的涵化和濡化,邊界的交叉和重疊,都互相映照。它們一方面在自己的實(shí)踐中,以新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不斷突破制度界限,將制度的滯后特征暴露出來(lái),另一方面又在自身的發(fā)展中,不斷矯正制度偏差,修復(fù)制度空缺,形成新的制度體系。
第三,價(jià)值變遷引發(fā)的邊界問(wèn)題。各種社會(huì)主體在活動(dòng)過(guò)程中,存在著價(jià)值觀念的差別,由此引起不同的社會(huì)行為,這是社會(huì)的普遍現(xiàn)象。非制度化行為中,社會(huì)觀念尤其是傳統(tǒng)社會(huì)觀念會(huì)形成非正式制度,它是傳統(tǒng)自然經(jīng)濟(jì)和計(jì)劃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風(fēng)俗習(xí)慣構(gòu)成的文化體系,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下的文化行為存在著差異。表現(xiàn)為:政治理念和社會(huì)運(yùn)行規(guī)則存在矛盾,社會(huì)期望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存在矛盾,舊觀念與新思想存在矛盾。傳統(tǒng)社會(huì)中存在的迷信權(quán)威藐視法律的行為,把非制度化生存作為實(shí)施各種行動(dòng)的便利渠道,而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快餐式”特征和后果直接激勵(lì)了一些人的違規(guī)行為。一些人眼里,求助法律保護(hù)不如尋找關(guān)系有效,遵守制度規(guī)范不如實(shí)施土政策有效,依照程序辦事不如請(qǐng)客送禮有效。這樣一來(lái),思想上的共鳴造成行為方式上的互動(dòng),心理上的欲望轉(zhuǎn)化為在場(chǎng)的博弈。
第四,社會(huì)轉(zhuǎn)型帶來(lái)的邊界變化。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中,引起各種行為主體對(duì)利益格局作有利于自身的調(diào)整。這種調(diào)整有的是在國(guó)家法律法規(guī)內(nèi)進(jìn)行的,有的是在非法情況下展開(kāi)的,違規(guī)辦事與依法辦事形成了不同的行為分野。“各種社會(huì)優(yōu)勢(shì)資源過(guò)于集中在某一群體或個(gè)體身上,導(dǎo)致了社會(huì)整體結(jié)構(gòu)縱向分化嚴(yán)重,不平等性增強(qiáng),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產(chǎn)生廣泛的矛盾和沖突,成為危害社會(huì)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9〕20社會(huì)分化中,各種利益主體的“搶灘登陸”,不是我們期待的“軟著陸”,而是爭(zhēng)奪地位和生存空間的“攻城掠地”,是對(duì)制度界限的超越。
總之,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沖突與邊界移動(dòng)源于二者的差異性、變動(dòng)性、互動(dòng)性和開(kāi)放性。差異性導(dǎo)致不同行為主體在結(jié)合或摩擦?xí)r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在邊界處以一定的方式控制著能量的釋放流動(dòng)〔10〕,這給解決制度沖突提供了一個(gè)線索。變動(dòng)性為主體跨越邊界提供了機(jī)會(huì),“由于邊界可能不斷地發(fā)生變化,穿越邊界往往終究不完全是某個(gè)個(gè)體的事情。因此,當(dāng)某個(gè)沖突主體跨越某種社會(huì)分界線時(shí),邊界沖突將會(huì)產(chǎn)生,新的集團(tuán)便會(huì)形成,并且由此明確他們之共有某種與眾不同的性質(zhì)。”〔9〕66互動(dòng)性影響著行為關(guān)系中的透明度、參與度等,給邊界沖突注入豐富多彩的實(shí)踐內(nèi)容,在主體推動(dòng)下形成不同的演化和組合。開(kāi)放性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基本取向,建立一個(gè)合理開(kāi)放的反饋機(jī)制,使社會(huì)主體活動(dòng)保持良性動(dòng)態(tài)和能量交換,乃是對(duì)邊界沖突的良性反應(yīng)。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國(guó)內(nèi)博士論文 國(guó)內(nèi)形勢(shì)論文 國(guó)內(nèi)科技論文 國(guó)內(nèi)投資論文 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發(fā)展 紀(jì)律教育問(wèn)題 新時(shí)代教育價(jià)值觀
- 國(guó)內(nèi)NGO
- 國(guó)內(nèi)社會(huì)貧富狀況
- 國(guó)內(nèi)公債史
- 國(guó)內(nèi)翻譯界
- 國(guó)內(nèi)公債史
- 國(guó)內(nèi)公債史
- 國(guó)內(nèi)公債史
- 國(guó)內(nèi)旅游業(yè)
- 國(guó)內(nèi)利用外資
- 國(guó)內(nèi)證券
熱門(mén)文章排行
相關(guān)期刊
- 國(guó)內(nèi)外招投標(biāo)現(xiàn)狀分析
- 國(guó)內(nèi)外園林景觀研究現(xiàn)狀
- 國(guó)內(nèi)旅游線路設(shè)計(jì)方案
- 國(guó)內(nèi)對(duì)財(cái)務(wù)風(fēng)險(xiǎn)的研究
- 國(guó)內(nèi)外音樂(lè)教育的現(xiàn)狀
- 國(guó)內(nèi)外工程造價(jià)研究
- 國(guó)內(nèi)金融市場(chǎng)現(xiàn)狀分析
- 國(guó)內(nèi)網(wǎng)絡(luò)營(yíng)銷(xiāo)現(xiàn)狀分析
- 國(guó)內(nèi)內(nèi)部控制研究現(xiàn)狀
- 國(guó)內(nèi)外稅收籌劃研究現(xiàn)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