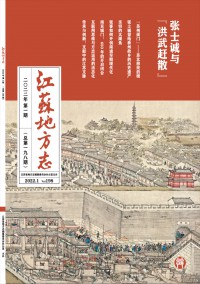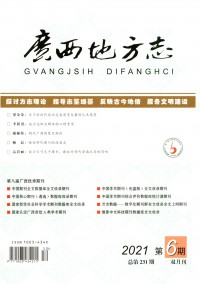方志學與歷史學的關系及相互影響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方志學與歷史學的關系及相互影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目前,被各家稱之為方志起源之書的還有許多,如有人列舉了前述之魯《春秋》、晉《乘》、楚《梼杌》,以及宋、齊、周的《春秋》、《周志》、《鄭志》等;有人列舉了《山海經》、《禹頁》、《越絕書》、《南陽風俗傳》、《華陽國志》等。雖然這些古代典籍與后世之志書有很大的區別,但還是被學界認為是志書的起源。這些古代圖籍大都為成書較早的諸侯國或郡國史書,即使地理書性質較為突出的《山海經》與《禹貢》,其記史性質也是不可否認的。所以,北宋著名志家李宗諤說:“地志起于史官,郡記出于風土”,主張修志應該“舉春秋筆削之規,遵史官廣備之法”[5]。目前學界關于方志的起源有多種說法,有主張“志源于史”,有主張“志源于地”,有主張“亦史亦地”,有的甚至認為中國志書起源于甲骨文[6]。其實,上述所有列舉為方志起源之書的典籍與后世正式定型的方志之書相比,都只是具備了某一個方面的因素,正是在長期不斷借鑒融合的過程中,才最終形成了后世有完整體例和固定記載內容的志書。因此,志書并非起源于哪一類古籍,更不是起源于哪一種古籍。這與史書的起源一樣,我們只能說某一史籍是現在最早的史書,而不能認定史書就是起源于哪一部史書。上述古籍既是志書的源頭,也是史書的源頭,正是這些古籍匯成了志書和史書共同發展的歷史長河。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志書更多的起源于記載地域、地理與諸侯郡國歷史的史書,而史書包括的范圍更廣。到了近代,志書從這一志、史同源的長河中分流出來,形成了具有獨立地位的方志學。由此可以看出,志書與史書是同源的。正如章學誠所言,“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7]。
一、從方志的發展看:志、史相伴而行
一般來說,志書經歷了全國性區域志、地理志、圖經、地方志的發展階段。按其發展的成熟程度而言,大致分為漢唐魏晉南北朝的形成與初步發展時期、隋唐宋元的完善與成熟時期、明清的全盛與方志學形成時期[2]。如果把民國后方志學的發展也包括在內,則有民國與新中國成立后方志與方志學的現代形態轉型,并獲得大發展的時期①①。在方志學形成獨立學科前,方志的發展與史學的發展是并行的,有時甚至是合一的。嚴格來說,被稱為志書淵源的各種先秦古籍其實都只是在某個方面具有后世志書的因素。真正形成約定俗成的體例,并且有廣泛記載內容的志書是在漢以后。班固《漢書•地理志》從方志的角度來說是一部以當時行政區劃為綱的全國區域志,從史書的角度來說,首創后世歷代正史地理志體例,“為各朝代匯纂圖經總集、地理總志創立了模式”[8]。西晉摯虞作《畿服經》,該書除敘述地理風俗外,還增添“先賢舊好”等人物事跡,開創了方志記載人物事跡的先例,從而突出了記史的屬性,為歷代方志學家盛贊。我國最早以志名書者為西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該書集歷史、地理、人物于一編,從而具備了方志的雛形,被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而這些公認的方志古籍同時又是非常著名的史學名著。隋唐宋元時期,地方志經歷了圖經到方志的階段。唐宋元中央政府都制定了較為完整的圖經定期編呈制度,并出現了許多重要的圖志、圖經和方志,如唐李吉甫纂著的《元和郡縣圖志》、宋李宗諤等編纂《祥符州縣圖經》,元札馬剌丁等主持編撰的《元一統志》等。從體例上看,唐代形成了圖、志兼括之體,《元和郡縣圖志》是其開創之作,宋《祥符州縣圖經》繼承此體;到南宋,志書體例已有平列門目體、綱目體和史志體三種類型,完成了古代圖、志、籍的融合。從內容上來看,這一時期志書都從偏重地理記載轉向人物、政事的記錄。這一時期的方志作者大都將方志納入史書行列,認為“史志同義”。元代張鉉在主修《至正金陵新志》以志擬史,他對該志各部分的作用進行了如下表述:“首為圖表,以著山川郡邑,形勢所存;次述通紀,以見歷代因革,古今大要;中為表志譜傳,所以極天人之際,究典章文物之歸;終以摭遺論辨,所以綜言行得失之微,備一書之旨。”他將司馬遷著《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引為撰志宗旨,并一反修志“隱惡揚善”的傳統,提出志書應實錄“是非善惡”,尤其是人物志,要“巨細兼該,善惡畢著”[9],這也是把史家“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筆風運用到修志實踐中,將方志修為信史的一種嘗試。由此可見方志書與史學之關系。明清時期是中國方志發展的全盛時期,也正是在這一階段的后期,形成了具有獨立地位的方志學。然而即使是已經獨立發展的方志學,其與史學的聯系也是極為緊密的。這突出表現在中國傳統方志學的開創者之一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中。章學誠在其重要的史學與方志學理論著作《文史通義》中論述了志書的性質、編修原則與方法。他認為,“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文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7]因此,他認為志書就是“一國之史”,即古代“列國史官之遺”。據此,他主張修志應該遵循史家修史的原則與方法,即要有“史家法度”。從他論述的修志原則與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實際上就是認為修志即為修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方志學與史學的緊密關系。
二、從方志學的轉型看:志、史互相促進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期,隨著西方進化論思想傳入我國,傳統史學與傳統方志學都遭到了猛烈的沖擊,因而發生了史學與方志學由傳統形態向近代形態轉化的現象。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方志學與史學互相促進,從而形成了近代方志學與近代史學。為進化論在中國傳播作出重大貢獻的梁啟超于1902年寫了《新史學》一文,最早提出了“史學革命”的口號。他將進化論理論來改造中國的舊史學,提出了“民史觀”,主張重視下層民眾在史書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后,他撰寫了一系列方志理論著作,主要有《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1924年)、《說方志》(1924年)及《龍游縣志序》(1925年)。他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中將“史學”、“方志學”、“地理學”并列,最早提出了“方志學”這一概念。他在《龍游縣志序》一文中借評價《龍游縣志》的優長,對傳統方志學理論進行了總結,并在方志學理論領域進一步闡發了他的“民史觀”。他對舊志書中“一般民庶,概付闕如”表示不滿,而極力贊賞《龍游縣志》“根據私譜,熟察其移徙變遷消長之跡,而推求其影響于文化之優劣,人才之盛衰,風俗之良窳,生計之榮悴者何如。……其功用則抉社會學之秘奧,于世運之升降隆污,直探本源”。同時,他又論述了“志”與“史”的關系:“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開物成務之業有所憑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獻之寄而已,民之榮瘁、國之污隆,于茲系焉。”[10]然而,梁啟超基本上是在“新史學”的范圍內,“從史的角度對方志學進行探討”[11]。雖然其理論對于方志學的近代轉型有著重要的影響,但他本人似乎并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這種方志學近代轉型的趨勢。
較早地認識到方志學近代轉型的趨勢,并正確地指出這一趨勢的是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方志學家傅振倫先生。他在1928年寫的《修志芻議》中指出了這一趨勢:“今則新史學出而志亦當與之俱變其體例矣”,“志猶史也,近世且有科學化之趨向矣。則今之修志,其必以社會體相之‘志’為重心也審矣”,“書之作也,必應乎潮流。則方志之修訂,不宜專詳沿革與地輿矣。即雖不能完全與新史學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12]1935年他在其出版的《中國方志學通論》一書中對修志工作不注意新史學潮流,不符合新史學體例的現象進行了批評:“近人即昧于先哲志乘精義,又不講求新史因素,操觚修志,每斤斤于文字之雕飾,抹煞事實,或廣錄載籍,忽略現代,自以為工,實深乖史體,余則極力矯成之。”[13]與傅振倫先生一樣,李泰棻先生也是在進化論的影響下,在“新史學”思潮的推動下致力于方志學的現代轉型。他認為:“一切現象,不外二種。一曰循環狀,一曰進化狀。……學之屬于循環狀者,謂之天然學;學之屬于進化狀者,謂之史學。故史者,研究進化之現象也。”既然“史乃記載及研究人類進化現象者,然則方志亦必為記載及研究一方人類進化現象者無疑。”[14]在此基礎上,他對方志學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如他在《方志學》一書中,專列“應增社會經濟之資料”一節,強調“社會經濟,在今日應為全志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商工各業,經過先民若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應將以上各事,追述經過。至少亦須將現代社會經濟,全部編入。”[14]其他如黃炎培、黎錦熙、顧頡剛、于乃仁等都主張在地方志中“擴充社會及經濟史料”,以適應進化論對史學提出的新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方志學的發展實際上是“緊緊跟隨‘新史學’而反思、揚棄傳統方志觀,以求與中國歷史學同步向現代轉型”[15]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一些方志學家已經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并試圖用這一科學理論指導地方志的編修。如傅振倫先生在1930年寫的《編輯北平志蠡測》中指出:“居今修志,應加改革。宜除道德之空談,側重于物質方面。自馬克思唯物史觀表揚于世以來,而‘社會嬗變(社會之嬗變,即人類之歷史),恒視經濟之變更為轉移’之理大明。故欲闡明事理,須求當代經濟狀況。今后必加強于地理之自然資源、人文地理以及擴充舊日史志食貨門類目,誠當今日修志之要義矣。”又說:“自唯物史觀之說興,歷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則解釋之,而史學遂成專門之學。唯歷史之科學化也,則必:第一,須為實錄;第二,須注意進化方面;第三,須作真理規律之探求。此外又須兼重科學之記錄。”因此,志書中各種專志,“凡獨立成為專門之學者,亦應敘其源流,詳其嬗變之理”[16]。這說明,隨著新史學思潮的興起,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其理論也對方志學產生了積極影響。這一動向預示著方志學現代轉型的一種更加光明的未來。當然,方志學的轉型及其發展對史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主要表現在方志學的近代轉型推動了民國地方志的大量編修,從而為史書的編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料。當時的方志學家大都認識到“方志為國史資料所出”,因而搜集地方資料非常廣泛細致,“以為國史約取余地”[17]。特別是轉型后的方志大量記載和收錄了地方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這些都為史學研究提供了難得的資料。民國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很多都利益于地方志中的資料,如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國史研究,他在民國時期就出版了《太平天國史叢考》、《洪秀全金田起義前年譜》、《太平天國金石錄》、《太平天國史考證》、《太平天國廣西首義志》等,還出版了稱為兵志系列的《綠營兵志》、《湘軍新志》、《晚清兵志》三種。這些研究成果中就引用了大量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地方志資料。民國地方志還記載了各地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大量史實。如廣西《桂平縣志》記載的太平天國運動史料、河北《固安縣志》、《琢州志》、《霸縣志》記載的義和團史料、《黑龍江志稿》和《璦琿縣志》記載的沙俄入侵黑龍江以及邊疆軍民反侵略斗爭的資料。這些都為史學工作者研究這些歷史事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建國后,在整理地方志基礎上編纂出版了許多地方志專題資料,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
三、結語
綜上所述,從方志的起源和發展演變來考察方志學與史學的關系,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傳統方志是多源的,但其中與傳統史學的關系尤為密切。傳統志書與史書同源而分流,長期共同發展;到清代,方志學開始形成,并出現獨立發展的趨向;到民國則開始向現代方志學轉化,最終成為與史學并列的一個重要的獨立學科。然而,當代方志學與歷史學的聯系還是非常緊密而廣泛的。考察方志學與歷史學的聯系及相互影響,研究在新的條件下兩者更緊密結合的途徑,應該是地方志工作者和史學工作者的共同任務。
作者:彭平一單位:中南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