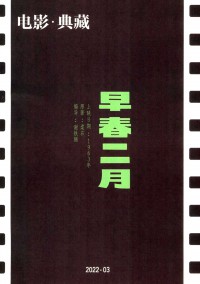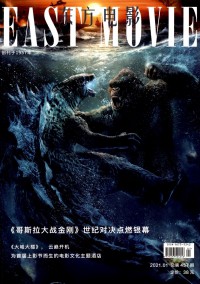電影政法文化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電影政法文化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以《上海二十四小時》為例1933年,夏衍與明星影片公司導演程步高合作,攝制了第一部左翼電影《狂流》,后聯華、藝華、天一等制片公司在同一年,相繼攝制了《三個摩登女性》、《都會的早晨》、《城市之夜》、《母性之光》、《上海二十四小時》、《女性的吶喊》、《春蠶》、《豐年》、《小玩意》、《大路》、《姊妹花》、《鐵板紅淚錄》、《掙扎》、《神女》、《鹽潮》、《脂粉市場》、《民族生存》、《中國海的怒潮》、《惡鄰》等三十余部影片,1933年由此被稱為“左翼電影年”。1934-1935年,當局對左翼電影運動壓制加劇,秘密電影小組通過個人聯系方式,向公司或導演提供劇本,并成立電通影片公司。兩年中,《同仇》、《漁光曲》、《女兒經》、《鄉愁》、《船家女》、《劫后桃花》、《黃金時代》、《逃亡》、《生之哀歌》、《人之初》、《桃李劫》、《風云兒女》、《自由神》、《都市風光》等近三十部優秀影片誕生。筆者選取影片《上海二十四小時》為例,分析左翼電影作品中的法律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特點:
(一)社會底層群眾所處的法律地位
非為被法律保護的“人”影片《上海二十四小時》描繪了30年代上海的一天,通過童工受傷事件將資產階級與社會底層兩個階層聯系起來,并使用蒙太奇對比手法鮮明刻畫了兩個階層截然不同的生活。故事發生在下午四時,資本家周買辦在雇傭的童工受傷后,對其置之不理,拒絕提供醫藥費等補償。童工的姐姐只知哭泣,哥哥陳大前往周公館告貸,卻空手而回,童工的傷情漸漸惡化,一家人悲憤之余也無可奈何。此時周買辦正瞞著太太和舞女玩樂,而買辦太太也在和男友狎游。午夜,為救童工性命,失業青年老趙生平第一次到周公館行竊。買辦太太倦游回家發現遇竊,立刻報警。兩小時后,陳大因被指控偷盜而入獄,老趙則拿著竊取的錢包為童工四處奔走。老趙得知陳大被抓后,隨即到警察局投案自首。當陳大被釋放回到家時,他的弟弟已經斷氣。時針再次走到下午四時,買辦太太睡醒起床,如往日一樣開始盤算如何消磨即將到來的夜晚。影片截取的時間維度僅二十四個小時,在對比的視角下卻反映出許多問題,最突出的便是群眾過于淡薄的法律意識。童工受傷事件本屬民事法律調整的范圍,然而無論是童工和其哥哥姐姐、老趙還是周買辦,無一人尋求法律解決的方法。童工奄奄一息,姐姐只知哭泣,哥哥不尋求周買辦的補償,反而去周公館告貸,空手而回后,無計可施,只能頂著大雨去賣菜,卻是杯水車薪;周買辦為維護自己的資產利益,對童工的生命置之不理,周買辦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違法行為,自然也不會想到通過法律解決;老趙出于善意甚至走上違法之路,這個違法的英雄同樣未曾思考過如何通過法律解決問題,群眾法律意識的欠缺可見一斑。而探究導致群眾法律意識如此淡薄的原因,正是30年代具有反動性的法律。當時的法律非將社會底層群眾所處的法律地位認定被法律保護的“人”,而將其界定為法律的受害者。在非把底層群眾當人的法律文化之下,底層群眾在法律上不懂什么是無辜受害的法理,也無可尋求救濟的法律,更沒有依法保護自己的權益的法律意識,當然不可能主張在法律體制下解決問題。而以周買辦為代表的剝削階級,因法律本身是其專政的工具,而非限制其權力的手段,當法律對其有利時便選擇遵守法律,當法律對其不利時便選擇棄置法律,其本質上并無法律意識可言。影片同其他的左翼電影一樣,將底層的不公之事訴諸于眾,引發社會大眾的共鳴,《上海二十四小時》中的不公平事件在對比手法的作用下尤為凸顯。在30年代的法律體系下,周買辦雇傭未成年兒童、在童工受傷后拒絕提供醫療費這樣的事件盡管需受到道德的譴責,但卻是合法的;而老趙行偷竊之事,雖是片中善的象征,卻要受刑法的處罰;陳大僅因去周公館告貸未成,便被認為存在偷盜的動機而鋃鐺入獄。為何合法之事讓人覺得如此不公?原因在于當時的法律本身便是不公的,這種不公不僅體現在法律的制定之上,如僅規定盜竊應當受到處罰,卻沒有依據實際情形規定減輕處罰的情形,導致老趙不能得到合適的量刑,再如存在《兒童保護法》、《勞動保障法》等對弱勢貧民的法律救濟規定之空白,導致周買辦“見死不救”的行為被判定為合法的現象;同時也體現在法律的執行上,如司法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僅憑周買辦的一面之詞,草率認定陳大有罪,短短“兩小時”就使一自由之人身陷囹圄。而左翼電影正是通過突出這些不合理的現象達到批判法律不公,社會制度、階級差別不合理的目的。
(二)濃重的道德色彩大于法律上的理性啟示意義
蒙太奇對比手法貫穿影片的始終,無業游民老趙的轉變無疑使得周買辦的“喪心病狂”再次加深,《上海二十四小時》中,為替童工治病,老趙平生第一次行竊,得知陳大被冤入獄,老趙主動投案自首,影片將老趙塑造成為悲劇式的英雄,引得觀眾無限的同情。按照歷代法律,偷盜都是觸犯法律的犯罪行為,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老趙的舉動卻被社會大眾贊美,這不僅是出于藝術處理的需要,也為契合于左翼電影所表達的政治理念。在文學藝術的感染力之下,法律與道德、法律與人情的矛盾沖突深刻展開,影片在揭露窮人的生存困境和法律的不公時,揭示了社會的不公和罪惡,在善惡的強烈對比中,激發人們對不合理社會的反思和批判,從而達到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的政治目的。中國涉法作品歷史悠久,習慣上將其稱為公案戲劇、公案小說,傳統的涉法作品通常強調標榜個案或個人彰顯公理,較少闡述對案件中涉及的法理法意的含義,最多只是講述一些道德與法律之間的關系。《上海二十四小時》傳承了傳統涉法作品的特點,老趙這一形象的設置,其道德的訓戒色彩遠遠大于法律上的理性啟示意義。老趙的悲慘遭遇展示了道德與法律的矛盾,影片引導社會大眾棄法律而偏向道德,對當政者對制定法的信仰又是一大貶斥。而左翼電影的其他作品中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如影片《神女》中阮玲玉所扮演角色,集兩個沖突的身份———妓女與母親于一體,在受到無數偏見不公對待后,女主角因無奈殺人被判處十二年徒刑,這一情節的安排博得觀眾的無數嘆息,影片中同樣毫無法理的闡述,在道德與法律的沖突之間,毫不猶豫地將天平偏向道德。左翼電影僅揭示社會不公的表面,卻沒有闡釋法理法意,沒有解釋不公背后所存在的法律缺陷,反而著眼于道德的訓戒,這正是凸顯了作者對國民黨的法律持根本的不屑和批判態度———因為國民黨虛偽的法律僅為統治者服務,而非弱者伸張權利的依靠,才與公理相左,造就社會種種的不公。總而言之,盡管國民政府以司法獨立、民主政治為目標,但是20世紀30年代左翼電影中體現出的法律仍為專制人治時代的法律,法律思想呈現明顯的政治化趨勢,深入到社會大眾潛意識的古典正義觀,仍然占據社會群體的大腦。
二、左翼電影背后的博弈———政治與法律評判作品
往往是從作品本身出發,是否應當關注作品背后作者的主觀創作動機?筆者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在研究左翼電影時期的政法文化時,不僅應研究法律的實然性,同時也應該研究法律的應然性,即研究法律變革的方向。左翼電影自誕生以來,便受到國民黨政權的監督和控制,可以說左翼電影的歷史便是圍繞左翼電影創作者與審查者展開的,要全面掌握左翼電影所體現的政法文化,也應解析影片創作者與審查者背后各自的主張。左翼電影工作者高舉批判現實主義的旗幟,主張暴露帝國主義的侵略,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剝削以及國民黨政權的壓迫,描寫工農群眾的反抗斗爭并指出知識分子的出路。左翼電影表現為強烈的政治性,與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主張法律層面的改良不同,左翼電影工作者主張通過政治行動或革命行動來打破原有的秩序,通過否定國民黨的法律達到否定其統治的目的,因此在影片中對不公現實進行描述的同時對法律體系產生了根本性的質疑,因此,作者將《上海二十四小時》中的警察塑造成反面人物,而非公義的象征。而在1933年天一影片公司拍攝的《孽海雙鴦》中,富翁劉彥文因萬貫家財招來旁人嫉妒,致使骨肉分離十幾年而頓悟,大辦公益事業,影片原意通過資本家劉彥文的經歷達到警示剝削階級、打倒遺產制度的目的,左翼電影評論刊物《每天電影》對該影片做出批判,認為這仍然是維護當時遺產法律制度的象征,標榜“打倒遺產制度”,而實際在推行“遺產應有合法的繼承人,不容旁人凱覷”的正統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評論者認為影片情節開展的前提便是承認遺產制度的合法性,覬覦財產的人正是因為侵犯法律賦予劉彥文的財產權利,才遭受懲罰,影片以推翻國民黨的遺產制度為目的,但片中隱含的前提卻是維護當時的遺產制度,自相矛盾。由此可見,左翼電影工作者不僅在創作層面以否定國民黨的法律為主旨,而且在此基礎上通過評論等方式對創作的電影進行反思修正。而國民黨政府為鞏固政權,對左翼電影進行審核,對生產左翼電影的公司進行整改,1933年11月“藝華”被搗毀,1934年更成立了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重審許多已經過了審的左翼電影。夏衍編劇、趙丹主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時》,回爐后被剪一千多尺膠片,雖獲準上映,但已支離破碎不知所云。“劇本審查委員會”和“電影檢查委員會”的運作,對左翼電影劇本的創作,電影的拍攝、放映進行限制,從而控制了左翼電影的傳播。在左翼電影創作者與審查者的博弈中,電影無疑成為了兩者訴諸政治主張的媒介,從側面而論,此時的法律與藝術均受到了政治的影響,法律政治化顯而易見,國民黨政府為限制左翼文人的革命主張,將電檢法律制度異化為“對付左翼電影、迫害左翼影人”的工具,而左翼電影工作者通過否定國民黨不公的法律達到推翻其統治的目的,因此,從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訴求高于法律的角度和左翼電影工作者的主張而言,30年代整體為重政治輕法律的“非”法環境。
三、對現代法治的關照解讀
左翼電影中的政法文化,不僅可以了解左翼電影隱藏的社會觀、法律觀和道德觀,更容易看出現代法治的缺失,反過來促進現代法治的發展。正如前文所述,左翼電影中所反映的法律非為保護社會底層群眾的法律,而是維護國民黨統治的工具,底層群眾為反動性法律的受害者,不公正的法律被政治主張所驅使,與公理道德相沖突。在法律與道德的沖突時,為否定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左翼電影創作者正確地把握了民眾審美情趣和電影藝術的特質,通過對不公事件的描述激發社會大眾潛意識中的古典正義觀,引導群眾棄政治化的法律而偏向于道德,從而否定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左翼電影運動之后,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文化領導權,左翼電影是第一次將電影與政治結合起來的有益實踐,其所建立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應當繼承和發揚,但同時也要看到左翼運動極左傾向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如左翼電影評論工作者對中國20年代的電影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顯然犯了“潑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的錯誤,這是一種偏激的歷史觀。在左翼電影中,以批判國民黨專政為目的,左翼工作者對國民政府的一切法律予以抨擊,然而非所有的法律條文都是不公正的,如《孽海雙鴦》中,因資產階級的財產是剝削勞動人民的結果,因此創作者對片中所體現的遺產制度予以批評,但如將影片中的遺產制度與現行的《繼承法》相比較,在具體條文內容上兩者并不存在很大的區別。不可否認的是,左翼電影創作者和評論者的做法具有歷史合理性,也只有通過革命的方式左翼文人才能實現其政治理想,但在階級矛盾非為主要矛盾的當代社會,強調法律的重要性,選擇依法治國的方式才應是當下正確的選擇。在左翼電影創作者與審查者的博弈中,國民黨為控制左翼電影所傳播的政治主張,維護自己的政權,而啟用了法律武器,然而由于審查者濫用司法權力,許多左翼電影工作者被無辜迫害,國民政府最終走向滅亡。從反面而論,國民政府最終腐敗的原因正是以專制人治為主而忽略法律的重要性、濫用法律,法治的必要性由此可見。
20世紀30年代左翼電影中,古典正義觀被社會大眾所普遍認可,而在法治的現代,部分古典正義觀仍被群眾所認同,如包公至今仍然是人民心中理想的裁判官形象。筆者認為,社會大眾之所以仍然對古典正義觀持肯定態度,是因為了解其優勢所在,但社會大眾卻忽略其缺點或潛在的危險。毋庸置疑,包公的確辦理了許多彰顯正義的案件,然而如包公一樣既掌握司法知識又有強烈的職業道德的司法官畢竟為少數,一個包公并不能解決宋朝所有的案件,且個人的價值觀并不能完全趨于一致,為保證公平,相同案件獲得相同裁決,仍需采用“依法治國”的方式。今天,盡管司法仍然存在不足,但以這些不足為由而全盤主張依法治國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過去的經驗教訓始終在提醒我們,專制人治、將法律政治化最終會滋生腐敗,導致政權的傾覆,且中國的司法總體呈現出良好的發展趨勢,對于司法中存在的不足,司法工作人員可以通過司法改革、完善法律予以解決,但“依法治國”的大前提始終不應動搖。
作者:高瑛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