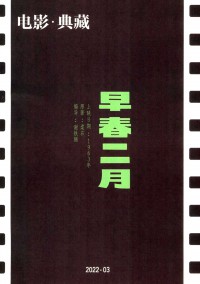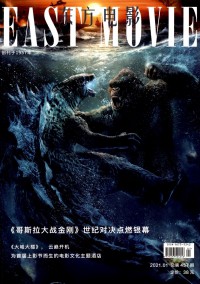電影名著改編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電影名著改編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都是名著惹的禍
隨著電視劇《我這一輩子》的播出,人們對(duì)改編的批評(píng)意見很快就在媒體上反映出來(lái)。《北京青年報(bào)》率先發(fā)表文章,認(rèn)為這部電視劇“頂多半個(gè)老舍”;《京華時(shí)報(bào)》也發(fā)表署名文章,批評(píng)該劇“不過(guò)打著老舍的幌子”。一系列批評(píng)意見中,老舍之子舒乙的意見最有代表性。最初,他并沒有直接批評(píng)《我這一輩子》,只是說(shuō),在所有根據(jù)老舍作品改編的電視劇中最令人滿意的是《四世同堂》,其次是《離婚》,因?yàn)椤端氖劳谩方^對(duì)忠實(shí)原著。實(shí)際上,他在這里已經(jīng)暗示了對(duì)《我這一輩子》的不滿,其原因顯然是《我這一輩子》沒有忠實(shí)于原著。前不久,他到北京廣播學(xué)院做了將近兩個(gè)小時(shí)的演講,當(dāng)時(shí)有學(xué)生問(wèn)他,如何評(píng)價(jià)電視劇《我這一輩子》,他承認(rèn),自己“非常地不欣賞”這種脫離原著的改編。報(bào)道還說(shuō),舒乙一再?gòu)?qiáng)調(diào),改編經(jīng)典小說(shuō)要特別小心,藝術(shù)形式可以改,但“必須非常忠實(shí)于原著”。
《橘子紅了》也使得有些人大為不滿,因?yàn)檫@也是一部只有4萬(wàn)字的自述式的作品,要把它拉長(zhǎng)到25集,改編者需要增加許多東西,不可能完全忠實(shí)原著,甚至完全不能忠實(shí)原著。按照忠實(shí)論者的邏輯,不忠實(shí)原著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在這方面,《橘子紅了》受到了太多的指摘,比較多的意見是,說(shuō)它“用品位來(lái)掩蓋故事的蒼白,創(chuàng)作者的無(wú)力”。一位觀眾寫道:“電視劇首先需要一個(gè)扎實(shí)的劇本,《橘子紅了》明顯在試圖抻長(zhǎng)一個(gè)故事,又不去借助情節(jié)發(fā)展,而一味沉溺于所謂人物刻畫——就跟《橘子紅了》真的揭示了什么深刻人性似的。”還有觀眾指出:“看來(lái)看去,這實(shí)在是一個(gè)十分牽強(qiáng)的故事。所有的人物都是從概念出發(fā),因而他們的性格邏輯格外生硬……一個(gè)完全建設(shè)在假定性上的故事,情節(jié)進(jìn)展又緩慢到讓人無(wú)法忍受,就那么一點(diǎn)兒事,翻來(lái)覆去,繞來(lái)繞去,配上古怪的音樂(lè),真叫人昏昏欲睡。”這樣的意見很多,都是說(shuō)改編者對(duì)劇作的處理不能盡如人意。
同樣的麻煩還發(fā)生在李少紅把《雷雨》改編成電視劇的時(shí)候。在這里,李少紅大膽地、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周氏家族悲劇命運(yùn)的全部歷史。電視劇突破了舞臺(tái)劇的時(shí)空局限,給劇中人物重新搭建了一座上演歷史活劇的舞臺(tái)。但是,不喜歡電視劇的人還是發(fā)現(xiàn)了它的問(wèn)題,因?yàn)椋筒茇壬脑拇_太不一樣了。有人說(shuō),電視劇把曹禺先生的名著粗俗化了,成了不倫不類的東西。《北京晚報(bào)》曾召開座談會(huì)專門討論這個(gè)問(wèn)題,會(huì)上有些觀眾開誠(chéng)布公地表達(dá)了他們對(duì)電視劇的不滿,他們希望看到一個(gè)符合自己想象的、完全忠實(shí)原著的作品。而李少紅的《雷雨》真的使他們非常失望。
其實(shí),任何一部根據(jù)名著改編的作品,要避免觀眾拿原作和新作做比較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實(shí)上,很多改編者都遭遇過(guò)“不忠實(shí)原著”的指責(zé)。最近的一個(gè)例子是人藝導(dǎo)演李六乙對(duì)昆曲《偶人記》的改編,這臺(tái)小劇場(chǎng)戲曲剛一上演,就有人批評(píng)他改糟了,說(shuō)他純粹是在糟蹋東西。這種批評(píng)對(duì)李六乙來(lái)說(shuō)絕不是頭一次,就在2000年,在北京人藝舉辦的紀(jì)念曹禺的系列活動(dòng)中,李六乙執(zhí)導(dǎo)的《原野》被認(rèn)為完全背離了原著的精神,從而受到了遠(yuǎn)比這一次嚴(yán)厲得多、激烈得多的批評(píng)。有人當(dāng)即指出,無(wú)法讓經(jīng)典重現(xiàn)舞臺(tái),那是我們?cè)谀芰ι系娜毕荩且环N并不值得夸耀的缺陷。我們本該更加努力,通過(guò)加倍的工作使作品盡可能地逼近經(jīng)典,而不應(yīng)該以對(duì)經(jīng)典不負(fù)責(zé)任的改編,作為藏拙和偷懶的借口;沒有天分或者沒有通過(guò)刻苦訓(xùn)練,掌握前輩藝術(shù)家的表現(xiàn)手段,更不能以所謂創(chuàng)新來(lái)掩飾自己的不足與無(wú)能。在人藝自己組織召開的座談會(huì)上,多數(shù)專家都婉轉(zhuǎn)地表達(dá)了自己對(duì)《原野》改編本的不滿。有人說(shuō),戲中人物從馬桶里拿出可樂(lè),這讓我看不懂。我破解不了其中的意思,一點(diǎn)也產(chǎn)生不了共鳴。有人稱之為“解構(gòu)主義的東西”,從情節(jié)到主旨,導(dǎo)演把原作完全“解構(gòu)”了。
改編的不大容易討好,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永遠(yuǎn)有一本名著高高懸掛在我們的頭頂上。在那些捍衛(wèi)傳統(tǒng)的人看來(lái),經(jīng)典名著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不容質(zhì)疑的,改編者只能按照經(jīng)典名著已有的模樣,一絲不茍地把它呈現(xiàn)在舞臺(tái)上或屏幕上,任何改動(dòng)都可能破壞經(jīng)典名著固有的完美。一位專家在一次座談會(huì)上說(shuō):“經(jīng)典是一個(gè)民族、一種文化標(biāo)志性的存在,經(jīng)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jīng)典,正在于它的創(chuàng)作者往往是擁有超乎常人的個(gè)人體驗(yàn)與能力的天才,并且以某種具有超乎尋常的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的形式,凝聚著一個(gè)民族、一種文化最深刻的思維與情感內(nèi)涵。一部經(jīng)典戲劇作品的出現(xiàn)還有更多要求,它不僅需要偉大的文本,同時(shí)還需要一位甚至數(shù)位與之相稱的舞臺(tái)體現(xiàn)者。因此,經(jīng)典就是民族與文化前行的腳印,后來(lái)者只有沿著經(jīng)典指引的道路才能腳踏實(shí)地地前行。在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經(jīng)常讓經(jīng)典在我們的生活中和舞臺(tái)上重現(xiàn),是文化人必須擔(dān)當(dāng)?shù)呢?zé)任與義務(wù)。”他還說(shuō):“戲劇是一種特殊的、需要不斷通過(guò)舞臺(tái)呈現(xiàn)存在著的藝術(shù),只有經(jīng)典的經(jīng)典性呈現(xiàn),才是經(jīng)典劇作的經(jīng)典存在方式。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戲劇比起其它藝術(shù)樣式來(lái),更需要以對(duì)前輩藝術(shù)大師的模仿,使經(jīng)典劇作能夠重現(xiàn)舞臺(tái)。”
這是一個(gè)對(duì)文化傳統(tǒng)和經(jīng)典名著懷著虔誠(chéng)的、敬畏之心的學(xué)者的看法,類似一種宗教的情懷。英國(guó)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利維斯在他那本《偉大的傳統(tǒng)》中引了勞倫斯致歐內(nèi)斯特·柯林斯的一段話:“真正同想像較上勁——把一切統(tǒng)統(tǒng)拋棄,真是很難、很難的事。我總感到像是赤裸裸地站在那里,讓全能的上帝之火穿過(guò)我的身體……這種感覺是相當(dāng)可怕的。人要有極虔敬之心,才能成為藝術(shù)家。我常常想到的是我親愛的圣勞倫斯躺在烤架上說(shuō):‘兄弟們,給我翻個(gè)身吧,我這邊已經(jīng)烤熟了。’”這種對(duì)文化傳統(tǒng)的虔敬之心很長(zhǎng)時(shí)間以來(lái)一直是我們確定對(duì)改編的態(tài)度的心理基礎(chǔ),在有些人,甚至是一種本能的心理反應(yīng),只要一看到改編的作品,根本不用具體分析作品的好壞,想到的只有,與他心目中的經(jīng)典名著相比,改編者所呈現(xiàn)的,究竟像還是不像?而且,在這樣一種心理支配下,或者說(shuō),戴著這樣一副眼鏡來(lái)看改編作品,十有八九會(huì)得出不像的結(jié)論。至少人們還可以說(shuō),原著中的那種“味”沒有保留下來(lái)。田壯壯重拍《小城之春》始終是以一種虔敬之心對(duì)待原作的,他曾經(jīng)對(duì)采訪他的記者說(shuō):“這不同于我以前的任何一部電影,就像費(fèi)穆手把手在教我,讓我重新上了次學(xué)。甚至在拍攝現(xiàn)場(chǎng),我還每天不停地看費(fèi)穆的《小城之春》,我對(duì)其中的每一個(gè)片段都看了50至100遍,這當(dāng)然不是為了抄襲或者躲避,通過(guò)費(fèi)穆自信的鏡頭語(yǔ)言、游刃有余的表達(dá)方式,消除我自己對(duì)拍片的懷疑和猶豫。”盡管如此,人們?cè)诳戳颂飰褖雅牡摹缎〕侵骸芬院螅€是傾向于說(shuō),沒有費(fèi)穆拍得好。我在重新看了費(fèi)穆的影片以后甚至也有這種看法,可見,對(duì)文化傳統(tǒng)的維護(hù)在我們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
實(shí)際上,對(duì)很多改編者來(lái)說(shuō),忠實(shí)于原著也是必須遵守的一個(gè)原則。曾經(jīng)改編過(guò)許多經(jīng)典名著的夏衍在談到改編的時(shí)候說(shuō):“假如要改編的原著是經(jīng)典著作,如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這些巨匠大師們的著作,那么我想,改編者無(wú)論如何總得力求忠實(shí)于原著,即使是細(xì)節(jié)的增刪、改作,也不該越出以至損傷原作的主題思想和他們的獨(dú)特風(fēng)格。”說(shuō)到對(duì)魯迅小說(shuō)《祝福》的改編,他甚至顯得小心翼翼,“稍加一點(diǎn)也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說(shuō)到對(duì)《林家鋪?zhàn)印返母木帲瑒t不諱言“對(duì)林老板這個(gè)人物也有點(diǎn)小的改動(dòng)”。他這樣為這點(diǎn)“小的改動(dòng)”來(lái)辯護(hù):“改編時(shí),正當(dāng)1958年,社會(huì)主義三大改造已經(jīng)完成。如果照樣拍,在今天條件下,還讓觀眾同情資本家,那就成問(wèn)題了。為了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我在電影文學(xué)劇本中加了一些戲,即林老板出于自己惟利是圖的階級(jí)本質(zhì),便不顧別人死活,把轉(zhuǎn)給小商小販的臉盆都搶回去了,表現(xiàn)林老板這個(gè)人物對(duì)上怕,對(duì)下欺的本質(zhì),以抵消觀眾對(duì)他的同情。”為什么改編魯迅就一定“戰(zhàn)戰(zhàn)兢兢”,改編茅盾就可以理直氣壯?這個(gè)由夏衍表現(xiàn)出來(lái)的矛盾行為,恰恰暴露了所謂“忠實(shí)原著”的虛偽性。不是所有原著都應(yīng)該被“忠實(shí)”的,應(yīng)該被“忠實(shí)”的,只有那些被我們視為“經(jīng)典”,戴著神圣光環(huán)的作品。可見,忠實(shí)原著并不是一個(gè)客觀標(biāo)準(zhǔn),忠實(shí)的程度是要視原著在我們心中的神圣地位而定的。拿魯迅和茅盾相比,魯迅當(dāng)然更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固然,我們應(yīng)該懷著虔誠(chéng)的敬畏之心對(duì)待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乃至經(jīng)典名著,但是,對(duì)名著乃至非名著改編,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來(lái),經(jīng)典名著絕不是可望不可即的文化圣經(jīng),如果它們只能被束之高閣,在年節(jié)忌日拿出來(lái)做一番祭奠,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我們尊重經(jīng)典名著,是因?yàn)樗鼈冏甜B(yǎng)著我們,沒有它們的滋養(yǎng),我們很有可能就要患文化貧血癥了。而名著改編正是我們受惠于名著的一種方式,名著就在滋養(yǎng)我們的過(guò)程中顯示了它們的存在價(jià)值。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么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滅絕性的戰(zhàn)亂和破壞,經(jīng)典名著依然能和我們血肉相連?所以,我以為,任何一種對(duì)經(jīng)典名著的改編,都是經(jīng)典名著在新的時(shí)代的再創(chuàng)造,是鳳凰在火中的涅與新生。換句話說(shuō),經(jīng)典名著永遠(yuǎn)是可以被后人開發(fā)利用的文化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寶庫(kù)。這是可以被許多藝術(shù)的生長(zhǎng)和發(fā)展所證實(shí)的,比如電影,在它學(xué)會(huì)向觀眾講述一個(gè)故事時(shí)開始,便主要地向戲劇或小說(shuō)借取原料,電影改編也就隨之出現(xiàn)了。
以中國(guó)電影發(fā)展史為例,1914年,第一代電影導(dǎo)演張石川就將當(dāng)時(shí)上演僅數(shù)月,頗受觀眾歡迎的連臺(tái)文明戲《黑籍冤魂》搬上了銀幕,這是中國(guó)電影史上第一部改編影片。西方的第一部改編影片出現(xiàn)得更早,1902年,法國(guó)的梅里愛就根據(jù)儒勒·凡爾勒和H·C·威爾斯的同名小說(shuō)成功改編了電影《月球旅行記》。有資料顯示,在世界影片的年產(chǎn)量中,改編影片約占40%左右。我國(guó)根據(jù)文學(xué)作品改編的影片也在日益增多,大體占全年故事片生產(chǎn)的30%左右。早有人注意到,第五代導(dǎo)演尤其喜歡改編文學(xué)作品,他們最初的創(chuàng)作,譬如《黃土地》、《一個(gè)和八個(gè)》、《紅高粱》、《孩子王》,都是改編作品。歷屆獲“金雞獎(jiǎng)”的影片,絕大多數(shù)也是改編作品。像《天云山傳奇》、《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人到中年》、《駱駝祥子》、《紅衣少女》、《野山》、《芙蓉鎮(zhèn)》、《老井》、《秋菊打官司》、《鳳凰琴》、《被告山杠爺》、《那山,那人,那狗》,從1981年到1999年,共“金雞獎(jiǎng)”評(píng)選,就有12部獲獎(jiǎng)作品是根據(jù)小說(shuō)改編的。舉這個(gè)例子是想說(shuō)明,改編之于電影創(chuàng)作是多么重要。薩杜爾先生在回顧電影發(fā)展的歷史時(shí)曾說(shuō),電影依賴于小說(shuō)家或戲劇家講故事,是因?yàn)殡娪啊斑€不知道怎樣敘述故事”。但隨著電影敘事的發(fā)展,有些改編影片不僅出色地運(yùn)用電影敘事手段,在銀幕上傳神地傳達(dá)了原作的風(fēng)貌,甚至還超過(guò)了原作,以至于廣大觀眾,乃至原作者本人,都不得不承認(rèn)這是一部電影改編的佳作。根據(jù)臺(tái)灣小說(shuō)家林海音的小說(shuō)改編而成的同名影片《城南舊事》可以說(shuō)就是一個(gè)范例。林海音也很喜歡這部作品,她曾表示:“電影比小說(shuō)更好。”
電視劇的生長(zhǎng)和發(fā)展則更多地依賴于改編其他藝術(shù)門類的作品。如果允許,我可以在這里開列一個(gè)長(zhǎng)長(zhǎng)的名單,舉凡中國(guó)古代的文學(xué)名著或非名著,長(zhǎng)篇的、短篇的、文言的、白話的,幾乎很少不被改編為電視劇的,從《紅樓夢(mèng)》、《水滸傳》、《三國(guó)演義》、《西游記》,到《聊齋志異》和“三言兩拍”中的故事,都可以在屏幕上找到它們的身影。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名著也是電視劇改編者最為熱衷的,特別是在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電視劇改編者所看中的不僅是文學(xué)名著的故事,而且更看中名著中的“名”,在電視劇進(jìn)入市場(chǎng)化操作以后,無(wú)論是作家的名還是作品的名,都是進(jìn)入市場(chǎng)的最好的敲門磚,比如鄧建國(guó)投資拍攝《我這一輩子》,他看中的恰恰是老舍、石揮和這部作品的社會(huì)知名度,這種無(wú)形的資源同樣可以給投資者帶來(lái)巨額利潤(rùn)。
戲劇與文學(xué)以及戲劇與戲劇之間的改編也是一直被改編者津津樂(lè)道的,中國(guó)戲劇史和西方戲劇史上這樣的例子也很多。可以這樣說(shuō),沒有各藝術(shù)門類之間的相互利用和相互吸收,就沒有藝術(shù)發(fā)展史的繽紛色彩。如果改編只是對(duì)原作的一種模仿和克隆,它能夠吸引如此眾多的藝術(shù)人才,奉獻(xiàn)他們的藝術(shù)才華嗎?
所以,所有改編,或多或少總要對(duì)原著有所改變并作出新的解釋,舒乙所謂“必須非常忠實(shí)于原著”是不可能的,也是沒必要的。實(shí)際上,沒有一種改編是可以一絲一毫也不走樣,完全忠實(shí)于原著的。如果把“忠實(shí)原著”絕對(duì)化,從而抹煞改編者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dòng),那么,就等于取消改編,是不對(duì)的。
通常我們愛說(shuō),改編要忠實(shí)于原著的精神,這當(dāng)然沒有錯(cuò),但對(duì)于一部名著的精神則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樣。就電視劇《我這一輩子》而言,舒乙說(shuō)不符合原著的精神,張國(guó)立則認(rèn)為,他是對(duì)得起老舍的。許多專家也表示,改編基本上符合老舍原著的精神。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的關(guān)紀(jì)新先生是我國(guó)知名的老舍研究專家,曾撰寫過(guò)《老舍評(píng)傳》等著作,他說(shuō):“《我這一輩子》是改編名著的作品中比較好的一部,編劇和整個(gè)制作相當(dāng)講究。作品原來(lái)的基礎(chǔ)是一個(gè)中篇小說(shuō),而且老舍的這個(gè)中篇小說(shuō),并不是情節(jié)性的作品。從人物的塑造上講,原著比較多地反映內(nèi)心,并沒有過(guò)多的情節(jié)和動(dòng)作。對(duì)改編者來(lái)說(shuō),戲產(chǎn)生在今天,不可能完全按照老舍先生原作的框架去做。”他對(duì)改編者將一個(gè)人的一輩子改為三個(gè)人的一輩子表示理解,他說(shuō):“只有一個(gè)人物是不好表現(xiàn)的,這個(gè)作品要像當(dāng)年石揮拍電影那樣改編,估計(jì)就沒人愛看了,從中可以看出馬軍驤把握當(dāng)代受眾心理的能力很強(qiáng)。”至于京味不足,關(guān)紀(jì)新認(rèn)為這也是一種選擇,事實(shí)上,老舍先生晚年也不是完全遷就京味,如果影響表達(dá)他是會(huì)放棄的。現(xiàn)在劇中的京味,雖然不能盡如人意,卻也不是太離譜。
馬軍驤也認(rèn)為,對(duì)老舍先生《我這一輩子》的改編,沒辦法完全尊重原著。小說(shuō)中議論較多,占了很大篇幅,拍成電視劇可用的情節(jié)很少。不過(guò),他以為,“這卻帶來(lái)了一個(gè)好處,他把一些社會(huì)的觀點(diǎn)闡述得很清楚。我不太愿意改那種自己發(fā)揮余地不大的作品,那干脆不叫改編。我喜歡輪廓比較大的作品,像《離婚》中的小趙這個(gè)人物,就有很多空要填。有空可以創(chuàng)造,也容易招致批判,但有快感。電視劇《我這一輩子》雖然增加了原著中不曾有過(guò)的人物,但保留了‘我’的基本經(jīng)歷,不管怎么編,沒有編成金庸和瓊瑤,老舍的思想和出發(fā)點(diǎn)沒丟,‘我’的性格改編后也沒丟。”他有一個(gè)比喻我覺得很好:“改編名著就像是租人家的房子,房子是人家的,但住戶可以布局。”
改編名著不必完全忠實(shí)于原著的理由就包含在這樣一個(gè)比喻之中。這樣的理由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七種:
其一,以時(shí)代為理由。我們可以設(shè)想,以往任何一個(gè)時(shí)代的經(jīng)典名著,都不可能不帶有那個(gè)時(shí)代的特征和局限,同樣,在今天這個(gè)時(shí)代,任何一部改編作品,也必然會(huì)帶有自己的時(shí)代印痕,克隆和復(fù)制只是一相情愿,是改編的“烏托邦”。同時(shí),改編過(guò)去時(shí)代的作品,有意識(shí)地賦予作品和人物以時(shí)代感,也是合情合理的。比如北京人藝2000年重拍的《日出》,就以此為理由,進(jìn)行了適當(dāng)?shù)母木帯?/p>
其,以觀眾為理由。觀眾不是鐵板一塊,其中不僅有層次的區(qū)別,還有群體的區(qū)別,在我們這里,話劇、小說(shuō),特別是所謂純文學(xué)作品,都是服務(wù)于小眾的,而電影、電視劇,特別是長(zhǎng)篇電視連續(xù)劇,則是服務(wù)于大眾的,把小眾的話劇和文學(xué)改編為大眾的電影和電視劇,必須要有一個(gè)通俗化的過(guò)程,不僅能讓大眾看得懂,還要讓他們感興趣,愛看,我們改編古典文學(xué)名著和現(xiàn)當(dāng)代的著名作品,都不能忽略這一點(diǎn)。電視劇《雷雨》、《我這一輩子》、《日出》等都在這方面作出過(guò)努力。
其三,以樣式為理由。《我這一輩子》,一個(gè)是文學(xué),一個(gè)是電視劇,文學(xué)原著只有三四萬(wàn)字,而電視劇一集就要一萬(wàn)多字,因此,只能增加情節(jié)線索,設(shè)計(jì)更多的戲劇沖突。這正是主要人物從一個(gè)增加到三個(gè)的原因。再有,原著是以主人公的自述為線索展開敘事的,是一種內(nèi)心獨(dú)白的方式,這種方式改編電影時(shí)可以保留,電視劇卻不行,必須有更多的故事情節(jié)和戲劇沖突,才能使電視劇的敘事顯得比較充實(shí),才能推動(dòng)劇情的發(fā)展直到推向高潮。其實(shí),仔細(xì)閱讀原著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電視劇中增加的人物和情節(jié),幾乎都能在原著中找到蛛絲馬跡,有時(shí)老舍只是提了一句,改編者憑借自己豐富的藝術(shù)想像力和創(chuàng)造力將它大大地發(fā)展了。
其四,以觀念為理由。藝術(shù)創(chuàng)新很多時(shí)候是觀念的創(chuàng)新,20世紀(jì)以來(lái),藝術(shù)觀念的創(chuàng)新層出不窮。李六乙的許多作品都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觀念創(chuàng)新的欲望。《原野》是最近的一個(gè)例子。他要把曹禺的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張揚(yáng)出來(lái),即:人在爭(zhēng)取自由的過(guò)程中遇到的困難與困頓。他找到了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抽水馬桶、可口可樂(lè)、電視機(jī)等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物都成了現(xiàn)代仇虎們奔向自由時(shí)的障礙。
其五,以趣味為理由。人的趣味有雅有俗,有些很雅的作品,可以改編為通俗的作品,有些通俗的作品,也可以改編為很雅的作品。當(dāng)年,魏明倫改編《水滸》、《金瓶梅》走的就是由俗入雅的路線,而當(dāng)今更多的改編,走的多是由雅入俗的路線,這固然是因?yàn)榇蟊娢幕男枨笤诩彼僭鲩L(zhǎng),人們沒有理由不開發(fā)更多的資源來(lái)滿足這種需求。而無(wú)論是由俗入雅,還是由雅入俗,都有不必忠實(shí)原著的理由。
其六,以主體為理由。改編以改編者為主體,不能以原著為主體,改編者不是原著的奴才或仆人,即使它是經(jīng)典名著也罷。實(shí)際上,改編者選擇一部作品進(jìn)行改編,我們相信他一定與原著中的某種精神達(dá)成了契合,至少是認(rèn)同了原著中某種精神的存在。但是,他對(duì)于原著的藝術(shù)的解釋,則完全可以和原著有所不同,他必須尊重自己對(duì)于藝術(shù)的思考和理解,而不應(yīng)該屈從于任何外在的因素。
其七,以市場(chǎng)為理由。這是生活在今天的每一個(gè)改編者不得不考慮的問(wèn)題,從對(duì)于原著的選擇,到改編的方式,甚至包括忠實(shí)于原著還是不忠實(shí)于原著,或部分地忠實(shí)原著,都必須看一看市場(chǎng)的臉色,陰晴圓缺,不能不考慮。因?yàn)椋诋?dāng)今時(shí)代,不通過(guò)市場(chǎng)這個(gè)通道,我們就不可能將作品送到消費(fèi)者的手里。向市場(chǎng)作出必要的妥協(xié),恐怕正是一種以退為進(jìn)的策略。
電影評(píng)論家鐘惦指出,忠實(shí)原著不是目的,目的是通過(guò)對(duì)原著的改編,創(chuàng)造出新的藝術(shù)生命。他說(shuō):“如《祝福》,作為小說(shuō),它是完成了,而且是出色地完成了,但是對(duì)于電影,它還只能是一個(gè)出發(fā)點(diǎn);從這里出發(fā),要完成一部具有同一內(nèi)容但不同形式的作品。而形式,它是任何時(shí)候都不會(huì)簡(jiǎn)單地聽命于內(nèi)容的。”
實(shí)際上,批評(píng)一部改編作品不忠實(shí)于原著,是再簡(jiǎn)單不過(guò)的事,也是不負(fù)責(zé)任的、偷懶的辦法。追求克隆名著,復(fù)制名著,是庸人的做法,不是改編的歸宿和終極目標(biāo)。我們當(dāng)然尊重名著,但這種尊重并不表現(xiàn)為亦步亦趨,拜倒在名著的腳下。對(duì)于掌握了主體意識(shí)的改編者來(lái)說(shuō),他們對(duì)名著的尊重,就是像名著的創(chuàng)作者那樣,去創(chuàng)造新的作品。俗話說(shuō),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用這句話來(lái)形容名著改編,倒是恰如其分。有許多改編者,他們就是這么干的。日本導(dǎo)演黑澤明以此為原則改編了許多世界名著。他善于將外國(guó)作品本國(guó)化,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風(fēng)格、內(nèi)容都非常獨(dú)特的電影作品,而絕少忠實(shí)于原著,不僅形式完全改變了,思想、精神也是黑澤明自己的。譬如他就曾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日本化,還把莎士比亞的《馬克白斯》改編為日本古裝片《蛛網(wǎng)宮堡》,把《李爾王》拍成了場(chǎng)面宏偉的16世紀(jì)古裝影片《亂》。盡管這里已經(jīng)很少原著的影子,但似乎并不影響他的改編作品同樣成為經(jīng)典。這種情況在經(jīng)典名著改編的歷史上并不少見。
其實(shí),即使是忠實(shí)于原著的改編,原著也只能是個(gè)出發(fā)點(diǎn),改編者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dòng)是顯而易見的。同樣是老舍先生的作品,電視連續(xù)劇《四世同堂》被認(rèn)為是忠實(shí)于原著的作品,但電視劇的成功,卻并非因?yàn)樗爸覍?shí)于原著”,從編導(dǎo)到演員,從每個(gè)鏡頭到一招一式,他們所作的努力是不應(yīng)該被抹煞的。錢鐘書先生在《圍城》被改編為電視劇之前對(duì)改編者黃蜀芹和孫雄飛說(shuō)過(guò)這樣一段話:“詩(shī)情變成畫意,一定要非把詩(shī)改了不可;好比畫要寫成詩(shī),一定要把畫改變。這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改變是藝術(shù)的一條原則。”他還說(shuō):“媒介物決定內(nèi)容,把杜甫詩(shī)變成畫,用顏色、線條,杜詩(shī)是素材,畫是成品。這是素材和成品,內(nèi)容與成品的關(guān)系。這里一層一層的關(guān)系,想通這個(gè)道理就好了,你的手就放得開了。藝術(shù)就是這樣,我們每個(gè)人都是成品,每一本書都是成品,所以你放心好了。”
錢鐘書先生的這番話和鐘惦先生所說(shuō)的是一個(gè)意思,在將小說(shuō)改編為電視劇的過(guò)程中,小說(shuō)就是素材,是出發(fā)點(diǎn),而電視劇則是成品,是歸宿。因?yàn)槊浇椴煌≌f(shuō)的媒介物是語(yǔ)言文字,電視劇的媒介物是電視形象。這種差異決定了它們之間的變換是不可避免的。實(shí)際上,改編的過(guò)程就是把小說(shuō)作為創(chuàng)作的素材,通過(guò)改編者的消化、融通、取舍、發(fā)展、重新排列組合成電視劇的過(guò)程。
在我看來(lái),如果只是為了表現(xiàn)自己對(duì)經(jīng)典名著的虔誠(chéng)態(tài)度,那么,改編真的就變得半點(diǎn)意義也沒有了。只有把改編作為出發(fā)點(diǎn),改編者才可能根據(jù)自己的選擇,走向不同的歸宿。當(dāng)然,忠實(shí)于原著也不失為一種歸宿。只不過(guò),它不是惟一的,它只是名著改編中許許多多歸宿中的一種。
李六乙是個(gè)能為自己做主的導(dǎo)演,他所改編的作品,都是經(jīng)過(guò)他大膽改造過(guò)的。有些時(shí)候,他只是從原著中提取一個(gè)意念、一種思想或某些素材,而將原作中的人物、故事都做了變動(dòng),但原著中的精神還是隱約可見。他的《原野》就是這樣的作品。去年紀(jì)念魯迅先生誕辰120周年,逝世65周年,北京人藝上演《無(wú)常·女吊》,也是這樣一部作品。改編者是將魯迅先生的六個(gè)作品加以綜合,提取其精神,更多的是寫改編者對(duì)當(dāng)今社會(huì)生活的感受和體驗(yàn)。
這種情況在西方更盛行,特別是20世紀(jì)晚期,經(jīng)典名著受到了更多方面的挑戰(zhàn)和質(zhì)疑,包括對(duì)于誰(shuí)有權(quán)決定選擇一些留存于世的作品成為經(jīng)典的質(zhì)疑。很顯然,確定一部文學(xué)作品是不是經(jīng)典,并不取決于普通讀者或改編者,決定它在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的主要有三種人:文學(xué)機(jī)構(gòu)的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有著很大影響力的批評(píng)家和擁有市場(chǎng)機(jī)制的讀者大眾。其中,前兩類人可以決定作品的文學(xué)史地位和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后一種人則能決定作品的流傳價(jià)值,有時(shí)也能對(duì)前一種人做出的價(jià)值判斷產(chǎn)生某種影響。由此可見,在經(jīng)典構(gòu)成的背后有著權(quán)力的運(yùn)作機(jī)制。而改編者就居于這三種權(quán)力的中心,稍一不慎,就成了被人左右的傀儡。所以改編者確立其主體地位是十分必要的,西方近年來(lái)有許多改編都是不忠實(shí)于原著,而只忠實(shí)于自己的。有些甚至采取了解構(gòu)主義的立場(chǎng),在改編過(guò)程中消解了原著的精神。
實(shí)際上,在當(dāng)下這個(gè)時(shí)代,人們對(duì)閱讀過(guò)程的重視程度已經(jīng)超過(guò)了對(duì)于文本的重視程度,文本的神圣性正在日益消失,它對(duì)于經(jīng)典名著的改編也將產(chǎn)生不可低估的影響。人們更傾向于在改編的過(guò)程中重新建構(gòu)經(jīng)典名著的意義。只有經(jīng)典名著能做主人的時(shí)代已經(jīng)瓦解,改編者要做自己的主人了。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電影營(yíng)銷 電影課題 電影藝術(shù) 電影藝術(shù)概論 電影創(chuàng)作論文 電影申報(bào)材料 電影畢業(yè)論文 電影營(yíng)銷論文 電影藝術(shù)理論 電影心得體會(huì) 紀(jì)律教育問(wèn)題 新時(shí)代教育價(jià)值觀
- 個(gè)人電影和先鋒電影
- 電影備忘
- 電影文化
- 從電影發(fā)展電視電影
- 電視電影民族電影生存方略
- 電影影像本位
- 農(nóng)村電影講話
- 當(dāng)代電影
- 民族電影生存
- 999電影備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