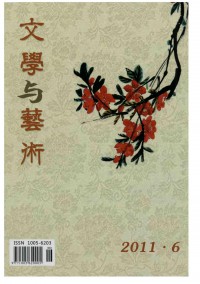文學和影視文化影響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文學和影視文化影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新時期應該說是一個特定的時期,一個過渡時期。在長遠的文學史上,“新時期”這一有深刻時代話語傾向的詞匯顯得不倫不類,但從歷史的角度說,這個名字又是20世紀文學各階段中,僅次于“新文學運動”的時代自我認識口號。“新時期”文學雖然沒有真正回歸為文學,但卻獲得了20世紀文學最大的受眾群體。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受影視文化傳播影響。本文試圖從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影視文化傳播方面做一些有益的闡述。
事實上,文學與影視,從根本意義上說,都是人類語言工具的不同表現方式。人類的語言在歷史長河中,隨著技術的進步不斷發展出各種形態。從圖形到話語,從話語到文字,再從聲音傳輸到視頻圖像,語言工具是越來越豐富,但并沒有在表意的精確性上有真正的進步。在文化長河中,也并沒有發生傳統的工具,像書本、文學被擠出人類生活的質變。文學,雖然與影視文化并行,但市場份額在減少,影響力也大不如從前。這時候,選擇合作幾乎是必然的。新時期文學,就走上了這條摸索前行的道路。
一新時期文學與影視的發展之路
1、新時期文學的開端:喧嘩和影響
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一個瘋狂時代的結束,中國文學也重新走向正軌。回到正軌的路走過了傷痕,走過了反思,也走出了新的啟蒙。盡管那時很多作品在文本形式上還有一些粗糙和平庸,但經歷過“反右”斗爭、文化革命、文化荒漠的中國人,對這些回歸到人性的文學作品卻如獲至寶。在80年代后期之前,中國文學獲得了其他時代難以企及的發展。無論從發行量還是從影響力,文學都獲得了讓其他藝術門類羨慕的地位。作家們既承載藝術,也承載著思想、道義、品格等等。在文學愛好者心中,作家仿佛就是自己的人生導師。
不必列舉那些如雷貫耳的作品了,單是那十年里讓人眼花繚亂的流派,就已經很讓人敬畏了。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新寫實小說,以及先鋒派文學等。這些文學流派,不但承載了文學的意義,同時也深刻地反映了那個年代人們的生活現實。也可以說,新時期文學是在一種喧囂中開始的,在作家們重新審視這個國家、這個時代中誕生的,然而其中更多的是在書寫一份責任、一種渴望。在這樣的訴求中,另一種語言的工具被廣泛采用了,那就是電影和電視。寫作論文
2、文學和影視:第一次親密接觸
從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后期,中國新時期文學和電影電視開始了越來越深入并且是互相促進的蜜月時期。剛剛進入新時期,許多老一輩電影人按照慣性,沿著被“”中斷的軌跡發展,現實主義傳統獲得繼承,再一次成為主潮。與之同時,文學與影視的再度結合,大批現當代小說被勝利地搬上銀幕。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現實主義傳統,觀照當世成為新的文學主潮。隨著《陳奐生進城》、《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赤橙黃綠青藍紫》、《花園街五號》、《今夜有暴風雪》、《人到中年》、《天云山傳奇》、《芙蓉鎮》等一大批知名當代小說被相繼改編成影視作品,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直接而深刻地影響著電影藝術的整體風貌。
對昔日的反思、對時代的描述、對真理的追求,成為了這一時期文學與電影共同的主題。這一時期也是文學改編電影速度最快、最忠實原作的時期,它創造的影響使得文學的影響翻倍。值得一提的是這時期的大部分觀眾是因為讀過小說,慕名走進電影院的。所以,與其說文學借了電影的影響力,不如說電影借了文學的光更正確一些。在人們熟知原著并被原著深深感動的情況下,電影的改編恐怕也只有忠實原著這一條路線好走。
80年代中前期,新興的電視劇也有很多改編自文學的精品涌現。影響較大的有:《喬廠民上任記》、《新星》、《凡人小事》、《尋找回來的世界》、《走向遠方》等等。其中改革題材的作品數量最多,也引起了最大的反響。像《新星》還創造了“萬人空巷”的收視狂潮。
另外一些導演從追求電影形式的變化創新出發,創造了像《城南舊事》、《湘女蕭蕭》、《香魂女》、《本命年》、《人生》、《老井》、《青春萬歲》、《青春祭》等一系列影片。由于原著就比較富于文學性,改編后的電影也著力表現出這種強烈的文學色彩,而且流露出濃郁的詩化意境。在西方電影技巧與民族背景的結合之下,以陳凱歌、張藝謀、張軍釗、田壯壯等為代表的第五代電影人,走上了一條更為深刻的藝術探索之路。他們以強烈的主體意識進入民族歷史文化,創造獨特的新興藝術空間。第五代電影人還顯現出與同時代文學創作之間的緊密關聯,他們的電影作品絕大多數都由當代文學作品(小說、散文、詩歌)改編而來,尤其那些“經典”之作幾乎全部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第五代”發軔之作《黃土地》其母本為柯藍的散文《深谷回聲》;張藝謀成名作《紅高粱》由莫言同名小說改編而成;張軍釗《一個和八個》源于郭小川同名敘事詩;張賢亮《浪漫的黑炮》脫胎而成《黑炮事件》;吳子牛將喬良的《靈旗》重新組合而成《大磨坊》;劉恒《伏羲伏羲》改編成《菊豆》;史鐵生《命若琴弦》改編成《邊走邊唱》;陳凱歌巔峰之作《霸王別姬》也是由香港作家李碧華同名小說改編而來……
不過對于第五代電影人來說,他們對于文學作品的看法不再是“忠實”,他們在改編的觀念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對張藝謀、陳凱歌、張軍釗等人來說,現有的文學作品提供的只是內容、題材上的參照,甚至僅僅是一個激發靈感的“由頭”,他們所要做的———是依據自身的價值判定和藝術觀念,從影像本位出發,對文學原著進行大刀闊斧的改動。改編后的作品,應該首先屬于“電影的”。《一個和八個》、《黃土地》、《黑炮事件》、《紅高粱》、《孩子王》、《菊豆》等一系列影片,無不彰顯著影像對文字的強盛駕馭能力。在一個浮躁的時代到來之前,這一轉化為文學的競爭失敗埋下了伏筆。從某種程度來說,新時期文學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了自己最大的競爭對手,而這個對手又成為最后把文學擠到邊緣化的主將。
3、90年代:走上不歸路
20世紀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作家認識到影視的強盛影響力,而實際上,這是以他們意識到文學的讀者群逐漸減少,文學的影響力逐漸衰落為前提的。在80年代后期,中國文學把世界現代文學發展史演示了一遍,但作家們終于發現,在他們認為自己的作品在形式上做出很多出色探索的時候,文學也陷入了“自說自話”的境地。
從“第三代詩歌”到“新潮小說”,中國文學在技法上越來越出色,讀者群卻越來越少。文學,成為學院里小圈子的沙龍唱和,與普通百姓無關。百姓更為關注的,是自己的柴米油鹽,衣食住行。當物質追求遠大于精神追求時,以啟蒙自居的作家們陷入了無人問津的困境。實際上,這時文學才真正回到了它本來的意義和地位,而先前的喧嘩,應該是時代的特例,與文學無關。
不管怎么說,作家們要考慮生計問題了。也許老作家,或者體制內的作家們衣食無憂,還可以高枕,但對于新興的作家們,考慮作品的市場,考慮作品的影響力,是已經上升到生存和發展的大問題。尤其是90年代中國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在市場這個試金石面前,文學必須考慮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在某種思路上,借用外力,成為自然的選擇。這外力的首選,當然就是正在冉冉升起的影視。
還有很多作家在這個轉軌面前很不適應,他們很不喜歡影視這個暴發戶小兄弟來搶市場,認為它低俗,只知迎合受眾。但對于更多的聰明人來說,受眾就是市場,就是文學生存和發展的未來。與影視合作,獲取更廣闊的市場,成為他們對于文學的營銷策略。而在客觀上,這也導致了90年代文學依賴影視傳播的現象。
更多的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被改變成了影視。以張藝謀改編的諸部作品為例,從80年代后期的《紅高粱》(改編自莫言同名小說)到90年代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妻妾成群》)、《菊豆》(改編自劉恒《伏羲伏羲》)、《秋菊打官司》(改編自陳源斌《萬家訴訟》)、《活著》(改編自余華同名小說)、《我的父親母親》(改編自鮑十的小說《紀念》)、《一個都不能少》(改編自施祥生小說《天上有個太陽》)和《有話好好說》(改編自述平同名小說)等等,張藝謀“捧紅”了一系列作家,讓這些人名利雙收。在90年代后期,張藝謀似乎成了中國文學的試金石,很多作家都期盼著作品被張導演選中,從而使自己在文學失去市場的時代一炮走紅。最為典型的表現是張藝謀向蘇童、北村、格非、趙玫、須蘭、鈕海燕等六位作家“訂購”以武則天為題的長篇小說,號稱“同題作文,相互競爭,以便于電影改編”,而趙玫、須蘭的《武則天》合集的封面上,更是印著“張藝謀為鞏俐度身定做拍巨片,兩位女性隱逸作家孤注一擲纖手探秘”的廣告語。這種雇傭寫作的方式告訴我們,在新的時代,為導演寫作正成為一種時尚,而作家們,也正在自覺地向編劇的身份轉變。
張藝謀曾表示:“我一向認為中國電影離不開中國文學,你仔細看中國電影這些年的發展,會發現所有的好電影幾乎都是根據小說改編的……我們研究中國當代電影,首先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因為中國電影永遠沒離開文學這根拐杖。看中國電影繁榮與否,首先要看中國文學繁榮與否。”張藝謀對小說原著進行電影化的刪改,《紅高粱》在國際獲獎后,張藝謀注重刻畫具有儀式性、符號化和寓言化的東方造型,諸如影片對紅色的渲染,諸如《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關于“燈”的儀式,諸如《菊豆》中的染坊,諸如《活著》中的皮影戲。甚至對于原著的情節,張藝謀也根據需要做出變動。
不能非議張導演的審美情趣,電影是工業社會和商業社會的產物,屬于工業產品,在進入藝術殿堂的同時,也必須關注如何把產品賣得更好。與文學不同,電影畢竟有著強烈的商業屬性,從它誕生那一天就注定與永恒、與不朽無緣,而與市場、與觀眾、與當下的商業成敗有著密切的聯系。改編影視勝利的還有陳凱歌由香港作家李碧華同名小說改編的《霸王別姬》,根據史鐵生小說《命若琴弦》改編的《邊走邊唱》。何平改編自楊爭光的《雙旗鎮刀客》和馮驥才的《炮打雙燈》。姜文根據王朔《動物兇猛》改編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等。
與作品被名導演改編相對應的另一現象是,一些更為醒悟的作家開始主動“觸電”,主動經營自己作品的影視傳播,有的則把寫作變成了影視寫作,更有甚者直接走上了影視經理人的道路。
1992年,以王朔為董事長的“海馬影視中央”正式登記,成員中有很多叱咤文壇的重要作家。1993年,王朔、馮小剛、彭曉林創立“好夢影視公司”,王朔任藝術總監。楊爭光辭職創辦“長安影視公司”,出任總經理。諶容、梁左、梁天等一家人也成立“快樂影視中央”。
作家“觸電”很快就結出了一些碩果。1990年,我國第一部大型室內電視連續劇《渴望》播出,獲得了出乎意料的勝利。隨后的《編輯部的故事》、《愛你沒商量》、《海馬歌舞廳》等電視劇中也都獲得了很好的收視率。這些劇目并非作家的“創作”,而是根據市場規律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王朔顯然走在風氣的前列。他的十幾部小說幾乎都被改編成了影視劇,有的還不止一次改編。在早期,王朔還待價而沽,后期則干脆直面市場,為影視寫作。后來他還干脆在電影《爸爸》中做起了導演,親自闡釋自己的作品。劉毅然、朱文、劉恒等人也嘗試做了導演。劉毅然執導根據茅盾小說改編的《霜葉紅于二月花》,朱文執導獨立電影《海鮮》并且獲得威尼斯電影節評審團非凡獎,劉恒擔任電視劇《少年天子》的總導演。劉恒說:“作家辛辛勞苦寫的小說可能只有10個人看,而導演清唱一聲,聽眾可能就達到萬人。”
這種反差讓作家們走向時代的中央。不能埋怨我們的作家們“媚俗”,在文學失去“中央話語”地位之后,作家們不能甘心地退居邊緣地位,他們要通過其它手段走向時代的中央。他們的才華不僅能適應嚴厲的創作,同樣能適應影視產品的制作。
二影視文化傳播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影視傳播推動了文學的發展,使文學盡快適應新的傳播工具和傳播方式,并且重新獲得了對大眾的廣泛影響。
從80年代后半期開始,中國文學就碰到了“門前冷落”的困惑。幾乎是同時,電影這一藝術方式開始崛起。很多文學家困惑于文學的式微和電影的“爆發”,但實際上,電影的崛起恰是以文學為底本的,一些優秀的影視作品改編了文學,給了文學在新市場上新的生命力。很多作家因為作品被改編為影視作品而獲得了更為廣泛的影響,很多作品也以影視傳播的方式獲得了更為普遍的受眾。盡管從文學到影視,形式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作品必須按照導演的需要去改編,但作品的內核并沒有發生巨大的改變。文學,通過這種非凡的方式被重新演繹,獲得更為廣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影視傳播也使得文學從業人員對于文學自身的發展,對于文學的本質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文學,終于回歸它本來的屬性,也找到了自己應有的位置。坦率地說,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文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和轟動效應,實際上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或者說是一種在非常時期發生的非常現象。在“”之后,出現了思想的真空,所以文學擔起了“啟蒙”的重任,作家擔起了思想導師的角色。實際上從真正的藝術水平上,這一時期并不是很卓越。很多作品是因為思想而不是藝術水平影響社會。當社會走向穩定發展的時期,人們對于“精神食糧”的需求退居次位,文學也就失去了轟動效應。當人們對精神產品的需求從信仰轉向消費的時候,文學這一形式當然不如更具娛樂性質的影視受到大眾的歡迎。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一些不甘寂寞的文學家們與影視合作,把文學的“啟蒙”功能暫時放下,而更多地發揮文學的服務、娛樂功能,使得我們的影視作品也具備了更強烈的文學性。另一方面,一些敢于坐冷板凳的作家則在冷清中看清了文學的本質,寫出越來越優秀的作品。畢竟,放眼文學史,真正優秀的作品,很少產生于文學熱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