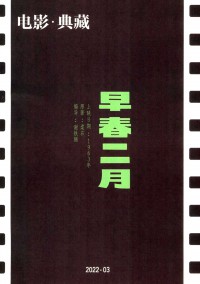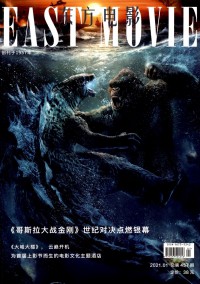電影藝術(shù)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電影藝術(shù)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xué)習(xí)和借鑒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yōu)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電影藝術(shù)文化
2000中國電影呈現(xiàn)出整體疲軟和局部亢奮的狀態(tài),表面上看,不時有一些興趣熱點激起波瀾,但藝術(shù)散化狀態(tài)和文化潛流起伏構(gòu)成創(chuàng)作較為平淡的表現(xiàn)。隨著世紀(jì)交替的臨近,原本應(yīng)當(dāng)激動人心的影像世界平鋪直敘,藝術(shù)話題被市場、進(jìn)入WTO、降價風(fēng)潮、評獎風(fēng)波、賀歲片等所遮蓋,電影的確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角色,但中國電影生生不息的藝術(shù)傳統(tǒng)卻依舊潛流般綿延,探究世紀(jì)末創(chuàng)作的走向和主題,應(yīng)該會更好提示我們關(guān)注藝術(shù)的本質(zhì)表現(xiàn),并對新世紀(jì)的中國電影發(fā)展前景有啟發(fā)意義。
一、藝術(shù)表現(xiàn)探究
走向百年門檻的中國電影,在大半的時候是流連在藝術(shù)和商業(yè)的此起彼伏爭斗中,也許東方傳統(tǒng)無法像好萊塢那樣縫合藝術(shù)片與商業(yè)片的截然界限,商業(yè)與低俗的連帶關(guān)系難以抹去,但隨著時展,崇尚藝術(shù)與貶斥商業(yè)的習(xí)俗卻日漸消退。盡管我們需要呼吁中國電影更加看重市場和大眾需求,但中國電影的興盛史似乎在申說著藝術(shù)的支撐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至今所見證明,沒有藝術(shù)的色彩,中國電影的感召力就無從談起,正如沒有商業(yè)和技術(shù)的支撐,好萊塢將失去光彩。所以,世紀(jì)末的中國電影依舊可以看到藝術(shù)的軌跡如何蜿蜒在幾近泥濘的路途中。
首先是藝術(shù)主題的核心:人性關(guān)懷。
在2000年度出品或放映的影片中,關(guān)于人性意識探究的影片并不多見,這固然是商業(yè)潮流所左右的現(xiàn)實,也是中國電影藝術(shù)主題偏移于社會宏觀教化的影響,這的確是導(dǎo)致中國電影發(fā)展難以深入的重要因素。人是世界精神的主要體現(xiàn),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復(fù)雜性和深入性表現(xiàn)的淺嘗則止,是中國電影拓展中十分重要的藝術(shù)難題。中國電影人在有限的嘗試中作出了一些探索,但這一關(guān)鍵問題還是缺少更有力度的表現(xiàn)。由此,看到謝飛教授的《益西卓瑪》就不由發(fā)出感嘆。在這部充滿奇異邊域風(fēng)光和風(fēng)土人情的影片中,同樣充滿了人情的魅力和人性的光芒,影片人物的一生的遭際不是全圍繞政治風(fēng)云,而是借助男性和女性的情感悲歡離合來表現(xiàn),在已見的東西方關(guān)于這塊地域表現(xiàn)的電影藝術(shù)中,《益西卓瑪》的人性主題所蘊(yùn)涵的魅力是真摯動人的。這部影片的出現(xiàn)破費周折,也說明傳統(tǒng)觀念對人性表現(xiàn)某種程度的陌生和局促,實際上,在我們的習(xí)慣領(lǐng)域中,對人的認(rèn)識還較多把守著外在行動人的尺度,對情感動因和心理機(jī)緣的探入缺少成功的經(jīng)驗。
于是,黃建新的《說出你的秘密》就是本年度中角度與深度頗值得探討的影片。在對人性挖掘與心理拷問方面,該片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是成功的。影片的心理探索成分占據(jù)很大比重,它對人性的認(rèn)知方式是有別于以往的故事電影或較多心理表現(xiàn)色彩的影片。應(yīng)該說,中國電影的世紀(jì)末憂慮其實多半和觀眾疏離有關(guān),除了大眾化時代必然產(chǎn)生的藝術(shù)變遷而導(dǎo)致的分流,和以電視為代表的娛樂傳媒對正經(jīng)看電影方式的沖擊之外,電影停留在事件描述層面和粗淺道理的直接說教是質(zhì)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熟悉這一套表現(xiàn)規(guī)程的觀眾已然厭倦了俗套。中國電影除非屈從世俗墮入打打殺殺和脫、透、漏式的泥沼,否則就要在根本的人文精神上下硬功夫。而中國電影的人文藝術(shù)味日漸消失是很值得憂慮的大事,人文電影的天地其實很大,而其要害是對人性和人的內(nèi)在思想與心理世界的剖析。從這一意義說,《說出你的秘密》是較為典型的例子。影片落腳于一對夫婦因妻子造成車禍后隱匿不說,而導(dǎo)致整體生活世界的微妙變化,特別是深入挖掘了人的復(fù)雜心理內(nèi)涵,絲絲入扣,逼真現(xiàn)實。影片直面人的現(xiàn)實困境--心理靈魂境界,毫不猶豫的以審視自我而拷問人生的深度,探入了隱秘的個人內(nèi)心世界的細(xì)微之處,揭示了我們常常不敢正視的心理現(xiàn)實。就此而言,顯示了創(chuàng)作者對人生探討的認(rèn)識深度。影片的揭密不僅在撞人逃逸者是誰的謎底上,而且更重要的落腳在常人面對這道難題時將如何正視的心理謎底上。在夫妻恩愛和懷疑猜忌之間,在良心譴責(zé)的道義感和惟恐罹難的恐懼感之間,影片讓我們看到人性的真實弱點、本能與人性良知之間的搏斗。著意于生活危難之際人心角逐與良知愧疚搏斗的表現(xiàn),是創(chuàng)作者對人的認(rèn)識深入化的體現(xiàn)。丈夫在同情執(zhí)著尋找目擊者的小女孩的道德感和益發(fā)產(chǎn)生深重犯罪感的痛苦心理,與惟望不是事實的僥幸心理的角逐,把當(dāng)代生活中一個清白家庭可能遇到的恐懼和抉擇平鋪在我們面前,于是,我們會油然聯(lián)想到人人熟悉的一個關(guān)于女性心理中常有的疑問:當(dāng)丈夫在自己和婆婆同時落水時先救何人上岸?這種源于懼怕失去所愛而執(zhí)拗式的無理追問就變成了影片中男女主人公類似的尷尬處境。
電影藝術(shù)特征藝術(shù)
摘要世紀(jì)之交,數(shù)字技術(shù)迅速介入影視領(lǐng)域,網(wǎng)絡(luò)不斷對影視媒體產(chǎn)生沖擊,如何在新的形勢中總結(jié)經(jīng)驗,把握規(guī)律以求得更好的發(fā)展,是電影工作者面臨的課題之一。
要害詞電影傳播數(shù)字技術(shù)多媒體網(wǎng)絡(luò)
進(jìn)入21世紀(jì),數(shù)字技術(shù)介入電影領(lǐng)域,不僅意味著制作方式和傳播方式上的革命,更帶來了電影理論與電影美學(xué)觀念的更新;而網(wǎng)絡(luò)等媒體的快速發(fā)展,也給電影帶來了挑戰(zhàn)與新的變化。
一、傳統(tǒng)電影藝術(shù)的變化作為一種伴隨著技術(shù)發(fā)展而誕生的藝術(shù),電影與文學(xué)、繪畫、戲劇、音樂等藝術(shù)相比更容易受到科技革新的影響,這種革新使傳統(tǒng)電影理論遭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甚至可能顛覆既有的美學(xué)基礎(chǔ)。1.傳統(tǒng)電影美學(xué)的解體經(jīng)典電影理論認(rèn)為,電影影像具有照相的本性,通過攝像機(jī)和膠片捕捉現(xiàn)實世界中物體的運動,經(jīng)由藝術(shù)家不同風(fēng)格的創(chuàng)造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多年以來巴贊的影像本體論觀點一直是人們理解評析電影的起點,然而數(shù)字技術(shù)的出現(xiàn)改變了一切,如《阿甘正傳》中來自阿拉巴寫作論文馬的年輕人與已故總統(tǒng)握手言歡,《角斗士》中恢宏的古羅馬城,《變相怪杰》里的百變超人,更不要說《玩具總動員》和《最終幻想》等拋開攝影機(jī)、膠片和演員,而由計算機(jī)直接生成畫面的影片了。科技的無窮威力使得數(shù)字技術(shù)成了“影像造物主”,影像與物質(zhì)、影像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變得越來越脆弱,影像不再是物質(zhì)現(xiàn)實的復(fù)原,數(shù)字技術(shù)模糊了時間與空間、現(xiàn)實和虛擬的界線,讓觀眾沉浸在虛擬的世界中,使電影這個“真實的神話”變成了“真實的謊言”,巴贊的影像本體論也宣告解體。除了影像,數(shù)字技術(shù)還使電影的傳播性質(zhì)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巴贊曾認(rèn)為作為電影唯一載體的膠片是“現(xiàn)實的一面永恒的鏡子”,《星戰(zhàn)前傳》、《女巫布萊爾》等數(shù)碼電影的誕生和數(shù)字影院、網(wǎng)吧院線等的建造,使這一論斷顯得過時。2.電影語言系統(tǒng)的裂變視聽語言是電影藝術(shù)的表意手段,影像的創(chuàng)造需要依賴編劇、演員、攝像師、剪輯師、美工師、化妝師等人的共同努力,而“合成影像技術(shù)不但使創(chuàng)作者擁有著自由處理空間關(guān)系、運用速度和明暗效果的能力,甚至也把握著對人物型貌與表情的控制手段,從而使電影書寫獲得了一種真正的自由。電影美學(xué)在這種變革面前不能不重新思索自身的位置和使命。”①據(jù)調(diào)查,由于計算機(jī)技術(shù)的運用,美國有90%以上的特技演員面臨失業(yè)的危險,因為以前表演人物從150英尺高空躍入水中的場面需要1.5到2萬英鎊,現(xiàn)在只需花2009英鎊讓演員從50英尺的高度跳下,計算機(jī)會完成后續(xù)的工作。許多主人公在銀幕上大展身手的場景不過是數(shù)字化處理的結(jié)果,不用演員、燈光照明師、美工師、攝影師的純數(shù)字電影照樣擁有很好的票房成績。
3.藝術(shù)審美價值的迷失數(shù)字技術(shù)豐富了電影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手段,但過度的炫耀崇拜技術(shù)、追求感官刺激,影片就會顯得蒼白無力。制作精良的電影當(dāng)然更能吸引觀眾,非凡是數(shù)字技術(shù)營造的視聽盛宴帶給觀眾極大的感官刺激,使電影越來越具有愉悅性和消費性,但高科技、大投資的制作并不等同于優(yōu)秀的電影作品。今天的銀幕上充斥著很多模式化、平面化、世俗化的產(chǎn)品以適應(yīng)觀眾的大眾娛樂消費心理;另一方面,電影的圖像化語言表情形態(tài)消解了觀眾的想象力,尤其好萊塢電影用流暢曲折的故事給大眾提供消遣,看他們的影片只須要投入影像而不須要費心思索,“在這圖像的盛宴之中,合理的壓抑的閥門被打開,非理性的感官的享樂左沖右突”,而無法沉下心來思索社會及人性的價值與意義。我們須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呈現(xiàn)內(nèi)心期盼卻難以實現(xiàn)的畫面,來表達(dá)一定的真情實感和精神內(nèi)涵,一旦電影失去了這種最寶貴的藝術(shù)品質(zhì),即使畫面喧囂華麗、美輪美奐,也只是一具缺乏生命力的軀殼。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為電影藝術(shù)提供了強(qiáng)盛的物質(zhì)支持與保證,電影藝術(shù)對真實與美的追求反過來又刺激了數(shù)字技術(shù)的不斷開辟。數(shù)字技術(shù)開發(fā)了人類創(chuàng)造影像的無窮潛力,造就了新的電影時空。今天,藝術(shù)家們可以突破限制天馬行空,過去認(rèn)為無法實現(xiàn)的、匪夷所思的想法都可以變幻成銀幕上的生動影像,也難怪詹姆斯·卡梅隆不無得意地說:電影的困難不再是能否拍攝,而在于能否想象。數(shù)字技術(shù)更新了電影語言,帶來創(chuàng)作手法和創(chuàng)作觀念的變化。計算機(jī)控制的攝影機(jī)能夠以人無法到達(dá)的角度和動感進(jìn)行拍攝;數(shù)字化的燈光照明、布景道具、色彩聲音、服裝化妝等電影表現(xiàn)元素可以創(chuàng)造出更為精美的畫面;鏡頭組接剪輯更加靈活自如;數(shù)字高清晰攝影機(jī)使電影離開膠片制作的年代;計算機(jī)三維動畫、計算機(jī)生成圖像等技術(shù)更讓攝影機(jī)毫無用武之地……這一切意味著傳統(tǒng)電影創(chuàng)作觀念的變革。對于觀眾來說,數(shù)字技術(shù)不僅能夠讓人經(jīng)歷驚心動魄的視聽刺激,也能傳達(dá)人類的美好情感,讓觀眾在視聽和心靈上感觸電影的魅力,同時形成新的觀影方式和觀影習(xí)慣。例如像《羅拉快跑》這樣的影片,震撼的音樂、快節(jié)奏的剪接、鮮活的三段式敘事結(jié)構(gòu)、Flash與動畫的結(jié)合等等,共同制造出一個有著無窮答案的游戲模仿世界。電影傳播渠道的多元化,也改變了在電影院群體看片的觀影習(xí)慣,電視、電腦、網(wǎng)絡(luò)、手機(jī)等載體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三、技術(shù)與藝術(shù)的雙面性特征科學(xué)技術(shù)只是電影表現(xiàn)的工具和方法,藝術(shù)家的思想性和創(chuàng)造力才是電影藝術(shù)和科技發(fā)展的源泉,前蘇聯(lián)電影理論家B.日丹進(jìn)行過精辟的論述:“無論技術(shù)元素對擴(kuò)大和加深我們對生活的認(rèn)識起著多么重要的作用,這一元素本身卻不是也不可能是形成藝術(shù)形象的獨特形式和決定因素。藝術(shù)與技術(shù)、詩學(xué)與材料之間的關(guān)系不可簡樸化對待。不管超感光度的膠片對于銀幕多么重要,還是藝術(shù)家超敏感的目光和思想具有更大的意義。在藝術(shù)中起決定作用的,開辟通向觀眾道路的,是藝術(shù)家的目光和思想,而不論膠片的質(zhì)量和規(guī)格如何。”②現(xiàn)代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拓展加強(qiáng)影視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力,也可以在感官刺激的同時降低藝術(shù)表現(xiàn)的深度。假如忽視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只能使自己迷失在數(shù)字技術(shù)的虛榮之下。電影藝術(shù)家們應(yīng)該把技術(shù)與藝術(shù)有機(jī)地結(jié)合在一起,強(qiáng)化電影的敘述內(nèi)容,提升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發(fā)揮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用那支高科技的萬能筆描繪出感動人們靈魂的電影藝術(shù)精品。四、多媒體時代的電影傳播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引發(fā)了電影從本質(zhì)、形態(tài)到內(nèi)容的一系列變化,使電影可以從制作工藝、制作方法到傳輸、發(fā)行及播映形式實現(xiàn)全面數(shù)字化,也影響著電視以錄像磁帶采集、處理、傳遞信息的方式,這種以計算機(jī)為交互中央,以數(shù)字為共識符號的新系統(tǒng)的出現(xiàn)加速改變著影視技術(shù)和影視觀念,促進(jìn)電影、電視與網(wǎng)絡(luò)等傳播媒體不斷融合與滲透,形成一個信息共有、共享、共同前進(jìn)的多媒體環(huán)境。電影開創(chuàng)的數(shù)字特技、三維動畫等制作手段,正在電視中推廣使用,高清晰數(shù)字?jǐn)z像機(jī)已是不少影視工作者的共同選擇,這種從前期攝錄到后期制作過程的趨同,使二者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
張藝謀的電影藝術(shù)
色彩的意象與現(xiàn)代“神話”建構(gòu)
色彩是一種藝術(shù)語言。當(dāng)藝術(shù)家把涂料提煉、加工、組合構(gòu)成藝術(shù)話語世界時,他是經(jīng)過發(fā)現(xiàn)與創(chuàng)造過程的。色彩,也是最大眾化的藝術(shù)手段。在電影藝術(shù)中,色彩、光線、構(gòu)圖與運動被視為電影造型的四大要素。因此,有經(jīng)驗的藝術(shù)家總是利用一切時機(jī)強(qiáng)化色彩的審美效應(yīng)。張藝謀是從攝影師轉(zhuǎn)化為藝術(shù)導(dǎo)演的,對于色彩的作用仿佛更為敏感。他認(rèn)為,色彩是最能喚起人的情感波動的因素,因此他更為自覺地把色彩運作視為重要手段。尤其在他藝術(shù)營造的早期,幾乎達(dá)到醉心與偏執(zhí)的境地。如此,他終于贏得了世界性的榮譽(yù),其中自然也難于排除色彩的作用。毋庸諱言,色彩藝術(shù)的格調(diào)總是依據(jù)時代、作品的需要和作家個人的審美情趣的不同而定格的。對于色彩的追求也是如此。研究者認(rèn)為,在古往今來的藝術(shù)家中,王維作為一個畫家和詩人對于色彩是異常敏感的。“他非常講究詩之色彩的表現(xiàn),通過全詩色彩的搭配、色調(diào)的明暗來顯示自己的審美情趣。讀王維的詩感受到他不愜意于暖色調(diào)的字,而比較喜好近于冷調(diào)的‘青’、‘白’這一類的顏色,還時常將幾種相近的色彩互相配合,構(gòu)成全詩清淡、和諧的色調(diào)。如‘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送邢桂州》)。
‘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輞川閑居》)等”[1]。在現(xiàn)代藝術(shù)家中,孫道臨在導(dǎo)演《雷雨》時,基于人物和情境的需要,便分外的強(qiáng)化了紫色的作用。“在影片中,導(dǎo)演不僅讓繁漪穿著紫色的衣服來表現(xiàn)復(fù)雜的性格,而且以紫色布置環(huán)境并貫穿全劇來體現(xiàn)繁漪的悲劇命運。”孫道臨認(rèn)為,“紫色是紅與藍(lán)的復(fù)色;紅色代表熱烈,藍(lán)是冷色,代表壓抑的鎮(zhèn)壓,這是一種矛盾斗爭的色彩”。為此,他把繁漪這個外似冷若冰霜,而內(nèi)心卻燃燒著追求愛情幸福之烈火的性格,用色彩的象征手法表現(xiàn)出來(《服裝美學(xué)》P46)。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中,張藝謀則深深地感到色彩在電影藝術(shù)中有著不可忽視的藝術(shù)分量。他在早期的電影藝術(shù)中,對于紅色便有著刻意的追求。我們從《紅高粱》的顛轎、釀酒、野合以及整個的文化氛圍;《菊豆》中的大紅布;《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大紅燈籠;乃至《秋菊打官司》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一串串的辣子(紅辣椒);《我的父親母親》中招弟心愛的大紅襖,紅綠藍(lán)紫疊合的五花山,無不浸染著藝術(shù)營造的用心。顯然,在張藝謀的電影藝術(shù)中,色彩已不再是自然的簡單再現(xiàn),而是一種意象性地建構(gòu)現(xiàn)代“神話”的藝術(shù)符號。正是如此,它不再是簡單地復(fù)制生活的手段,而是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不是實驗的,而是體驗的。王蒙認(rèn)為張藝謀的電影藝術(shù)表現(xiàn)是一種“偽風(fēng)格”,對于民眾的生活習(xí)俗來說,可能有著虛構(gòu)與假想的因子,但是對于第五代電影導(dǎo)演來說,則是他刻意追求的審美儀式。
它所營造和獲取的是影片所需要的文化氛圍和情緒的宣泄。這一點張藝謀在與香港影評家列孚的對話中說得很清楚:張藝謀:……我自己認(rèn)為,從生理上說,色彩是第一性的,能馬上喚起人的情緒波動。列孚:所以《紅高粱》的酒是白的,你卻變成紅的。張藝謀:是的。我和美工師一起,常常不惜工本,不顧事實。《菊豆》的染布,《紅高粱》的釀酒,《大紅燈籠》中,很多地方是不真實的,我們要超越真實,要有這種勇氣。由此可以看出,在藝術(shù)實踐中,基于風(fēng)格流派的差異,對于真實的理解也是各具千秋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茅盾與郁達(dá)夫,同樣崇尚藝術(shù)真實,但是一個是再現(xiàn),一個是表現(xiàn)的;一個注重于客觀真實,一個重于內(nèi)心真實體驗。現(xiàn)代藝術(shù)所營造的真實,則顯然與現(xiàn)實拉開了距離。他們立意要表現(xiàn)自我。愛特希米在他表現(xiàn)主義的宣言中聲稱:“自然的終點便是藝術(shù)的起點”。他所追求的是內(nèi)心的真實、內(nèi)省的真實和心理的真實。在我看來,中國第五代的電影導(dǎo)演張藝謀所追求的,也是這種藝術(shù)的真實。他們所努力實踐的是與現(xiàn)實相悖的文化儀式,是一種大寫意的情緒的抒寫。從受眾的心理感應(yīng)來說,基于傳統(tǒng)文化模式的歷史積淀,我們可能習(xí)慣于追索生活的本真,對于陌生的、離格的藝術(shù)處理一時會違逆接受。實際上,后現(xiàn)代與時代轉(zhuǎn)型期的藝術(shù),無意于正經(jīng)八百地來復(fù)制生活原版,他們的荒誕自然是有意為之的,其中就包含著對一步一個腳窩的藝術(shù)的反諷和調(diào)侃意味。
所以有人認(rèn)為,先鋒就是時代錯位的產(chǎn)物。他的敘述可能是超前的,但形之于作品時,則完全可能是生民原生態(tài)的粗獷與癲狂。這種畸形狀態(tài),無疑是對現(xiàn)存藝術(shù)秩序的巔覆。《紅高粱》的背景是不太久遠(yuǎn)的血的歷史,但是張藝謀的電影藝術(shù)或許并不完全在于對這段歷史進(jìn)行反思或解讀,而是要把傳統(tǒng)的歷史詩學(xué),轉(zhuǎn)化為文化詩學(xué),轉(zhuǎn)化為審美風(fēng)俗史的范疇。是要敘說他自己的“神話”故事,是他感興趣的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野史。對此,片子出世的時候,人們一時之間有些陌生感,有些冷場;后來在外面獲得了殊榮,有人說,這是用“東洋景”給“洋鬼子”看的,實際上,我們自己人,我們的大眾文化,我們社會轉(zhuǎn)型期的民眾的心理失衡狀態(tài)何嘗不需要有多種的精神調(diào)節(jié)。如果承認(rèn)世界是五彩繽紛的,那么藝術(shù)又何嘗不更需要如此呢!就色彩的有意揮灑來說,它無疑地強(qiáng)化了作品的狂歡節(jié)氛圍。從“顛轎”到釀酒中的惡作劇,自然是偽風(fēng)俗的,但卻給人以不少的快感。就色彩的內(nèi)蘊(yùn)來說,它的終極目的,顯然是一種人文關(guān)懷,是人性、人的生命精神和民族魂魄的張揚。在色彩的鋪張中宣泄著背離傳統(tǒng)文化秩序的躁動與不寧。其中過去的事件,不是著重于歷史的復(fù)現(xiàn),而是解構(gòu)、斷裂后的隱顯。
正是如此,它時時引發(fā)出一種超現(xiàn)實的藝術(shù)張力。自然,也寄植了藝術(shù)家的敘說。而這種生命的自我,人性的東西,正是人類相通的。認(rèn)真想來,這種色彩的意象,它與現(xiàn)實也并非是完全失去聯(lián)系的。以張藝謀所營造的紅色為例,它實際上也保有著民間的風(fēng)習(xí)。魯迅在《女吊》中曾說,“看王充的《論衡》,知道漢朝的鬼的顏色是紅的,但再看后來的文字和圖畫,卻又并無一定的顏色,而在戲文里,穿紅的則只有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為她投環(huán)之際,準(zhǔn)備作厲鬼復(fù)仇,紅色較有陽氣,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紹興的婦女,至今還偶有搽粉穿紅之后,這才上吊的”[2](P617)。這里有兩點是值得重視的。一是紅色,作為一種文化傳統(tǒng)是比較久遠(yuǎn)的。在我的記憶里,少年時代看到的娶親的情景,依然是紅彤彤的。不用說,那新郎官是穿紅掛綠的;新娘子更是用紅褲子、紅襖、紅頭蓋裹起來的。這時候紅色完全賦予以吉慶的象征。至于紅色被革命所接納,則構(gòu)成全新的命意。想到陜北民歌的“太陽一出滿山紅”;想到革命者在犧牲時,那種火紅的身影,無不肅然起敬。二是它的內(nèi)蘊(yùn)的陽剛之氣,顯然是民間所接納的內(nèi)核。在我看來,渾厚、熱烈、粗獷與陽剛之氣是《紅高粱》的色彩感不可剝離的藝術(shù)生命。這鋪天蓋地的渾厚氣息,在現(xiàn)代藝術(shù)中,也早已為作家所洞察,所把握,并造成顯赫的審美效應(yīng)。試看魯迅在《補(bǔ)天》中這段描寫: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從海思考電影藝術(shù)
沒看到海之前,我對海的認(rèn)識是模糊的,它僅僅是由洶涌、澎湃、壯闊、浩瀚、深邃、蔚藍(lán)一些詞匯組成的模糊而簡單的認(rèn)識。即使在看到海時,也覺得他平淡、枯燥,以至于失望。
然而,當(dāng)我靜下心來,拋開一切成見、偏見和顧慮。但是站在海本身的角度和位置,再一次仔細(xì)地思考和認(rèn)識眼前的海時,我發(fā)現(xiàn)我錯了,我誤會了海,從某個角度說,我犯了這樣一個錯誤:我站在海邊,吹拂著海風(fēng),沐浴著海浪,聆聽著海聲,卻忽略了海本身所有的存在。
由此引發(fā)開來,作為一個藝術(shù)的崇拜和追隨者,作為一個新時代的電影人,我想到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在高舉藝術(shù)大旗大聲疾呼的同時,卻忽略了藝術(shù)的根本。或許,我們都只是站在自己為自己雕塑的象牙塔里,用自己主觀甚至武斷的眼光和思維,定義著電影,定義著我們信誓旦旦要為之奉獻(xiàn)一生的藝術(shù)。
大海的干涸,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源泉的干涸。當(dāng)我們?yōu)殡y得的素材而歡呼的時候,當(dāng)我們驚嘆阿巴斯的精美藝術(shù)時候,當(dāng)我們感嘆韓流的來勢兇猛的時候,當(dāng)我們驚呼好萊塢電影咄咄逼人的時候,我們在為別人歡呼的同時,在因為自己的貧乏而苦惱。我們是否想過,我們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什么?而且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一種什么?是否真正認(rèn)真地探討過什么是藝術(shù)的根本?又是不是忽略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電影藝術(shù)最為重要最為根本的東西——那就是我們的生活,已經(jīng)煙塵散去塵埃落定的過去的生活,和我們現(xiàn)在正生龍活虎風(fēng)風(fēng)火火的生活,屬于自己的生活。
生活是一切藝術(shù)的唯一源泉。這不僅是開國元勛對藝術(shù)的真知灼見,更是藝術(shù)規(guī)律和本質(zhì)的精練概括。不走近大海,我們無法了解大海的廣闊。在飛機(jī)上鳥瞰大海,會覺得大海也不過就是一片大點的水域,在宇宙飛船上看大海,我們會發(fā)現(xiàn),眼前的大海不過就是那么小小的一片藍(lán)色。然而,當(dāng)我們駐足大海之濱,尤其是處身于大海之中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自己是那么渺小,就連滄海一粟也不足以形容,而大海是那樣的廣闊無垠。同樣,如果我們把生活比喻成海。那么,我們是雙手抱胸冷眼相看,甚至還是吹毛求疵挑肥揀瘦的對待它,還是應(yīng)該讓自己與之更加接近更加親密呢?需要從母親那兒吸取乳汁,但又總是對母親敬而遠(yuǎn)之,甚至因為母親樸實無華就不愿意與之接近,我們能吮吸到甘甜的乳汁嗎?而脫離了母親的乳汁,我們小心呵護(hù)的藝術(shù)的雛兒能茁壯地成長嗎?所以,我們只有瀕臨大海,才能真正發(fā)現(xiàn)大海的遼闊。只有親近母體,才有嬰兒的生存和成長。我們應(yīng)該做水手,為了電影藝術(shù)尤其是中國電影藝術(shù)的新的高潮和發(fā)展,我們應(yīng)該把自己的生命之舟和藝術(shù)之船放進(jìn)生活的海洋。
海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它淺,淺得肉眼也能看見它的底;它深,深達(dá)一萬三千多米。要徹底全面地感受大海的神奇,目光停在表層是局限的。大海深處的寶藏、大海深處的絢麗神秘,只有時刻游弋在深水里的魚兒最先知道和了解。生活的海洋同樣是豐富多彩、魅力無窮的。也許它被枯燥、單調(diào)的表面所掩蓋,但我們?yōu)槭裁床蛔屪约褐蒙砗Q笊踔脸寥牒5祝ビ|摸每一株海草,欣賞每一棵珊瑚,撫摸每一塊石頭呢?攝影者知道,即使一個破爛的窗筐,只要我們?nèi)フJ(rèn)真地體會,合理地利用,巧妙地把握,就能創(chuàng)造出良好的藝術(shù)效果。藝術(shù)其實就是對生活的提煉,而提煉需要原料,原料依靠積累,積累在于采集。沒有一個一鋤就能采掘到大塊黃金的淘金者,也沒有一接觸就能邂逅到藝術(shù)的鉆石。更何況,我們的責(zé)任不是為了一次兩次成功。海是有層次的,下潛一百米所能得到的收獲與下潛兩百米所得到的收獲就截然不同。做敢于不斷深潛的潛水員吧,潛入生活的大海中去,多層次、更深刻地認(rèn)識生活、體驗生活、感悟生活。
作家電影藝術(shù)
從劉震云把自己的小說《我叫劉躍進(jìn)》改編為同名電影始,關(guān)于“作家電影”的特質(zhì)、藝術(shù)形式、涵蓋內(nèi)容等,引起了不少人的關(guān)注和討論。以中影集團(tuán)董事長韓三平提出的關(guān)于“作家電影”概念影響為最大。韓三平把“作家電影”解釋為:生活閱歷豐富、對社會生活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卓越表現(xiàn)力的作家(也包括部分導(dǎo)演),在現(xiàn)實生活中捕捉到為大眾廣泛關(guān)注的生活熱點、社會話題,用質(zhì)樸的電影手法加以表現(xiàn),用鮮活的人物、生動的故事、真切的情感,去喚起觀眾的注重力。這其中既包括冷峻深刻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電影,也應(yīng)包括“夢幻”式的作家電影。2009年初,低成本、小制作的《瘋狂的石頭》,曾給國內(nèi)電影市場帶來一絲希望的亮色,但并未能扭轉(zhuǎn)國產(chǎn)電影的頹勢。面對國產(chǎn)片普遍疲軟,票房收入持續(xù)下降,賺了錢的大片卻罵聲一片,韓三平希望團(tuán)結(jié)一批作家,以他們有影響的創(chuàng)作優(yōu)勢,拍攝一批不靠明星和特效,靠故事本身打動觀眾的小成本影片,這就是韓三平心中的“作家電影”。他的良苦用心是重新振興中國電影,但這個“作家電影”的概念與國際普遍理解的“作家電影”概念相距甚遠(yuǎn),僅這個提法而言,顯然是有商榷余地的。
“作家電影”不應(yīng)該狹義理解為作家自己創(chuàng)作或改編電影劇本、參與制片、導(dǎo)演甚或串演某個角色,去表現(xiàn)真切、平實的百姓話題。假如這樣說,一批被稱為“第六代”的導(dǎo)演們早在20世紀(jì)90年代就這么做了,并形成小氣候。他們主張每一個人都應(yīng)以其本性裸呈,不加任何作偽粉飾,人人人性平等,企望表現(xiàn)真實人性的作品,能給觀眾造成強(qiáng)盛的心靈沖擊力量。王小帥曾說過:“要掙脫技法本身的束縛,把人的本體,人最深處的東西拍出來,這才是電影的真諦。”[1](P27)他們拋棄一般電影那種全知敘述,代之以親歷式的主觀敘述,使影片更加貼近生活的真實。由于這一批導(dǎo)演大都是自己編寫電影劇本,謝飛曾經(jīng)批評過:“我說你們非要死盯著都市,死盯著你這撥人自己,為什么都是自己寫劇本不改編?而第五代的優(yōu)勢就在于改編的作品多。”[2](P48)他們拍的電影,有一些非常優(yōu)秀,但常常因為這樣或那樣的體制原因,無法進(jìn)入正常的電影市場。這一批導(dǎo)演都極自信、有才華,但他們過早地與文學(xué)“離婚”,導(dǎo)致他們的文化底氣不足。當(dāng)然,十幾年后的今天,這一批導(dǎo)演正以自己的作品證實了他們破繭而出的成熟和實力,在國內(nèi)、國際上都取得了相稱的聲譽(yù),更重要的是已經(jīng)培養(yǎng)了一大批認(rèn)識、喜愛并懂得他們電影的觀眾,但是沒有人稱他們的影片為“作家電影”。
“作家電影”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紀(jì)30年代的無聲電影時期,真正形成流派是在20世紀(jì)50年代末期的法國。誕生的標(biāo)志作品是1958年特呂弗導(dǎo)演的《淘氣鬼》和夏布洛爾導(dǎo)演的《漂亮的塞爾日》。“作家電影”是以法國“新浪潮”的理論為基礎(chǔ)的,法國聞名電影理論家巴贊及他創(chuàng)辦的《電影手冊》集聚了后來成為“新浪潮”的眾多年輕影評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幾乎都是業(yè)余作家和影評家。“新浪潮”主將戈達(dá)爾曾聲言:“拍電影,就是寫作。”今天,“作家電影”是泛指那些身為職業(yè)作家而客串導(dǎo)演拍出的電影,比如法國作家阿蘭·羅伯·格里葉的《橫跨歐洲的非凡快車》,瑪格麗特·杜拉絲的《卡車》,前蘇聯(lián)作家舒克申的《紅莓》,以及中國作家朱文的《海鮮》《云的南方》,等等。
單單作為概念的“作家電影”是可以借鑒的,如同中國的“西部片”就是借用美國好萊塢開發(fā)西部的類型片的概念。20世紀(jì)80年代,當(dāng)一大批如《人生》《黃土地》《老井》《紅高粱》《野山》《雙旗鎮(zhèn)刀客》等以中國西部生活為題材的優(yōu)秀影片問世,中國觀眾認(rèn)可了中國的“西部片”,專家也認(rèn)可了。聞名電影評論家鐘惦棐看了吳天明導(dǎo)演的《人生》,欣喜地說:太陽有可能從西部升起!這里要害的是中國式的“作家電影”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是否應(yīng)根據(jù)現(xiàn)在中國電影機(jī)制的轉(zhuǎn)型期的特點,給予它更加寬泛、廣闊甚至包容的內(nèi)涵?假如將由作家參與編劇或制片或客串的電影認(rèn)定為“作家電影”,可能造成對“作家電影”的最大誤會,而最終受到傷害的還是電影本身。
從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中國電影復(fù)蘇,被稱為“輝煌而又悲壯的拓荒者”的一批導(dǎo)演使用幾乎全新的電影語言以及具有濃烈的象征、隱喻和極強(qiáng)的電影造型意識,包括光影造型、色彩造型、聲響造型等,打破了“戲是電影之本,影像只是完成戲的手段”超穩(wěn)定的“影戲”觀念。他們用電影反思?xì)v史、民族的命運,反映中國真實的現(xiàn)實生活。“當(dāng)民族振興的時代開始到來時,我們希望一切從頭開始,希望從受傷的土地上生長出是足以振奮整個民族精神的思想來。”[3](P106)這是陳凱歌的一段話,表明了這一批導(dǎo)演從一開始就站寫作論文在電影該怎么拍的制高點上。后來他們的確改寫了中國電影的歷史,他們的一大批影片已載入中國電影史冊,成為經(jīng)典,拉近了中國電影與世界電影的距離。他們的電影直到今天仍使大批觀眾不能忘懷。他們的電影勝利,和當(dāng)時文學(xué)作品碩果累累分不開的。《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孩子王》《邊走邊唱》《霸王別姬》《風(fēng)月》《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活著》《有話好好說》《一個都不能少》《晚鐘》《藍(lán)風(fēng)箏》《大磨房》《黑炮事件》等,還有后來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甲方乙方》《永失我愛》,包括最近上映的《集結(jié)號》等,都是根據(jù)郭小川、柯藍(lán)、余華、葉兆言、莫言、蘇童、劉恒、阿城、王朔、史鐵生、陳源斌、李碧華、張賢亮、楊金遠(yuǎn)等詩人和作家的詩歌、散文或小說改編而成的,有的還是作家直接參與編劇。一大批優(yōu)秀電影的涌現(xiàn),究其根本,它們都是站在“文學(xué)的肩膀上”。這批聰明的導(dǎo)演實施的是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但是又為我用,他們勝利地借助了文學(xué)作品易于傳播、受眾廣的優(yōu)勢,所以他們勝利了。中國導(dǎo)演借助外國文學(xué)作品,改編為地道中國味道的電影,也不乏其人。徐靜蕾改編了茨威格的《一個生疏女人的來信》,李少紅根據(jù)馬爾克斯的小說改編拍攝了《血色黃昏》,片中彌漫著中國北方山區(qū)特有的黯灰色、還有老百姓對于一個生命隕落的冷漠和看客心理,令人不禁悲哀地聯(lián)想起魯迅的《阿Q正傳》。
說到一個事物的本性時,很重要的方面是該事物的根本、本源。文學(xué)作品(也包括可讀的電影文學(xué)在內(nèi),有別于導(dǎo)演的分鏡頭劇本)是由作家依賴生活積累,把自己對于生活的感觸、理解、思索等,通過藝術(shù)的形象思維,用語言文字創(chuàng)造出生動的人物形象和他們的命運故事。電影藝術(shù)是以“影”為本的,而故事即“戲”只是電影的一種形態(tài)和因素,它是一種運用電影聲畫的多種可能性,探索、認(rèn)識和把握生活的藝術(shù)思維方式。電影的根本是“以攝影機(jī)為核心”的機(jī)械裝置,用攝影機(jī)對于客觀現(xiàn)實進(jìn)行紀(jì)錄式的模仿是電影的基本手段。它在反映現(xiàn)實時第一次做到了反映者和被反映者之間中介的消失;電影影像可以達(dá)到對客觀現(xiàn)實最逼真的“漸近線”,以致使觀眾會覺得和物質(zhì)現(xiàn)實幾乎毫無二致。電影藝術(shù)完全擯棄了戲劇舞臺的假定性,代之以客觀存在的運動著的物質(zhì)世界。它不僅可以表現(xiàn)尖銳沖突,也善于表現(xiàn)低徐舒緩的尋常生活,還可以潛入人物內(nèi)心隱秘的領(lǐng)域,就像生活中的一段被攝影師偶然拍下來一樣。電影藝術(shù)要求參與的各種元素都要逼近生活的本相,如符合時代的環(huán)境、化妝、服裝、道具、人物語言等,僅說對演員的選擇,就要求在年齡、形狀、生活習(xí)慣、氣質(zhì)等方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劇中人。中外電影都不乏為某個演員專門量身定做的電影劇本,比如吳宇森1986年拍攝的《英雄本色》,就是根據(jù)周潤發(fā)的形狀、表演、性格、氣質(zhì)特點自編自導(dǎo)的。《英雄本色》充分展示了吳宇森“暴力美學(xué)”的特點,奠定了他在香港影壇的地位,它也是周潤發(fā)表演事業(yè)的巔峰之作。電影給予觀眾的美感,是建立在記錄真實的基礎(chǔ)上的,任何一丁點兒的造作、虛假都會引起觀眾的反感。電影特有的藝術(shù)手段還表現(xiàn)在鏡頭的分切和組合上,即“蒙太奇”手法,這是電影藝術(shù)家對于生活進(jìn)行分析綜合的非凡方式。鏡頭的組接方式能夠給畫面中賦予現(xiàn)實中原來沒有的意義,它“不是二數(shù)之和,而是二數(shù)之積”。電影就其本性而言,不是想象藝術(shù)而是感覺藝術(shù)。其它如文學(xué)、音樂、舞蹈、書法、建筑等藝術(shù)門類,離不開感覺,但本質(zhì)上還是想象藝術(shù);電影也離不開想象,但本質(zhì)是感覺藝術(shù)。
相關(guān)欄目更多
電影營銷 電影課題 電影藝術(shù) 電影藝術(shù)概論 電影創(chuàng)作論文 電影畢業(yè)論文 電影申報材料 電影藝術(shù)理論 電影營銷論文 電影心得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