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教學困難思考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現當代文學教學困難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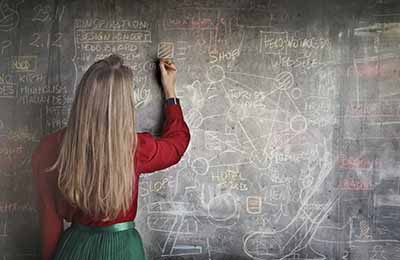
不管是本身的藝術魅力還是對歷史的重要程度,都和文學史敘述的權力相關。換言之,選擇那些作家、作品進入文學史,本來就不是約定俗成的,而是基于不同起點的有意識地選擇。在既有的文學史敘述中,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啟蒙視野的文學史敘述和革命視野的文學史敘述對作家、作品的選擇和評價會有非常大的差別。如果說,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和趙家璧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等著作,相對客觀得描述了中國新文學的淵源、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創作實績,那么在建國后的文學史中,對革命的合法化敘述就成為文學史寫作的基本訴求。在革命視野的文學史敘述中,作為革命者的魯迅、茅盾、郭沫若等受到推崇,判斷文學作品的價值也常常以是否運用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否體現了反封建的思想內容等作為評價的標準。而在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活動中,現代文學中的自由主義作家、非左翼作家才有機會付出歷史地表。此次的“重寫文學史”,一方面受到域外的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和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和國內以“啟蒙”、“審美”的文學標準取代“革命”的文學標準的期待相關,作品的“文學性”受到關注,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史才重新發現了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等重要作家。因此,基于不同視野的文學史書寫,在凸顯某些作家的同時也遮蔽了豐富的文學現象。那么,如何回到歷史現場、發現歷史敘述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就需要大量的原始資料的支持,這對文學講述者的史料積累是一個考驗。而且,不僅要掌握史料、重要的是學會分析與總結史料,從紛繁復雜的歷史境遇中洞見彼時的文學創作的基本脈絡,并能夠透過歷史的重重迷霧對作家、作品做出相對客觀、全面的評價。
因為文學史敘述的權力問題,多年以來,我們對現代文學的經典講述主要集中在魯、郭、茅、巴、老、曹這些作家身上。但即使是對這些作家的經典作品的講述,可能依然會有遮蔽與鄙陋。比如對魯迅的講述,在過去我們比較關注作為革命者、啟蒙者的魯迅,這在1980年代魯迅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中可得以體現,而在1990年代的學者王暉的《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抗爭絕望的存在主義者的魯迅形象。從啟蒙者魯迅到存在主義者魯迅,可以看到對“經典”的不斷重讀所發現的新的視野與問題。同樣是魯迅,在課堂教學中,往往比較重視對《吶喊》和《朝花夕拾》的講述,在《吶喊》中,我們理解了魯迅對“吃人”的封建禮教、封建文化、國民劣根性等的批判,而在《朝花夕拾》中,我們讀到了魯迅所有作品中最溫情的一面。但是,如果越過了《彷徨》、《野草》、《故事新編》,那我們根本就無法理解魯迅作為先知者、啟蒙者的深刻、孤獨與無地彷徨、反抗絕望的精神及其對歷史的深刻體察。再比如現代文學教學都會精講曹禺的《雷雨》,以一個大家庭的分崩離析控訴了封建家庭的罪惡和預示了舊時代的毀滅,但是,如果把《雷雨》的“序幕”和“尾聲”作為問題,可能會對《雷雨》有非常不同的解讀,我們會看到曹禺內心的悲憫、對人類不可捉摸、無以把握的命運的敬畏等。因此,對經典的重讀,不僅涉及歷史本身的復雜,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在把作品還原到歷史現場的同時所具有的穿透歷史的目光,使對作品的理解和分析可以從多重意義上展開。
那么,再來看在“重寫文學史”中發現的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等作家。在對沈從文的講述中,基本上都會選擇《邊城》作為精講篇目,在邊城真善美的世界里,沈從文構建了一個世外桃源、一曲田園牧歌。但是,正如沈從文所說的:“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而這背后的“深憂隱痛”并不單單是翠翠等待那個“也許明天回來,也許永遠不回來”的戀人的憂傷,而是在“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背后人事與命運的蒼涼,是對湘西世界在“現代”的擠壓下即將風流云散的悲劇體察,爺爺去世了、白塔倒了,明天的邊城會是什么樣的呢?沈從文的個人隱憂和對那個時代的憂患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以邊城世界重塑民族未來的熱情和期待的背后是他自己也許已了然的“不能”,是不得不為的“挽歌”。因此,沈從文并不是一個逃避現實、背對時代的自由主義作家,而是深切感受到了時代的風雨并深懷憂患。那么,錢鐘書呢,這個以“文化昆侖”而著稱的學者以一部長篇小說《圍城》名世,但大家更多關注了《圍城》中的“婚戀”圍城,看到了方鴻漸與孫柔嘉的離亂悲歡,但是,“圍城”中的文化圍城、個人存在的圍城狀態,其實是錢鐘書更為深遠的寄托。所以,即使對文學史上這些“經典”的自由主義作家的解讀,也不可能脫離具體的歷史語境與寫作者的個人隱憂而僅談“文學性”的問題,在“文學性”的背后經常隱含了個體的生命經驗與一個大時代的悲愴。總之,在現代文學的文學史敘述與經典重讀中,應該有一個必要的認識的前提,那就是文學史敘述是一種權力,而經典是被不同的文學史建構的。對重要作品的解讀、對“文學性”的分析,都需要納入作家的生命經驗極其時代的意識形態特征。如何有歷史的理解與同情,同時能夠超越歷史敘述洞見文學作品的多重內涵與意蘊,是文學史講述、作家、作品解讀必須面對的問題。
當代作家與文學現場
雖然關于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歷史分期的問題早在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活動中已有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等都是對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政治分期的糾偏。但是,在很多大學的教學中,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教學是分開的(比如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沿用這種約定俗成的分法,當代文學一般從建國后一系列文藝批判運動講起,闡釋當代文學“一體化”格局的形成,這和政權政治有著直接的聯系。當然,從建國后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學科建制,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設置具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深刻內涵,那就是要建立高于現代文學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但這種對學科的歷史定位到1980年代又發生了翻轉,現代文學因其對五四傳統的繼承與發展,而具有了高于當代文學(在彼時,人們對文學與政治聯系過渡緊密的反感)的價值。姑且不論作為學科的價值的高低,這本來也是歷史敘述的問題。在當代文學的教學中,構成討論重點的是對十七年文學中“經典”的講述,比如《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因為受到建國后當代文學“一體化”的規約,這些作品有著明顯的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特征,他們講述革命的合法性、勝利的來之不易、農村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農民的成長問題、知識分子的成長問題等。如果在當代文學教學中,繼續在這樣一些脈絡上進入作品,那么只是陳述了文學史的常識而容易陷入陳詞濫調,學生也會因其與政治的亦步亦趨而本能得厭倦十七年文學。實際上,自1990年代后期以來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已經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視角,比如李楊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唐小兵的《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從文化研究等多種視角進入作品,豐富和拓展了對十七年文學“經典”的解讀。于是,對《紅巖》的講述,不再單純是革命英雄敘事,而是納入了革命的烏托邦、人性與神性、身體的意識形態等視角,從“革命不回家”、革命與家的對立、在同志、親情等之間的選擇中,革命的敘事模式昭然若揭。而在《青春之歌》中,在知識分子的改造中介入了林道靜的個人成長,這部小說就不單是關于知識分子道路的革命敘事,同時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女性的故事。在啟蒙知識分子余永澤、革命知識分子盧嘉川、江華等背后攜帶的是林道靜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長所需要的不同的知識資源:西方人道主義的啟蒙思潮、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而在性與政治之間,林道靜沒有主體性的個人成長也是被不同的男性引導、塑造的過程。于是,單一的政治解讀變成了多角度、多視野的“再解讀”,在文學史的常識之外豐富了對“經典”的理解,也引導學生透過慣常的歷史敘述洞見政治“一體化”敘述的縫隙中所透出的豐富意蘊。
當代文學教學的另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對當下文學現象的關注,眾所周知,今天既有的文學史一般都只講到了2000年左右(這也是極少數的),而即使講到了2000年左右,但對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分析相對都比較薄弱。現實的問題是,新世紀文學也已走過了10多個年頭,而且在這些年里涌現出眾多優秀的作家、作品,如何把這些納入當代文學的教學一方面能豐富文學史的講述,另一方面也是要引導學生關注當下的文學創作情況。目前,在當下文壇主要有兩部分作家構成,一部分是從1980年代登上文壇并成名、如今仍在持續寫作的作家,這一部分也是新時期以來文學的中堅力量,如莫言、賈平凹、余華、蘇童、格非、鐵凝、王安憶等,一部分是新涌現的70后作家,如魏微,馮唐,魯敏、張楚、徐則臣等。針對前一部分作家,就需要建立他們的創作譜系,也就是在講述1980年代的作家時,把他們三十年左右的創作進行梳理,并重點講述代表作品,一是可以看到他們創作前后的變化、建立作家個體的寫作檔案,二是可以從作家寫作的變化透視文學史中敘事形式、審美風格等的變化。比如莫言,在1980年代,他以《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家族》等小說奠定了自己在文壇的地位,《透明的紅蘿卜》中奇異的想象力和少年記憶、《紅高粱家族》中對高密東北鄉的民間記憶的重構等在此后的寫作中都有不同的延續,1990年代的《豐乳肥臀》對大地民間豐厚博大的母性力量的贊美、新世紀文學中《生死疲勞》的奇異想象力、《蛙》對高密東北鄉故事的辛酸講述,和他1980年代的寫作構成了有趣的對話。比如,余華,這個寫作變化非常大的作家,在先鋒思潮中登上文壇,從《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小說中的暴力敘事到90年代左右的轉型之作《細雨中呼喊》、之后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的悲憫、新世紀文學中《兄弟》的欲望狂歡敘事,從表層很難看出是出自一人之手,但是從余華的變化,我們可到先鋒寫作的問題及其后來的走向。這樣,不僅可以建立起對一個作家的比較全面的認識,而且他們的創作變遷也記錄了三十年間文學書寫中中國經驗的變化。而對于后一種作家,也就是在新世紀文壇顯影的70后作家,他們對瑣碎的日常生活的書寫、對現實疼痛的撫摸,目前看來仍然缺少歷史感,但是他們的文學寫作可能和今天的90后學生的生命經驗更能產生共鳴,把這些作家介紹給同學們,讓他們體察到文學和今天“現實”的切近,但也要提醒這種瑣碎的日常生活敘事可能產生的問題,提高學生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和鑒別能力。在當代文學的講述中,有關當下寫作的問題是學生們比較感興趣的一部分,這不僅是當下寫作中的優秀作品已構成了文學史的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家都是“現在進行時”的,他們不斷有新的作品出現,而隨著大眾傳媒對文學事件的介入,學生對許多熱點問題會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每次茅盾文學獎頒獎了,學生們都會要求對茅獎的獲獎作品進行介紹與討論,尤其是這次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第二天上課,學生馬上會問:老師你怎么看?他有哪些好的作品?因此,關注當代文學教學中當下文學創作情況,可以幫助學生解在自己成長的年代中文學寫作發生了哪些變化,并引導他們培養文學閱讀的興趣、提高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力。
構建文學史的知識譜系
優秀的作家、作品是文學史的基石,但既然是“歷史”,那么文學史也是歷史敘事,而“歷史敘事”都會和“歷史”產生對話,換言之,任何文學事件、文學思潮在與此前的歷史傳統構成承續關系的同時也與當時的歷史語境構成對話。因此,構建文學史的知識譜系、透視文學背后的歷史和現實境遇,是現當代文學教學的一個有效的路徑。在整個現代以來的文學史中,很多文學現象、文學事件都與此前的歷史有復雜的聯系、同時又和此后的文學現象構成對話,因此,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必須打破現代、當代文學的政治化分期,把整個現代以來的文學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我們的現代文學教學一般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講起,因為五四新文學開創的形式上的白話文實踐、思想文化上的反封建、個性解放等具有鮮明的歷史斷代的特質。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從來就不可能是和過往歷史斷然決裂的文學、文化與思想運動,“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目前已成為學界共識,因此,在教學中對晚清所孕育的現代性因素的追溯,成為理解五四新文學何以發生的一個必須的“前史”。“五四”所開啟的“啟蒙”文學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那么,1980年代的“新啟蒙”又是怎樣挪用和重構了“五四”資源并為1980年代“新啟蒙”的意識形態服務的,這不僅是一個文學史的事實,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史需要厘清的問題。從1980年代的“一切又仿佛回到了五四”的感嘆到“文明與愚昧的沖突”的歷史判斷,都暗含了“新啟蒙”和“五四”啟蒙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又比如,建國以后左翼文學的極端發展,在文學史、思想史上常常歸罪于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經驗,而實際上,“十七年文學”對“革命”的合法化敘述、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的兩結合的創作方法,不僅和延安時期的文學實踐密切相關,而且和1930年代的左翼文學、后五四時期的“革命文學”都有著及其深厚的聯系。因此,對文學史的知識譜系的梳理,有助于建立對整個現代以來的文學的歷史整體性的認識,并理解歷史的多元與復雜。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建構文學史的知識譜系時,要注意文學現象或者文學思潮與當時的歷史語境的關系,也就是文學的“接地”或者說“及物”,使文學現象不僅和歷史構成對話,而且可以對現實發言。比如,狂飆突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新文學的重要起點,成為此后的文學史家念茲在茲的一個高峰,但是,1990年代以來對五四“激進”的反省提供了考察五四的另外的緯度。于是,我們就需要把五四新文化運動還原到當時的歷史語境,發現他“激進”的不得不為、當然,還有“不得不為”的“激進”所產生的另外的問題。因對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過度緊密的反感,人們會想當然得厭倦十七年文學,但是,如果把十七年文學中的左翼實踐和時代的社會主義目標結合來看,可以發現時代的“反現代的現代性”(汪暉)。而被文學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指認為“激情與浪漫”的1980年代,今天看來很大程度上是知識精英自我想象的“燃情歲月”,而1980年代包含的歷史復雜性、在多重緯度上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想象,始終伴隨著當時國家意識形態的規約、及其對規約的反抗與突圍。又比如,1980年代的“純文學”、“讓文學回到自身”所暗含的“非文學”的訴求,對突破當時的政治規約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但“純文學”在1990年代以后的寫作中面對“現實”的虛弱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包括今天新世紀文學中的“底層寫作”和當下中國現實的關系,何謂底層?底層如何發言?誰有權力代表底層?這一系列問題的背后都暗含了知識群體面對當下中國現實的思考及其面臨的困境。或者說,任何文學現象都是時代的“鏡子”,而在文學中讀到的“歷史”與“現實”或可留下比歷史書寫更為真實、豐富的細節。當然,構建文學史的知識譜系,也必須關注不同時代的作家之間的傳承,在前輩作家與后代作家構成的書寫傳統中,如何突破“影響的焦慮”、賦予傳統新質成為文學持續創新的重要動力。比如,在20世紀文學的鄉土書寫中,大概有三種不同的傳統,一是魯迅開創的啟蒙主義的鄉土書寫,以現代知識者的目光審視鄉土,重在社會批判與文化批判;二是以三十年代的沈從文為典型的審美的鄉土書寫,通由對故土湘西的審美想象,寄寓重鑄民族靈魂的熱望;三是四十年代進行政治化的農村書寫的趙樹理,以鄉土在革命中的變遷演繹鄉村與政治錯綜復雜的關系,為新的政權進行合法化敘述。這三種不同的鄉土書寫在此后的文學史中都有回聲與對話,如高曉聲之于魯迅、汪曾祺、沈從文的師承、柳青、周立波等的農村書寫與趙樹理構成的頗有意味的對話關系。又比如,在女性書寫的譜系中,從張愛玲的“傳奇”到王安憶的上海故事,“海派”文學一脈相傳,而蕭紅對東北大地的歌苦與今日遲子建溫暖、日常的敘事演繹了女性寫作中沉靜、溫婉而在內里又孕育著力量的一脈。當然,同時代作家之間也會形成一個大的文學場,而把他們放入這個大的文學場域中可以看到不同個體的文學書寫提供的經驗與存在的問題,比如同為先鋒作家,馬原的敘事圈套、余華的暴力演繹、格非的斷裂敘事、蘇童的家族傳奇、孫甘露的語言游戲等,都構成了“先鋒”的不同面相,而他們轉向后的寫作,也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總之,在現當代文學的教學中有意識得梳理文學現象的知識譜系,一方面可以幫助學生建立他們完善的文學史譜系、作家譜系,另一方面,這種史學素養的形成,有助于他們增進歷史的理解力和對歷史的同情。從閱讀“經典”的文學作品開始,發現文學的魅力、重獲閱讀的樂趣;從建構文學史的知識譜系開始,厘清文學現象的歷史脈絡、了解文學書寫中中國經驗的演變;從關注當下文學創作開始,洞見紛繁復雜的現實、豐富個體的生命經驗。
作者:吳雪麗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