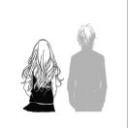現代詩歌與古代詩歌的意象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現代詩歌與古代詩歌的意象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凝合于自然的意象審美心理
在中外詩學范疇中,意象是一個內涵豐富,眾說紛紜的概念之一。但是,把意象作為一種心物交感互滲的審美產物的這一觀點是較普遍認可的。客觀物象是意象中的基本的要素,選擇什么樣的物象入詩,主體對物象取什么樣的心態,或物象引發主體什么樣的情感,可以因其異同透視詩人特有的文化心態與審美傾向,辨識意象藝術所蘊含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特征。中國古代詩人與中國現代詩人在意象的經營上有著鮮明的共性。首先,對自然物象的相親相近,詩人心靈與自然意象的凝合,是古今詩歌意象最為突出的共性特征,其中深刻烙印著傳統的文化心理情結。陸機在《文賦》中指出:“遵四時以嘆逝,贍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一位日本漢學家指出:“在中國古典詩里,季節與季節感作為題材與意象,幾乎構成了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設想一下,從歷來被視為古今絕唱的諸作品中除掉這一要素會如何,這種不可或缺的程度立刻就會清楚了。”①古代詩歌中的季節感特別突出。如春秋意象,從《詩經》、《楚辭》以來,頻繁出現的是傷春、悲春、惜春、嘆春、春恨、春愁;悲秋、驚秋、秋懷、秋思等。
季節感的產生又是與自然意象緊密相關的。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自然意象現象構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其中包含了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與審美意趣。這種自然意象情結源遠流長。據三國吳人陸璣統計,《詩經》中寫到自然意象之草木凡八十余種,鳥獸凡三十余種,蟲魚凡三十種②。當代詩人流沙河統計,僅毛公所標明之《詩經》之“興”詩,共三百八十九種意象,其取材于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者,凡三百四十九種③。此種現象,與幾乎同時期的古希臘史詩,多述海上之征伐,社會人事之沖突,顯然大異其趣。司馬遷云:“《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以達意”④,這也正是看到了詩之原典所呈現的人與自然之生命共感所形成的詩的自然意象現象。詩人或聽蟋蟀鳴歲,感光陰之逝(《秦風•蟋蟀》);或睹鳥兒入林,傷夫君之未歸(《秦風•晨風》);或因風中飄葉,興男女之依戀(《鄭風•兮》)。自然的豐富意象形態與人的心靈的豐富情感構成了互感與交融。在中國古代哲學文化觀念中,自然物象是具有人本意義的。人與自然有著自然感性生命的同一。如:《尚書•洪范》將大自然之“五行”與人之“五味”相對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鄭子產所謂“六志”生于“六氣”說。莊子齊物論思想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物不是純然外在的客體,物象和人之間存在著心心相印的聯系,人的心靈世界和外在物象的感性品質之間構成了一種互相映照、感應的關系。因此,主體心靈總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內心情感的對應。蘇軾曾說:“寓意于物則樂,留意于物則病”,指的就是詩人多在具體的物象間悟道達意、表情言志的現象。
這樣一種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學文化基礎之上的心物相感的特征,是與由自然經濟構成的農業文化心態緊密相關的。只有在農業文化心態中,人們才能對人與自然之生命節律,抱有親切的認同與不言而喻的意會。中國的內陸農業經濟,以土地自然物為限,與水土、風雨、陽光等自然資源關系緊密。而華夏民族賴以生存的中原一帶,又以溫帶之優越氣候,黃土之肥沃,水利之便利,自然資源之豐富,優于其他文明發源地。像以巴爾干半島、愛琴海為生態基礎的古希臘人,由于土地貧瘠,資源貧乏,氣候惡劣,在對外界不斷的抗爭與奪取的生存競爭中,逐漸形成了人對大自然的征服、奴役、占有的態度。正如黑格爾所說:希臘人一方面“在自然面前茫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又學會了“勇悍地、自強地反抗外界”⑤。而中國古代先民,則在長期的農耕生產過程中,遵守節氣,留心季節氣候,觀察日月星辰意象,逐漸形成了與大自然生命相依的心態。外部自然世界的風云變幻、花開花落、日月輪回等都能引起人們產生一種生命的共感。因此,中西文化意識中,自然物象的地位、面貌是有較明顯區別的。西方文化對外在物象的認識一般不是確立在其與人的自然感性現象的一致性上的,外在物象一般不以其自然的感性品質進入西方文化意識中,只是作為人的精神理性的體現才有意義,自然是被人的自由意志所認識、所利用的,以其被改造的面目確證人的力量。
因此,在古希臘藝術中,自然是人格化的,西方古典藝術在本質上是“擬人主義”的。在基督教教義中,自然被認為是上帝對人類的饋贈,人類不應對自然表示過多關注而忘記了造物主。在基督教世界中有這樣一個三層次結構:上帝居上,人類居中,自然居下。總之,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西方文化一般強調的是人對自然的主宰。西方文化意識的種種表現皆是以自然與人的各自本體存在的關心為基礎的。中國哲學文化一般并不十分關心自然宇宙在本體存在意義上究竟是什么東西,它認為人既然處于自然宇宙之中,那么人的行動當然是應該與自然運行規律相一致。因此,它關心的是人與自然的合一、溝通。這樣一種自然與人的一元論哲學文化自然觀,直接化入了中國古代詩人的審美意識中。中國古代詩人不僅喜愛將自然意象作歌詠對象,而且大多表現出人與自然的物我相得,欣然融洽的意趣。如李白的“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獨坐敬亭山》),人與山相對無語,含情脈脈。辛棄疾的“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賀新郎》),人與山情貌相通,忘形爾汝。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游原》),凄艷的落日與黯淡心情相互對應,融為一體。這種深深烙印著中國文化意識的自然意象情結依然深深植根在中國現代詩歌意象之中。20年代的中國現代詩歌,整體上是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最初過渡期。
“五四”白話新詩運動中,胡適的新詩意象論從理論源頭看,是受到了英美意象派詩學觀的啟發。如果我們就他對意象的本質性闡釋看,他的意象論更多體現的是中國傳統意象詩學的感性論色彩,與西方意象派所包含的現代象征主義意象論有著較大的差異。他站在“文學革命”的立場上,為我所用的吸取了意象派的某些具體的主張,其中主要是采納具體鮮明的意象論反對晚清以來詩壇的陳腐守舊以及新詩初期的說理化傾向,并沒有采取西方象征意象重理性內涵的暗示性表現方法。他寫于1919年10月的《談新詩》一文中提出:“詩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的腦子里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像。這便是詩的具體性。”他所列舉的“具體性”的詩歌都是中國古代以自然為中心的意象化詩歌,如“綠垂紅折筍,風綻雨肥梅”,“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等。
宗白華1920年就新體詩的作法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說,詩人應在自然的活動中養成詩人人格,“直接觀察自然現象的過程,感覺自然的呼吸,窺測自然的神秘,聽自然的音調,觀自然的圖畫。風聲水聲松聲潮聲都是詩意詩境的范本”,詩的意境“就是詩人的心靈,與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觸映射時造成的直覺靈感”⑥。他把詩人心靈與自然的凝合看作是美的詩境與真詩好詩的源泉,極力肯定的是中國詩歌傳統中人的生命情意與詩的自然意象形態融化為一的契合。“五四”初期的新詩創作在意象化的探索上并沒有真正走出傳統詩歌的意象化的格局。到了郭沫若體的《女神》的出現,第一次造成了中國詩歌意象體系的某些現代性變化。《女神》的意象世界中自然意象仍占據中心的位置。詩人在自然意象中滲透了強烈的時代感與現代意識,極大地擴展了中國詩歌自然意象的審美境界。他酷愛大海,崇拜太陽。他在《浴海》一詩中寫道:“太陽當頂了!/無限的太平洋鼓奏著男性的音調!”“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我的心和日火同燒”。詩人主體的人格力量與情感宣泄與大自然融而為一,企望借自然之偉力完成自我的蛻變,實現新生命的創造。在郭沫若的眼里,“無限的大自然,/成了一個光海。/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光海》);眺望十里松原無數的古松,“他們一枝枝的手兒在空中戰栗,/我的一枝枝的神經纖維在身中戰栗”(《夜步十里松原》)。
自然與生命合一,宇宙外象的自然世界與個體生命內在世界的心物融契是《女神》最主要的,也是最具審美詩情的抒情方式。這一抒情方式既源于西方泛神論思想的影響,又與莊子齊物論的自然生命的哲學觀有著內在的聯系。《女神》是雄渾壯麗的自然意象與靜穆優美的自然意象的合奏與交響,沿襲了古代詩歌自然意象的感性抒情傳統,又給中國詩歌自然意象增添了崇高偉美的現代品格。也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朱自清稱道:“郭沫若先生歌詠大自然,是最特出的”⑦。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詩歌不滿意“五四”詩人盲從歐化的傾向,希望恢復“對于舊文學底信仰”與雅韻的東方文化的精神。新月派詩歌的意象審美選擇與價值觀體現也主要圍繞著自然意象的核心展開。聞一多在“紅燭”、“菊花”、“紅豆”等傳統自然意象中寄托自己理想情懷。徐志摩借快樂的“雪花”、飄逸的“云彩”、星光下的“白蓮”抒寫對美與愛的向往與留念。自然意象成了他們與中國雅韻文化精神與風騷詩歌傳統溝通的橋梁。在自然意象的傳統繼承中有他們的創造,這突出地表現為現代浪漫主義抒情詩人的人格化、性靈化在自然意象中的浸潤,自然意象成了詩人現代人格與現代性靈的凝合物,自然意象內涵聚合了傳統與現代多種復合的文化心理因素與美感因素。在30、40年代的詩歌潮流中,現代主義詩歌逐漸成了一股具有生氣與聲勢的詩潮,這種主要接受外來現代主義詩潮影響的詩歌,也同樣鮮明而深刻地表現出崇尚自然意象的文化心理與審美傾向。像戴望舒詩歌意象頻率出現最多的是:秋天、落葉、殘陽、月、花、燈等,自然意象在他的詩中占有絕對的優勢。
他鐘愛“秋”之意象:“秋天的夢是輕的,/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戀”,“但卻載著沉重的昔日”(《秋天的夢》)。“誰家動刀尺?心也需要秋衣”(《秋夜思》)。他詩中的秋夢、秋思皆是心靈惆悵、青春煩擾的象征,明顯體現了傳統詩歌“悲秋”情結的文化心理意識的積淀。卞之琳在評述戴望舒時說:“到郭沫若的草創時代,那時候白話新體詩的創始人還很難掙脫出文言舊體詩的老套。現在,在白話新體詩獲得了一個鞏固的立足點后,它是無所顧慮的有意接通我國詩的長期傳統,來利用年深月久,經過不斷體裁變化而傳下來的藝術遺產。”“傾向于把側重西方詩風的吸取倒過來為側重中國舊詩風的繼承。”⑧以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在中西意象傳統溝通中,自覺借鑒象征主義意象藝術,把中國傳統詩歌的感性化的單質性比喻意象發展為寄興的、隱喻式的象征性意象,他們在傳統的繼承中是有他們現代性創化的。
到40年代馮至的《十四行集》,他的詩歌在自然意象與生命體驗的深度凝合中,把中國詩歌自然意象的內在品質與外在形態的呈現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他說:“有些自然現象,它們給我許多啟示”,“凡是和我的生命發生深切的關聯的,對于每件事物寫出一首詩”⑨。在他的詩中處處表現的是自然萬物的生命交流,人與自然的息息相通:“哪條路、哪道水,沒有關聯,/哪陣風、哪片云,沒有呼應:/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第十六首)。自然意象“在生命的深處”與“我們”發生“意味不盡的關聯”⑩。馮至詩中這種心物合一的生命體驗既接受了西方存在主義哲學觀的影響,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國禪宗哲學文化的烙印。自然意象不僅是一種感性生命的外化,而且與生命打成一片,直接成為了生命永恒的象征,傳統自然意象在馮至手里獲得了感性生命與理性智慧的同一的內在品質。
九葉派詩歌沿著馮至的意象化方向進一步開拓,他們的詩歌關于生命的主題,依然與自然意象為核心,不過他們在自然意象的傳統因素中賦予了更多新的品質與內涵。同樣是秋天的意象,鄭敏筆下的“金黃的稻束站在/割過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無數個疲倦的母親”,她并沒有停留在秋的自然意象的感性情緒的表達上,而是引向時間,指向生命,表達一種理性沉思,“歷史不過是/腳下一條流去的小河/而你們,站在那兒/將成了人類的一個思想”(《金黃的稻束》)。再看穆旦的“春”之意象:“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它渴望著擁抱你,花朵”,“光,影,聲,色,都已經赤裸,/痛苦者,等待伸入新的組合”(《春》)。春是生命欲望的象征,它表達的是一種與青春生命同質的肉感的生命的體驗,顯然,它與傳統的“傷春”情結毫無瓜葛,使傳統的自然意象更富有鮮活的生命氣息與現代色彩,給傳統的自然意象輸入了新鮮的血液,它較出色地體現了中國詩歌自然意象深度的內質性的現代嬗變。如鄭敏的《樹》:“我從來沒有真正聽見聲音,/像我聽見樹的聲音”,“即使在黑暗的冬夜里,/你走過它也應當像/走過一個失去民族自由的人民/你聽不見那封鎖在血里的聲音嗎?/當春天來到時/它的每一只強壯的手臂里/埋藏著千百個啼擾的嬰兒”。這里的自然意象把現實的人生感受、時代的民族情緒,歷史嬗變的規律,生命蛻變的永恒哲理高度凝合,是九葉派“現實、象征、哲理”這一詩學原則的典型的體現,也是現代詩歌自然意象藝術的新的境界與新的開拓。
二感物興會的意象思維
在中國古代詩學看來,意象是情與景的統一,心與物的渾融。情與景的統一,心與物的交融過程就是意象思維的過程,意象是意象思維物化的結晶,或者說就是主體通過感觀接觸外物之后所引發的想象、體驗而形成于心中的意象。先秦的《禮記•樂記》最早從心物交感的角度來論述音樂的本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質在人心之感于物者也。”強調的就是物對人的感發作用。鐘嶸《詩品》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他們講的這樣一種心物交感過程中的感物興會、情以物興的詩之生成方式就是詩的意象思維的特征。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中更加深入一步地闡釋了心物交感、“睹物興情”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過程。一方面是“情以物興”,作者的情因物的感觸而起興,在觀察或接觸外境萬物之時,物引發作者的感受、誘發他的想象,物是起主導作用的。另一方面是“物以情觀”,從“物”的角度看,它不僅僅為了表達自身,而且是作為“情”的體現者而出現的。感物的意象生成作用,決不僅僅是“物”本身,而且它的指向與根本意義還在于物所蘊蓄或所激發的情思。他還進一步地闡述了“隨物婉轉”的意象思維規律:“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婉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他突出的是作家主體遵從客觀“物”的內在之“勢”,因物變而情遷,使心與物適應、混融,達到化境。
這同西方詩學中主要突出客觀物象作為人主體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人對物的主宰,意對象的支配的文化心理與思維定勢是有著本質區別的。中國詩學傳統也要求物隨心動,景因情變,“與心徘徊”,但它是以感物為前提的,是情景相生的相輔相成,是“情無景不生”。作為感物的傳統思維方式,它對中國詩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情”與“物”的關系中的藝術呈現方式。這種呈現方式主要體現為比興的意象思維特征,尤其是“興”的詩性思維形式。有學者認為:“比興用于詩歌創作,最初并非出于修辭學上的動機,而是由比興所代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11比興的方法是一種建立在心物關系的認識論基礎上的詩性思維方式。葉嘉瑩在《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之關系例說》中認為,在賦、比、興三種詩歌表達方式中,“比”和“興”兩種作法,都明顯體現了“情感”與“形象”,“比”與“物”相互感發的關系。她認為“興”的作用大多是“物”的觸引在先,“心”的情意感發在后。“興”的感發大多是由于感性的直覺的觸引,而不必有理性的思考安排。“興”的感發多是自然的、無意的○12。葉嘉瑩將感物的思維與比興的方法直接聯系,把比興作為中國詩歌感物傳統的詩性思維方法是極有見地的。她對賦比興的闡釋,引宋李仲蒙說,從心物關系上探討他們寫物的關系:“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這種“敘物”,特別是“索物”、“觸物”的詩思方式,正是中國詩歌傳統的意象思維方式,這一意象詩思方式對中國現代詩歌發生著深刻的影響。中國現代詩歌受感物的意象思維方式的影響,首先表現為“感物起情”的意象詩思形式。所謂“感物起情”既包含了先言他物,以引起詩情,又包含有索物為比,情附物中的意象思維方式。也正如古人所云“比者,比方于物也;興者,托事于物也”○13。
“比則取物為比,興則托物興詞。”○14從“五四”開始至40年代感物起情的意象思維模式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繁復的發展過程。如胡適的《湖上》就是感物起興:“水上一個螢火,/水里一個螢火”,接下是描繪螢火蟲越飛越遠,“漸漸地并作了一個”。在觸景生情,感物賦情的詩思中,他不點破情感,把情緒的表現寄寓在意象的客觀呈示中,有一點意象派的意味。像戴望舒的《樂園鳥》體現了比興兼有的意象思維特征:“飛著,飛著,春,夏,秋,冬,/晝、夜,沒有休止”,由樂園鳥終年無有休止的漫飛引發對“樂園鳥”憂樂的追問與命運的關切,象征性表達生命旅途的復雜感慨。感物起興的現代意象思維形式,在不少詩歌中不是一種簡單顯現,一首詩所感之物或起興之物往往不是一種,所引發的情感也不是單向的貫串到底,由這種起情之物的更替出現而生成的詩情也隨之起伏變化,詩情顯得更加豐富復雜,形成一種復合多層的感物起興的意象思維模式。這類意象模式借比興的運用,靠藝術的聯想把多重相關意象連接在一起。如卞之琳的《白螺殼》,由“空靈的白螺殼”起興,引發的是“掌心里波濤洶涌”的感慨,接下由此轉向“大海”,生發出“我感嘆你的神工,/你的慧心”。在此,意象出現了轉換挪位。在一般的意象化的現代詩歌中,每一個相互聯系的意象系列中或形成意象的主輔關系,或構成意象的對應關系,起到意象之間的映襯、烘托、強化或對比、類比、集合的作用。
如戴望舒的《印象》,用飄落深谷的“鈴聲”,航到煙水去的“漁船”,落到古井暗水里的“真珠”作為并列的聚合意象,構成一種相關情緒的模糊體驗,營造出情感意緒的朦朧迷離之美。中國現代詩歌的復合多層意象思維模式比起古代詩歌的意象結構來,顯得自由、復雜,更適合現代生活與現代人的情感表現。像古代詩歌中的意象之間的關系及其所表達的內蘊要明朗一些,如“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李白《贈孟浩然》),這是意象思維的平行展開,上句寫孟浩然的青年時代,下句寫他的老年時代。“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登高》),這是空間的廣闊與時間的悠長的意象組接,表達一種秋色無邊無際的感慨。現代意象思維的規則是少了,但它的多重性多樣性體現的是與現代人思想情緒的豐富性、復雜性的一致與統一。感物興會的意象思維方式的另一種形態則是感物興思,它與感物起情一道共同構成了感物的意象思維方式的完整內涵。感物所興常常不只是情感或情緒,詩人因“觸物”而引發對社會人生、宇宙、生命的智性體驗與哲理的沉思,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感物興思的意象思維形式。在中國古代詩歌中這類意象思維的詩也是大量存在的。
像李商隱的“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游原》),觸物抒懷,將家國之感、身世之慨與時光流逝之嘆熔為一爐,情景與哲思化而為一,耐人尋思。“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李商隱《無題》二首之一),“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劉禹錫《酬樂天揚州逢席上有贈》),也是托物興思,索物為比,比中興思的意象化表現。中國現代詩歌中的感物興思的詩思模式與古代詩歌一脈相承,然而,比起古代詩歌來現代詩歌的感物興思更加繁復,它較多地受到了西方象征主義、現代主義意象詩思的影響,感物興思常常體現為意象的隱喻結構,或隱喻意象思維,這種意象隱喻不暗示情感,而是隱含人生經驗或生命體驗。像辛笛的《航》,先感物起興:“帆起了/帆向落日的去處/明凈與古老/風帆吻著暗色的水/青色的蛇/弄著銀色的珠”。由此興發出生命旅程的感慨與思考:“從日到夜/從夜到日/我們航不出這圓圈/后一個圓/前一個圓/一個永恒/而無涯的圓圈”。陳敬容的《律動》,由一組并行意象作為感發對象:“水波的起伏,/雨聲的斷續,/遠鐘的悠揚”,“宇宙呼吸著,/我呼吸著;/一株草,一只螞蟻/也呼吸著。”最后升發出“宇宙永在著,/生命永在著,/律動,永在著”,一切生命本質與意義都在生命萬物的律動之中。像穆旦的《春》一開始起興之物就是托比興思,比中寓思,“綠色的火焰在草上搖曳,/他渴望著擁抱你,花朵”,接下轉向“花朵”“反抗著土地,花朵伸出來”,再由花朵引出暖風,暖風吹醒“滿園的欲望”,由春天里自然欲望的蘇醒流轉到20歲青春的“緊閉的肉體”被點燃,卻無處歸依。最后升發出春天里一切生命蘇生中的渴望:“呵,光,影,聲,色,都已經赤裸,/痛苦著,等待伸入新的組合。”意象層層遞進,思維隨物婉轉,所感之物與所興之思高度融合,給人興會無窮的感受。詩的意象思維不是單線直進,也不是平面平行展開,而是一種曲線流轉,容涵了更為豐富的人生體驗。
可以說這是現代詩歌的一種高層意象象征藝術。這一類詩歌在現代詩歌中并不多見,在40年代九葉詩人的創作中的出現,是現代詩歌意象藝術逐步成熟的體現。感物興會的意象思維體現了中國古代詩歌與現代詩歌在詩歌本體上的內在聯系。有學者指出:“從興產生以后,詩歌藝術才正式走上主觀思想感情客觀化、物象化的道路,并逐漸達到了情景相生、物我渾然、思與境偕的主客觀統一的完美境地,最后完成詩歌與藝術特殊的本質的要求。”○15現代詩歌對傳統的感物興會意象思維方法的倚重的原因,還在于他們感受到了或自覺到了“興”與“象征”的聯系。“五四”白話新詩運動中出現了一系列詩歌形式上的問題:淺顯的寫景,刻板的紀實,說教似的議論,想象的貧乏,體式的散漫等,這些都擺在20年代新詩建設者面前。特別關注新詩建設的周作人與聞一多不約而同地看到了中國古代詩歌的“興”與西方現代詩中的“象征”的暗合與聯系。周作人在1926年為劉半農的《揚鞭集》作序時指出:“新詩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歡嘮叨的敘事,不必說嘮叨的說理,我只認抒情是詩的本分,而寫法則覺得所謂‘興’最有意思,用新名詞來講或可以說是象征。”聞一多在《說魚》中指出:“西洋人所謂意象,象征,都是同類的東西,而用中國術語說來,實在都是隱。”而“隱在《六經》中相當于《易》的‘象’和《詩》的‘興’”○16。周作人與聞一多把“興”與象征等同,顯然缺乏周嚴的辨析,忽略了它們之間的相異,但是他們都揭示了二者之間相通的內在因素是“隱”,看到了“隱”能增加詩的含蓄性。并把中國傳統詩學中的“興”同西方現代詩學范疇“象征”相聯系,找到了中西詩學相通的交融點,把“象征”的借鑒與繼承作了新詩建設的重要途徑。這對后來新詩的感物的意象思維的發展是有著重要影響的。
三意境化的意象旨趣
在意象藝術上,中國古代詩歌對中國現代詩歌的影響還突出表現在意象藝術的審美價值傾向上,這就是詩人借意象的整合,創造出一個意象之間有機融合、虛實相生、具有象外之象,激發讀者主觀聯想的一種審美的深層境界,即意象的意境化的審美理想境界。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意象和意境是密不可分的。“境生于象外”(劉禹錫),一般認為意境是由意象群組合而成的,它是一首詩中諸多意象渾然融合而生成的一種藝術境界。如果說意象只是抒情主體主觀情意與客觀物象的個別性的融合,那么意境則是主觀情意與客觀物象的整體性的融合。意境所顯示的是在具體生動的意象畫面的組合中,一個能激活觀賞者想象的藝術空間。王國維認為:“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意勝,或以境勝。茍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17王國維把“意與境渾”作為意境生成的最佳境界,也視之為文學足以感人的上乘之作的準則。將意境美作為意象藝術的審美理想的詩學傳統,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現代詩歌意象的審美價值取向。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詩人在意象的有機性聯系中,追求意象系統的整一渾成的意境之美。
意境構成的基礎是情景交融,情景渾成則生成意境,情與景格格不入則無意境可言。意象的意境之美,體現在一首詩的意象結構系統中,在意象之間的情感或情緒體驗的內在聯系中。無論意象結構的關系多么復雜,意象之間必須有它一以貫之的內在意脈的聯系,意象的共同旨趣在統一渾融的意境營造。在西方詩歌傳統中,特別是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不大注重意象之間構成的整體性蘊含,也不強調追求意象組合之外的象外之境。他們習慣將意象作智性化處理。特別是現代主義詩學多把意象作為思想的對應物,意象背后所隱藏的東西,讀者必須冷靜思索,理性分析。中國詩歌的傳統思維注重的是直覺感悟、模糊體驗,講究妙悟神思、心解了悟。這樣一種傳統思維方式積淀為一種文化心理與審美心理定式,給中國現代詩人以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詩歌的意象意境化在唐代是最有成就的。像李白的《望天門山》: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整篇沒有一句抒情的言辭,皆為意象呈示。作者選取的是,對峙的天門山,奔騰的東流水,遠望中的太陽,一片直下的孤帆。四種意象組成一種雄渾壯闊激蕩的境界,詩人青年時期開朗、奮進、昂揚的心態流露其間。這一組意象情與景相兼相愜,渾然一體,折射出一種昂揚奮發的盛唐時代的人文精神與審美風韻。宋人司馬光《詩話》中評杜甫《春望》一詩時說:“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近世謂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此言山河在,明無余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全篇詩歌一片凄楚荒涼意象,傳達出感時傷亂的憂患與悲愴之情,營造出一種令人無限感傷的意境之美。中國現代詩歌中的意象構成,受傳統詩歌的影響,十分注重意象之間的有機性聯系,注重意象內涵品質層面的同一性或意象情調與情感色彩的統一性,在意象的渾然整合中給人以“象外之象”、意外之旨的意境美的感受。像何其芳的早期詩集《預言》中的代表性詩篇,是以意境美為意象價值追求的典范之作。《月下》一詩寫“銀色”的夢境,“如白鴿展開沐浴的雙翅,/又如素蓮從水影里墜下的花瓣,如從琉璃似的梧桐葉/流到積霜的瓦上的秋聲”,夢如“一只順風的船”,盼望駛到她“凍結的夜里”去。感覺的意象化的多向展開,集中營構的是一個渾融的愛之沉醉、愛之神秘的意境之美。一般來說,現代詩歌比起古代詩來,有時體現為一種更為復雜的意象關系層次,往往一首詩包含有幾種不同情感色彩或思想質地蘊含的意象群,構成多重意象時空組合,達到對比、烘托或突出強調的作用,營造出一種具有復雜蘊含的審美意境。
像徐志摩的意象化抒情詩《再別康橋》,就是兩組意象化意境:由西天的云彩、河畔的金柳,夕陽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艷影、軟泥上的青荇、榆蔭下的清泉、斑斕的星輝等構成清新優美的意象系列,營造的是對康橋理想的無限眷戀的意境之美。另一組意象是從夢境般的憶念回落到現實的情景意象:別離的笙簫、沉默的夏蟲、無語的康橋等,是一組感傷寂寞的意象群,傳達的是理想失落后無限惆悵與迷惘之情。兩組意象系列形成對比,強化詩人主體對康橋理想的眷戀與惜別之情以及現實的感傷落寞的情懷。整個詩還具有激發讀者深思的潛在意境之美:康橋理想是詩人致力追求與畢生向往的精神之圣境,是詩人唯美的人生與唯美的藝術之境的象征,是徐志摩的精神之戀與心靈的家園,“再別”康橋,蘊含了徐志摩“西天的云彩”幻滅后的無限的心靈之痛與精神之苦,是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理想幻滅的挽歌。意境的虛幻空間作為一種審美的召喚結構,可以激發讀者的意境化的審美聯想性感受。戴望舒的《雨巷》也是這樣一首意境化的現代經典之作。意象的虛實相生而形成的意境的空靈之美是意象意境化的又一特征。一般認為,意境的形成是諸多藝術因素相生的結果。
主要由意象及其表現的藝術情趣、藝術氛圍以及可能觸發的藝術聯想所形成。簡而言之,由“象外之象”而生成“象外之境”。這種虛實相生的詩學觀有著久遠的思想淵源。《易經》的乾坤感蕩,陰陽相推的觀點,老子的“有無互立”、“大音希聲”的思想,荀子的“形而具神生”的主張,至魏晉哲學中的“得意忘象”、“寄言出意”的玄論,都是意象與意境虛實轉化論的哲學思想資源。詩歌的意境實際是由意象組合而生成的實境與虛境的結合。意境是由可以捉摸之“象”(或象內)與不易捉摸之“象外”的結合。可以捉摸之象是指詩人用語言描繪出來、為欣賞者可以還原的具象,而“象外”是指欣賞者在象的激活下聯想到的更豐富的內容。這也就是司空圖所言“象外之象”,“象”是顯意象,象外之象為潛意象,意境是雙重意象機制化合而生成的結晶。意象的意境化生成主要由于潛意象的作用,具體轉化而為虛幻或空洞的意境(虛境)之美。當然整體上離不開顯意象的觸發或外在顯示,它仍是虛實相生的結果。如元稹的《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話說玄宗。”宋人洪邁稱其“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詩中取象少而精,并在“閑話說玄宗”中升發隱情,給讀者無盡遐想,讓人在撫今追思的聯想中體會江山易代之感。再看杜牧的《江南春絕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廓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眼前江南春色繽紛,可詩人感懷的是歷史興衰,廣闊的空間與悠遠的時間相互交織,現實景觀與歷史追憶共生共存,讀者想象的翅膀飛翔在歷史的治亂興衰的長河中,可謂意境幽深廣遠,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的美感。
這種意象的組合而生成的虛實相生的意境之美在中國現代詩歌中是一種常見的審美境界。像廢名的詩《花盆》中的春草、樹、種子、植樹人是生命的意象,而池塘、墓、花缽是與生命相對的生命歸宿意象。全詩由六朝謝靈運的《登池上樓》詩句引發感興,一方面表現詩人愛憐自然天籟之美的禪意,另一方面面對生意盎然的自然界,又讓人產生一種人生易老、向往化歸自然的感慨,在意象的流動與組合中形成了特有的虛實相生的意象化意境。在形式上采用對白,類似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戲擬,但由意象組合而生成的淡泊、寧靜、寂滅的意境卻是中國傳統詩歌的。廢名的《星》、《十二月十九夜》、《掐花》等都具有虛實相生的意象化意境之美。這與他受禪宗影響,注重冥思玄想的詩思特征有關,也有他推崇的晚唐詩風的影響。卞之琳曾回憶他30年代的寫詩經驗:“我寫詩總富于懷舊,懷遠的情調”,“我總喜歡表達我國舊說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說的‘戲劇性處境’”○18。
卞之琳在30年代的詩作很少直陳人事或直抒情感,多在客觀化的意象組合中,表達普遍性的情緒體驗或人生哲理,這種意象暗示出的情緒體驗或人生哲理,是他所喜歡表達的意境,是一種區別于意象的情感化意境,即我們稱之的意象的哲理化意境。如《魚化石》采用了較典型的“戲擬”方式,意象具有了可替代性的內涵,他所要表達的哲理意境更具有了某種玄秘性特征。作者在詩題“魚化石”下用括號注明“一條魚或一個女子說”。詩中的發話主體意象“我”可以是魚,也可以是一個女子。詩人通過“戲擬”的敘述與意象的不確定性要達到的是非個性化的表現。從意象的模糊性轉換與對置的關系中升華出具有形而上意義的相對性人生哲理:“從盆水里看雨花石,水紋溶溶,花紋也溶溶”○19,意象的可變性與多義性想象空間造成哲理意境的模糊性與玄妙性,正是卞之琳有意追求的境界。這一類意象的哲理化意境既有中國傳統的意境詩學的影響,也明顯化入了西方現代主義智性化與戲劇性處境的詩學論的因素,是中國意象藝術的一個深層次的發展。它直接影響了40年代馮至與九葉派詩人的創作。馮至40年代初期的《十四行集》走的與卞之琳是同一條道路,他在感性的生命化的意象的整體性凝合中,激發出一種象外之象的生命意義的冥想與玄思,既有哲理意境,又有一種繞人心靈,令人感動的情韻,形成了一種哲思意境與情感意境統一的境界之美。
如第二十一首詩寫道:“我們聽著狂風里的暴雨,我們在燈光下這樣的孤單”,人感到了與自己身外一切東西的對立與分離,身邊無比親近的東西也變得與人有了“千里萬里的距離”,它們各自向往本原的回歸,“銅爐在向往深山的礦苗,瓷壺在向往江邊的陶泥”。馮至在詩中表達的是個體生命的孤獨體驗,呈現的是一種沉郁悲涼的意境之美。意境化的意象旨趣是與中國詩歌的比興意象思維或感性化的悟覺思維有著不可分的聯系的。詩歌的意境是詩性思維的產物,在意境的生成過程中,思維起著重要的作用。從選擇意象到意象的結構以及其他藝術手段的運用,皆凝聚著思維的心血。悟覺思維是一種創造性的直覺思維方式,它與比興思維的共同之處在于皆是一種建立在物感論基礎上的,一種以意象為基礎,情感為中介,理趣為歸宿的藝術思維方式,它包涵感性直覺、理性直覺,并以妙悟為最佳形態,追求一種空靈玄妙、情景渾融的意境之美。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論文化傳統之上的創造性直覺思維方式與思維狀態,對中國古代、現代詩歌思維的影響與意象意境化的創造是有著潛在性的深刻作用的。嚴羽在《滄浪詩話》中道:“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之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相,言有盡而意無窮”。詩中意境之美惟在妙悟之中。
中國現代詩歌中的悟覺思維方式,在30年代現代派詩人廢名、卞之琳以及馮至等人的一些詩作中,是有較普遍性的體現的,當然其中也容納了西方某些智性化的思維因素。像馮至的《十四行集》中的第二十五首:“案頭擺設著用具,/架上陳列著書籍,/終日在些靜物里/我們不住地思慮。”由終日相伴的身邊的靜物的凝神觀照引發對自我的生命存在的感悟:“只有睡著的身體,/夜靜時起了韻律:/空氣在身內游戲,//海鹽在血里游戲———/睡夢里好像聽得到/天和海向我們呼叫。”由物到人,由外界到內心,意象聯絡呈現為一種直觀性的頓悟玄思的感受與體驗,傳達出一種對一切生命之物的本源及歸向的沉思默會,形成了一種玄幽的意境。在現代詩歌中,現代主義詩歌意象,比較起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詩歌來,一方面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詩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國現代主義詩歌與中國古代詩歌意象藝術傳統表現出一種更內在的深層聯系。這樣一種深層聯系正是中國現代詩歌在現代化探索中所葆有的民族性品質與民族性審美特征的根底之所在,也是現代詩歌生生不息,繁衍發展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