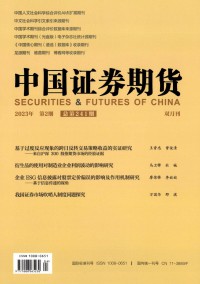證券爭議可仲裁性管理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證券爭議可仲裁性管理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可仲裁性問題是涉及仲裁程序能否進行的重要問題,除了一些爭議領域,各國對于可仲裁性問題都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而那些負隅頑抗的爭議領域,表面看似將可仲裁性抵制于千里之外,實質上很難抵擋可仲裁性“潤物細無聲”的侵入。反托拉斯領域的變化即為明證。值得注意的是,一國之內對于可仲裁性“爭議”基本上都是橫向的,鮮有縱向的。因此,美國證券爭議的可仲裁性問題就顯得別有韻味。一方面,證券領域是傳統抵制可仲裁性領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法中先后出現了兩種對于證券爭議的可仲裁性的不同態度,而對于這兩種不同的法律規定發生沖突時并沒有明確的法律適用條款。因此,美國證券爭議可仲裁性的發展可謂是內外交困,一波三折。不過美國對于“內外交困”的突破符合國際商事仲裁發展的一般規律,即先在國際領域取得勝利,再慢慢由國際而延伸至國內。
首先對于可仲裁問題作出規定的就是《聯邦證券法》。1929年美國證券市場大崩潰以后,美國國會于1933年出臺了《聯邦證券法》。該法考慮到證券投資者和證券經紀人談判能力的差異,授權投資者將其與證券經紀人之間的爭議提交聯邦法院。除此以外,與可仲裁性問題聯系更為緊密的是《聯邦證券法》規定,聯邦法院對于此類爭議的管轄權是排他的。排他不僅是排除聯邦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更是排除了當事人將此類爭議提交仲裁的可能性。然而,這種本是出于保護投資者的規定并沒有博得投資者的歡心:此種排他管轄權規定出臺以后,很多證券交易合同中仍然訂入了仲裁條款。出現這種態勢兼具內發和外推的因素:內發是由于證券領域爭議所涉數額相對較小,當事人希望快速便捷地解決;外部推動力量就是聯邦支持仲裁政策的影響以及對仲裁認識的不斷深化。這種態勢表面看來是立法和實踐的矛盾,實質上是主觀可仲裁性對客觀可仲裁性發展提出要求的外部表現。正是由于主觀可仲裁性對于客觀可仲裁性的渴望及召喚,《聯邦仲裁法》應運而生。《聯邦仲裁法》在可仲裁性問題上最大的貢獻在于:該法規定了當事人之間的仲裁協議是有效的、不可推翻的和可執行的。至此,證券爭議的可仲裁性就出現了兩種并行的同一效力等級的法律規定:一方面,《聯邦證券法》著眼于穩固整個美國證券市場以及保護投資者的需要,禁止當事人通過仲裁協議放棄司法訴訟權利;另一方面,《聯邦仲裁法》是支持仲裁政策的產物,賦予當事人之間的仲裁協議與其他合同性質的協議以同等效力。
面對并行而又相互矛盾的法律規定,法院在威爾可案件中首次就沖突時的法律適用問題作出了明確的論述。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中將仲裁協議視為一種“約定”,而司法訴訟權利則是不可放棄的“規定”。以“約定”放棄本不能放棄的“規定”被法院視為規避國會立法行為。可見,美國最高法院當時的態度是《聯邦證券法》優先適用于《聯邦仲裁法》。但是,該判決并沒有真正解決《聯邦證券法》和《聯邦仲裁法》之間的沖突。雖然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聯邦法主張不能提交仲裁,但對于附屬主張以及州法主張和普通法主張(該州法主張和普通法主張與聯邦法主張源于同樣的事實)能否提交仲裁并沒有論及。此點遺漏導致巡回法院對此問題產生了“同一論”和“二分法”的分歧:一些法院認為州法主張和普通法主張應同聯邦法主張一起歸于聯邦法院。如果與聯邦仲裁有關的事項通過仲裁或在州法院處理,將會剝奪聯邦法院的排他管轄權。而另一些法院則認為在聯邦法主張經過司法解決后,附屬主張應歸于仲裁。這就使暫時歸于平息的證券爭議的可仲裁性問題,仍然留下了懸而未決的問題。
隨著證券業的發展、證券自律性組織的增強以及仲裁產業的勃興,美國率先在國際商事領域取消了對仲裁解決證券爭議的限制,這一態度轉變的標志就是碩克案。該案中的仲裁協議是一份徹底的國際協定,這一點完全有別于威爾可案。面對這樣一份國際協定,法院指出,要實現國際商事交易的可預見性和有序性,當事人爭議前的法律選擇和法院選擇條款必須予以尊重。可見,從威爾可案到碩克案法院不自覺地穿插了一種利益分析方法:在威爾克案中法院視投資者利益的保護高于一切;而碩克案中雖然也涉及到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問題,但此時保護國際商事交易的可預見性和有序性的重要性顯然超過了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問題。碩克案標志著證券爭議至少在國際領域取得了可仲裁性,由此開始了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的區分。
碩克案之后,證券交易爭議的可仲裁性仍然在進一步發展。發展的趨向就是由國際引至國內。先是美國最高法院在1987年謝爾森案中認定,依1934年《聯邦證券交易法》提出的請求即使在純國內案件中也可以仲裁;1989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又直接推翻了1953年威爾克案的原則,認定依1933年《聯邦證券法》產生的請求在國內案件中也是可仲裁的。至此,美國的證券爭議無論是在國際領域還是在國內領域都具備了完全的可仲裁性,遺留的懸而未覺的問題也就失去了繼續探討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