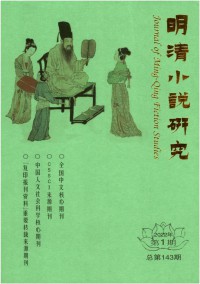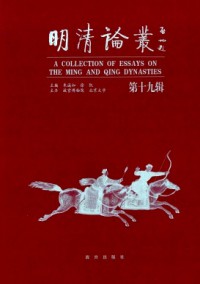明清時期少數民族繪畫鑒賞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明清時期少數民族繪畫鑒賞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在云南省博物館的藏畫中,有一些明清之際的作品,用傳統技法表現了當時云南少數民族的風俗,如反映明代云貴地區苗族節日歌舞斗牛盛況的《斗牛圖》;清代苗族的《百苗全圖》、《百蠻圖》,傣族的《寫經圖》、《騎象圖》,彝族的《踏歌圖》,哈尼族的《采茶圖》以及《清代少數民族風俗畫屏》,《開化府圖說》、《普洱府圖說》等等。這些畫均采用國畫的技巧、設色,技法粗獷,用工筆墨的技藝,刻劃出當時在民族地區的民俗和風情,亦可看出在另一方面各階層中生活等級情況。如:象是幸福吉祥的象征,騎大象,并有驅象者,只有在上層人物中才能有權力乘坐出游。這些少數民族風俗畫的作者多半名不見經傳,生平幾乎無從查考,但從其畫風技法和收集地多在內地來看,畫的作者可能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過的漢族畫家,在少數民族被歧視的歷史時代里,在山水花鳥畫充斥的畫壇中,畫家能用傳統的筆墨反映少數民族居住環境、生活習俗,實在難能可貴。這類作品不僅對研究少數民族的歷史風貌頗有價值,而且有助于了解清末云南美術史中一個鮮為人知的側面。云南省博物館收藏的這些明清書畫作品,我在《收藏家》雜志上也作了些陸續介紹,這次介紹的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云南省博物館在昆明市征集到的一組(6幅)反映云南少數民族生活畫卷的畫作,有《寫經圖》、《乘象圖》、《踏歌圖》、《沐浴圖》、《采檳榔圖》和《狩獵圖》。6幅皆為紙本設色,縱116.3、橫28厘米。作者不明,但從畫風來看,應是清代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漢族畫家所作。
圖1《采檳榔圖軸》。檳榔是熱帶地區少數民族,如傣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哈尼族等都喜愛嚼食的一種食物,特別是婦女,認為嚼食檳榔可以保護牙齒,對身體有益。長期嚼食檳榔,牙齒會變黑,所以明、清時期曾對嚼食檳榔的民族稱之為“黑齒蠻”,《蠻書》及其他史書也有過記載。《采檳榔圖》就真實記錄了邊疆少數民族采檳榔的這一情景。在一片檳榔樹叢中,一群男女正在忙于采摘檳榔:一裸露上身,穿短褲、跣足的男子正抱著檳榔樹桿往上爬;兩個裸露上身、穿短褲的男子各采摘了一串檳榔,呼喚著樹下人過來接拿;樹下一挽髻,穿短衣長袖,著條紋短裙、跣足的女子正用布袋接著欲往下拋的檳榔。另一裸露上身、穿短褲、跣足的男子跪在地上張開雙手欲接往下拋的檳榔,他的面前放著一袋采摘下來的檳榔,站在他身后的一男一女愉快的交談著什么,其中女子挽髻、穿短衣長袖、著條紋短裙、跣足,一手還拿著檳榔,側身站著,男子則身背一袋捆扎好的檳榔欲往回走;一挽髻、穿長衣、著短褲、跣足的男子跪著用一根繩子捆著裝入布袋的檳榔,神情專注;挽髻、穿短褲,背著檳榔準備回家的男子側身與捆扎檳榔的人打著招呼。畫面表現了采摘檳榔的整個場景—爬樹、采摘、捆扎、運送。人物描繪栩栩如生,畫面層次感強,分工明確,簡潔明了。從畫面描繪的人物和場景來看,應是生活在熱帶地區的少數民族,具體是當今什么民族還須進一步考證,但從服飾來看,也可能是生活在西雙版納的佤族或是哈尼族支系,因這兩個民族的服飾與畫面所描繪的服飾基本相同,而且直到今天,傣族、哈尼族、佤族、德昂族還有嚼食檳榔的習慣,所以這幅《采檳榔圖》,可能反映的就是哈尼族、佤族的一個生活場景。黑齒蠻以漆漆其齒“黑齒”、“漆齒”與嚼檳榔和石灰的習慣有關,由于長期嚼食,以致齒染為黑色。但這不僅限于傣族,佤、景頗等族也有此俗。不過《云南志》卷四說茫蠻“或漆齒”;又卷六提到茫乃時,同時提到黑齒部落,可見其中至少一部分是指傣族。
圖2《沐浴圖》。生活在熱帶雨林、水邊的傣族自古以來就是個愛美的民族,他們與水相融,每當傍晚太陽西下時,只要你走進傣族村寨,總能看到傣族婦女在河里沐浴洗澡的情景。《沐浴圖》就真實記錄了這一場景。整幅畫面共由四個部分組成:頭戴斗笠、披著披風、身穿長筒裙的兩個婦女由遠處款款而來,并且邊走邊談,衣著頗為華麗,似為貴族;大青樹下一挽髻女子坐于地上正把脫下的上衣放入筐內,裸露上身做沐浴前的準備,披著披風站立的女子與頭戴斗笠坐地吹簫的老婦在嬉鬧,另一頭戴斗笠的老婦抱胸坐于岸邊作觀浴狀,坐于水邊的女子,身穿彩色筒裙、裸露上身,行將下河就浴;河中三個女子正慢慢的邊脫筒裙邊走向深水區,另二個挽髻、豐乳的女子則站在沒至臍的水中歡快的洗浴并愉快的交談著;岸邊一裸露上身、彩色筒裙卷起系于腰間、身挎一只黃鱔籮的女子正彎腰在水草叢中專心致志的捉魚捉蝦。畫中共13人,各人神態不一。從畫中人物的服飾、沐浴的習俗等來看,畫面表現的應為傣族,因傣族居住地區氣候較為炎熱,傣族婦女愛水、愛美,自古以來養成注重衛生、浴于江河以潔身體的良好習俗,該畫忠實的描述了傣族婦女到河邊水浴的這一情景。表現了傣族人民的居住與水習習相關。而且由于該畫設色,又展示了清代傣族婦女艷麗多彩的服飾,同時表現了作者對傣族婦女愛美、愛潔的贊美,使人們對傣族的風土人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今天只要你走進西雙版納、德宏等地的傣族地區仍可看到這一情景。
圖3《踏歌圖》。今天只要進入云南。你就會被眾多的民族、五彩繽紛的各式各樣的民族服裝、載歌載舞的情景深深吸引住,讓你仿佛走進歌的海洋、舞的世界,自然不自然的融入到他們中間,與他們一道歡歌載舞。云南的少數民族從古至今,他們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無論節日喜慶、婚喪嫁娶、勞動之余、農閑之時,他們都要載歌載舞,用歌聲、舞步表達他們的心聲,無論史書、考古發掘、書畫作品等等都有真實的記錄。《踏歌圖》就是真實記錄了邊疆少數民族歡歌鶯舞踏歌的這一盛況:在郊外,有山有樹的大自然中,兩人自成一組,自娛自樂,整個畫面由四部分組成:坐在松樹下,纏著頭,身穿圓領衫、大短褲、綁腿、穿鞋的男子正彈著三弦;包頭、身穿斜襟長衣長褲的女子,正低聲吟唱著,他們相對而坐,邊彈邊唱,兩人中間還放有一瓶水和三盤食物,以備渴了、餓了之時享用;另一棵大松樹的樹根上盤腿坐著兩人:戴圓帽、身穿斜襟衣、系腰帶,一手拿著酒杯、一手拿著樂器的人盤腿坐著,面前放有酒杯、碗,似乎邊喝酒邊彈琴;兩腿相交坐于樹根邊沿的人正深情的吹著口弦;下面兩人正在忘情的跳舞,他們邊彈邊跳。頭戴圓帽、身穿斜襟衣、長褲、系腰帶的男子,兩手分別拿著一種樂器,左腳抬起,正翩翩起舞;頭纏包頭,斜挎掛包的則邊彈邊舞,舞姿優美、嫻熟,讓人禁不住的也想參與進去;另兩人好像已經跳夠、唱完,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頭戴斗笠,肩挎掛包的人用手指著前方,回頭跟手抱三弦的人說著什么。整幅畫描述了踏歌跳舞的情景,層次分明,含義深刻,并且對踏歌跳舞的整個過程都有了描述,從開始到結束,從平淡到高潮,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讓人記憶猶新。今天只要你走入民族地區,仍能看到這一情景,這不僅印證了歷史,對研究民族服飾、民族歌舞等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圖4《狩獵圖》。獵捕野獸,堪稱人類最古老的生產方式之一,并且從古至今延續不斷,縱觀歷史的“腳印”,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沒經歷過以狩獵為生的歷史階段,關于云南少數民族的狩獵史,漢代以前文字記載較少,但在考古發掘中皆有較詳細的實物記載。如:青銅器的箭鏃、弩機及長矛等。更具有說服力的是還出土了數十件反映狩獵場面的青銅飾物、器物。如:滇人獵鹿、滇人獵虎等。文字記載自漢以后,也逐漸增多,最為詳細的是唐人樊綽的《云南志》,涉及民族的幾乎沒有一個民族不進行狩獵活動的。《狩獵圖》更為形象逼真的反映了狩獵的整個過程。整個畫面由正在捕獵和滿載而歸兩部分組成。畫的上部分是兩個裸露上身的男子,正高喊著用梭鏢和弩弓射打奔跑著的馬,膘肥體壯的馬肚子和后腿被各射一箭,痛苦的掙扎著往山坡上奔跑。另一男子正用力吹響牛角號。在平緩的山道間,正走著滿載而歸的狩獵者,穿著長袖衣、短褲,肩負弩弓的男子正側身與背著籮筐、拿著牛角號和梭鏢的人講述著什么,邊講邊用手指著前方,一條狗在前面帶路。另兩個男子用木棍扛著四腳拴在木棍上獵獲的動物,前面頭戴斗笠、肩挎挎包的男子一手扶著木棍、一手扶著獵物,慢慢的往前走。后面一人右手扶著木棍,左手拿著弩弓,三條狗在他們前后左右跑來跑去。另三人一路走著:斜挎挎包、肩扛獵物的男子邊走邊往后看,一條小狗正抬頭看著他;隨后一人左手拿著梭鏢、右手拿著煙斗邊走邊吸著煙;背著背籮的男子正吃力的走著。整個畫面栩栩如生,既表現了狩獵的整個過程又展現了滿載而歸的情景。讓人既能感受到獰獵的激烈緊張,又能分享到成功所帶來的喜悅。今天只要你到山地民族中走走,仍能看到一些捕獵的場景。
圖5《寫經圖》。《寫經圖》描寫的是傣族僧侶在大青樹下寫經誦經的情景。整幅畫共由兩部份組成:上部樹下兩個傣族僧人相對而坐,中置葫蘆形黑陶小瓶一個。他們皆挽髻,分別穿黑、紅無領對襟衫,大小腿均刺有花紋,手拿著貝葉經,在讀誦經書。畫面的中部大樹下,在兩塊石頭上置有一木案,上放一葫蘆形陶瓶,還有一些貝葉。挽髻、披紅袈娑、紋身的佛爺坐于木案邊的地上,正用竹筆在貝葉上寫經,神態專一;旁立一披紅袈裟、紋身、手抱經書的小和尚正專心致志的看著,對面案旁則坐著一個挽髻、穿黑色無領對襟衣的男子,他也在全神貫注的看著寫經。整幅畫面真實地反映了古代傣族寫經誦經的活動。傣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燦爛的民族,不但有自已的語言,還有自己的文字,傣文的使用為時已久,通用的有傣那文和傣泐文兩種,傣那文流行于德宏及耿馬等地;傣泐文則流行于西雙版納及孟連等地,它們都系拼音文字,由印度南部巴利文演化而來,從左向右橫行書寫,形式以貝葉和手抄本書籍為主。在明代,專事翻譯少數民族文字的“四夷館”中即設有專譯傣文的“百夷館”(專譯傣那文)和“八百館”(專譯傣泐文)。可見當時兩種文字已為官方文牘往來所通用。《寫經圖》就真實的記錄了傣族刻貝葉經、誦經的場景。傣文大部份刻于貝葉上(貝葉是一種生長于熱帶、亞熱帶的棕櫚類木本植物的葉片,通過加工后,利用它來書寫和記錄經典文獻,特別是佛教傳入后,貝葉就被大量用來刻寫經文,大量的佛經故事、佛教經典、傣族民間故事、神話和傳說,都是記載在貝葉里,故也稱為貝葉經)。傣族利用貝葉保存和發展了他們的文化,西雙版納以前有佛寺500多座,保存的貝葉經多達50000多部。今天,各處佛寺還沿用古老方法制作貝葉經,在今天的傣族地區仍可看到這種刻經誦經的場景,因傣族全民信佛,男子一般都要到佛寺內學習傣文,以及相關的一些文化科學知識,佛教經典等等。千余年來流傳下來的這些貝葉經典文獻,反映了傣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也為研究傣族社會歷史、宗教信仰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重要的依據。這幅畫還記錄了傣族男子喜好紋身的這一習俗。紋身是古代越人的重要標志。早在先秦時期,史料就有傣族先祖越人紋身的記載,說越人常在江河湖海中捕撈,紋身可避蛟龍之害,表明越人紋身,與他們常在水下作業有關。傣族一直沿襲著這一古老的歷史習俗,但紋身的目的不再是為了避免蛟龍之害,而是一種帶有審美意義的民族標志。在傣族心目中,男人必須紋身才美。假如男子不紋身,必然會遭到人們的恥笑,認為他不是傣族,連姑娘也不愛。今天傣族男子紋身,其部位在胸、上肢和后背,所刺紋樣,有動物、花紋、文字等。史書曾有記載:繡腳蠻則于踝上腓下,周匝刻其膚為文彩。衣以緋衣,以青色為飾。繡面蠻初生后數月,以針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如繡狀。
圖6《乘象圖》。大象是傣族心目中最神圣的動物,據傣族創世史詩《巴塔麻嘎捧尚羅》記載,英叭神開天辟地之時,便用污垢捏制了一頭巨大無比的“掌月朗宛”(光芒四射的神圣大象)。創世史詩中的大象神奇威武,力大無窮。由于在開天辟地時立下了神功,傣族把它當作神靈崇拜。傣族民間還流傳有《七頭七尾象》、《金牙象》等許多與象有關的傳說。傳說中的象既神奇又與人的社會生活有著密切關系。《云南志》卷四“茫蠻”條說:“土俗養象以耕田”。至于象,用于載運,負重致遠;用于戰爭,沖鋒陷陣。《史記•大宛列傳》所說今洱海地區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便是指的這種情況,而“滇越”就是傣族的先民。早在漢初,傣族的先民“滇越”就已知道役使象,因而被稱為“乘象國”。傣族先民在2000多年前就馴化了大象,把大象運用于作戰、生產和乘騎。唐朝史料記載,今德宏地區“象大如水牛,土俗養象以耕田,仍燒其糞。”明清時期,大象是德宏土司敬獻朝廷的主要貢物。《百夷傳》描述了傣族領主乘象出巡時的盛況:領主貴族穿著華麗的衣服,每出入,象、馬仆從滿途。大象身上的皮帶上,飾有數十面銀鏡,邊緣全是銀釘。象鞍上有交椅,交椅之上有錦緞制的障蓋,四周懸掛著銅鈴。象奴坐在鞍后,手執長鉤駕馭大象。歷代的漢文古籍和傣文史籍,也有許多有關傣族地區盛產象的記載。先秦古籍《竹書記年》說:“越王使公師偶來獻犀角、象齒”,說明自秦漢以來,傣族先民便常以象和象牙進貢中原王朝。到了元、明時代,貢象之事則更為頻繁。據《明史》和《明實錄》載:洪武、永樂時期,僅從車里、景東、麓川、干崖、潞西等傣族地區進貢的象,便達80余頭,朱元璋為此專門設立了馴象所統一管理。傣族進入農耕生產之后,象或牛就成為最重要的農耕助手。此外,象還是傣族先民的戰爭利器。傣族古代戰爭離不開象,象隊是傣族古代的勁旅,象陣是傣族古代著名的兵法,這一點,史籍文獻均有記載。例如,有名的《厘俸》開篇便寫道:“海罕按照天意出征,威武的戰象在壩子里布成象陣”,戰爭開始后,只看見“象腳踏出一條條血路,染血的長鼻在風中飛舞”。史籍中,有關“養象用以乘騎,馴象用于戰爭”的記載也隨處可尋。傣族的先民百越族群在遠古時就與象結下了不解之緣。亞熱帶叢林中的象與生活在亞熱帶河谷平壩的傣族長期以來友好相處,傣族的土地是象的樂園;叢林中有象群,村寨和寺廟中有塑象,水井旁有塑象,壁畫和布畫中有象的圖畫,家里擺設中有各種象工藝品,貝葉經中有象的傳說故事,宗教節日中有賧白象總之,象崇拜滲透到傣族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傣族群眾心目中,白神象是最值得崇拜的,因為白神象是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和平安寧的象征,據說,白神象和谷魂住在一起,有密切的姻緣關系,所以白神象出現在哪里,哪里就消災除難、風調雨順,谷物豐收。白象除了消災除難,帶來風調雨順,谷物豐收外,還是傣族和平安寧的守護神,因為從游獵時期到農耕時期,各氏族部落為爭奪獵區,爭奪水源和土地,經常發生爭戰。而白象就是威力無比的守護神象。傣族群眾以各種方式來表示對象的崇拜,主要有:1.象雕塑。有佛象木雕、戰象木雕、家象木雕、象石雕和隨處可見的泥雕塑象。2.象織錦、象壁畫、象工藝美術品。象壁畫集中在佛寺的墻上,而最精美的藝術品要數傣族女手工織成的織錦上栩栩如生的象圖案。3.象音樂與象舞蹈。在傣族的節慶和宗教活動中,只要在群眾聚會的場所,都能聽到一陣陣有節律的鑼聲,都能看到象腳鼓舞和白象舞。
畫面描述了一頭正回首側視的大象背馱著口朝前開的竹鞍座,內坐著四人:一身穿無領衫、右手拿煙袋的老婦;一懷抱乳嬰、敞胸喂奶的少婦;一小孩正在嘻戲。竹鞍座內還放有雨傘、食物、包袱、水罐等物。象頸上坐著一執鞭驅象的馭者,上身袒裸、遍刺花紋,肩扛著一驅象長釣,似為趕象人。象旁則有一身穿短衣、下著褲,肩挑竹籮、跣足紋身的男子、似為仆從之屬。另一頭大象上騎有一頭戴斗笠、手執長釣、紋身的男子,象背上還馱著兩束直立的筒狀物,似為驅象運貨之狀。此畫反映了傣族上層婦女乘坐大象出游的情景。因大象在傣族人民生活中是吉祥和權威的象征。另還反映了清代云南傣族諸多習俗,如:男子紋身、吸食煙草等。整幅畫面人物表情刻畫較為細膩,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歷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