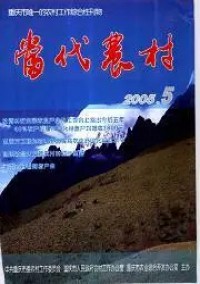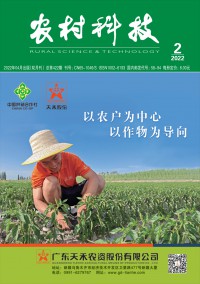農(nóng)村婚姻狀況計(jì)量分析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nóng)村婚姻狀況計(jì)量分析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利用族譜資料和計(jì)算機(jī)對(duì)明清以來(lái)的農(nóng)村社會(huì)進(jìn)行探討,已經(jīng)有若干學(xué)者做了開創(chuàng)性工作,特別是臺(tái)灣的劉翠溶女士,卓有建樹[2]。對(duì)江西地區(qū),劉女士也曾對(duì)宜黃北山黃氏家族做過(guò)計(jì)量研究[3]。但僅此單一的個(gè)案當(dāng)然遠(yuǎn)遠(yuǎn)不夠,且單純的族譜計(jì)量統(tǒng)計(jì)若無(wú)其他文獻(xiàn)和實(shí)地調(diào)查相配合,也難以深入認(rèn)識(shí)地域社會(huì)的真實(shí)內(nèi)涵和運(yùn)動(dòng)過(guò)程。作為江西省樂(lè)安縣流坑村研究課題的一部分,筆者以民國(guó)二十五年(1936)底刻印的《撫樂(lè)流坑董氏復(fù)彥房譜》為基本資料,將該譜全部人口記錄輸入電腦,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再結(jié)合以往調(diào)查研究所得加以分析,這里是其中的婚姻部分。希望這能夠深化我們對(duì)明清以來(lái)江西農(nóng)村的認(rèn)識(shí),并對(duì)有關(guān)研究有所助益。
材料與方法
關(guān)于流坑村,幾年來(lái)我們已經(jīng)發(fā)表了多篇文章[4],故這里不重復(fù)介紹。本文所使用的基本資料──《撫樂(lè)流坑董氏復(fù)彥房譜》,是流坑董氏第三級(jí)宗族組織中最大的一房──復(fù)彥房的房譜。流坑現(xiàn)能看到的20余種族譜中,唯一的大宗譜修成于萬(wàn)歷十年(1582年),早期的記載也并不完整,用于計(jì)量研究不夠理想。而八個(gè)二級(jí)宗族組織的宗譜,最后編修時(shí)間多屬清代,只有文晃房譜成于1936年,歷時(shí)最長(zhǎng),內(nèi)容也很充實(shí),可惜我們未能借出復(fù)印,暫時(shí)無(wú)法使用。故只好退而求其次,根據(jù)成譜時(shí)間、內(nèi)容和保存情況,以流坑董氏八大房之一的胤隆房下之復(fù)彥房房譜作為研究對(duì)象。
復(fù)彥房的房祖,是流坑董氏第19代的復(fù)彥公,由此下至第36代,共18代。該譜記載的人口歷時(shí)跨度,從明中期的1436到民國(guó)的1936年,正好500年。由于記載開始時(shí)流坑宗族組織已經(jīng)高度發(fā)展,按時(shí)修譜有制度保障,本房士紳亦比較多,故內(nèi)容較為翔實(shí)和完備。另外本房是流坑諸房人數(shù)最多者之一,又絕大多數(shù)居于流坑,在外者很少,所以數(shù)據(jù)更具完整性。
本譜樣本總數(shù)為7083人,其中男性4349人,女性2734人(均為男性配偶)。男性生年記錄可確知和大致推出者4260人,占男性人口的97.95%;女性則為2297人,占女性人口的84.02%。男性有卒年記錄以及修譜時(shí)尚存活者2510人,占男性人口的57.71%;女性為1956人,占71.54%。生卒年記錄均詳?shù)模行?969人,占男性人口的45.27%;女性1530人,占55.96%;如包括修譜時(shí)尚存活者,則男性為2509人,占57.69%,女性1915人,占70.04%。
由此可見(jiàn),復(fù)彥房譜的人口記錄不僅數(shù)量較大,而且相對(duì)而言也較為完整[5]。特別是3499個(gè)生卒年俱詳?shù)挠涗洠?對(duì)我們分析人口狀況及其變動(dòng),尤為重要的資料。
這樣一個(gè)有30個(gè)字段的數(shù)據(jù)庫(kù),基本可以全面反映該譜的所有人口信息,并較為方便地編制程序進(jìn)行各種統(tǒng)計(jì)和檢索。
婚姻基本狀況
一、婚姻締結(jié)
*比率此項(xiàng),所統(tǒng)計(jì)僅為22代至34代,而略去了基數(shù)太小的19、20、21代和修譜時(shí)年齡尚小的35、36代。
根據(jù)上表,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diǎn)認(rèn)識(shí):
第一,復(fù)彥房男子結(jié)婚人數(shù)(等于全部配偶數(shù))只占全部男子數(shù)的57.8%左右。這個(gè)比例,在已有的統(tǒng)計(jì)數(shù)字中是比較低的(如劉翠溶對(duì)南方23個(gè)家族的同一統(tǒng)計(jì)數(shù)字是65.9%[6],而毗鄰的宜黃北山黃氏則為71%。)。由于本數(shù)字已經(jīng)略去了修譜時(shí)年齡普遍尚小的世代,且漏載數(shù)量不會(huì)很多,所以導(dǎo)致其偏低的可能原因只有兩個(gè),即早卒未婚和成年未婚的人數(shù)較多。據(jù)上表,50歲以上未婚而卒的男子為66人,占1.5%。因這個(gè)數(shù)字僅是有生卒時(shí)間者,故偏低;如與生卒時(shí)間俱全的男子總數(shù)相比,則上升到2.6%。筆者另統(tǒng)計(jì)了30歲以上到50歲以下死亡的未婚男子,結(jié)果是占男子總數(shù)的2%和生卒時(shí)間俱全的男子3.4%。但二者相加最高仍不超過(guò)6%,說(shuō)明男子30歲以下未婚而卒的達(dá)34%以上,即未婚的主要原因是早卒,排除這一因素,結(jié)婚是極為普遍的。然而男子未婚數(shù)量之大,畢竟值得注意,這將對(duì)生育率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也從一個(gè)特定方面證明流坑未成年男性死亡率較高的事實(shí)。
第二,該房男子有較高的再婚率。在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由于死亡率高,較高的再婚率乃是普遍的事實(shí)。但是流坑繼室與元配比為22%,不僅大于宜黃黃氏家族的15.5%,也大于劉翠溶調(diào)查的23個(gè)南方家族中的任何一個(gè)(以下所稱南方家族,均指此),并比其平均數(shù)字高出近一倍。本譜中妻子被丈夫生出的情況極為少見(jiàn),不構(gòu)成再婚的一個(gè)要素。求其緣故,當(dāng)?shù)赝B(yǎng)媳較多似為一重要原因。道光年間,流坑一位老儒提到家族中“童養(yǎng)之婦,世俗動(dòng)以未合不成婦而為辭,往往兄亡
弟收,弟亡兄收”;又反對(duì)溺女,贊成“與他姓童養(yǎng)為婦”[7],可證當(dāng)?shù)赜写肆?xí)俗。檢索本譜有確切生卒時(shí)間的成員,有13位夭亡于10歲以下的男孩是已婚之身,另有9位元配死亡年齡在10歲以下,因本譜對(duì)配偶未過(guò)門即死亡的均有說(shuō)明,則這些男孩的妻子和早死的元配屬于童養(yǎng)媳無(wú)疑。而下面我們會(huì)看到,流坑元配妻子的結(jié)婚年齡明顯低于其他地方,說(shuō)明童養(yǎng)媳可能非常普遍。由于她們具有更多的死亡歷時(shí),所以童養(yǎng)媳多必然導(dǎo)致男子的再婚率高的事實(shí)。再看這里的男子三婚率和四婚率,分別為18.3%和18.6%,也高于劉氏的數(shù)字,似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第三,復(fù)彥房男子納妾的現(xiàn)象較少。妾只占全部配偶的0.6%,在劉氏研究的南方家族中居于非常低的水平而大大低于平均數(shù)(3.7%)。從另一個(gè)角度看,納妾男子只占結(jié)婚男性的0.89%(21位側(cè)室分屬19位男性),也充分說(shuō)明了這一事實(shí)。據(jù)劉氏的研究,城鎮(zhèn)家族的納妾比例較高,以江西本省的南昌東關(guān)甘氏為例,其比例為8%,13倍于復(fù)彥房。流坑基本上屬于農(nóng)村聚落,低于城鎮(zhèn)家族亦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宜黃黃氏家族的納妾比例也比較低,為2.3%,這也許示意著贛中農(nóng)村的共性;第二,復(fù)彥房納妾行為始于27代,其時(shí)間大致為17世紀(jì)末到18世紀(jì)中葉,正好是該房竹木貿(mào)易大發(fā)展的時(shí)期,這不是偶然的。再看表二:
*此二人均納二妾。
從表二可知,取妾者近70%為有各種身分之人,平民只占31.6%(納妾數(shù)則為28.6%)。而根據(jù)我們的研究,這些有身分之人除儒士(童生)和秀才外,全是通過(guò)捐納取得地位的,且?guī)缀跞巧倘恕<词故潜矶矫窈屯⑿悴胖校灿腥舾缮倘俗拥堋K晕覀兛梢哉J(rèn)為,流坑士紳特別是商人家庭,納妾的可能性遠(yuǎn)大于一般家庭;也就是說(shuō),流坑清代納妾現(xiàn)象的發(fā)展,和當(dāng)?shù)刂衲举Q(mào)易的發(fā)展直接相關(guān)。這和劉翠溶的研究有一致之處。
二、初婚年齡、夫妻年齡差和平均年齡
初婚年齡,族譜中均不記載,但可以通過(guò)父母(元配)與長(zhǎng)子的年齡差大致加以推斷。筆者將復(fù)彥房無(wú)女兒的家庭挑出,統(tǒng)計(jì)得到該房長(zhǎng)子出生時(shí)夫妻的平均年齡,夫齡為28.70歲,妻齡為23.12歲。而劉翠溶對(duì)南方十五個(gè)家族的統(tǒng)計(jì)數(shù)字是,夫齡在27至31之間(筆者據(jù)以計(jì)算其平均數(shù)為28.56),元配年齡為24至25歲(平均數(shù)24.76)之間。兩相比較,流坑男性在長(zhǎng)子出生時(shí)的年齡非常接均數(shù)字,但女性則低于平均數(shù)1.64歲,也低于十五個(gè)家族中的任何一個(gè),說(shuō)明流坑女性婚齡顯著偏小。如果我們按照劉女士的推算方法,假定由結(jié)婚到長(zhǎng)子出生間隔為三年[8],那么流坑的平均初婚年齡大約在男25.70,女20.12歲左右。這組數(shù)字的意義在于,雖然大量存在早婚的事實(shí),但男性平均婚齡并不太小,也就是說(shuō)實(shí)際上仍有相當(dāng)多的人是在比較大的年齡上才結(jié)婚的。而女性婚齡偏小,可能印證了當(dāng)?shù)厥震B(yǎng)童養(yǎng)媳之風(fēng)較甚,這在上面已經(jīng)提到了。
依據(jù)族譜中每一對(duì)夫妻生日(如果有記載的話),即可以知道他們之間的年齡差。表三的第一欄即是元配、繼室和側(cè)室與丈夫的平均年齡差。丈夫比元配要大近5歲(這和上面根據(jù)長(zhǎng)子生育時(shí)間計(jì)算出來(lái)的初婚年齡差5.58歲相近),這是一個(gè)比較高的數(shù)據(jù)[9],再次證明了女性結(jié)婚年齡偏低的事實(shí)。而且顯然,隨著婚姻次數(shù)的增加,丈夫與配偶之間的年齡差距也逐漸拉大。這表明,流坑男性在妻子死后再次結(jié)婚時(shí),更傾向于選擇較年輕因而可能未婚的女性。而比較年輕女性的家長(zhǎng)愿意把女兒嫁給董氏年齡較大的男子,則可能是董氏在當(dāng)?shù)赜休^為突出的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地位所致。
不過(guò)盡管如此,我們?nèi)匀豢梢园l(fā)現(xiàn)有一定數(shù)量的女性年齡大于她們的丈夫。元配組為五分之一強(qiáng),這個(gè)數(shù)字在北方地區(qū)無(wú)足稱道,但在南方就是特別高者。就是繼室組也高達(dá)8.68%,接近于南方地區(qū)一些家族元配的水平[10]。甚至再繼之中,她們也依然存在。故而流坑男子娶妻并無(wú)男必須大于女的約束。但檢索的結(jié)果表明,極少有妻子比丈夫大10歲以上的事實(shí)(元配亦只有0.14%),而且還有一部分大妻其實(shí)與丈夫?yàn)橥瓿錾耐g人(元配3.01%,繼室1.74%),這與丈夫常常大于妻子20、30歲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
根據(jù)生卒時(shí)間俱全的記錄,統(tǒng)計(jì)得到復(fù)彥房男性平均年齡為42.84歲,女性為47.04歲。女性壽命長(zhǎng)于男子,這是一般的通例,可是這里女性平均年齡超過(guò)男性較多,原因在于女性多為成年嫁入,不像男性有許多夭殤者進(jìn)入統(tǒng)計(jì)。
三、守寡與醮出
由于復(fù)彥譜對(duì)女性生、卒記載不如男性詳盡,特別是醮出者的卒年一律闕如,表四a、b的守寡數(shù)字,只是配偶雙方有明確生、卒時(shí)間記錄從而可以判定的寡婦和有“出”即醮出記載的寡婦數(shù)字,很不完全。盡管如此,其仍然可以幫助了解流坑女性守寡和出醮的一些情況。本表只列出數(shù)據(jù)較充分的元、繼配的數(shù)字,再繼和三繼因數(shù)據(jù)較少?gòu)穆裕A魝?cè)室的數(shù)據(jù)以為參照。
復(fù)彥房的婦女元配守寡的比例為43.89%,繼室為45.59%,總比例為47.28%,接近半數(shù)。雖然明顯低于劉翠溶的南方15家族57.9%的平均守寡率,但也還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元配45歲以上的守寡人數(shù)少于45歲以下者,與南方諸家族情形完全相反,只有繼室是45歲以上組大于以下組。如果不是因?yàn)橛写罅繜o(wú)法歸屬的數(shù)據(jù)存在影響了計(jì)算精確的話,則首要的一個(gè)原因可能是,復(fù)彥房未成年男性的死亡率較高,這對(duì)元配45歲以下守寡比例較高是有影響的。而且劉氏的45歲以下組只包括20到44歲的妻子,沒(méi)有計(jì)入事實(shí)上并不算少的20歲以下的寡婦(如上面提到的童養(yǎng)媳中的一些人及其他低齡妻子)。復(fù)彥房元配中20歲以下的寡婦為43人,占總數(shù)的6.07%,減去她們后差距就有所減少(46.61對(duì)33.90變?yōu)?0.54對(duì)33.90)。從理論上說(shuō),該房妻子的平均壽命是47.04歲,丈夫的平均壽命為42.84歲,由于婦女婚齡偏低,夫婦之間有約5歲的年齡差,故婦女37歲時(shí)就有極大的守寡可能性,所以45歲以上者守寡比例有限。
另外從總體上看,隨著婚姻次數(shù)的增加,續(xù)娶配偶守寡的比例也有所提高,這顯然是因?yàn)槔^妻與丈夫的年齡差越來(lái)越大的緣故。
再看醮出。復(fù)彥房共有元配女子235人醮出,是所觀察的元配寡婦總數(shù)的33.19%。即是說(shuō),大體上守寡的元配里面,每三個(gè)就有一個(gè)改嫁。而在總體上,大約每四個(gè)寡婦會(huì)有一人改嫁。所以,宋代以來(lái)理學(xué)家們和政府努力提倡的極度貞節(jié)觀,在贛中農(nóng)村和許多地方一樣,實(shí)際上并未能成為支配的觀念。當(dāng)時(shí)流坑的一位士人說(shuō):“守貞難得三從,自是經(jīng)常;逐物易移再醮,亦屬權(quán)變。與其淫奔而玷戶,不如改節(jié)以棲身”[11],這很可以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社區(qū)精英們對(duì)此也是持寬容態(tài)度的。當(dāng)然,流坑至今還能發(fā)現(xiàn)一些清代官員表彰節(jié)烈女子的牌匾,族譜里面也不乏類似的文字和榜樣,但這種極力的贊美與提倡,恰恰說(shuō)明當(dāng)時(shí)社區(qū)中大量存在的,其實(shí)是相反的事實(shí)(復(fù)彥房譜的《貞節(jié)傳》收入33人,僅占婦女總數(shù)的1.21%而已)。
再一個(gè)明顯的情況是,45歲以下寡婦改嫁的比例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以上者。表中元配是15倍,繼室則是8倍。計(jì)算兩組寡婦改嫁的比例(醮出人數(shù)/守寡人數(shù)),45歲以下組為26.05%,以上組則為2.32%。前者也是后者的11.23倍。因?yàn)橛写罅坎辉敋w屬于何組的寡婦和醮出者,這兩個(gè)比例肯定都偏小。如果將不詳歸屬的寡婦按1:1分到兩組,即使按照2:1的比例分配不詳歸屬的醮出者,45歲以下者仍將達(dá)到43.83%,以上者則為17.97%;如按3:1分配醮出者,這兩個(gè)數(shù)字則為46.60%和11.89%。可以認(rèn)為,復(fù)彥房的妻子如果不到45歲死去丈夫,近半數(shù)甚至更多會(huì)改嫁;以上組就少得多,最多不會(huì)超過(guò)20%。
復(fù)彥房娶進(jìn)女子與女兒所嫁姓氏極其近似。前十位中有9個(gè)相同,而且位次和總比例也很接近。前二十位中則有18個(gè)相同,即90%保持一致。這說(shuō)明,該房無(wú)論嫁娶,通婚對(duì)象均很一致,而且主要是固定在一二十個(gè)姓氏上(按:通婚姓氏總數(shù)為107個(gè))。這種通婚對(duì)象的相近有諸多原因(詳下),其中亦包括“親上加親”的傳統(tǒng)習(xí)俗,以及在社會(huì)交往較少的情況下出嫁女性在助成婚姻方面的重要作用。能夠說(shuō)明這一點(diǎn)的一個(gè)現(xiàn)象是,譜中母親和女兒出嫁對(duì)象的姓氏往往相同。房譜共計(jì)949位女性有生女記載,生女2243人,內(nèi)1240人有所嫁姓氏記載,而與母姓相同的為135人。可知14.23%的母親至少有一位女兒會(huì)嫁給自己的同姓;10.89%女兒的夫君與母親同姓。如果說(shuō)這一比例還不算高的話,房譜還表明,有更大數(shù)量的女兒出嫁后婆家之姓與其繼母、嫂子或嬸子相同,這更能反映同樣的事實(shí)。
根據(jù)梁洪生對(duì)流坑其他房支明中期到近代婚入姓氏的統(tǒng)計(jì),胤明房前15位依次為王、陳、曾、黃、丁、張、胡、譚、吳、鄧、詹、徐、袁、樂(lè)、邱;坦然公房為王、陳、曾、丁、邱、黃、譚、張、詹、元、鄧、闕、劉、謝。比較起來(lái),復(fù)彥房前15名與二者相同的均有10位(66.67%)。這說(shuō)明整個(gè)流坑的通婚對(duì)象有很大的共同性。但某些姓氏的出入,特別是某些房位置在前的姓氏在另一房可能位次很后,如復(fù)彥房列第九的謝氏在胤明房的的前15名中蹤跡皆無(wú),而胤明房的樂(lè)氏和坦然房的闕氏在復(fù)彥房的通婚對(duì)象中僅都只有0.32%,僅在30位左右。個(gè)中差別,說(shuō)明各房的通婚對(duì)象亦具有一定的特點(diǎn)。
復(fù)彥房90%以上的通婚對(duì)象在本縣范圍內(nèi),這是傳統(tǒng)農(nóng)村社區(qū)帶有普遍性的現(xiàn)實(shí)。但有兩個(gè)現(xiàn)象應(yīng)該關(guān)注:一是仍然有一定的跨縣甚至跨省的婚姻,主要是入嫁女性有11.34%來(lái)自縣外;二是娶入和出嫁,亦即男女兩方面之通婚地域有微妙的差異,男子在外縣娶妻的比例大大高于女兒出嫁到外縣,且有1.14%的跨省婚姻。這表示,當(dāng)?shù)鼗橐霾⒉皇峭耆忾]的,男性獲得配偶的范圍尤較女性為大。仔細(xì)觀察上述地點(diǎn)可以發(fā)現(xiàn),縣外婚姻較多地集中在永豐和贛江、長(zhǎng)江水道上(湖北一例為小池,江蘇一例為南京)。流坑所在的“下樂(lè)安”地區(qū)本屬永豐,南宋才分出,但歷來(lái)方言、風(fēng)俗一致,交通便利,至今居民心理上仍很親密。而恩江經(jīng)永豐下注贛江,經(jīng)吉水、樟樹、豐城、南昌、鄱陽(yáng)湖到長(zhǎng)江中下游的水道,則是流坑竹木貿(mào)易的主要路線。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上述地點(diǎn)的分布。另外跨省婚姻中湖南和浙江兩例,都是外出做官者娶的側(cè)室,乃是男性社會(huì)政治活動(dòng)的結(jié)果。所以,這里傳統(tǒng)社會(huì)中主要由男子進(jìn)行的各種超越社區(qū)的經(jīng)濟(jì)、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行為,是部分打破通婚圈的封閉的主要原因。
同姓氏一樣,在復(fù)彥房100個(gè)左右的通婚地點(diǎn)中,有一二十個(gè)最集中的地點(diǎn),而全部又都在樂(lè)安南部的恩江流域即所謂“上樂(lè)安”地區(qū),具有非常高集中性。從地圖上看,這塊地域南北約50公里,東西40公里,即董氏的主要通婚圈。由于大族聚族而居,所以這和上面姓氏的集中實(shí)際上是相通的。雖然同地未必同姓,但同姓的比例很高。以幾個(gè)大姓為例,見(jiàn)表十:
上表是根據(jù)譜中出嫁地和所嫁姓氏俱全的記錄,統(tǒng)計(jì)得出的從十大通婚姓氏主要居住地婚入女子在所有同姓配偶中所占比例。其從近80%到20%不等,成為相同姓氏中的主要通婚對(duì)象。其實(shí),有不少同姓本為一支所孽,如譚港、員陂、官莊等處的黃氏,水南和蓮河等處的丁氏,將他們合并計(jì)算后,黃、丁二氏的比例即上升到53.85%和97.22%。所以流坑董氏的通婚對(duì)象,實(shí)際上主要為一些類似董氏這樣在當(dāng)?shù)赜械匚缓陀绊懙木圩宥拥拇蠹易濉.?dāng)然,也有的地方雜居程度很高,如縣城21個(gè)婚入的女子分屬10個(gè)姓氏,這是城鎮(zhèn)的特別之處,體現(xiàn)了流坑董姓在縣境內(nèi)的地位及其與縣城士紳的較深關(guān)系。
流坑的婚姻,確實(shí)存在著一個(gè)空間狹小、大家族之間世為婚姻的固定圈子,這是不容置疑的。這種圈子的形成,除了是上面指出的歷史、風(fēng)俗和交通、商貿(mào)等因素的產(chǎn)物,還與鄉(xiāng)村宗族成員和精英人物試圖獲取和保持社會(huì)聲望和地位,維系宗族組織的穩(wěn)固與和諧相關(guān)聯(lián)。明代中、期以來(lái)一批董氏士紳不斷地在加強(qiáng)宗族的制度化,其中就包括加強(qiáng)婚姻限制。由知縣董極撰寫的萬(wàn)歷大宗譜之祠規(guī),明定可以通婚的若干“鄉(xiāng)中世姓與凡清白守禮之家”。有敢于“開列之外,乖亂成法,”“貪利忍恥,將男女約婚小姓”者,處以“罰銀十兩”和“追譜黜族”的嚴(yán)厲處分[13],在若干族譜里我們看到一些具體事例,證明這一規(guī)定曾確實(shí)得到執(zhí)行,其對(duì)世婚的確定和維持作用,自不待言。所以,至少在較早的譜牒中,出嫁地和嫁入地的明確記載,是有一定的社會(huì)意義的。
然而也需看到,復(fù)彥房存在著不少與小姓結(jié)婚的例子,約40個(gè)僅一、二見(jiàn)的婚入姓氏,恐怕多屬于此。其中如蕪頭的周氏,燒元的李氏,在其他房譜內(nèi)明見(jiàn)娶而受罰的記錄;又如藍(lán)、鐘、賴、雷之類的姓氏,應(yīng)為客家山民,也不屬于世族。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個(gè)族人娶了本村的外姓女子(一姓李,一姓羅),我們知道,村中極少數(shù)的外姓人均為董族的佃仆賤役,其為嚴(yán)禁通婚的對(duì)象無(wú)疑。可是復(fù)彥譜中竟無(wú)一人因此而有受處罰的記錄,令人囑目。這些現(xiàn)象較多發(fā)生在29代也就是清代中期以后,可能表明隨著乾隆以來(lái)人口的急劇增長(zhǎng)和商貿(mào)活動(dòng)的發(fā)展,流坑通婚世姓的傳統(tǒng)規(guī)條有所松動(dòng)。這對(duì)于我們研究流坑董氏家族的解體過(guò)程,有一定的意義。不過(guò),某些房這一時(shí)期制定的家法還在強(qiáng)調(diào)“娶必相當(dāng),先分良賤;配非其偶,重玷門楣。如果貪財(cái)辱宗,定行削譜黜族”[14],并且確有具體記載,表明各房之間這種松動(dòng)的程度是不同的。
進(jìn)一步觀察復(fù)彥房紳士家庭的婚姻情況,我們還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認(rèn)識(shí)。這里所說(shuō)的紳士,是指包括童生以上有科舉名分或通過(guò)捐納、軍功等途徑得以取得散官或?qū)嵚氄摺U?qǐng)看表十一和表十二:
比較表十一、十二可以看出:復(fù)彥房的士紳無(wú)論娶妻嫁女,在可能的情況下總是追求門當(dāng)戶對(duì),所以該房絕大多數(shù)對(duì)方為紳士的婚姻(婚入為93.75%,出嫁為82.35%)都發(fā)生在這個(gè)圈子里頭,普通成員極少。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對(duì)方之所以愿意與其通婚,也是因?yàn)槠渖鐣?huì)地位相近。表十三可以進(jìn)一步說(shuō)明這一點(diǎn):由表中可見(jiàn),復(fù)彥房的士紳主要是兩類人,一是低級(jí)的科舉功名的獲得者,一是捐納人員(本表國(guó)學(xué)以下至議敘全為捐納所至),二者的地位都不高。他們的親家,也完全是這兩類低級(jí)士紳。但他們之間同一身分者數(shù)量多較懸殊,則表明他們?cè)诮Y(jié)親時(shí)并不要求絕對(duì)對(duì)等,兩類人員間也沒(méi)有明顯的隔閡。超級(jí)秘書網(wǎng)
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實(shí)上他們也遠(yuǎn)遠(yuǎn)達(dá)不到真正的門戶相當(dāng)。只有7.59%的士紳在娶妻時(shí)、7.09%的士紳在嫁女時(shí)能夠如愿以償,大部分則只能與平民通婚。從全房的范圍來(lái)說(shuō),在婚入和出嫁的兩種場(chǎng)合,董氏的親家中紳士都只占1%多一點(diǎn),所以實(shí)際上,當(dāng)?shù)厣鐓^(qū)中士紳通婚的次數(shù),在總數(shù)中是不足道的。復(fù)彥房的紳士人數(shù)該房是男性成員的9.08%(395/4349),其和親家的差距也許反映了流坑紳士比例較高的特點(diǎn)(流坑董氏利用族大人繁、控扼河流,壟斷流域的竹木貿(mào)易后,大量捐納職、監(jiān)和資助子弟讀書,形成了較大的商人和生、監(jiān)群體,這方面深入的計(jì)量研究,將另文探討),這也是他們會(huì)較多地與平民通婚的原因之一。當(dāng)然這些平民可能較為富有,而不是下層的貧民。
注釋:
[1]本文是流坑研究計(jì)劃的一部分。該項(xiàng)研究工作主要由江西師大歷史系的梁洪生副教授和我進(jìn)行,并得到了周鑾書研究員、鄭振滿博士的指導(dǎo)和香港科技大學(xué)人文學(xué)部的資助。本文計(jì)算和寫作過(guò)程中,又得到了曹樹基博士和胡振鵬博士的熱忱幫助,在此一并致謝。
[2]劉女士有關(guān)研究成果很多,最集中和完整的見(jiàn)《明清時(shí)期家族人口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變遷》,臺(tái)灣中央研究院經(jīng)濟(jì)研究所,1988年6月。
[3]《宜黃北山黃氏之成長(zhǎng)與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第二屆國(guó)際漢學(xué)會(huì)議論文集》,臺(tái)北,1989。以下有關(guān)這個(gè)家族的情況,均據(jù)此文。
[3]梁洪生:《家族組織的整合與鄉(xiāng)紳──樂(lè)安流坑村“彰義堂”祭祀歷史考察》;邵鴻:《竹木貿(mào)易與明清贛中山區(qū)土著宗族社會(huì)之變遷──樂(lè)安縣流坑村的個(gè)案研究》,俱見(jiàn)周天游主編:《地域社會(huì)與傳統(tǒng)中國(guó)》,西北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10月。梁洪生:《社區(qū)建設(shè)實(shí)驗(yàn)──江右王門學(xué)者與流坑村》,1995年香港“經(jīng)營(yíng)文化:中國(guó)社會(huì)單元之組織與營(yíng)運(yùn)”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論文。梁洪生:《流坑村何楊神崇拜考述》;邵鴻:《明代江西農(nóng)村社區(qū)中的會(huì)──以樂(lè)安縣流坑村為例》,俱見(jiàn)《南昌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贛文化專號(hào),1996年。
[4]劉翠溶上揭書中所研究的族譜,知道生年者為80-68%,卒年為40%左右,見(jiàn)該書第一章。又劉氏研究的北山黃氏族譜,生年詳知的男子占97%,女子占72%;卒年詳知者男子占56%,女子占43%,劉氏已認(rèn)為“此譜對(duì)于成員的生命日期記載相當(dāng)完整。”
[5][6][8][9]劉翠溶:《明清人口之增殖與遷移──長(zhǎng)江中下游地區(qū)族譜資料之分析》,《第二屆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研討會(huì)論文集》,臺(tái)北,1983。
[7]董泰然:《家戒八條》,道光十九年(1839)《樂(lè)邑流坑董胤明公房譜》。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農(nóng)村工作會(huì)議 農(nóng)村工作意見(jiàn) 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 農(nóng)村工作計(jì)劃 農(nóng)村工作總結(jié) 農(nóng)村普惠金融 農(nóng)村集中供水工程 農(nóng)村電商論文 農(nóng)村教育 農(nóng)村新農(nóng)村建設(shè) 紀(jì)律教育問(wèn)題 新時(shí)代教育價(jià)值觀
- 農(nóng)村
- 農(nóng)村離婚
- 農(nóng)村文化
- 農(nóng)村講話
- 農(nóng)村講話
- 農(nóng)村選舉
- 農(nóng)村金融支持農(nóng)村建設(shè)
- 農(nóng)村改革及農(nóng)村城鎮(zhèn)化
- 農(nóng)村土地流轉(zhuǎn)
- 農(nóng)村會(huì)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