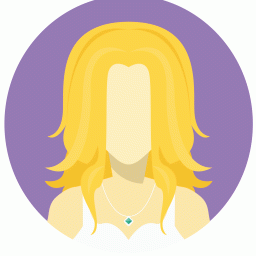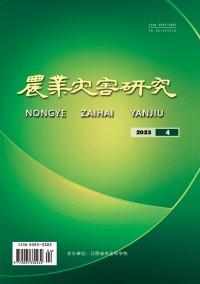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考察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考察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1959—1961年我國經歷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關于其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錯誤地完全歸咎于三年自然災害。但近年來國內外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認為這三年“風調兩順”,根本沒有自然災害,“人禍”即決策錯誤是唯一的原因。本文根據對災情、受災面積等資料圖表的分析,證實這三年發生了持續的嚴重自然災害;同時分析了各種決策錯誤帶來的不同影響,重點把糧食作為決定國家經濟興衰的生命線和因果關系鏈的比較指數,用計量方法分析當時農村因災減產、因決策錯誤減產、因高征購而減少糧食存量之間的比例狀況。本文的結論是:從農業糧食減產因素看,自然災害略大于決策錯誤;從農村一個時期的集中缺糧情況因素看,決策錯誤影響遠大于自然災害,可以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關鍵詞]災害經濟學三年困難時期自然災害決策錯誤
1998年中國發生特大洪水以后,一門新興的經濟研究學科一一災害經濟學得到了關注。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中南財經大學等校開設了專門課程,并有相關專著問世。2003年出現SARS疫情以后,這門學科成為熱點。關于災害經濟學的定義,有人認為:“災害經濟學首先研究的課題是災害對經濟的直接負面效應與間接正面效應,并探討如何充分挖掘其間接正面效應,降低直接負面效應。”[1]有人認為:“災害經濟學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自然災害,而應對人為災害以及人與自然交互作用下的各種災害予以高度重視”,“人災互制、害利互變是災害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或規律”。[2]總的來說,災害經濟學是研究人與災害的關系的學科。用這門新興學科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發生過的災害,不僅對于國史、經濟史研究有著跨學科的創新意義,而且對粗具規模的災害經濟學本身也有奠基作用。建國以來對經濟影響最大的災害,人所共知的是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本文擬從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
有沒有“三年自然災害”?這本來不成其為問題,只是在人與災害的關系(即“人禍”與“天災”)上,不同時期的說法有別。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災呢,還是由于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范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3]但是,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嚴厲批評了所謂“黑暗風”之后,“人禍”的原因被絕口不提。直到1978年以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直成為這三年歷史的代名詞。1981年6月,《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主要由于‘’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與劉少奇1961年的判斷是基本相同的。
但引人注目的是,近幾年來,根本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文章又不斷出現,開始成為輾轉引證的熱點。
例如,金輝的《風調雨順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一文,利用氣象專家編制的1895—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中的120個水文站資料得出全國平均指數,認為:“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么‘自然災害’。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4]
王維洛的《天問一一“三年自然災害”》一文認為:“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介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被反復重復的謊言,終于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于那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根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中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干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干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范圍之內;1960年全國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圍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干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5]
本文無意于論證需要氣象學家研究的問題,只想引用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的《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以下簡稱《災情報告》)中的史實進行說明。
中國經常發生的自然災害主要是氣象(包括旱災、雨澇等災害)災害、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災害的程度基本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災害較大,但從受災面積看仍“屬中等水平”[6]。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范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收成減產30%以上為成災)面積1373萬公頃[6](p.378)。其中成災占受災面積的30.8%,與歷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占全國成災面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的影響十分嚴重。
1959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卑,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的生長,黑龍江受旱達4寸—5寸深,為歷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等地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6—8月,出現以江淮流域為主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面積已達821.2萬公頃,持續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面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臺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1959年災害種類繁多,在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并不多見的蝗災、粘蟲災、鼠災。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后,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后最嚴重的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50年來首位[7]。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臺風洪水災害。
1960年1—9月,從1959秋季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陜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天一400天未下雨,受災面積達2319.1萬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糧區合計受災1598.6萬公頃,成災808.5萬公頃,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68.9%和56.9%。流經山東、河南的黃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地區除西藏外旱災面積達3812.46萬公頃,是建國50年來最高記錄。
1960年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臺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里臺風登陸達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數近兩倍。臺風過境時間長達10小時—20小時,高于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6](p.379)。臺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面積達993.3萬公頃,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內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米—4米。東北遼河、太子河泛濫,流量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地143.7萬公頃,“鞍山、本溪等地區農田、村莊受到毀滅性打擊”[6](pp.378,379)。
1960年3—5月、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11個省區,受災面積138.1萬公頃。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個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面積達392.26萬公頃。
1960年大災害不僅成災面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受災的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更大。另一個特點是早、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水泛濫,部分地區則持續干旱,給救災工作帶來極大的困難。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于1960年,為建國50年來的第2位。成災面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7](p.35),其中1/4面積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也超過了1960年。
從1960年冬季持續到1961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的農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面積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的小麥比1960年最低水平又減產50%,湖北省有67萬公頃土地未能播種,河南省有73萬公頃農田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凍、大風災害,淮北地區有375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毀房屋504萬間。
1961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泛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面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面積的54%,近100萬公頃農田沒有收成。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土地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風雨侵襲,山洪暴發沖人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產。松花江流域7萬公頃農田絕收。
1961年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遭受臺風襲擊11次,其中12級以上的占9次,是建國50年里最多的[6](p.82)。淹沒180萬公頃農田,造成的如漁船損壞、房屋倒塌、海堤被沖毀、人口死亡等損失都超過了1960年。
19491998年受災成災面積曲線表單位:千公頃
資料來源:據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1966—1969年統計數字原缺。
圖1
由圖1可見,1959—1961年確實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成為出現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原因。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已經多次提到這個判斷,并不像金、王二文所斷言的是后來才編造的。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8]1961年9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一個“特別的理由”就是了解是否發生了大的自然災害。他在分別會見、劉少奇時,幾次問到這個問題。劉少奇認為:當前的“一連三年大災”是80年來沒有的。也同意說:“過去局部性旱災有過,但全國性的沒有。”他還指出,中國水利灌溉抵御旱災的作用“還差得很遠。中國幾千年來,加上我們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還是靠天吃飯。要逐步來。”[9]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生產力十分低下,綜合國力很弱,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有限,遇到持續三年特大嚴重自然災害,出現經濟困難是不可避免的。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當時出現了嚴重的“左”傾錯誤。
二、決策錯誤對當時經濟的影響
“三年經濟困難”的最大損失,莫過于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農村糧食存量大減,致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這三年因旱災糧食年均損失率(因旱災糧食減產量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比重)為13.26%,大大高于全國1949—1969年因旱災糧食損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圍。按照另一種全國不完全統計的損失量計算,這三年年均因旱災糧食損失平均117.7億公斤,相當1949—1959年均33.97億公斤的3.46倍[10]。但是,農村糧食存量的減少,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自然災害使糧食減產。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采用比較自然災害程度相似時期的辦法,分析有哪些因素影響著糧食存量的變化。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到,1978年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上與1959—1961年時期有比較相似的地方:
第一,兩個時期的主要災害、災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災,不僅范圍大、程度重,僅就旱災而言,超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建國以來最大的,而且是歷史上罕見的。1978年全國受災面積達5079萬公頃,成災面積2180萬公頃,低于1960、1961年,高于1959年。
第二,兩個時期的經濟決策相似,都出現了盲目的“躍進”運動。1978年提出一個“新的躍進”規劃,要求分三個階段打幾個大戰役,到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使我國的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和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世界先進水平。在當時情況下,這個規劃是冒進的。
第三,兩個時期都處于災害的群發性時間段。據專家研究劃分,我國1479—1691年和1891年至今為干旱期,在后一個時間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為三個災害嚴重的群發時期[6](p.5)。
第四,兩個時期的農村經濟、政治體制相似,都屬于農村體制的生產方式。就全國來說,1978年執行的仍然是改革開放以前的路線。
然而,兩個時期的經濟狀況卻出現了較大的不同:全國糧食產量:1959、1960、1961年分別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則比1977年增長7.8%(1977年產量較低也是一個原因),達建國以來最高的3047.7億公斤;全國農業總產值:1959、1960、1961年分別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則比1977年增長9.8%。此外,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如前所述急劇增加,而1978年則沒有出現值得注意的現象。分析造成兩種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說明“”決策錯誤的嚴重影響。
1.“”時期嚴重高估了糧食產量,采取了一系列錯誤決策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估計并正式公布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3000億公斤—3500億公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8年底,有關部門把預計產量又夸大為4250億公斤。按照這個產量計算,全國平均每人糧食占有量為650公斤,早已超過需要。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公報雖然指出“過去發表的1958年的農業產品產量的統計偏高”,認為經過核實后的糧食的實際收獲量為2500億公斤,但仍然嚴重高估。實際上,經過后來核實的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遠低于公布數字,只有2000億公斤。根據嚴重失實估計,當時得出了糧食已經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現了五項錯誤決策:
第一,大辦吃飯不要錢的食堂。取消了糧食定量,實行敞口吃飯,宣傳所謂“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個月就吃掉了3個月的口糧。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的統計,全國農村已經辦有公共食堂391.9萬個,參加吃飯的有4億人,占總人數的72.6%,其中主要產糧區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區達90%以上。
第二,大量增加城鎮和職工人數。1958年6月,中央決定勞動力的招收、調配由省市區確定后即可執行,各地又將招工審批權層層下放。職工1960年達到5969萬人,比1957年增加2868萬人,城鎮人口1960年達到13000萬人,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11]。全國農業勞動者人數由1957年的19310萬人急劇下降到1958年的15492萬人,占工農業勞動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
第三,投資和人力物力繼續向工業方面傾注,排擠農業。1958年秋收未完,就將大批農村勞動力調出,參加沒有計劃的水利工程,抽調農村勞動力3000多萬人搞鋼鐵等其他事業。1960年9月,譚震林向中央報告說,主要產糧區的河北、山東、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機和排灌機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開動,農民的小農具也缺乏很多,因為廢鋼鐵原料都被收集煉鋼,農具廠也改煉鋼。10月,山西省委也報告說,農忙的4、5月份,全省參加田間勞動的勞動力只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壯少。這些都造成糧食有一部分不能收獲到倉。回家鄉調查時收到一位老紅軍的字條:“谷撒地,黍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請為人民鼓嚨胡”,也深刻地反映了這種現象。
第四,減少糧食播種面積。根據糧食問題已經解決的不實估計,1958年做出了次年減少糧食播種面積的決策,1959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74034萬畝,比1958年的191420萬畝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種面積下降9.1%,小麥播種面積下降8.5%[12]。按照1957年糧食畝產計算,等于1959年全國減少了169.5億公斤糧食,相當于總產量的lO%。
第五,實行糧食高征購政策。為了支持工業“”,要求各地區加大征購指標,在發現農村缺糧難以完成的情況下,又進行了“反瞞產”斗爭,強行征購。如1959年1月27日,廣東省委書記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說,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造成的。再如2月19日,《經濟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組對桐城的調查報告說,發現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征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干部的思想問題。在這種錯誤認識的支配下,1959年全國糧食征購量、出口量達到建國以來最高的674億公斤和41.6億公斤,即使到了嚴重遭災的1960年,征購量和出口量仍高達510.5億公斤和26.5億公斤,出口量與豐收的1958年相等[13]。當然,繼續實行高征購政策還有一個國際方面的原因,1960年7月,中蘇關系破裂后,蘇聯向中國逼債很緊,為了還債,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這樣,當自然災害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甚至絕收的情況來臨,國家、集體、家庭都嚴重虧空。河北省1959年1月全省農村已經普遍出現了饑餓導致的浮腫病。到5月,已有55個村255個食堂斷糧停炊。全國的情況也大致如此。
1978年的情況則不同,從1977年起,國家采取了大量進口糧食的政策。1977—1983年年平均進口104.5億公斤,是建國以來的一個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規定糧食統購價從1979年夏糧上市起提高20%,超購部分再加價50%,糧食征購指標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穩定在1975年的基礎上并減少25億公斤,凈征購率只有15.6%。這些政策均使農民得到了休養生息。
從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1959、1960年,全國糧食產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購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開始調入和進口。1979—1982年,糧食產量逐年增加,卻采取了低征購率和大量進口的政策。一縮一盈,一消一長,自然就使兩個時期人民糧食占有水平相差甚大,1978年比1960年增加48%。
應該說,兩個時期的歷史情況也不相同。在以農業產品為主要原始積累的20世紀50年代,為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不得不大量征購和出口糧食。而在國家已經初步奠定工業化基礎的70年代末期,采取進口糧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客觀條件變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積累增加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意義。因此,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從領導人的決策看。
表11958—1961、1977—1982兩個時期糧食變動表
全國糧食變動量
全國人均
年份
總產量
(萬噸)
凈收購比例
%
出口量
(萬噸)
進口量
(萬噸)
占有量
(公斤)
1958
1959
1960
1961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20000
17000
14350
14750
28273
30477
33212
32056
32502
35450
20.9
28.0
21.5
17.5
13.3
14.0
15.6
15.0
15.0
15.6
266
416
265
445
569
695
1071
1181
1348
1534
306.0
255.0
215.0
240.5
299.5
318.5
342.5
326.5
327.0
350.5
資料來源:據《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1992年版編制。出口為正值,進口為負值。凈收購比例指收購量減去返銷農村數量后占總收購量的比例。
2.“”時期過高地估計了主觀意識的作用和農業生產條件的變化,把“人定勝天”的決心當作了現實,加上“反右傾”,因此對抗災關注不夠,反而繼續要求“”,對農業及抗災投資也相對較少
應該說,在發動“”的1958年就掀起了興修水利的高潮,為防治自然災害做了重要的準備。但是,這種程度低下的農村抗御災害能力卻被“浮夸風”拔高到不適當的高度。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其中規定:在一年內基本消滅水災和旱災的縣(市),都可以派代表參加年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這樣一來,許多地區都紛紛宣稱根治了自然災害。
1959年出現嚴重春旱之時,和中共中央對防災抗災是注意的。4月17日,在看了國務院關于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后,親自擬定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在3天內用飛機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里,迅即處理緊急危機[14]。4月24日,他又對東部沿海發生風暴的報告批示:“再接再厲,視死如歸,在同地球開戰中要有此種氣概。”[14](p.217)但是,到了8月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后,由于政治壓力,一些地區隱匿災情不報或者報告已經戰勝了災害,使從中央到地方都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情緒,對自然災害的嚴重程度缺乏思想準備和應對措施。如8月1日,新華社內部報道說廣東增城縣遭受重災,“總的印象是情況很好,比想像的好。受災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蕩然無存’,農民生活安排得不錯,生產蓬蓬勃勃”。看后更加深了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的認識,要求繼續進行“”。到1960年3月送來安徽“餓死人事件”的群眾來信,等才對真實情況有所了解。在此之前,盡管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也進行了各種抗災斗爭,但并沒有及時地作為全國的中心工作。綜合國力的低下,也使當時投入的資金十分有限,20世紀60年代中央財政補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經費實際支出年均只有0.61億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災害”的教訓,經濟好轉以后,國家對防災抗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后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和“廣積糧”政策,提醒“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在具體部署上,1966年決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余秋里等國務院領導分別擔任各省區的抗旱工作組組長,還親自擔任河北組組長,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從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揮部,由總參、計委及水電、農林、財政、商業、交通各部組成,各地區、各部也建立了相應的機構,防治自然災害成為全國的長期性工作。20世紀70年代,中央財政補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經費實際支出年均為2.05億元,相當于20世紀60年代年均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現大旱災之初,國務院即召開全國會議,王震、康世恩講話動員,要求各部門各地區把救災工作作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陳永貴還親臨災區視察和指揮。11月,國家決定拿出10億元支持各地抗旱。對防治災害的重視和投入,成為1978年戰勝災害的重要因素。
3.兩個時期的自然災害和決策錯誤持續的時間、影響程度不同
1959—1961年連續三年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在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其損害力及致使人類承受災難能力的衰減,絕非算數級數,而是成幾何級數。而1978年的災害雖然嚴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災害屬于輕度和中上度。
1958年開始的“”,一直持續了三年,有些“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糾正。而1978年開始的“躍進”只實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國際環境和思路的變化,1978年“躍進”的資金來源主要靠大量引進外資,以后分期償還。雖然超過了國家的綜合國力,但對農業影響不是很大。
4.兩個時期的農業生產力條件有了很大的變化
這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參見表2:
表21957—1962、1978兩個時期農業生產條件比較
由表2可見,1978年與1957、1962年相比,農業機械總動力增加了96倍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倍和12.4倍,農村用電量增加了179.7倍和14.7倍,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是巨大的。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起,在“農業學大寨”的背景下,全國掀起了一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農業機械化高潮,取得了重要成就。據統計,1978年與1957年相比,全國農田機耕面積增加14.4倍;機電排灌面積增加19.7倍,占總面積比例由4.4%上升到55.5%。雖然這一時期在“左”的思想影響下,也出現了違背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現象,但總的說來,成績是主要的,使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上了一個大臺階,“因此可以說,從70年代開始,我國災害防御能力已經有了質的飛躍”[15]。直到進入21世紀,中國現有水利設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16]。
農業生產技術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秈型雜交水稻優良品種開始在南方推廣,取得了顯著成效。從1976—1987年,全國累計種植面積10.66億畝,平均每畝增產108.3公斤,共增產115.45萬噸。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20世紀70年代起北方擴大夏播作物復種面積,將兩年三熟改為一年兩熟;南方發展雙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積增長72.5%。1965—1977年累計增產稻谷4085萬噸,其中靠提高復種增產的占30%[17]。全國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78年與1957年相比,由每畝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產72.4%。
綜上所述,我們對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成因,可以做出一個基本的評價立場一一應當將自然災害和決策錯誤的作用結合進行分析,否認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全面的。
三、以糧食為指數分析自然災害和決策錯誤的影響比重
我們仍然把農村糧食存量作為一個比較指數,這也是許多災害經濟學家考察的方法。因為:糧食在當時作為農業國的中國,是決定國家經濟興衰的基礎,是一條生命線。1959—1961年這三年農村糧食存量減少大致可以分解為三個部分:因災減產;因決策錯誤減產;因高征購而減少。前兩項使農村糧食產量減少,第三項使農村糧食存量減少。
先考察一下因災減產的情況。1959—1961年全國糧食因旱災共減產糧食611.5億公斤[6](p.67),1959年減產糧食378億公斤中旱災損失約為260億公斤[6](p.6)。按照1959年旱災占全部災害損失比例的68.8%計算(1960年旱情超過1959年),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災害減產的糧食數量至少為888.8億公斤。
以“”之前的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為正常標準(1958年數字不實),1959—1961年共減產糧食1241.5億公斤(未考慮年增長率,只能作為一個比較參數,不等于實際減產量)。其中,除去因自然災害減產的糧食數量888.8億公斤,其余的352.7億公斤可以視為決策錯誤減產。
我們再來考察使農村糧食存量減少的主要因素一一高征購(大量增加城鎮和職工人數所多消費的糧食,一般來講,已包括在高征購所得之內)。高征購的決策源于高估產。1958年,根據有關部門正式公布的糧食預計產量3250億公斤計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區征購糧食計劃為579.5億公斤。從表面上看,征購率為17.8%,比上一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來核實1958年產量只有2000億公斤計算,凈征購率(減去返銷農村的數量)就高達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嚴重災害,糧食大幅度減產,而年均凈征購率反而高達22.3%,大大超過1957年。考慮到遭受災害應當減少征購的原則,按照1957年每111.4億公斤糧食占一個凈征購率百分點的比例,1959—1961年的凈征購率應該為15.3%、12.88%、13.2%,三年共計多征購402.7億公斤,則三年農村共減少糧食1644.2億公斤。其中,因災減產888.8億公斤占54%,決策減產352。7億公斤占21.5%,多征購402.7億公斤占24.5%。后兩項都屬于決策錯誤。
至此,我們得出最后的數據:從糧食看,因災造成的減少略大于決策錯誤的減少,兩者之比約為54:46。
三年中農村減少糧食1644.2億公斤,幾乎相當于1959年全年糧食總產量,數額是驚人的。但這仍然不能完全說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農村出現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為,1959—1961年國家通過調入、進口等辦法向農村返銷了大量糧食,三年共546.6億公斤,占總征購量的34.4%[18],那么,這三年實際并沒有多征購,高征購政策似乎不應成為農村發生嚴重缺糧危機的因素。
還有兩個重要的特殊情況值得考慮:
一是高減產、高征購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進口返銷糧食的1961年之間有一個時間差。1959年全國因災減產數量高達378億公斤,占三年因災減產總數的42.5%;而這一年“浮夸風”仍在盛行,“反右傾”后繼續“”,10月,中央批準了農業部1959年全國糧食產量爭取達到6500億公斤的報告,使得遭受災害嚴重損失的1959年反而成為建國以來凈征購率最高的一年,高達28%,比1957年多征購180億公斤,占三年多征購總量的44.7%。1960年,凈征購率仍高達21.5%[13](p.393)。這樣,產量劇減,征購激增,僅滯后半年(征購年度為每乍4月至次年3月底),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到了農村缺糧危機的高峰,后果極為嚴重的河南信陽事件便是發生在這一時期。全國農村平均每人糧食消費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劇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19],人均口糧每天不足一斤,重災區只有幾兩,春荒時期甚至持續斷糧。農村的嚴重缺糧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0年u月3日,中央起草了《關于農村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堅決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12月,國務院財貿辦公室指出了糧食多征購的問題,但其估計仍偏低,認為“1958、1959兩年大約多征購貿易糧200億斤左右。”[18](p.108)從1961年開始,國家大量進口、調撥糧食(1959、1960、1961年調入糧食量分別為-589.8、-169.5、409.4萬噸,進口糧食量分別為0.2、6.6、581萬噸)向農村返銷,凈征購率降為17.5%。但是,當時已經錯過了救災時機,這不能不主要歸咎于1959年8月本應糾“左”卻更加向“左”發展的廬山會議“反右傾”和繼續發動“”的決策。
二是還應考慮一個重要的因素,即1958年起持續至1961年的大辦公共食堂,使得農村寅吃卯糧,缺糧危機高度集中在夏糧未下的次年春季。從理論上講,提前消費并沒有減少農村的糧食存量,但嚴重打亂了農民為維持全年溫飽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現長期的缺糧、斷糧期,不僅不能保證種子和其他再生產的需要,還導致次年繼續人為減產因素加大,甚至影響到生存。以1960年農村每人年均消費156公斤[19](p.336)計算,平均每天消費0.425公斤,但如果辦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費0.5公斤計算,則要出現53天的無糧期。因為無法統計各地農村的積蓄糧食數字和因辦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糧食的頻率,這個因素雖然難以列出數據,但惡性后果是很明顯的。
由此可見,決策錯誤對1959—1961年農村糧食減少的實際影響,并不僅限于上述的比例。從糧食減產看,自然災害略大于決策錯誤;從一個時期的集中缺糧情況看,決策錯誤影響遠大于自然災害。可以說,由于“”和“反右傾”的錯誤決策,使農村因自然災害遭受的損失增加了一倍。這與劉少奇在報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基本一致的。況且,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災害和農業決策錯誤對農村糧食的影響,如果加上大煉鋼鐵等的工業損失,“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成因,更毫無疑問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本文的數字統計和考證,并不是為了重復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斷,而是想說明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的。出現兩者中任何之一,都足以導致經濟困難。如果決策正確,遇到大的自然災害,也遠不應發生如此之大的經濟損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沒有“三年自然災害”,決策失誤雖然會導致經濟嚴重遞減,也不應是集中爆炸性的。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一個人不顧自身體質疲弱奔跑過快,在平地上會摔跟頭,頭破血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現一個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斷骨裂。試想一下,如果“”導致1967年、1968年出現“全面內戰”的極為混亂時期,出現了像1959—1961年那樣的持續大自然災害,經濟損失將比“”時期更不堪設想。所幸的是,“”十年中除1972年是災年外,其余各年災情都在中等以下,這也是一種偶然性。再加上接受“”時期的教訓注意“備戰備荒為人民”并采取了“廣積糧”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經濟建設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既然人類現在還遠不能制止自然災害的爆發,那么,我們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總結教訓、認識規律上,盡量減少自然災害的影響。首先,必須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增強人類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時期只強調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而沒有強調提高人掌握科學技術的素質。對于提高生產工具水平、認識自然界災害作用,也沒有予以相應的重視。這個教訓是深刻的。正是經過了20世紀70年代的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80年代以后改革開放迅速提高綜合國力,使得國家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加強。因此,雖然70—80年代我國的自然災害發生密度大于50年代,呈不斷加劇趨勢,卻再也沒有發生災難性的后果。其次,必須正確認識生產力狀況,采取適應其發展的生產關系,否則將受到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懲罰。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狀況,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生產關系,必然要使損失大大超過自然災害本身造成的損失。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時期的災難,就是客觀規律借自然之手對我們的懲罰。這個沉痛的教訓值得永遠記取。
[參引文獻]
[1]魏杰:《應當建立災害經濟學》,《國有資產管理》1998年第11期。
[2]鄭功成:《重視人災互制規律與害利互變原理》,2003年6月11日《人民日報》。
[3]《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頁。
[4]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5]王維洛:《天問一一“三年自然災害”》,美國《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1期(總第72期)。
[6]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頁。
[7]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
[8]金沖及主編《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8頁。
[9]《、劉少奇、會見蒙哥馬利談話記錄》,《黨的文獻》2003年第1期。
[10]中國國際減災十年委員會辦公室編《災害管理文庫》第1卷,《當代中國的自然災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5、576頁。
[11]《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頁。
[12]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全國農業統計資料》(內部發行),1980年,第45—49頁。
[13]《中國統計年鑒(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422頁。
[14]《建國以來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減輕自然災害報告》,1994年5月日本橫濱聯合國減災大會中國政府文件。
[16]新華社2000年6月10日訊。
[17]《當代中國的農作物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頁。
[18]《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頁。
[19]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統計提要》(內部發行),1980年,第3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