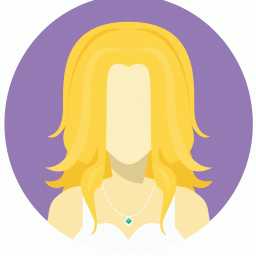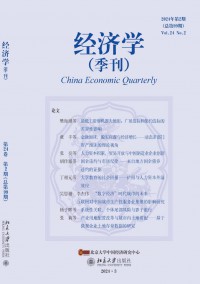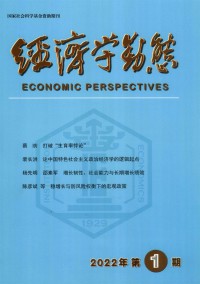經濟學中價值判斷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經濟學中價值判斷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我深深地有感于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來的這樣一種傾向,即哲學家們與經濟學家們的發言互有誤解。我敢肯定,哲學家們多少會有這種印象:經濟學家們在回避那些他們認為是根本性的問題,即影響并進入私人政策與公共政策的價值判斷問題。而且,哲學家們使用價值判斷一詞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對交換價值。他們指的是“道德”或“倫理”價值。在我看來這些哲學家們是正確的。為了有助于說明為什么我們一直在回避“他們的”問題,從而為消除這一隔閡做點貢獻,我將討論三個要點:(1)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經濟學中不存在價值判斷;(2)這種矛盾的現象,部分地來自于這樣一種趨勢:將這些所謂的價值判斷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對政策結論方面的分歧的說明;(3)市場本身(在廣泛的意義上)是發展價值判斷的一種機制,而不僅僅是價值判斷的反映。
1.經濟學中價值判斷之缺乏。內格爾教授在其評論中已經提出了這一點,而且我完全贊同他的看法。原則上,經濟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學科,所涉及的是環境變動對事件進程的影響,涉及的是預測與分析,而并不涉及評價問題。它所研究的是這樣一些問題:某些特定的目標是否可以實現,同時如果可以實現的話,應如何實現;但是嚴格說來,它并不研究這些目標的好壞問題.
然而,經濟學的確涉及到價值判斷問題。首先,沒有任何目標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們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結果之中。第二,我們永遠也不會真正了解我們的全部價值觀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師,弗蘭克·H·耐特通常所說的那樣,盡管我們都一再重復著“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實際上,我們卻將時間花在對其他小事的爭論上去了。而且,這種討論是相關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我們的價值判斷的含義是什么,他們是否是內在一致的。這正是艾羅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貢獻所在,同時這也是一些被稱作福利經濟學的著作的貢獻所在。
而且,經濟學家不僅僅是經濟學家,他們同時也是人,所以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念毫無疑問他會影響到他們的經濟學。“無價值”經濟學只是一種理想,而且,同大多數理想一樣,常常最容易受到人們的椎崇。經濟學家的價值判斷無疑地會影響到他所從事的研究課題,有時也許還會影響到他所得出的結論。而且。正如人們已經提出的,他的結論又會反作用于他的價值判斷。然而這并不改變下面這種根本觀點,即原則上,經濟學中并不存在價值判斷——盡管這次會議用了這樣的名稱。
2.把所謂的價值判斷作為借口。我深深地感到:在許多關于經濟政策問題的爭議中,大部分關于美國經濟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著價值判斷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著實證經濟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經多次發現:在混雜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這樣既有經濟學家又有非經濟學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經濟學家們(盡管起初人們趨于認為他們代表著廣泛的政治觀點),傾向于與非經濟學家相對而結成聯盟。但是,常常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將發現他們自己與非經濟學家們站在一起。他們可能會就一些尖銳的問題而在他們之中展開爭論,但當他們所面對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時,這些分歧就煙消云散了。
然而,即使在經濟學界當中,這一點也同樣適用。近些年來。保羅·薩繆爾遜與我經常在這一問題上產生分歧:即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所應給予的相對側重問題。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羅·薩繆爾遜也會同意這種看法——我們在基本目標或是在相當接近的目標方面的任何差異。它所反映的是我們在所接受的、關于貨幣及財政變動(作為一個方面)與經濟變動(作為另一個方面)的相互關系的各種嘗試性假說方面的差異。
我經常使用的一個例子就是最低工資比率問題。這個例子也會導出同樣的結論。如果我們撇開那些對這一問題有著特殊興趣的人不談,那么,最低工資比率的贊成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分歧,決不是關于目標的分歧,而是關于結果的分歧。雙方面都希望看到貧困的減少。那些象我一樣,反對最低工資比率的人預測:這些法律的結果是使得人們失業,從而增加貧困;但那些贊成最低工資比率的人卻預言這些法律將減少貧困。如果他們在結果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那么他們將在政策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這種分歧不是一種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種科學上的分歧,是一種原則上可以為實證證據所解決的分歧。
為什么處于同種文化之中的人們在政策判斷問題上的明顯分歧大致都屬此類呢?在我看來,原因就是艾羅及博爾丁在他們的文章中所指出的:為避免“不可能”原則而對在基本價值觀念方面的一致意見的需要。來自于不同文化的人們之間的觀點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價值判斷方面的“真正的”分歧。
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預測方面的大部分分歧這一事實——或者是我稱之為事實的這種現象,為下面這種廣泛的趨勢所掩蓋:即將政策分歧歸因于價值判斷方面的分歧。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是:責問一個人的動機,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辯論,或迎戰他的論據要容易得多。通過把與我們持有不同觀點的人視為要想取得“壞”目標的“壞”人,我們可以縮短進行分析及收集證據的艱苦過程,而與此同時,又可以贏得公眾義憤與道徳熱情對我們的觀點的支持。我特別有感于1964年總統選舉期間這種方法所產生的誘惑力。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大部分人民群眾,幾乎斷絕了合理討論的可能性,他們拒絕認識這種可能性;即塞納特·戈得華特可能與他們擁有同樣的目標,只不過是在他關于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的判斷方面是不相同的。
為了避免誤解,我要強調的是,我并不是在斷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歸因于實證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確明顯地反映了價值判斷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把這一解釋留作最后一著,而不是作為最先一著使用的話,那將有助于實現達成合理的一致意見這一大業。
我還要說明的是:在人們的價值判斷與他們關于客觀情況的預測之間,毫無疑問地存在著一定的相互關系。存在著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復雜的相互關系。然而在這一問題上,我無可奉獻,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談。
3,市場在發展價值判斷中的作用。我的第三個要點與博爾丁的文章聯系得更為緊密一些。博爾丁將“精心計算的盈虧”作為經濟交換的本質,他對于經濟交換的局限性的看法,與J·M·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論述中所如此恰當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觀點非常相似:“對不帶偏見的理性的無理性的熱愛,奪去了生活的樂趣。”博爾丁最后還討論了為完成市場交換(按照狹義的定義)所必需的一體化制度。
雖然博爾丁的論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們僅限于經濟分析與價值判斷之間的關系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場作為很多人在共同價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種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論這些共同價值是市場上的交換比率,還是博爾丁所提出的一體化制度的組成部分。在這一方面,與狹義經濟下的情況相比,“交換”與“市場”有著遠為廣泛的含義。我的論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那些初看起來與狹義經濟構成物一樣的東西的更為廣泛的關聯上去。
博爾丁強調的是市場交換的報酬特征。這一特征恰恰是一項交易成為自愿的必要條件。除非交易的每一個參加者都能夠得到某種他認為比他放棄的東西更為值錢的東西,否則的話,他是不會進入交易的——如果那種不能使交易雙方獲利的交易得以發生的話,那么交易的參加者則必須受到強制。在一“自由”市場中,參加者必須‘心悅誠服”,這與“受賄”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
交易要想發生,參加者的價值觀念必須是有差別的。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時雙方都認為X物品優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來換Y物品的交易永遠也不會發生。唯有當A先生認為Y物品的價值高于X物品的價值,而B先生認為X物品的價值高于Y物品的價值時,用X物品換Y物品的交易才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A與B兩人都從用X換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處,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礙,否則的話,這一交易將得以發生。正如這個小小的例子所說明的,交易的本質是不同的價值觀念的協調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點的情況下,一致意見的取得。與用所有的X來交換所有Y的一次性交易活動不同,如果我們將X與Y看作是可分割的總量,而且交易是逐漸進行的,那么,A先生與B先生之間的交易將繼續下去,直到在邊際點上,兩人對僅存的X或Y都賦予同等的相對價值。從這一意義上說,他們通過交換而取得了關于價值的一致意見。然而,這種一致僅在他們之間交易的現存點上才是成立的。盡管交易的結果是使得A先生擁有(比如說)大部分的Y,而B先生擁有大部分的X,但他們倆人對于早先的這些交易都是非常滿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參與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點的情況下取得一致意見的過程也就拓寬了:通過整個市場,所有參與者亦將在邊際點上獲得共同的價值觀念。正如諺語所說的那樣,需要有意見的分歧才會存在賽馬,而且對結果下賭注的機會,使得意見的分歧成為共同滿足的源泉,而不是爭端的契機。
同樣的分析直接適用于自由言論及自由討論。同樣,言論的自由并不意味著擁有聽眾,正如售賣的自由并不意味著有買主一樣,這僅意味著尋求聽眾與買主的機會。在思想市場上,只有當講者與聽者雙方都能獲利時,交易才會發生。同樣,交易要想圓滿完成,通常要求意見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經歷比與一個在一切方面都有著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進行交流更為乏味的了——盡管在一切方面意見完全一致這種概念明顯地只是一種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們中甚至沒有誰能與自己完全一致。
自由言論的本質與自由交換的本質一樣,在于參與者的雙方獲利。希望在于:在這一過程中,在我們每個人都有所得的同時,它使得我們得以協調我們的分歧。實際上,我不應該說“與自由交換一樣的自由言論’,因為自由言論是自由交換的一個特例。
類似地,我們來考慮一下學術自由,或者追求人們在研究與寫作方面的智力興趣的自由,如果將知識分子引入產品與勞務市場的那種分析,也應用于這一領域,那么,很多人,或許是大多數人,將不得不反對這樣的自由.他們將悲嘆于這樣的“混亂”局面:這種混亂局面使每個人為他自己而決定什么是重要的;他們將悲嘆于這樣的“重復”與“競爭浪費”,這種重復與競爭浪費使得不同的學者在研究同樣的問題;他們還將悲嘆于在確定哪一些問題應該予以研究的重要問題時,“社會優先權”的缺乏。他們將轉而呼吁中央計劃,用一管理體系來決定哪些問題最需要進行調查研究,將各學者分派到他們將能(按照那種管理體系的判斷)作出最大貢獻的領域,確保不存在重復勞動的浪費,等等。
這一點顯而易見,所以知識分子更會了解這個問題,他們知道;如果在這一領域中,在價值觀念及知識方面人們的意見完全一致,那么,這樣的中央計劃則毫無害處——同時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與無知程度下,他們更喜歡要自由競爭市場的“浪費”,而不喜歡中央計劃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論證(這一論證也與我的預見相一致)又加強了他們的這種偏好:與對有選擇的幾個機構的依賴相比。這是豐富我們的知識的更為穩妥的方法。遺憾的是,他們并沒有認識到在將完全不同的標準應用到產品市場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
博爾丁強調指出;“經濟學家通常帶著一種近乎于迷信的敬畏來看待價格體系”,而且常常驚奇于“在決策的制定及決策的相互影響中所反映出來的那種難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換的更為一般性的應用,也引起了同樣的看法。整個現代科學知識的宏偉體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場上,為自由交換所建立的。或者再來考慮一下另一個例子,即語言的發展。語言是一個能夠不斷演化的、相互關聯的、復雜的結構。然而,并沒有人那樣地計劃它。它只不過是經過為自由的語言交換所協調起來的、成千上萬的個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公共法律結構是另一個出色的例證。
我的討論是從博爾丁提出的那個觀點開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這一點上:即對一體化制度的需要,我將這一需要解釋為對一系列共同的價值觀念的需要,而為了任一穩定的社會的存在,在大多數時候,這一系列共同的價值觀念必須無須考慮地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這些價值觀念是如何發展、變化,并最終為人們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這樣一系列價值觀念(它們仍存在著變動的可能性)的理想機制呢?這正是我所提出的經濟分析能夠對政治科學家及哲學家作出最大貢獻之處。原因在于:它揭示了這樣一種結構如何能夠從個體人類的自發的、且自愿的合作中,產生并得到發展,而并不需要由達觀帝王、貴族政治論者、總統或立法人的實施、建造或立法來實現——盡管對于這一結構的發展來說它們都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構成了自由市場在產品及思想領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類得以在研究與發展價值觀念的進程中攜手合作.
勿庸置疑,價值觀念的社會演化過程,并不能確保所發展的一體化體系,與你我在我們的價值觀念下所喜歡的那種社會相一致——的確,實踐證明:這是最不可能的。人類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難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無疑問,需要進行調查研究的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什么樣的一體化體系將與我們所尊重的那種社會相一致,什么樣的環境將有助于這樣一種體系的發展,而且,在什么樣的程度上,關鍵因素是這一過程本身——例如自由討論——或者,這種一體化體系的廣泛內容是什么。我們中的每個人,當他力圖影響他同伴的價值觀念時,就構成了一體化體系的這一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正如他必須做的那樣,都在剛才所提出的那些問題的嘗試性答案的基礎上前進。所以,在如此這樣的會議中,我們同時既是演員又是觀眾,既是觀察家又是被觀察者,既是老師又是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