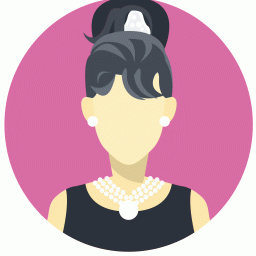德里達傳播哲學與方法論啟發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德里達傳播哲學與方法論啟發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符號的分異、延擱加深了符號的不確定性。如此一來,符號就不存在所謂恒定性的本源意義,一切符號意義都是在一個巨大的符號網絡中被暫時確定,又不斷在差異和延宕中出現新的意義。簡言之,德里達通過"延異"體現了解構的基本立場:世界上不存在所謂終極不變的意義;符號只存在不斷分延著的符號語境中的流動著的意義,意義選擇充滿了無窮可能性。
一、播撒(dissemination)
這是對"延異"一詞的進一步擴展。在德里達看來,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功能。由于文字的延異所造成的差異和延緩,意義的傳達便不可能是直線傳遞的,不可能像邏各斯中心主義所宣稱的那樣由中心向四周散開,而是像種子一樣,將不斷分延的意義四處播撒,不斷地以向四面八方散布所獲得的零亂性、松散性來反對中心本源,并拒絕形成任何新的中心。作為解構策略的重要之維,播撒以瓦解一切的主宰姿態,"試圖挫敗這樣一種企圖:以一種頗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義或知識"[1]5657。換言之,播撒試圖進一步消解那種通過等級秩序而獲求明晰的意義去把握真實的可能性,顯示出在無始無終的符號延異網絡中的文本自主性。播撒揭露了文本的零亂、松散、不完整、非自足性,標志著一種不可還原和生生不息的意義多樣性。
二、蹤跡(trace)
所指被延擱所造成的符號殘缺不全,使其永遠成為指涉其他符號的一組蹤跡———對德里達來講,語言一旦以"延異"為基礎,符號就變成了"蹤跡"。一個符號總是要借助其他符號來界定其意義,在它上面留下它們的"蹤跡"。蹤跡指向延異,它永遠延擱意義。這樣一來,文本就不再是一個超驗所指的給定結構,不再是一個意義明確的封閉的單元,而是一系列的"蹤跡",它沒有一個終極的意義,只為我們提供了多種可能性。(四)替補(supplement).一方面替補既是一種補充增加,是存在的增補和積累;另一方面,它雖是附加的、次要的,但在增補過程中又成了取代者。替補因存在的空虛而起,是存在不完善的證明,這樣作為替補的東西和被替補之物之間的絕對區別就消失了。"替補"否定了形而上學所信奉的絕對真理的神話,將追問本源、抱持永恒意義的回歸之路置換成一條永遠走向不確定性、增補性、替代性的敞開之路。
簡言之,通過延異、播撒、蹤跡、替補等策略,解構主義揭露了邏各斯中心主義所假定的結構的確定性、封閉性、中心性的人為荒謬性,將其還原為敞開的、非中心化的、充滿差異的、無限流動的,它產生具有無限可能性的意義網絡。解構主義進而瓦解了邏各斯中心主義所信奉的絕對真理、絕對意義的神話,表明固守絕對意義是一個不可能的、自我毀滅的夢想。在解構運動中,"意義"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它再也不是單一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多重的、不穩定的和擴張的,它存在于運動的過程中。而意義的運動正是傳播學的研究內核。傳播學以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和傳播現象為研究對象。傳播活動是人們相互溝通、傳達指令、享受娛樂、展開討論、獲取信息的日常行為。但是,無論我們選擇傳播現象的任何層面對其進行考察總有一點是我們始終無法回避而必須確認的,那就是在復雜多樣的人類傳播活動中,相伴始終的是‘意義''''的動態活動過程。"[2]56傳播是人類社會的信息交流活動和過程,同時,人類社會的傳播也是一種精神交往活動,一個斯圖亞特•霍爾所說的"編碼/解碼"的"‘意義''''的運行過程"[2]56。信息的流動與意義的運行構成了傳播的兩種屬性。但是,就人的世界的角度來看,就傳播學的人學角度來看,信息的流動僅僅是傳播的物理形式和載體,它所承載的"意義"更體現了傳播的人文價值:意義體現了人對世界的認識、理解和構建,"體現了人與社會、自然、他人、自己的種種復雜交錯的文化關系、歷史關系、心理關系和實踐關系它是人類交往的紐帶,文化傳播的橋梁,自我理解的媒介。沒有意義,人類社會不但無法繼續下去,而且也無法存在。因此,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意義的社會"[3]23。意義"具體體現為人類思想傳遞和交流載體的符號系統"[2]57———意義的構建活動"是由廣義的人類傳播活動來實現的"[2]57。而人類的傳播活動也正是由于意義的構建活動體現了人和世界的關系,才成為人類的基本活動。因此,信息流動只是人類傳播活動的表層現象,傳播更是人類社會意義構建的活動和過程;傳播活動中的意義構建是我們研究傳播問題所不可忽視的領域。就此而言,德里達解構主義哲學也就構成了某種傳播哲學。這種傳播哲學對意義的構建進行了深刻的重新思考,凸顯出意義的開放性與多元性:無止境的差異與延緩取消了符號意義的確定性,一切符號意義都只能說是在一個巨大的符號網絡中被暫時確定,又不斷在差異和延宕中出現新的意義。意義不可終極,它的選擇充滿了無窮可能性;延異所造成的區分和延擱,使意義的傳遞不是遵循一定的等級秩序,而是向四面八方播撒開來,零亂、松散,沒有中心本源,也不以形成任何新的中心地帶為目標;所指被延擱,符號只構成了指涉其他符號的一組蹤跡而非提供一個終極的意義。文本不是一個意義明確的封閉的單元,而是成為一系列的"蹤跡",它們提供了多種可能性;這些"蹤跡"是非自足性的,它們處于不斷的"替補"運動中———本文敞開著,本文外面的東西不斷涌入對原有的蹤跡進行替代、增補,意義就是這樣無限流動、生生不息。
德里達解構主義哲學對意義的深入思考與探索實際上構成了一種宏觀的傳播學研究。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它展現給傳播學研究者的是一種新的意義觀。在其理論視野中,意義是不可終極的,它敞開著,無限流動,以零亂松散對抗著中心性和等級秩序,并且具有生生不息的多樣性。這是一種迥異于形而上學傳統的、充滿生機的意義觀,一種新的傳播理論的視野。長期以來,邏各斯中心主義統治著人們的思維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它信奉意義的確定性、封閉性、穩固性、中心性,追求通過等級秩序深入中心而獲得某種絕對的真理。相對于德里達解構主義哲學凸顯開放性與多元性的宏大而開闊的意義世界,這種追求所謂恒定性的本源意義、終極意義、絕對真理的意義觀顯得荒謬而狹隘。換句話說,德里達解構主義哲學解放了一直以來為在場形而上學所封閉、僵化和教條化了的意義,復活了意義的廣闊自由和無限可能性。因此,德里達解構主義哲學關于意義構建的重新思考不僅已經構成了一種宏觀的傳播研究,而且是一種富于解放性內涵的傳播哲學。
三、方法論啟示:建構包容“一種語言以上”的體驗的傳播情境
傳播,是人類社會構建意義的活動和過程;意義的生產與交流,是傳播學的內在研究領域。"但是,長期以來,傳播學研究領域對傳播問題的認識,就具體的傳播現象的構成研究較多,而對深層意義構建關注較少。"[2]57在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看來,傳播的傳遞觀和傳播的儀式觀是美國自19世紀以來對"傳播"的認識的兩大主要傾向,而其中傳遞觀的研究又占有明顯的主導地位。所謂傳播的"傳遞觀",即把傳播活動理解為"傳遞",認為傳播是一個訊息得以在空間傳遞和的過程,以達到對距離和人的控制。而就目前傳播學界的研究來看,相對而言,較多地展開的也是對傳播作為信息傳遞的基本模式的研究,而對建基于信息流動基礎之上的意義生產活動關注較少[2]57。反觀德里達解構主義傳播哲學,其富于解放性內涵的意義觀可以給我們許多有益的啟示,開啟一種立意高遠、視角開闊的意義研究,而這種研究將有助于推動當前傳播情境的改善。正如德里達所說,"解構不是拆毀或破壞"[4]18,解構主義傳播哲學是一種富于建設性的傳播學意義研究,它呼喚以一種充滿生機的思維方式建設包容"一種語言以上"的體驗的多元化、沒有壓迫的傳播情境。
(一)釋放意義自由,還原無限
德里達解構主義傳播哲學既提示了一種編碼方式,也提示了一種解碼方式,即釋放意義自由、還原意義的無限可能性。換句話說,解構主義啟示我們無論是在編碼還是在解碼運動中都應打破意義的牢籠,避免各種固定的、僵化的思維模式抑制意義自由、思維自由。編碼過程亦即文本的書寫過程"是一種‘延異'''',即‘產生差異的差異''''。這種‘延異''''在時間和空間上既沒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為這種運動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標準,也沒有此后的確定不移的目的和發展方向,更沒有在現時表現中所必須采取的獨一無二的內容和形式"[5]。因而在傳播活動的編碼過程中要正視"延異"的這種特性,避免走入追求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標準和固定的絕對化的誤區。另一方面,在解碼過程即文本的閱讀過程中,德里達說:"沒有一種自在的、對一切時代都適用的對存在和世界的闡釋,闡釋并不意味著在事物或文本的外殼下找出一種完整的、固定不變的意義"[6]35。按照傳統闡釋學的觀點,闡釋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并使之絕對化和標準化,其目的就是要限制文本所表達的意義的歧義性、多意性和不確定性。如此闡釋以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傳播哲學來觀照顯然帶有狹隘的非正義性:闡釋文本的重點并非發現原文本所謂的完整、固定的意義,而是使作者及其歷史條件獲得重生,使文本的書寫過程在被閱讀和闡釋的差異化中復活[5]。解構的原則啟發我們改變并且放棄追求一種絕對的、固定不變的意義的自我封閉的做法,復活意義的自由,還原意義的無限可能性,無論在編碼還是解碼運動中都應避免將無限以某種有限的形式給出,或是將某種有限夸大、抬高成無限。這里必須澄清的是,釋放意義自由、還原意義的不可終極性,"并非荒謬地試圖否認相對確定的真理、意義、特性、意圖、歷史的連續性這些東西的存在"[7]175,而是要反對意義的僵化,承認并且正視意義處于永恒的運動過程中,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生長的過程:你盡可以說你已經接近了真理,但你卻無法聲稱你已經掌握了絕對的真理。這樣一種對意義的哲學認知有助于從根本上極大地提升傳播活動以及相應的傳播學研究的寬容度和開放度:對意義的無限可能性有所了解,我們不僅能夠對傳播過程中的編碼和解碼運動所體現出的差異化和多樣化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持更寬容的態度,尊重意義的多元化,而且可以使我們不再視意義的不斷更新變化(例如時下流行的對經典影視作品的翻拍)如洪水猛獸。因為解構的原則使我們看到了意義天然地是敞開的,處于無限流動和不斷的生成中,這是不可抵擋、無法變更的事實。我們需要做的是以一種開放的心態正視意義的歷史性變化,容許意義的重新闡釋和重新建構,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堵截。
(二)復活意義的個體性、精神性
意義是基于對象的解釋和思想。在解構主義傳播哲學看來,既然沒有一個本源性的意義,本文便成了一個無限開放的東西,闡釋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著原文本留下的一系列蹤跡,在自由游戲過程中創造新文本。或者說,闡釋者對原有的蹤跡進行主觀性的增補,生成屬于自己的意義。這種意義始終都是構建性的,打上了他們各自特定的精神性情、主觀志趣的烙印,因而是獨一無二的。在解構主義的視域中,意義的構建具有個體性、精神性特征。同一個信息或者說同一個蹤跡極有可能在不同的個體那里引發不同的主觀替補,從而構建出不同的意義。意義的個體性與精神性已經融進了解構主義傳播學的基本視野和理論品格中。反觀目前正統的傳播學領域,主流傳播學研究并未充分關注到意義構建的個體性與精神性。占據主導地位的美國經驗主義研究范式雖然十分重視受眾研究,但在其實證研究模式中,受眾只是被簡單視為一種客觀存在的外在事物,"淪為沒有個性差異的可以進行統計測量的存在"[8]。可以說,在迄今為止的主流傳播學中,受眾是以非個體性、非精神性的形象出現的;受眾概念的非個體性與非精神性是經驗主義傳播學的一個方法論和世界觀的基本視野。雖然在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受眾研究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和改觀,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進行研究方法的轉換,意義的個體性、精神性并沒有在主流傳播學那里獲得獨立的品格。個體性與精神性既是人類個體存在的基礎,也是文化科學存在的基礎,更是人類的精神科學或文化科學變化發展的動力學基礎[9]。喪失了對個體性、精神性的關切,就不成其為精神科學或文化科學。傳播學是一門文化科學,是人的科學,是精神科學,也就應該是一種進行個性探索的科學。這就意味著,傳播活動中意義構建的個體性與精神性,應當成為傳播學的一個基本視野。但是,主流的經驗主義研究范式卻將重心置于外在客觀性,根本上不理解個體性與精神性的人文價值與學科意義,正在使傳播學日益偏離文化科學的軌道。在此語境中,解構主義傳播學方法論再次凸現了它的價值,它對意義的個體性、精神性的關注有助于彌補經驗主義研究范式片面倚重外在客觀性的缺陷,使意義的個體性與精神性融進傳播學研究的基本視野和理論品格中,從而使傳播學真正成為一門進行個性探索的文化科學、一門人的科學。
(三)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義,建設包容多元化體驗的傳播情境
解構主義是一種破除一切中心話語的態度,它要瓦解一切的主宰姿態,還原多元化。德里達認為,支配著西方哲學與文化的二元對立思維建構了一種非常有害的價值等級體系,在那里,"沒有對立雙方的和平共處,而只有一種暴力的等級制度。其中,一方(在價值上、邏輯上,等等)統治著另一方,占據著支配地位"[1]56。這種二元對立構成迄今為止一切社會等級制和暴戾統治的理論基礎。換句話說,由于沒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義,整個哲學傳統在意義深處與同一的壓迫和集權主義沆瀣一氣。解構主義則體現出非凡的氣度,因為它是根據他者面孔的絕對先在性而得到把握的。解構主義看重的是差異與多元,而非矛盾與對立,中心主義在解構主義看來只能導致自我毀滅。因為在解構主義的視域中,差異是無止境的;意義零亂、松散,沒有中心本源并且拒絕形成任何新的中心;蹤跡只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而沒有終極的意義;替補更是存在不完善的證明,那些貌似不容置疑的先驗假定前提、基本概念和絕對真理其實都是空虛軟弱、站不住腳的。因此,通過森嚴的等級結構以一種頗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明晰的意義去把握真實就是不可能的,只能人為地造成某種壓迫情境。解構主義的目標就是要介入,瓦解人為的等級結構,消解虛假設定的中心,對不能被還原之物說"是",從而修復正義。以解構的視角觀察當前人類的傳播活動,我們會發現其中也或隱或顯地存在著二元對立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凸顯了某種中心、霸權。最突出的便是男性/女性、西方/東方、大眾傳媒/受眾視角的二元對立,其中隱含著男性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大眾傳媒中心主義的霸權,對處于他者地位的女性、東方、受眾造成了壓抑。傳播的目的是促進意義在人群中的交流與溝通,而在現實的傳播情境中這種交流與溝通卻由于沒有正確地對待他者而畸變為某種壓迫與暴力。霸權擠壓差異,傳播因此成為非正義的。同時大眾傳播本身也隱含著大眾傳媒的暴力。信息單向地由大眾傳媒流向大眾,這種單向傳播模式賦予了大眾傳媒霸權地位。雖然近年來隨著新媒介的興起,傳統的單向傳播模式受到沖擊,受眾的傳播權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復,但是總體來說,大眾傳媒仍然占據著大眾傳播的中心地位,大眾仍然是失語的一方。因此,取消傳播場域中的二元對立結構,破除種種導致壓迫的中心主義,從而營造一個平等、公正、多元的交流情境,就成為亟待解決的傳播學課題。因為只有消解二元對立結構、取消"中心"的暴力,才能實現傳播的正義。我們的目標是要使尊重差異成為人們在交流過程中的共識,明確"交流是差異的舞蹈任何交流的成就,都是差異的和諧樂章"[10]60,從而使與他者的關系體現出正義;同時,改善人們的媒介近用權,保障人們的傳播權利,或者說,保障人們的話語權。在這個角度上我們說,解構主義傳播哲學展現了能夠包容"一種語言以上"的體驗、沒有壓迫的理想的傳播交流情境,它可以引領我們去除目前傳播領域中存在的種種霸權,推動傳播之正義的實現。
四、結語
解構主義傳播哲學的無中心、差異化的多維思路開啟了一種開放的、無限界的意義觀,這樣一種對意義的認識論有助于人們跳出傳統的思維體系,從更高的、更廣的視角觀察和思考意義與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意義的不確定性和生生不息的多樣性,使我們了解人類任何時候的差異化都是在共時和歷時的橫縱軸上發生的,文化就是在延長和被擱置的過程中成為一種無限發展的可能結構。這就可以啟發我們破除那種執著于追求一個權威、一種絕對正確的標準、一個答案的單線式思維,在傳播活動中尊重與我們相異的他者,還原"一種語言以上"的體驗。解構主義傳播哲學是一種批評立場,它描畫出具有高度兼容性的多元化、沒有壓迫的傳播交流圖景。只有當包容"一種語言以上"的體驗的傳播情境真正建立起來了,才能還原人類文化發展的自由。這也意味著,吸取解構主義方法論有助于極大地提升傳播學的學科品格,使其成為一門解放性學科。
作者:陳旭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