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音經題記中孝道思想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觀音經題記中孝道思想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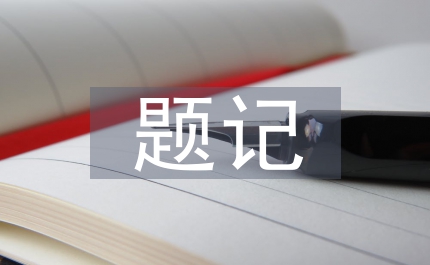
光緒二十五年(1899)敦煌藏經洞文物重現于世,專家們從敦煌遺書赫然發現各種體裁的佛教孝道文獻,多為前所未見的唐五代抄本,彌足珍貴,極具研究價值。潘重規先生說:“等到敦煌石室開啟,文獻資料漸漸流布,我們才看清佛教徒提倡孝道的事實,他們力量之偉大,影響之深遠,方法之周密,實在令人欽佩贊嘆不能自己。”(潘重規:《從敦煌遺書看佛教提倡孝道》,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主辦《華岡文科學報》第12期,1980年3月)。
有關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關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規《從敦煌遺書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鄭阿財博士論文《敦煌孝道文學研究》一書,探其內容主要有俗講經文、佛教歌詠及佛教齋會三方面。由于筆者多年來關注《觀音經》在中國的流傳與弘揚,故于敦煌遺書的《觀音經》抄經題記中,發現許多造經者基于中國孝道思想為親人抄寫《觀音經》。為此,本文擬從《觀音經》抄經題記中探討有關孝道思想的文獻,一則說明抄寫《觀音經》也是佛教徒表達孝思的方式;其次說明敦煌《觀音經》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響,并與凈土信仰結合,使觀音在中國成為超渡亡靈、接引往生西方凈土的重要菩薩,而孝子們對菩薩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觀世音菩薩與《觀音經》在中國的地位不斷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產生
冉云華先生總結說,在印度經典與龍樹山出土的碑銘中,可以知道印度社會雖然也重視孝道,但不像中國佛教,孝被視為“天地之本”。由于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對孝道的重視遠勝于印度,因此中國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壓力遠比印度沉重(冉云華:《中國佛教對孝道的容受與后果》,收入《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頁)。
中國原本重視孝道,當佛教傳入中國,最為中國傳統社會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發”與“無后”二項。中國佛教祖師為了使佛教見容于國家、社會,遂積極闡揚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譯佛教孝道經典”、“注釋印度孝道經典”及“闡揚佛教孝道思想優于儒家”等三個方面。佛教歷經幾個世紀與儒家論辯后,經過一次次質疑,最終積極地建構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僅因此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為中國特有的文化資產。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獻
敦煌雖地處邊陲,但與中國政治與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對于孝道的重視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間主要的教育機構,其兒童教育教材以《孝經》為最主要內容。如前賢的研究,敦煌藏經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獻,主要有俗講經文、佛教歌詠及佛教齋會三方面。
這些作品主要說明孝順必須出于真心,且實踐于晝夜十二時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僅在世能消災免難、得富貴、獲封侯;死后還可升往極樂凈土。此外文獻中也常引用《孝經》、《論語》、《曲禮》等儒家經典來互相印證,并說“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贊揚,反映出敦煌儒釋兩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還將儒家推廣《孝經》的事跡編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號“皇帝感新集孝經十八章”第三首:“歷代以來無此帝,三教內外總宣揚。先注《孝經》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剛》。”歌曲中這位廣為敦煌百姓歌詠的皇帝,就是天寶三年下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見唐代政策確實擴及于敦煌。當然敦煌地區也像漢地一樣,流行參加盂蘭盆會,藉以供養三寶,超渡先亡,并為生者祈福。遺書中有:伯2055佛說盂蘭盆經,乃翟奉達為妻馬氏追福,每齋寫經一卷;另外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尚有敦煌盂蘭盆經卷子以及“二太子盂蘭節薦福文”的超度疏文。顯然敦煌地區并沒有脫離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圍,釋門徒眾反而極力會通儒、佛兩家的孝道思想,而創作出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獻,其目的無非是啟發人們的善根,強調學佛不離世間,尤其必須要盡倫盡分、恪盡孝道。在如此重視孝道的文化環境中,我們可以從敦煌大量的遺書題記發現,子女也常為父母抄經祈福或超薦度亡,敦煌《觀音經》抄經題記中就有不少這方面的記錄,以下逐一說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觀音經》題記
在注重家庭人倫“孝道”的中國環境中,子女面對父母的去逝,不免傷痛;對于父母的追思,傳統儒家亦強調“喪則致其哀”,習俗必須守喪,甚至要遵從國家所立服喪的嚴規。而佛門所闡揚的孝道思想,除了說到能與儒家一樣做到這些世間的孝道,更強調使父母脫離輪回之苦、獲得往生凈土的出世間孝道。敦煌佛教對孝道思想的闡揚,正是深受漢地的影響,所以從敦煌孝道文學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弘揚者極力宣揚佛弟子必須于父母在世時,勸化其持戒修行;父母喪時,不像儒家殺生祭祀,增重父母惡業,而是延僧誦經作七超渡,或親自參加盂蘭盆會、書寫念誦佛經、敬造尊像、佛經變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號有題記的《觀音經》造經中,有十三部是子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眾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經題記
從所見《觀音經》抄經題記來看,在家者為超薦亡父母的題記,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張海晟為亡父的抄經。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張氏為超渡七代父母所寫這部經是與《無量壽觀經》合抄,說明七世紀中葉以后敦煌《觀音經》信仰與西方凈土信仰已密切結合。這類“凈土觀音”的信仰當是受到西方凈土經典的影響,而從唐高宗、武后開始廣為流行,并且歷經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論貧、富、貴、賤,人們不僅深信書寫、受持、讀誦《觀音經》能免除人世的災難,而《觀音經》中的觀世音菩薩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謂是冥陽兩利。敦煌孝道文學作品中,除了描述母親懷胎十月的艱辛以啟發子女孝心,更極力強調侍奉父母當和顏悅色,對于孔子所說:“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許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對于那些未能親自孝養父母、離鄉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號“父母恩重難報經講經文”也說到:“經求仕宦住他鄉,或在軍中鎮外方;兒向他州雖吉健,母于家內每憂惶。心隨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斷腸。”講經文指責的是忘卻父母恩德、拋棄父母于不顧的不孝之子。這類人雖然榮華富貴,但因為見利忘義,背棄人倫,所以特別為中國社會所不容,往往被稱為連禽獸都不如。然而,羅振玉舊藏唐至德二載(757)長孫顏夫婦的抄經,所呈現的是中國人最傳統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三日,攝豆盧軍倉曹參軍、宣節副尉、守左衛西河郡六壁府別將長孫顏妻清河路氏,為亡妣遠忌敬寫《觀音》、《多心經》同一卷。
長孫顏官拜“攝豆盧軍倉曹參軍、宣節副尉、守左衛西河郡六壁府別將”,他是豆盧軍軍糧的負責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與陜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將領。這對武官夫婦顯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棄人倫的負心人,從題記中可以知道他們雖然身處異鄉,但適逢亡母忌日,難掩思母之情,遂親自恭敬書寫《觀音經》與《心經》各一部,為亡母追福。從這條題記,我們看到佛教傳入敦煌后,抄寫《觀音經》也成了中國人家族祭祀、慎終追遠的重要宗教活動之一,敦煌的《觀音經》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經題記
誠如前言所說,佛教傳入中國后最為人所詬病的便是“剃發”與“無后”兩項。僧佑《弘明集》記載反佛人士引《孝經》,首先對牟子提出“剃發”的問難:“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沙門剃頭,何其違圣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責僧人出家修行,有違孝道“無后為大”的觀念:“福莫踰于繼嗣,不孝莫過于無后;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2,第2~3頁)雖然牟子極力辯論,佛門為此所受到的責難卻有增無減。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佛教祖師為了順應民情,遂積極闡揚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盡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獻中,我們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觀念的引導者,也是實踐者。僧人除了以各種活潑善巧的方式宣揚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樣,藉由參與抄經、造像、法會等宗教活動,為俗家的父母親追福。如斯4366號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統十六年(550)為先亡抄《大般涅盤經》卷十二;另外甘博002號卷子,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為七世宗師、父母等抄《大集經》及《入楞伽經》。這些僧人的愿求,與前述在家信眾的抄經題記,基本上沒有很大差別,也就是相信不論造的是大小乘經典,都有利益現世生者與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樣的觀念可見于敦煌僧人的《觀音經》抄經題記。
在有紀年的題記中,僧人抄寫《觀音經》的比例僅是在家信眾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開元廿五年(737)才出現,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趨勢,但又沒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寫《觀音經》的現象。其中120號題記曰:“開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師師為身亡寫《觀音經》一卷。”從題記中可以知道,這是某人為亡者抄經的愿文。但是文內的“弟子支師師”意味著三種可能:(一)姓“支”名“師師”的佛弟子為某人抄經;(二)姓“支”名“師師”的佛弟子,為自己未來身亡預寫經典。(三)是僧人“支師”為其師父身亡親自寫經。若采用第三說,則“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蓋道安法師統一僧人以“釋”姓之前,中國的僧侶出家后多從其師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9,第341頁),而“支師”這份寫經也說明晚唐時期敦煌佛教對于出家姓氏仍沒有嚴格的規范,且約定俗成的力量也還不是很強。其次,“支師”的題記不禁令人想到中國人“尊師重道”的觀念,儒家五倫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種的人際關系,師倫雖未列入,但《禮記·學記》說:“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可見老師在儒家的人倫關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韓愈更說道:“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對師長應保持恭敬與感恩,都是僧俗應該有的基本修養。“支師”為師身亡,而以中國的書寫工具與方式發心抄經,除了說明西域胡僧對《觀音經》的信仰及漢化的事實及他們對于華、梵“師道”傳統的接受,也似乎讓人看到了中國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影子。
北新879號寫卷,是晚唐天復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區寺院住持,虔誠刺血抄《金剛經》與《觀音經》各一卷。由于整個愿文所回向的對象,涵蓋“四生九類”、“水路飛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經愿文,看來三峗禪師似乎將法會祈愿模板,作為個人抄經愿文。如文說:“……師僧父母,各保安寧;過往先王,神生凈〔土〕。……”但這類愿文中“孝道”與“師道”觀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項目之一,而僧人寫作的順序也置“師僧”于“父母”之前。可見,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經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強調對父母的孝道。S.3054號是后梁貞明三年(918),報恩寺僧海滿為亡父所造,并委托師兄弟勝智抄寫。它與其它《觀音經》抄經最大的不同,是海滿特別回向父親往生“彌勒凈土”,而不是廣泛的“凈土”或“西方凈土”,說明了五代時期報恩寺觀音信仰與彌勒信仰并存的現象。從這三條題記可以知道,隨著《觀音經》在敦煌流傳幾百年來,觀世音菩薩在人們心中的地位與功德幾乎提升到極點,抄一部《觀音經》的功德,也幾乎等同一場水陸等法會的效力,觀世音菩薩可以圓滿人間孝子的各種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隨愿往生各種凈土。
五、結論
佛教傳入中國后,其出家的制度由一開始被批判為“不孝”,但經過近千年的內部調整與吸收儒家思想,到最后反倒成為極度闡揚中國儒家孝道與佛家孝道的宗教,這些文化情感的反射不獨被保留在無數的佛教史籍中;敦煌藏經洞那數以萬計的斑斑墨跡,無不訴說中國佛教徒血液中,始終流有一股不可分離的“孝道”思想。隨著歷代帝王對儒家思想的提倡,并藉由各種法律與教育制度,“百行孝為先”的觀念已根植人心。雖然敦煌地處邊陲,但從藏經洞的豐富的《孝經》與佛教孝道遺書來看,敦煌十七所寺院是儒、佛并重的主要的教育機構,而“孝道”是所有教育的基礎;而儒佛教孝道思想在敦煌融合的事實,更可見于當地僧官“闡揚三教大法師”的頭銜中。儒家特重對父母生前盡孝,但對于死后的世界卻不多談。然而人們對于死后的世界是害怕、好奇,而孔子對于“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篇》)的回答,終究無法填補子女喪親的哀思,所以當《觀音經》中的觀世音菩薩,有如慈母般以其廣大神通力與無盡的慈悲,宣誓要傾聽眾生的苦難并以千百億化身救渡一切有情時,我們看到無論是平凡百姓、達官顯貴甚至是出家僧侶,都成了觀世音菩薩最虔誠的供養人,而觀世音菩薩果真是“此人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為說法”。從《觀音經》抄經題記可以看到,他們大半的愿求是為過世的父母、乃至七世父母追福、拔薦;尤其在唐代《觀音經》信仰又與凈土系的“凈土觀音”信仰密切結合時,有許多的愿求是希望觀世音菩薩能接引亡父母往生西方凈土,于是抄寫《觀音經》成了喪親家屬最佳的“悲傷輔導”,以及子女們為亡父母盡最終孝道的方式。這些題記也說明《觀音經》在敦煌民間的流傳是以“信仰”為主,因為大多數人關心的并非高深義理或法門的修持,而是如何快速地解除現實生活中的生老病死、愛別離與怨憎恚等痛苦。由于為人子女為父母抄《觀音經》,正是中國傳統的孝道思想與對觀世音菩薩信仰所驅策,所以人們的愿求一方面呈出現現世與來世解脫的色彩;一方面隨著孝子隨心所欲的愿求,到了晚唐五代的敦煌地區,觀世音菩薩還可以帶領亡者往生彌勒凈土。本來經典中的觀世音菩薩已經是“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到了中國之后觀世音菩薩更是無所不能了,其中“孝道”觀念的驅使,可以說是觀世音菩薩與《觀音經》地位不斷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