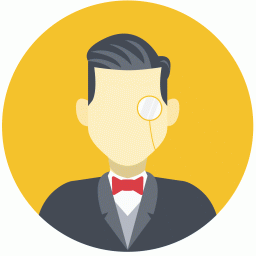基督教傳統人性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基督教傳統人性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bstract:ThisArticleexposesthe4typicalpositionsaboutHumanNatureinthetraditionofChristianthoughts:(1)Augustine’s,(2)PelagianismandSemi-Pelagianism,(3)Gnosticism,(4)Aquinas’.
我們知道中國哲學傳統中的性善論與性惡論之爭,孟子主性善,荀子持性惡,并且我們常以為這是中國哲學的特色。然而在西方基督教哲學中也有性善論與性惡論之爭,它最初發生在西方最重要的一位基督教思想家奧古斯丁與諾斯替主義和貝拉基主義的爭論中,并對往后的基督教思想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如果說中國思想學說中的性善性惡之爭關系到德治或法制這一重大政治問題的話,那么在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性善性惡之爭則關系到拯救是否必要和得救如何可能這一重大的神學問題。當然,這種爭論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進行的。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在討論人性問題時有一個在先的神學問題,即上帝創造世界和人,人如何通過耶穌基督而獲得拯救;他們把人性問題放在神人關系的問題中加以考慮。中國哲人在討論人性問題時沒有這樣的神學框架。他們從外觀天地社會,內察自己的切身體驗出發,談論性善或性惡,并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現世問題上。
我在這篇文章中無意比較東西方的人性論,只是引出一個話題,希望人們能對西方文化傳統中的性善論與性惡論之爭有較為清楚的了解。
概述
簡單地說,在西方的傳統中存在著四種有關人性的典型看法:(1)奧古斯丁的觀點,(2)諾斯替主義的觀點,(3)貝拉基主義和半貝拉基主義的觀點,(4)托馬斯·阿奎那的觀點。奧古斯丁主張人性本來是善的,因為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甚好”的,但由于人犯了原罪,墮落而變惡,因而現實的人性是惡的。諾斯替派持善惡二元論,主張人由靈魂和肉體兩部分組成,靈魂原初來自善的光明世界,肉體屬于惡的黑暗世界,這樣現實的人性不免是善惡二元的,而且惡的一面常常罩蓋善的一面。貝拉基主義和半貝拉基主義派持性善論,主張人性中始終存在善端,應通過自由意志的努力把這善端發揚出來,克服惡的習性。托馬斯·阿奎那主張人為上帝所造,有著原初的正直性,但也有自然的欲望;在上帝的關照下,人能朝好的方向發展;當亞當和夏娃冒犯上帝,失去上帝的關照后,他們就不能控制這種欲望,并順著肉欲和物欲而墮落作惡。這也就是說,人性之善惡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和神人關系的基本處境兩方面決定的,雖然上帝的恩寵是最主要的,但是人在接受恩寵時,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動的,因為他也能拒絕恩寵。
在基督教的傳統中,奧古斯丁的觀點被視為正統派,諾斯替主義的觀點、貝拉基主義和半貝拉基主義的觀點被視為異端。托馬斯·阿奎那的觀點是對奧古斯丁的觀點的修正,被天主教接受,但遭到新教的激烈反對。
奧古斯丁的有關原罪與性惡的理論
奧古斯丁把人性的問題與罪的問題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他在基督教的有關人性學說方面的功績在于把圣經中的有關觀點、柏拉圖的哲學和他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的理論表述。奧古斯丁堅持一元論的觀點,強調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是一個好的世界,太初所造之人是善的人,被置于一個完善的環境之中,在上帝的安排之下過著幸福的生活。由于上帝所創造的一切都是“甚好”的,惡在這個原初的世界中并無位置。用哲學的術語來說,世界在本體論上是一元的,世界起源于上帝的創造,上帝是完善的,上帝的創造世界和護佑世界使得世界有一個善的開端,并還必將有一個善的結局。因而在這樣的一個開端和結局都是善的世界中,惡沒有本體論上的地位,惡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惡不是與上帝并駕齊驅的,惡也決不是一種能與上帝相匹敵的力量。
那么世界上的惡是怎樣產生的呢?是由于墮落。奧古斯丁除了引證圣經談到魔鬼是天使的墮落外,特別強調了人的墮落。上帝原先創造的人是善的,但他們卻墮落了。這不是因為他們生性本惡,而是因為他們的意志做出了惡的選擇。他們的錯誤選擇使得他們的品性墮落了。上帝所創造的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當人自覺地追求最高的善,并服從上帝的命令的話,那么人就能夠走向完善。然而人卻背離了上帝,從而墮落到一個低等級的世界中去。在這里,一切存在物都是可變的、易腐敗的,人更容易受魔鬼和自己肉欲的引誘而干壞事。背離了上帝的人不再把追求完善當作自己的目標,而把自己所欲望的東西當作好的東西,把滿足自己的欲望當作目標。
人為什么要做出背離上帝的選擇呢?這是由于人的“驕傲”。奧古斯丁所說的驕傲,不僅僅指人的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看不起別人的品性,而且還包含更深層次的內容。驕傲意味著人的極度的自我提高,以至內心產生了對博愛的上帝的厭惡,而想自己成為上帝,也即從以上帝為中心轉向以人自己為中心。人渴望自己解放自己,而其結果使自己把自己置于奴役之中,因為人離開了上帝的指導,而被自己的肉欲牽著鼻子走。因而在奧古斯丁看來,驕傲是罪惡之源。驕傲是驅使人離開上帝的人類學上的動因。
那么人怎樣才能克服驕傲呢?人必須獲得謙虛之心。按照奧古斯丁的看法,對于已經墮落的人來說,只有依靠耶穌的拯救才能獲得這樣的謙虛之心。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CityofGod)這本書中構想了兩座城市:一座是“世上之城”,以自愛和驕傲為標志,住在那里的人只愛自己,不愛他人,狂妄自大,甚至連上帝都遭輕視;另一座是“天上之城”(上帝之城),以愛上帝和謙虛為標志,住在那里的人愛上帝甚于愛自己,謙虛地順從上帝的指引。這兩座城的居民分別以該隱和亞伯為代表。雖然這兩座城市是奧古斯丁構想出來的,但他稱世上之城的最高代表是異教的巴比倫和羅馬,在某種程度上,一切世俗國家都是它的體現,而基督教的教會則是天上之城的體現,“教會甚至在現在已是基督之國,也就是天國”[1]。上帝之城由那些蒙上帝揀選而得救的人組成,如今這些人都在有形的教會中,盡管并非教會中的所有的人都是蒙上帝揀選的,正如在麥田中麥子和莠草一起生長一樣。這是奧古斯丁為現存的教會辯護,他相信,基督教的教會必將在全世界發展,并逐步統治全世界,從而上帝之城將取代地上之城。
奧古斯丁主張,上帝是理性生物的一切美德的母親和保護者,因而人只有謙卑地順從上帝,才能發展自己的美德,因而謙虛便是智慧和愛的前提。由于人墮落已久,唯有憑借耶穌基督的恩典人才能克服其祖先亞當、夏娃所犯的原罪和每個人自己所犯的本罪,才能以謙虛之心克服驕傲之心,因而只有在教會中(教會是耶穌的身體)才能獲得那種摒棄私欲的力量。一旦我們成了謙虛的人,就會專心聆聽上帝的教誨,發展人的全部美德。
奧古斯丁認為,上帝是我們的一切善的事物和理想的善的盡善盡美的化身,因而追隨上帝就是追求最高的善。當然,這種追求不是為了使自己成為上帝(驕傲),而是為了順從上帝(謙虛),從而建立與上帝的奇妙的聯系(神人修和)。我們通過信上帝而聆聽上帝的教誨,讓上帝的真理和神圣占領我們的心靈,啟迪我們的心靈,實現幸福生活的美德。我們因為信仰上帝,從而克服惡而成為義人,這就是奧古斯丁所提出的“因信稱義”的原則。一旦我們全心全意地愛上帝,我們也會愛同胞和教友,以及懂得合理的自愛。這樣,奧古斯丁把善和幸福的原則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之上。在這種信仰中,心向上帝,依附上帝,就有幸福和安寧,而背離上帝,就是罪孽和毀滅。
簡言之,奧古斯丁主張原罪之前的人是性善的,因為上帝原初所造的是善的世界,而不是惡的世界。惡沒有本體論的起源,而只有人類說的起源,即惡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行為的結果,人自己的罪使自己墮落為惡。
諾斯替派的善惡二元論
奧古斯丁以時間上的某一個點為分界劃分人性的原初的善和現在的惡,并闡發人類將經由耶穌基督的拯救,克服惡,最終達到善的大結局。與這種一元論的善-惡-善的歷史理論相反,諾斯替派主張一種善惡二元論的歷史理論:世界在起源的時候是善惡絕對分明地二元的,中間是善惡混雜的,最終又將恢復善惡絕對分明。
奧古斯丁曾信仰摩尼教,當過九年摩尼教的聽眾(一般教徒),但他在她母親的影響下,通過閱讀基督教的經典和自己的切身感受,逐步懷疑摩尼教,并最終皈依基督教和激烈批駁摩尼教的觀點。奧古斯丁本人在他的《懺悔錄》第6至12章清楚地描述了他的思想的這一轉變過程。摩尼教在當時的基督教神學家眼里是某一種類型的諾斯替派。因此,我們在談論諾斯替派的善惡二元論的時候將結合奧古斯丁的思想轉變過程和對諾斯替派善惡二元論的批評。
諾斯替派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包括許多強調神秘靈智的二元論的教派,而其本身并無統一的組織形式和教義。追其淵源,它的產生比基督教還要早,或許它起源于中東,在古代波斯的瑣羅亞斯特教的二元論的基礎上,吸納希臘哲學的某些觀念,在希臘-羅馬世界中秘傳,在公元初年已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在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后,屬于這一思潮的某些派別又融合一些基督教的概念,成為基督教諾斯替派,在早期基督教的神學爭論中,是基督教正統派的強勁對手。諾斯替派主張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的二元對立,靈魂本屬于光明的精神世界,因受肉體的囚禁而受苦,得救在于靈魂受到光明之神的感悟,把握真知(Gnosis),從而通過修煉努力從肉體的囚禁中解放出來,回到他本來的精神世界中去。
摩尼教是由摩尼(Mani,216-276)于公元3世紀在波斯創立,其教義與諾斯替派的學說相似,所以被正統的基督教歸為諾斯替派。摩尼教的主要教義是“二宗三際”:“二宗”指光明與黑暗的二元對立;光明的德性是善和精神性,黑暗的德性是惡和物質性。“三際”指三個時代。在初際,光明的世界與黑暗的世界絕對區分,光明的王國占據北、東、西三方,黑暗王國占據南方。在中際,黑暗王國的勢力入侵光明王國,形成一個光明與黑暗相混淆的格局,致使某些光明的元素被囚禁在黑暗的妖洞中。此間,光明王國的最高神派出一系列的明使與暗魔斗爭,拯救被囚禁的光明的元素。光明國之神還感悟諾厄(Noe)、佛陀、瑣羅亞斯特、耶穌和摩尼等宗徒來喚醒世人,使人們認識到他們的靈魂本屬于光明之國,要通過修煉擺脫肉體的囚禁。在第三際,在摩尼及其宗教的教化之下,失落的一切光明的元素都被拯救出來,光明和黑暗又恢復各自的王國,彼此分離。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譴責摩尼教的“五元素化身大戰黑暗五妖洞”之類的教義是毒害信徒的荒誕不經之說[2],并為自己在年輕時竟會相信這種荒誕不經之說而深感內疚。從神學的角度來講,奧古斯丁轉向猶太-基督教的一神論,反對摩尼教的神魔二元論;從哲學角度來講,奧古斯丁主張只有一個最高的存在或本體,反對光明與黑暗、善與惡、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的二元論。奧古斯丁論證道:上帝是本源和最高的存在,因而沒有任何東西能與之抗衡和限制它。上帝是善的,因而它所創造的一切本來都是“甚好”的。上帝作為最高的善,他定然希望世人分享他的善,他樂意與人交流溝通。既然世界是由上帝而不是由惡魔創造的,那么世上的一切有生命、有靈性的存有者就不是如摩尼教所說的那樣是光明與黑暗兩種力量相混合的結果,于是惡就沒有本體論上的地位。奧古斯丁嚴格區分存在的起源與惡的起源:存在起源于上帝,惡起源于人自己的墮落。上帝是存在的作者,而不是惡的作者。這也就是說,存在有本體論上的起源,而惡沒有本體論上的起源。那么惡是怎樣產生的呢?根據圣經的“創世記”,“原罪”是人自己選擇的結果,因而惡只有人類學上的起源。存在確實是可以區分等級的,上帝是無限的存有者,人是有限的存有者,但人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人性的本惡。惡起源于人自己不服從上帝安排的善的秩序,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選擇的結果。只有當人作出了這種選擇之后,人的有限性才在加劇人的痛苦中起作用:人一方面驕傲自大,另一方面又能力有限(尤指避惡從善的能力),以致在罪惡的深淵中越滑越深,原罪加本罪,進一步墮落。
貝拉基主義的性善論
如果說諾斯替派倡導善惡二元論,否定惡的人類學起源的話,貝拉基派則正相反,過分強調人的自由意志,主張善和惡都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為。奧古斯丁認為,貝拉基派將導致否定原罪和基督拯救的必要性,因此在反對諾斯替主義極端的同時又反對貝拉基主義的另一極端。
貝拉基(Pelagius,約360-約420)生于英國,約于公元四世紀末時來到羅馬。他博學好學,刻苦修行,在當時聲望極高。他目睹羅馬道德風氣敗壞,企圖尋找其原因和解決辦法。他認為這與一種在道德修行上的無所作為的態度有關,因而希望促成一種較為奮發有為的倫理態度。他主張人有自由意志和道德責任心,認為上帝在創造人的時候,并不使人像其他所造物一樣完全服從自然規律,而是給人一種能按照自己的自由選擇實現自己的意志的獨特能力。“如果我應該這么做,我就能這么做”這句斯多葛主義的道德格言很能反映他的立場。他寫道:
每當我不得不談及道德教育和圣潔生活的品行的時候,我通常總是首先指出人性由優秀的質料構成,并表明什么是人性所能完成的。以這種方式我可以打動我的聽眾的心靈,使他們對人的德行有正確的看法,從而事先防止他們把這樣的德行看成是不可能的目標的想法。[3]
他主張,人的行為包含三個特征:能力(posse)、意志(velle)、實現(esse);其中,只有能力完全來自上帝,意志和實現屬于人。人進行自由選擇,尋求實現其所選擇的目標。這種自由選擇包含著選擇善和選擇惡的兩種可能性,人要為其行為承擔責任。人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將受到神的獎賞,否則將受懲罰。人擁有自由意志乃是上帝給人的特殊的恩惠;如果說人由于犯了原罪而內在地傾向于作惡的話,那等于否定了上帝給人的這份恩惠。因此他不承認任何由亞當遺傳下來的原罪,并堅定地認為現今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不犯罪。他還主張,上帝對人一視同仁,不偏愛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而是把恩惠施于每一個人。人之得神的保獎或受懲罰,完全是按照人自己的作為。貝拉基承認當今世界上存在大量的惡人,但他認為這不是由于人的內在的惡的本性或亞當的原罪,而是因為許多人模仿亞當,亞當的罪給他們樹立了一個壞的榜樣。但是這種壞的榜樣是外在的,是否決定模仿這種壞的榜樣或糾正它們,乃取決于人自己的內在的選擇。貝拉基寫道:
然而,我不得不慚愧地說,當我們討論人的條件的時候,許多人不敬和無知地說,人應該被如此造出來才好,以致他們能不作惡事,仿佛他們發現了他們的過錯乃出于上帝的工作。因此,正如陶器對陶工所說的那樣:“為什么你把我造成這個樣子呢?”我們發現最邪惡的人說,他們寧愿被造成另一個樣子,佯裝他們會做得很好,如若創造者授予他們一個好的本性的話。事實上,這些人并不想改過自新,而只是給出了一個他們想修改其本性的假象。[4]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說:
但是主啊,請你顧念我們都是灰土,你用灰土造了人類,并且失而復得。使徒保羅所以能如此,并非靠自身,因為他本身也是灰土,他是在你啟發之下道出了我所服膺的至言:“我依靠加給我力量的天主,能應付一切。”求你加給我力量,使我有這樣的能力;把你所命的賜給我,然后依照你所愿而命令我。保羅承認自己一切得自你:“誰要夸耀,夸耀應歸于主。”(《哥林多前書》1章31節)我又聽到另一位求你說:“請你解除我口腹之欲。”(《德訓篇》23章6節)于此可見,我的圣善的天主啊,凡依照你的命令而實踐的,都出于你的賜賚。[5]
貝拉基批評奧古斯丁的觀點過于消極無為,把人自己的過失歸于人的灰土所造的本性,這無異于否定人的道德責任心。奧古斯丁則從自己的宗教經驗出發,相信他自己是靠神的恩寵才從罪中獲救,倘若依靠自身的力量,永遠也無法從罪中自拔。他認為貝拉基的錯誤在于否定原罪,不承認得救是靠注入神的恩寵,高傲地相信人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過無罪的生活。貝拉基對恩寵的理解與奧古斯丁不同。貝拉基認為,恩寵是在受洗時罪得赦免,是上帝的一般性的教誨。而在奧古斯丁看來,恩寵的實質是上帝的愛的注入,人的品性依靠這種愛的注入才能轉變。神的恩寵是不可抗拒的,人的自由意志在此無能為力。因此,從根本上說,一個人的得救與否是預定的。
貝拉基有個學生名澤列斯蒂烏,他比貝拉基要激進得多,他不僅強調人的努力在克服罪的方面的作用,而且把這一觀點引向批評保羅的原罪說,因而有人控告他犯有以下六條錯誤:1、“亞當被造時就注定是要死的,不管他犯罪與否,他原本要死;”2、“亞當的罪只損害他自己,不損害人類”;3、“新生嬰兒所處的情況與亞當未墮落前一樣;”4、“全人類之死不是由于亞當的死與罪,全人類的復活也不是靠基督的復活;”5、“律法如同福音,也可以引導人進入天國;”6、“甚至在主降生之前,也存在著無罪的人。”
很明顯,如果這六個觀點能夠成立的話,保羅關于耶穌基督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死和替人贖罪的整個救贖的神學思想就要被推翻。因而不難理解奧古斯丁及其同道為什么極力鼓動召開宗教會議譴責貝拉基主義。在公元418年5月召開的迦太基會議上通過決議申明:亞當是由于犯罪而死的;為使原罪得赦免,小孩也應受洗;要過正直的生活,恩寵必不可少;人在今生不可能無罪。在這些行動的促使下,教皇索西穆斯也發了一道通諭,譴責貝拉基和澤列斯蒂烏。
半貝拉基主義的淡化了的性善論
在奧古斯丁與貝拉基主義的斗爭之后,還出現了一場半貝拉基主義的余波。有些基督教的神學家擔心奧古斯丁的學說會使人在道德修養上放松怠慢,不再努力去惡從善。他們認為,奧古斯丁的預定論和恩寵的不可抗拒性的說法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從而不利于激發人的道德責任心。但是他們也反對貝拉基主義,他們不否定原罪說,承認恩寵在人的得救方面的重要作用,在這一方面又采納了奧古斯丁的觀點。因此他們的立場被稱為半貝拉基主義或半奧古斯丁主義。
約翰·卡西安(JohnCassian)是半貝拉基主義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可能是高盧人,約公元360年出生。他去過以色列和埃及,在埃及的一個修道院中他遇到一位名為查來蒙(AbbotChaeremon)的隱修士。他在約425-430年間寫下的《對談錄》據說就是他與查來蒙談話的記錄。在《對談錄》中,他論證上帝在造人的時候,就在人的靈魂中播下善的種子,人知善惡,即使在人墮落以后,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人之得救,要靠上帝的恩寵,但也離不開人自己的努力。上帝的恩寵好比耕地和澆水一樣,如果沒有內在的種子,植物也不能生長起來。他寫道:
因為我們不主張,上帝造的人是從來不愿或不能從善的;或上帝沒有賦予人一種自由意志,仿佛他使人只愿和只能作惡,而不愿和不能做好的事情。如果正是這樣的話,如何才能解釋上帝在人墮落后說的第一句話:“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創3:22)[6]
……無疑,由于創造者的慈悲,在每個靈魂中生而就被置于某些好的種子;但是除非在上帝的協助下使得這些種子生長起來,他們將不能邁向完善,正如圣徒所說:“耕地和澆水的并不是他,而是上帝使之生長……”因而,在人身上,意志總是自由的,對于上帝的恩寵,一個人可以不予理會,也可以欣喜承納。[7]
里埃茨的主教福斯圖斯(FaustusofRiez)是另一位半貝拉基主義的代表人物。大約在474年,他寫了一篇名為《恩寵》的論文,承認恩寵對于人的得救必不可少,但設法排除由此容易導致的預定論,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為的救而奮斗的可能性”。他把恩寵界定為神的應許和告誡,恩寵使得變為軟弱但仍是自由的意志傾向于正義的選擇,而不是像奧古斯丁所認為的那樣,恩寵是一種內在的轉變能力。上帝預見到人們得到福音后將做什么,但上帝不預定他們將做什么。
奧朗日宗教會議的決議
公元529年在奧朗日召開了一次宗教會議,通過了反對貝拉基主義半貝拉基主義的決議。該會議經教皇卜尼法斯三世批準,因而具有重要意義,在形式上標志著這場延續二百年的激烈論爭的結束。
該決議的第一條和第二條申明亞當的原罪敗壞了整個人性,并遺傳給整個人類的后代。其原文如下:
條規一,凡主張亞當的不服從的冒犯沒有使包括身體和靈魂在內的整個的人變壞,而只是使他的身體敗壞,而他的靈魂的自由依然沒有損傷的人,是受了貝拉基的錯誤的欺騙,違背了圣經[以西結書18:20;羅馬書6:16;彼得后書2:19]。
條規二,凡斷定亞當的罪只損害了他自己,而不損害他的后代,或認為這罪只導致他的身體的死,而不導致他的靈魂的死,不從一個人傳至整個人類的人,是藐視上帝,是與使徒的話相矛盾的[羅馬書5:12]。[8]
該決議的第三條至第八條申明人由于受原罪的影響,失去了一切歸向上帝的能力,靠人自己是不能從墮落中自拔的,“只有圣靈的激發才能使我們的意志從不信轉變為信,從不虔敬轉變為虔敬”。我們具有的“信仰的意愿”是“靠主來預備的”,“我們通過洗禮獲得新生”,是主“無償賜予的恩寵的禮物”,是圣靈激發的結果。“由于第一個人的罪,自由意志避開正路和被消弱了,以致此后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應該的那樣愛上帝,或信上帝,或做任何對上帝來說好的事情,除非神圣的憐憫首先降臨于他。”[9]
以上這些論點與奧古斯丁相一致。然而,在這一決議中沒有一處肯定恩寵是不可抗拒的,相反把那些犯錯誤的人說成是“拒絕了那同一個圣靈”,并且還譴責了人注定要犯罪的預定論。這次會議的決議的最顯著的論點是把接受恩寵與受洗密切相連,以致把恩寵所具有的圣事的性質和善工的價值都置于突出的地位。
我們也相信這符合天主教的信仰,恩寵在洗禮中被接受,所有受洗的人,在基督的援助和支持下,如果他們虔信地努力的話,能夠和應該履行那些屬于靈魂拯救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但不相信,某些人是被神圣的力量預先注定去作惡的,而且如果有人希望去相信這樣的惡的事情的話,我們將非常憤恨,并要求把他們革出教門。[10]
托馬斯·阿奎那的人性的自由意志和處境的雙重決定論
雖然奧朗日會議的決議在形式上結束了教會的正統派同貝拉基主義和半貝拉基主義的斗爭,并在名義上確定奧古斯丁的觀點為正統,但實際上基督教在性善性惡問題上的爭論仍然沒有結束。天主教的觀點可視為奧朗日會議的精神的延續,并以托馬斯·阿奎那對奧古斯丁立場的修正為基準。
在奧古斯丁的思想中,似乎存在著一個矛盾:當他同諾斯替派斗爭的時候,他主張意志自由,堅持惡的人類學的起源,主張人犯罪是人自由選擇的結果;當他同貝拉基主義斗爭的時候,則主張人沒有從善的自由意志,人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寵才能得救。奧古斯丁本人意識到他的說法間的差別,但他不認為這是自相矛盾的。他寫道:
對那部分上帝已應許原諒他們,并分享他的永恒的國的人來說,他們能夠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嗎?絕對不能。一個獲罪于上帝的人除了從永劫中被救出來以外,他還能行什么善呢?他們能夠由他們自己的意志自由決定做任何事情嗎?我再說絕對不能。因為人已經由于他的自由意志的邪惡的使用,既毀掉了自由意志又毀掉了他自己。一個人當然是活著的時候自殺;當他已經自殺而死,自然不能自己恢復生命。同樣,一個人既已用他的自由意志犯罪,為罪惡所征服,他就喪失了自由意志。[11]
奧古斯丁通過活人能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自殺,而死人卻不能復生的比喻,說明一旦人對上帝犯了罪,便遭永劫,除了靠上帝的拯救之外,是不能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得救的。但是,死人(adeadman)和一個因獲罪于上帝而迷失和沉淪的人(alostman)還是有所不同的。前者顯然連同他的自由意志一起死了,而后者是否還留有自由意志的問題是可商榷的。如果說后者已經失去了他的自由意志的話,那么他繼續作惡是由什么驅使的呢?人犯原罪是由他的自由意志的驅使的,他犯的本罪(personalsin)難道就不是由他的自由意志驅使的嗎?如果他犯本罪時已經喪失了自由意志的話,那么他憑什么要承擔責任呢?對于這樣的問題,在奧古斯丁那里不能找到一以貫之的答案。
托馬斯·阿奎那對這個問題設想了一個較能自圓其說的解決辦法。他不像奧古斯丁那樣主張,亞當墮落之后就失去了自由意志,而是主張,亞當的原罪使人失去了上帝的慣常的恩惠(habitualgrace),從而不再能抵擋各種邪惡的欲念的引誘,犯下越來越多的新的罪。人一直保留著自由意志,但是在原罪之前和之后,人做出選擇的時候所面臨的條件不同了:在此之前具有上帝的慣常的關照,在此之后就缺乏這種關照了。這好比,具有家長教養的小孩和缺乏家長教養的小孩在成長道路上的差別。
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伊甸園并不等同于一個天堂,它與當今的世界在物質和物欲的層面上講沒有根本的區別。即使在最初的一對人還沒有犯罪的時候,狼還是要吞食羊;亞當和夏娃盡管被創造出來時是善的,但仍然具有各種欲望和勢必面對各種引誘。他們本來之所以能夠抵擋引誘和不犯罪,乃是因為他們本來置于上帝的慣常的恩惠之下,具有原初的正直性(又譯正義性)(originalrighteousness)。并且,如果他們能夠保持這種原初純正的話,他們就可以進入到一個更好的、不朽和極樂的境界中去。然后,亞當和夏娃背離了上帝。他們做了上帝禁止他們做的事情,這意味著他們主動地拒絕上帝的關照。這樣他們就失去了上帝賦予他們的慣常的恩惠的禮物,而人的原初的正直性(自我的統一性)是依賴于這份禮物的。這樣,基本的人性就受到損傷,變得紊亂和脆弱了。因而人就更容易犯罪了。對托馬斯·阿奎那來說,罪的本質從形式上說是指“喪失原初的正直性”,其原因是亞當和夏娃違背上帝的禁令,從而失去了上帝對這種正直性的神圣支持(慣常的恩惠)。從質料上說,是指俗人的欲念(concapiscence)或欲望的紊亂,這是由于失去了上帝的這種恩惠而導致的。
阿奎那企圖解決一個奧古斯丁遺留下來的有關原罪是如何遺傳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表述:是否亞當和夏娃的原罪也使人的自然屬性(人的身體和肉欲)發生了變化,從而原罪是通過生物遺傳的方式發生的?阿奎那否定了這一說法。就人的自然屬性而言,伊甸園中的人和現在的人沒有什么區別,區別在于他們的處境變了,他們失去了上帝的原有的關照,從而人性變得脆弱和紊亂了。原罪意味著一種容易犯罪的狀態或條件,亞當之后的人繼承了這種狀態或條件,所以特別容易犯罪,在原罪之后不斷增添上他們親自犯下的罪(本罪)。
阿奎那的結論是:人之善惡和得救與否,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和神人關系的處境兩方面決定的。雖然上帝的恩典是最主要的,它決定著神人關系的基本處境,然而人在接受恩典時并不是完全不動的,因為人也能通過他的自由意志拒絕恩典。上帝的恩典為人的從善和得救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如若人的內在的自由意志不作努力,那么只能咎由自取。
天主教以托馬斯·阿奎那的觀念為正統,而新教改革運動,在某些方面重新發現和復活了奧古斯丁的思想,反對天主教的立場。新教神學家,特別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認為天主教的立場否定了人性中所繼承的朝向惡的傾向。他們特別突出奧古斯丁的俗人的欲念的概念,把它表述為一種完全的腐敗墮落。他們主張,罪遠不止一種人性的缺損和匱乏,而是整個人性的腐敗墮落。人的存在中沒有一個方面或一種能力不是被罪腐敗的。因而,雖然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出來的,但人在墮落中已經失去了這一形象。路德評說道:
人在肉體里和靈魂里全都有一個攪亂的、敗壞了的和受到毒害的本性,人類沒有一點東西是好的。這是我由衷的意見,凡是主張人的自由意志能夠自由地在神圣的事物上有所作為,那怕是極微小的一點作為吧,這樣的人都是否認基督的。[12]
天主教針對新教的觀點,在1545至1563年間召開天特會議(CouncilofTrent),譴責新教的觀點,堅持阿奎那的立場。天特會議的第六次會議(1547年1月13日)通過《論稱義的教令》,其中第五章的標題為“論在成人心里必須有稱義的準備,并論其起始”,其論點與阿奎那的相一致:
本會議又宣言:在成人心里稱義的起始是先由于上帝因耶穌基督所賜的恩典,即由于他的召,籍此,人毫無功德而被召;好叫那因罪惡與上帝遠離的人,因他那感動并幫助人的恩典,由人樂意與那恩典同意并合作,而有意使他們自己歸正,得以稱義;這樣,雖然上帝用圣靈的光感動人的心,但是人在接受那感動時,他自己并不是完全不動的,因為他也能對它加以拒絕;可是沒有上帝的恩典,他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能叫自己在他眼中成為義的。[13]
天主教把人接受上帝的恩典與否歸于人的自由意志,新教,特別是加爾文宗,則把它歸于上帝的預定。加爾文宗主張,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人之中有一部份信上帝,并因而稱義,乃是上帝的恩賜。上帝揀選了一部份人,使他們信上帝,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人之是否成為上帝的選民,乃是上帝的預定,與人自己的努力是無關的。有關新教與天主教在自由意志和預定論方面的爭論這里就不展開了。就人性的問題而言,新教基本上持奧古斯丁的立場,而天主教基本上持阿奎那的立場。[1]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第14章,第28節。
[2]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43。
[3]貝拉基:“LettertoDemetrias”,引自RobertL.Ferm編:ReadingsintheHistoryofChristian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讀物),NewYork,1964,第291頁。
[4]貝拉基:“LettertoDemetrias”,引自RobertL.Ferm編:ReadingsintheHistoryofChristian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讀物),NewYork,1964,第293頁。
[5]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214。
[6]JohnCassian,《對談錄》(TheConferences),引自RobertL.Ferm編:ReadingsintheHistoryofChristian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讀物),NewYork,1964,第303頁。
[7]同上,也304。
[8]“奧朗日會議”(CouncilofOrange),引自RobertL.Ferm編:ReadingsintheHistoryofChristianThought(基督教思想史讀物),NewYork,1964,第305-306頁。
[9]同上,第306-307頁
[10]同上,第307頁。
[11]奧古斯丁:《教義手冊》,第30章(TheEnchiridion,Chapter30),引自TheNiceneandPostNiceneFathers(FirstSeries),Volume3,p.476,TheAGESDigitalLibrary,Version2.0,1997。
[12]馬丁·路德:《桌邊談話》,引自周輔成編,《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81頁。
[13]引自《歷代基督教信條》,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2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