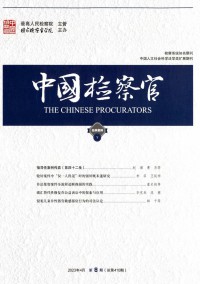實踐本體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實踐本體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作為一種傳統本體論,物質本體論的缺陷在于它是隱蔽的二元論并具有人的非在場性,由此決定了其無法證偽實踐本體論。后者所確認的實踐的終極的原初性,邏輯地要求實踐作為本體范疇具有無條件性,因而實踐本體論不能充當物質本體論的一個特例以同它相調和。通過實踐的本體論地位的奠基,馬克思哲學立足于人的在場性詮釋感性世界的歷史生成,這與那種人不在場的物質本體論大異其趣。
[關鍵詞]馬克思;實踐本體論;證偽
最近有幸拜讀了孫亮先生同我商榷的文章《馬克思實踐本體論:一個再證偽》(以下簡稱“孫文”),非常歡迎作者率直批評和對話的態度(因為這種態度在學術界似乎日漸減少),同時也對孫文觀點存有相當多的疑問,現作出我的初步回應,以就教于孫亮先生和讀者。
孫文名曰“證偽”,可究竟拿什么來“證偽”呢?在我看來,無非是重申物質本體論的傳統觀點而已。問題在于,如果不進一步“證明”物質本體論本身的預設是合法的,而僅僅局限于再次“宣布”物質本體論是正當的,那么,它就不具有“證據”的作用和價值,如此一來,所謂“證偽”云云也就無從談起了。因為這樣處理問題,面臨的危險是使有關是非的討論淪為不同哲學偏好的相互否定,從而將其變成一個完全見仁見智的相對主義的問題。
一、“本體論”的詞源學追溯幫不了什么忙
孫文說:“要想分清楚‘實踐本體論’的錯誤在哪里,以及‘物質本體論’的合理之處,明晰本體論這一基本的理論顯然是關鍵所在,這樣才能避免雙方論戰中出現‘獨斷’。”于是,孫文對于“本體論”一詞進行了一番常見的詞源學追溯。但在我看來,所謂“原生態的‘是論’”的考證,也幫不了物質本體論什么忙。事實上,澄清本體論之本義之后,恰好證明了物質本體論的致命缺陷和實踐本體論的優越之處。其結果不是“證偽”了實踐本體論,倒是證偽了物質本體論。何以見得?
本體只能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正因此它才能構成“第一原因”。既然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它必然具有唯一性。所以,從體系建構的角度說,本體論只有作為一個一元論系統,在邏輯上才是完備的。如果是兩個或多個,那么它一定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在這個意義上,二元論和多元論顯然是不徹底的,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
表面看來,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是一種一元論,其實不然。因為在追問物質和精神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時,它們實際上已經先行地設定了心與物之間的二元分裂。只有在這一預設的前提下,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的問題才是可能的。“一旦把身體和心靈割裂開,就會產生足以使哲學家們世世代代去研究的種種問題”[1]。因此,可以說,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是基于同一個前提而確立起來的。在此意義上,它們都不過是一種隱蔽的二元論而已,所以在邏輯上是不徹底和不完備的,從而有其致命的缺陷。先行地預設兩種實在(最抽象的實在就是心與物),然后再尋求二者之間的統一,把一個歸結和還原為另一個,這正是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缺陷。它只能得到一種非此即彼式的回答。就像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過古典哲學》第2章中所描述的那樣。這種追問及回答的方式均以思維(精神)與存在(自然界)之間的二元分裂為其前設,正是它才使問題成為可能。黑格爾固然是按照“自己構成自己”的方式建構邏輯學體系的,但仍然未能從本質上擺脫“精神”的狹隘性,從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走出舊本體論的二元論陷阱。馬克思實現的哲學變革,乃是一種哲學觀層面上的革命,而非在原有框架內對以往哲學的個別結論或具體觀點的置換或改變。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局限和缺陷,就在于它們的根本邏輯前提。在它們所固守和捍衛的框架內,必然派生出它們各自的局限性(即馬克思所揭露的舊唯物主義的直觀性和唯心主義的對精神的抽象發展)。因此,馬克思試圖超越而且事實上也已經超越了舊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之間的外在對立。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條中,他明確地表達了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雙重不滿。舊唯物主義離開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動去確立物質的本體地位,必然使之成為一種與人的存在本身無關的抽象的物質,也就是那個自在之物。如果說舊唯物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物質的話,那么與此相反,唯心主義則抽象地發展了精神。從邏輯上說,實踐乃是一個比心物及其二元分裂更為原始的范疇。把實踐置于本體論的前提地位,就消解了心與物之間的分裂和對立,從而超越了它們的二元性,達到了本體范疇的絕對性。當然,馬克思在命名自己的哲學時仍然使用了“新唯物主義”或“實踐的唯物主義”,其中保留了“唯物主義”的措辭。問題在于,馬克思所謂的“物”不再是指稱那種與人的存在無關的抽象物質,而是指人的實踐活動本身的客觀性。因此,馬克思雖然使用了“唯物主義”措辭,但已經不是在二元論框架的背景下使用了,而是在存在論的基礎上使用的。這是實踐本體論在邏輯上的必然要求。
必須指出,物質本體論之所以在應對唯心主義的挑戰時遇到難以克服的危機,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基本命題即“物質決定精神”已然隱含著物質與精神的二元分裂了。通過發生學關系,把精神逆向地還原為物質,有一個致命的困難:精神顯然有一種不可還原的特質即人造物被歸結為自然物之后的“剩余規定”。于是,唯心主義利用這一困難對唯物主義提出致命的詰難。實踐本體論不再沿著舊唯物主義這一失效的路數作出自己的回應,而是通過尋找比心物二元分裂和對立更為原始的原初基礎來取消這一問題本身。
孫文通過對本體論的詞源學追溯來反駁實踐本體論,實際上不過是拿傳統本體論的模式來裁決現代本體論,其結果只能是一種倒退和遮蔽。因為它使得已由現代本體論澄清了的問題又陷入被視而不見的境地。
本體論問題關乎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最終根據或理由,亦即尋找邏輯意義上的“第一原因”。誠然,本體之普遍性唯一地在于它使一切可能的“在者”分有了“在”,從而獲得“在者”之“在”的可能性。表面看來這同人的存在無關,其實不然。從歷史上看,本體論問題之所以誤入歧途,就是因為人們對于“在”(或者“是”)的追問方式出現了致命的偏差,即由于游離了人的存在,把一個原本應該是內在性的體認式的問題,置換成了一個與人的存在相梳離的純客觀的問題。如此一來,“在”的“在者”化,即海德格爾所謂的“在的遺忘”就在所難免了。因此,在建構本體論時,人們是否自覺地意識到一種反身性的關系,這是現代本體論同傳統本體論的一個重要區別。現代本體論對這一關系的自覺確認,正是其人的存在論立場之奠基的前提。
相對于傳統的本體論,現代本體論的優越性在于:一是超越了本質主義的追問方式,它不再按照預成論模式(以祛時間性為標志)給出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內在理由,而是按照生成論模式給出這種理由,從而與時間性達成“和解”。二是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對象性的前設框架,因此避免了科學認知式的本體論追問方式。從某種角度說,實踐的本體論意義在于它確立了絕對的主觀性視野,亦即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謂的“從主觀方面去理解”。這個“主觀方面”代表著本體論的發問者的體認式的領會姿態。馬克思誠然指出了唯心主義的危險,但陷入這種危險的原因僅僅在于“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2]。倘若立足于“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亦即確立起實踐的終極的原初性地位,就邏輯地排除了這種危險的可能性。“主觀”既可以是指主觀與客觀相對而言的規定,也可以是指絕對的主觀性。在后一種意義上,它類似于黑格爾所謂的“主體”即“實體”意義上的主觀性。作為本體論視野的實踐的主觀性,只能在這個意義上成立。不少人一聽到“主觀性”就神經過敏,更何況又是“絕對的”。事實上這里大可不必擔心唯心主義之嫌。三是實踐本體論由于真正地回到了比心—物二元框架更為原始的基礎之上,消解了使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及其對立成為可能的前提本身,因此,它不是解決了而是取消了問題。這也正是它的徹底性之所在。所以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采用的是“合取”的運思方式,而不是固守于舊的哲學框架并在此基礎上去尋求某種可能的答案的傳統思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明顯地區別于恩格斯。
對于發問者來說,本體論的追問為什么必須采取一種反身性的姿態?說到底這是為了避免本體論的誤入歧途。因為使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本身成為可能,恰恰是實踐這一特殊“在者”的“在”的方式。實踐所內在地固有著的生成性、創造性、開啟性,決定了它作為本體范疇的原初地位和資格。海德格爾所批評的“在的遺忘”,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把“在”誤當作“在者”來追問了,更根本的則在于它離開了人的存在來進行這種追問。這才是傳統本體論的致命缺陷和根本誤區。只有基于實踐所體現的內在性的而非對象性的角度才能開顯“在者”之“在”,從而避免“在”的“在者”化命運。這也正是海德格爾之所以立足于“此在”的原因。傳統本體論由于其追問方式脫離了人的在場性,不可避免地淪為科學認知的方式,它不過是要把哲學做成最大的“科學”而已。“在”的“在者”化之誤區,根源于那種把“在”當作一個外在對象來予以追問的設問方式。之所以陷入這一誤區,乃是因為設問本身離開了人的存在而企圖設想一種人不在場的外在式的追問。這顯然是想確立一種超出人及其存在之外的探究姿態。這種“無我”的方式恰恰導致把一切都對象化的科學認知方式。拿這種方式去領會本體論意義上的“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像科學般地認知對象那樣去看待“在”本身的結局。這種“客觀的”發問,造成了一種與人的存在無關的本體論假象。馬克思的實踐本體論克服了傳統本體論的上述缺陷,立足于人的現實存在來領會世界,并在此原初性根基上給出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得以開顯的內在理由。這就避免了那種與人的存在相脫離的舊式本體論設問方式的誤區。
也許有人會擔心,把這種立足于“我”的實踐作為本體范疇,是否有主觀唯心主義之嫌?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實踐的終極原初性決定了它是比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及其對立更具有始源性的基礎。在此意義上,確立實踐的本體論地位,恰恰意味著對唯心主義式的偽本體論形式的否定,其結果只能是后者的失效。這又怎么會導致唯心主義的偏差呢?倒是物質本體論只能在結論的意義上而無法在前提的意義上否定唯心主義,它的這種否定的不徹底性在于陷入一種知性意義上的否定,因而無法最終戰勝唯心主義。這是唯物主義所遭遇的命運,也正是馬克思不滿意于歷史上的唯物主義的地方。也許有人會擔心,實踐本體論豈不是存在著走向人類中心論的危險嗎?從人的存在這一內在視角契入問題,恰恰不會陷入人類中心論。因為人類中心論表征為以人類的狹隘性去測度作為對象之規定的外部世界的偏好。而作為本體論視野的人的實踐乃是“大我”,它并不存在于同對象之間相互對待的關系之中,相反,它是比一切對象性關系和結構之產生都更為原始的前提。總之,在先行地確立實踐的原初性地位時,一切使人類中心主義得以成立和表達的基礎尚不存在,談何人類中心論?
就本體使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存在成為可能而言,它的確是涵蓋一切的。但“物質”這一范疇能否扮演這一角色呢?恩格斯把世界的統一性歸結為物質性(很遺憾,從馬克思的文本中找不到類似的確認),并不能解釋精神何以由物質“決定”的充分理由。“決定”的含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時間在先意義上的發生學關系,二是邏輯在先意義上的根據關系。恩格斯只是給出了前者的揭示,卻并未解決后者的問題。這就給唯心主義留下了可乘之機。馬克思則試圖在另一個層面上解決問題,即通過追尋比心物二元對立更為原初的基礎而把問題本身消解掉。這恰恰是馬克思哲學的徹底性之所在。
對于本體論的詞源學追溯并不能澄清本體論的誤區,并不能克服海德格爾揭橥出來的所謂“在的遺忘”的歧途。因為對于本體論問題的撥亂反正來說,“Being”究竟怎么翻譯才是貼切的,已是次要的問題,真正吃緊的倒在于如何恰當地把握發問的機緣和立足之處。歸根到底,這不是一個翻譯問題,而是一個看待方式的立足點是否恰當的問題。
本體范疇的終極的原初性決定了它的確立必須是邏輯在先的,不然那個“第一原因”就不可能找到。但是,本體范疇本身又必須內在地固有其時間性的可能性。而真正的時間性只能是歷史性而非歷時性,這只有從人的存在在同一切非人的存在的異質性的差別中才能被發現。因此,本體論的原初范疇的確立,只有在回到人的存在本身上來的時候,才是可能的。這也恰恰是本體論與人本學之間走到一切來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傳統本體論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它遠離了人的存在的維度,在祛時間性的同時,把本體范疇的內在時間性給遮蔽掉了。海德格爾所批評的“在的遺忘”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在者”之“在”被剝奪了一種展現的可能性。在非時間的抽象的境域中,“在”本身所遭遇到的命運只能是被幽閉或者被遺忘。因為只有在表征為時間性的歷程中,一切可能的“在者”才能以其本真性的方式“在”起來,而“在”的這種開顯的機緣,是唯一地由人的存在本身所給予的。
我承認自己受到了海德格爾思想的某些影響,但我認為哲學家的名字不應成為一種標簽,成為一種先驗地加以取舍的標準,一聽到某位哲學家的名字,先存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好惡,然后決定對其思想的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就像一個哲學家的歷史就是他的思想的歷史一樣,同樣地,一部哲學史也并不是哲學家的歷史,而歸根到底不過是思想本身的歷史。所以,在我看來,哲學家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不應看思想出自誰人之口,而應看他所說的有無道理。否則,一個人無論是偏好還是厭惡某位哲學家,都有陷入獨斷論的危險。
因此,孫文充其量不過是再次表明了關于馬克思哲學的實踐本體論解釋同物質本體論解釋之間的對立,但僅僅指出這種對立并不能“證偽”實踐本體論,而且就目前人們對于這種對立本身已無什么分歧的情況而言,也缺乏真正的建設性。
二、作為“本體”的實踐之原初性是無條件的
把實踐的本體論意義限制在唯物史觀范圍內,這一做法的困境何在?一是曲解了本體論的含義,即終極的原初性,不可歸結和不可還原性,因而具有唯一性。二是本體論的確立還有賴于一個本體論之外的視野,這就把本體論視野有限化、相對化了,它顯然有悖于本體論的絕對性。
孫文說:“實際上‘物質本體論’在實踐是人類社會生成和發展的基礎,是社會結構生成和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動力這一點上從來沒有與‘實踐本體論’發生真正的分歧。”在孫文看來,“實踐是唯物史觀的基礎或者說是本體”,而物質則是整個世界的本體。按照這個解釋,物質本體論同實踐本體論可以并行不悖。孫文提出的問題是“實踐在何種領域內能夠成為‘本體’”?我認為,孫文的這種折中調和的做法,是有悖于本體論的邏輯意義的。實踐倘若是在有限領域內起基礎作用,那么它就與本體范疇沒有任何關系。
本體范疇的終極的原初性決定了它的唯一性。說物質本體論同實踐本體論可以并行不悖(因為據說后者只是在歷史領域有效),是對本體之唯一性的否定。這同本體的原初意義(孫文在談及“本體”時并沒有否認它的這一意義)也完全不符。孫文的這種把實踐的本體論意義有限化,從而把它看作是物質本體論的一個特例的解釋,在本體范疇的使用上存在著邏輯紊亂。
孫文以恩格斯的三部著作(即《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觀點為根據,試圖把馬克思哲學解釋并證明為物質本體論。問題在于,在我看來,這只能說明恩格斯哲學而非馬克思哲學是物質本體論的,因為孫文在這樣論證之前,需要先做一項前提性的鋪墊工作,否則就將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證明恩格斯在哲學上究竟是“補充了”馬克思還是異質于馬克思?對此問題的回答,取決于如何看待馬克思同恩格斯在哲學上的關系,也取決于把馬克思哲學定位于物質本體論是否恰當。恰恰在這些問題上,孫文并未做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回應。
孫文詰問道:“物質本體論者否認過實踐的作用嗎?”其實,物質本體論的癥結并不在于是否談論過實踐,而僅僅在于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談論實踐。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體系為例,它可以大談實踐的地位和作用,但卻始終不能在本體論意義上談論,而僅僅是把它局限在認識論的范圍之內。在本體論層面上,物質本體論強烈拒絕實踐的地位和作用,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否則,也就不會發生筆者同孫文的爭論了。
孫文認為,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中的“重要意義”,“并不能構成實踐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的硬性根據”。倘若真地如此,那至少說明馬克思所實現的哲學變革不具有本體論層面上的革命意義,它頂多不過是同舊哲學在共同的本體論基礎上的一種改良而已。孫文甚至抱怨拙作“很繁瑣的把早已很清楚的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中的意義(‘哲學的視野和立場’)敘述了一遍”。然而,從孫文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變革所做的了解看,其實它仍然是很不清楚的,從而有必要重申這一點。
實踐作為本體范疇,倘若是有條件的(譬如只是在某個有限范圍內成立),那么它就不配作為本體范疇而被確立起來。這是由本體論的性質和本體范疇的邏輯要求決定的。
孫文在對實踐本體論作了一番限制之后,宣布“物質本體論”與“實踐本體論”是“一致”的。然而問題在于,當把“實踐”的本體地位僅僅局限于歷史領域,而又外在地、旁觀式地思考“整個世界”時,實踐還具有本體范疇的意義嗎?當孫文提出,“用‘物質’規定‘實踐’,就是告訴我們,‘物質’是‘實踐’中的更為深刻更為普遍的本質,‘實踐’是‘物質’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態”時,實際上已經是把實踐本體論當作物質本體論的一個特例了。這事實上就意味著從根本上取消了實踐的本體論地位。在本體論意義上,實踐的原初性同物質的原初性是決不能并存的。因為本體范疇的原初性是終極的原初性,這就注定了實踐作為本體范疇,其原初地位是無條件的。倘若在它之前尚存在一個比它更具有始源性的規定(即“物質”)決定著它,那么它的原初性就被實際地消解掉了。這顯然同本體范疇的邏輯性質相悖。
三、“人”不在場的本體論想象與馬克思哲學無關
說實踐視野難以涵蓋自在物質,這實際上體現著一種外在于實踐的旁觀者意義上的把握方式。在馬克思的語境中,難道還存在著“把感性世界看成是實踐活動”以外的看待方式的合法性嗎?離開了實踐的看待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陷入馬克思所一再批評過的直觀地去看待的姿態。正是這一姿態,才不能不把世界區分為“天然自然界”(即自在世界)和“感性世界”(即自覺世界)之類的劃分。
事實上,當把“整個世界”設想為由“天然自然界”和“感性世界”兩部分構成時,設想者已經完全拋開了作為視野和立足點的實踐,使原本屬于歷史的自己硬要站在歷史之外(或之上)去想像人不在場的狀態下的分類及其格局(這里需要特別注意馬克思曾批評過的那種“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3]哲學的致命缺陷)。這種觀察方法,恰恰是馬克思一再批判的那種直觀態度。這樣做實際上就像一個人試圖抓著自己的頭發把自己提起來一樣荒謬。這不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又是什么呢?孫文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般世界觀’,它必須對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做出回答,而這就是立足于把‘整個世界’作為研究對象”。這里所謂的“整個世界”如果抽掉了實踐本體論這一基礎,就只能淪為馬克思所擯棄的那種作為“感性對象”而非作為“感性活動”的規定。
如果不是從內在的視野確立實踐的本體論地位,那么就難免會產生孫文存在的“客觀地看待”的問題,這正是舊唯物主義難以領會實踐本體論的癥結之所在。這種看待方式必然會出現孫文所提出的那類問題,即除了實踐之外,怎么會沒“有”天然自然界的存在呢?若按照馬克思的運思方式,是不會也不應該提出這類問題的。因為在以實踐為視角和原初性范疇的看待方式那里,這類問題不過是偽問題。實踐的終極的原初性已經取消了使這類問題成其為問題的那個前提。馬克思本體論變革的合法性恰恰來自傳統本體論存在的因人不在場而導致的致命缺陷。否則,所謂的馬克思哲學變革的意義就大打折扣了。
孫文質問道:“僅僅限定在實踐開辟的這樣一個世界,試問你從何處開辟?如果只在這樣一個‘實踐的世界’,那如何拓展?人類還要不要發展?”在筆者看來,這恰好應該被用來回敬孫文:離開了實踐所內蘊的開啟性,離開了實踐所固有的向未來敞開著的可能性,又如何“拓展”?人類又何以“發展”?孫文所謂的“天然自然界”又怎樣造成這種“發展”?這不禁讓我們想起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評費爾巴哈的那種脫離實踐的直觀立場時早就說過的話:“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4]。難道馬克思在這里說得還不夠明確么?
孫文反問道:“‘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對人沒有意義嗎?”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無法作出一般地回答的,倘要給出答案,就必須先行地澄清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追問的。也就是說,其關鍵在于所謂“天然自然界”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才是“有意義”的?筆者從來就未曾在“前提”的意義上否認“天然自然界”的意義。正是在被孫文當作商榷對象的那篇拙作中,筆者專門澄清過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話(即“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5])的特定語境和含義,并把它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章中的一段批評費爾巴哈的論述相比較,指出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批評的對象上,一是針對黑格爾的,一是針對費爾巴哈的)和內在的一致性。然而,不知為什么孫文卻對此梳理和辨析采取置之不理、視而不見的態度,說什么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那段論述“至今仍然被‘實踐本體論’者加以歪曲,以此把‘非人化自然界’說成是對人沒有意義的,甚至否定‘非人化自然界’的客觀存在,這只能說明‘曲解’者缺乏科學的研究態度”。筆者本人似乎應該屬于孫文所一再批評的“實踐本體論者”,但是筆者不知道像孫文這樣的討論是不是認真的和鄭重的。
孫文還提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類解放為旨歸,故而以整個世界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必須研究世界、社會和人的普遍規律,這是由他們所承擔的歷史責任、歷史任務決定的。無產階級的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是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是解放全人類,最終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一般地這樣說,似乎也沒有什么問題。但是,由“以人類解放為旨歸”,并不能必然地推出必須“以整個世界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這一結論。而且在筆者看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崇高目標,同實踐本體論立場不僅絲毫不矛盾,相反,它們之間恰恰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正是馬克思再明白不過地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6]。共產主義何以同實踐本體論內在地一致呢?這歸根到底是因為實踐本體論所確立的看待方式超越了那種科學認知式的直觀態度。因為后者最多“只是希望確立對存在的事實的正確理解”[7]。而這種“解釋世界”的態度,必然導致對于實然世界的肯定,因而總是保守的和辯護性的,它不可能引發“改變世界”的“革命”。“共產主義”是決不可能在這樣的基礎上歷史地生成的。這也恰恰是馬克思之所以特別強調“改變世界”的原因所在。
孫文說:“我們發現《辯護》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早年馬克思的著作來理解馬克思本體論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思一生哲學向度邏輯進路中有一個‘哲學時期’、‘否定哲學時期’。如果把視角僅僅限于他的‘哲學時期’而不能以整體的視角兼顧考察那樣一個否定舊哲學的時期,勢必就會得出了那樣一種‘實踐本體論’這樣一種哲學本體論范式。原因是在早期是馬克思思想極具嬗變的時期,他脫離舊哲學領地的一個重要界碑就是實踐。這一點何先生在文中對于實踐的一些重要意義的分析,我們認為是事實。但是到了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并沒有僅僅把視角局限在‘實踐本體’,而是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對象不只是實踐活動所涉及的‘感性世界’。”
毫無疑問,馬克思不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的一生中,總是存在著一個由非馬克思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問題僅僅在于,這個轉變的標志和時間究竟何在。孫文也承認“他(指馬克思——引者注)脫離舊哲學領地的一個重要界碑就是實踐”。既然如此,那么奠定了實踐基礎的馬克思哲學難道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嗎?什么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意義上的馬克思?難道《德意志意識形態》還不是成熟的著作嗎?按照孫文的解釋,似乎所謂“否定哲學時期”的馬克思有一個視野上的改變,即由“哲學時期”的以實踐為原初基礎的視野擴展為“整個世界”(即除了“感性世界”,還包括處在實踐范圍之外的所謂“天然自然界”構成的自在世界)。這種觀點并不符合馬克思哲學的一貫立場。筆者認為,馬克思思想的嬗變并不存在一個所謂“哲學時期”和“否定哲學時期”的劃分。那些過于看重詞句的考據家們總是喜歡拿這類把戲為自己的成見服務。但如果注重馬克思思想的實際,就不難發現,馬克思的思想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有其內在的連貫性,在哲學的建構問題上,它不是一種斷裂的關系,而是一種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備的關系。所謂“哲學時期”的馬克思不過是奠定了他的哲學的基本立場和原則,亦即確立了實踐范疇的終極的原初性,而所謂“否定哲學時期”的馬克思并沒有出現一個思想上的斷裂,不是否定“哲學”,而是對他所確認的哲學立場和原則的貫徹、運用和實際地體現。正像我們每個人宣稱一種觀點,事實上都不過是一種解釋學意義上的“我認為”,但并不需要每一次宣稱都必須重復這一告知一樣,馬克思后來的研究(包括其晚期思想在內)不過是他早期確立的哲學立場和原則在實際的運思中的表征而已,它決不是否定了,恰恰相反,而是以最本真的方式肯定了原有的立場和原則。因此,馬克思哲學已經實現了由“說”向“做”的回歸。在馬克思后來的文本中,人們可能找不到有關哲學的多少詞句,但卻可以發現那里無處不充滿著鮮活的思想。所謂馬克思思想存在一個“哲學時期”和“后哲學時期”,不過是一種基于表面化的判斷而得出的膚淺之論。筆者已經就此作過有關的探討[8]。馬克思后來的思想乃是其早年所奠定的實踐之原初性地位之后在思想上的展開和完成。他不再直接談論哲學,不再使用哲學的辭藻,但已經把哲學融入了實際的運思之中,融入了對人的存在的歷史的現象學把握之中。晚期的馬克思已經在自己的哲學敘事中進行人的存在的現象學建構,這是運思中的哲學,如果說在其早期他更多地還是“談論”哲學,晚期則更著眼于“做”哲學了。但這決非哲學觀的改變,而是哲學的成熟和完備。因此,這是馬克思對其早期所奠定的哲學基礎的踐行而非背叛。后來的馬克思決非終結了“哲學”,而是本真地肯定了“哲學”,使其真正地成為有生命的、“活”的運思方式。如果僅僅拘泥于知識論形態的哲學標準,拿它去衡量所謂成熟期馬克思的思想,當然發現不了任何“哲學”的痕跡,然而這恰恰是由錯誤的哲學觀造成的遮蔽,而非馬克思告別了“哲學”。所以,對于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其思想不是缺乏“哲學”,缺乏的只是“發現”。
我們過去對于馬克思哲學有一種被視作理所當然的看待方式,即更愿意從某一部所謂“成熟的”著作中尋求對于馬克思思想的充分解釋,而寧愿撇開其前期的所謂“不成熟的”著作。這完全是一種非歷史的、機械的,從而是不恰當的看待方式。那種認為被我們認可的馬克思思想僅僅存在于所謂成熟著作中的看法,是不符合馬克思思想的演進邏輯的。馬克思并不是在某一本著作(哪怕該著作是被人們認為的所謂成熟著作或經典之作)中完成自己的哲學敘述的,相反,他是通過其一生的思想的實際發生及其展開來表征自己的思想脈絡的。可以說,這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邏輯的東西與歷史的東西相統一的體現。馬克思并非經過研究,把自己的思想結論用一本著作集中陳述出來,其余的都是無關緊要的準備工作。相反,他的不同時期的著作共同組成了他的思想的展現環節。這也正是為什么馬克思思想只有被當作實際地運思過程及其全部展開來對待時才能得以本真地呈現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筆者看來,孫文無非是基于正統的物質本體論立場,重復了它同實踐本體論的對立,但未曾進一步證明物質本體論的正當性,因此,自然也就沒有相應地兌現孫文為自己確立的證偽實踐本體論的宏愿。最后,筆者還是要感謝孫文對拙作的質疑。因為沒有它,就不可能引發筆者對相關問題作進一步思考,從而也就不會有這篇文章的寫作。
[參考文獻]
[1]理查德·泰勒.形而上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17.
[2][3][4][6][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78,76,75,96.
[5]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16.
[8]何中華.關于恩格斯思想中的一個矛盾——兼評所謂的“哲學終結論”[J].山東社會科學,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