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倫理教育哲學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道家倫理教育哲學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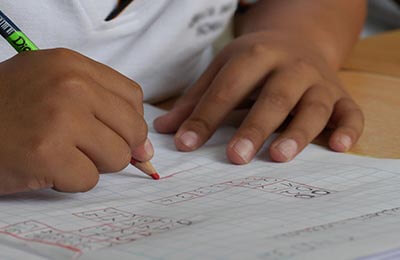
要開創一個新起點,只需打開過去的偉大哲學著作,并努力領會其精髓。曾經被長久地隱埋了的基本真理的重現,將徹底根除在近代造成災難性后果的錯誤。--莫提梅·阿德勒《哲學十大錯誤》一、引言:韋伯問題的后現代倒置以馬克思為代表的19世紀西方社會理論試圖從經濟生活方面去解答現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根源和歷史必然性,并進而論證它注定要被新的公有制社會形態所取代。20世紀以韋伯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馬克思的命題,但轉而從精神生活和價值觀念方面重新論證資本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必然性,同時也放棄了對資本主義注定要滅亡的公有制預言。1989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日益高漲的全球一體化浪潮,使資本主義、市場化經濟成為新的國際秩序的唯一代表。美國國務院思想庫(PolicyPlanningStaff)的代言人福山(FrancisFuknyama)適時地拋出“歷史終結”論,宣稱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經沒有對手,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使歷史的演進過程宣告完成。1一時間,為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及其世界化進行辯護,成為當今媒體和各國主流思想的大合唱。韋伯所提出的命題“什么樣的精神價值在過去數百年中為催生資本主義或現代化的制度提供了基本的動能”,不僅在西方社會學界產生廣泛反響,而且也在非西方的所謂“后發展社會”的理論界引發出熱烈的討論:非基督教的其它宗教價值觀可否成為現代化的又一種動力?2在提出和回答此類問題的過程中,東方傳統社會的某些思想和宗教遺產受到不同程度的關注,其中以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現代化之關系的討論最為熱烈。相形之下,佛教倫理、道教倫理在這場價值重估運動中雖然也被涉及,但受重視的程度遠不如儒家那樣充分。本文旨在從后現代主義的視角出發,對以韋伯為代表的思想史與社會史命題進行倒置,不再為既成的資本主義制度去尋找種種原因,去推進那種辯護性的歷史解釋學,而是從道家倫理的邊緣性立場去審視所謂的現代化的不合理方面,討論道家倫理在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的21世紀所具有的思想資源意義,它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有助于我們避免由資本主義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性所造成的扭曲和異化,又在何種程度上警示追逐現代化的潛在問題和潛伏危機。換言之,本文確信道家智慧與資本主義和現代化本來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馳的。我們現在所能做的不是如何去判定“小國寡民”烏托邦在全球化現實面前的虛幻性,而是在被迫卷入現代化進程的同時保持以淡漠和節制為特色的后現代古典主義精神,嘗試在道家倫理與后現代思想之間的對話與會通,從而得出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相對的“道家倫理與反資本主義精神”的后現代命題。舍勒指出:在資本主義的企業形式占優勢的地方,人肯定就自動般地生長到這一環境中去,即使他們不屬于資本主義類型的人,他們迫于社會和經濟的必然性也不得不沿這一方向前行。就此而言,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促進著資本主義“精神”的繼續存在。3目前,資本主義的組織形式借助于全球市場的力量正在世界各處蔓延,因而也到處催生著與各國族的本土傳統相沖突的資本主義精神。如何保留和汲取傳統的本土智慧,并使之同批判性的后現代精神相互溝通,成為每一個不愿意盲從市場社會消費主義洪流的知識人所面臨的迫切選擇。文章擬從三個方面揭示道家倫理作為抗衡資本主義精神的重要思想資源,如何可能獲得后現代的理解和闡發:以天人不相勝的生態觀為基礎的道家經濟學如何抵制“增長癖”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為“增長癖”效忠的唯科學主義和技術萬能論如何重新面對道家對“機事”與“機心”的尖銳診斷,西方的工具理性的現代困境及后現代超越的可能性;相對主義思想方式對于消解個體、民族的自我中心主義的現實效應。
一、從佛教經濟學到道家經濟學經濟學作為西方社會科學之一門已經獲得了長足發展。在資本主義走向全球的時代,西方的經濟學也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流傳和普及,成為現代高等教育的必要知識門類。然而,發源于資本主義之西方的經濟學真的是一門“客觀的”科學嗎?泰國佛教學者近來已對此提出全面質疑:從理論上講,科學應當能夠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復雜的、相互交織的問題。但是由于經濟學切斷了它同其它學科的關聯,切斷了同更廣闊的人類活動領域的聯系,所以它在面對當今的倫理的、社會的和環境的問題時就顯得無能為力。況且,它對我們的市場導向的社會施以巨大的影響,狹隘的經濟學思維事實上已成為我們最緊迫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危機的主要根源。把經濟學看作科學,究竟值得嗎?雖然有許多人相信科學可以拯救我們,但畢竟局限甚多。科學所揭示的僅僅是有關物質世界的真相之一面。如果僅僅從物質一面去考察事物的話,便無法得到有關事物存在的全面真相了。既然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處在自然的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狀態中,那么,人類的問題也必然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單面的科學的解決方式注定要失敗,問題和危機要蔓延開來。4從經濟學所關注的生產和消費的互動增長指標看,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確實已將人類帶入前所未有的發展之中。“消費文明下的快樂奴隸”總認為自己比祖先時代享有更多的技術優勢和物質財富,卻不能從終極意義上追問經濟增長數字之外的發展限度問題和生存意義問題。對此,佛教經濟學的倡導者們從環境倫理的背景出發,為走入死胡同的西方經濟學敲響警鐘。他們認為對全球環境的持續惡化,經濟學所鼓勵的無節制的生產和消費當然要負重要的責任。他們希望把生態學和倫理學的要素整合進來,重組經濟學的學科體制,使它不僅關注分析數據,而且也關注人與自然的合諧;不再單純鼓勵增長,而要更多地強調增長的極限。從倫理的意義上說,經濟活動必須按照不傷害個人、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方式展開。換句話說,經濟活動不應該對自身造成損害或對社會造成動蕩,而是應當加強這些領域中的良好秩序。如果將倫理價值作為重要因素運用到經濟分析中去,那么可以說一頓便宜而營養充分的餐飯當然要比一瓶威士忌更富有價值。5通過這樣的對照之后,我們可以說,西方的專業化經濟學與佛教經濟學的根本差異來自于不同理解的“經濟”概念。后者要求不只是從經濟看經濟,也要包含生態和倫理的、價值的視界。這種廣義的“經濟”似與文化人類學者的看法有不謀而合之處。美國的著名人類學者馬文·哈里斯便強調:對經濟的兩種界定均有其合理性。人類學者更傾向于關注由文化傳統所構建出的生產、交換和消費的動機(motivations)。6而此種動機又往往由文化背后更深層次的生態因素所決定。在他看來,經濟學家用樂觀主義的態度所觀照的生產力進步,如果改換長距離的文化生態眼光去看,其實是迫于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而被迫選擇的“生產強化”之結果。從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到農業革命,再到以機器生產為標志的工業革命,人類迫不得已地走上強化生產、毀壞環境的惡性循環之旅:“當代的國家社會正全力以赴強化工業生產模式。我們只不過才開始為新一輪生產強化所造成的環境資源枯竭付出代價,而且無人可以預言為了超越工業秩序的增長極限應采取什么新的控制措施。”7在當今最富于遠見卓識的智者感到為難的地方,道家思想的真實價值也就得到凸顯:自然無為的生活方式也許是避免陷入生產強化惡性循環的唯一途徑。道家圣人們似乎早就獨具慧眼地看到無限制擴大生產與消費對人自身的危害,特別標舉出“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8的生活理想,希望通過節制人的野心和貪欲來達到人口與自然資源間的平衡。道家思想反復強調的“恬淡寂寞無為”、“虛則無為而無不為”、“莫為則虛”,表面上看好象是講修行的訓練,從大處著眼則可以理解為一種調節物我關系、天人關系的生態倫理。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們有可能象佛教經濟學的建構者那樣勾勒一種道家經濟學的原理輪廓。道家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在于擺正人與自然的關系。首先,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一部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生死與共,唇齒相依的。所以不容忍把人自己凌駕于自然之上的狂妄態度,也就不會導致征服、劫取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暴行。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四大,而人處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莊子云: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10這樣理解的“并生”關系是保證人類效法自然,順應自然的理論前提。人的經濟活動當然也要在這一大前提之下加以統籌,以求得樸素簡單的生存需求為限度,盡量回避人為的增加生產和消費的做法。《莊子·大宗師》所描繪的真人,可以代表道家經濟學的這種自然主義理想:“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11真人是善守天然而拙于人為的楷模。真人式的生活將會最小限度地妨害自然,最大限度地防止生產強化,使“天與人不相勝”的純樸合諧狀態得以長久維持。在馬文·哈里斯的經濟觀中,導致環境資源枯竭的是人為的生產強化,而導致生產強化的又是人口的增長所帶來的生存危機,他把這稱為“生殖壓力”。人與自然之間原始均衡狀態的打破,就是由這種生殖壓力所造成的。如果我們不得不承認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眾多的動植物物種是不可再生的,而人口的增長卻是無止境的,那么如何限制人口增長,就成了保證天人不相勝的合諧關系的根本。對此,道家經濟學已有非常充分的認識。從老子的“小國寡民”到莊子的“人民少而禽獸眾”之說,都是把問題的實質落在人口的“少”這個必要條件之上。“禽獸多而人少,恰恰同今日世界人口爆炸而動物大量滅絕的現實形成鮮明對照。對于狩獵采集者來說,禽獸多便意味著食物資源的豐富供給,人少則意味著人均獵獲食物的數量和時間相對要求不高,使原始生產式的分享和不爭建立在優裕的物質和生態基礎上。禽獸多和人少的遠古現實還使人口與資源的比例處在最優狀態。人們在優游卒歲的生活方式中當然也不會激發出過分追求物質利益的貪欲和奢望,那正是老莊標舉的無為哲學盛行于世的地方。”12如果把“增長癖”看成結束了狩獵采集式古樸生活方式的人類所患上的文明病癥,那么其潛在的病根就在于人口本身的增長以及與人口增長成反比例的生存空間的負增長。老莊早在文明史的早期階段就已經意識到這將是一個無法克服的矛盾,所以針鋒相對地設想出一系列應對措施:一方面控制人口總量以保持生態系統的均衡,另一方面教育個人少私寡欲,防止陷入無休止的物質追逐。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13這是莊子為受物欲驅使而不能自覺地世人所發出的由衷嘆息。不論是對以傳宗接代、增殖人口為目的儒家信徒來說,還是對患有“增長癖”與“發展癖”的西方企業家來說,這嘆息都有充分的警世效應吧。“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財用有余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14正與反兩個方面的榜樣就這樣為道家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形象的說明。
二、反思唯科學主義與技術萬能論與西方經濟學相呼應的另一種理性異化形式是唯科學主義。由于科學是西方近代文化的主要崇尚對象,唯科學主義的價值觀也伴隨著西學東漸的歷史過程而傳播到世界各地,科學取代神靈,成為現代生活中的救世主,技術萬能的信念日益深入人心。受西方經濟學思維定勢左右的人們既然把增加生產作為人類進步的根本尺度,于是科學技術作為實際的生產力當然被幻想成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東西。殊不知科技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增加人的能力的同時,也會改變人性和破壞人的生存環境。最為可悲的是,人類一味追求科學技術的進步,陶醉在“人定勝天”的自我中心幻夢之中,越來越淪為喪失本真面目的科技奴隸而不自知。美國的后現代主義學者霍蘭德指出:現代夢想繞了一個奇怪的圓圈。在這個圓圈中,現代科學進步本打算解放自身,結果卻危險地失去了它的地球之根,人類社區之根,以及它的傳統之根,并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它的宗教神秘性之根。它的能量從創造轉向了破壞。進步的神話引出了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15這就呼應了海德格爾有關科學技術正在將人類從地球上連根拔起的告誡,對科學技術的負面作用有了清醒的認識。這些負面作用究竟有多嚴重呢?霍蘭德的描述是相當令人震驚的:在接近20世紀末期的時候,我們以一種破壞性方式達到了現代想像(modernimagination)的極限。現代性以試圖解放人類的美好愿望開始,卻以對人類造成毀滅性威脅的結局而告終。今天,我們不僅面臨著生態遭受到緩慢毒害的威脅,而且還面臨著突然爆發核災難的威脅。與此同時,人類進行剝削、壓迫和異化的巨大能量正如猛獸一樣在三洪水個“世界”中到處肆虐橫行。16科學的本來目的是掌握和控制自然,把人類從自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現在人們終于發現,從自然束縛下解放出來的人原來是能夠毀滅自然和自身的人,有如從漁夫的瓶子中放出來的魔鬼,變得不可收拾了。這種始料不及的惡果,其實早已為道家的智者所預見過。道家千方百計地呼喚人類回歸自然,效法自然,是因為充分體認到自然與人的關系是母子關系、魚水關系。一旦人類以自己發明的技術手段反過來對付自然,也就等于實際上背叛這種母子關系。所謂“征服自然”之類的自大狂說法,在道家看來無異于弒母之罪過。《道德經》第五十七章云: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無為,人自化;我好靜,人自正;我無事,人自富;我無欲,人自樸。17可見在老子眼中的技術進步也就是災禍的隱患、人性的毒藥、因為一切人為的強化生產手段都違背自然的“樸”和“無為”狀態,是和“道”相乖離的。《莊子·天地》中描繪一位抱著瓦器灌溉菜地的老農,斥責子貢向他建議采用新的灌溉機械,其言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18這種對“機事”與“機心”之間因果關系的洞察是非常可貴的,看上去道家好像是有意地和科技進步唱反調,實質上是堅決拒絕淪為工具理性囚牢中的奴隸。二千年后的西方理性異化批判者尼采也對“機事”的危害性有所洞悉,他說:各位所能了解的“科學化”的世界詮釋方式可能也是最愚昧的;也就是說,是所有詮釋方式中最不重要的。我之所以如此說,是為了向我那些搞機械的朋友們保證,今日雖然他們最愛與哲學家作融洽的交談,并且絕對相信機械是一切生存結構的基礎,是最首要和最終極的指導法則;但是機械世界也必然是一個無意義的世界!19如果我們用漢字提供的信息來補充尼采的高見,那么機械世界(當然也包括當今的電腦世界和互聯網世界)豈止是無意義的世界,那本來就是束縛人、拘禁人性的苦難世界。清人張金吾《廣釋名》指出,漢字“械”今指機械或器械,但其原有之意卻是“腳鐐”或“手銬”。其音符“戒”字由雙手加上斧匕組成,意指警戒。英國漢學家,專門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博士引證《廣釋名》的這個發現去說明:機械本身和社會統治集團利益之間有密切聯系,最早的機械是用以拘禁抗命農民的枷鎖。而道家的反技術心理情緒,肯定代表了這樣一種普遍情緒,即不管引用了什么機械或發明,都只會有利于封建諸侯;它們若不是騙取農民應得之份的量器,就是用以懲治敢于反抗的被壓迫者的刑具。20李約瑟從階級壓迫和對立的角度闡釋道家創始者的思想立場,這固然不無啟發意義,但是社會政治的解說似乎不足以揭示反技術心理的更深層的根源。這一點,只要看一下莊子對伯樂治馬而損失其天性的批評,就不難理會了。21“機事”最大的危險是戕害自然之性和造成人性的癌癥--"機心",剝奪生物與生俱來的自由真性。相比之下,它與階級壓迫的政治性關聯反而是次要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道家倫理中蘊含著的對抗唯科學主義和技術萬能論的寶貴思想,長久以來根本沒有得到正面的理解,更不用說認識這種思想的超前性了。受人類中心主義的意識局限,人們把征服自然看成值得驕傲的功績,老莊的反科技態度當然也就被誤解為保守乃至反動。拒絕“機事”的老人也就成為科學崇拜者的笑柄。然而,后現代思想對唯科學主義的抵制和批判,終于給道家倫理的合理價值提供了再認識和再評價的良好契機。如果人類不想加速走向自我毀滅的泥潭,那么道家觀點同后現代科學觀間的對話將會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鑒。在19世紀末,當尼采向人們呼吁警惕“科學化”帶來的愚昧和無意義世界時,人們只當他是在說瘋話。到了20世紀末,西方的有識之士越來越多地站到尼采的立場上來了。英國物理學家大衛·伯姆(DavidBohm)寫道:“在20世紀,現代思想的基石被徹底動搖了,即便它在技術上取得了最偉大的勝利。事物正在茁壯成長,其根基卻被瓦解了。瓦解的標志是,人們普遍認為生命的普遍意義作為一個整體已不復存在了。這種意義的喪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意義在此指的是價值的基礎。沒有了這個基礎,還有什么能夠鼓舞人們向著更高價值的共同目標而共同奮斗?只停留在解決科學和技術難題的層次上,或即便把它們推向一個新的領域,都是一個膚淺和狹隘的目標,很難真正吸引住大多數人。”22他還呼吁,人們必須在現代世界徹底自我毀滅之前建立起一個后現代世界。其具體的措施同前面提到的佛教經濟學的觀點似乎是殊途同歸的:如果人們采取了一種非道德的態度運用科學,世界最終將以一種毀滅的方式報復科學。因而,后現代科學必須消除真理與德行的分離、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倫理與實際需要的分離。當然,要消除這些分離,就必須就我們對知識的整個態度進行一場巨大的革命。23筆者確信,在人類重新看待科學技術的這場認識革命中24,道家倫理所體現出的超前智慧必能發揮積極作用。
四、相對主義與消解自我中心
道家倫理與后現代精神的另一個重要契合點是相對主義。在哲學史上,相對主義一直同本質主義相對立,屬于認識論方面的差異。自從20世紀的文化人類學家倡導文化相對主義以來,相對主義的問題就已經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范疇,成為在多元文化時代實現跨文化對話和理解的一種公認的倫理準則了。后現代主義在顛覆中心(decentering),反叛認知暴力(epistemicviolence),消解霸權話語,揭露和對抗意識形態化的虛假知識,關注和發掘異文化、亞文化、邊緣文化話語方面,大大拓展了文化相對主義的應用空間。而這一切,又恰恰同道家倫理達成某種超時空的默契。人類學的文化相對主義原則要求一視同仁地看待世界各族人民及其文化,消解各種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文化偏見和歷史成見。這是對人類有史以來囿于空間地域界限、民族和語言文化界限而積重難反的“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價值取向的一次根本性改變。正如個體兒童認知發展過程就是不斷消解自我中心的過程,各民族文化也只有在擺脫了“我族中心主義”的思維和情感定勢之后,才有可能客觀公正地面對異族人民和異族文化,建立起成熟的全球文化觀。這也是21世紀擺在各個文化群體面前的共同課題。人類學家麥克杜格爾(Mcduogall)博士在1898年說道“任何動物,其群體沖動,只有通過和自己相類似的動物在一起,才能感到心滿意足。類似性越大,就越感到滿意。……因此,任何人在與最相似的人類相處時,更能最充分地發揮他的本能作用,并且得到最大的滿足,因為那些人類舉止相似,對相同事物有相同的感情反應。”25從這種黨同伐異的天性上看,人類種族之間的彼此敵視和歧視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人們在接受相似性的同時必然會排拒相異性。《在宥》云:“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于己也。同于己而欲之,異于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于是,丑化、獸化、妖魔化異族之人的現象自古屢見不鮮。人類學家報告說,從某些未開化民族的古代文獻和繪畫藝術中,可以找到種族歧視的許多實例。在法國山洞和其他地方發現的人類粗糙畫像,大概是描繪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的,這些圖畫或者雕刻,很像近代末開化民族的藝術作品,說明了畫動物比畫人物容易,畫動鈞的技術要比畫人物技術高超得多,因此,只依靠圖畫來描述當時存在的人類的生理特征是不可靠的,但是反映巴休人和卡菲黑人戰斗的巴休人名畫則大不相同。種族的相對尺寸、不同膚色和兩個種族所使用的戰爭工具都特別具體。一般說來,巴休人夸大了他們自己的某些特征,弱化了其它種族。例如,對方的頭部一概畫得很小而沒有特征,平平淡淡。在埃及,發現了許多在幾個世紀中出現的大量的繪畫和雕刻藝術品,它們是民族學研究的珍貴資料、3000多年前,藝術家們末受訓練但并非不善于觀察的民族學家用人類四大種族的畫像裝飾了皇墓的墻壁。第19朝代的埃及人認為世界只可分為:(1)埃及人,藝術家們把他們漆成紅色;(2)亞洲人或閃族人,被漆成黃色;(3)南方人或者黑人,被漆成黑色;(4)西方人或北部人,被漆成白色,眼晴發藍,胡子美麗。每一種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裝束和特征,能彼明顯地區分開來。除了這四大種族體型,古代埃及人還畫了其它人類種類。它們的絕大多數至今仍能辨認出來。這種民族歧視傾向較早地出現在埃及史前和史后早期的石板彩畫中。人類學所揭示的以上事實表明,自我中心和歧視異端的心理是人類文明一開始就根深蒂固地存在的,也可以說是從史前時代帶來的。要克服它當然并非易事。然而,中國上古的道家的圣人早就教導人們擺脫認識上、情感上的自我中心傾向,能夠以相對的、平等的眼光來面對萬事萬物。老子《道德經》中充滿著關于對立的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莊子·齊物論》更是古往今來傳授相對主義思想方式的最好教材。其中齧缺與王倪對話一段,非常生動的說明為什么要提倡相對主義。莊子借王倪之口說,人睡在潮濕處會患腰疼乃至半身不遂,泥鰍整天呆在濕處卻不怕。人爬上高樹就要害怕,猴子會這樣嗎?這三種生物到底誰懂得正確的生活方式呢?人吃飯,鹿食草,蜈蚣吃小蛇,貓頭鷹愛吃死老鼠,這四者究竟誰的口味是標準的呢?26莊子說到的這些情況雖然是在不同的物種之間發生的,但其棄絕偏執,防止絕對的道理同樣可以適用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既然每一種文化都是自我中心和自我本位的,那么也只有站在無中心、無本位的立場上,才能夠走向相異文化、相異的價值觀念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容忍。就此而言,后現代主義要求消解被意識形態絕對化的種種信念、價值、思維和感覺的方式,揭發絕對主義和本質主義話語的虛假實質,這和莊子的見解是相通的。認識上的消解中心關于是非之爭的標準問題,《齊物論》也做出了雄辯的說明: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27這里所提出的是對不同主體之間爭執時的是非評判標準的徹底質疑。在莊子看來,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固定標準,相對的標準也只能通過放棄自我中心后的交流協商去尋求,去磨合。著名的“吾喪我”命題,以及“心齋”“坐忘”之術,一方面講的是如何悟“道”的功夫,另一方面也是擺脫自我中心的感覺和思維定式的具體訓練措施。如果擴展到跨文化交往的層面上來看,在當今的許多國際政治和外交上的爭端,如人權問題,各國總是自我本位,各執一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大家都懂一些道家相對主義,是完全能夠避免沖突,展開有效對話的。象“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一類的一相情愿的行為,也只有學會用相對主義的眼光去看事物之后,才能夠從根源上得以避免。《莊子·秋水》云:“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由此看來,相對主義的眼光也就是“道”的要求,是一視同仁的平等待物之方。當今正在走向全球化的各個民族、國家,非常需要認真考慮“道”的這種平等原則。唯有首先自覺的放棄以往那種“自貴而相賤”的傳統習慣,和平共處的理念才不至于淪為空話。
綜上所述,道家倫理資源中潛存著某些與后現代精神相通的要素。在21世紀的跨文化對話的世界性潮流中,回過頭來重新傾聽道家傳統的聲音,也許就象哲學家阿德勒所說的那樣,能夠為處在危機之中的我們“開創一個新起點”。
注釋:
1福山《歷史的終結》(TheEndofHistory),《NationalInterests》1989,Summer,中譯本,遠方出版社,呼和浩特,1998年。2參看[日]富永健一《社會學原理》第十三章,嚴立賢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又:黃紹倫編《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3舍勒(M.Scheler)《資本主義的未來》,羅悌倫等譯,三聯書店,北京,1997年,第8頁。4佩尤托(VenerablePrayudbPayutto)《佛教經濟學》(BuddhistEconomics),泰國曼谷佛學基金會,1994年,第頁。5佩尤托《佛教經濟學》,第頁。6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文化人類學》(CulturalAnthropology),HarperandRowPublishers,NewYork,1983,p.62.7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CannibalsandKings:TheOriginofCultures),黃晴譯,華夏出版社,北京,1988年,第3頁。8《莊子·馬蹄》,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北京,1961年,第341頁。9《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見朱謙之《老子校釋》。10《莊子·齊物論》,郭慶藩《莊子集釋》,第79頁。11郭慶藩《莊子集釋》,第234-235頁。12葉舒憲《莊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漢,1997年,第621頁。13《莊子集釋》,第56頁。14同上書,第441頁。
15喬·霍蘭德《后現代精神和社會觀》,格里芬編《后現代精神》(SpiritualityandSociety:PostmodernVisions),王成兵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64頁。16同上。
17朱謙之《老子校釋》,中華書局,北京,1984年,第231-232頁。18《莊子集釋》,第433頁。19尼采《快樂的科學》,余鴻榮譯,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年,第285頁。20李約瑟(JosephNeedham)《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140頁。21《莊子·馬蹄》,見《莊子集釋》,第330頁以下。22大衛·伯姆《后現代科學和后現代世界》,大衛·格里芬(DavidRayGriffin)編《后現代科學》(TheReenchantmentofScience),馬季方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75頁。23同上書,第86頁。
24關于這種革命的癥兆,可參看赫伯特·豪普特曼(H·Hauptman)《科學家在21世紀的責任》,保羅·庫爾茲(PaulKurtz)編《21世紀的人道主義》,肖鋒等譯,東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1-8頁。25哈登《人類學史》,廖泗友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頁。26《莊子集釋》,第93頁。27《莊子集釋》第10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