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學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教育哲學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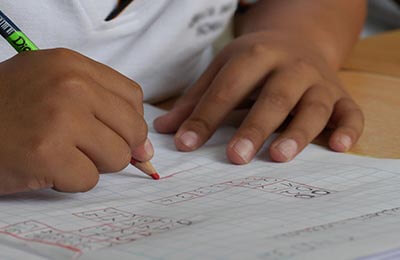
張楚廷教授對教育哲學的求索近40年,以其富于智慧和熱情的工作經由數學、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等領域“自然流淌”著“走向”了哲學。2003年,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國內第一部課程哲學專著《課程與教學哲學》,引起強烈反響,獲得第14屆中國圖書獎。2004年,又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國內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學著作《高等教育哲學》,從結構主義落筆,以哲學與歷史學的眼光考察現代、后現代課程觀、教學觀,對長期以來教育界一直習焉不察的許多觀念發出了深刻的追問,洋溢著濃厚的人本主義思想。2006年8月在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哲學》,將視野投向了更深邃、更廣垠的教育空間,此書可視為他對教育問題思考、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他思考一般哲學問題的奠基之作。[摘要]張楚廷先生主要以教育為論域闡釋著他的哲學。先生對于人本理念、生命情懷、審美精神、哲學情結和民族深情的一以貫之的堅持和關切,凝結成其教育哲學的靈魂和主旨。先生的哲學堪稱“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哲學”。
[關鍵詞]張楚廷;教育哲學;旨趣
Abstract:ProfessorZhangChu-tingexpoundshisphilosophybymainlytakingeducation
asthedomain.MrZhang’sconsistentinsistenceandconcernforthepeople-orientedideas,
thefeelingsofcherishingforlife,thespiritofesteemingbeauty,thefeelingsofcherishingforphilosophy
andthedeeplovefornationcongealsthesoulandpurportofhisphilosophyofeducation.Mr.Zhang’sphilosophycanbecalled“theChinesePhilosophyofOurOwn".
Keywords:ZhangChu-ting;educationalphilosophy;purportandinterest
先生之于哲學,正如《課程與教學哲學》前言所說的那樣——“從未想過要見見它”,“從未欲立一個什么目標”,是在“操練著、欣賞著”、“琢磨著、探索著”的過程中“情不自禁”地走向哲學的。先生主要以教育為論域,卻始終指向更為根本的人本身,指向對真善美的終極追問。先生不只是一名學者意義上的哲學家,還把哲學理念和情感推及整個人生,先生的學術和人生無不充滿哲學意味,而且這意味越來越濃烈。
列寧說過:“沒有’人的情感’,就從來也不可能有人對于真理的追求。"[1]讀先生的哲學,總能感受到其一以貫之的堅持和關切,總能感受到他那鮮明的人本理念、生命情懷、審美精神、哲學情結和兼具歷史和時代感的民族深情。先生內心深處的這份堅持和關切,流淌著先生“情不自禁”的情真意切,凝結成其哲學的靈魂和旨趣。
一、始終秉持人本理念
先生的教育哲學處處流露出他對人本身的尊重和珍愛,人本理念始終是先生展開教育哲學研究乃至一般哲學研究的一個“基點”。正如先生所言,“從最基本的意義來說,‘人是什么’,或者,‘生命是什么’,無疑是教育必須面對的第一問”[2](P24);“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抓住了這個根本就抓住了教育的根本”[2](P27)。
《課程與教學哲學》一書站在人本立場,凸現“人文引領”的思想主線,在對人文課程、科學課程和社會課程內涵界定的基礎上,構建了以“人文引領的和諧課程觀”為核心的課程與教學哲學體系。《高等教育哲學》以人本為基調,“鮮明地提出了高等教育哲學的人本之‘底’,這與布魯貝克第一次提出‘高等教育哲學論題’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比較全面科學地構建出人本高等教育哲學體系”[3]。《教育哲學》的第一至四章分別以“從哪里開始考察教育”、“人是什么”、“關系中的人”、“人發展什么”為標題,全書8個一級標題中有3個以“人”為中心語,69個二級標題中有15個以“人”為中心語(另有8個二級標題通過承前省略或設問等方式省略了其中心語“人”),一、二級標題中共有18個“人”字。如果這些符號意義上的統計尚不足以說明作者對“人”的看重的話,只要你能打開書本,幾乎每一頁、每一段都在說“人”,可謂通篇見人。
先生堅持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和情感闡釋著對“人”的思考和期待:
——人是神圣的和復雜的。他說:“教育在喪失了對人的神圣感的時候,教育的神圣頃刻喪失;社會在喪失了對人的神圣的感覺的時候,社會的神圣充其量只是一種虛無的實在。"[2](P123)人的神圣和尊嚴源于人的復雜性。他在《教育哲學》的“人是什么”一章中對把人的本質簡單歸結為社會性甚至是階級性的論調進行了正面批判,進而提出了人的反思性、反身性、自增性、自語性、自育性和審美性六大基本特性。他還意猶未盡地說道:“相信任何真正的科學家(人文科學家、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唯有在‘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質是什么’這個問題上,不會有他們必然會有的那種高傲。”[2](P35)
——人是發展著的人。他從康德的“胚芽說”與馬克思的“需要說”入手,深刻論述了“人的可發展性”,認為“人是可以獲得新的生命的生命”[2](P107),“發展得最好的人,不只是因可發展而發展了的,而是其可發展性也得到了發展的人”[2](P113),進而指出,“教育的根本在發展人的可發展性”[2](P110)。沈又紅等:“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哲學”——張楚廷教育哲學旨趣五解——個性與自由是人的生命。他在論著和演講中多次表達了對于個性與自由的珍愛,并在《教育哲學》的“人發展什么”一章中鮮明地提出:人的全面發展實質是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他這樣訴說著人的個性:“發展個性就是發展多樣性,發展豐富性,發展創造性",“教育在于把每個人培養成為他獨特的自己,更高大的自己”[2](P132);他這樣贊嘆著人的自由:“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標志,人獲得自由的狀況即它的生命狀況,人對自由的把握力即他的生命力。”[2](P228)
——個人、個體、“我”是談論“人”的前提和出發點。他謹慎地反思著那段“我”被“我們”遮蔽的歷史,進而指出:“馬克思說‘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是出發點,是前提,是第一前提”[2](P77),“人的消逝是從個人的消逝開始的”[2](P79)。
——做自信的人。他的學術和人生無不顯示出對于自信的堅持和追求。他飽含激情地說著,“人們希望人成為高大的人,人也就把這種希望寄托給教育,唯愿教育能使人真的高大起來”[2](P71)。他不無欣喜地說著,“如今的中國,人字越寫越大,從政治學的角度,我們看到了最基本——人權;從社會學的角度,我們回到了最基本——人心;從心理學的角度,我們回到了最基本——人性;從科學學的角度,我們回到了最基本——人學;從課程學的角度,我們回到了最基本——人文(課程);從經濟學的角度,我們看到了最基本——人才;從倫理學的角度,我們看到了最基本一一人格;從哲學的角度,我們大踏步地走向最基本——人!”[4]他十分堅定地說著,教育的第一使命是“讓人像人,讓人更高大”,“對于自信,我看得特別重,甚至于我的基本追求之一就是把學校辦成‘自信的大學’”。
二、始終洋溢生命情懷
伴隨著對人的追問,先生的哲學中洋溢著濃濃的生命情懷。
他在《課程與教學哲學》的“‘存在’的諸種含義與生命哲學”等章節中著力追問“生命是什么”、“存在與生命的關系”等問題。他這樣闡釋著生命哲學:“生命是世界的內在本質,最終根源”[5](P183),“生命先于哲學”[5](P185)。這部著作處處流淌著他對于生命的熱愛和敬重,有論者這樣評述該書——“課堂生活里自然流淌著的生命”[6]。
在《高等教育哲學》第一章“認識論、政治論與生命論”中,他對布魯貝克提出的認識論與政治論互相補充的高等教育哲學觀進行了批判與發展,認為“對于高等教育哲學,不能僅僅歸結為政治論和認識論那兩種基礎之上”,并對蘇格拉底、培根、洪堡等人的觀點進行了評述,進而感嘆:從這里“我們也看到了高等教育的生命論根基”。他通過對既有哲學的考察和對一些不同類型的大學誕生的案例的分析,認為高等教育原本是作為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誕生的,高等教育是人的特殊生命活力的進一步騰升和上揚,旗幟鮮明地提出以生命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觀。
通篇見人的《教育哲學》更是通篇流淌著生命,正如書中所言:“‘教育的對象是生命’”或‘教育的對象是有生命的人’”;“本書關于教育的主題不需要我們說那么遠,我們暫且可以把更神奇的地球擱置一下,還是來討論生命,并且,還只討論人這種生命,它可能是神奇生命中的神中之神”[2](P23)。
三、始終貫穿審美追求
先生的哲學是關注和凸顯人的哲學,而先生篤信馬克思關于“人也是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的論斷,在哲學著作中反復引用馬克思的這句話,因而,先生的哲學在最基本的理念層次始終貫穿著一種執著的審美追求。
他在《教育哲學》第二章“人是什么”中以“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為題專門設立一節來闡述其教育哲學的美學基礎和審美追求。他構建了一個由5個基礎性命題組成的教育公理體系,創立了教育的美學公理——“人在通過反身性作用于自己的時候,基本的中介是美學因素。人按照美的規律構造自己。”[2](P171)他指出,“人在對象自我化、自我對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學的(這是人可發展性的基本因素,這也就是教育的基本要素)”[2](P221)。在論述真善美的關系時,他說,“美是所有這一切,或美關聯著這一切”[2](P172),“美育是更高層次的教育,甚至可以說,離開了美育不能想像出有效的教育”[2](P172),進而指出,每位教育工作者,不僅在自己所教授的任何科目中向學生展示或揭示必然存在的美,而且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教授活動本身也是美不勝收的(藝術的),從而讓美進入學生的心靈,成為他構造自己的豐富資源,獲得自己美好的新生命。這很可能是教育的真諦,是教育成為一種難得的藝術的根由。
先生在自己的哲學中追問著教育之美,構建著美好人生,同時,他也在美的指引下試圖呈現美的哲學,構建可愛的哲學。哲學之美主要寓于思想內容和表現形式之中。先生始終堅持著說自己的話,表達自己的思想,形成了個性鮮明、深入問題本質的獨特內容體系。先生論天、論地、論人、論我、論教育,無處不閃耀著靈性和智慧的光彩,展示出理性與德性的力量。哲學表達亦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種哲學是否可讀和可愛,能向實踐領域和現實生活走多遠,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對它的表現形式。先生的哲學充斥著結構美、語言美和意境美,可謂詩情畫意,美不勝收。他在著作和演講中盡情描繪著體育之美、音樂之美、藝術之美、數學之美、科學之美、教育之美、德性之美、理性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等一組組意境和意象之美,自由揮灑著他那文采紛呈、邏輯嚴密、靈動詩意、富于個性的語言之美,而數學家的經歷和對結構主義的深層把握又使得先生的哲學具有獨特的結構之美。/
四、始終懷揣哲學情結
先生哲學的發展過程正好與哲學發展的歷程相吻合,從《教學論綱》到《課程與教學哲學》,到《高等教育哲學》,再到《教育哲學》,從教學、課程、管理、高等教育等具體領域的哲學思考到整個教育學領域的哲學思考,從局部到整體,從具體到一般,從經驗到超驗,是欣然而至、自然生成的過程,是在欲罷不能的層層追問中展開教育之思的過程。先生在走向哲學的途中深深地喜愛上了哲學,這種喜愛又吸引著他更加堅定和瀟灑地走向哲學研究的縱深,以致于近些年把學術研究的主要旨趣和精力轉向了哲學領域,并在這一領域頻頻收獲,建樹頗豐。先生走向哲學,不只是他所說的“不期而遇”,更源于他幾十年“問天、問地、問人、問自己”的不懈追問,源于一種濃烈的哲學情結。先生的哲學是愛哲學的人的哲學。
先生的哲學情結首先是一種對哲學的敬重與熱愛之情。他十分推崇恩格斯的論斷——“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這句大家十分熟知的話中,“理論思維”指的就是哲學。他多次在演講和著述中闡述哲學對于一個人、一所大學、一個民族的重要性,他多次不無欽羨地談起德國哲學的繁榮對于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人類的意義。他在《哲學對于大學意味著什么》一文中集中描繪了哲學與大學、哲學與科學、哲學與民族的共盛共榮景觀,他在文章末尾說道,“哲學必定是世界頂尖大學上空懸掛的一顆巨星”。他十分欣賞柏拉圖關于“教育的最高形式是哲學”的觀點,他指出,“教育的貧乏源于哲學的貧乏”[7](P23),“哲學的貧乏與教育的貧乏幾乎同時存在”[7](P24)。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作為校長的他從北大、人大、武大引進了一批哲學博士,在一所地方師范大學率先辦起了哲學專業,并建立了哲學系,不僅使湖南師范大學的哲學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且以此為支撐全面提升了大學品位。其次,是一種不懈追問根本、追問基點或起點問題的情結,一種走向哲學縱深的執著。哲學是一門追問的學問,是一門問出來的學問。他始終“堅持從世界本身去說明世界”,他的哲學著作中關于“我們的‘底’在哪里”、“教育第一問”、“教育公理”等問題的論述,關于元問題的探究,無不貫穿著一種追問本源和終極的自覺和執著。再次,是一種強烈的批判意識。思想使人成為萬物之靈,思想的力度在于批判。批判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存在方式。批判也是哲學思考的基本方式,是哲學的生命和使命。先生認為真正的哲學是質疑的、批判的、反思的,先生的哲學正是在富于邏輯力量和個性魅力、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理性批判基礎上“生長”出來的。《課程與教學哲學》用了較大的篇幅對當前流行的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科學主義、人本主義以及社本主義課程與教學觀給予了清醒的反思和冷峻的批判,對這些流派和主義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進行了理性分析和評判,進而創造性地建構了自己的課程與教學哲學體系。《高等教育哲學》更是一部充滿批判光彩的著作,他從對布魯貝克提出的認識論與政治論互相補充的高等教育哲學觀的批判著筆,提出了以生命論為基礎的高等教育哲學觀,并對“驕傲使人落后”等中國教育長期持有的一些基本理念以及高校的定位問題、特色問題提出了質疑與反思。“這種質疑,對中國教育界乃至整個社會都是非常可貴的警示”[3](P26)。《教育哲學》構建了一個教育哲學體系,這種構建總與批判相伴隨,“教育社會性問題”、“教育就是教育”、“人有沒有本質”、“人與個人”、“關于全面的‘全’”、“在泛化中窄化”、“‘靈魂工程師’論”、“‘適應論’評析”等章節更是通過批判顯明作者的立場和主張,充滿了獨創性和建設性的批判。
五、始終飽含民族深情
先生曾經深沉地寫道:“如果我曾有過一些靈感,那是來自大自然;如果我曾有過一些奇思異想,那是來自歷史,來自我的祖宗,我的民族,我的祖國……宇宙爆炸,其中出了一個銀河系,太陽系在它的邊沿,太陽系已生出了一顆小行星,它幸運地有了生命,尤其是奇妙地孕育出了人,從此,它成了一顆有意識的星球,從此,有了美麗和幸福,也有了丑惡與苦難,有了同苦難的抗爭,有了對幸福的追求,有了夢想,有了璀璨斑斕。也有了我們的祖宗,有了我們的民族,有了我們今天寫不完的詩篇,唱不盡的歌謠。”[8]在《課程與教學哲學》的前言中,他飽含真情地寫道:“不會忘了我的祖國已進入到了一個最美好的世紀這一歷史對這部著作的決定性影響”,“我們更深切地期待,在這個領域里,有我們中國人而真正屬于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哲學”[5](前言)。
無論先生的人本理念,還是生命情懷、審美追求,乃至哲學情結,都凝結在先生對自己偉大民族——中華民族——的深情厚意之中。先生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追尋著“真正屬于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哲學”。先生哲學之途的“情不自禁”集中表現為民族之情。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先生的哲學亦堪稱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哲學。
誠哉斯言,先生一直致力于建設中國人自己的哲學。先生對國外學說的謹慎態度、對于中國理論與實踐的熱切關注,無不透射著一名學者對自己祖國和民族的赤子之情。先生的哲學植根于歷史文化,潤澤于民族真情,著生于當今時代,著眼于中國社會的實際,富于文化底蘊和時代氣息,飽含民族深情,是中國人自己的哲學。
[參考文獻]
[1]列寧.列寧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5.
[2]張楚廷.教育哲學[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
[6]張傳燧.課程哲學:課堂生活里自然流淌著的生命[J].當代教育論壇,2005,(3):128.
[7]張楚廷.新世紀:教育與人[J].高等教育研究,2001,(1).
[8]張楚廷.張楚廷教育文集·校長敘論卷(第4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613.
[3]魏飴.人本高等教育哲學的誕生與發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5,(7):25.
[4]張楚廷.高等教育哲學[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433.
[5]張楚廷.課程與教學哲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