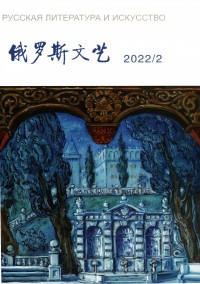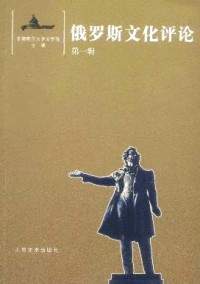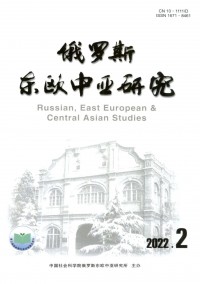俄羅斯哲學發(fā)生發(fā)展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俄羅斯哲學發(fā)生發(fā)展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還是在五十年代,一批蘇聯(lián)哲學專家來到中國傳授馬列主義。不僅我們這些哲學系的學生要去聆聽教導,而且連馮友蘭、賀麟、張岱年、任華等老教授也要去接受教育。就是從這些蘇聯(lián)專家口中,中國人首次聽說俄國偉大的哲學家和光輝的俄羅斯哲學史,知道了俄國從遠古時代就已經(jīng)存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唯物主義在不斷戰(zhàn)勝唯心主義的斗爭中愈益壯大,終于成為俄羅斯哲學的主流。布爾什維克正是繼承了俄國的唯物主義傳統(tǒng),將其與馬克思主義相結(jié)合,創(chuàng)造了列寧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嶄新階段。經(jīng)過幾近半個世紀的宣傳—懷疑—揭露—探索,我們終于明白:這一些說法有很大的水分,尤其是關(guān)于俄羅斯哲學發(fā)生發(fā)展的特點的說法簡直是不能成立的。這幾年接觸到過去被蘇聯(lián)禁止發(fā)行與閱讀的不少書籍(其中許多已被介紹到我國)的朋友都大呼上了蘇聯(lián)專家的當,原來俄國哲學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是另一種樣子,原來俄羅斯哲學史有其自身極為獨特的、非日丹諾夫的唯物唯心斗爭的公式所能概括的、與西方或東方哲學發(fā)展所不同的特點。
一
與希臘不同,也與中國和印度不同,俄羅斯哲學的出現(xiàn)甚晚。過去蘇聯(lián)為了吹噓自己的文化悠久,常常把俄國的哲學發(fā)生的時間推前到十一、二世紀。究其手法,大致有二:一是將當時并非俄羅斯所屬,但后來并入俄羅斯以至蘇聯(lián)版圖的地區(qū),都看作俄國哲學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地區(qū),這樣,就很容易地將俄國哲學的發(fā)生推前好多年。比如,在敦尼克等主編的《哲學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二節(jié)“蘇聯(lián)各民族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中,竟然將十—十一世紀的阿拉伯哲學家伊本—西拿列入其中。二是在前人的著作中尋章摘句,煞費苦心地從中尋找哲學語言,用以證明哲學的產(chǎn)生和存在。但是我們?nèi)绻J真地看看這些書,就可以知道這種做法的荒謬了。原來這些書籍都是些宗教用書,如圣經(jīng)注釋、祈禱文、宣道書以及教義爭論等等。敦尼克等的《哲學史》說,這些東西反映了僧侶的世界觀,以為說了“世界觀”三個字,就能列入哲學之中,難道不是笑話。實際上,宗教本身自然也是一種世界觀,但那并不能說就是哲學,而只能說是宗教,頂多能說是神學。如果說到哲學的發(fā)生,那么至少它要有自己的獨立形態(tài)。敦氏《哲學史》在此問題上是極不嚴肅的,按照它的說法,當人類喊出“啊,天哪!”的時候,哲學就誕生了。嚴格地根據(jù)俄國真實的歷史演變,也嚴格地根據(jù)哲學本身的要求,俄國的哲學發(fā)生自何時呢?按照著名的俄國哲學史家弗洛羅夫斯基(1893—1979)的說法,俄國的文化史自羅斯受洗開始,在此以前的文化是多神教的文化,而且是沒有文字記載的文化。但是羅斯受洗之后,大量涌入的是拜占庭文化,這種文化并不能成為大多數(shù)人的文化,而只能是少數(shù)人的高雅文化,大多數(shù)平民甚至仍然留戀多神教文化—粗俗文化。前者雖然高雅,但卻是一元化的;后者雖然粗俗,但卻是多元化的,因而也是涵有較多自由的。俄羅斯文化就是在這樣兩種文化的長期沖突和融合中逐漸形成的。不過,由于拜占庭的東正教文化是官方所推崇的,因而它很快就占了主導地位,并在發(fā)展過程中衍生出俄羅斯東正教的神學。這種神學還不就是哲學,因為它依附于宗教,為宗教服務,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只是到了十八世紀,才逐漸出現(xiàn)了獨立的哲學。(參閱弗氏《俄羅斯神學之路》)第1--6章,巴黎,俄文版,1937)而別爾嘉耶夫和洛斯基則將俄國哲學的誕生期推得更晚。別氏認為,“獨立的俄羅斯哲學的綱領(lǐng)是由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亞科夫第一次提出的------他們徹底宣告抽象哲學的終結(jié),并竭力追求完整的知識。通過克服黑格爾哲學而從抽象的唯心主義轉(zhuǎn)向具體的唯心主義。索洛維約夫繼續(xù)了這條路線,并寫出了體現(xiàn)自己哲學的著作。”(《俄羅斯思想》,中譯本,157—158頁)洛斯基在其《俄國哲學史》中說得更加明確:“俄羅斯哲學思想系統(tǒng)發(fā)展的開端可以追溯到19世紀。------獨立的哲學思想在19世紀開始形成,其起點是與斯拉夫主義者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來科夫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是部分實現(xiàn)從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來科夫思想的精神出發(fā)創(chuàng)建基督教哲學體系的第一個人,他的繼承者是一大批哲學家。”(《俄國哲學史》中譯本,第6-7頁)
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還是一個甚為艱難的任務,必須深入俄羅斯古代文獻之中,才能得出自己的結(jié)論。但是現(xiàn)在起碼可以確定,真正獨立的俄羅斯哲學出現(xiàn)是較晚的。
二
俄國哲學發(fā)生發(fā)展的第二個重要特點是:自神學而生。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從其內(nèi)容來說,與宗教神學關(guān)系極為密切,甚至可以說,它最初就是對神學的前提及其所提出的重大問題的哲學探究,因而主要內(nèi)容是宗教哲學。從其代表人物來說,雖然大部分人并非宗教神職人員,而是些自由思想家,但由于俄國深厚的宗教傳統(tǒng)以及他們所受的神學教育,所以宗教問題及神學前提常常成為他們思考的起點,并由此升華為哲學。從其產(chǎn)生過程來說,在東正教意識形態(tài)的長期統(tǒng)治下,獨立的俄羅斯哲學遲遲沖不出思想的牢籠;當自由意識發(fā)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脫離神學而獨立,但又明顯地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當一種意識形態(tài)實行思想專政時,要想沖破這種統(tǒng)治,首先要討論的問題不可能是遠離這種意識形態(tài)所提出的重大問題,而只能是這些問題。就像我們這里前些年討論人道主義問題時那樣。(當時,首當其沖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是否人道主義,而不可能深入于人道主義本身的諸多問題。)
由于東正教被定為國教,在意識形態(tài)甚至文化領(lǐng)域成為統(tǒng)治力量,所以,多少世紀以來,俄羅斯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自從基輔羅斯的弗拉基米爾大公皈依基督教以后,基督教的“文字和書面文化便在羅斯得到普遍傳播和迅速發(fā)展”(蘇聯(lián)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俄國文化史綱》,中譯本,1994,第19頁)。十一世紀,在諾夫哥羅德創(chuàng)辦了第一所可容納300人的學校,這主要是為神職人員子弟設(shè)立的,以使他們繼續(xù)為宗教服務。到十四—十五世紀,雖然有一些小型的教人識字的私塾出現(xiàn),但是由神職人員辦的,教師也都是神甫等;“教材”不過是圣經(jīng)、祈禱文之類。到了十六世紀,仍然如此,只不過規(guī)模比過去大了:“識字教育由專門的‘教書先生’來做。一些私塾往往養(yǎng)著一批教書先生。這些私塾有時設(shè)在修道院里或教堂中,由修道士或神甫任教師。有時非教徒也開辦私塾,甚至農(nóng)村也有。孩子從七歲起認字,而且數(shù)人同時學習。課本是手抄的,孩子開始時先學字母,再學音節(jié),初步掌握語法。學生在學習的第二階段要背熟日課經(jīng),還要學會寫字。學習結(jié)業(yè)就是學會念圣經(jīng)詩。”(同上書,第139頁)一直到十七世紀,正規(guī)的初等學校教育仍未建立起來,但是為了使識字這種文化普及工作大體統(tǒng)一起來,編寫了統(tǒng)一的識字課本、語法書、乘法表,此外的重要教材就是贊美詩、日課經(jīng)和教堂禮拜用書。更高等的教育則是由修道院創(chuàng)辦的,如1665年在莫斯科巴斯基修道院開辦的“語法學校”;1867年根據(jù)西爾維斯特.梅德維杰夫的建議創(chuàng)辦的“斯拉夫—希臘—拉丁文學校”(后改為學院,再后則成為俄國神學院。這是俄國第一所高等學校)。可見,長期以來,教育的中心內(nèi)容是宗教。從這幾個世紀的印刷事業(yè)也可看出宗教在精神領(lǐng)域的統(tǒng)治,在這么長的時期里,俄國的印刷業(yè)幾乎集中于印刷宗教書籍,因而使得“俄國許多代人都是從宗教書籍(《圣詩集》、《日課經(jīng)》等)學會讀和寫的。”(同上書,第143頁)直到十八世紀彼得大帝時代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為了改變俄國落后面貌,彼得在俄國設(shè)立了一批軍事學校、一批職業(yè)技校學校,大力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shù),培養(yǎng)科技人才和軍事人才。但是在人文領(lǐng)域,他仍堅持東正教的統(tǒng)治地位。“為了培養(yǎng)有文化的神職人員,下令‘教士與助祭之子’就學于斯拉夫—希臘—拉丁文學院。這所學院成了高級神學院。初級的神學教育則在教會學校進行,這些教會學校不僅是培養(yǎng)專職神職人員的教育場所,而且也是普通教育的發(fā)軔。”(同上書,第201頁)直到1755年莫斯科大學成立時,才設(shè)立了俄國世俗學校中第一個哲學系。(當然,當時哲學系的重點課程仍然是宗教神學)以上這些情況充分說明東正教對于教育的長期統(tǒng)治。在這種統(tǒng)治下,很難出現(xiàn)具有獨立性的哲學。
當然,在東正教的神職人員學校特別是修道院中都設(shè)有哲學課,甚至設(shè)有哲學教研室,研習從拜占庭傳來的經(jīng)院哲學,研修古希臘羅馬的哲學。但是,這一切都是服務于宗教體驗的。在很長時期里神甫和修道士們從事的工作是翻譯,即使很著名的學者的著作也不過是希臘或羅馬或拜占庭的學者著作的注釋、編篡以至匯編。如十三世紀的佩切爾斯基最著名的著作是《圣僧傳》、《詳解帕里亞書》、《反猶太人辯論匯編》等;十五世紀的約瑟夫.沃洛斯基(1439—1515)著名的《啟蒙者》一書“幾乎沒有超出解釋有爭議的經(jīng)文的范圍”(《俄羅斯神學之路》,第14頁),因為整本書幾乎全部由一系列摘錄和證據(jù)構(gòu)成。至于約瑟夫派的另一創(chuàng)始人、著名的神甫尼爾.索爾斯基(1433—1508)的代表作《背叛信仰》一書,也“和約瑟夫的《啟蒙者》一樣,與其說是獨立的論著,不如說只是作為資料匯編或資料‘鏈條’而編輯的。”(同上書,第16頁)直到十六世紀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據(jù)俄國學者研究,“在十六世紀,希臘的史料開始被自己的、古代俄國的史料所代替。”(轉(zhuǎn)引自《俄羅斯神學之路》,第21頁)而十六世紀發(fā)表的《百項決議集》則完全沒有提到希臘人的榜樣問題,當時擺脫希臘人的影響成了主要的宗教和文化心理。不少神職人員致力于斯拉夫語的、獨立于希臘羅馬傳統(tǒng)和拜占庭傳統(tǒng)的俄國神學。幾個世紀以來,在宗教內(nèi)部出現(xiàn)了許多重大問題的爭論,從而產(chǎn)生了各種不同的宗教派別的對立,如約瑟夫派與禁欲派、改革派與舊禮儀派(亦稱分裂派)、合并教派與反合并教派;等等。東正教神學的相當部分的內(nèi)容就是闡述不同派別的觀點的。另外,它的重點就是:以圣經(jīng)和東正教教義為前提和依據(jù),對東正教的信仰內(nèi)容進行理論闡述和系統(tǒng)研究。東正教神學研究主要是由神學院和修道院的教師和修士從事的。十八世紀彼得一世改革以后,盡管在人文思想上的管制仍然很嚴,但西方近代的先進哲學還是迅速地傳入俄羅斯。這種哲學的自由精神深深地打動了俄國知識分子,一時間伏爾泰成了他們的偶像,連葉卡捷琳娜二世都以結(jié)交伏爾泰為榮。在專制制度的精神高壓下,這種自由精神就像閃電一樣沖破了沉沉黑夜,使俄羅斯文化出現(xiàn)了新的轉(zhuǎn)機。就哲學來說,這種自由精神是獨立的俄羅斯哲學誕生的催生劑。從此,俄國哲學便勇敢地沖破宗教神學的制約,爭取自己的獨立地位,為俄羅斯文化增添了新的奇葩。莫斯科大學設(shè)置哲學系后,不論它的課程如何受到東正教及其教義的限制,但它究竟在神學統(tǒng)治下開了一扇門,使西歐的先進哲學得以潛入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羅蒙諾索夫及一批哲學教授有了相對自由的研究空間,思想比較解放,出現(xiàn)了與官方不同的認識和觀點。羅氏本人受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很深影響,《俄國文化史綱》評價他說:“羅蒙諾索夫的總的世界觀是唯物主義的。羅蒙諾索夫相信物質(zhì)不依賴于意識而存在。誠然,對于物質(zhì)運動引起的物理現(xiàn)象,他還只能機械地理解。羅蒙諾索夫的認識論接近十八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的水平。他認為,經(jīng)驗和思維乃是認識的基礎(chǔ)。思維是總結(jié)經(jīng)驗所必需的,經(jīng)驗離開總結(jié)便失去認識的意義。一切自然都是可知的,不存在人不可認識的現(xiàn)象。”(見該書,第226頁)這里所以引了這么多話,是因為這是我見到的對羅氏哲學觀點最為實事求是的評價,而蘇聯(lián)大多出版物都是任意吹噓,把羅氏說成是世界級的哲學大師。上述可以說明,盡管當時俄國有一批學者受到西歐先進哲學的影響,但他們并沒有超越西歐哲學的創(chuàng)造,他們只是受到影響和進行傳播而已。因而,還不能認為他們開始創(chuàng)造了獨立的俄羅斯哲學,更不能認為俄羅斯哲學已經(jīng)在他們的手上誕生了。
獨立的俄羅斯哲學的誕生,既要具有自由的精神,能夠沖破東正教神學的束縛,又不可能離開俄國精神文化的基礎(chǔ)。只是單純地接受西方的影響,是不可能在俄羅斯大地上扎根的。這樣,真正獨立的俄羅斯哲學便只可能在既有深厚的東正教神學基礎(chǔ),又受到當時先進的科學教育和哲學教育、具有自由精神和創(chuàng)造意識的學者手上誕生。不論是弗洛羅夫斯基的《俄羅斯神學之路》、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思想》還是洛斯基的《俄國哲學史》,它們所肯定的俄羅斯哲學的創(chuàng)始人,都是這樣的人。正因為如此,他們在哲學上也就謀求既保留東正教神學的精髓,又從時代的高度改造東正教神學,創(chuàng)造出一種既高于現(xiàn)有的東正教神學又高于當時的西歐哲學的新的哲學。他們既不滿足于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也不滿足于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古典哲學,他們力圖將宗教與哲學融合起來,將信仰與理性融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一種“整體性”的哲學。在這點上,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的話極具代表性。他說,他們的哲學雖然以教父的著作為發(fā)源地,但它是“與科學的現(xiàn)代狀況相適應、與現(xiàn)性的要求和問題相一致”的學說。當其發(fā)展到高峰時將可消除“理性與信仰、內(nèi)心信念與外在生活之間的病態(tài)的矛盾”,“填補本應結(jié)合在一起的兩個世界被分裂之后所出現(xiàn)的真空,在人的頭腦里確立起精神真理,把它看成是對自然真理的統(tǒng)治,并用它與精神真理的正確關(guān)系把自然真理加以提升,最后把這兩種真理結(jié)合為一個活生生的思想。”(轉(zhuǎn)引自《俄國哲學史》中譯本,第16—17頁)這樣的思想后來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傳統(tǒng),獨立的俄羅斯哲學就沿著這樣的傳統(tǒng)發(fā)展起來。
三
既然俄羅斯哲學力圖既繼承又超越東正教神學和西歐哲學,它就不能不具有內(nèi)在的矛盾。這種矛盾首先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矛盾。從其發(fā)生和發(fā)展的過程來說,這與俄國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特殊文化背景有著緊密的關(guān)系。別爾嘉耶夫曾經(jīng)深刻地指出:“俄羅斯精神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可能與下列情況有關(guān),即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歷史之流在俄羅斯發(fā)生碰撞,俄羅斯處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羅斯民族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俄羅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東方—西方,它將兩個世界結(jié)合在一起。在俄羅斯精神中,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永遠在相互角力。”(《俄羅斯思想》,第2頁)就俄羅斯哲學來說,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是其發(fā)生發(fā)展的另一個特點。
俄國哲學既然從神學中生,它就必然帶有俄國東正教神學的特點。俄國東正教神學恰恰是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誕生和發(fā)展的。這里所說的東方文化主要是指希臘—拜占庭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是指羅馬—拉丁文化。眾所周知,在羅斯受洗之后,俄國主要接受的是希臘—拜占庭文化。當然,羅馬—拉丁文化也在不時地對俄羅斯進行滲透。俄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在其《俄國史教程》中說:“十世紀時從拜占庭傳來了基督教,隨同也來了神職人員,傳來了基督教的書籍、法律、祈禱儀式、圣像畫術(shù)、聲樂與傳教術(shù)。這些物質(zhì)與精神財富流到羅斯,流入基輔,其大動脈是第聶伯河”。那時的王公貴族并不是只吸收拜占庭文化,他們對羅馬文化也取歡迎態(tài)度。克氏說,他們“甚至在學校設(shè)置希臘語、拉丁語課程,尊重來自希臘與西歐的學者。”(《俄國史教程》第一卷,中譯本,第270頁)不過,由于基督教東西教派的關(guān)系異常緊張,所以拜占庭的神甫與羅馬的神甫并不能和平相處,東西方的教會更把爭奪俄羅斯當作重要戰(zhàn)略,這樣也就逐漸引發(fā)了俄國內(nèi)部不同派別之產(chǎn)生。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的西方派與東方派(即斯拉夫派)的大爭論,事實上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已經(jīng)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著。例如,“在約瑟夫派與禁欲派的著名爭論中,我們發(fā)現(xiàn)這實質(zhì)上是新東西和舊東西的沖突,是拉丁系文化和希臘文化的沖突。”(《俄羅斯神學之路》,第23頁)在約瑟夫主教的身上,有許多非拜占庭的文化因素。如他把沙皇也包括在“神的仆役”的系統(tǒng)之內(nèi),認為沙皇也要受法律約束,也只有在圣訓的范圍內(nèi)擁有自己的權(quán)力。甚至認為對于“非正義的”也即是與上帝不保持一致的沙皇根本不應當服從,因為這樣的沙皇根本不是沙皇,而是折磨者;不是神的仆人,而是魔鬼。這種說法有違于東正教的傳統(tǒng),倒是與羅馬天主教的主張相近。不僅如此,約瑟夫派還主張入世,關(guān)心現(xiàn)實的人類苦難,舉辦慈善事業(yè)等等。禁欲派則主張隱遁的、孤獨的苦行和精神的修行,克服俗世的偏心及戀世,他們更多地保持和繼承了拜占庭文化即東正教的傳統(tǒng)。再如,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合并教派與反合并教派的爭論,更是一場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較量。當時,俄羅斯西部教會有一股潮流,一些受羅馬文化影響較深的神職人員不斷揭露拜占庭文化的缺陷,公開主張與羅馬教會和解,甚至說“我們不能永遠生活在希臘人的保護之下”,羅馬教會那里有“真理的清泉”。這股力量聚集起來,形成合并教派。另一些神職人員則在“護教”的旗幟下聯(lián)合起來,形成反合并教派。他們認為,教會合并就意味著自動納入西方的傳統(tǒng),這正是宗教文化上的西方派。要戰(zhàn)勝合并教派,只能依靠對拜占庭的教父學傳統(tǒng)的信守和忠貞不渝。“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東正教的奮斗者就是這樣理解自己的任務的。”(《俄羅斯神學之路》,第48頁)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出現(xiàn)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大爭論,更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較量。面對舊俄的黑暗狀況,這兩派都在尋找俄國的出路,這也是他們爭論的焦點。斯拉夫派認為,俄國可以從農(nóng)村公社過渡到工業(yè)公社,從而走向現(xiàn)代化;西方派則認為,社會發(fā)展有其普遍的規(guī)律,俄國不可能超過資本主義階段,而只能按照西方發(fā)展的道路前進。在政治上“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熱的無原則的復古派,他們的主張實際上反映的是受到傷害的俄羅斯民族感情,是對彼得一世以來外國文化影響泛濫的一種反作用。------改革必須同人民的精神傳統(tǒng)和風俗習慣相符合,自上而下地進行。”他們“試圖走一條獨特的俄國式的發(fā)展之路。”(姚海:《俄羅斯文化之路》,浙江,1992,第32—133頁)所以,實質(zhì)上,他們與西方派一樣,并非沙皇政府的幫兇,而是具有自由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從這一點來說,正好證明了西方文化對俄國知識界的廣泛影響。獨立的俄羅斯哲學正是在這次大爭論中誕生的。當時,俄國知識界已經(jīng)受到十八世紀法國啟蒙主義和唯物主義哲學的很大影響,接著德國古典哲學又以更強勁的力量傳入,它使俄羅斯知識分子一下子吸收到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哲學。但是,這些哲學與俄羅斯的神學傳統(tǒng)之間產(chǎn)生了一定的沖突,由這種沖突引發(fā)了西方派與斯拉夫派之間在哲學上的分歧。一般地說,西方派比較輕視宗教和神學,而頗為重視西歐的哲學,認為它才是先進的思想,盡管他們在哲學上并非始終如一地認同某種哲學,像別林斯基甚至在不同的哲學觀點之間變來變?nèi)ィ珜ξ鳉W哲學的推崇卻是一貫的和一致的。赫爾岑說過,俄國所有的一切只是基石,“但基石畢竟是基石,------沒有西方的思想,我們本來的大廈將始終只是一片地基而已。”(《往事與隨想》中冊,中譯本,第1**頁)他們把西歐哲學直接服務于反對專制制度的政治斗爭,正像赫爾岑所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shù)學。不過,就學理而言,西方派并沒有什么創(chuàng)造,他們并沒有創(chuàng)立一種獨立的俄羅斯哲學。相反,斯拉夫派固然有一定的保守傾向,但他們卻由于尊重俄羅斯的傳統(tǒng),因而能夠在吸收西方哲學成就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新的哲學。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保守傾向,并非是在保護舊制度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在與西方派的激進傾向比較的意義上說的。就實質(zhì)而言,斯拉夫派也是改革派。后來,赫爾岑在紀念斯拉夫派的重要代表阿克薩科夫的文章中說道:“是的,我們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與眾不同。我們有同樣的愛,只是方式不一樣------我們像伊阿諾斯(注:古羅馬神話中的門神,有前后兩個面孔)或雙頭鷹,朝著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臟卻是一個。”(《警鐘》,第90期)別爾嘉耶夫非常有趣但又非常中肯地談到兩派的異同:“兩派都熱愛自由,兩派都熱愛俄羅斯,但是斯拉夫主義者把她當作母親,西方主義者則把她當作孩子。”(《俄羅斯思想》,第38頁)斯拉夫派的哲學家并非傳統(tǒng)體制內(nèi)的、為政府和教會服務的人,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由世俗學校畢業(yè)的,是自由思想家。盡管他們創(chuàng)立的俄羅斯哲學是宗教哲學,但他們對教會與對國家的態(tài)度是一樣的,認為都要進行認真的改革,因而他們的哲學并不被政府和教會所認可,反而遭到官方的迫害。他們運用西歐的進步哲學來審視傳統(tǒng)的俄羅斯神學,力求在綜合二者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一種新的獨特的俄國哲學。因此,他們認為西方派那種輕視俄國傳統(tǒng)的態(tài)度是不可取的。事實證明,單純地吸取外國文化是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獨特的本民族文化的,因為失去了本民族的基石。這正是西方派沒能創(chuàng)造出獨立的俄羅斯哲學的緣由。一般地說,在政治上比較激進的派別,容易對傳統(tǒng)的東西采取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反對繼承傳統(tǒng)的東西。這樣的態(tài)度雖然容易接受外來的先進文化,但卻使自己失去了民族的根基。
獨立的俄羅斯哲學發(fā)展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便被人為地從俄羅斯大地驅(qū)逐出去。1922年5月,列寧致函捷爾仁斯基,批示經(jīng)過周密研究,采取新的措施,把“為反革命幫忙的作家和教授驅(qū)逐出境”(《列寧文稿》第10卷,中譯本,1988,第224頁)。8月,《真理報》刊登題為《第一次警告》的重要文章,指出知識分子中的某些階層不愿歸順蘇維埃政權(quán),斷定在高等學校、出版界、哲學界、文藝界、醫(yī)務界、農(nóng)業(yè)界------甚至合作社中,存在著反蘇維埃活動的“據(jù)點”。同時宣布:“根據(jù)國家政治保安局的決定”,知識分子中那些“積極反對革命”的人,“思想上的弗蘭格爾分子和高爾察克分子”,或者將從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驅(qū)逐到北部省份,或者將被驅(qū)逐出境。該文聲稱采取驅(qū)逐手段是“蘇維埃政權(quán)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警告。”接著,蘇維埃政權(quán)擬定了驅(qū)逐160名“最積極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的名單。1922年9月,俄羅斯的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弗蘭克、洛斯基、弗洛連斯基與莫斯科大學校長、動物學家諾維科夫;彼得堡大學校長、哲學家卡爾薩文;莫斯科大學數(shù)學系主任斯特拉托諾夫,經(jīng)濟學家布魯茨庫斯、茲沃雷津;歷史學家卓韋捷爾;社會學家索羅金等一起被永遠逐出國門。在蘇俄本土,接下來的是列寧主義的絕對統(tǒng)治。獨立的俄羅斯哲學只能成為一種“流亡哲學”,而在國外延續(xù)。這也可算是俄羅斯哲學發(fā)生發(fā)展的另一個特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