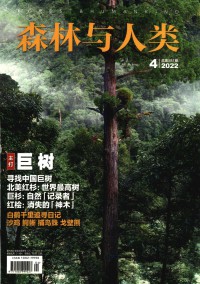人類本質(zhì)藝術(shù)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人類本質(zhì)藝術(shù)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人和人的解放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問題,也是現(xiàn)代美學(xué)的中心問題。
審美能力是人的一種本質(zhì)能力。審美的需要是人的一種基本的需要。所以美的本質(zhì),基于人的本質(zhì)。美的哲學(xué),是人的哲學(xué)中一個(gè)關(guān)鍵性的有機(jī)組成部分。研究美則不研究人,或者研究人而不研究美,在這兩個(gè)方面都很難深入。
由于極“左”路線的干擾,“人”這一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問題,長(zhǎng)期以來是一個(gè)重門深鎖的禁區(qū),以致于現(xiàn)在要研究這個(gè)問題,不得不從頭開始。本文的寫作,是為尋找出發(fā)點(diǎn)面蜍的一個(gè)初步的努力,只談了一個(gè)人的本質(zhì)問題,即便如此也還是感到題目太大。“茫茫大海與無齊,無限行程望欲迷”。不知一葉蓬舟,能得幾許?
一
我們關(guān)于“本質(zhì)”的理論,是一種方法論,而不是本體論。它是我們把一事物與一切其他事物及其有機(jī)整體區(qū)分開來加以研究的方法。宇宙本體是一個(gè)有機(jī)的和生態(tài)的過程,一股生生不息的永恒之流,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方法,則所有的事物在其終極的意義上將合而為一,而在現(xiàn)象上的多樣性將不可理解。
分開來看,一事物、一過程與其他事物、其他過程是有區(qū)別的,但不是獨(dú)立的。
所謂“本質(zhì)”,是指一件事物或一個(gè)過程在生生不息的宇宙萬物及其有機(jī)整體中有別于其他事物、其他過程的內(nèi)在基本特征。所以要確定一中物一過程的本質(zhì),只有把它放在與他事物、他過程的整體關(guān)系中來考察,才有可能。例如生物的本質(zhì)是相對(duì)于無生物而言的,它必須以無生物為對(duì)象,與無生物作比較,才能確定。人的本質(zhì)是相對(duì)于自然界的其他動(dòng)物而言的,它必須以動(dòng)物為對(duì)象,與動(dòng)物作比較,才能確定。
所以關(guān)于本質(zhì)的規(guī)定性,不僅來自人類具體地考察各別事物的需要,也來自人類整體地認(rèn)識(shí)世界的需要。孤立的、單獨(dú)的事物是沒有本質(zhì)的。孤立的、單獨(dú)的個(gè)人也是沒有本質(zhì)的。用馬克思的話說,這就叫“無對(duì)象的本質(zhì)是非本質(zhì)”。在馬克思看來,人怎樣超越出動(dòng)物界,人就怎樣進(jìn)入歷史,而形成自己的本質(zhì)。
所以馬克思著作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人的本性”、“人的本質(zhì)”這種提法,同現(xiàn)在在我國(guó)學(xué)術(shù)討論中所通用的“共同人性”這一提法,有重大區(qū)別。我們所謂的“共同人性”,是同人的“階級(jí)性”相對(duì)而言的。后者是指在一定歷史階段上和一定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中處于一定地位的人的屬性;而前者則是指這種“階級(jí)地”不同的人們之間相同和共有的東西,即人的自然本性。而無論是后者,還是前者,都不能把人和動(dòng)物區(qū)別開來。后者是指人和差異而不是指人和動(dòng)物的差異。在歷史和社會(huì)之中,人和人的這種相同之處,只能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如食欲、性欲之類生物學(xué)上的本能,而這些本能,是動(dòng)物也有的。
這兩種說法,表面上有所不同,實(shí)際上殊路同歸。說人的思想行為是由他的階級(jí)利益所決定,實(shí)際上也就是說追求利益的本能是一切人共同的本能,也是人性論。二者的差異僅僅在于,一是指具體的人性,一是指抽象的人性;一是指人性在不同社會(huì)必然性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不同異化形態(tài),一是搦產(chǎn)生這一切社會(huì)必然性及其異化形態(tài)的同一個(gè)自然必然性。歸根結(jié)底,二者并不矛盾。人類之劃分為不同階級(jí),不過是歷史發(fā)展的長(zhǎng)河中短暫的一瞬。在么衣制出現(xiàn)以前漫長(zhǎng)的原始社會(huì),和消滅了私有財(cái)產(chǎn)以后的漫長(zhǎng)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都是沒有階級(jí)的人類社會(huì),那時(shí)沒有階級(jí)性,不等于沒有人性。二者是一個(gè)東西的兩種表現(xiàn)。
所以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不是人的本質(zhì)。把階級(jí)性當(dāng)作人的本質(zhì)是對(duì)于社會(huì)必然性的盲目。把共同人性當(dāng)作人的本質(zhì)是對(duì)于自然必然性的盲目。而歸根結(jié)底。所謂“社會(huì)必然性”,例如經(jīng)濟(jì)必然性,不過是社會(huì)中的自然而已。盲目(無意識(shí)、不自覺)是動(dòng)物的特點(diǎn)。這兩種對(duì)于必然性的盲目,具有同一種動(dòng)物的性質(zhì)。正如在原始自然中人和動(dòng)物是一樣的,在社會(huì)的自然中,人也具有自己的動(dòng)物性。例如在等級(jí)森嚴(yán)的中世紀(jì)封建社會(huì),“君君臣臣”被看作和“父父子子”一樣的自然現(xiàn)象,人類社會(huì)就象自然界生出狼和羊,或者蜂王、雄蜂和工蜂那樣直接生出王公、貴州和奴隸。這種情況,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史上的動(dòng)物時(shí)期,是人類動(dòng)物學(xué)”。
當(dāng)然,“人類動(dòng)物學(xué)”不完全等于動(dòng)物的動(dòng)物學(xué)。它經(jīng)過了人類異化勞動(dòng)的一系列中介,如法律、政治經(jīng)濟(jì)制度等中介環(huán)節(jié),打亂了原來的自然秩序,呈現(xiàn)出一種錯(cuò)雜的狀態(tài)。例如,馬克思指出,在自然界是工蜂殺死雄蜂,而在人類社會(huì),則是雄蜂殺死工蜂,即不勞而獲者殺死勞動(dòng)者——用工作把他們折磨死。這種情況不同于自然界,但同樣“使人脫離自己的普遍本質(zhì),把人變成直接本身的規(guī)定性所擺布的動(dòng)物”。
把人性或人性的某種異化形態(tài)(階級(jí)性)當(dāng)作人的本質(zhì),無異于把動(dòng)物學(xué)當(dāng)作人學(xué)。在這個(gè)領(lǐng)域內(nèi)尋找人的本質(zhì),那就——借用一個(gè)現(xiàn)成的比喻來說——象易卜生筆下的人物培爾·金特在剝洋蔥皮;他剝了又剝,除了皮還是皮,終于沒有得到“洋蔥本身”。對(duì)人人瓣語言和行為,用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或者心理分析學(xué)的術(shù)語作出解釋是容易的。例如,數(shù)學(xué)家們?cè)缫言谧C明,心靈不過是無數(shù)復(fù)雜反應(yīng)的總和,它接受信息并進(jìn)行處理,以維持機(jī)體的穩(wěn)態(tài);而對(duì)于生物學(xué)家,人腦也象其他生理器官一樣,不過是生物體為了維持生存,在進(jìn)貨過程中形成一種特殊工具而我們的理論工作者則根據(jù)“存在決定意識(shí)”的原理,把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即他們的階級(jí)利益作為人的一切思想和行為的動(dòng)力。假如社會(huì)科學(xué)家們得出結(jié)論說人的心靈,包括思想、感情和意志都可以在這些特性的基礎(chǔ)上,通過一定程序的聯(lián)合國(guó)吧操縱,那我們是沒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奇怪的。但是這樣一來,人就變成機(jī)器,或者不寄托了動(dòng)物了。而這也就是說,當(dāng)洋蔥皮剝完時(shí),“洋蔥本身”也沒有了。這種結(jié)果一定會(huì)使得拉·美特利在九泉之下高興得眉開眼笑的。
受客觀必然性——無論是生理必然性還是經(jīng)濟(jì)必然性——的支配是動(dòng)物的屬性。人對(duì)于必然性的盲目是它的動(dòng)物性的表現(xiàn),是朦昧遠(yuǎn)古自然狀態(tài)在社會(huì)和歷史中的遺物。這種情況把人和大自然結(jié)為一體,而使他消失在太古時(shí)期的背景之中。“人的本質(zhì)”。所以“人的本質(zhì)”是和人對(duì)于必然性的認(rèn)識(shí)、把握和駕馭分不開的。人類史表明,人類離動(dòng)物界愈遠(yuǎn),他的活動(dòng)就愈帶有自覺的和有意識(shí)的、因而是主動(dòng)能動(dòng)的特征。“他的政黨狀態(tài)是和他的意識(shí)相適應(yīng)而由他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本能的人,即野蠻人沒有把自然界區(qū)分開來。自覺的人則區(qū)分開來了”。
“共同人性”是變化的,人在改變世界的同時(shí),也改變著自己的本性。這種自我改變,即自我創(chuàng)造的本質(zhì)是人的本質(zhì),這個(gè)本質(zhì)則是不變的。所以共同人性不等于人的本質(zhì)。對(duì)于“共同人性”的論證,不能代替對(duì)于“人的本質(zhì)”的論證。至多,共同人性只能算是人的本質(zhì)的自然基礎(chǔ),即人的本質(zhì)的第一個(gè)層次。
二
意識(shí)是勞動(dòng)和社會(huì)的產(chǎn)物。勞動(dòng)和社會(huì)性是人的本質(zhì)的第二個(gè)層次。
我們通常把勞動(dòng)理解為“干活”,理解為狹隘的物質(zhì)生產(chǎn),理解為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手段。這種理解是不正確的。按照這種理解,勞動(dòng)不是人的本質(zhì)。因?yàn)閯?dòng)物也能這樣“勞動(dòng)”(例如野獸覓食,蜘蛛結(jié)網(wǎng),螞蟻、蜜蜂、海貍構(gòu)筑巢穴)。并且正是這樣的勞動(dòng),把人異化為“非人”,異化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隸。天天這樣為維持一已怕生存而不斷“干活”的人們,事實(shí)上已經(jīng)和動(dòng)物沒有區(qū)別了。這是對(duì)“人”的否定而不是對(duì)“人”的肯定。馬克思指出:“對(duì)于這種狀態(tài)來說,人類勞動(dòng)尚未擺脫最初的本能的形式的狀態(tài)已經(jīng)是太古時(shí)代的事了。”
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勞動(dòng)”這一概念具有深廣的實(shí)踐意義,不同于通常所謂的“干活”等等。他寫道:“我們要考察的是專屬于人的勞動(dòng)。蜘蛛的活動(dòng)與織工的活動(dòng)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lǐng)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jīng)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dòng)過程結(jié)束時(shí)得到的結(jié)果,在這個(gè)過程開始時(shí)就已經(jīng)在勞動(dòng)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jīng)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fā)生形式變化,同時(shí)他還自然物中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目的。”
很明顯,在馬克思那里,勞動(dòng)只有作為人類目的樹立和目的實(shí)現(xiàn)之間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即有意識(shí)的創(chuàng)造性的實(shí)踐活動(dòng),才是“人的”勞動(dòng)。只有在這樣的勞動(dòng)中,才存在著人的一整個(gè)族類生活的共同特征。這種勞動(dòng)不僅創(chuàng)造手段,而且創(chuàng)造目的;不僅滿足需要,而且創(chuàng)造需要,這種創(chuàng)造常常表現(xiàn)為手段對(duì)于目的的超越。它代復(fù)一代地進(jìn)行,形成文化,形成復(fù)雜的精神文明。這樣一來,各個(gè)具體人的感性的、現(xiàn)實(shí)的存在,不僅是生物學(xué)和社會(huì)學(xué)上的存在,而且是這種精神文明的存在,是這種精神文明的現(xiàn)實(shí)的生成。
這個(gè)生成過程,不僅表現(xiàn)為勞動(dòng)轉(zhuǎn)化為創(chuàng)造,性欲轉(zhuǎn)化為愛情,感覺轉(zhuǎn)化為審美,本能轉(zhuǎn)化為道德,而且表現(xiàn)為感性材料轉(zhuǎn)化為語言文字符號(hào),以及符號(hào)的符號(hào)——信息系統(tǒng)。從而形成了一個(gè)復(fù)雜的、能動(dòng)的、反思的精神結(jié)構(gòu)——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馬克思所說的那個(gè)“觀念地存在著”的蜂房,正是觀念地存在于這個(gè)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之中。這個(gè)蜂房的由觀念的精神的東西轉(zhuǎn)化為客觀的物質(zhì)實(shí)體,只有通過“勞動(dòng)”這一中間五一節(jié)才能夠?qū)崿F(xiàn)。所以勞動(dòng),是作為主體的人的有意識(shí)的、自由自覺的、主動(dòng)能動(dòng)的實(shí)踐活動(dòng),這種活動(dòng)不僅創(chuàng)造了世界,也創(chuàng)造了人。換句話說,世界歷史和在其中不斷遞變的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不過是這個(gè)實(shí)踐活動(dòng)及其后果的總和而己。
這樣一種持久的、廣泛的、世界歷史性的活動(dòng),當(dāng)然不是任何個(gè)人能夠完成的。“孤立的一個(gè)人在社會(huì)之外進(jìn)行生產(chǎn)……就象許多個(gè)人不生活在一起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fā)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為了進(jìn)行生產(chǎn),人類必然結(jié)成一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含義是指許多人的合作,至于本質(zhì)并不是單個(gè)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馬克思的這一思想,是和他的勞動(dòng)創(chuàng)造人的思想有機(jī)地密切聯(lián)系著的。
條件、方式、目的等等及其組合,是一些能動(dòng)的因素。所以歷史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發(fā)展途徑,我們不能把人類的歷史看作單一的歷史,看作由一個(gè)點(diǎn)出發(fā)向著另一個(gè)點(diǎn)前進(jìn)的歷史,因此也很難說什么方式和目的的是歷史的方式和目的。不過,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這一基本規(guī)律,則是歷史進(jìn)步的普遍形式。這種形式恰恰是人類主動(dòng)性、能動(dòng)性的現(xiàn)實(shí)的表現(xiàn)。所以馬克思又說,“每個(gè)個(gè)人和每一代當(dāng)作現(xiàn)成的東西承受下來的生產(chǎn)力、資金和社會(huì)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xué)家們想象為‘實(shí)體’和‘人的本質(zhì)’的東西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這就直接把勞動(dòng)包括在這個(gè)總和之中了。
基礎(chǔ)不等于上層建筑,人的本質(zhì)的基礎(chǔ)不等于人的本質(zhì)。這是因?yàn)樗摹翱偤汀辈⒉皇歉鱾€(gè)部分相加之和,而是指一種包括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在內(nèi)的主動(dòng)能動(dòng)的整體結(jié)構(gòu),即人的主體性。它是一個(gè)乘積,遠(yuǎn)遠(yuǎn)大于各個(gè)部分相加之和。正因?yàn)槿绱耍詣趧?dòng)和社會(huì)性還不直接等于人的本質(zhì),而只是人的本質(zhì)的第二個(gè)層次。以往的哲學(xué)給人的本質(zhì)所下的定義,在最深刻的情況下也只是達(dá)到這個(gè)層次。而只要達(dá)到了這個(gè)層次,一種定義也就能標(biāo)導(dǎo)出一種社會(huì)的特征。例如亞里斯多德說人是政治動(dòng)物,這標(biāo)志出歐羅巴的古代的特征;孔子以有仁、義、禮、智為人,這標(biāo)志著亞細(xì)亞的古代的特征;弗蘭克林把人看作“制造生產(chǎn)工具的動(dòng)物”,這標(biāo)志著當(dāng)時(shí)美國(guó)社會(huì)的特征。
但是人并不是抽象地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正如我們不能在離群索居的、孤獨(dú)的個(gè)人身上尋找人的本質(zhì),我們也不能在一種從個(gè)人抽象出來,只得個(gè)人相對(duì)立的所謂“社會(huì)”中去尋找人的本質(zhì)。人的本質(zhì)只能在這種個(gè)體和整體的統(tǒng)一之中。
三
所以人的本質(zhì)的第三個(gè)層次是人的世界。即個(gè)體和整體的統(tǒng)一。“人并不是抽象地棲息在世界以外的東西。人就是人的世界”,馬克思的這一思想,是同他的“人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的看法相一致的。人的世界并不是歷史運(yùn)動(dòng)的力場(chǎng),不是在人之外的盛裝人類的容器,它本身就是人的表現(xiàn),人的活動(dòng)及其后果的總和,亦即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一個(gè)對(duì)象。
動(dòng)物的肉體需要是動(dòng)物行為的動(dòng)力。動(dòng)物至多只能利用自然環(huán)境。它適應(yīng)環(huán)境變化的手段則依靠進(jìn)化,依靠進(jìn)化來修補(bǔ)它們的生理器官,改進(jìn)它們的肉體本能。它們沒有自我意識(shí),不能把自己作為對(duì)象。所以世界對(duì)于它們也不是對(duì)象。它們是自然本身的一個(gè)自在的部分,沒有從自然背景中脫離出來。人和動(dòng)物不同,他在自然材料面前是一個(gè)對(duì)立的力量,是一個(gè)把自然作為客體加以改造的主體。他運(yùn)轉(zhuǎn)他肉體方面的自然力,手臂和腿,頭和手,來把自然材料加工改造,轉(zhuǎn)化成一種對(duì)他有用的形式。于是自然物作為他的工具,變成了他的活動(dòng)器官——“生產(chǎn)的骨胳與肌肉系統(tǒng)”。他用這個(gè)人工的活動(dòng)器官,不僅延長(zhǎng)了自己的四肢,而且擴(kuò)大了自己的大腦(人工智能,“思考”信息咨詢中心系統(tǒng)等)。于是人在加工發(fā)行自然的同時(shí),不僅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與他自己相適應(yīng)的世界,而且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與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相適應(yīng)的新的自我,即包函著繼承和揚(yáng)棄了全部歷史成果的、作為創(chuàng)造者的自我。
于是主體性這一概念,也就獲得了自由的含意。所謂“工業(yè)的歷史和工業(yè)的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對(duì)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找開了的書本,是感性地?cái)[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xué)”。其所以是心理學(xué),就因?yàn)樗鳛槿说膭?chuàng)造物,和人類進(jìn)行創(chuàng)造的人工器官,是人的主體性即人的自由的現(xiàn)實(shí)的證明。工業(yè)如此,人的一切其他創(chuàng)造物、宗教、藝術(shù)、法律、政治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等等及其總和,莫不如此。人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感情和他和理性,在這個(gè)他所創(chuàng)造的、外在于他的世界中都有與之相對(duì)應(yīng)的東西。他和這個(gè)世界都是同一歷史過程的產(chǎn)物。他作為主體擁有這個(gè)世界,并參加在這個(gè)世界之中,被這個(gè)世界所創(chuàng)造,也創(chuàng)造這個(gè)世界。正因?yàn)槿绱耍軌蛟谶@個(gè)世界中“直觀自身”。
在創(chuàng)造世界的勞動(dòng)實(shí)踐中,人類作為主體通過掌握必然性而獲得自由,他所創(chuàng)造的對(duì)象世界,包括勞動(dòng)勞動(dòng)工具(或者說人工器官)的存在和發(fā)展,也就標(biāo)志著他的自由和存在和發(fā)展。從石矛、石斧到用牛犁地、用馬拉車,從拖拉機(jī)、火車頭到航天工業(yè)和巨型符號(hào)控制器,這一勞動(dòng)工具即人工器官的發(fā)展史,形象地反映出人的自由的發(fā)展史。因?yàn)樯a(chǎn)力的程度,不僅標(biāo)志著人類征服自然的程度,即人類從自然辦獲得解放的程度,而且標(biāo)志著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程度,即人類從落后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獲得解放的程度。當(dāng)然這二者并不是平衡的(例如工業(yè)發(fā)達(dá)的國(guó)家未必是政治進(jìn)步的國(guó)家),甚至常常是有矛盾的,但它們總是在矛盾斗爭(zhēng)中發(fā)展的。并且總是這種矛盾斗爭(zhēng)推動(dòng)歷史發(fā)展。在這全過程中,勞動(dòng)工具作為生產(chǎn)力的基因,它的狀況是時(shí)代的象征,也是照耀歷史前進(jìn)的火炬。
“實(shí)際創(chuàng)造一個(gè)對(duì)象世界,改造無機(jī)的自然界,這是人作為有意識(shí)的類的存在物(亦即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當(dāng)作自己的本質(zhì)來對(duì)待,或者說把自己本身當(dāng)作類的存在物來對(duì)待)的自我確證”。“因此,正是通過對(duì)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實(shí)際上確證自己是類的存在物。這種生產(chǎn)是他的能動(dòng)的、類的生產(chǎn)。通過這種生產(chǎn),自然界才表現(xiàn)為他的創(chuàng)造物和他的現(xiàn)實(shí)性。因此勞動(dòng)的對(duì)象是人的類的生活的對(duì)象化:人不僅象意識(shí)中所發(fā)生的那樣在精神上把自己公分為二,而且在實(shí)踐中,在現(xiàn)實(shí)中把自己化分為二,并且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
這里所說的“化分為二”,可以理解為人把自己化分為主體和客體。客體是主體的客體,即對(duì)象是主體的對(duì)象(對(duì)象如果沒有主體,就會(huì)失去對(duì)象性而不成其為對(duì)象)。這種分化是人確立自己的本質(zhì)——主體性的、自由的證明。主體感到?jīng)]有外在于自身的他物,世界之對(duì)于人成為客體和對(duì)象,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的現(xiàn)實(shí)的證明。
誠(chéng)然,馬克思也說過,不僅主體可以為自己創(chuàng)造客體,客體也可以為自己創(chuàng)造主體。一種被客體所創(chuàng)造的主體可能是自由的嗎?但是,所謂客體創(chuàng)造主體,實(shí)際上也就是歷史創(chuàng)造個(gè)人(正如同主體創(chuàng)造客體是個(gè)人參與創(chuàng)造歷史);是邏輯、認(rèn)識(shí)結(jié)構(gòu)轉(zhuǎn)化為感生存在,亦即歷史的東西轉(zhuǎn)化為個(gè)人的東西。一句話,所謂客體創(chuàng)造主體,是客體轉(zhuǎn)體為主體,被主體所“吸收”。這種“吸收”是主體創(chuàng)造客體的“再生產(chǎn)”的過程的一個(gè)部分。在這個(gè)過程中,精神的東西通過勞動(dòng)實(shí)踐轉(zhuǎn)化為物質(zhì)的東西,轉(zhuǎn)化為客觀世界。而這個(gè)客觀世界作為歷史的既成事實(shí),又影響和鑄造著當(dāng)時(shí)和后來的無數(shù)的個(gè)人。所以達(dá)個(gè)過程中物質(zhì)的東西不僅是物質(zhì)的東西,而且是精神的東西,是“客觀地揭開了的人的心理學(xué)”。這一點(diǎn)不僅適用于工業(yè)的歷史,而且適用于美與藝術(shù)。美之所以能影響欣賞者的思想感情(即客體創(chuàng)造主體),是因?yàn)樗旧硎且粋€(gè)歷史的產(chǎn)物,一個(gè)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的產(chǎn)物,一個(gè)人的主體性的表現(xiàn)。
“人的世界”是一個(gè)復(fù)雜的主體性結(jié)構(gòu),一個(gè)能動(dòng)地結(jié)晶了、物化了的主體性結(jié)構(gòu)。正因?yàn)槿绱耍陀^的自然界對(duì)于人才成了屬人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實(shí)際上也就是人的物化。也只有作為人的物化,世界對(duì)于人才成為對(duì)象,人對(duì)于世界才成為主體。才有可能“人就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的豐富性,包括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的豐富性,才有可能如此感性而又如此生動(dòng)地呈現(xiàn)出人的本質(zhì)的豐富性。
四
把人的勞動(dòng)、人的社會(huì)性、人和人的世界的統(tǒng)一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可以得出一個(gè)明確的結(jié)論:人的本質(zhì)是自由。馬克思指出:“生命活動(dòng)的性質(zhì)包含著一個(gè)物種的全部特性,它的類的特性,而自由自覺的活動(dòng)恰恰尺是人的類的特性”。“人是類的存在物。這不僅是說,人無論在實(shí)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把類——既把自己本身的類,也把其他物的類——當(dāng)作自己的對(duì)象;而且是說(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己本身當(dāng)作現(xiàn)有的、活生生的類來對(duì)待,當(dāng)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duì)待。”
“自由”一詞,在這里可以直接理解為人類活動(dòng)的萬能性。馬克思有時(shí)也用“萬能”這一提法來代替“自由”的提法。例如《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寫道:“人較之動(dòng)物越是萬能,那么,人賴以生活的那個(gè)無機(jī)自然界的范圍也就越廣闊。”這是因?yàn)槿恕岸冒凑杖魏挝锓N的尺度來進(jìn)行生產(chǎn),并且隨時(shí)隨地都能用內(nèi)在固有的尺度來衡量對(duì)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規(guī)律來塑造物體。”人之所以懂得并實(shí)現(xiàn)這一切,是由于他們?cè)诟脑焓澜绲拈L(zhǎng)期實(shí)踐過程中認(rèn)識(shí)了客觀必然性,駕馭了客觀規(guī)律的緣故。只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diǎn),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
人類對(duì)必然性的認(rèn)識(shí)是他們從必然性的制約下自為地獲得解放的前提。認(rèn)識(shí)是主觀的東西,它通過勞動(dòng)實(shí)踐轉(zhuǎn)化為客觀的東西。于是意識(shí)獲得了物質(zhì)的實(shí)體。客觀的事物成為人的一個(gè)表現(xiàn)。這個(gè)表現(xiàn)的“總和”創(chuàng)造人,也就是所謂客體創(chuàng)造主體,即歷史創(chuàng)造個(gè)人。于是人對(duì)世界的實(shí)踐的改造,也就成為人類對(duì)于自己的意識(shí)的一個(gè)超越,即他的自我超越。手段對(duì)于目的的超越,表現(xiàn)為實(shí)踐對(duì)于意識(shí)的超越。這樣的一個(gè)超越過程,也就是人在創(chuàng)造世界的同時(shí)創(chuàng)造自己的過程。于是人類對(duì)必然性和客觀規(guī)律的認(rèn)識(shí),由于改造世界的實(shí)踐而變成了意識(shí)的自由。意識(shí)的自由的生成,是一個(gè)歷史過程。而這個(gè)過程同時(shí)也是歷史、即人的生成。
自由作為人的本質(zhì),并不是必然性的對(duì)立物,而是一種被認(rèn)識(shí)和超越了必然性。在這里必然性不是它自身,而是自由的媒介,是自由過程中一個(gè)被揚(yáng)棄的環(huán)節(jié)。在這里自由和必然的關(guān)系是同自在和自為的關(guān)系相對(duì)應(yīng)的:人作為自為的實(shí)體才成了自由的實(shí)體,而這個(gè)過程的開始,也就是人類歷史的起點(diǎn)。
自由是人類歷史的起點(diǎn)。人曾經(jīng)是動(dòng)物,與大自然結(jié)為一體,是大自然的一個(gè)自在部分。人之所以成為人,是從他不是把自己當(dāng)作自然的部分,而是把自然當(dāng)作自己的對(duì)象進(jìn)行加工改造的時(shí)候開始的。換句話說,人之所以成為人,是從他超越了環(huán)境的束縛,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束縛,把自己當(dāng)作自由的主體加以解放的時(shí)候開始的。當(dāng)人不是盲目地受環(huán)境和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是作為能駕馭自然性以改造環(huán)境的主體而出現(xiàn)的時(shí)候,人才成其為人,人的歷史才成為自然界生成為人這一過程的現(xiàn)實(shí)的部分。
以勞動(dòng)工具的發(fā)展為標(biāo)志的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本質(zhì)上是人類自由的發(fā)展。所以生產(chǎn)力是人的一種本質(zhì)能力。在這個(gè)基礎(chǔ)上形成的經(jīng)濟(jì)、政治等人與人的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以及與之相應(yīng)的人的精神結(jié)構(gòu)即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隨著這種發(fā)展而不斷地改組,就形成歷史的變遷。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種種宗教、藝術(shù)、哲學(xué)和政治經(jīng)濟(jì)制度等等都無非是作為腐朽的人類在實(shí)現(xiàn)他的自我,即爭(zhēng)取自由、進(jìn)步的道路上留下的足印罷了。這些足印是凌亂的、尺疑的、非線性的、迂回曲折的,但始終是向著自由前進(jìn)的。
歷史是滄海桑田,并沒有現(xiàn)成的道路。歷史之路完全是人類自己走出來的。從這條漫長(zhǎng)而又崎嶇的道路上,我們可以得到的啟示是無窮的。從原始社會(huì)、奴隸社會(huì)、封建社會(huì)到資本主義社會(huì),再到將來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的必然發(fā)展,重疊、交叉而又曲折地呈現(xiàn)出一種人類不徹底解放的實(shí)現(xiàn),也就是這個(gè)過程的必然歸宿。從歸宿的意義上來說,自由的實(shí)現(xiàn)也就是人類現(xiàn)有的歷史,即階級(jí)社會(huì)的歷史的終點(diǎn)。歷史是人的歷史,所以自由作為人的本質(zhì),即是它的起點(diǎn)也是它的終點(diǎn)。
當(dāng)然,所謂“終點(diǎn)”,是相對(duì)于迄今為止的全部人類歷史而言的。由于人的徹底解放提供了世界發(fā)展的無限豐富的可能性,那種寫在歷史最后一頁上的永恒的社會(huì)形態(tài)是永遠(yuǎn)不會(huì)出現(xiàn)的。所以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gè)所謂的“終點(diǎn)”,實(shí)際上是真正的人的歷史的真正起點(diǎn)。馬克思把迄今為止的,存在著分工、私有制和階級(jí),以及政黨、軍隊(duì)和國(guó)家等等階級(jí)斗爭(zhēng)工具的全部歷史,稱之為人類史的“史前史”。他指出,史前史的結(jié)束,才是真正的人的歷史的開始,因?yàn)椤爸皇菑倪@時(shí)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shí)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huì)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長(zhǎng)的程度上達(dá)到他們所預(yù)期的結(jié)果。這是人類從必然的王國(guó)進(jìn)入自由王國(guó)的飛躍”。馬克思又指出,那時(shí)候,“代替那存在著各種階級(jí)以及階級(jí)對(duì)立的資產(chǎn)階級(jí)舊社會(huì)的,將是一個(gè)以各個(gè)人自由發(fā)展為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的聯(lián)合體。”所以那時(shí)候,所謂人類社會(huì)就會(huì)成為一個(gè)“自由人的公社”。
馬克思對(duì)于人類過去和將來歷史的這各確切而又具體的描述,正是建立在他對(duì)于人的本質(zhì)的深刻理解之上的。歷史是人的歷史,沒有對(duì)于人的本質(zhì)的深刻理解,要作出這樣確切的描述是不可能的。
五
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是自由的思想,在哲學(xué)史的不同時(shí)期,都曾經(jīng)被探索過。如果說,佛教哲學(xué)中關(guān)于“解脫”的思想和中國(guó)道家關(guān)于“逍遙”的思想還沒有直接明確地同人的本質(zhì)聯(lián)系起來的話(其實(shí)已經(jīng)有某種間接模縛的聯(lián)系了),那么古希臘人關(guān)于人是微觀宇宙和人是萬物尺度的觀點(diǎn),則無疑是一種人的哲學(xué),包含著對(duì)人的本質(zhì)的初步認(rèn)識(shí)。在中世紀(jì),奧古斯丁關(guān)于“從現(xiàn)實(shí)的我出發(fā)而轉(zhuǎn)到真實(shí)的你”的思想,在神學(xué)的外衣下仍然透露出某種對(duì)于人的本質(zhì)的哲學(xué)認(rèn)識(shí)。后來新教思想家路德和加爾文關(guān)于信徒對(duì)自己的信念個(gè)人自己負(fù)責(zé)的思想,則不僅在理論上涉及到人的自由問題,而且賦予這種認(rèn)識(shí)以某種實(shí)踐意義了(當(dāng)然是在宗教的錯(cuò)誤前提之下的)。
笛卡兒把自由意志同純理性的必然性加以區(qū)分,斯賓諾莎則強(qiáng)調(diào)二者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強(qiáng)調(diào)理性與意志的統(tǒng)一。二人貌似不同,但在肯定人是認(rèn)識(shí)的主體,自由是認(rèn)識(shí)了的必然性這一點(diǎn)上則都是一致的。這種一致看法中包含著他們不自覺地作出的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的結(jié)論:人是有理性的動(dòng)物,而理性是在認(rèn)識(shí)客觀必然性的基礎(chǔ)上自由而積極的活動(dòng)。這一結(jié)論為十八世紀(jì)啟蒙學(xué)者的思想提供了營(yíng)養(yǎng)。后者都把對(duì)必然性的認(rèn)識(shí)作為人的自我實(shí)現(xiàn)的條件。
關(guān)于自由與必然統(tǒng)一的思想,在康德那里被表述為感性與理性的統(tǒng)一。通過論證這種統(tǒng)一,康德宣稱,人既是悟性的擁有者和受人支配的現(xiàn)象世界的立法者,又是純粹理性和意志的擁有者,以及自由和價(jià)值的道德世界的立法者。他用這種抽象思辨的形式,間接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對(duì)人的否定和奴役。但是由于他把對(duì)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二元論式地加以割裂,這種批判的力量減弱了。費(fèi)希特在否定了這個(gè)與主體及其活動(dòng)相對(duì)立的自在之物的同時(shí),提出了自我與非我對(duì)立的理論。非我是由自我設(shè)定與創(chuàng)造的。自我設(shè)定自身,然后據(jù)以設(shè)定其余的一切——非我。非我包括形形色色的自然形態(tài)和社會(huì)形態(tài),這一切在費(fèi)希特那里不是從“絕對(duì)主體”引申出來的。而在謝林那里,則是從“絕對(duì)觀念”引申出來的。至此,德國(guó)古典哲學(xué)已經(jīng)很接近于直接斷言人的本質(zhì)是自由了。
但是在馬克思以前,除克爾凱郭爾以外(他對(duì)馬克思沒有多少影響),把這一思想表達(dá)得最為明確和圓滿的還是黑格爾。在黑格爾看來,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精神的一切屬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得以存在。人是唯一有思想(精神)的動(dòng)物,所以只有人才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質(zhì)。但是,這一正確的命運(yùn)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具有完全唯心主義的內(nèi)容。黑格爾無視歷史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因素和人的現(xiàn)實(shí)的實(shí)踐作用,而用客觀觀念的發(fā)展來說明歷史例如他說,由于中國(guó)人“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賤的、自信生下來是專給皇帝拉車的”,所以他們便成為“沒有自由的奴隸”。又如他說奴隸制度的基礎(chǔ)是“人類還沒有取得他的自由的意識(shí),因而降為一件毫無價(jià)值的東西”。這種用觀念來說明歷史的做法,與后來的空想社會(huì)主義者如圣西門、傅立味等用人性來說明歷史的做法,同樣不能解決問題。因?yàn)榉催^來說,觀念和人性也是用歷史來說明的。不論在他們的宏偉的菱中有多少天才的閃光,他們的主要目的——為政治找到堅(jiān)固的科學(xué)基礎(chǔ)——都沒有達(dá)到。特別是黑格爾,他由于把人變成邏輯過程的一個(gè)片段而從歷史哲學(xué)中既取消了政治,也取消了人。
馬克思以前的哲學(xué),作為對(duì)神學(xué)的揚(yáng)棄,都是把自己的體系,建立在它們對(duì)人的本質(zhì)的理解之上的。馬克思指出,它們從種種不同的理解之中引伸出種種不同宗教、政治的、倫理的、法律的、美學(xué)的觀念,然后又拜倒在這些觀念之下,成為這些觀念的奴隸,這種情況應(yīng)當(dāng)徹底改變。自從馬克思批判了那一切,把“人”放在世界歷史的中心,指出主體地位的確立,是人的自由即人的本質(zhì)的證明;指出現(xiàn)實(shí)的人類世界,包括各種社會(huì)關(guān)系、意識(shí)形態(tài)和“屬人的”自然界,都是人的創(chuàng)造物和人的表現(xiàn),在歷史中形成和歷史地發(fā)展著的,人應(yīng)當(dāng)而且能夠從這一切之中解放出來的時(shí)候起,以往那些對(duì)于人的本質(zhì)的理解都過時(shí)了,都不值得我們?cè)偃ヒ灰簧钊胩接懥恕?/p>
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同時(shí),吸取了他的思想中的合理的內(nèi)核,為人的本質(zhì)是自由這一正確的例題找到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馬克思指出,人之所以失掉自由,不是因?yàn)樗麤]有自由意識(shí),而是“迫于歷史過程的力量”。因?yàn)槿耸亲孱惖拇嬖谖铮恰叭说氖澜纾菄?guó)家、社會(huì)”,個(gè)人的族類本質(zhì)只能體現(xiàn)在他和族類的統(tǒng)一之中,亦即只能體現(xiàn)在他和外間世界的統(tǒng)一之中。一個(gè)脫離歷史進(jìn)程和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人不可能是自由的,一個(gè)和外間世界相矛盾相對(duì)立的人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是由于歷史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必然性,個(gè)人和世界、和社會(huì)的矛盾和對(duì)立是不可能避免的。正是這種矛盾和對(duì)立反過來奪去了人的自由。等到人通過實(shí)踐認(rèn)識(shí)了這種必然性,并且能駕馭它而達(dá)到自己的目的時(shí),他就不僅超越了世界而且超越了他的自我,而從束縛他的客觀必然性中解放出來,進(jìn)入新的歷史行程了。這個(gè)過程正是人的現(xiàn)實(shí)的生成過程。人為了征服自然而創(chuàng)造了社會(huì)關(guān)系即人的世界,社會(huì)作為人的創(chuàng)造物而和人相對(duì)立,表示著人的族類的自我分裂。如果把歷史社會(huì)關(guān)系從人抽象出來加以考察(如黑格爾),或者把人從歷史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抽象出來加以考察(如費(fèi)爾巴哈),就不能抓住問題的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社會(huì)關(guān)系是人與人的分工合作關(guān)系(其異低級(jí)形式就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guān)系),在社會(huì)中的人是不能離開這個(gè)關(guān)系而生存的。由于生產(chǎn)力,社會(huì)狀況和意識(shí)三個(gè)因素之間可能而且一定會(huì)發(fā)生矛盾(這種經(jīng)濟(jì)必然性是社會(huì)中的自然,正如食物鏈結(jié)構(gòu)是自然中的社會(huì)),單獨(dú)的個(gè)人隨著他們的活動(dòng)擴(kuò)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dòng),也可能而且一定會(huì)愈來愈受到異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擴(kuò)大的、歸根到底表現(xiàn)為世界市場(chǎng)的支配。這在一定的歷史的階段上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發(fā)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動(dòng)對(duì)人來說就成為一種已的、與他對(duì)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qū)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
于是階級(jí)社會(huì)的歷史作為異化的歷史就奪去了人的現(xiàn)實(shí)的本質(zhì),使它變形為宗教、國(guó)家、資本等等,而與個(gè)人的現(xiàn)實(shí)的存在相對(duì)立,成為一種否定和壓迫人類的東西,把人變成一種和自己的本質(zhì)相矛盾的存在物,一種“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非人化的存在物”。這種人的本質(zhì)的被異化,直接表現(xiàn)為人的自由的喪失。人喪失自由等于喪失他的自我,因?yàn)樵诓蛔杂傻臓顟B(tài)下,他不是屬于自己的而是屬于他人的,他是他人手中的工具,為他人做自己所不愿做的工作,由于這個(gè)工作只是加強(qiáng)了人人控制自己的力量,所以他等于用自己的力量來反對(duì)自己,于是他自己的和自己分裂了。個(gè)人的這種自我分裂,是人與人互相為敵,即人的族類自我分裂的必然結(jié)果。
人為什么不得不這樣做呢?為了生活,即為了維持肉體的存在。僅僅為了生存而勞動(dòng)和動(dòng)物沒有兩樣,人的這樣的存在是動(dòng)物的存在,是和人的本質(zhì)相矛盾的存在。這種存在使人脫離了自己的普遍本質(zhì),變成直接接受本身規(guī)定性擺布的動(dòng)物。人首先必須超越于這種無情的物質(zhì)規(guī)定性,然后才能在個(gè)體和整體的統(tǒng)一之中獲得自由即自己的本質(zhì)。所以馬克思又說,“自由的領(lǐng)域,是在必要的外在目的的規(guī)定要做的勞動(dòng)終止的地方開始的”,是在“狹隘的物質(zhì)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彼岸。”
存在和本質(zhì)的矛盾是人類獨(dú)有的矛盾,是人自己造成的矛盾。這種矛盾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動(dòng)物的存在都是自然存在,本質(zhì)都是自然本質(zhì),它們的存在和本質(zhì)都統(tǒng)一在自然之中。人作為一種與自然相對(duì)立的主體,與必然相對(duì)立的自由,并沒有完全脫離自然和必然,產(chǎn)生這種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認(rèn)識(shí)和駕馭必然以獲得自由是人類自我實(shí)現(xiàn)的中心問題。所以“問題不在于如何說明世界,而在于如何實(shí)踐地變革和改造世界”,無產(chǎn)階級(jí)應(yīng)當(dāng)而且能夠通過對(duì)私有制基礎(chǔ)上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必然性的深刻了解和實(shí)踐的駕馭,消滅分工和私有制,解放全人類,從而最終地解放自己,“象其他任何人一樣滿足自己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guān)系還給人自己。
這個(gè)任務(wù)的實(shí)現(xiàn),也就是“人的本質(zhì)的自我復(fù)歸”,即人和自然之間同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解決,亦即人的存在與本質(zhì)、個(gè)體和整體、主體和客體(自身與對(duì)象)、自由和必然之間矛盾的解決。這些矛盾一旦解決,各個(gè)個(gè)人的全面的依存關(guān)系,他們的這種自發(fā)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dòng)的形式,必將“由于共產(chǎn)主義革命而轉(zhuǎn)化為對(duì)那些異已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業(yè)是由人們的互相作用所產(chǎn)生的,但是對(duì)他們說來卻一直是一種異已的、統(tǒng)治著他們的力量。”在號(hào)召和組織無產(chǎn)階級(jí)為實(shí)現(xiàn)這些目標(biāo)而進(jìn)行斗爭(zhēng)的過程中,馬克思的哲學(xué)發(fā)揮了巨大的力量,這就不僅把歷史和邏輯,而且把理論和實(shí)踐結(jié)合起來了。正是這種結(jié)合,為無產(chǎn)階級(jí)政治找到了堅(jiān)固的科學(xué)基礎(chǔ)。
六
手段對(duì)于目的的超越是人作為主體的自我超越。這種超越也就是揚(yáng)棄。所以自然本性的被人化,即自然人類史的轉(zhuǎn)化為社會(huì)人類史,也就表現(xiàn)為異化和異化揚(yáng)棄,即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運(yùn)動(dòng)。這個(gè)運(yùn)動(dòng)的動(dòng)力,是人類的需要。
需要并不是人類特有的東西。一切生物都有需要。有需要是生物區(qū)別于無生物的一個(gè)標(biāo)志。但人類的需要不同于動(dòng)物的需要。動(dòng)物的需要是天生的,人類的需要,則是人類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勞動(dòng)之所以是“人的”,是因?yàn)樗粌H滿足需要,而且創(chuàng)造需要。
需要的人化也就是自然的人化。一種人化了的需要人作為人的第一個(gè)標(biāo)志,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新的需要的產(chǎn)生是第一個(gè)歷史活動(dòng)”。異化勞動(dòng)之所以成為人的本質(zhì)的否定,就因?yàn)樗鳛榫S持肉體生存的手段,僅僅限于滿足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即動(dòng)物的需要,這就把類從人那里異化出來了。
對(duì)食物和異性的需要不僅是各個(gè)時(shí)代各種社會(huì)每一個(gè)人的需要,也是人和動(dòng)物共同的需要。所以它不是“人的”需要。盡管如此,人還是必須首先滿足這些大自然所安排的需要,因?yàn)槿水吘共荒芡耆撾x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形影不離的身體”,馬克思說:“人的萬能正是表現(xiàn)在他把整個(gè)自然界……變成人的無機(jī)的身體,所以自然需要的滿足是產(chǎn)生新的需要的前提。人們的勞動(dòng)當(dāng)初僅僅是滿足自然需要的手段,現(xiàn)在這個(gè)目的早已被超越了。所以人們?cè)缫巡煌緷M足于那種食宿起居中的、生物學(xué)上的滿足,并把僅僅活著和存在著體驗(yàn)為一種束縛和痛苦了。人類提出了新的而不是大自然所安排的需要,對(duì)于人類來說,僅僅活著,僅僅吃好,穿好,住好,已經(jīng)不夠了,他還需要更多的。這更多的是什么,人的需要就是什么。”
相對(duì)于動(dòng)物的需要來說,“人的”需要意味著更高的生物效能。人類愈是進(jìn)步,社會(huì)愈是復(fù)雜,需要愈是多樣化,人的本性愈是豐富,人和人也就愈是千差萬別。個(gè)別差異意味著人的本質(zhì)的豐富性。但是在人與人,個(gè)人與社會(huì)相矛盾的歷史的條件下,這種差異往往得不到承認(rèn)。不承認(rèn)個(gè)體差異的力量,也就是限制人類創(chuàng)造,束縛人類自由的力量。所以它又是否定人的本質(zhì)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人類活動(dòng)的產(chǎn)物,它通過與創(chuàng)造主體相疏遠(yuǎn)而與人對(duì)立。為要實(shí)現(xiàn)人的本質(zhì),必須突破這種力量。為要突破這種力量,必須在承認(rèn)個(gè)體差異的基礎(chǔ)上而不是在消滅個(gè)體差異的基礎(chǔ)上,即在自由的基礎(chǔ)上而不是在必然的基礎(chǔ)上,尋出個(gè)體和整體的統(tǒng)一。于是這樣的一種尋求,也就成為一切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普遍的需要。滿足這種需要的活動(dòng),也就是追求真、善、美的活動(dòng)。真、善、美的統(tǒng)一是自由。所以這一切需要又可歸結(jié)為對(duì)自由的需要。它們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得到滿足。沒有自由,就沒有任何除自下而上以久的“更多的”需要。
對(duì)真的需要可以表述為認(rèn)識(shí)世界和認(rèn)識(shí)自己的需要,包括對(duì)知識(shí)的需要,對(duì)哲學(xué)的需要,對(duì)理論上的參照系統(tǒng)和價(jià)值系統(tǒng)的需要。熱愛真理,為真理而獻(xiàn)身的精神,“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是人類特有的精神。所謂真理是認(rèn)識(shí)和客觀現(xiàn)實(shí)的符合。人的需要本身就離不開這種認(rèn)識(shí),離不開人對(duì)具體情況、即它得到滿足的可能性的認(rèn)識(shí)。這種認(rèn)識(shí)是人的一切精神需要和肉體需要相統(tǒng)一的基礎(chǔ)。這種認(rèn)識(shí)是人的一切精神需要和肉體需要相統(tǒng)一的基礎(chǔ)。這種認(rèn)識(shí)和基于這種認(rèn)識(shí)的勞動(dòng)實(shí)踐(包括生產(chǎn)建設(shè)、科學(xué)研究、哲學(xué)思考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等等在內(nèi)),是人類取得自由的第一個(gè)前提;對(duì)善的需要,可以表述為同他人聯(lián)系的需要,包括同情心,羞恥心,被理解的需要,受新生的需要,愛與被愛的需要,關(guān)心別人甚于關(guān)心自己的需要等等在內(nèi),都無不是人與人互相聯(lián)系的途徑,都無不是個(gè)體與整體走向統(tǒng)一的通道。由于自由只能在個(gè)體與整體的統(tǒng)一之中才能實(shí)現(xiàn),所以向善的努力本質(zhì)上仍然是一種追求自由的努力,它的滿足乃是人類取得自由的第二個(gè)前提;對(duì)美的需要可以表述為自我解放的需要。美作為人的本質(zhì)的對(duì)象化意味著我從有限的自我超越出來,而同外間世界達(dá)到同一。這種同一是有條件的,暫時(shí)的,永不滿足、永不停留的。是在不斷的超越中不斷的揚(yáng)棄、從而把人不斷地推向更高的人生境界的。所以審美的能力作為一種感性動(dòng)力,審美活動(dòng)作為一種能力,包括人類為自己創(chuàng)造的每一種更高的生物效能,都必然地要求自身的實(shí)現(xiàn)。所以對(duì)于具備了這種能力的人類來說,對(duì)真、善、美的需要也就成為最基本的需要。
這三種需要是互相密切聯(lián)系的。任何真理都不是屬于個(gè)人的。一個(gè)人重視真理甚于重視個(gè)人的物質(zhì)利益到什么程度,他就人化到什么程度。同時(shí)也就善和美到什么程度。市儈根本不知道真理的價(jià)值,這是他的動(dòng)物性的證明。任何一個(gè)真正的人都不會(huì)去追求市儈的幸福。不管伊壁鳩魯說得多么動(dòng)聽,人在老饕的餐果上和守財(cái)奴的保險(xiǎn)箱里找不到真正的幸福。人類的幸福始終是和自由聯(lián)系在一起的。自由和幸福的判別只是我們觀念上的一種差別,事實(shí)上它們是一個(gè)東西:人只有在自由的時(shí)候才感到幸福,也只有在幸福的時(shí)候才感到自由。如果一個(gè)人感到自由卻又不夠幸福,那么這只能意味著這自由還不完全;反之如果一個(gè)人感到幸福卻又不夠自由,那么這也只意味著他的幸福還不完全。真、善、美之所以比個(gè)人的物質(zhì)利益更使人幸福,也就因?yàn)樗葌€(gè)人的物質(zhì)利益更能使人接近自由的緣故。這種體驗(yàn)具體到什么程度,人就人化到什么程度。
狹隘的物質(zhì)利益對(duì)人的支配,也就是自然必然性對(duì)人的支配,這是一種古老的支配力量。在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下,一切生物都弱肉強(qiáng)食:狼吃羊,藤蘿爭(zhēng)奪樹木的陽光,以及整個(gè)動(dòng)物界寄生在植物社會(huì)里面,這一切都是天經(jīng)地義的。其所以天經(jīng)地義的道理,達(dá)爾文早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了。然而歷史的這種無情的必然需要早已經(jīng)被超越了。與之相反,主體的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dòng),往往是通過幫助弱者才體現(xiàn)出人的體質(zhì)的。當(dāng)他饑餓的時(shí)候,同情心使他不去搶劫另一個(gè)更弱小者的食物,反而把自己僅有的一點(diǎn)分給那別一個(gè)。這個(gè)我們稱之為“同情心”的東西,其歷史的含量顯然多于任何生物學(xué)上的本能。不,這是一種在生物界根本沒有過的東西。從生物學(xué)的觀點(diǎn)來看,那另一個(gè)正是他生存競(jìng)爭(zhēng)的對(duì)手,自然必然性只會(huì)批示他去戰(zhàn)勝他。他的同情與友愛恰恰是對(duì)于大自然的一個(gè)背叛。大自然根據(jù)同一法則創(chuàng)造了萬物,包括人、鷹和狼,它既然給了鷹以利爪,狼以尖牙,他又怎么能不把人的這種行為看作一種背叛呢?然而個(gè)人作為單獨(dú)的存在物正是通過這樣的背叛把自己和野獸區(qū)別開來的。百當(dāng)他弱肉強(qiáng)食的時(shí)候,例如當(dāng)他行兇、強(qiáng)奸、搶劫、詐騙、壓迫和剝削等等的時(shí)候,他就和動(dòng)物沒有兩樣了。在生活中,人們?cè)缫寻堰@樣的行為稱之為“獸行”,把這樣的人稱之為“衣冠禽獸”,這不是偶然的。“獸行”是對(duì)自然必然性的盲目,它造成人的族類的自我分裂。與人之相反,人對(duì)自然必然性的這種背叛是一種超越,是他的自由的證明,而正是在這個(gè)證明之中,他找到了通向族類整體的途徑。
這絕不是說,人的社會(huì)本質(zhì)同他的自然本質(zhì)是對(duì)立的。絕不是說人類的文明、文化同他們的生理需要是對(duì)立的。絕不是說人的社會(huì)本質(zhì)是天使而人的自然本質(zhì)卻是惡魔,或者人類的文明、文化是勒馬的韁繩而人的生理需要卻是馬:當(dāng)一方勝利的時(shí)候另一方就失敗了。我們常說靈與肉的斗爭(zhēng),我們常說理智與感情的矛盾,好象二者是根源于不同的東西,好象我們對(duì)真、善、美的需要,性質(zhì)上不同于我們對(duì)食物和異性的需要。好象我們?cè)诳次覀兊暮⒆映悦牢妒澄飼r(shí)得到的快樂,性質(zhì)上不同于我們自己吃這些東西時(shí)得到的快樂。如果真是這樣,如果我們的靈魂和肉體真是這樣互相離異而又互相對(duì)立,我們就只能把我們的本質(zhì),看作是一種外在與我們自身、并時(shí)刻窺伺著準(zhǔn)備控制我們的東西了。神性加獸性等于人性的公式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誤解,是一種異化了的觀念,完全沒有事實(shí)根據(jù)。恰恰相反,人的需要是人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人自身的本質(zhì)力量,正因?yàn)橛羞@種力量,人才是一種不同于其他任何動(dòng)物的特殊的動(dòng)物。人才比其他動(dòng)物更強(qiáng)大。在這個(gè)意義上人的需要意味著更高的生物效能,它只能是歷史和進(jìn)化的統(tǒng)一、社會(huì)和自然的統(tǒng)一、精神和肉體的統(tǒng)一,而絕不會(huì)是二者的分離。任何二者的分離都是人的本質(zhì)的自我異化和自我否定。正因?yàn)槿绱耍瑵M足這些需要,才意味著實(shí)現(xiàn)人的本質(zhì),實(shí)現(xiàn)自由。如果我們不理解二者之間的這種深刻的同一性,不理解無論精神的需要還是肉體的需要都是推動(dòng)人類進(jìn)步的同一種內(nèi)在動(dòng)力,我們就很難理解人。
七
上述二者的統(tǒng)一不僅是人的內(nèi)心世界的統(tǒng)一,也是人和外間世界的統(tǒng)一。所以它在外間世界必然有其對(duì)應(yīng)物——對(duì)象。所以對(duì)象化的需要,作為審美需要的一個(gè)重要內(nèi)容,也是一種基本的人的需要。
因?yàn)橹黧w性的人的本質(zhì)是自由,所以“我的對(duì)象只能是我的本質(zhì)力量之一的確證,從而,它只能象我的本質(zhì)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而自為地存在著那樣對(duì)我說來存在著……只是由于屬人的本質(zhì)的客觀地展開的豐富性、主體的、屬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即感受音樂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簡(jiǎn)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樂和確證自己是屬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感覺,才或者發(fā)展起來,或者產(chǎn)生出來。因?yàn)椴粌H是五官感覺,才或者發(fā)展起來,或者產(chǎn)生出來。因?yàn)椴粌H是五官感覺,而且所謂的精神感覺、實(shí)踐感覺(意志、愛等等)——總之,人的感覺、感覺的人類性——都只是由于相應(yīng)的對(duì)象的存在,由于存在著人化了的自然界,才產(chǎn)生出來的。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產(chǎn)物。”
這就是說,“隨著對(duì)象性的現(xiàn)實(shí)在社會(huì)中對(duì)人說來到處成為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現(xiàn)實(shí),成為屬人的現(xiàn)實(shí),因而成為人自己的本質(zhì)力量的現(xiàn)實(shí),一切對(duì)象也對(duì)他說來成為他自身的對(duì)象化,成為確證和實(shí)現(xiàn)他的個(gè)性的對(duì)象,成為他的對(duì)象,而這就等于說,對(duì)象成了他本身。”
這種情況表明,對(duì)象對(duì)于我已不是我自身的界限,“人的世界”對(duì)于人已不是外在于他的異物,這是他的自由的確證,他因此而感覺到對(duì)象的美,并因?yàn)檫@感覺面體驗(yàn)到幸福,或者說快樂。所以審美的快樂是一種體驗(yàn)自由的快樂,審美的經(jīng)驗(yàn)是一種體驗(yàn)自由的經(jīng)驗(yàn)。而美,作為對(duì)象化了的人的本質(zhì),也就是自由的象征。
在審美活動(dòng)的一剎那,人由于與對(duì)象世界的暫統(tǒng)一,而得以從一己的憂慮之中逃遁出來,而感覺到自身的解放。“解放”的需要是人類特有的需要,審美的快樂就是這種人的需要的象征性滿足。所以任何事物,從萬古長(zhǎng)存的雪山到瞬息即逝的鳥語花香,只要一旦成為審美對(duì)象,也就同時(shí)成了接通個(gè)體與整體,有限與無限的中介,而成為人們從一已的憂慮之中遁逸出來的橋梁。而這,也就是所謂“微塵中見大千”。因?yàn)橥黄屏恕拔m”與“大千”的界限,人在其中才得以實(shí)現(xiàn)人他的自由,并且直觀他的自由的自我。如果說離群索居的孤獨(dú)的個(gè)人是不自由的,那么,當(dāng)這樣的個(gè)人在審美的時(shí)候,就意味著他的“自我”這個(gè)黑暗的斗室里透講了一絲倏忽即逝的微光。美之所以能夠?qū)τ诓恍液屯纯嗟娜藗兪且环N無言的慰藉,原因就在這里。
正因?yàn)閷徝赖男枰且环N人的需要,所以一種犯罪的心理是同美不相容的,所以粗野庸俗的、動(dòng)物性的人,例如市儈、惡棍之類是沒有美感的,他可能只看到珠寶的價(jià)值而看不到它的光澤的美,他可能認(rèn)為一個(gè)立柜成一對(duì)沙發(fā)比一幅名畫更有價(jià)值。美是人的人化程度的標(biāo)志,美的哲學(xué)是人的哲學(xué)的最高境界,這不僅是指五官感覺,也是指精神感覺、實(shí)踐感覺——理性、意志、愛。不僅是指人的快樂,而且是指人的痛苦,——人的特有的痛苦。
動(dòng)物只有肉體的痛苦,這痛苦通常是由肉體需要的缺乏(“缺乏”表示著每個(gè)生物存在的界限和它對(duì)外間世界的依賴)所引起的,例如食物的缺乏表象為饑餓,溫度的缺乏表象為寒冷等等;人則除此以外還有精神的痛苦,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那些人類特有的痛苦,如孤寂、悲哀、空虛的煩悶、無所可愛的痛苦等等,就會(huì)看到這些痛苦都是由于人的對(duì)象缺乏所引起的。內(nèi)心里有的東西實(shí)際上沒有,表明“我”和世界的疏遠(yuǎn)。在這種疏遠(yuǎn)里存在著個(gè)體和整體、存在和本質(zhì)、自由和必然的矛盾。這矛盾被體驗(yàn)為痛苦。矛盾越是尖銳,則痛苦越是強(qiáng)烈。
無愛是一種低能,無所可愛則是一種不幸。無愛是內(nèi)在的空虛,無所可愛則是外在的空虛。無愛者是不會(huì)感到無所可愛的痛苦的,因?yàn)閷?duì)于他來說根本不存在的那樣的對(duì)象,所以也不會(huì)有對(duì)象的缺乏。這種情況的極端就是麻木不仁,麻木不仁并不等于罪(例如契訶夫《第六病室》中那相“桶子似的”農(nóng)民并不是惡人),但人愈麻木,就愈是接近動(dòng)物。你不可能使一個(gè)無愛的人感動(dòng),正如你不可能使動(dòng)物感動(dòng)。用我國(guó)的成語說,這就叫“對(duì)牛彈琴”。正因?yàn)槿绱耍砸环N共同的審美判斷,也就是不同的人們尋找共同點(diǎn)的一種立場(chǎng)。與之相同,自豪感、羞恥心等等都是在“看到別人”或者知道有別人的情況下表現(xiàn)出來的。由于有別人,我便具體地意識(shí)到了我存在的意義,這意義作為歷史的產(chǎn)物要求自身的對(duì)象化,這個(gè)需要的滿足,就被主體體驗(yàn)為自豪、羞恥等等;它的不滿足就被體驗(yàn)為悵惘和寂寞之類。“更無人處一憑欄”,寂寞是充實(shí)心靈空虛的以太。
屈原、李賀之向往山靈水神;拜倫、萊蒙托夫之迷戀于幽谷深山;安徒生之一味拂弄孩子們的心弦;席勒之有意識(shí)地遁跡于希臘羅馬遙遠(yuǎn)的“黃金時(shí)代”,都是由于寂寞。甚至司馬遷之寫出宏偉的歷史著作《史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寂寞。你看他筆下那些慷慨悲歌、“相樂也,已而相泣”的人們,往往為了封建領(lǐng)主的一點(diǎn)微不足道的知遇之情,甘愿漆身吞炭,挖眼剖腹以報(bào),不是寂寞是什么?但是司馬遷之寫出這些人物,也就是他在寂寞中對(duì)于寂寞的一種超越。藝術(shù)是一種超越。正如美是自由的象征,藝術(shù)也是自由的象征。美和藝術(shù)的區(qū)別,是在于它們作為一種人的需要的象征性滿足,前者僅僅是人的五官感覺的對(duì)象,后者則同時(shí)也是實(shí)踐感覺的對(duì)象。藝術(shù)品是人類勞動(dòng)實(shí)踐的產(chǎn)物,所以它也是勞動(dòng)產(chǎn)品。藝術(shù)創(chuàng)作活動(dòng)也是人類的一種生產(chǎn)活動(dòng),不但物質(zhì)生產(chǎn),也是精神生產(chǎn)。如果這產(chǎn)品使人感動(dòng),能夠征服人的心靈,那么這也就是“客體為自己生產(chǎn)主體”。作為一種歷史的因素,作為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實(shí)現(xiàn),藝術(shù)也是人類走向進(jìn)步的現(xiàn)實(shí)的運(yùn)動(dòng)的表現(xiàn)。
八
由于人的本質(zhì)只能存在于個(gè)體和整體的統(tǒng)一之中,所以抽象的、靜止的、孤立的個(gè)人不具備人的本質(zhì),也不具備人的價(jià)值、意義和豐富性。孤獨(dú)的個(gè)人不具備人的本質(zhì),也不具備人的價(jià)值、意義和豐富性。孤獨(dú)的個(gè)人的存在歷史上是曇花一現(xiàn)的現(xiàn)象,這樣的人的存在是動(dòng)物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存在。所以一旦人和歷史、社會(huì)脫節(jié),一旦人和“人的世界”疏遠(yuǎn)了,一旦人的族類由于內(nèi)在的矛盾而自我分裂,孤獨(dú)的、不自由的、在歷史命運(yùn)面前無能為力的“個(gè)人”,就會(huì)發(fā)現(xiàn)自己的渺小、空虛、生活沒有意義;就會(huì)被異化為“非人”的事物,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
人之孤立而成為個(gè)人是迫于歷史過程的力量。但人仍然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歷史仍然是人的創(chuàng)造物和人的現(xiàn)實(shí)性。自由在這里是一個(gè)主體性的東西,即使它被壓抑、被異化了,它仍然是被壓抑異化的人的本質(zhì);從另一方面來說,在一定的歷史發(fā)展階段上,人又是一個(gè)在不斷自我創(chuàng)造的過程中被自己的本質(zhì)所壓抑的偉大的存在物。世界歷史的曲折、緩慢而又艱難的進(jìn)程,無非也就是這個(gè)不斷地自我實(shí)現(xiàn)又自我否定的、人類從自由出發(fā)而又向著自由前進(jìn)的運(yùn)動(dòng)的可以觸摸到的現(xiàn)實(shí)而已。
所以每一個(gè)歷史地不自由的個(gè)人又都以其獨(dú)特的、不可重復(fù)的方式參與創(chuàng)造歷史,而在這創(chuàng)造中實(shí)現(xiàn)他的自由即他的自我。正因?yàn)槿绱怂攀亲晕覄?chuàng)造的生物。所以自由并不是一種只有在遙遠(yuǎn)的將來才能實(shí)現(xiàn)的宏偉目標(biāo),人類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時(shí)候才需要對(duì)自己的行為負(fù)責(zé)。如果那樣,歷史也就不能前進(jìn)了。當(dāng)布魯諾在認(rèn)罪書和火刑柱之間作出選擇時(shí),當(dāng)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請(qǐng)求赦免和終生苦役之間作出選擇時(shí),鐐鏈正鎖著他們的手足,但他們?nèi)匀皇菑?qiáng)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yàn)樗麄兯x擇的火刑柱和終生苦役把他們和整個(gè)人類的歷史命運(yùn)聯(lián)系在一起了。他們被與社會(huì)隔離,但他們并不孤獨(dú),他們是族類整體的一部分,因而屬于一個(gè)永不失敗的隊(duì)伍。個(gè)體做不到的事情,整體都能做到,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人的萬能性。整體是不會(huì)失敗、也不會(huì)死亡的,因?yàn)樵谡w中,這一個(gè)人的生命和事業(yè)可以通過另一個(gè)人延續(xù)下去,薪盡火傳而生生不息,以至于無窮。對(duì)于族類整體來說,提起腳是在走路,放下腳也是在走路,而上升的道路和下降的道路是同一條道路。在這條路上,每一個(gè)為真理而受苦受難的布魯諾和軍爾尼雪夫斯基都由于超越了個(gè)體生命的物質(zhì)規(guī)定性而從狹隘的“自我”之中解放出來,而和全人類一同受苦受難。正因?yàn)槿绱耍匀魏慰嚯y都不能越過他心中的某個(gè)東西。而同時(shí),由于意識(shí)到自己是一個(gè)真正的人,他們的痛苦也獲得了某種快樂的性質(zhì)。因?yàn)樽鲆粋€(gè)痛苦的人總比做一個(gè)快樂的動(dòng)物要好。他們的痛苦是他們的人的本質(zhì)的證明,他們通過這一痛苦而體驗(yàn)到自己的人的存在。所以他們寧愿選擇痛苦。在這里,我們看到,人由于在個(gè)體和整體的統(tǒng)一中實(shí)現(xiàn)了存在和本質(zhì)的統(tǒng)一,痛苦獲得了快樂的性質(zhì),囚禁獲得了解放的性質(zhì)。
這里用布魚諾和車爾尼雪夫斯基作為例子,并不意味著他們的理論是正確的。不,他們?cè)缫呀?jīng)被超越了。他們是應(yīng)當(dāng)被超越的。他們是作為人類通向真理的橋梁被超越的。就是說他們是作為人類自我創(chuàng)造過程中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被揚(yáng)棄的。而他們的被超越和揚(yáng)棄,也就是他們的參與創(chuàng)造歷史。如果沒有這各步斷的超越,歷史也就停止了,人也就不成其為人了。如果不是和路連在一起,橋還有什么意義?成為橋,是他們?yōu)槿祟悶闅v史作出的貢獻(xiàn)。一定的社會(huì)歷史條件,以及由這些條件所形成的各個(gè)人的現(xiàn)實(shí)的物質(zhì)生活狀況,和基于這些狀況的物質(zhì)需要,是人的存在的“彼岸”,而“彼岸”世界的存在正是由于有這些橋梁的緣故。所謂個(gè)人創(chuàng)造歷史,也就是橋梁創(chuàng)造彼岸。不是橋梁“通向”彼岸,而是橋梁創(chuàng)造彼岸。“知足常樂,能忍自安”的哲學(xué),是此岸的哲學(xué),因而也是動(dòng)物的哲學(xué)。成為橋梁也就是成為人,這是他們的自我創(chuàng)造。人只有參加到歷史的行程中才能夠自我創(chuàng)造,只有在創(chuàng)造世界的同時(shí)才能夠自我創(chuàng)造。
歷史是人創(chuàng)造的,所以它不是不可逆轉(zhuǎn)的過程,它就是創(chuàng)造活動(dòng)本身的表現(xiàn)。歷史上有些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變成了荒淫殘忍的暴君,有的資產(chǎn)階級(jí)出身的知識(shí)分子參加了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事業(yè),這期間個(gè)人的選擇作為無數(shù)力的平行四邊形的組成部分,縱模交錯(cuò)地影響著歷史的進(jìn)程。茫茫塵世中無數(shù)人的這些微小的、看不見的活動(dòng)的總和,是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深遠(yuǎn)的潛在動(dòng)力。所以一個(gè)人有可能在實(shí)踐地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選擇而實(shí)現(xiàn)自由的過程中,把偶然性引進(jìn)歷史。正因?yàn)槿绱耍驗(yàn)閭€(gè)人把偶然性引進(jìn)歷史是可能的,歷史才不是抽象的歷史,才不是黑格爾式的無情的邏輯行程,才不是把人當(dāng)作工具當(dāng)作從一個(gè)點(diǎn)向著另一個(gè)點(diǎn)直線前進(jìn)的手段的人之外的力量。
承認(rèn)個(gè)人參與創(chuàng)造歷史,就邏輯必然地要求每個(gè)人對(duì)自己的行為負(fù)責(zé),而不是把一切都?xì)w因于歷史的必然,用自己沒有自由來解釋。每個(gè)人的生活條件各不相同,但是探索還是盲從,正直還是卑鄙,勇敢還是懦怯……選擇的機(jī)會(huì)對(duì)每個(gè)人同樣存在。正因?yàn)槿绱耍總€(gè)人的生活都不是平庸的沼澤,每個(gè)人的生活都通向人類歷史的偉大行程。而這也就是個(gè)人存在的意義、價(jià)值和豐富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如果一個(gè)人的生活不是那樣,那么這決不完全是歷史和社會(huì)的過錯(cuò),他自己也有責(zé)任。
如果不承認(rèn)這一點(diǎn),那么我們就應(yīng)當(dāng)說,在這個(gè)世界上沒有什么正義和罪惡、偉大和渺小、英雄與懦夫,也沒有什么美和丑、崇高和卑下,因?yàn)槿耸遣蛔杂傻模贿^是體現(xiàn)和完成某種看不見的規(guī)律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不論是皇帝還是小偷)不能對(duì)自己的行為負(fù)責(zé),所以在這個(gè)世界上沒有什么好人和壞人,只有被一定的客觀必然性放進(jìn)一定的關(guān)系之中,不得不通過由這種關(guān)系所決定的途徑和所許可的手段謀求生存和滿足的人。如果他殘暴,或者卑鄙,那么這殘暴和卑鄙作為外在必然性的傳導(dǎo)物,也臺(tái)同蛇的毒牙或豬籠草的觸須一樣,是一種我們無法用價(jià)值尺度來衡量的東西,事實(shí)上價(jià)值尺度已經(jīng)不再存在,因?yàn)檎f到究竟,精神,作為有機(jī)體的一種屬性,也象有機(jī)體本身一樣,必須從屬于適應(yīng)自己的生存條件這一自然法則。這一法則在歷史和社會(huì)中變形為政治、經(jīng)濟(jì)等等,于是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代替了人的哲學(xué),歷史變成了邏輯的篇章,而具體的人卻被抽象出來,完全否定和取消掉了。
這是自然的領(lǐng)域而不是人的領(lǐng)域,在這個(gè)領(lǐng)域中尋找人的本質(zhì),當(dāng)然也就只能是“剝洋蔥皮”。如果我們抓住事物的根本,把歷史和人的世界還給人本身,我們就會(huì)看到,個(gè)人參與創(chuàng)造歷史是個(gè)人存在的價(jià)值和意義。正因?yàn)槿绱耍驗(yàn)閭€(gè)人參與創(chuàng)造歷史,個(gè)人才作為自由的主體而和類合而為一。沒有這種個(gè)體和整體、存在和本質(zhì)的統(tǒng)一,也就既沒有創(chuàng)造,也沒有歷史,更沒有人的本質(zhì)了。人就和大自然結(jié)為一體,而成為物質(zhì)自然中一個(gè)自在的部分了。
九
黑格樂孔德所強(qiáng)調(diào)的那種把人類歷史看作是一個(gè)有規(guī)律地向前發(fā)展的過程發(fā)展的過程的思想,可以同以牛頓為代表的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決定論互相印證。它根據(jù)單一的線性因果律,為我們給定了歷史的過去和未來。隨著量子力學(xué)取代經(jīng)典物理學(xué)而成為自然科學(xué)的徑緯,這種決定論的歷史和未來社會(huì)的假設(shè)都是不可鴣的。面對(duì)著多維的世界和多元的人生,我們唯一能依賴和依靠的只是我們自己。
為了依靠自己,我們首先必須認(rèn)識(shí)自己的限度。我們的全部觀點(diǎn),我們的全部知識(shí),都無不受著我們?cè)谄渲蝎@得經(jīng)驗(yàn)和知識(shí)的有限的歷史社會(huì)條件,以及在這些狹小范圍內(nèi)形成的我們自己的知識(shí)、視野和思想方法的局限。并且這個(gè)局限性,隨著知識(shí)和信息爆炸性發(fā)展正在增大。隨著人類感官不能直接經(jīng)驗(yàn)的無數(shù)事物(從微觀世界的基本粒子到宏觀世界的時(shí)空和宇宙)進(jìn)入我們的視野,我們尤其深切地感覺到我們觀察力和理解力的限度,感覺到自己身上有一種結(jié)構(gòu)性軟弱無能亟需克服。宇宙的奇異使我們感到神秘莫測(cè),而我們所熟悉、所認(rèn)為理所當(dāng)然的許多原理、原則和思維范疇,例如因果律、質(zhì)量不滅定理等等,以及其他許許多多被主為是不可違反的絕對(duì)定律,現(xiàn)在都被證明為不正確的和無效的。假如在一些極為簡(jiǎn)單的物理現(xiàn)象背后仍然隱藏著許多使我們的智力感到迷惑的事物,那么面對(duì)著如此多維、多元、多義而又能動(dòng)的世界和人生,我們又將如何措手足呢?
愈是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我們也愈是確信,人要依靠自己,首先必確立自己,在意識(shí)到自己對(duì)于世界的主體地位的同時(shí),使自己的精神保持開放。那種單線的決定論的歷史觀和世界觀之所以不能適應(yīng)現(xiàn)代世界,最根本的原歷也就在于它們的的封閉性。
“封閉性”一詞,現(xiàn)在絕對(duì)是一個(gè)否定性的詞。但這種否定性是有其異化前提的。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也不能完全排斥封閉性。主體性就是在封閉與開放之間所保持的一種動(dòng)態(tài)平衡,即以開放為主導(dǎo)的平衡。如果完全開放,也就沒有主體了。沒有主體也就沒有客體。如果沒有知、意、情,也就沒有真、善、美,從而也就沒有科學(xué)、道德、藝術(shù),以及作為這一切的總和的主體意識(shí)——哲學(xué)。哲學(xué)作為一種價(jià)值體系,也是一種主體意識(shí)。由于真理不是唯一的,歷史是不可預(yù)料的,所以我們必須有所選擇,當(dāng)一個(gè)人在進(jìn)行選擇的時(shí)候,他敢就是在確立他的自我。沒有這個(gè)自我,他就會(huì)無所適從。
由于上述理由,我不同意某些西方學(xué)者把電子計(jì)算機(jī)和機(jī)器人作為“人工主體”加入認(rèn)識(shí)論,把科學(xué)思想、詩的思想、和藝術(shù)作品等等作為“第三世界”(或“世界”)的“沒有主體的認(rèn)識(shí)論”加入認(rèn)識(shí)論。我也不同意說電子計(jì)算機(jī)的任何作品(詩、畫、音樂)是藝術(shù)作品,不同意機(jī)器人的任何行為是道德行為。面對(duì)無限深邃而又冷漠無情宇宙,我們需要愛,需要溫暖,需要同情,需要信仰,需要真誠(chéng),需要英雄主義,需要夢(mèng),需要值得為之而獻(xiàn)身的東西。沒有這些,我們就無所適從。沒有這些,我們就不能前進(jìn)。這些都是構(gòu)成我們的自我的必要的因素,也是我們的自我借以膠進(jìn)的動(dòng)力。尋找這些,也就是尋找失落的自我。
為確立自我,我們就不能拒絕某種程度的封閉性。這種封閉性和開放性的矛盾,是我們自身固有的矛盾。人作為具有社會(huì)性的自然存在物,既具有開放的一面,又具有封閉的一面。這開放的一局也就是我們稱之為感性動(dòng)力。這封閉的一面,我們暫時(shí)稱之為僵化的理性結(jié)構(gòu)。感性動(dòng)力植根于人的自然生命力,理性結(jié)構(gòu)來自歷史的積淀。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就象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關(guān)系,都以實(shí)踐(或者是勞動(dòng)實(shí)踐,或者是審美實(shí)踐,或者是其他社會(huì)實(shí)踐)。為中介互相依存(所謂“感覺變成理論家”),有時(shí)又互相疏遠(yuǎn)。在互相疏遠(yuǎn)的情況下,亦即在理性結(jié)構(gòu)在僵死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成為僵死的精神結(jié)構(gòu),從而與感性動(dòng)力相異化的情況下,理性結(jié)構(gòu)就會(huì)成為一種束縛感性動(dòng)力的桎梏(所謂“以理殺人”),它既扼殺了進(jìn)步,又扼殺了美。在我們這個(gè)千年的封建古國(guó),這方面的例子是不勝例舉的。作為主體的人的自我,都無不是這種感性與理性的統(tǒng)一,所以他既有開放的、進(jìn)取的一面又有封閉的保守的一面。
感性動(dòng)力作為人的自然生命力天然地具有開放的性質(zhì)。作為自然生物的人的本性是分子類型的,個(gè)人結(jié)構(gòu)的遺傳信息是以分子的形式儲(chǔ)存在人體內(nèi)的,我們的本質(zhì)就有可能具有許多量子偶然性和量子模糊性,而不可預(yù)料,不可設(shè)計(jì),不可事先規(guī)定,而必然要在其“歷史的”發(fā)展中通過某種選擇,同我們自古遺留下來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得十分神圣而珍貴的信念和倫理規(guī)范相沖突。“歷史的”進(jìn)化并不取消這種生物學(xué)上的自然過程,這就使得感性與理性發(fā)生矛盾具有某種必然性。如果換一種說法,也可以說量性本身處在不斷更新的運(yùn)動(dòng)過程中,這樣的理性是與感性相一致的理性,它的僵死的結(jié)構(gòu)化了的理性的沖突,也就是感性和理性的沖突。正是這種沖突,構(gòu)成了主體性概念的多層次性和多元性。構(gòu)成了我們心理生活的動(dòng)態(tài)平衡。
我們對(duì)愛、溫暖、嶼、信仰……等等的需要,不論其獲得何種理性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種感性的需要。正是由于這種感性的需要,才產(chǎn)生了審美的需要和審美的能力。所以這咱需要和能力的實(shí)現(xiàn)——它的對(duì)象化和客觀化是人的主體地位的確證,是人的本質(zhì)——自由的確證。所以作為感性對(duì)象的客觀事物的美,從本質(zhì)上來說,也就是審美主體的自由的象征。這需要另文探討,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有機(jī)會(huì)一試。
文檔上傳者
- 人類自然觀轉(zhuǎn)變
- 人類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
- 人類本質(zhì)藝術(shù)
- 人類政治文明
- 政治人類學(xué)
- 構(gòu)成人類文化現(xiàn)
- 人類政治文明
- 人類虛擬經(jīng)濟(jì)
- 政治人類學(xué)
- 人類學(xué)人本設(shè)計(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