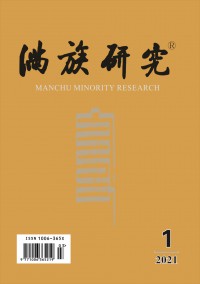滿族女詩人詩歌創作探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滿族女詩人詩歌創作探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詩中的各地風光與社會百態
扈斯哈里氏少年時即隨父宦游蓋州,婚后隨翁宦游熊岳,兩地及沿途風光皆入其詩。如《繡余小草》卷二有《路過耀州廟夜游即景》,詩題后注曰“:廟在蓋州城北五十五里,山勢極高,盤道崎嶇,廟宇輝煌。每年四月十八日大會七天,遠近往觀者絡繹,晝夜不息。”卷三則有數首詩描寫遼陽及熊岳一帶名勝古跡如首山、馬鞍山、青石關、饅首山、王小兒山等,且詩題后皆注明其地理位置、歷史淵源及民間傳說等相關情況,可補方志之不足。《繡余小草》卷三有《黃鱗魚市》詩,詩題后注:“在熊城北十里,立夏日起,海上打魚,設棚無數,海上如市,魚車往來如云。”詩曰“:立夏風和四月天,黃魚有信至年年。一方佳味隨潮擁,眾網齊張逐浪圓。雜亂席棚街市旺,往來商賈馬車連。漁人生計原依水,鎮日紛紛在海邊。”生動描繪了同治年間熊岳海邊捕黃魚及黃魚交易的景象。沈陽是扈斯哈里氏的家鄉,《繡余小草》卷三有《詠陪都》“:鐘靈沈水帝王鄉,山海包羅氣象長。人布旗民皆有署,官分文武定規章。地形千里連雙島,城勢八門列四方。最好金鑾龍鳳闕,天然世業永無疆。”此詩氣象宏偉,充滿了對本族根本之地的自豪感,而“人布旗民皆有署”則正是當時盛京旗民分治的實錄。《繡余小草》卷三《詠行圍采獵》七律二首其二曰“:將軍圍合又排兵,鼓角齊鳴號令行。雪盡鷹飛雙眼疾,山空月色一輪明。旌旗遍野豺狼懼,火炮連天虎鹿驚。獵罷歸來皆得意,寒風相送馬蹄輕。”寫出了盛京將軍行圍采獵的浩大聲勢與武器裝備的強大震懾力,顯示了這一活動的準軍事演練特征。此詩題后注曰:“盛京將軍每年小雪出圍,大雪回圍。時在同治九年事也。圍場在威遠堡邊門外,現今停圍,全行開地,歸海龍城總管衙門管理。”據《盛京典制備考》所載“圍場處應辦事宜”稱“:圍場原設一百零五圍,按年輪轉捕獵”,“小雪節前圍長、翼長帶領梅倫委官、專達兵八十名領纛打圍”①。雖然盛京將軍的行圍采獵與皇帝的木蘭秋狝皆是滿洲騎射傳統的體現,但晚清時皆已停止,盛京圍場在光緒末年亦最終解體。詩題后注當為作者在整理詩稿時所補,透露出作者對這一傳統式微的惋惜,而她的詩與注正可與史料合觀,是史料的形象化注解。光緒十九年,惠格赴任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府,扈斯哈里氏生平第一次離開東北家鄉,隨夫自長灘河由水路經煙臺至上海,在上海勾留月余,再由上海至江西。《江右隨宦紀事》正是這次隨任經歷的文字結晶。八月十一日她由牛莊上輪船,作有《火輪船中即景》組詩七絕四首,其一曰:“難辨風聲與水聲,黑煙漠漠一舟輕。往來不用艄人力,始信輪船妙法精。”其三曰“:蒼茫一望水連天,機器聲如鼎沸煎。到此已非塵世界,乾坤浩大信誠然。”她由衷嘆賞機器輪船不用人力的妙法,四首詩將火輪船航行于海上的景象寫得有聲有色。到了上海,近代城市的先進與繁華使她乍見之下贊嘆不已,《上洋即景》詩曰:“五方雜聚旅人稠,海上繁華紀勝游。入夜張燈開戲館,排空耀眼是洋樓。高懸電燭光無際,隨處笙歌鬧不休。最好路平車馬快,往來莫見起塵頭。”洋樓、電燈、馬路是對她視覺沖擊力最大的城市設施,此詩尾聯對平坦、潔凈的馬路就大加夸贊。但第一眼的震撼過去后,她對上海的生活方式卻發出了質疑,這在《上海竹枝詞》組詩七絕六首中表露無遺。扈斯哈里氏是受到儒家思想薰陶的傳統女性,長期生活在東北邊疆,習慣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業社會生活,因此,組詩第一首末句“偏從夤夜作生涯”顯示出她對上海夜生活的不以為然。第二首則對“入夜沿街婦女游”的現象提出批評,在她眼中,這是缺少教化的表現,違背了儒家的女性行為規則。第三至第六首渲染了上海不夜城游人如織、戲館青樓徹夜笙歌的景象,但是卻發出“繁華太甚應難久”的警告,并以“莫道繁華為可羨,須知樸厚始能綿”徹底否定了上海式的浮華生活,標舉其對立面———樸厚的風俗與生活方式,這種觀點在當時的傳統人士中亦頗有代表性。
勸誡詩、諷諭詩與時事詩的寫作
扈斯哈里氏隨任袁州,積極襄助丈夫的政務活動。文化成為其詩集所作序中提到“:本年夏五亢旱,公中夜徒步泣禱諸神,為民請命,夫人于內署設壇,清齋櫛沐,未向晨即稽首吁天,迄日入弗少息。如是者經旬,甘霖大沛,禾則盡起。郡民讙頌公德,兼戴夫人。”雖然祈禱求雨在現代人看來是一種迷信行為,但卻是她系心民瘼、努力在政務上為其夫分憂的表現。她又發揮自己的才能,以詩為政治教化的工具,做有《閨訓》組詩12則,其末有自識,開篇即標舉曹大家《女誡》與宋若昭《女論》為“不朽之偉言”,其《閨訓》之作自有追步前賢之意。她希望《閨訓》與其夫《勸戒娼賭竹枝詞》、《勸民改過從善詞》內外配合,移風易俗。《閨訓》組詩12則多是重申儒家對于女性德行的要求,如:戒閨中勤檢束以全婦德、戒閨門盡孝道以事翁姑、戒孀婦守貞節以示不二等等,但也有頗具現實針對性的,如:戒婦人為繼母以愛前男,戒為婦藉歸寧以生放蕩,戒閨門應洗作以成冬衣等等。《戒閨中宜詩書以明禮義》一詩曰“:書中禮義最精詳,閨閣還應學典章。節孝傳中多淑女,裙釵隊里有賢良。循規蹈矩通情理,開卷留心識短長。休看淫詞聽艷曲,幽閑貞靜姓名彰。”這顯然是她將自己讀詩書的體會與所得寫以示人,雖然她強調的仍是詩書的道德教化作用,但在不重視女性教育的社會氛圍中,這種勸誡仍有其積極作用。晚清國勢衰微,社會風氣敗壞,扈斯哈里氏寫作了一系列針對社會不良現象與陋俗的諷諭詩,《繡余小草》卷二有《戲詠入泮竹枝詞》四首,其一揭露當時以假底筐夾帶之法:“進場欲作好文章,夾帶全憑假底筐。幸遇一篇方寫上,秀才身價不尋常。”諷刺了當時科舉作弊之風。卷三有《詠吸洋煙竹枝詞》七絕八首,組詩由煙槍之名聯想到這一工具如同兵器傷人肺腑,又細致描繪了吸食場景及吸食后的精神狀態。第八首充分表達了作者對整個社會嗜鴉片成風的擔憂,詩曰“:人人食土近來多,土更吞人可奈何。入此迷途全不醒,畢生氣血盡消磨。”以“土吞人”的意象揭示出了鴉片吃人的巨大危害。她深知一旦吸食成癮即迷不能返,因此呼吁人們莫與鴉片結緣。作者在袁州時,甲午戰爭爆發。《江右隨宦紀事》卷下有十余首詩皆針對當時戰況而作。《聞奉天南數城失守因之有感》七律四首中作者指出了戰敗原因,一是“大帥寡謀空耗帑”,二是“眾官喪膽懼前征”,三是“諸營訓練不精詳”,因而交戰即敗。遼東是作者家鄉,她對這場戰爭格外關切。“九連城接鳳凰城,猾虜披猖一掃平”,清軍節節敗退,邊關重鎮接連陷落,敵軍長驅直入,由遼東進占威海,百姓遭難令她心情沉痛,而清軍的潰敗令她憤慨。她在詩中直斥“無謀將士羞中國,喪膽軍官守盛京”,發出了“無限干戈無限恨,彼蒼何不憫群生”的感嘆。《悶坐偶成(因日本擾亂邊陲)》組詩七絕八首寫到自己牽掛身陷東北的兒子與公公,因戰事而音信稀少,作者憂急之下,“癡心日日卜金錢”。她掛念的不僅有家人,更有戰區遭難的廣大百姓。組詩其五曰“:諸城不守動干戈,罹劫人民可若何。倭寇到時皆束手,圣朝枉自有兵多。”末句表達了她對清軍的極端失望。組詩其七更是憤怒譴責將帥“臨陣敗時翻作勝,冒功邀獎計偏高”。
扈斯哈里氏詩歌創作的文學與歷史價值
《江右隨宦紀事》卷下有《自詠》七絕六首,扈斯哈里氏總結了自己學詩的經歷。詩中稱其三胞伯及盟伯楊世堂為其良師,其父亦曾利用三余時訓其學詩。她學詩以三唐為宗,《自詠》詩中她自謂“幼年原不解詠詩,大半粗詞是竹枝”,雖是謙詞,但也的確道出了其作的特點。她的詩才自是不容否認,所作清新自然,平易暢達,但學唐者若學殖不厚,則易流于粗淺,卻也是事實,她的某些作品正有其弊。周汝昌曾疑心扈斯哈里氏亦如其他女詩人,有時不免有父兄輩潤飾之例。細讀其作,筆者以為扈斯哈里氏的情況與那些女性詩人有異。在其幼年學詩階段,因其父、三伯與盟伯曾予指點,或有潤飾或改定其詩作的情況。但隨其詩藝的進步與成熟,她自己可指點其長子做詩,并為人,如《繡余小草》卷六就有詩題為《代人和臥云禪師原韻》。逗留上海期間,她甚至為丈夫捉刀,《江右隨宦紀事》卷上即收其兩首代丈夫所作的應酬詩。如前所述,其夫惠格并非科甲出身,應是詩才不逮妻子,才會由其。筆者甚至懷疑他在江西所作的《勸戒娼賭竹枝詞》、《勸民改過從善詞》亦是妻子代作,不過假其名以公諸于世。扈斯哈里氏成年后所做詩應無假手他人潤飾之嫌疑。不過,在她將自作詩稿整理付梓時,她為不少詩加了注,注明詩作背景,略述詩中人物生平事跡,不排除她此時對自己的少作加以潤飾的可能。扈斯哈里氏雖然屢隨家族中男性宦游,但其詩友圈卻并不大,其詩集中僅有與家族中男性及盟伯贈答唱和之作,無一首與女性詩友唱和的作品。《八旗藝文編目》中所收錄的滿洲女詩人大多家居北京,可與匯聚于京師的各族女性詩人交游,扈斯哈里氏則缺乏這一便利條件,她的生活圈中無一可與其詩才相頡頏的同輩閨友,婚后,其生活圈中人如其夫與子詩才皆不及之。若有詩友互相切磋,彼此激勵,其詩藝當更精進。雖然扈斯哈里氏的詩歌創作是一樁孤獨的事業,但她卻憑著對詩歌的熱愛而堅持不懈,做詩使她感覺自己沒有虛度光陰,是她的樂趣所在。扈斯哈里氏亦如其他清代女詩人,常以眼前風物入詩。她的寫景狀物之作不少,其中不乏佳作。由于隨宦游歷,她的眼界更為開闊,她的詩中不僅有其他女詩人筆下常見的家宅庭園的四時風物,更有自北至南的各地風光風俗。尤為難得的是,她為遼東與上海這兩處在中國近代史上頗為重要的地區留下了詩的記錄,拓展了清代女性此類作品的題材范圍。遼東本是滿族的發祥之地,卻見證了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上海雖有傲視其他地區的近代文明,卻也是半殖民地的屈辱標志。扈斯哈里氏在詩中描繪了遼東的山川勝跡、沈陽的富庶繁榮與社會百態,她對家鄉滿懷眷戀與熱愛,正因如此,她才會由于這片土地被侵略者蹂躪而痛心疾首。她在上海受到近代文明的沖擊,愈覺傳統生活方式的恒久價值。這種種復雜的感情與內心沖突使她的此類詩歌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至于其寫作的家事詩,則以對家庭與家族生活的秉筆實錄,成為后世讀者了解晚清東北旗人生活的一扇窗口。扈斯哈里氏并不是一個眼中只有小家的女子,她以濟世自期,頗不同于一般以文才傲人的才女。正是積極用世的人生理想促使她寫作了勸誡詩、諷諭詩與時事詩。雖然扈斯哈里氏的勸誡詩效果堪疑,她也并沒有超越其時主流思想的先進女性觀,但她認為女子亦應讀書明理的觀點卻是難能可貴的。其以洋煙等為題的諷諭詩及關于甲午戰爭的時事詩則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表現了憂國憂民的情懷,是清代女性詩壇上的閃光之作。扈斯哈里氏的詩藝固然遜于早其半個世紀的同族女作家太清,但卻是晚清東北滿族女詩人中的翹楚。其詩作不僅記敘了自身經歷與家族情況,且多方面地展現了晚清社會現實,可目之為詩史,在百余年后的今天具有不容忽視的文學與歷史價值。
本文作者:詹頌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國際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