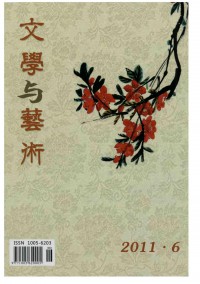文學轉向論文:文學的人類學轉向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文學轉向論文:文學的人類學轉向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銀浩單位:四川大學文新學院
在西方19世紀中后期,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寬泛的“文化”定義。在他的影響下,人類學家弗雷澤(1854~1941)完成了長篇巨著《金枝》,使人類學對文學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進。接下來,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1908~2009)進一步發展了這種以神話為主要對象的人類學文學研究,締造了一套影響深遠的結構主義哲學。在文學方面,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對當代文學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文學人類學”為題的學術研究不斷面世。1978年美國學者伊瑟爾出版了題為《從讀者反應到文學人類學》的文集,明確號召“走向文學人類學”。
從中國,文學人類學的發展也經歷了自“西學東漸”到逐步本土化的過程。在早期的萌芽階段中,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的方法論。茅盾、聞一多等借鑒西方的圖騰和神話理論,對中國神話、圖騰、儀式進行研究,建構著名的“龍圖騰”等理論。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導的“歌謠運動”開始了對中國口承傳統的研究。林耀華的人類學報告《金翼》則開創了中國的“小說體民族志”。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中國學術界出現了明確以“文學人類學”為標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評和文學的人類學批評成為新時期文學批評的潮流,并由此引發了尋根文學熱。21世紀,中國文學人類學有了令人振奮的發展,涌現出一大批諸如蕭兵、方可強、葉舒憲、徐新建、彭兆榮等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對話的優秀學人,使該學科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和重要的歷史新階段。隨著學科發展的不斷推進,傳統的文學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戰,文學研究的眼光也從原有的文字文本,擴展到文字之外的廣闊世界,研究對象也從書寫文本轉向了民間的活態文本、口頭傳統、儀式展演等人類文化層面,這為人類學在文學中的“合理進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從本次中國文學人類學青年學術論壇的代表發言中,筆者發現了兩大轉向:第一,研究對象的轉向。傳統的文學研究者,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有所拘泥,他們很少關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種眼光的缺失。文學作為現實生活的反映,與其社會文化背景有著緊密聯系,如果不關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種文本的解讀都是有失偏頗的。因此,在本次論壇的代表發言中,年輕的文學研究者們把目光更多地轉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從重慶文理學院教師王先勝對中國古代紋飾的歷史解碼,到四川大學梁昭老師對民族志小說的文本解讀,研究的“觸角”都已伸向了傳統文學之外,他們將人類學的視野引入具體的個案研究中,為既有的文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轉向。研究對象的拓寬,勢必帶來研究方法的延展。傳統文學的研究方法,在資料的獲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務虛”。而人類學方法的進入,則彌補了這一方面的缺失。人類學作為一門“務實”的學科,在方法論上強調實證,將個案研究與具體史實相結合,把田野考察作為獲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論是廈門大學博士生張馨凌對鼓浪嶼家庭旅館的人類學闡釋,還是四川大學博士生楊驪談考古學方法論的啟示等等,都自覺地將人類學的學科范式引入具體的個案研究中,從不同角度顛覆了傳統文學研究的窠臼,讓我們感受到了文學與人類學兩門學科聯合起來所釋放出來的理論魅力。所以,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類學轉向并非偶然,它是學術發展歷程中“破學科”探索的理論訴求,這一轉變將對未來的學科發展帶來劃時代意義。其次,“人文社會科學怎么向人類學轉向?”筆者認為這是兩個向度的問題,即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類學轉向并不是單維度的,兩者不是孤立的對象,從學科發展史上看,兩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滲透關系。人文社會科學在借鑒人類學的學科范式,對舊有理論進行補充的同時,也會將自身學科研究中的優秀方法提供給人類學,充實人類學的理論基礎[2]。
在與會代表的發言中,筆者感受最深的是人類學方法論對文學研究的啟示。從文學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開始,學者研究的對象勢必要從書齋走向田野,接觸的材料也從文本文字變成口頭文本、古跡碑刻、儀式展演等等來自民間的活態資料。如何將紛繁復雜的文化事項收集整合起來,這是傳統文學研究無法突破的瓶頸。但人類學方法的進入,使這類問題迎刃而解。結合筆者的田野經歷,田野調查前的文獻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調查中遇到情況是無法通過前期的文字準備所能預知的,這時就必須運用人類學的方法論進行指導。比如研究一個民族的神話,與之相關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環境、民族社會的構成等等都是一個研究者必須關注的。說到細微處,假如我們對某一個碑刻進行文化解讀,除了要對碑刻中的文字進行破譯外,還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狀態,通過考證其所處環境、風水朝向、實際用途、樹碑年代等,還原一個“真實的存在”①,這些都是傳統的文學研究無法處理的。因此,正如水漲船高的道理一樣,隨著文學研究對象的不斷擴大,文學研究方法的理論創新,需要人類學方法論的進入,為學界提供新的思維方式。盡管如此,筆者認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類學轉向不是單向度的,人類學的方法論同樣需要借鑒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優秀傳統。本次中國文學人類學青年學術論壇還討論了一個如何讓學術研究“落地”的問題。人類學作為西方世界的“舶來品”,有著悠久的學術發展史,其學科范式自成體系。當用人類學的方法來處理中國具體的個案時,貼標簽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別是中國的傳統社會,任何一個文化事項,都有其固有的言說方式。而兩套不同話語的碰撞,必然無法回避學術研究的“落地”問題。因此,筆者認為單純的人類學研究如果脫離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支持,也無法為現實的社會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盡管人類學是一門強調田野考察、實證的科學,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結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樣是一紙空文。人類學的學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寫的《菊與刀》為何被奉為經典,除了著作本身對日本民族性格淋漓盡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這本書受益于美國軍方的支持,為戰后美國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標”,僅憑這一點,我們能分清其中人類學與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等人文社會科學的關系嗎?“在地化”②是人類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術語,在此形容人文社會科學向人類學靠攏的過程再貼切不過。人文社會科學需要人類學的理論補充,用以處理具體的文化事項,人類學同樣需要尊重人文社會科學在地方性敘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類學轉向不是一個單純的過程,它包含了兩者不斷融合、不斷互動的歷史。
綜上所述,所謂“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類學轉向”并不是單一的過程。首先,人文社會科學與人類學不是兩個孤立的存在,兩者是交集關系。其次,人文社會科學的人類學轉向,不是要廢除某個學科的研究范式,教條地將某種理論強加于研究對象之上,而是充分地運用各學科在各自領域上的理論優勢,完成既定學術目標。因此,在這一過程中需要一種“破學科”的張力。學術研究不能拘泥于學科間的限制,不能閉門造車,而應該在尊重既有學科范型的基礎上,打破成規,合理地將人文社會科學和人類學并置起來,才能找到未來學術發展的正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