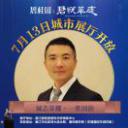文學史解讀論文:對周作人附逆的思想史解讀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文學史解讀論文:對周作人附逆的思想史解讀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陳帥鋒
日偽報刊上,此類言論甚多,比如日偽《晨報》1938年的一篇社論表達了和他為秦檜翻案類似的意思:痛恨于黨政當局人才之缺乏,盲動禍國,雖欲求一秦檜式之策士而不可得也。黨府當事變前所處境地,外有強鄰,內有赤匪,何其神似明末之時勢耶?自審貧弱,便應和親。黨府干部重任,稍有明于世事者,外附浮議,內懼覆亡,稍露和平之論,便遭國共黨匪之打擊,此又何其神似“賈似道主和而旋又諱之”之情景耶?嗚呼!千秋是非,豈“少不更事”者所與知?
另外,1938年汪偽立法院長溫宗堯在《庸報》上公開表示宣傳自己與日本合作不是漢奸傀儡:宗堯不敢曰,有過人之處,然亦不敢曰,無眾人之常識也。今日與日本合作,必不免傀儡漢奸之唾罵,此乃眾人常識之所及。宗堯豈無此常識?豈不愛七十二之衰年?豈不念閉門十八年之灰心絕望,乃忽出而與日本合作?豈以傀儡漢奸為美號,而樂取之耶?宗堯不若是之愚也,則必有不得不出之故今日之出,自積極言之,則不忍舉中國以聽之永葬自消極言之,即不能為救國之志士仁人,亦決不至如世人所慮為賣國之漢奸。蓋國已為所斷送,已為人所占領。昔者國為我有,宗堯居其位操其權,尚不忍賣;今者國為人有,尚何所賣?能賣國斯可尊之曰漢奸,以與日本合作者為秦檜,是認已經斷送之地,為南宋偏安尚保存至地也。不惟宗堯一切與日本合作者,皆不敢妄蒙此尊號也。12(標點為引者所加)溫宗堯所謂“自命上流無補于實際”,與周作人“道義之事功化”說法邏輯一致,貌似高明,但正如戰時一篇批判周作人的文章所指出的,“自古出賣名節的人總有一大篇大道理可說,這就是既能屈身,又何患無辭呢”。13審判漢奸時偽宣傳部長林柏生辯護道:“許許多多生長或留落在淪陷地區的老百姓,不能不需要自己的同胞來照料,而寧可受敵人的踐踏,或者乞憐于猙獰面孔的假慈悲。有了他們,便得有為他們照料的有一群他們。”14據此邏輯,偽方體察百姓之苦,貢獻民族良多。但日本人之所以要偽政權,正是因為自身無力控制,所以需要“以華治華”,建立傀儡政權,幾乎是大多數侵略者的權宜之計,所以偽政權之實質就是為虎作倀,以“中日親善、東亞共榮”等假相瓦解人民斗志。從戰爭的角度來看,還涉及輿論宣傳。周作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聲名決定了他不可能置身事外,即就1938年日軍組織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而言,周氏出席與否不僅關涉個人是非,同時也牽涉交戰雙方的“事功”。對日本侵略軍而言,需要維持秩序、粉飾太平,而從抗戰一方來說,則要揭露真相、呼呼抵抗。正如郭沫若所說:“日本信仰知堂的比較多,假使得到他飛回南邊來,我想,再用不著要他發表什么言論,那行為對于橫暴的日本軍部,對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舉國為軍備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無上的鎮靜劑吧。”15而姚蓬子的文章更清楚地指出:“便是如某博士所說,留在北平可以研究學問這一理由罷。這理由促看也顯得冠冕堂皇,實際卻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在日本軍閥血腥的指揮刀下,能夠讓中國人有思想的自由,研究學問的自由嗎?我們也知道留在北平的這部分教授們,精神上或許是怪痛苦的,但僅僅痛苦并不能避免被日本軍閥所無形的利用,那這種痛苦還是不能得到中國人民的絲毫原諒的。”16周作人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事雖非萬惡,但事實上是協助了日偽的宣傳。文協給周作人的公開信力陳此中是非:“我們每聽到暴敵摧殘文化,仇害讀者青年,便慮及先生的安全。敵軍到處奸殺搶劫,已表現出島國文明是怎樣的膚淺脆弱;文明野蠻之際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惡,殊欠明允。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察熟慮,為先生告者。”17周案發生后,后方文化界很多人對周作人的人格多有批評。李金發就用“文人無行”這樣一個俗語來評價周作人,他感嘆:“但是我以為萬一真的日本人會亡中國的話,我不相信不會沒有如首陽的伯夷叔齊,食元祿的許衡,趙復,做開國元勛的徐乾學,殘殺同胞而成功之曾國藩,左宗棠,以身殉董卓之蔡邕的文人出頭在社會上,不過漢奸一多,我們就以為是名士忠臣而不為怪了。我們身為文人,可不戒慎恐懼也乎哉!”18獨孤旦則指出:“老中國文士正義感并不是怎樣薄弱,薄弱得像抗戰以來的一些有體面的文壇知名之士,舉個例說吧,在從前的學人(分不開文學合文學以外的界線)到了氣節的關頭,順逆正反的表示是絲毫不茍且的,——若是茍且了呢,那就歸到‘文人無行’一類里去了,這在他們互相間是有一個共同系維的東西,我們最好用‘知恥近乎勇’做這種系維的解釋。逆反的人是大家羞與為伍的,因為他喪失了人格,毫無羞恥了。”19這里所借用的倫理依據都是傳統的道德資源,即“節氣”、“道義”,而且這種歷史資源的借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周作人顯然不以傳統的節氣觀為然。他的“晚明想象”(道義事功化)在邏輯上與五四的歷史文化批判相仿。在他看來,晚明文人的抵抗之聲,不過是封建的思想。“上邊所根據的意見(道義之事功化——引者按)可以說是一種革命思想,在庸眾看來,似乎有點離經叛道,或是外圣無法,其實這本來還是出于圣與經,一向被封建的塵土與垃圾所蓋住了,到近來才清理出來道義之事功化本是小問題,但根底還是在那里,必須把中國思想重新估價,首先勾消君臣主權的倫理觀念,改立民主的國家人民的關系,再將禮教名分等舊意義加以修正,這才可以通行。”20簡言之,這是和傳統的“南渡經驗”剛好相反的一種歷史理解,南渡經驗所包含的“節操”在周作人那里毫無價值,而成為“愚忠”,他以“國家人民”關系來處理,無需對抽象的國家負責,而只需對民眾負責,據此邏輯,事偽——即在日本人手里維護人民利益,因此是忠于人民。周作人的論說中含有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立場,因而具備很大的迷惑性。他的邏輯起點是五四的歷史文化批判,在事偽期間的一些論題和以前的變化并不大,比如在對婦女兒童等問題上,他堅持并深化了五四的主張。1930年代后期的中國,“救亡”的呼聲高起,恐怕不單是左翼宣傳、舊思想復活的結果。他附逆后的種種辯說,與其說是騙人不如說是騙己。這里最為極端的一個例子,就是替秦檜翻案,他的思維過于簡單,單從反對愚忠、駁斥節氣、情操等舊道德,是很有見地的。但在國難當頭的歷史語境之下,這樣的見地卻并非“少數的真理”,此時的罵秦檜、頌文天祥其目的不是復活舊道德——而是救國難。五四思想啟蒙的進程中,有一條線索就是“公民意識”,陳獨秀的《我們究竟該不該愛國》《愛國心與自覺心》等文章,并非是籠統地批判“忠臣”這樣的觀念,而是進一步明確公民與國家之關系。換句話說,面對當時的政治現狀,啟蒙者們的思路是把公民的責任從對政府的具體服從中抽離出來,個人主義并非完全超脫民族國家。馮雪峰就認為,“照我們看來,現在是這一種德行——節操,得到了廣泛的自覺和輝煌地發光的時代”21。
抗戰與五四的差距不僅是在時間上,時代的中心議題也是不相同的,此時向民間、向傳統借助資源和五四時期向域外借助資源一樣,是歷史邏輯的必然相反,無論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將抗日與建國并舉還是文協等文化團體將五四傳統與時代結合起來,都標示著一種新的時代命題的產生。而對周作人而言,萬事如常,甚至為文的方式——讀書,寫文章——也一如既往,不能不說是極其遺憾的,茅盾等人給他的公開信就指出了這一點,“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動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來對中華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圖書,與世隔絕之人,每易患此精神異狀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態度之超然,深得無動于心之妙諦,但對素來愛讀先生文學之青年,遺害正不知將至若何之程度”。南渡諸人對于周案的意見并不一致,主要意見有三種:維護、存疑、批評。朱光潛與左翼文人的爭論,已廣為人知。簡言之,周氏出席日方座談會的消息傳來,何其芳撰文評論:“比如去年秋天,我風聞日本人要弄周出來了,就告訴一位害了多年的肺病的朋友,他說他不會。而且遞給我一本《宇宙風》看,那上面刊著周的一些短信,有的說希望南邊的人不要把他當李陵看,應該看作蘇武表面上看起來那些話是凄慘的,但骨子里卻是胡涂。他既不是國家派遣到異域去的使者,而且現代的‘匈奴’又沒有扣留他,我們無法把他當作蘇武。至于家的問題呢,南邊雖說沒有舒服的風雅的‘苦雨齋’,卻有無數的人在活著,在流亡著,在工作著。寬大的人頂多只能說他是‘被拉下水’。然而他為什么要坐在‘苦雨齋’里等著被拉呀?這是值得找出一個答案來的。長久地脫離了時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使他胡涂到想在失陷的北平繼續過舒服的日子,因此雖說他未必想出賣祖國以求敵人賞賜一官半職,也終于和那些出賣祖國的漢奸們坐在一起了。”27何氏的批駁極為銳利,要害之處在于指出“脫離了時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這其實也是很多人的看法。朱光潛撰寫了文章有所維護,文中援引了俞平伯的來信,認為周氏是上當參加座談會,實際上并未事偽,并且不要像明末東林黨人逼阮大鉞事偽一樣待周。茅盾則反駁道:“我想提起朱先生的注意,說東林名士逼阮大鉞走上附逆之路的明末議論原來是偏袒阮大鉞的人們的‘發明’,朱先生既以公正自居,這一史例的引用還待斟酌罷!”并且特意指出:“‘全文協’早就看見后方還有不少的‘周作人氣質’和‘周作人主義’的文化人,覺得他們的力量不拿出來幫助抗戰,太可惜了。特別他們還是‘青年的指導者’,所以更覺擔心——是這樣觀感的蘊已久,沉痛已甚,這才周作人事件一來,會引起了那樣大的刺激,很‘不世故’地發了通電。”28這就進一步點出了當時討論周作人事偽事件的話外之意,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涉及到抗戰時30年代的左翼與京派、抗戰時“與抗戰無關論”的討論等一系列討論,這些討論所處理的實際上就是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這并不是皮相的文學是否隸屬政治,而是文學能否超離政治,而后者正是“京派”的文學主張之一。沈從文1940年9月在《國文月刊》上發表了總題為“習作舉例”的一組文章,其中《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由冰心到廢名》兩篇引起了左翼人士的批評。爭議主要有兩點,一是沈從文文中對周作人附逆只是輕描淡寫:“似因年齡堆積,體力衰弱,很自然轉而成為消沉,易與隱逸相近,所以曹聚仁對于周作人的意見,是‘由孔融到陶潛’。意即從憤激到隱逸,從多言到沉默,從有為到無為。精神方面的衰老,對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因之嗜好是非,便常有與一般情緒反應不一致處。二十六年北平淪陷后,尚留故都,即說明年齡在一個思想家所生的影響,如何可怕。”29他對周氏的文章仍很推崇,比如認為周作人《自己的園地》“談文藝的寬容,正可代表‘五四’以來自由主義者對于‘文學上的自由’的一種看法”。30又說俞平伯“文章風格實于周作人出。周文可以看出廿年來社會的變,以及個人對于這變遷所有的感慨,貼住‘人’。俞文看不出,只看出低徊于人事小境,與社會儼然脫節”。31其二,在文學上推崇周作人而貶抑魯迅:“周作人作品和魯迅作品,從所表現思想觀念的方式說似乎不宜相提并論:一個近于靜靜的獨白;一個近于恨恨的詛咒。一個充滿人情溫暖的愛,理性明瑩虛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個充滿對于人事的厭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憤激,易惱怒,預言轉見出異常天真。”“對社會去退隱態度,所以在民十六以后,周作人的作品,便走上草木蟲魚路上去,晚明小品文提倡上去。對社會取迎戰態度,所以魯迅的作品,便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32左翼人士對此很不滿意。前引茅盾的文章已經道出,他們不僅要聲討附逆的“周作人”,還要清算“周作人主義”。姚蓬子指出,“我們需要前仆后繼的,踏著同胞們的血沖上前去,而作為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孫的教授們,豈不是負有領導的責任嗎?然而,我們留在北平的一部分教授們的夢想,卻是在敵人血腥的屠刀下研究學問”。
某種意義上就把傳統的“節操”落實為具體的行為,即在民族危難時刻,個人對于國家有絕對性責任,文人不能超脫于這個責任之外而追求自己的“志業”。孔另境則認為:“從他近來數年來表現給我們看的姿態和他的家庭關系交往關系來看,他決不是一個堅決支持抗戰的人,即使他還剩留一些早年的民族思想,對抗戰并不持反對的態度,然而也是悲觀的。所以最近的曹聚仁先生和前些時的一些對周先生還存著熱望的人們,勸他從速南來,和蘇武一般的持節南歸,我總覺得那是一些廢話。即使他果然南來了,甚或至于原本居留在南方的,都一樣不能改變他的一種悲觀的謬見。(著重號為引者所加)”這里就點出了要旨之所在,即左翼文人對周作人附逆的批判,內在蘊涵了對抗戰無關論者的批判。認為周作人主義是一條危險的道路,唐弢則認為周氏的“隱逸”不過是為了“出山”而已,“志士謀國,功敗垂成,匿跡以求再逞,這正是積極的斗爭,書生遭變,求死不得,高蹈以事播種,這也不失為消極的反抗。即使毫無作為,真能像蘇武那樣的‘苦住’幾年,也不失為自愛的一種。棄家既有所不能,‘苦住’又有所不能,這就自然會摜掉木魚,拿起鋼鑼,趕著去開路喝道,撰《中國文藝》之稿,理‘東亞文協’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