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文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漢字文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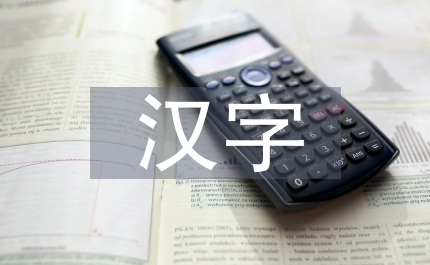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語言文化熱的影響下,漢字文化研究逐漸形成一股熱潮,一批中青年學者紛紛著書立說,表現出對漢字文化研究的極大興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不容否認,這些研究還缺乏應有的深度,其中多數是對某些個體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現象的孤立描寫,一些著作在具體操作時還經常出現種種失誤,缺乏必要的科學性。問題的關鍵在于,漢字文化研究的理論探討還十分貧乏,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論問題,如漢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漢字與文化關系的解說、漢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還存在著許多模糊的認識。因而,迅速進行理論建設,是當前漢字文化研究的當務之急。
一、“漢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確界定“漢字文化”的概念,科學解釋漢字與文化的關系,是漢字文化理論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目前,人們對于“漢字文化”概念的界定,雖然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漢字文化的某些特點,但總體的研究力度還不夠,挖掘還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們認為,界定“漢字文化”應該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著眼。宏觀的漢字文化,是指漢字的起源、演變、構形等基本規律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微觀的漢字文化,是指漢字自身所攜帶的、通過構意體現出來的各種文化信息。宏觀的漢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觀的漢字文化基礎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驟上,應從微觀起步,逐步積累材料,總結規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觀的研究上。但微觀的研究并不是對單個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從整個漢字系統出發,著眼于宏觀的背景,并以宏觀的研究為最終目的。無論是宏觀的漢字文化研究,還是微觀的漢字文化研究,都必須圍繞漢字這個中心,要以漢字的自身因素為根本的出發點,而不能脫離漢字,把本不屬于漢字的東西生拉硬扯進來。
科學解釋漢字與文化的關系,必須首先了解“漢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質。就漢字而言,它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體系,它的產生,主要是為了滿足有聲語言的不足。對此,清代陳澧曾做過精彩的描述:“蓋天下事物之眾,人日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成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構成之者也。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1](P8)意義是抽象的,是感覺器官所不能感知的;聲音是一縱即失的,只能作用于聽覺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視覺器官,它雖然能夠成為意義的符號,但在技術落后的古代,卻無法傳之異地,留于異時。而人類社會的日益發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廣泛的時空范圍內進行思想交流。這種需要,促成了文字符號的誕生。漢字作為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以一種特殊的符形將漢語的意義和聲音物化下來,從而擴大了漢語的交際功能。可見,漢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記錄漢語,是否與漢語的詞相對應,是判斷某一符形是否為漢字的決定性條件。漢語是各種社會文化的載體,漢字記錄了漢語,因而也就與文化發生了聯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會文化的復雜性,對“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為難題,各家之說竟多達幾百種。有人認為文化專指人類的精神活動,有人認為文化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個方面,也有人認為文化泛指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我們比較傾向于17世紀德國法學家S·普芬多夫的說法。他認為,文化是社會人的活動所創造的東西和有賴于人和社會生活而存在的東西的總和。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會生活的物質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總和。根據這個定義,漢字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現象,是整個社會文化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漢字”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應該是上下位的種屬關系。然而,在社會文化結構中,漢字這一結構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發生關系,所以“漢字”與文化的關系,并不僅僅表現為漢字與整個文化體系的關系,而更多地表現為漢字與整個文化體系中除漢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關系。關于這一點,王寧先生曾作過明確的辯證:“‘漢字與文化’這個命題實際上屬于文化項之間的相互關系范疇,具體說,它是指漢字這種文化項與其他文化項之間的關系。文化項之間是彼此有關系的,在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時,一般應取得一個核心項,而把與之發生關系的其他文化項看作是核心項的環境;也就是說,應把核心項置于其他文化項所組成的巨系統之中心,來探討它在這個巨系統中的生存關系。如此說來,‘漢字與文化’這個命題,就是以漢字作為核心項,來探討它與其他文化項的關系。”[2](P78)許多學者談漢字與文化的關系時,總是籠統地將“漢字”和“文化”這兩個概念簡單地對應起來,讓人覺得漢字似乎是獨立于文化之外的,這種割裂“漢字”與“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漢字在整個文化體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種文化項之一,又是書寫和表達其他文化項的載體。它通過記錄語言中詞的方式,保存了詞的意義所反映的各種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項之間建立了極為密切的聯系。漢字的悠久歷史與其跨時代性的特點,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價值,成了研究歷史文化及其變遷的重要依據。漢字與文化的這種密切聯系,使得二者之間具有著特殊的互證關系。人們既可以從漢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漢字的起源、演變及其構形等各種規律中所包含的整體文化特質和具體文化信息;又可從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漢字,探討其他文化項對漢字自身發展規律的影響。漢字自古至今一直頑強地堅持自己獨特的表意性,始終沒有割斷同文化的聯系,這使漢字文化的研究對各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定的適用性。因此,漢字文化研究不僅在理論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實踐上具有可行性。
二、“漢字文化”與“漢語文化”的區別
在漢字文化研究領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漢字文化”和“漢語文化”這兩個基本概念,將漢語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內涵當成漢字文化現象來研究,從而影響到漢字文化研究的科學性。
其實,“漢字文化”和“漢語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著各自不同的內涵。漢字和漢語雖然同是文化的載體,但二者之間卻存在著本質差別。就其構成要素來說,語言只有音、義兩要素,而文字則有形、音、義三要素。漢字的音、義要素是從漢語那里承襲過來的,而形體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獨有的。字形雖然與音義有關,但卻有著自己獨立的作用和價值,具有自身的構造規律和系統。這就決定了漢字既與漢語有密切關系,又與漢語有著本質的不同。漢字與文化發生關系,一方面是以漢語為中介的,即通過記錄漢語而成為文化的載體;另一方面,由于漢字形體的特殊性,使得漢字具有了漢語所不具備的文化功能。漢字是表意文字,特別是早期漢字,形體與所記事物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人們可以從字形當中,窺探出與所記事物相關的文化信息,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詞義能夠反映的,有些是詞義所不能反映的。從主觀上講,漢字構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記錄漢語中的詞,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詞義之間建立聯系的一種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說,人們采用表意構字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據形知詞,而不是據形知物。但從客觀結果上看,漢字的表意構形不僅記錄了詞,而且還記錄了除詞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記錄了“王”這個詞外,還以其像斧頭之形的構形告訴人們,古代統治者是靠武力統治天下的。這些信息,由于遠古文獻的貧乏,我們無法從“王”的詞義本身獲得。在最初造字時,古人并不是有意識地要將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當時統治者必然擁有武器,人們看到武器極易聯想到擁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為記錄“王”這個詞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詞義之間建立一種明確的聯系。后來,統治者的形象發生了變化,“王”的詞義也隨之改變,人們通過“王”的詞義本身已無法了解到古代統治者的特點,而“王”的字形則成了古代統治者形象的歷史見證,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價值。由此可見,漢字的文化功能實際上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于漢語中的詞,一個來源于漢字的自身形體。前者是漢語的文化功能在漢字形體中的物化,是與漢語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應歸于漢語文化的范疇。后者是漢字自身所獨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漢字文化。
在具體研究中,不少人把漢語文化貼上了漢字文化的標簽,把許多本屬詞匯范疇的現象也歸到漢字身上。如有人在名為漢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說文》“牛”、“馬”二部字多的事實,去印證我國古代曾經歷過畜牧業時代。我們且不說這種印證有何實際價值,僅在理論上,就存在著混淆漢字文化與漢語文化的傾向。“牛”、“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當時語言中與牛、馬有關的詞多,除此之外,漢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對“牛”、“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現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詞匯文化問題,而不能稱為漢字文化。假如把屬于詞義的東西都歸于漢字,漢字的文化功能就確實無所不包了。如果這樣的話,任何文字都是記錄詞義的,因而也就必然記錄文化,那么,漢字與其他文字還有什么不同之處呢?我們研究漢字的文化功能,必須從漢字的特殊構形出發,只有這樣,才能發掘出漢字文化的本質特點。
三、漢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對漢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準,甚至隨意夸大,是目前漢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個較嚴重的問題。不少學者受“漢字優越論”的影響,將漢字夸得神乎其神,說“漢字是一串怪異的密碼”,“是古代社會的活化石”,“每個漢字都成為了一定文化的鏡像”。這些說法明顯與漢字文化功能的實際量度不相符合。
漢字與文化之間雖然存在著互證關系,但這種互證關系并不是完全對等的。從總體上來講,文化對漢字的證明功能要大于漢字對文化的證明功能,因為漢字畢竟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而且是歷史積淀的產物,盡管它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但它并不具備細致描寫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備最終確認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備確認文化所屬時代的功能。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漢字文化研究時,一定要對漢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認識,準確把握漢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隨意加以夸大。在這方面,王寧先生等人所著的《〈說文解字〉與中國古代文化》可謂成功的典范。該書《前言》中明確表示:“漢字中所貯存的文化信息,只能從每個字的構形——一個小小的方寸之地,簡化了的線條、筆畫,以及字與字的關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從自己的主觀臆測出發,弄出許多玄之又玄,廣之又廣的新鮮事來,其實是難以說服人的,也就把《說文解字》與中國古代文化這個題目給糟蹋了。”[3](P2)
漢字創造的最初目的是為了記錄語言,而不是為了細致描寫文化。漢字字形所體現出的除詞義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創造過程中的副產品。如果將這種副產品上升為其主要功能,就會導致對漢字本質的誤解。受夸大漢字文化功能觀念的影響,一些學者不能正確擺放漢字的位置,不能正確看待漢字和文化的關系。他們不是把漢字看作記錄漢語的工具,而是把它當成了考證和確認文化的靈丹妙藥,試圖通過漢字構形去構建整個中國古代文化史。于是,他們任意夸大漢字的文化功能,將本來毫無聯系的漢字構形和文化現象牽強附會在一起。如有人說:“它的存在無疑是一個活化石,能使我們透過文字的靜態形體步入到古人動態的文化意識中去,把文字內蘊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經濟、宗教、藝術觀念以及古人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認識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來。漢字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征,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漢字比喻成中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說它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華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漢字字形當中找到根據,這無疑是對漢字文化功能的過分夸張。我們認為,漢字構形當中確實保存著不少有關古代社會狀況的文化信息,但漢字并不具備細致描寫文化的功能,它對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僅靠漢字構形無法確認文化,更無法全面構建古代的文化系統。
漢字構形系統是歷史積淀的產物,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逐步形成的,這就決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強的歷史層次性。但當漢字積淀為一個完整的構形系統時,這種歷史層次性已深深地隱藏在整個構形系統的背后,變得很難甚至無法考察了,因而也就無法運用漢字去確認文化所屬的時代。漢字構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現象,究竟應歸屬于哪一歷史層面,是很難有確切的結論的。這就要求我們在運用漢字考證文化時,一定要持謹慎的態度,要盡可能排除主觀隨意性,在漢字構形和文化現象之間建立起客觀、真實的聯系。有人不了解這一點,而是籠統地不分時代層次地去考察漢字的文化功能,其結果只能導致錯誤的結論。如同樣是《說文·女部》字,有人根據從女的字多,認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從漢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證明。《說文》中女部下面有258個字,可以看出早先婦女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5];又有人認為,女部中的“大量貶義詞,反映了古代社會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視受侮辱”[6];為什么會有如此差異的結論呢?問題的關鍵在于《說文·女部》字本身的復雜性,它們決不可能是同一時代產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個時代的社會觀念。究竟哪些漢字起源于母系社會,哪些漢字起源于父系社會,現在已無法考察,所以,單憑女部字,既不能證明“早先”婦女的社會地位高,也不能證明“古代”社會女子地位低。《從女偏旁字看古代婦女的尊卑嬗變》一文[7],更是試圖通過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婦女地位的演變史。作者認為,我國古代婦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地位極尊,從商代開始由尊向卑轉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極卑,這種演變過程都可以在漢字構形中找到證據。作者似乎對哪個字起源于什么時代、反映哪個時代的文化現象胸有成竹,但實際上,他在證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婦女地位高時,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證明商代是婦女地位的轉化期時,用的還是甲骨文;甚至在證明西周時期婦女地位低時,仍然用甲骨文就已產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的現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現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預先反映了西周時期的現象呢?這種缺乏歷史觀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漢字是一個符號系統,每個字符的存在都受著系統的制約,它既以某種方式與其他字符相聯系,又以不同的構形與其他字符相別異。聯系和別異是每個字符存在的兩個必要條件,是漢字符號的本質內涵。漢字符號的系統性特點要求我們在分析漢字構形時,一定要從系統性原則出發,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單個字符。有些學者受夸大漢字文化功能觀念的影響,總是戴著有色眼鏡去審視漢字字形,習慣于到字形當中去為某種文化現象尋求印證。如有人認為甲骨文“母”字中的兩個指事符號象征“胸前兩乳十分發達”,并據此論證原始社會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們認為這種論證是十分牽強的。漢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類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顯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將相類似的事物區分開來。如“牛”、“羊”二字的構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個向上彎、一個向下彎的特點,從而使二字的形體有了明顯的區別。“母”字的構形之所以突出兩乳,也是出于與其他字符相別異的考慮,因為“女”字所表示的母親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難區別,除了母親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較為發達外,其他特征很難在字形中體現出來,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礎上加上表示乳房的兩點,作為“母”字的構形。這種構形,既保持了與“女”字的聯系,又體現了與“女”字的區別,顯然是為了滿足漢字構形系統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見,漢字是一個具有嚴密系統性的符號體系,每個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個系統制約的。因此,我們不能為了一時方便而胡亂講字,否則就會造成講了一個亂了一片的嚴重后果,給讀者造成困惑。
總之,“漢字文化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不能違背漢字的發展規律,也不能違背文化的發展規律。漢字文化學是科學,不是幻想,更不是個人無根據的聯想和猜測。”[9]漢字構形確實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但是,我們在研究漢字文化時,一定要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用謹慎的態度去操作,要樹立正確的漢字文化觀念,準確把握漢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漢字的構形;要明確漢字文化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弄清漢字文化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能夠解決什么問題,正確認識漢字文化學方法的適用對象,避免出于趕時髦心理的隨意濫用。只有這樣,才能使漢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確的體現。不過,要想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堅實的漢字學功底,又需要有較高的文化學修養,兩個方面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1]陳澧.東塾讀書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2]王寧.漢字與文化[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6).
[3]王寧,等.《說文解字》與漢字學[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4]李逢甫.漢字的文化積淀[J].黔東南民族師專學報,1996(3).
[5]陳建民.語言與文化漫話[J].宏觀語言學,1992(1).
[6]何毓玲.從《說文·女部》窺古代社會之一斑[J].古漢語研究,1996(3).
[7]殷寄明.從女偏旁字看古代婦女的尊卑嬗變[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5).
[8]李家祥.原始生殖崇拜在甲骨文中的表現[J].貴州文史叢刊,1995(2).
[9]王寧,等.《漢字與文化叢書》總序[A].《說文解字》與漢字學[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