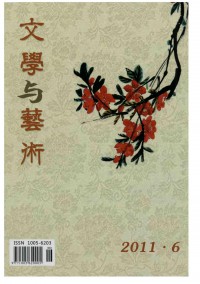辜鴻文學觀念教育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辜鴻文學觀念教育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辜鴻銘最看重文學中的道德內涵,他有關文學的一些精辟之論常常為道德本體的文學觀所遮蔽、沖淡,甚至改造。辜鴻銘發出“惟詩貴有理趣,而忌作理語耳”的議論;提出適合于各民族文學研究者對于異族文學進行高層次研究的文學“整體研究觀”;極力捍衛中國傳統文學及文言文的地位。但是,他的道德人文觀念已經滲透到他所涉及的各個話題中,其文學批評已經很難回歸到文學軌道。從辜鴻銘對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所展示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背景而言,他是一個當然的文學家;但從文學觀念方面說,他更多地體現出一個道德家和社會工作者的本色。
[關鍵詞]辜鴻銘;文學觀念;道德教化
Abstract:GuHongmingheldthemoralcontentinliteratureinthehighestregard,andhistrenchantcommentaryonliteraturewereoftenovershadowed,dilutedoreventransformedbyhismoralliteraryview.Heonceremarkedthat“Poetryshouldbeofrationalisticinterest,butbevoidofrationalistjargons”;headvancedthe“wholeviewofstudy”thatissuitableforscholarsofnationalliteraturestoengageinhigh-levelstudyofothernationalliteratures;hetriedhisutmosttosafeguardtheposition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andlanguage.Yethismoralliteraryviewhadpenetratedintoeachandeverythemehetouchedsothathisliterarycriticismcouldhardlyreturntoitsdueliterarycourse.Fromtheknowledgestructureandculturalbackgroundshowninhissocialcriticismandcivilizationcriticism,Guwasnodoubtamanofletters,butwithrespecttohisliteraryview,hewasmoreamoralistandsocialworkerthanawriter.
Keywords:GuHongming;literaryview;morality
辜鴻銘專文討論過“文化教養”問題。跟討論許多問題一樣,出于一種多少有些偏執的人文關懷,他熱衷于在相當廣泛的文化傳統和道德教化意義上實施賣力的和賣弄式的鋪展。他將文化教養問題分別從外在形式和內在含義兩方面作了這樣的鋪展,認為文化教養的外在表現形式乃是禮儀,而內在含義就是有關天、地、人—神、自然、人生的整體知識,抵達這種文化教養的途徑就是文學,雖然他的文學,特別是他所說的中國文學,完全包括孔子的學說,不過從他對歌德、華茲華斯等歐洲文學家的援引可以看出,他的文學概念還是比較清晰和現代的,他的關于文化教養的理解較多地倚重于文學[1]289-291。從文化教養的意義上說,將辜鴻銘稱為一個文學家不僅恰如其分,而且似乎也勢在必然從他對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所展示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背景言之,他是一個當然的文學家,一個批評本體的文學寫作者。但從文學觀念方面說,辜鴻銘則疏離了文學家的角色,而體現出一個道德家和社會工作者的本色。
一
如果對他幼稚的政治見解持原宥態度,將辜鴻銘還原為一個文學家,則我們自然希望這位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飽學之士即使不持有公允、辯證的文學態度,也應具有老到、持重的文學觀念,能夠將一般的文學評價融入他的文學批評,使得通行的文學價值感在他富有才情和魅力的批評性表述和實際文學操作中得到正常的體現。然而這樣的希望經常落空。辜鴻銘無論是政治批判還是文學批評都遠離公允與辯證,在文學觀念上更力避任何世故、老到與持重,這個不甘平庸的文學家愿意以自己的偏激乃至錯誤兌換各種庸常的文學價值觀,于是他的許多文學理論都顯得兀然不群,奇崛怪異。
辜鴻銘最看重文學中的思想內容,更具體地說,看重文學中的道德內涵,他有關文學的一些精辟之論和真知灼見常常為這種道德本體的文學觀所遮蔽、沖淡,甚至改造。辜鴻銘在西方文學家中喜歡引述華茲華斯,在中國文論家中比較欣賞袁枚,但對這兩個文學家的某些持論都十分不以為然,因為他們都在一定意義上注重文學形式,貶抑文學道德本體內涵的價值,這樣的觀念無論如何難以為辜鴻銘所接受。他反駁華茲華斯強調文學形式的觀點:例如孔子早期的作品,在形式上并未達到完美的程度,但“它們被視作經典或權威作品,主要不是因其文體的優美或文學形式的完善,而是以它們所蘊含的內容的價值為準繩的”[1]129。也就是說,辜鴻銘得出了內容才是文學作品價值的決定性因素的結論。這樣的內容基本上與道德教化有相當的關系,于是他先對袁才子的文學觀提出了本乎道德本體論的質疑:“袁簡齋謂詩論體裁,不論綱常倫理,殊非篤論。詩固必論體裁,然豈無關綱常倫理乎?”[1]235
在引述前人的基礎上,辜鴻銘發出了“惟詩貴有理趣,而忌作理語耳”的議論。應該說這番議論十分精彩,它輕而易舉地解決了中外古今文論史上的一個詩學難題,那便是如何處理詩歌中的哲理內涵問題。自古以來,東方西方,人們都注意到詩歌中哲理內涵的復雜性,既不便貿然肯定與強調文學特別是詩歌中的哲理因素,又很難像后來的中國詩人郭沫若等那么毅然決然地否定詩歌中的理性成分。郭沫若曾就有關這一話題在《創造季刊》發表兩則內容相聯系的“曼衍言”:“耶穌說:有錢的人想進天國,比象鼻穿過針眼還要難。有學問的人想進藝術之宮,也是如此。”“概念詩是做不得的,批評家可以在詩里面去找哲學;做作家不可把哲學的概念去做詩,詩總當保得是真情的流露。”(《創造季刊》第1卷,第2期)雖然郭沫若說話絕對了一些,但這位有著深厚西方文學理論修養背景的新詩人表達的倒是西方詩學界頗為流行的史學價值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通常所批判的“席勒式”將文學的個人化創作當作時代精神的傳聲筒,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記了現實主義藝術,其實就是以理念沖淡了文學,這是詩學界普遍貶斥的現象。然而,席勒的那種融進了思想觀念和“審美教育”的創作,還是贏得了相當多的讀者和批評家的贊許,贏得了歷史的承認。這說明理念進入作品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到底如何理解文學中的合理的哲理成分,詩學界似乎并沒有統一的和妥當的定論。在這種情形下,辜鴻銘提出文學中可以有“理趣”但不能用“理語”的說法即可以在構思中融入理性的思想趣味,但不能直接進行思想觀念表達應該說是一種很有見識也比較行得通的理論建樹。
“理趣”、“理語”等概念來自于中國古代文論,但辜鴻銘同樣對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論作了建設性的貢獻。一般來說,審慎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家都不會偏激地否認哲理在文學中的價值,至少文學中的理趣得到了普遍的承認。鐘嶸《詩品》序對詩歌中的“理過其辭”現象予以批判:“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對此,清代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分析,鐘嶸所說的這些人詩歌的道德化現象,不過是缺乏“理趣”而已,并不是他們重視詩中理念的過錯,“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尚理之過哉!”劉熙載推崇理趣,主張詩可以而且應該表現理趣,不過不應將理念或哲理生硬地表達出來,且束縛住靈感與想象,那就成了一種“理障”(注:“理障”的概念顯然與明代文論家胡應麟的學說有關,后者在《詩藪》中說:“程邵好談理,而為理縛,理障也。”這里的“程邵”是指程顥、程頤、邵雍這些理學家、道學家以及他們的詩作。)。因此他提倡詩中“有理趣而無理障”,但他沒有清晰地劃分出“理趣”與“理語”的界限,他稱賞“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這里的“理語”就是“理趣”的別稱。辜鴻銘所引述的袁枚也將“理語”含混于“理趣”:“或云:‘詩無理語。’予謂不然。《大雅》:‘于緝熙敬止’,‘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嘗非理語?何等古妙?”(《隨園詩話》卷3)可見,在辜鴻銘之前,古代文論家一般都是將“理語”與“理趣”混為一談。
辜鴻銘富有創造性地區分了“理趣”與“理語”,將理性的思想內核與理性的文學表達區分開來,承認一定的理性思想內核在文學創作中的合法地位,同時認定文學創作的語言表達不應是邏輯的、理念的句式。
問題是辜鴻銘在解決這一中外文論和古今文論的共同難題時顯得那么漫不經心,這倒不是他的故作矜持,而是因為在他的心目中,這樣的理論創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絲毫不準備放棄的包含著道德教化的理趣、理式和理念,他認為文學必須承載包括三綱五常在內的道德教化,即詩教。詩教是辜鴻銘文學觀念的最重要的關鍵詞,作為觀念它十分古老,然而辜鴻銘最感興趣的是它的古老,而絕不是自己的理論開拓與創造。盡管他的一些文學批判出語不凡,但在強調文學的詩教功能的理論前提下,辜鴻銘不需要創造。
二
辜鴻銘提出過這樣的文學研究觀:“一個民族的文學,如果要研究,一定要將其視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去系統地研究,而不能割裂零碎”。這是十分妥當的觀點,適合于各民族文學研究者對于異族文學所進行的高層次的研究。然而,任何富有創見的觀念在辜鴻銘這里都可能包含著詩教的傾向。他接著引用阿諾德的類似觀點對整體研究的重要性作了點示:“無論是全部文學人類精神的完整歷史還是那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只有將其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貫通理解時,文學的真正力量才能體現出來。”[1]127他搬請阿諾德為他的“整體研究觀”張目,實際上就是要以更加有說服力的理論訴諸外國研究者,要求他們正確地對待中國文學,理清中國文學中的“真正力量”。這種“真正力量”就是他要宣說的“仁”、“義”、“禮”等,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春秋大義。這些他真心誠意地向世界推介的“真正力量”,是中國文學“整體研究”的必然結晶。
從保守的方面而言,辜鴻銘一直充任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護師;從積極的方面而言,他一直帶著民族自豪感表達著對中華歷史人文的深深尊重。他關于整體研究一個民族的文化以及注重民族文學真正力量的精辟論述,都是以中華歷史人文作為理想的對象的,正如他在《吶喊》中反復強調的,中國是“君子之國”,擁有“孔子之教”和“君子之道”的文化傳統,“她不僅能拯救自己,甚至可以拯救世界和目前世界的文明”[2]524。這是辜鴻銘關心中國文學并熱烈推介中國文學真正力量的最后動因和根本動力。面對中國文學是如此,面對中國語言也是這樣,他曾針對一些外國人非難中國語言和東方語言的文學表現力的謬論,理直氣壯地提出:“漢語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種詩的語言,它具有詩意和韻味,這便是為什么即使是古代中國人的一封散文體短信,讀起來也像一首詩的緣故。”[1]94為此他舉了大量的例證,分別從漢語表達與英語表達的對比研究中非常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漢語超卓于其他語言的非凡的詩性魅力。他的舉證和分析足以讓一個愿意公平地對待漢語的外國人相信,中國文學是一種“用極其簡明的語言表達深刻思想和深沉情感的文學”,它在“詩意的簡潔”中“帶著一種不可言狀的優雅、莊重、悲愴、哀婉和高貴”[1]94-97。這無疑是有關中國文學和中國語言的一種精辟之論,但這樣的論述在辜鴻銘那里遠不僅僅是學理的,更是一種文化的判斷,或者說是一種民族文化的捍衛。
辜鴻銘的文學態度,特別是對于中國歷史人文精粹部分的中國文學的態度,令人十分敬佩,盡管這其中掩藏著迂腐的德教內涵和平庸的詩教吁求,盡管這種迂腐平庸的東西常常使他的精彩、靈異的文學議論和理論獨創被磨蝕得黯然無光。辜鴻銘是一個文學家,至少將他定義為文學家遠比定義為政治家或哲學家更為準確也更容易為人所接受;但在他自己,卻很少以文學的創獲為自己的歸宿,他的歸宿仍是在德教、詩教以化成天下的人文理想。于是他似乎從不以文學為意,更不以文學為旨,而只是以文學為用。他在用文學的筆法對于社會政治和文明進行批評時,也即他在進行批評本體意義上的文學活動時,他是那么富有神采和才情,文學的性情和靈感伴隨著豐富的文學知識如漫溢的地泉肆意于永不干涸的沼澤;不過他在真正進入文學批評的角色時,由于他并不從心底里認同這樣的角色事實上他哪怕在進行純粹的文學活動,他也還是神情不屬地左顧右盼、東張西望,對于政治,對于歷史,對于各種文化問題和文明現象他常常犯下各種各樣的錯誤,從知識的到觀念的,從文化立場到人文態度。或許有些錯誤,例如知識性的錯誤,可能并不是真正出于辜鴻銘本人,而是出于翻譯者的誤解,例如《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曾提到《女誡》,稱作者是“漢朝偉大的史學家班固之妹曹大家或曹女士”[1]73。《女誡》作者班昭(約公元49—120年),加在前面的曹姓乃是其夫(世叔)姓,無論是按照中國習慣還是西方習慣,處在這種關系中的班昭或許可以稱為曹夫人、曹太太,但斷乎不能稱之為“曹女士”。
如果說關于“曹大家”的別稱可能是翻譯問題導致的知識性錯誤,那么,辜鴻銘對《紅樓夢》等文學經典作出的錯誤性批評就不應由翻譯者負責了。他在對西方人介紹這部不朽名著時,使用了一些“紅外線”資料:“據可靠說法,書中內容是以純粹的事實為根據的它記述的是一個名叫明珠的滿洲大貴族家族的興衰。”[2]359《紅樓夢》是以明珠家族的興衰故事為所本,這是關于《紅樓夢》本事的一種說法,此外還有多種說法并存。辜鴻銘將《紅樓夢》本事落實到明珠家族興衰史,認為此說是“可靠說法”,這樣的判斷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一種結論。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文學家,辜鴻銘應該深知敘事性文學不同程度地帶有普遍的虛構性的特性,認為一部小說,哪怕是真正的自傳體小說,其內容完全是以純粹的事實為根據,這就不是一個精通文學原理的人應有的持論。
辜鴻銘對《紅樓夢》一書總體內容和價值的描述并不準確,批判也過于嚴苛:“《紅樓夢》在寫作手法和風格上與《金瓶梅》不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寫實主義小說。……《紅樓夢》所描寫的是沒有高尚理想的社會生活:上流社會的男男女女,除了吃、喝、穿戴、互相調情之外,沒有一點正經事情……”[2]359如果從消極的意義上去理解這部巨著,那確實是沒有一點正經事情,所有的仕途經濟都被放置于討論的層次上,厚重的人文傳統則被應用于瑣碎的禮儀和日常的雅集與宴樂。然而,為什么一定要在小說中宣說和演繹仕途經濟之道和人文傳統內涵?在日常瑣碎的人生描寫中展示“幾乎無事的悲劇”不照樣能達到高尚的文學境界?更何況,辜鴻銘所相對贊賞的《金瓶梅》中究竟有多少“正經事情”?他最用心的批評都落實在道德評判上,因而他指責《紅樓夢》中的生活內容違反了摩西十誡中的第七條戒律:不可奸淫。而奸淫情節更突出也更惡劣的《金瓶梅》卻免受此責。批評標準的紊亂同樣說明,辜鴻銘對文學并不十分在意,他關注的與其說是文學作品本身,不如說是文學作品中的德教意義和詩教功能。
辜鴻銘不僅對于中國文學作品從德教和詩教的傳統意義上進行批評和品質判斷,對外國文學作品也同樣如此。備受世人贊賞的法國小說《茶花女》,就是因為不符合辜鴻銘的所謂戒律,便遭到如此指責:“在所有譯成中文的歐洲文學作品中,小仲馬的這部將污穢墮落的女人視作超級理想女性的小說,在目前趕時髦的現代式中國最為賣座……”不僅是作品中的人物和作品本身遭到他毀滅性的酷評,連作者小仲馬也在劫難逃。辜鴻銘指責不守婦道的茶花女,不僅使用了中國女性三從四德的標準,而且還參照了閃米特古代女性的理想品德:“如果你將閃米特種族的古想女性,那為了丈夫不怕雪凍、一心只要丈夫穿得體面的女性,同今日歐洲印歐種族的理想女性,那個沒有丈夫、因而用不著關心丈夫的衣著,而自己卻打扮得華貴體面,且最后胸前放一朵茶花腐爛而終的茶花女相比:那么你就會懂得什么是真實的,什么是虛偽的和華而不實的文明。”[1]71
一切的類比都存在著缺陷,道德文化和人格形態的類比更是如此。辜鴻銘在德教的意義上,一時間仿佛成了足以游說全世界的牧師,可以拿任何道德的典例比附和批判任何對象。對于歐洲的女性茶花女,他可以用中國古老的三從四德去衡量,對于歡場人物的茶花女,他可以用古老的閃米特女性的標準行為去規約,他不會覺得這樣的衡量和規約荒唐之至,因為他從來就不善于從文學的立場乃至人性的立場發言,而是從道德教化的宗旨出發。
三
辜鴻銘心目中的中國人文傳統完全保存在文學之中,這樣的認知與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極其相似。白璧德認為西方最有價值的人文傳統都寄植并體現在西方優秀的文學之中,于是他的政治議論、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都基于并有賴于文學分析和文學引述。在這樣的意義上,他們的人文立場自然就偏向于傳統文學這方面,任何關于現代文學和文學革命的倡導,他們都有理由視為一種對于人文傳統的挑戰。白璧德對于中國文化和文學的了解或許僅限于孔子,對于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現實更是非常隔膜,但當他從中國留學生那里得知中國正在進行文學革命運動的信息之后,便毫無保留地勸誡中國人對此須持十分慎重的態度。他的這種觀點和態度直接影響了他的一批中國學生,于是學衡派成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堅定反對者。辜鴻銘與所有持新人文主義立場的中外人士一樣,對中國的文學革命和新文學運動提出了懷疑甚至譴責,他面對世界文壇打出了如此醒目的旗號:“反對中國文學革命!”這是他的一篇文章的標題,發表于1919年7月,接著又發表《歸國留學生與文學革命讀寫能力和教育》,集中闡述了自己對文學革命的反對態度,其時正是文學革命如火如荼的光景。
根基立于文學之上卻無心于文學建設的辜鴻銘,對文學革命的反擊和批判可以說是輕描淡寫的,以他的文化立場和人文態度來說,這場聲勢浩大的文學革命對于他的刺激應相當強烈,他的反應也應同樣激烈,他或許會寫出連篇累牘的檄文對這場在他看來十分荒唐的文學革命運動迎頭痛擊,鳴鼓而批。但事實上他的反應相當平淡,他幾乎是以不屑置辯的冷漠對待這場革命的。確實,對于清算傳統文學和文化的文學革命運動,辜鴻銘有足夠的理由予以蔑視,予以忽略,因為他堅信中國的人文傳統不僅可以拯救中國,而且有朝一日可以拯救世界,作為這種人文傳統核心的中國經典文學和傳統文化,其價值在日趨世界化的運作中還遲遲未能得到顯現,怎么會在一撥人的鼓噪和喧嚷之中就會失去威力和效用?因此,辜鴻銘顯然從未覺得自己應該負起批判新文學、反對文學革命的責任,特別是理論責任;如果不是美國人密勒(Dr.ThomasF.Millard,1868—1942年)辦的《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Review)上刊載有辜鴻銘非常看不慣的“通訊員”對外國人宣揚文學革命的文章,致使他覺得有伸張言論以正視聽的必要,他很可能始終都不會理睬這種在他看來簡直不可理喻、“愚蠢”之極的文學革命運動。
辜鴻銘既然在他的批評策略上并沒有將文學革命列為主要對象,他對文學革命的批判也就不可能全面、深刻,事實上他在有關批判中只觸及了兩個大的問題:一是引進西方文學,另一是白話文的倡導。
在辜鴻銘以及所有具有新人文主義傾向的文學家心目中,講求德教和詩教的中國傳統文學是應該推諸世界并對現代世界進行道德教化的經典,它的崇高地位不容挑戰,更不用說經受革命以及外來文化的改造。在人文傳統價值特別是教化意義上,辜鴻銘對他非常熟悉的西方文學一向評價偏低,除了對世界文學經典如《茶花女》的道德指責外,對19世紀西方一些杰出的文學家也充滿著批判和否定的意味,而正是他所批判和否定的這些作家作品被五四文學革命家們當作先進的文學或活的文學加以舶進,并倡導師事。對此,辜鴻銘深為反感,他告誡胡適等文學革命家們:“在現今被引進中國的新式歐洲現代文學中,在諸如海克爾、莫泊桑和王爾德這些作家的作品中,他們并沒有被帶進活文學;他們被帶進的是一種使人變成道德矮子的文學。事實上,這種文學所載的不是生活之道,而是死亡之道,如同羅斯金所說的,是一種永久死亡之道。”[1]169“道德矮子”語出辜鴻銘未披露姓名的一位美國太太,據說她所著的《北京灰塵》中有“外表標致的道德上的矮子(Prettywelldwarfedethically)”一語,辜鴻銘非常便當且十分得意地將這一稱呼借來用于“愚蠢的”文學革命家,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將這種稱呼用于莫泊桑、王爾德等現代歐洲文學家。
辜鴻銘不僅挑剔現代文學家的作品在內容上宣揚死亡之道,暌違人倫道德和社會道德,而且將文學革命家對白話文的倡導,對文言文的攻擊等行為都定義為道德侏儒的小人行為,他明顯針對胡適等人議論道:“一個身為中國學者的人,能夠說出中國的文言不適合創造活文學的話,他一定是一個……外表標致的道德上的矮子”。這樣的道德矮子“矮到實際上連他們自己語言中的高雅、那種甚至像翟理斯博士那樣的外國人也能夠鑒賞的高雅也不曉得和感受不到”[1]167-170。反對文學革命的論調各種各樣,支持文言文、貶低白話文的文學批評家為數不少,但像辜鴻銘這樣將文言文的否定和白話文的倡導行為直接與文學革命家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品質聯系起來的闡論,確實是非常突兀。由此可見,辜鴻銘的道德人文觀念已經滲透到他所涉及的各個話題之中,他的文學批評很難真正回歸到文學軌道。
在捍衛文言文,否定白話文方面,辜鴻銘除了運用道德武器而外,還從語言文化和社會文明的角度施展出他的辯論才能。他痛斥文學革命家愚蠢,是因為后者那么武斷地宣布中國的文言已經成了“死語言”,并且斷言死語言不能寫出活文學。辜鴻銘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文言并不是死語言,因為它不但不像死語言那樣“粗陋笨拙”、“呆板臃滯”,而且精致高雅,富有生機與活力[1]167,由此他斷言:“正如古典式的莎士比亞英文不僅是合宜的、而且是較好的一種工具一樣,要寫出創造性的文學作品,文言或古典中國語文比口頭語文或白話要強得多”[1]171。同時,辜鴻銘指出,文言文代表著一種值得珍視的人文積累和文明傳統,并不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庸俗價值判斷所能輕易否定的。胡適等人從實用主義的立場指出了這樣的事實:“現代世界上廣泛傳授著比莎士比亞英文更通俗(!)的英文”,對此,辜鴻銘反唇相譏道:“這的確不錯。同樣,在世界各地,面包和果醬的消費比烤雞大得多也是事實,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認為烤雞不如面包和果醬味道鮮美或富于營養,而都應該只去吃面包和果醬”[1]171-172!這樣既從語言文化的特性肯定了文言文的價值,又從社會文明積累的角度確認了文言文的地位。
必須歷史地理解辜鴻銘對文學革命采取的敵對立場。辜鴻銘對于中國古典人文傳統寄予無限的希望,對于中國文學經典投諸很深的情感,面對臆想中的外國讀者,他本著民族尊嚴和文化自信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言辯護。有一位英國人曾這樣貶低包括中國文言在內的東方經典語言:“一接觸到東方各國枯燥乏味的語言,你就會深深地體會到歐洲語言是多么的優美、多么富于表現力。”辜鴻銘充滿義憤地引述了這種妄自尊大的謬論,然后分層次闡述中國文言如何富有內涵的含蓄和意境的優美,如何體現詩意的高雅。他非常有力地反駁道:“富于比喻,富于詩的表現力和意境美,恰恰是中國語言的長處。”隨后他信手拈來地舉出一個例子,一個朋友寫信來,講述分別以來,光陰似箭,久無音訊但一直惦記的意思:“別后駒光如駛,魚雁鮮通,三晉云山,徒勞瞻顧。”引述這段文字之后,辜鴻銘對其中包含的人文意蘊作了淺顯而生動地分析,然后反詰道:“這里難道缺乏詩意嗎?這里缺乏比喻嗎?這難道不可以說在表現手法上已達到了完美的境界嗎?”[1]324此外,他還實驗性地將中國古體詩歌用文言表達的詩歌同勉強翻譯成英文的譯作進行對比,有力地證明中國傳統文言的豐厚人文內涵和高雅精致的藝術表現力。例如“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包含著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蘊和非常悲涼的人生感嘆,可是翻譯成英文以后,這兩句詩就變成“人生中朋友很少呆在一起,就像星星各不相擾發著微光”(Inlife,friendsseldomarebroughnear;Likestars,eachoneshinesinitssphere.)。平面化的英文就像白話中文一樣只能平面地表達詩意,而參商之動所具有的含義是立體的:既表示空間的互不相擾,各自運行于自己的軌道,也隱含時間的流逝和世事的動蕩不安,只有中國文言可用如此簡潔的形式表達如此復雜的、立體化的內涵。當然辜鴻銘沒有闡述得如此詳密,不過他對中國文言的深深的尊崇和捍衛確實基于這樣的感受。
長期耽溺于為中國的人文語言文言進行辯論,面對文學革命的反叛,辜鴻銘很自然地會出于辯護士的角色慣性對否定文言文倡導白話文的運動進行嚴正的抗議,對大規模地引進西方現代文學作品,特別是那些承載和宣揚死亡之道的文學作品持有激烈反對的態度。從這一意義上看,辜鴻銘即使直接充任了文學革命的對立面,他也只是帶著某種人文敵意的文化對手。文化對手通常都是值得尊重并且應該獲得尊重的,辜鴻銘的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與一般的頑固守舊分子并不完全一樣。
[參考文獻]
[1]辜鴻銘.辜鴻銘文集:下[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辜鴻銘.辜鴻銘文集:上[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