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腳之小腳教育從大學門禁一事教育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小腳之小腳教育從大學門禁一事教育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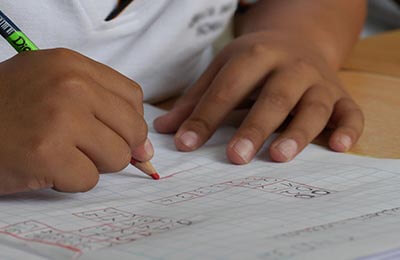
《世說新語·德行》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割"這一動作具有象征意義,其指向的并非簡簡單單的實物草席,而是他二人朝夕相處的統一空間。草席的割裂這一意象所表征的,正是他二人共處的空間的斷裂。細細發掘之,這則典故又可以有兩層意思:其一,空間是權力,它的裂與合代表了拒斥和接納;其二,在此典中,管寧通過對空間的恰當運用規制了自己的感性欲望。
福科在《規訓與懲罰》一書里討論了空間,他認為空間具有規制作用,是一個權力介入的領域。看來這話不無道理,"管寧割席"這則典故即是對之的一極好說明。當然,空間的這種規制作用并不僅僅體現在"管寧割席"上,事實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并且部分的構成了我們的生活。圍墻與長城就是其中的一種形態,前者相對于一個家庭的權力而言,后者則相對于一個國家的權力。再比如說"男女之大防",這就有一些抽象意味了,但還是不難看出空間在其中所起的規制作用。"男女之大防"這一規范的意思說白了,就是男女之間在空間上不得以太接近。"防"的本意是"堤壩",或許也可以用"墻"或"城"代替,當初沒有這樣,大概是"防"字能表現出洶洶洪水的意思。對于空間的規制與權力的最經典的表述是"門"。門的一張一翕,正是代表了接納與拒斥。張,是與外部空間的合二為一;翕,則是對外部空間的否認。這一張一翕,體現了權力與規制的不同姿態。
古代中國很善于運用空間而實現權力介入的目的。一個絕好的例子就是纏足。關于纏足起源的說法,莫衷一是。有一種說法是和南唐后主李昱有關,說李昱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于是李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窅娘以帛繞腳,纖小屈作新月狀,舞于其上,姿態頗為曼妙。唐縞詩:"蓮中花更好,云里月長新。"即因窅娘而作。于是后人以纖小為妙,紛紛仿效之。此之為纏足之濫觴。將纏足的盛行歸因于審美的需要,這種說法是大有問題的,其實纏足真正流行的原因,用林語堂的話說,應該是"纏足是婦女被幽禁、被壓制的象征"。以破壞腳力的方式對婦女活動空間進行間接的限制從而達到對其幽禁的目的,且還以唯美的名義,這就是纏足的本質及其流行的原因。說到底,纏足就是崇拜權力以及壓抑性的產物。福科說,權力壓抑性的同時也增生著性的話語。照福科所言,小腳作為對婦女幽禁與性壓制的象征,被賦予了無限的想象力,基于此而形成戀腳成癖,倒是自然之極。
如同古時大戶人家習慣將女子幽禁于深閨,纏足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在其背后支撐的可能是一些帶有根本性的東西。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帶來了一種新的思考方法,他考察了古希臘人的三個神話,卡德摩斯神話、奧狄浦斯神話以及波呂尼克斯神話,他的結論是,在這些神話中隱藏著一個一致的深層結構,即人類生于大地與人類生于男女這兩個彼此沖突的觀念的調和。如斯特勞斯一樣,從幽禁、纏足以及稍后要談及的門禁中我們能得出的一個一致的深層結構是--權力通過限制空間對性的壓抑。
更進一步,幽禁、纏足及門禁觸及了古代中國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文化結構,這一文化結構從一通俗戒律中反映出來,這一戒律就是"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當先"。"孝"為封建綱常的根本,"忠"實為"孝"的延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或多或少也都與此有關,"孝"的本質是對權力及等級秩序的服從;"淫"的字面意思是"淫亂放蕩",但是如果作寬泛的理解,它可以是人的所有感性方面的抽象或壓縮,是生命的沖動以及創造力。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主旨,《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所以說,纏足的盛行不是沒來由的,它的深刻背景是從孔子的"克己復禮以為仁"到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儒家思想。這一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軸,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統治中,它規制著物質意義上的"足",同時也規制著人們的心靈之足。難怪乎魯迅要說,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滿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橫豎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滿本都寫著"吃人"兩個字。而這個被吃的"人",則正是那個張揚生命、崇尚創造的大寫的人。
有一句話說得好,"見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如此,見步履蹣跚之小腳女子便可知步履蹣跚之小腳中國了!而步履蹣跚之小腳中國必有步履蹣跚之小腳教育。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素來很重視教育。根據殷墟甲骨文中的記載,早在殷商時期,學校已經產生。周代以降,學校教育逐漸完備,周代的國學與鄉學,漢代的太學,宋代的書院及至明清的國子監,這些都是古代中國教育發達的實證。但是問題在于,那些促成小腳女子的因素使得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激發人的創造力,卻在于從思想上及行動上對其進行規制與馴服。從兩個方面可以說明這一點:
教育內容上。古代教育重道德倫理而輕實踐技能。《禮記·大學》開篇即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論語·子路》中樊遲要求學稼藝,遭到孔子搶白,因為在孔子眼里,稼穡是小人的行當,而教學的根本則應該是禮儀。那么這"善"及"禮儀"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呢?無非是"克己復禮以為仁"以及"存天理,滅人欲"那一整套東西。
教育踐履上。古代學校對學生的思想及行動的管制十分嚴格。以明清為例,明清國子監的監規禁例繁多,"堂宇宿舍,飲饌澡浴,俱有禁例"[1]。監生的出入,乃至上廁所,都須持牌放行。國子監"每班給出恭入敬牌一面,責令各班值日生員掌管。凡遇出入,務要有牌。若無牌擅離本班,乃敢有藏匿牌面者,痛決。"[2]除這些規定之外,還設有嚴厲的懲罰機構,國子監特設"繩愆廳",對違規的監生有執行刑罰的權力。凡有不守監規者,輕則廷杖,重則發配邊疆乃至處死。洪武二十七年,監生趙麟因受不了管制,貼了"帖子"提出抗議,被處以極刑,并在國子監前立一長桿,懸首示眾。這桿子一直豎了162年,即到1556年方才撤去。
二十一世紀的校園自然不會有洪武時代的那根長桿,甚至因為出于對學生個人權利的尊重,肉體的懲罰原則上就像1556年的那根長桿,被永久性的撤出了校園。但是,這并不意味權力的不介入,事實上,那些對于生命與創造力的壓制仍然大量存在,只不過罩了一副面具,變得隱蔽與委婉。
近代以來大學"門禁"現象種種,可能是對此種隱蔽與委婉的規制方式的一絕好例證。注意門禁問題肇始自一次網絡聊天,一自稱南方某著名高校女生借了這無拘的網絡訴苦,大約說些學校管理生硬,男女宿舍不得互訪之類。當日我忽然很有興致,進了這學校的網站,結果該校"學生宿舍會客制度"第五條赫然寫著,"男性一律不得進入女生宿舍,特殊情況須經值班員傳呼"。
其實我早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
高校的門禁,是一個不舊不新的話題。當年鬧得風風雨雨的開女禁,就是圍繞大學的那扇"門"展開的。對一個男女關系規制得厲害的國度,每向前邁一步大概都會很艱難。1920年2月,時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北大先行向女子開放,但是因為未得到教育部的許可,暫時不招正科生,只設女生旁聽席,當時即有王蘭、奚湞、察曉圓三位女士入北大旁聽。大學開女禁,這在當時頗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意味,自然引起軒然大波,鼓掌叫好者有之,激烈反對者有之,徘徊觀望者亦有之。當時徐彥之曾作《北京大學男女共校記》一文,文中說就事實上觀察,北大此舉"算是深冬時節的霹靂一聲雷……怪不得教育部怕得什么似的"。徐彥之文中的"教育部怕得什么似的"是指四月份北京政府教育部致北京大學的公函一事,函稱:
"大學允許女生旁聽一事,倍諗各情。外間所傳,自屬失實。旁聽辦法雖與招收正科學生不同,惟國立學校為社會觀聽所系,所有女生旁聽辦法,務須格外慎重,以免發生弊端,致于女學前途轉滋障礙,斯為重要。"
因為風氣所向,北大開女禁后,國內各大學紛紛仿行。據有關數據統計,至1922年,全國大學有學生34880人,其中女生887人,占2.5%。不過女禁問題并不止這些,后來開了又禁,禁了又開,倒是一波三折。1927年,北京軍政府教育部就曾下令京師大學各部科取締男女同校。
打破校門、開女禁的直接后果,是將"門禁"問題轉移到了校園當中來。學校大門的身影漸漸隱去,湮沒在歷史的積塵中,而男女生宿舍的小門卻凸現出來。"禁"的實質似乎并沒有改變,不同的只是換了一扇門。以國立北京大學為例,北大的向例是男生宿舍不得招待女賓,更無須妄談女生宿舍招待男賓。但時至1927年,學生因男女生來往多感不便,便群起反對這種禁例,與學校爭論多日的結果是齋務委員會作出讓步,暫準女生前往男生宿舍參觀,并定條例三條:
㈠女賓來舍參觀時間,為每日下午一時至五時,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㈡在規定時間以外,不得留女宿在宿舍;㈢女賓來舍參觀,先在號房留名,由號房請出本人,由本人引導入舍。[3]
好事多磨。1933年北大發生李靜淑事件,即女生李靜淑在男生宿舍勒斃。學校借此事發難,除將當事學生葛天民開除學籍外,決定嚴格禁止男生宿舍出入女生。北大學生為此曾一度向學校請求,學校都拒絕接受。事發當時北大學生會致校長蔣夢麟的信函云:
"呈為請求開放門禁事,竊本校自葛李案件發生后,各齋舍即禁止外賓出入,當時齋務委員會聯合會曾呈請收回成命,但未荷恩準。緣是敝會不得不重申理由,在事實上門禁而后同學多感不便,接待室又復簡陋不堪,且葛李案之發生,乃新舊思潮之爭,并非由于門禁之嚴于不嚴,故經第一次代表大會決議,復經第三次執行委員會通過,請求開放門禁在案,敝會特此披瀝直陳,伏乞鈞座恩準是為德便。此呈蔣校長"。[4]
一十四年之后,即1946年,北大學生開始為開放女生宿舍事奔波。11月27日,北京大學訓導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制定了學生宿舍規則。這一規則可謂是體察細微,十二條"宿舍內燈泡不得超過學校規定之燭火,亦不得安置插銷并嚴禁使用電爐"、十四條"宿舍內午睡時及熄燈后至起身之時間內,不得玩弄樂器或高聲喊唱"及十九條"住宿生有自行車者應存入車棚或指定場所,不得逕推入寢室"的規定都極為瑣碎。[5]但其中并未提及"女生不得入男生宿舍"或"男生不得入女生宿舍",可見當時男女宿舍已解禁。
但及次年,北大校長胡適又重提北大女生宿舍禁男賓入內事,遭到學生抵觸。時北平《益世報》亦發文聲援學生:
"在清華、燕京、師范等校在爭取開放女生宿舍聲中,北大胡適校長,又提出北大女生宿舍重禁男賓入內,該校賀訓導長主張應尊重女同學之意見。該校女同學認為于去年爭取開放宿舍頗費周折,尤以高唱男女平等之今日,女生宿舍重提男賓止步,實是一大諷刺。女同學會以無三分之一提出否決開放,故仍維持原議"。[6]
然而在半個世紀之后,諸如"男性一律不得進入女生宿舍,特殊情況須經值班員傳呼"這類的規章仍舊頑固的活著而并沒有從我們的生活中剔除出去。活著或者死去,這是一個問題!有一個意象強烈震撼著我,馬爾克斯筆下年老的奧雷良諾整天制作著小金魚,做滿了二十五條又把金魚融化,再從頭做起,時間就是在打圈圈。而門禁,這就是中國的百年孤獨啊!
門禁與纏足在形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它們都是中國小腳文化的產物,都是通過對空間的合理運用而達到規制的目的--尤其對性的規制。"睡覺是死亡的影像,寢室是墓地的影像……盡管寢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擋,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寢都不會被人看見"。[7]這段福科用來形容修道院修女生活的話可能也很合用于校園里的女生們。當然,不能排除門禁有其實踐上的考慮,它確實能夠帶來管理上的便利,學校是學習的場所,一個秩序井然的人際關系是必需要的。如果情況僅是這樣,那么對門禁的任何詰難豈不是吹毛求疵?但是問題不僅僅只在于門禁本身,而在于隱藏在門禁背后的那種小腳的文化結構,這種文化結構注定了一種教育理念的壓制性與專斷。在這樣的一種文化結構和教育理念下,奢談什么創新教育是自相矛盾及自欺欺人。
即便作為一種實踐中的管理模式,門禁的實際效果也是大有可商榷之處。如同幽禁與纏足一樣,門禁的用意最為明白不過,即通過空間隔離將性幽禁的方式,以達到秩序的井然。但是按照福柯的觀點,這種幽禁與規制往往適得其反。事實上也是如此,當學生意識權力的介入及幽禁與規制是因為性別差異,性別意識被強化了。權力試圖防患于未燃,禁絕一切可能是非的舉措不但沒有使學生乖乖就范,反而激發了他們對情事的無限的想象力。況且,宣泄會自發地尋找另外的空間。有一則生動的例子,一位訪學日本歸來的學者在講堂上談到,日本的學生要比國內的學生文明,根據是國內的男女學生常常在公眾場合肆無忌憚地勾肩搭背,而在日本很少有這樣的事情。有一個女生站出來委婉地表示反對,她認為不能僅從表面上看待這一現象,深層的原因很可能是,國內沒有給學生提供可以相互表達情感的適當空間。一語中的!當然,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被幽禁與規制的性會找到途徑宣泄,而不是要鼓勵學生把勾肩搭背的事都放到宿舍中去做。
總而言之,門禁的實際效果往往會有悖于初衷,教育的狹隘可能才是問題本身。關于目前教育存在的諸多問題,都與這門禁背后的理念有關,這里也不再細表。西哲黑格爾曾說,"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門禁的"合理"大概是其能夠滿足這個社會崇拜權力與畏懼性的心態。日倡夜倡多元、寬容、民主、創新,但骨子里還是祖宗留下來的那一套東西。昔黃河泛濫,堯命鯀治水,傳說鯀盜得"息壤",采用強行堵塞的方法,未見成效,本人則被殛于羽山。后堯命鯀的兒子禹治水,禹采用開渠疏導的方法,終于獲致成功。這大禹理水的故事,我們皆耳熟能詳,但悲哀就悲哀在,雖是耳熟能詳,但如今到底還是一個迷信"息壤"的時代。
近百年以前,魯迅在《狂人日記》的結尾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魯迅若生活在當世,不知他又會做何觀感……
[1]《明史》卷六十九《選舉志一》。
[2]《明會典》卷二二O《國子監·監規》。
[3]《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110頁。
[4]《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115頁。
[5]《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第843頁。
[6]北平《益世報》1947年10月4日。
[7]福柯:《規訓與懲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版,第163頁。(公務員之家整理)
文檔上傳者
- 小腳之小腳教育從大學門禁一事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