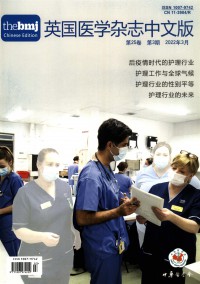英國獨特氣候給作家和讀者帶來的影響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英國獨特氣候給作家和讀者帶來的影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個民族的文學的生發、發展和成熟與該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歷史條件等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當然,英國文學也不例外。在影響英國文學的眾多因素中,氣候條件往往容易受到忽視。實際上,在漫漫歷史長河中,英國獨特的氣候條件對英國文學產生了潛移默化卻又至關重要的影響。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英國人鮮明的民族性格,使英國文學逐漸形成區別于其他國別文學的相對穩定的總體特征。此外,氣候還影響到英國文學的具體創作活動、閱讀活動以及整個民族的文化生活。
一、民族性格與文學審美
眾所周知,談論天氣是英國人見面時打招呼、寒暄的一種普遍方式。但事實上,英國人對天氣的關心程度遠不止此。2008年11月9日英國《電訊報》(TheTelegraph)刊登了一個關于英國人典型特點的調查結果:在所選出的五十個典型特點中,“談論天氣”名列首位。無獨有偶,英國《每日郵報》(TheDailyMail)于2010年5月14日公布了LlyodTSB保險公司對兩千名英國人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每個英國人一生中要花費六個月的時間談論天氣。英國人對天氣話題的熱愛勝過任何日常生活、工作或體育運動等話題。這種熱情甚至已經蔓延至網絡空間,僅Twitter網每日發表的與天氣有關的微博文章就達五十萬篇之多。英國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具有典型的溫帶海洋性氣候特征,季節間的溫度變化很小,雨量豐沛,特別是冬季時溫帶氣旋更為活躍,雨天很多。潮濕的氣候致使英國多霧,冬季經常飛霧迷漫,即使在天氣晴朗的夏季,時常還有薄薄的煙靄。19世紀英國工業的迅猛發展加重了英國的霧氣,倫敦就曾經以“霧都”而聞名于世。陰雨天氣導致的日照缺乏憂郁癥SAD(SeasonalAffectiveDisorder),每年使五十萬英國人深受其苦。此外,由于受到四季海風的影響,英國的天氣異常多變。英國人常說:“國外有氣候,在英國只有天氣”,以此來表明這里天氣的變化莫測。在一日之內,忽晴忽陰又忽雨的情況并不少見。多變的天氣不僅為人們提供了經常的話題,還使英國人養成了愛抱怨天氣的習慣,同時也讓英國人變得格外謹慎。英國人出門隨時都得帶著雨傘和外套,以備不時之需。如果某人被大家議論為“他連雨傘都不帶”,就說明大家認為這人不夠穩重、欠考慮。天氣在這里并非只是氣象學意義上的陰晴云雨溫差濕度,它還關系著健康、教養、性格、習俗、文化甚至哲學。對天氣話題的鐘愛已經成為深入英國人骨子里的一個特點,也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對于英國人這樣一個相對保守的民族來說,談論天氣是一種簡單又緩和的開始談話的方式,而且還存在一種被稱為“贊同定律”的交流方式,即不管對方如何描述天氣,聽者都應表示贊同,這樣雙方才會覺得具有“共同點”,才能繼續交談下去。總之,英國獨特的氣候條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英國人委婉、謹慎、憂郁、保守的民族性格。這種性格在英國經典作家身上得到了具體的體現。例如,英國文學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們(如莎士比亞和斯賓塞等)大都從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中尋求啟發。他們的作品風格比較婉約,常常通過寓教于樂的方式探討哲學問題或進行道德教育。此外,多愁善感的性格也使英國作家(塞繆爾•理查遜和勞倫斯•斯特恩等)成為18世紀風靡歐洲的感傷主義小說的先行者和引領者。他們的小說大多都以描寫人物心理感受見長,書中的人物富于情感,常常對瑣事之事感嘆不止,讀來有一種哀婉情調;同時,小說中對工業革命的籠統否定和對過去鄉村風光的美化又反映出作家們保守的人生觀。浪漫主義詩人們更是集中體現了英國人的典型性格。拜倫、雪萊、濟慈等詩人無不是優雅的英倫紳士,歌頌自然、熱愛自由,卻又時常陷于悲觀、孤獨和苦悶之中。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英國文學的審美基調,也凝練出了英國古典文學中那憂郁哀怨、冷艷清絕之經典美的靈魂。蒼茫的曠野,斜雨飄忽,天地一色;遠樹彌漫,曲徑荒幽;荒野上的哥特城堡,昏暗而神秘;郊外的鄉村農場,蔥郁寧靜卻又生氣勃勃。這正是經典的英國文學審美基調和背景。
二、氣候差異與文學特征
氣候條件不僅對人們性格、氣質、情趣和追求產生影響,還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文學作為文化的載體和文化本身的一部分,無疑也受到了氣候環境的影響。在《〈英國文學史〉序言》中,丹納(Taine)在闡述他所發現的文學發展規律時指出,文學創作和它的發展決定于“種族、環境、時代”三種要素或三種力量。其中環境是“外部壓力”,主要指自然環境,包括地理條件、氣候條件,這些條件的不同會造成人們不同的性格、氣質、情趣和追求,并在文學藝術和文化創造上鮮明地體現出相應的不同特點來[1](P10-11)。在《藝術哲學》中,丹納把“精神上的氣候”與文學藝術的關系比作自然界的氣候與植物的關系:“自然界有它的氣候,氣候的變化決定這種那種植物的出現;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氣候,它的變化決定這種那種藝術的出現。我們研究自然界的氣候,以便了解某種植物的出現,了解玉蜀黍或燕麥,蘆薈或松樹;同樣我們應當研究精神上的氣候,以便了解某種藝術的出現,了解異教的雕塑或寫實派的繪畫,充滿神秘氣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學,柔媚的音樂或理想派的詩歌。精神文明的產生和動植物界的產物一樣,只能用各自的環境來解釋。”[2](P42)顯然,這里的氣候已超越“自然界的氣候”而指向“精神上的氣候”。關于氣候對文學的影響,法國19世紀著名文學批評家斯達爾夫人在《論文學》一書中有更為詳細的論述。她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劃分了歐洲南北文學并且將二者進行平行比較。斯達爾夫人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文學存在著,“一種來自南方,一種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馬為鼻祖,后者以莪相(注:傳說中三世紀蘇格蘭行吟詩人)為淵源,希臘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時代的法蘭西人屬于我稱之為南方文學這一類型,英國作品,德國作品丹麥和瑞典某些作品應該列入由蘇格蘭行吟詩人,冰島寓言和斯堪的那維亞詩歌肇始的北方文學”[3](P145)。她認為氣候是北方文學(英國、德國、丹麥、瑞典、蘇格蘭等國的文學)與南方文學(希臘、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國的文學)之間產生差別的主要原因之一。以英國為代表的北方文學形成了以下的特點:“憂郁、遐想、思想的強烈、對痛苦的深切感受、對自由的熱愛、哲理傾向、對鄉村和孤寂的愛、對婦女的尊重。”[3](P19)根據斯達爾夫人的考察,聯系英國文學的實際狀況,可以發現氣候對英國文學的影響確實是明顯的。第一,英國地處歐洲北方,氣候寒冷,天氣陰霾而暗淡,人們的生存環境較為惡劣,因而他們憂郁傷感、喜愛沉思、富有想象力。這種憂郁氣質帶有民族精神的印記,同時也構成了這個民族的本質。可以說,英國人的憂郁是與生俱來的民族氣質,他們甚至以此為豪,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的詩篇《憂郁頌》即是一個例證。另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哈姆雷特的憂郁和痛苦,從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典型的英國式的憂郁和審慎。莎士比亞可謂是把哈姆雷特精神的痛苦和內心的沖突描繪得淋漓盡致,從而凸顯出憂郁性格與人物命運的必然聯系。與戲劇相比,英國的詩歌在表現英國人憂郁氣質和內心強烈情感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18世紀中葉,以大自然和情感為主題的感傷主義詩歌風行一時。其特點是排斥理性,崇尚情感,強調對大自然和死亡意義的探索。“墓園詩派”代表人物托馬斯•格雷的《墓園挽歌》和哥爾德斯密斯的《荒村》都集中體現了英國詩歌中普遍的陰郁色調;威廉•科林斯的《頌詩集》對自然美的敏感、憂郁感傷的情調都近似格雷;蒲柏的《埃洛莎致阿貝拉詩》將真摯的愛情描寫得悱惻動人;愛德華•楊格的《夜思》則把死亡的感傷情緒與關于生死的神學討論交織在一起描繪了詩人深刻而痛苦的思緒。這些作品大多都是通過對大自然景物的描寫抒發孤獨、哀怨、低沉的情緒,同時也表現出啟蒙時代和諧理想的危機。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再版序言中也把詩歌看作“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這篇序言后來成為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宣言。的確,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在表達情感方面成就輝煌達到了難以逾越的高度,甚至對歐洲其他國家的浪漫主義文學產生了深刻影響。不僅如此,對憂傷與痛苦的描寫還使英國文學中的許多作品具有了嚴肅崇高的色彩,甚至描寫戲謔場景時也擺脫不了憂郁色彩。這是一種獨特而自然的戲謔,暗含著郁悶甚至憂傷的意味。“這種戲謔是英國氣候和民族風尚的產物,在沒有這樣的氣候和民族風尚的地方是模仿不來的。”[3](P174)在菲爾丁、斯威夫特、斯摩萊特特別是斯泰恩的作品中,這種戲謔得到了完整的體現。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英國式幽默。加拿大心理學家羅德•馬丁(RodA.Mar-tin)在《幽默心理學:綜合研究》中對英國人的幽默作了專門研究,提出一種假設:幽默源于環境。他認為,英國變幻莫測的陰雨天氣,密集的人口,明顯的社會等級和各自為陣的社會階層,都是自嘲內斂、尖銳刻薄的“冷面幽默”滋長的肥沃土壤[4](P254)。第二,根植于歐洲北方特定氣候環境中的英國文學不僅激發了人們高尚的熱情,還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正如斯達爾夫人所述,“憂郁的詩歌是和哲學最為協調的詩歌”[3](P146)。英國詩人繼承了以莪相為代表的蘇格蘭詩歌的風格,增加了自己的哲性思考,并且保留了喜愛海濱、喜愛風嘯、喜愛灌木荒原的北方想象和厭倦命運的心靈對來世的想象。從彌爾頓的《失樂園》到蒲柏的《人論》,再到菲爾丁的《湯姆•瓊斯》,都提出了有關責任、知識和自由等人生的根本問題,也包括人與上帝的關系、人的自然本質與社會中的偽善之間的對立。自20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英國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熱衷于對生活進行哲學思索。愛麗絲•默多克的創作跨越文學和哲學,她的小說不僅展示了失去本質后人的掙扎與痛苦,也對現代西方人如何重新找到本質歸屬并結束精神流浪這一問題進行了孜孜不倦的哲性探索;威廉•戈爾丁的小說《蠅王》《繼承人》探討了人性和道德,富于哲理;柯林•威爾遜的小說《必要的懷疑》《思想寄生蟲》《哲學家的石頭》通過文學的形式對人的潛能和意識等進行哲學思考。當存在主義哲學在法國已成強弩之末時,在英國卻方興未艾,這一哲學傾向在塞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作品中得到了突出體現。詩歌方面則有葉芝、T.S.艾略特等。他們把現實、象征和玄思結合起來,大膽創新,引起人們理性的激動。相比之下,南方氣候溫和,使人耽樂少思,充分享受生活的安逸和舒服。明媚的陽光,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氣,繁茂的樹林,清澈的溪流等生動活潑的自然條件,造就了明顯不同于北方文學的南方文學。人們身心愉悅,興趣廣泛,生活安逸,但是耽于安逸的詩歌遠不能和沉思默想和諧一致。所以,歐洲南方文學中體現出的思想的強烈程度和豐富性都遜于歐洲北方民族。第三,斯達爾夫人將歐洲北方民族和自己處身其間的歐洲南方作比較并且表明自己對北方文學的偏愛。她從自由主義的政治觀點出發,認為北方詩歌與一個自由民族的精神更為相宜。雖然南方民族的文明程度較高、藝術樣式較豐富,但理性的增長卻導致對人性的壓抑,由此產生的文學便受到諸多規矩的限制。她以南方文學公認的創始者雅典人為例,指出“對藝術的愛、氣候的美”等所有賜予希臘人的享受可能比較容易使希臘人習慣于奴役;而對于北方民族來說,“土壤磽薄和天氣陰沉而產生的心靈的某種自豪感以及生活樂趣的缺乏,使他們不能忍受奴役”[3](P147-148),自由獨立就是他們首要的和唯一的幸福。這種精神在文學上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表現:首先,英國文學的思想內容上所體現的自由精神,如具有神話傳奇色彩的民族詩史《貝奧武夫》、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以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都具有天馬行空的想象和針砭時弊的諷刺等鮮明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文學的政治諷刺傳統,以其獨特的表現方式享譽世界文壇且經久不衰。18世紀的《朱紐斯信札》中一系列不署名的抨擊性政論文章是最為生動的諷刺作品之一,作者將諷刺手法運用至爐火純青。18世紀英國小說家塞繆爾•巴特勒的《埃里汪奇游記》被認為是與《格列佛游記》齊名的一部經典諷刺作品。一直到20世紀的伊夫林•沃《一把塵土》和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等作品中,針砭時弊的諷刺之風依然自由馳騁。正是其中所體現出的英國的自由氣氛使這些作品讀起來興趣盎然。其次,這種自由精神還體現在文學的形式上。法國戲劇由于受到古典主義影響,其創作有很多嚴格的規則限制,從而能夠達到恰當得體的效果。相比之下,英國戲劇創作更為自由。它超越了傳統劇種風格,刻畫英雄人物的同時也不隱瞞他們的缺點,使崇高與卑俗、悲壯與詼諧交相輝映。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把國王寫成弒君篡位者,王后成了淫婦,王子變成了瘋癲之人,但伏爾泰從古典主義興趣出發,指責這個劇本粗俗野蠻,荒唐不堪,充滿著時代的錯誤,尤其是在舞臺上埋葬奧菲利婭的戲令人觸目驚心[5](P177)。有趣的是,伏爾泰對《哈姆雷特》的這些評價恰恰反映了英國戲劇的自由之特點———美德與缺點、崇高與粗俗的并置。正是在這種神圣與粗俗、崇高與卑下的戲謔性混合中,《哈姆雷特》實現了狂歡精神顛覆官方文化及正統意識形態的功能,從而表現了莎士比亞“徹底的非教條主義”以及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識。進入20世紀,這種自由精神連同英國小說創作的能量在“現代主義”潮流中再度爆發,形成了一個新的高峰。喬伊斯、吳爾夫、康拉德、勞倫斯等文學巨擘在藝術技巧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創新試驗,創造了一種能夠傳達“變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6](P128)。
三、創作靈感與“感情誤置”
如前所述,英國的氣候條件造就了英國人憂郁傷感、自由獨立、熱愛哲思、想象力豐富的民族特點,為偉大作家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這是一片文學的沃土,洋溢著整個民族對文學的熱愛。英國作家對人性和人的命運的哲性思考,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探究,賦予英國文學厚重的文化內涵和深切的人文關懷,也成就了英國文學的深刻、崇高和雋永。戴維•洛奇在《小說的藝術》的第十八章“天氣”里指出:19世紀以前的小說對天氣的關注不多,只有一些關于海上風暴的描寫;而到了19世紀,小說家似乎開始關注起天氣來。“這一方面是因為自浪漫派詩歌和繪畫開始產生了欣賞大自然的傾向,且這種傾向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因為文學對反映個性,對以下事實越來越有濃厚的興趣:即人的感情既影響人對客觀世界的感覺,同時也受到客觀世界的影響。”[7](P96)自然界直接投射于人的情感和認知,培養了英國人敏銳細膩的情感、審美的形象思維以及對自然景象和生活細節的觀察能力。更重要的是,英國獨特的氣候條件或具體的氣象事件為作家創作提供靈感來源;也可作為小說故事背景,對故事情節產生關鍵影響;還可以單純作為一種修辭手法,反映了人物的情感心境在自然現象上的投射,增強小說的感染力。關于作家從氣候事件中汲取靈感的例子不勝枚舉。1703年11月英吉利海峽生成的颶風襲擊了英格蘭南部海岸,摧毀了一萬四千所民居,八千人喪生。普利蒂斯附近的燈塔被毀,十二艘戰船沉沒。丹尼爾•笛福正好目睹了這場災難,他于次年發表了《暴風雨》,記錄下他在那場暴風雨中的所見所聞。這次經歷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其后來的成名作《魯賓遜漂流記》提供了素材和靈感。1815年印度尼西亞坦博拉火山爆發。這是自1500年以來最強烈的一次火山爆發,它引發了非同尋常的惡性后果———全球氣候變化。這是因為火山爆發所產生的大量火山灰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煙云,進入大氣層并滯留了兩年之久。陽光穿透大氣層的強度大幅減小而導致全球氣溫下降超過5華氏度(約2.8攝氏度)。在這年秋季,英國人常常能夠看到持續時間很長的暗紅色的黃昏和黎明。接下來的1816年天氣更為惡劣,農民無法正常播種,導致歐洲和北美的農作物歉收,這一年又被稱作“無夏之年”。此次極端不尋常的天氣變化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被譽為“科幻小說之母”的瑪麗•雪萊的傳世之作《弗蘭肯斯坦》。1816年夏季,雪萊夫婦和拜倫住在瑞士阿爾卑斯山腳下,陰雨連綿,無法出門,于是他們閱讀、講述德國鬼怪故事并相約每人寫一則。在丈夫的鼓勵下,瑪麗最終完成了小說《弗蘭肯斯坦》,于1818年出版。拜倫同樣也從那個寒冷的夏季獲得了靈感,寫下了《黑暗》這首詩。“我做了一個夢,卻不僅僅是夢境。光明的太陽熄滅了,星辰們也在無盡的天空中黯淡,昏暗、無路而又冰凍的大地盲目地搖擺在昏黑無月的空中;清晨來了又走———從未帶來白晝,人們在對悲傷的恐懼中忘記了激情;他們的心全都僵冷成一個自私的祈求,祈求光明。”[8](P189)拜倫在詩中描繪了世界末日的景象,人類完全喪失了愛、憐憫和行動的勇氣。整首詩彌漫著沮喪和憂傷的色調。直到1819年,這種惡劣天氣才得以好轉,農民也迎來了久違的豐收。約翰•濟慈對此頗有感慨,這一年8月,他在給妹妹芳妮的信中寫道:“我們有爽快的天氣已經有兩個月之久了,這是我最大的欣慰———不會把鼻子凍得紅紅的———不會冷得瑟瑟發抖……我最喜歡晴朗的天氣,認為那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的賜福。”[9](P248-249)也正是在這一年濟慈寫下了膾炙人口的《秋頌》,贊美了秋天的美景和豐收的喜悅。而之后的1860年,喬治•艾略特由于從英格蘭林肯郡蓋恩斯伯勒的特倫特河水泛濫得到靈感,創作了她的第二篇長篇小說《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故事的結尾是弗洛斯河泛濫成災,瑪琪獨自駕船到被淹的磨坊去救湯姆,兩人在危難中和解,但小船覆沒,兩人淹沒在洪水之中。這讓人聯想的圣經里大洪水的故事,因而,洪水意象在小說中具有象征意義。其次,氣候狀況在文學的結構和內容上可以起到實用性作用。莎士比亞的很多戲劇都是這方面的范例。這些作品都以暴風雨等惡劣天氣為背景,甚至將其作為情節的一個重要環節。例如,在《暴風雨》中,米蘭公爵普洛斯彼羅被其弟安東尼奧篡奪爵位,和女兒米蘭達公主被迫流亡到一座荒島。十二年后的一天,普洛斯彼羅趁安東尼奧、那不勒斯國王和王子乘船出游時,指揮島上的精靈們喚起一場劇烈的狂風暴雨,讓船上的人相繼落水。安東尼奧等人在面臨暴風雨即將給他們帶來的死亡時幡然悔悟并得到了普洛斯彼羅的原諒。可見,暴風雨對故事發展和轉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樣,《李爾王》中一個著名的場景就是“暴風雨”,它在結構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李爾被驅逐荒野,在暴風雨中發狂,既是前幾場故事發展的必然結果又是以后一系列事情的起因之一。從內容上看,正是由于李爾身處曠野,遭受暴風雨的洗禮,他才有了對世間的新感悟:“衣不蔽體的不幸的人們,無論你們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著這樣無情的暴風雨的襲擊,你們的頭上沒有片瓦遮身,你們的腹中饑腸雷動,你們的衣服千瘡百孔,怎么抵擋得了這樣的氣候呢?啊!我一向太沒有想到這種事情了。安享榮華的人們啊,睜開你們的眼睛來,到外面來體味一下窮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們享用不了的福澤給他們,讓上天知道你們不是全無心肝的人吧!”[10](P145)可見,暴風雨是李爾王頓悟并走上救贖之路的開端,也是其轉變思想觀念的契機。最后,氣候和天氣作為自然界的一種現象,往往留有人的情感投射上去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主觀性甚至虛假性。這也就是約翰•羅斯金所提出的“感情誤置”。但戴維•洛奇認為,只要用得明智和謹慎,它不是一種暴露作者心理狀態的方式,而是一種能產生特殊效果并使讀者獲得獨特感受的修辭技巧,具有流暢和感染力強的效果,小說中缺少了這一項將會貧乏得多[7](P96)。簡•奧斯丁在小說中擅長不著痕跡地運用“感情誤置”這一技巧。她在愛瑪的運氣處于最低潮時,寫道:“這一個黃昏是漫長的憂傷的。天氣又盡量增添了陰郁氣氛。”[11](P362)天氣是人物眼中之景,打上人物的心理烙印,看似寫天氣,實則寫人。因為愛瑪發現了有關簡•費爾凡克斯的事情的真相,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尷尬;她還意識到自己深深愛著奈特利先生,但已太遲,因為她有理由相信他要娶哈麗埃特為妻———所有這一切,使那一天成為她最倒霉的一天。狄更斯在《荒涼山莊》的首段中直接寫道:“無情的十一月天氣。滿街泥濘,好像洪水剛從大地上退去……煤煙從煙囪頂上紛紛飄落,化作一陣黑色的毛毛雨……陰冷的下午再也陰冷不過了,濃霧再也濃不過了,泥濘的街道再也泥濘不過了。”[12](P4-5)狄更斯的想象頗富隱喻性:他把天氣擬人化,謂之“無情”,用“濃霧”、“黑煙”和“泥潭”來暗指大法官法庭判案毫無定法、胡亂了事的作風。他把普通的19世紀倫敦陰雨天氣的景象轉化成啟示錄式的幻覺,讓人仿佛看到英國都市淪落為原始沼澤地。同樣,哈代的小說中的晴朗天氣不多,“天上烏云籠罩,地上一片蒼茫;時而狂風怒吼,時而聚雨如注,時而迷霧四塞”[13](P20)。天氣描寫為他所寫的悲劇制造了荒涼粗獷、沉郁凝重的氣氛。這些作家將“感情誤置”這一技法運用得自然嫻熟,反映了人物的情感心境在自然現象上的投射,起到了烘托人物、渲染氣氛的作用。可見,用是否合乎邏輯性和準確性這條標準來衡量這種修辭手法的價值是不恰當的,正如不能用此標準來衡量隱喻一樣。還有一點不容忽視,那就是英國的氣候對文學讀者群的培養和構成也具有重要影響。陰雨天氣往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們的戶外活動,尤其在電視電影尚未出現的時代,人們在雨天大多在室內活動,讀書看報也就成了最受歡迎的消遣方式。在維多利亞時代,文學閱讀到達前所未有的盛況,成為人們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另外,如前所述,英國人的氣質和現實環境培養了整個民族對閱讀和文學無比的熱愛。在英國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看來,閱讀文學作品是人們重要的認知和審美活動,而閱讀經典著作更是獲取知識的最佳來源,因此,英國人非常樂于保持愛讀書的傳統。有調查顯示,英國女性讀書量明顯高于男性,而女性的讀書趣味會直接影響丈夫和孩子,極大地增加了讀書傳統承傳的可能。成熟而龐大的讀者群和普遍的文化活動又對英國文學的繁榮起到了推動作用。英國文學產業,包括出版、報紙、書籍、書評之發達恐怕也是因為天氣太壞,人們只好在家讀書看報消磨時間。事實上,英國是世界上藝術和文化遺產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他們最引以為豪的是對文字的擅長,不僅為世界貢獻了大量的詩人、小說家、文藝評論家,而且每年為世界提供十萬冊新書,是所有英語國家的總和。就每年讀者需要的印書種類,英國讀者比德國讀者多一倍,比法國讀者多二倍,比美國讀者多幾乎七倍,比中國讀者多二十倍。英國的讀書活動貫穿全年,每年單是學校、圖書館、書店所舉辦的慶祝活動便已超過一千項。圖書館、書店、藝術館之多超乎想象,僅圖書館全國就有五千多家。
四、結語
綜合上所述,英國潮濕多雨、陰晴變幻的氣候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英國人憂郁、謹慎、保守的民族性格;反映在文學中,逐漸形成了憂郁的遐想、強烈的情感、對痛苦的深切感受、思想的哲理傾向、對自由的熱愛等總體特征;具體的氣候事件為作家的文學創作活動提供了靈感,也豐富或優化了他們文學創作的內容、結構和技巧;英國的氣候環境等條件也有利于讀者群的培養,成熟而龐大的讀者群和普遍的文化活動又對英國文學的繁榮起到了推動作用。我們在這里討論氣候對英國文學的影響并不是宣揚氣候決定論,也非一味夸大氣候對文學的絕對影響。事實上,英國文學源遠流長,經歷了一個長期、復雜的發展和演變過程。這一過程中,文學本體在遵循自身發展規律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外在的諸如自然條件、社會現實、歷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本文僅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中,跨越文學、文化、氣象等學科,對可能影響英國文學的其中一方面的因素———氣候進行探討,旨在更為全面地探索文學發展的規律及其外部影響,同時也為文學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一次嘗試。也許從氣候這個易被忽視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英國文學一個別樣的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