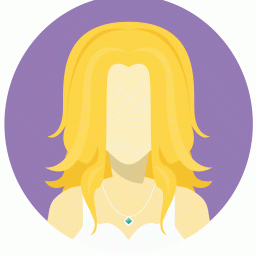合同仲裁論文:合同爭端仲裁適用辨析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合同仲裁論文:合同爭端仲裁適用辨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張健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研究生院
兩個認識誤區(qū)
雖然我國的涉外仲裁案件在數(shù)量上早就實現(xiàn)了“零的突破”,但是在涉外仲裁案件中,仍然在法律適用的問題上存在認識誤區(qū)。
(一)混淆涉外合同準據(jù)法與仲裁協(xié)議的準據(jù)法問題
在我國簽訂的涉外合同,主要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以及其他涉外商事合同,這些合同往往具有標的大、內(nèi)容多、法律關系復雜等特點。在合同內(nèi)容中,對于仲裁協(xié)議的約定也是常態(tài)。關于仲裁協(xié)議的法律適用,很多人會當然地認為:涉外合同適用的法律在中國是強制適用的,不單包括主合同,也包括從合同。這一點在我國《民事訴訟法》、2006年《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中外合資企業(yè)法實施細則》都做了詳細的規(guī)定,屬于強行規(guī)范。因此,一旦涉外合同中存在仲裁協(xié)議,我們會想當然地推導出仲裁協(xié)議也適用于中國法律。但是有一個問題不能忽略,那就是涉外合同中仲裁協(xié)議有自己的準據(jù)法,仲裁協(xié)議的準據(jù)法未必等同于涉外合同的準據(jù)法。這是一項法律原則,在1958年的《紐約公約》中就確定下來了。[2]即合同的準據(jù)法與仲裁協(xié)議的準據(jù)法“分立而治”。這也許難以理解,為何合同中的仲裁協(xié)議不受合同的約束?實際上,仲裁制度具有相對獨立性,法律尊重當事人的合意與選擇,仲裁協(xié)議及條款在效力上具有優(yōu)先性。換個角度來看,如果要求仲裁協(xié)議也受中國法律管轄,必須在合同中另行規(guī)定類似于“本仲裁條款也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法律適用約定才可以。
(二)誤將有效仲裁協(xié)議認定為無效
何為有效的仲裁協(xié)議?《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二條第一款規(guī)定:“涉外經(jīng)濟貿(mào)易、運輸和海事中發(fā)生的糾紛,當事人在合同中訂有仲裁條款或者事后達成書面仲裁協(xié)議,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gòu)或者其他仲裁機構(gòu)仲裁的,當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訴。”由此可知涉外合同已受我國法律管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對無效仲裁協(xié)議的情形列舉“:(一)當事人在合同中沒有訂有仲裁條款或者事后沒有達成書面仲裁協(xié)議的;(二)被申請人沒有得到指定仲裁員或者進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屬于被申請人負責的原因未能陳述意見的;(三)仲裁庭的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與仲裁規(guī)則不符的;(四)裁決的事項不屬于仲裁協(xié)議的范圍或者仲裁機構(gòu)無權(quán)仲裁的。”據(jù)對立法本意的理解,若仲裁協(xié)議有效,須具備三個要素:首先需要有仲裁的合意;其次要約定明確的仲裁機構(gòu);再次要明確約定仲裁事項。如仲裁協(xié)議出現(xiàn)上述瑕疵,則不能認為仲裁協(xié)議有效。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單純根據(jù)上述理由,確定涉外仲裁協(xié)議有效與否呢?如果合同當事人約定的仲裁地以及仲裁機構(gòu)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nèi)的,仲裁條款的有效性與否應當嚴格按照國內(nèi)法的規(guī)定進行判斷。然而,如果涉外合同當事人約定的仲裁地或者仲裁機構(gòu)是國外的,按照前面方法用國內(nèi)法進行判斷是否正確呢?合同的當事人在合同當中約定應適用仲裁協(xié)議的準據(jù)法,認為涵蓋了一切,但是事實上是,法律上規(guī)定是不涵蓋的。仲裁協(xié)議跟主合同的法律適用在某種情況下它們是可以分離的,即合同的準據(jù)法是中國,但是仲裁地約定的是中國以外的地方,這時候適用與否就不一樣了。對于上述判斷,在實踐中是有案例支持的。1999年,內(nèi)地與香港共三家公司達成了合同,合同中約定了仲裁條款:“由本合同產(chǎn)生,或者與本合同有關的所有分歧,爭議,或者違約事項,應當在香港依據(jù)國際商會的仲裁規(guī)則進行仲裁”。之后,三方真就合同產(chǎn)生糾紛,其中一方在湖北中級法院起訴。湖北中級法院根據(jù)被告的抗辯,認為當事人之間存在仲裁條款,法院不應當受理,因此最后駁回原告起訴。后原告不服,上訴至湖北高級人民法院,湖北高院認為,本案的被告及爭議的財產(chǎn)所在地均在湖北,合同雖定有仲裁條款,但仲裁條款內(nèi)容不明確,仲裁適用法律條款內(nèi)容相互沖突,因此該仲裁條款無效。湖北高級人民法院出具此意見后,按照1995年8月28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處理涉外仲裁和外國仲裁若干問題的通知》第1條“:地方高級法院要認定一個涉外的仲裁條款無效,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來得到它的批復同意。”的規(guī)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最高院在1999年6月21號以法【經(jīng)】1999年143號文進行答復。大致內(nèi)容:“你院的……文已經(jīng)收悉,經(jīng)研究認為本案當事人在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約定在香港,依據(jù)國際商會的仲裁規(guī)則進行仲裁,按照仲裁地香港法律的規(guī)定,該仲裁條款是有效的,可以執(zhí)行的。據(jù)民訴法規(guī)定,人民法院對本案糾紛無管轄權(quán),你院應當通知當事人,按照仲裁的方式解決。”[3]這是我國最高法院第一次把合同中的準據(jù)法與仲裁條款的準據(jù)法相互分離出來的案子。可以得出結(jié)論,在涉外合同中對涉外仲裁的認識上,我們?nèi)匀淮嬖谥欢ǖ恼J識誤區(qū)。而這些誤區(qū)與目前我國仲裁制度不完善、落后于國際相關制度、立法不健全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認識誤區(qū)的淵源即解決路徑
上述兩個認識誤區(qū)的存在,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表現(xiàn)。主要問題是目前我國沒有臨時仲裁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例如當事人約定在江蘇仲裁,在江蘇的南京、徐州、連云港、鹽城、南通、蘇州、無錫、常州全部都有仲裁機構(gòu),此時沒有辦法來使得當事人的仲裁意識通過某一個特定機構(gòu)來實現(xiàn)。與此同時,190多個聯(lián)合國成員絕大多數(shù)都承認臨時仲裁。只有中國或者沒有建立起仲裁制度的國家是不承認臨時仲裁。涉外合同中約定“:由此合同產(chǎn)生的相關糾紛,雙方應在瑞士日內(nèi)瓦進行仲裁。”按照我們國內(nèi)法判斷,該條款只約定了仲裁地,仲裁規(guī)則和仲裁機構(gòu)都不清晰。條款所說的瑞士日內(nèi)瓦是地點,而不是仲裁機構(gòu)。假定說,一個仲裁地點已經(jīng)指明了,此時在合同約定適用中國法的情況下,如何判斷這個仲裁條款的效力呢,判斷依據(jù)是以中國法還是以瑞士法律呢?答案是按瑞士法律。第一個依據(jù)是上文提到的1958年《紐約公約》:“第2條所稱的仲裁協(xié)議所稱的‘雙方當事人根據(jù)對他們適用的法律’,如果當時是處于無行為能力的情況,或者說是根據(jù)當事人所選定的法律,或者在沒有這種選定的時候,根據(jù)仲裁地國的法律,這種仲裁協(xié)議是無效的,那么這樣一個仲裁裁決,可以被當?shù)氐姆ㄔ壕芙^承認和執(zhí)行。”需要注意,這是仲裁協(xié)議的準據(jù)法,而不是合同的準據(jù)法。第二個依據(jù)是瑞士的仲裁法規(guī)定。如果仲裁地國有相關法律能夠承認臨時仲裁的,仲裁條款有效。瑞士1989年1月1號頒布的《國際私法法典》就有關于仲裁效力的確認規(guī)則。第12章第4節(jié)第179條規(guī)定:“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行約定產(chǎn)生仲裁員的方式,如雙方不能夠通過約定產(chǎn)生仲裁員,則組成仲裁庭的方式可以交仲裁庭所在地的法院,由法院按照該州的法律,加以指定或者替換。”該法典是基于臨時仲裁,而不是機構(gòu)仲裁。簡言之,只要雙方當事人約定了仲裁地,其他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不存在仲裁條款無效的問題。對于誤區(qū)的消除,不但要轉(zhuǎn)變看法,重新認識涉外合同中仲裁條款的法律適用問題,還要想辦法解決產(chǎn)生誤區(qū)的根源,從立法以及司法構(gòu)建角度入手,做到標本兼治。在立法上,應當完善立法,將涉外合同中仲裁條款效力確定問題納入立法日程。我國目前對于涉外合同仲裁條款的效力采用“個案審查制度”。個案發(fā)生后,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該條款有效的,可以直接作出裁定,認為無效的,需要上報高院批復;高院認為有效的,可以直接作出裁定,認為無效的,需要上報最高院批復。因此,涉外仲裁案件往往同案不同裁或者同案不同判。由此要統(tǒng)一進行立法,將仲裁條款效力判斷具體化、規(guī)范化。在制度構(gòu)建上,應當引入或者承認臨時仲裁制度。誠然,臨時仲裁制度也有自身的弊端,比如會造成當事人恣意、拖延訴訟,破壞我國強制管轄權(quán)等負面影響。但目前國際上承認臨時仲裁制度還是主流或者大趨勢,在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承認臨時仲裁不失為一種與國際接軌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減少法律適用上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