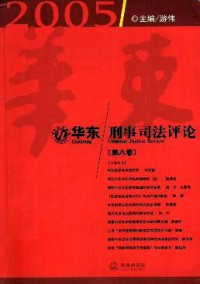刑事診所課程建設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刑事診所課程建設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刑事診所課程建設,是診所教育法律援助目標的具體落實,社會對此有強烈的期待。
“診所法律教育不僅要傳授給學生法律知識、培養學生的法律操作技能,更要通過特定的法律實踐(法律援助)使所有參與者增強公益意識,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保障人權,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真實案件,無償地為刑事被告人辯護,不僅是刑事診所課程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教學形式,而且能維護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在當下的社會生活中,這種法律援助更有著廣泛而迫切的社會需求。縱觀我國的刑事審判,被告人無律師辯護的案件占有相當數量,在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法院,這種案件的比重更高。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被告人欠缺經濟能力,無力聘請律師;而在這些被告人當中,相當部分的文化水平很低,對刑事法的規定了解甚少、缺乏理解,甚至不能清楚陳述事實,因而幾乎沒有有效的自辯能力,加之對自行辯護普遍存在顧慮,他們很難依靠自身力量進行應有的,甚至是起碼的辯護。在刑事訴訟關系中,這樣的被告人無疑是弱勢群體,他們需要、也渴望得到刑事法律援助,獲得較為專業的辯護,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為他們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社會應責無旁貸,也正好契合刑事診所課程的實踐性目標,回避刑事法律援助,是診所教育的缺憾。刑事診所的學生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在法律范圍內維護被告人的辯護權,不僅大有可為,同時也是法律診所自身公益目標的訴求和公益特征的折射。
在診所法律教育的體系建設中,刑事診所課程有其特殊的意義和重要性,課程建設和持續發展,其結果是法學教育和社會服務的雙贏。
(二)刑事診所課程建設是診所法律教育目標的客觀要求和完整實現。
作為診所法律教育的有機組成和法學教育改革的實踐,刑事診所課程有其自求的目標,概而言之,就是培養、訓練學生在刑事法方面的思維能力、推理能力、職業技能和職業素養。這種培養和訓練之于法科學生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首先,刑事診所課程教學指向的刑事法及其運用,是法科學生必須具備的知識和能力。欠缺刑事法知識和運用能力學生,很難說是合格的法科學生;其次,著眼于學生未來的職業選擇,他們需要有刑事法的知識和經驗。雖然加速進行的社會轉型和體制改革使法科學生畢業后獲得的刑事法律工作崗位在減少,但最終的從業人數依然龐大。忽略在校期間的刑事法學習和訓練,是法學教育的失職;第三,刑事法作為重要的部門法,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制度內容、運行要求、適用方法。通過刑事診所課程的實踐性學習,有利于是學生法律思維和能力的拓展,促進其他部門法學習能力和運用能力的提高。毫無疑問,刑事診所課程是診所法律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刑事診所課程的診所法律教育以及法學教育,在體系上是不完整的。簡言之,刑事診所課程建設,是診所法律教育自身的需要和完善。
二、刑事診所課程實踐性教學的法制空間檢視
“診所教育最關鍵的界定要素是它是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學習。”如果刑事診所不進行真實刑事案件的援助,學生不介入訴訟,為刑事被告人提供辯護,不僅會使診所教育的效果打折扣,而且有違引入診所教育,促進實踐性法學教育改革的初衷。問題在于,學生有無資格以及以何種身份刑事辯護?辯護是否違法?這種質疑成為刑事診所課程建設滯后最主要的認識障礙。事實上,質疑學生辯護是欠缺法律根據的。且不說被告人的辯護權和法律援助的受助權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刑事診所學生為被告人辯護,在道義上應得到肯定和支持,我國立法也為刑事診所課程的學生辯護也“預留”了應有的空間。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學生辯護的資格和身份不是問題。
(一)《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許可和保障
刑事診所學生介入刑事訴訟,為刑事被告人提供辯護是否允許,法律上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有無刑事訴訟法上的根據。我們知道,委托辯護是刑事辯護的主要形式,《刑事訴訟法》第32條確定的委托辯護人包括:(1)律師;(2)人民團體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這一規定清楚地表明,在委托辯護的案件中,辯護人不限于律師,如果由人民團體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非律師的公民同樣可以接受委托而辯護。毫無疑問,非律師的公民應該也能夠包含年滿18周歲、經過法律專業訓練的診所學生,除非他(她)是“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誠然,《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沒有賦予公民直接接受被告人委托而辯護的權利,進入訴訟的渠道相對狹窄,但允許以公民的身份辯護卻是明白無誤的,至少沒有禁止性規定。診所學生作為公民辯護,自無問題。
進一步講,公民依法接受委托而辯護的案件范圍,也沒有特別限制。《刑事訴訟法》第34條的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從此規定看,法院指定辯護的辯護人應當是律師,不能是公民,但是公民接受委托而充當辯護人的,并不在限制之內。
《人民法院組織法》則從法院保障被告人辯護權實現的角度,擴展了委托辯護人的范圍。該法第8條規定:“被告人除自己進行辯護外,有權委托律師為他辯護,可以由人民團體或者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或者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公民為他辯護,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監護人為他辯護。人民法院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指定辯護人為他辯護。”其中“經法院許可的公民”可以是被告人或其近親屬、監護人委托的公民,也可以是人民團體或被告人單位推薦公民。遵循這一規定,刑事診所課程的學生辯護有了更多的機會和空間。
(二)政府法律援助制度的支持
診所課程的學生參與刑事法律援助,為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和規定所肯定和支持。在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關系到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人權的司法保障和平等權利的保護。2003年頒行的《法律援助條例》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化躍上新臺階的標志。該條例不僅確定了法律援助的基本制度和主要措施,而且為以法律援助為己任的法律診所及其學生提供了進入各種法律援助的渠道,使診所學生辦理刑事案件有了更多的法律依據。如此認識的主要理由是,第一,條例第8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我國,“真實當事人”的法律診所,其工作平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經過管理機關核準或備案的法律援助機構,該機構屬于本條規定的“社會組織”范疇。診所學生也由此獲得了雙重身份,既是課程的學習者,又是該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人員。診所學生受所在法律援助機構的指派,開展刑事法律援助在內的各種法律援助,符合該條規定的精神。第二,條例第21條規定,“法律援助機構可以指派律師事務所安排律師或者安排本機構的工作人員辦理援助案件;也可根據其他社會組織的要求,安排其所屬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著眼于援助者的身份考察,該條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規定有著相同的精神。提供法律援助既可以是律師,也可以是法律工作者,即使援助的對象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如果診所學生成為條例所指“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人員,接受其安排而辦理刑事援助案件,不應有援助資格和身份的疑慮;若非如此,也屬于“根據其他社會組織的要求,安排其所屬人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情形。按照《法律援助條例》,診所學生進行刑事援助,在資格和身份也該沒有障礙。
以診所課程的學生沒有律師資格,因而限制其介入刑事訴訟提供刑事法律援助,不允許診所學生出庭辯護的認識和做法,在法律上是沒有依據的。誠然,法律提供的空間是有限的,但這不是刑事診所課程建設裹足不前的理由,需要努力的是挖掘和利用有限的法律空間。
三、刑事診所課程建設的基本運作思路
(一)立足刑事診所的實際,恰當地選擇援助案件
經驗告訴我們,刑事診所課程在援助案件的選擇上,一是要避免“貪大”,二是要避免片面地追求“社會反響強烈”。診所教育的本質在于“幫助學生培養經驗式學習的能力以及憑借經驗進行反思的能力”。忽略經驗學習的本旨,選擇案件不是以是否適合學生以及應否獲得援助為標準,而是過分看重所謂案情重大和社會關注度,以致追求所謂“轟動效應”,把援助變成“作秀”,其結果可能是事與愿違,甚至產生負面的社會反響,無論于法律援助還是于診所教育本身,都是一種損害。相反,刑事診所課程的實踐教學和法律援助,可以從小而簡單的案件做起。這樣的案件除了與學生的能力較匹配,被人的利益能夠得到較為充分的維護外,其有利之處還在于:(1)由于量多分布廣,案件的可獲得性強。基此,既能為有需要的刑事被告人施以援助,又能較好地保障診所教學有“實踐資源”,使課程實踐具有可持續;(2)這種案件同樣能達到“經驗性學習”的效果。“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實體內容和程序過程上,小案與大案并無本質的差別。在援助中,學生同樣能得到經驗性感受,而這種經驗恰恰為重大、復雜案件的處理奠定了基礎;(3)“拾遺補缺”,使更多的被告人得到刑事法律援助。在律師相對關注大案援助,無力顧及小案的情況下,由診所學生補位,在客觀上與律師援助形成“社會分工”,這是維護各類刑事案件被告人權益,全面推動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由是,刑事診所的援助主要應著眼于基層人民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
(二)尋求與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和人民團體的合作,借力發揮。
雖然學生可以公民身份代為辯護,在法律上沒有根本性的身份障礙,但學生僅以公民身份參與訴訟,出庭辯護,還是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質疑,客觀上成為一種限制,從而減損刑事法律援助的參與度和效果。面對這樣的現實,一個較為可取的解決方式是尋求與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和人民團體合作,把學生開展的刑事法律援助融入政府和人民團體的法律援助之中,把掣肘和限制降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合作與融入的一個重要的進路,就是讓學生成為這些法律援助機構中從事法律援助的人員,讓他們實施的法律援助成為政府法律援助活動的組成部分和具體體現。由此,學生不僅可以依照《法律援助條例》規定,以“社會組織”成員的身份實施,還可以接受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安排,以“本機構的工作人員”的身份實施刑事法律援助,出庭辯護。在運作方式上,可考慮以法學院的法律援助中心為基礎,建立政府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一方面在身份上多一份保障,便于法律援助的實施;另一方面也便于接受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指導和監督,利于援助活動的規范開展。這樣做雖然不能解決實際存在的所有問題,但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來自不同方面的對診所學生在身份上的疑慮,為他們較為順當地進入刑事訴訟減少障礙。
與人民團體的法援助機構建立和保持聯系,成為他們可資利用的法律志愿者。在有需要時,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2條的規定,接受人民團體的推薦,實施援助,出庭辯護,是另一個可選擇的路徑。
(三)與法院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獲得法律許可的支持。
目前,診所學生要在審判前介入而開展刑事法律援助,是不現實的。相對而言,在案件起訴后,為刑事被告人充當辯護人而進入訴訟,較具可行性。要進行有效的辯護,必須清楚案件的事實,明確起訴方的指控以及證據,因此取得案卷材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和環節,此外還應當盡可能地會見被告人。按照《刑事訴訟法》第36條的規定,非律師身份的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可見,在獲得案卷材料、會見在押被告人方面,非律師身份的辯護人法院并無必須提供便利的義務。為此必須高度重視與相關法院的溝通,爭取支持,以便依法進入訴訟,確保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渠道暢通,獲得會見被告人的機會。
為使溝通富有效率和持續進行,一方面要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充分說明診所教育的教學模式以及刑事法律援助的多重意義,得到他們的認同和支持,另一方面要著眼于“長效機制”的建設,盡量避免一案一溝通的做法。因此不妨采取“重點建設”的方式,將刑事診所課程的援助案件相對集中于某些法院,使溝通常態化,同時可借助這些法院的渠道,向在押而未聘請律師的刑事被告人傳遞可提供法律援助的信息,并獲得委托辯護意愿的信息反饋,保障刑事案件的案源,將診所課程中出庭辯護的刑事法律援助落到實處。在現實的司法背景中,與法院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形成法律允許的合作關系,是刑事診所課程建設和持續運行的重要保障。
此外,結構合理的教師隊伍、注重援助過程的把握、多樣化援助方式的運用等,也是刑事診所課程建設應當認真對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