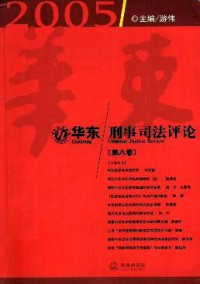刑事證明標準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刑事證明標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刑事證明及其標準的內涵,是具有主觀思維活動性和具體法律行為性的有機統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質量互變規律”,即“質、量、度”三維度,進一步探析刑事證明標準可以得出:刑事證明標準的“質”,即為標準性——法律真實(傳統法律真實和現代法律真實);刑事證明標準的“量”,即為標準化——主觀法律真實和客觀法律真實及其層次化建構;刑事證明標準的“度”,即為現代化。
【關鍵詞】刑事證明;刑事證明標準;法律真實;層次化建構
一、證明標準之內涵的反思
關于證明標準涵義眾說紛紜,現擇其一二分析如下。有說證明標準是指“法律規定的運用證據證明待證事實所要求達到的程度的要求”;[1]有說其是指“承擔證明責任的人提供了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程度”;[2]還有說其是指“法律關于負有證明責任的訴訟主體運用證據證明爭議事實、論證訴訟主張所須達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3]上述關于證明標準的說法分別從不同側面強調了證明標準的部分本質內容,但也有其亟待完善之處。第一種說法沒有指明證明主體和證明達不到標準時應否承擔責任;第二種說法沒有指出證明主體和證明標準的法定性;第三說法將訴訟主體視為證明主體,有引人誤解之嫌。其實,證明標準既非程度,也非要求,它是刑訴證明必須達到的標尺和準則,是衡量證明結果的參照物,是卸除證明主體的證明責任的分界線。
筆者認為,證明標準是指法律規定的,關于負有證明責任的證明主體運用證據證明爭議事實,論證訴訟主張,在主觀和客觀兩方面所須達到的程度上的具體標尺和準則。如上所述,證明標準是尺度、參照物和分界線,然而其是否至善至美而沒有必要去探討呢?筆者認為不然,正因為其處在衡量證明結果、卸除證明責任等關鍵的尺度和分界線之位,更有在理論上對其進行探析的必要。故筆者試圖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量互變規律”,即質、量和度三個維度進一步探析證明標準。
二、證明標準的“質”:標準性——法律真實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一事物成為它自身并使它區別于他事物的一種內在規定性,即為質。即質和事物的存在是直接的同一。事物總是具有一定的質,喪失了自己的質,它就不再是自身而變成他物。”而刑訴證明標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是因為刑訴證明標準也有其自身存在的“質”。刑訴證明標準的“質”是什么呢?這需對其進行的定性的探析,實際上,就是筆者所提出的證明標準的標準性,即一切刑事案件所要達到和遵循的原則和定性的標準。
正如田口守一所言:“隨著近代合理主義的興起,開始通過人的理性發現事實真相。因此,形成了一項原則:認定事實必須依據證據,其他任何東西都不是認定事實的依據。”[4]在證明過程中,關于證據有“證據材料——證據事實——待證事實——法律事實”之說。其關系詳述如下:案件事實均不同程度地留下蛛絲馬跡,這些蛛絲馬跡便是司法機關獲取案件信息和查明案件真相的證據材料。這些證據材料在證明過程中通常在法庭調查階段經過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的整合,符合通說“三性——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的便被整合為“證據事實”。這些證據事實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明系統,證明案件待證事實的各要件或情節,并能排除各種合理解釋的差異和矛盾,同時能得出唯一合理的結論,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即證據事實通常在法庭辯論階段,在刑訴程序和證據規則的整合下,證明待證事實達到在法律上的意義,從而成為在法律上得以認定的事實,即法律上的事實或法律事實,而法律事實正是“訴訟中所呈現的并最終為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乃是經過證據法、程序法和實體法調整過的、重塑了的新事實”。[5]“案件判決只能以法律事實為依據,客觀事實具備唯一性,而法律事實則是不斷變化的,隨著證據及主審法官判斷的變化而變化”。[6]“法律事實實際上是強調了法律的作用,在一定程序上說,是法律程序自主產生的,即嚴格地按照法律程序的規定,將公民的各項訴訟權利落到實處,通過公民的參與所發現的事實”。[7]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在事實層面上具有基本內容的一致性,這是因為“在刑訴中,不存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客觀事實,所有的事實必須在進入刑事程序之中的證據的基礎上,并且依照法定程序推論出來,即在法律規定的機制和標準上得出關于事實的結論,也就是法律事實,而其應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8]“如果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價值觀念的表達的話,那就是讓價值在事實的認定中發揮作用,而這里的法律事實也就具有了一種‘合理的可接受性’”。[9]故在法律上衡量待證事實查明與否,論證主張成立與否和證明責任卸除與否的一種內在規定性——證明標準的“質”即證明標準的標準性,就是證明待證對象是否達到在法律上具有意義——法律真實。法律真實作為證明標準的標準性,是一種原則性標準、定性標準和從各具體證明標準中抽象出來的標準。
法律真實是指“在發現和認定案件事實過程中,必須尊重體現一定價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在對案件事實的認識達到法律要求的標準時,即可定罪量刑,否則,應當宣布被追訴人無罪”。[10]所以,法律上的真實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其可接受性“包含了和客觀事實相一致的極大可能性,也包含了通過程序而獲得的正當性,還包含了國家為平紛止爭所表現出來的強制性,并不是單純地發現案件的客觀真實性情況”。[11]它也有別于“實質性的、客觀存在的、本原性的、絕對意義上的真實和被法律剪裁,框定下來的范圍較為狹窄的真實”。[12]法律真實不同于事實真實,前者強調真實的本原性和法律性,后者強調的只是真實的本原性;法律真實不同于形式真實和實質真實,法律真實是真實的實質性和形式性的有機統一;法律真實也不同于絕對真實和相對真實,法律真實強調真實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有機統一;法律真實也不同于客觀真實和主觀真實,以上正是筆者從法律真實的起源和本質上對之進行的論證。
筆者從不同時代的法律規定的證明標準的特征出發,將法律真實分為原始的法律真實、傳統的法律真實和現代的法律真實,并將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傳統的法律真實和現代的法律真實的區別。
第一,產生的法律依據不同。前者依據封建制國家的法律,該法律是封建統治階級意識的體現,是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和保護封建特權和等級制度,鎮壓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廣大勞動人民成為訴訟客體;后者依據民主制國家法律,該法律是廣大勞動人民意志體現,維護其利益并使其成為訴訟主體。第二,性質不同。前者只追求證據事實反映的形式合法,以形式上的真實代替了實質上的真實;而后者是形式真實和實質真實的完善地有機統一,并統一于法律事實。第三,適用的目的和方法不同。前者從有罪推定出發,并把被告人的口供視為“證據之王”,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維護封建專制主義者的意志和利益;后者從無罪推定出發,重證據輕口供,是為了實現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雙重目標,尤其是保障無辜。第四,前者強調形式真實,忽視甚至排斥法官對認定案件事實與審查判斷以及運用證據方面的主觀能動性;而后者則不同,其吸取了傳統法律真實尤其是證明標準法定的形式上的法治精神的合理內核,舍棄了法官不得依法自由評斷和取舍的機械操作,同時,它給這一合理內核注入新的內涵和活力。現代法律真實將證明主體由法官擴展到公安司法機關和當事人;將法官的職權由機械地操作擴展到依法主觀能動地居中裁判;將證據由形式規定擴展到形式規定和內容規定的有機統一。一言以敝之,它強調了證明主體的結構合理性、法官職業的獨立性和法定內容的完備性和科學性。
三、證明標準的“量”:標準化——主觀法律真實和客觀法律真實及其層次性建構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量是事物的規模、發展速度和程度以及它的構成成份在空間上的排列結合等可用數量表示的規定性。量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直接同一的,相同質的事物可以有量的區別。認識事物的量是認識的深化,是把相同事物區別開來的依據。證明標準的“量”即標準化是認識證明標準的深化,是把證明標準的“質”即標準性——法律真實可用“量”即標準化加以區別建構,即證明標準的“質”即標準性——法律真實的構成成份一主觀法律真實和客觀法律真實在空間上的排列結合方面用數量表示的規定性。此處標準化是一個相對量化和宏觀上量化,而不是一個絕對量化和微觀量化,否則,充滿活力的法律真實便退為形式真實,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證明主體便成為機械識別法條形式的機器,似有回到傳統法律真實之嫌。
如前所述,證明具有主觀性和客觀性,證明過程是主觀思維活動和具體法律行為的有機統一的過程,證明標準是主觀和客觀兩方面所要達到的標尺和準則,則筆者認為,從邏輯上講,證明標準的“質”即標準性——法律真實也有主觀法律真實和客觀法律真實之分。主觀法律真實是指發現和決定案件事實的過程中,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證明主體在尊重體現一定價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時,對案件事實的主觀認識世界具有法律規定的意義,即法定的真實性,其能保證有關的人員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可以將主觀任意性降到最低限度。客觀法律真實是指在發現和認定案件事實過程中,必須尊重體現一定價值的刑事程序的要求時,認定案件事實的客觀依據具有法律規定的意義。
首先,主觀法律真實是人的意識、觀念外在化和法律化,即人的頭腦反映案件事實的精神活動以及心理活動的總和,包括意識活動的過程及其結果達到對案件事實真實性認定的法定標準。刑訴證明過程是人的主觀思維活動過程,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13]即若思維或認識能夠用來改變世界,則就具有真理性。其次,主觀思維活動結果是否具有真理性,看其在程序正義基礎上能否根據零碎的證據材料和系統的證據事實,將待證案件事實和訴訟主張整合為“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為造成的……它們是根據證據規則、法庭規則、判例匯編傳統……等等而構設出來的”法律事實。使待證事實上升為法律事實,主觀思維必須達到法律上有意義。最后,主觀思維活動具有規律性和價值性。對認識過程來說,存在著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辯證統一,并統一于社會實踐。主觀思維活動過程和抽象的、普遍的、分散的法律規范合成為一個具體的、有機的、系統的法律規范,由理性認識到感性認識的法律意識上的主觀思維活動過程統一于符合程序公正的刑訴證明實踐,因此主觀思維活動過程也就具備了主觀法律真實的價值意義。主觀真實往往“以主觀上認為其為真實為滿足,盡管人在確認實質真實的時候,其主觀狀態也表現為主觀上相信其為真實,但主觀真實往往不是指這種情況,而是認為世界乃人的感覺的組合,人只能就自己的感覺依據經驗進行判斷,當自己相信其為真實則確認其真實,至于是否與實際情況相符則因不可獲知而不必考慮”。[14]綜觀主觀真實與客觀法律真實的實質性、真理性、規律性和價值性可知,它們完全不同。
關于證明標準層次化建構的總體設想,一方面是主觀法律真實層次化建構。在司法實踐中,有些國家和國際性組織的法律文件對主觀法律真實標準具體落實到對“疑”作出明確的規定。聯合國關于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的法律文件就有如此規定。1984年批準的《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第4條規定:“只有在對被告的罪行根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而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的情況下,才能判處死刑。”[15]其“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是要求證明主體在主觀思維上達到絕對確信,或者排除一切合理懷疑。臺灣學者李學燈先生認為,排除合理懷疑“在英國法上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初期。開始要求如對被告定罪量刑,須有明白的根據。以后曾用各種不同的術語,用來表信念的程度。最后仍有疑字作標準,即所謂‘合理懷疑’,亦即須信其有罪至無合理之懷疑。到19世紀初期,流行一種典型的說法,就是由于良知的確信,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懷疑”。[16]但根據“疑”的程度不同即有‘量’,上的區別,故筆者認為,主觀法律真實應建構為“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排除合理懷疑,有確實證據的推定和證據不足而存疑”[17]四個層次。其中證據不足而存疑有其自身的豐富內容和確立的必要性。有罪與無罪之間的“疑罪”,在司法實踐中,確屬疑難雜癥,是司法人員尤其是法官感到棘手的問題,對“疑罪”的處理,法律已有明文規定,但現實中對法律明文規定也有作變通處理的。更有甚者以此為借口,徇私枉法,而法律上未有為主觀法律真實在“疑罪”上作出判斷而規定其參照標準,這在客觀上也為少數人枉法裁判打開綠燈。基于此,確有建立“證據不足而存疑”標準之必要。
另一方面是客觀法律真實層次化建構。與上述主觀法律真實層次化建構相適應,筆者認為,客觀法律真實應建構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案件主要事實清楚,主要證據確實充分;有確實證據推定事實清楚;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四個層次。關于層次化建構的具體內容及每一層次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刑事證明的“度”(即現代化)的論證,由于篇幅關系,在此不再詳細論述。筆者試圖強調,不論從哪一視角來建構層次化的證明標準,均不能采用純主觀或客觀標準,而要將二者結合考慮,否則難免給人以主觀定罪或客觀定罪之嫌,也難免給人以人文主義或物文主義之感,只有在主觀法律真實和客觀法律真實有機結合達到對應的標準,才真正達到法律真實之標準,正確適用法律,實現刑訴法的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之目的。
【注釋】
[1]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頁。
[2]樊崇義主編:《刑事證據法原理與適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頁。
[3]卞建林:《論刑事證明的相對性》,載陳光中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4](日)田口守一著:《刑事訴訟法》(中文版),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頁。
[5]江偉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6][7][8][9][10][11]何家弘主編:《新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頁,第214頁,第206頁,第208—209頁,第214頁。
[12]張建偉:《證據法學的理論基礎》,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編輯出版《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2年第8期,第14頁。
[13]姚莉主編:《刑事訴訟法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頁。
[14]轉引自齊樹潔、吳旭莉:《民事審判方式改革與證據制度的完善》,載陳光中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二卷,第590頁。
[15]陳光中、郭志嬡:《量刑公正與刑事訴訟制》,載陳光中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16]李學燈:《證據法比較研究》,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2年版,第665頁。轉引自樊崇義:《落觀真實管見》,《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
[17]第二、三層次的標準引自陳光中:《構建層次性的刑事證明標準》,載陳光中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七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